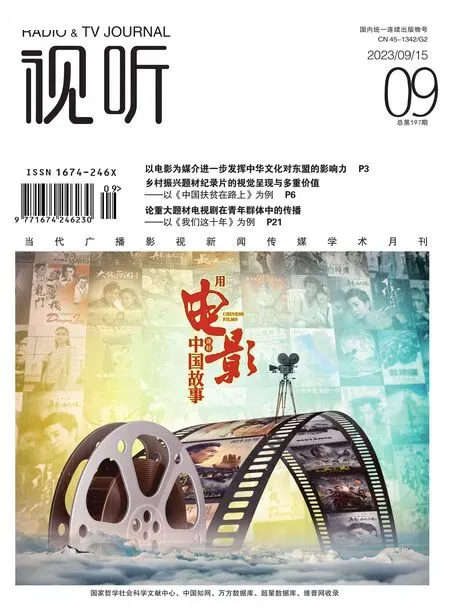筑·居·思:《張素英的“城堡”》之哲學解讀
◎李冬冬 蘇濤
《張素英的“城堡”》是獨立紀錄片人孟小為耗時一年多拍攝的一部作品,該片入圍第三屆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紀錄之光”展播單元。故事發生在甘肅省隴南市成縣一個偏僻的小山村,60 多歲的流浪者張素英花費四五年時間,在沒有圖紙、不用機械的情況下,從垃圾堆里淘來石塊和廢料,徒手建造了一座七八米高、形似“城堡”的房子。然而,就在大雪紛飛的年關,在“工程”即將竣工之際,張素英被送往當地的救助站,“城堡”則在轟鳴的機械聲中再次歸為瓦礫。
該片時長約90分鐘,采用倒敘的手法,自“城堡”被拆后尋找逃離救助站的張素英為始,以張素英離開棲身的磚瓦窯到“高處去”作終,中間穿插著春、秋、冬三季“城堡”的建造過程。從題材方面來說,沿用目前我國慣用的兩分法,可以將紀錄片分成“人文社會”和“歷史科教”兩大類①,很顯然《張素英的“城堡”》屬于前者。就表達模式而言,按照比爾·尼科爾斯的六分法,《張素英的“城堡”》屬于參與模式(participatory)與觀察模式(observational)二者的結合體。②該片全程用手機拍攝,部分鏡頭畫面抖動,兼有跳幀(注:主要指筆者觀看的成都場放映版)現象,幾處轉場也略顯生硬。其間除卻鳥鳴、汽笛、雪落等自然的環境音和間或夾雜的幾句人物對白外,并無任何旁白輔助理解,僅在片尾以字幕形式寥寥數語稍作點睛。
本文無意于臧否具體的表現手法和拍攝技巧,上述分析只是對該片作簡單且業余的介紹。一般情況下,若是處在文明時代,居無定所、行無定向、食無定取的人往往是社會與精神雙重意義上的流浪者③,這類人無法實現其自身的棲居狀態。筆者所好奇的是,若果真如此,張素英是否就注定無法完成其棲居呢?這樣一個離奇、怪誕,充滿著戲劇張力和沖突感的故事意在說明什么?身為一名流浪無著人員,張素英過著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生活,明明已經有了可以宿身的窯洞,卻為何要耗心費力地建造“城堡”?“城堡”被拆后,她又為何拒絕回到條件相對較好的救助站,而偏要舍近求遠“往高處去”?高處又是何處?在更深層次上,建筑與人究竟有著怎樣的關系?其奧義為何?
誠如瓦爾特·本雅明所言,意義產生于消費之中。本文著意借助馬丁·海德格爾的筑造(buan)與棲居(Wohnen)思想,從現代技術給人帶來的存在危機以及人類對自身棲居困境的理解這一更加形而上的主題出發,嘗試對《張素英的“城堡”》進行哲學解讀,以期在加深對這一思想理解的同時,循著先哲給予我們的現實指引,嘗試破解現代人的棲居困境。
一、何為筑造:作為物的生產與棲居本質的“城堡”
作為存在主義的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語言保存著存在的秘密,他堅信通過追溯語言的詞源,進而確定其本源的意義,就能夠揭示出事物的本質。其原因在于語言是存在的家,人對感性世界的領會,通過對象性活動所創造出來的對象性關系作為“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在語言中得到保存。④了解了這一大的前提之后,我們不妨沿著海德格爾一貫的邏輯論證進路,來探討何為筑造及其在《張素英的“城堡”》中的具體呈現。
對筑造本質的探尋,海德格爾回溯到古高地德語中。筑造即為“buan”,它意味著棲居,而棲居則表示持留、逗留。他指出,把筑造作為棲居的手段和途徑,從一般意義上來看有其正確性,但它在無意間將棲居的真正意義遺漏了,因為這種觀點未能將棲居經驗視為人的存在。而事實上,筑造乃是真正的棲居,棲居是終有一死者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⑤換言之,海德格爾從詞源的考據出發,得出筑造的本質在于“讓棲居”,人作為棲居者而存在,才使得筑造成為可能。這一結論看似難以理解,但倘若將其與笛卡爾以降流行的主客二元對立的哲學思維方式聯系起來,其中的精辟之見就可窺一斑。在此基礎上,海德格爾進一步將筑造拆解成作為保養的筑造(即拉丁語的colere,cultura)和作為建筑物之建立的筑造(即拉丁語的aedificare)⑥,前者指耕種田地和種植葡萄等,而后者則主要涉及房屋寺廟與道路橋梁等的建立。這二者均寓于真正的棲居之中。
本文將探討的對象限制在物的生產,也即作為建筑物之建立的筑造這個層面上。《張素英的“城堡”》前后一共涉及了四個作為物的生產的筑造,下文將隨鏡頭的移動逐一對其進行分析。影片一開場,一雙皸裂的手用樹枝在地上寫下“張素英”三個字,繼而鏡頭一轉便出現了瓦窯洞,這是主人公棲居的第一個筑造。這個磚瓦窯是村里廢棄不用的廠房,四五年前張素英來到村里后便居宿于此。毫無疑問,磚瓦窯是建立之物,盡管它并非張素英親手所建,但實實在在地傾注了她的心血——保養。張素英撿來一張折疊沙發當作床,將他人棄如敝履的衣服像展品一樣懸掛起來,架灶起鍋、生火做飯,在破舊的窯洞中給自己筑了一個棲居之所,抵風御雪。
紀錄片著墨最多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筑造就是張素英耗費五年之久卻最終并未建成的“城堡”。稱其為“城堡”僅就從其形似而言,并非指涉其功能,這點從片名中的雙引號便可得知。在瓦窯洞附近的空地上,張素英從垃圾堆里淘來空心磚、碎瓦片、鋼筋、鐵皮和木椽子,一塊一塊地背回,將其壘放整齊;然后從不遠處的河邊一桶一桶汲水,混合著泥巴和建筑速溶膠粉填補縫隙,使其牢固。就這樣,鏡頭由樹木蔥蘢轉到大雪紛飛,“城堡”也一厘米一厘米地增高。旁人質疑“城堡”不能住,張素英反問:“不能住嗎?”隨即又開始建造。2018 年臨近春節,一則關于流浪人員收容管理的制度出臺后,張素英被送往當地的救助站,“城堡”在鏟車的轟鳴聲中被夷為平地。盡管張素英并未在“城堡”內生活過哪怕一時半刻,但是在日復一日的勞作、一磚一瓦的搭建中,她已經實現了在“城堡”內的棲居。這是因為筑造不只是獲得棲居的手段和途徑,筑造本身就已經是一種棲居。⑦
張素英短暫停留而又旋即逃離的救助站是第三個作為生產的建筑物,但不是棲居之所。除此之外,片中另外一條隱而不彰的暗線構成了最后一個建立的筑造——張素英拒絕回去的湖北老家。如果說前兩個作為生產的建筑物可以被稱為“棲居之所”,后兩種充其量只能被稱為“容身之地”,這二者有著云泥之別。其原因在于對某個住宿地的占用并不等同于棲居,因為并不是每個住宿地都能實現讓棲居的本質。
從古高地德語中推演出的筑造的本質只是西方人的意會,由于文化區隔和語言轉譯的問題,這種意會無形中加大了我們理解的難度。姑且換一種更符合東方語境的說法——“此心安處是吾鄉”,鄉即是家,“家”是“心安之所”⑧,能稱為“家”的筑造,才能實現讓棲居的基本特征。如此一來,救助站和湖北老家從現實物質層面比破窯洞和“城堡”更能御寒,卻依然無法實現讓棲居的實質便不難理解了。這就從側面回應了海德格爾的質疑,居所本身并不能擔保棲居的必然發生。
二、何以棲居:終有一死者及其詩意存在
既然居所不是棲居實現的充要條件,那么筑造在何種意義上才能歸屬于棲居呢?“心安之所”是中國人的意會,倘若要言說清楚“棲居”的具體內涵,仍需再次回到海德格爾的邏輯,從詞源的角度追蹤“棲居”的本己之物,以便獲得更為恰切的理解。
對于棲居本質的探賾,海德格爾再次從詞源入手尋找答案。他在古薩克森語和哥特語中分別找到了同為“持留、逗留”含義的“wuon”和“wunian”,并根據哥特語中“wunian”一詞的含義得出結論:棲居,即被帶向和平,意味著始終處于自由(das Frye)之中,這種自由把一切都保護在其本質之中。棲居的基本特征就是這樣一種保護。⑨其中,對于“自由”二字的理解需要特別予以說明,它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不受任何限制和約束的絕對自由,而是指一種防止受到干擾和破壞的狀態。這樣說來或許有些抽象,既然海德格爾將筑造的本質歸結為讓棲居,在此我們不妨斗膽依樣畫瓢,借木心之說法將棲居的本質意會為“使我之為我”,這種語言的轉譯無疑會降低理解的難度。需要強調的是,這里所說的“使我之為我”中的“我”不僅僅指個人,甚至不是指所有人,而是指海德格爾所言的天、地、神、人“四方”(die Vier)。所謂人存在,就等同于人棲居。通過開展筑造活動,終有一死者將“四方”歸于一體,同時保護著四重整體的本己之物,使其免受干擾。
終有一死者也即人,作為筑造的建筑者和“四方”的保護者,保護的對象自然也包括他自身。在《張素英的“城堡”》中,本文主要探討棲居者對于其自身的保護。海德格爾強調,把終有一死者護送到死亡的本質中,這決不意味著把作為空洞之虛無的死亡設定為目標;它的意思也不是說,由于盲目地盯著終結而使棲居變得暗沉不堪。⑩回望張素英的種種行為,便不難發現這一說法的生動注腳。身為一名流浪無著人員,張素英卻總是穿戴整齊、發型利落;每次做活,她都會系上圍裙、戴著袖套。如果簡單地將上述行為歸結為“干凈愛美”,就不免失之淺表。為了支撐這一論斷,我們還可以從前述的筑造——破窯洞和“城堡”來展開論述。即便是在憑四壁以御寒、仰天光以照明的窯洞里,張素英并沒有混混度日、得過且過,而是精心裝飾棲身之所。與一般的農家院落注重實用性不同,張素英的房子頗具美感,外觀形似城堡,內里落錯有致。以上種種無不表現出張素英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美的追求,她并不因必死的本質而潦草過活。
如果說對于筑造的建立和保養還只能算作是流于表面的證據,那么張素英渴望自由、不為世俗羈絆的內里則更具有說服力。別人問是不是因為丈夫不愛她,所以才選擇流浪,張素英回答說:“愛呀,我不愛他。”有人開玩笑:“女人不能抽煙。”張素英叼著煙答道:“可我就是女的呀!”有人給她錢,她堅決不收;碰到對方硬塞,她接下后轉手就贈給村里其他的流浪漢。得知“城堡”被拆,張素英從救助站逃了出來,在廢墟前哭了好一段時間。后來,她用一個蛇皮袋子將所有行李背在身上,附近村民問她去哪兒,她答:“往高處去。”臨走前,她還不忘將剩余的米面糧油分給近鄰。張素英不追求物質上的豐饒,只期盼精神上的富足,用雙手給自己建造一座棲身之所,在“城堡”里守護著她的本己之物。這樣的人生態度,難怪有影評人評價她有“草芥一般的命運,貴族一般的精神”,稱她是“漂泊的圣徒、不語的‘阿希克’”。因此,從這個層面上而言,“城堡”確又名副其實。
該片最后的字幕一語道破迷津:“人活著,深遠的內在本質是靈魂的自由。”行文論證到這里,海德格爾的疑問也就有了明確的答案,居所本身并不能保證棲居(Wohnen)的必然發生。當救助站和湖北老家無法讓張素英保持作為棲居者的本己之物,無法實現靈魂的自由,無法使其“我之為我”時,也就意味著它們作為建立的建筑物不能實現讓棲居的本質,自然也就無法被稱為筑造,因而只能淪為“容身之地”而非“棲居之所”。
三、思考:存在與我
海德格爾在《筑·居·思》一文中曾開宗明義地指出,他并不是要發明建筑觀念,甚或給建筑活動制定規則?,而是要把筑造納入一切存在的范疇,借此來思考筑造和棲居的關系。說到底,筑造和棲居都是人的活動,是作為終有一死者的人在大地上、在天空下、在諸神面前的存在方式。對于筑造和棲居的思考,隱含著將人在空間中的實踐活動看作是一種由物理建構而至精神文化的營造和釋讀的升華過程。?一言以蔽之,海德格爾的終極之問就是思考人究竟應該如何存在的問題。談論這樣一個宏大而抽象的問題,如果僅僅從邏輯推導的角度進行純粹的思辨,往往極易玄之又玄,以致走向艱澀難解的地步;倘若將抽象的問題具體化,一不小心又會跌入庸俗主義的陷阱。
本文嘗試對《張素英的“城堡”》進行拆解,分析片中出現的瓦窯洞、“城堡”和救助站等多個建筑物與張素英及其棲居生活,來探討現代社會中人的棲居問題,這種做法并非筆者個人首創。海德格爾在探討這一問題時,就引入了“橋”這一實在之物以幫助理解。有學者稱,海德格爾之所以在建筑的諸多例子中選中了“橋”,其目的就在于用這個最實用、最帶工具性的例子來分析出筑造的棲居本質?,這樣才更有說服力。竊以為,既然海德格爾將人的存在方式稱為“棲居”,那么作為住房的建筑物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更能表明筑造的內在本質。事實上,海德格爾在其后論述筑造的本質時,所列舉的正是黑森林里農家院落的例子,而本文的思路正與其同出一轍。
反思“人詩意地棲居”不僅是一種闡釋學的意義,更是對人的居住現代性的思考。?我們身處在一個高速發展的時代,城市高樓林立、車水馬龍;廣大農村也在城鎮化的道路上加速馳騁,日新月異。然而,一個直觀的感受是:我們越來越焦慮,越來越不快樂。對此,我們不禁發問:棲居的真正困境是什么?是住房的匱乏,還是經濟的拮據,抑或是其他種種?海德格爾在關于筑造和棲居的思考中一針見血地挑明,真正的居住困境甚至比世界戰爭和毀滅事件更古老,也比地球上的人口增長和工人狀況更古老。我們不應一味地尋找棲居的本質,而是首先必須學會棲居。?
既然如此,人的詩意棲居何以實現呢?事實上,棲居無關乎人的住宅,而關乎人的靈魂所在和本真生存狀態。?作為終有一死者,人一旦將自己的存在遺忘,而代之以各種具體的活動,就把自己在大地上的居住逐漸變成人的存在的單純手段,把自己的家變成了越來越陌生的、有待于自己去操控和利用的對象,也就從此失去了家園和生活的目的?,自然也就無法實現自身的棲居狀態。換言之,當我們孜孜以謀利、汲汲以求名時,就會離棲居越來越遠。相反,像張素英那樣,盡管已經意識到作為終有一死者的本己之物——死亡的必然存在,但依然努力保持著“使我之為我”的本真,用雙手和勞動為自己筑造一座“心安之所”并宿身其中,就能將流離的靈魂導向返鄉之途,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
注釋:
①聶欣如.尼科爾斯紀錄片分類芻議[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01):102-109+179.
②[美]比爾·尼科爾斯.紀錄片導論[M].陳犀禾,劉宇清,鄭潔,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7:114.
③?胡瀟.詩性空間的思辨——海德格爾“筑·居·思”之思[J].天津社會科學,2016(03):22-27+77.
④胡立剛.論海德格爾“語言是存在的家”[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04):36-38.
⑤⑥⑦⑨⑩??[德]馬丁·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M].孫周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156,155,153,156,158,152,170.
⑧郭建斌,王亮.“家”作為一種傳播研究視角——基于“獨鄉”20 年田野資料的討論[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1(11):49-68+127.
??鄧曉芒.西方哲學探賾——鄧曉芒自選集[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341,332.
?熊攀.“人詩意地棲居”何以可能?[J].美與時代(下),2019(08):29-31.
?韋拴喜,楊恩寰.海德格爾的詩性救贖及其理論局限性試析——兼談詩意地棲居何以可能[J].蘭州學刊,2011(07):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