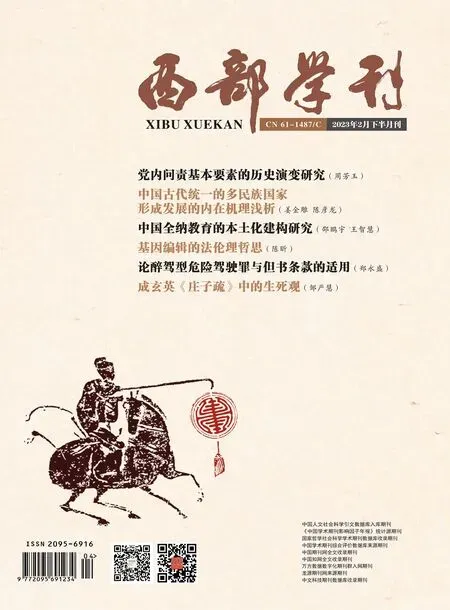日本社區理論與文化嬗變研究
曾 翔
一、關于“社區”概念的起源
“社區”這一概念最早發源于德國,德國古典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在1887年出版的社會學著作《共同體與社會》(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首次提出了“共同體”概念,他寫道,
“共同的風俗和共同的信仰,它們滲透在一族人民的成員之中,對其生活的統一與和平至關重要,雖然絕不是可靠的保障,但是共同的風俗和共同的信仰在一族人民當中或者由他們出發,以日益增長的強度,風靡于一個部落的各支脈世系”。[1]
他認為“共同體”是一種逐漸旺盛充滿生機活力的有機體,在這樣一種有機體中,通過依靠共同的信仰、道德與文化,賦予人與人之間親密的人際關系,共同的精神意識以及對有機體的認同感與歸屬感,而這正是現代意義上“社區”存在的內在屬性。但由于滕尼斯所處的時代是介于鄉村社會與工業社會的轉型過渡期,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以及個人經歷的局限,他筆下的“共同體”更多側重于鄉村共同體,描寫的是基于血緣與地緣的“小共同體”;同時,由于工業社會的迅猛發展,傳統的鄉村社會面臨解體,當時對于社會學的研究范式也只是簡單地將社會分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兩種形態進行敘事研究,并未以地域性的視角來整體看待社會的發展與變遷,現代意義上的“社區”還未真正出現[2]。
時間來到20世紀初,隨著城市化運動的興起,美國社會也經歷著由熟人的鄉村社會到陌生人的城市社會轉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分工帶來了諸如人口流動、分散居住等新特點,但這也由此導致諸如鄰里關系的冷漠、親情友愛的缺失,城市中的人們陷入了精神生活的真空之中,人們迫切地需要人文主義的精神關懷,由此傳統的“共同體”理論早已不適用于現代化的都市社會。以美國社會學家R.E.帕克(ROBERT EZRA PARK)為領軍人物的芝加哥學派,將“社區”理念引入城市發展中,并以地域性的視角研究地域社會的變遷及其發展。他認為一定地域下的人們對于生存的土地有著不同尋常的聯系,若是將他們按照地域進行組織,就能夠使他們重新處于充滿關懷、人情味的熟人社會當中[3]。同時,帕克還認為正是城市化的過度發展才使得不健康的非人際關系替代了和諧穩定的人際交流[4]。因此,他重新審視地域內人的地域性,并賦予“共同體”以新的“社區”含義,推動社會學關于區域社區方面的研究新范式,由此產生了現代意義上的“社區”概念。
二、關于日本的“社區”理論
日本關于現代意義上的“社區”研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在此之前日本主要開展以農村為中心的地域社會學研究。二戰以前的日本農村社會主要是以地主制度為社會體制的核心,此時的地域社會學研究也主要是以農村社會中的地主制度作為主要研究領域。日本出現現代意義上的“社區”概念則是處于與美國相類似的都市化發展進程中。二戰結束初期,日本通過政治經濟的民主化改革以及美對日特需(如朝鮮戰爭時期的特需采購),日本逐步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日本也逐漸開始實施以東京為核心的大都市圈城市化進程。同時,伴隨著日本經濟進入高度成長期,日本的城市化進程也顯著加快,但由此也帶來了農村的解體,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導致農村出現大量的過低人口村落(日本稱為過疏地區)。相對地在那些人口激增的地區(日本稱為過密地區)由于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導致城市的生活環境急劇惡化,社會資源出現嚴重不足,社會功能減弱,城市人的生活質量嚴重下降,社會關系不和諧導致的鄰里糾紛也時常發生。于是在昭和44年(1969年),日本國民生活審議會和東京都社會福祉協議會相繼發布并出版了『コミュニティ―生活の場における人間性の回復―』、『東京都におけるコミュニティ·ケアの進展について』(筆者譯:《恢復社區內的人際關系》《關于東京的社區護理進展》),旨在研究在社區內生活的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系、社區內的居住環境以及社區之間的人口流動,由此日本掀開了關于“社區”的社會學研究的大幕[5]。同時在這一時期,日本對于傳統的農村社會學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觀點。例如,日本民俗社會學家宮本常一就曾指出:“隨著都市化進程的不斷發展,而由此導致的農村崩潰其實并不用特別擔憂,農村并未崩潰,只是從事第一產業的農村人口常規化轉移至第二、第三產業,從而導致第二、三產業人口的激增,但這種過疏與過密其實只是一種暫時現象,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都市工作的農村人口會再度回流,上述出現的城鄉現象也只是反映了農村的外部變化。”[6]宮本認為研究農村自身的農村文化以及由文化導致的農村遷移才更應該受到關注。這其實也符合之后日本“社區”研究的主流——“社區文化”。
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裂,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狀態,同時由于城市與農村產業構造分布的不平衡,城鄉經濟依舊是在“不平等交換”機制下維持和發展,“城市—農村”的對立關系依舊十分嚴峻[7]154。城鄉區域社區間的人口稀疏問題仍未得到解決,且愈發嚴峻。以三大都市圈為核心的城市社區由于經濟發達,對周邊農村人口產生虹吸效應,城市人口進一步激增,都市社區中以町內會和自治會為代表的住民組織會員人數居高不下,與此相對的農村社區卻面臨著由人口持續流失帶來的集落解體。城鄉之間大量的人口流動使得日本民眾不得不思考個體在社區中如何尋找歸屬感以及如何掙脫以“擴張和增長”為導向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束縛,找尋充實幸福的人生意義。由此,日本的“社區理論”研究學者將視野轉向“創造性社區”理論,即“創造性社區”能夠創造并維護一個包含自然、物理、歷史、社會以及文化內容的“環境”,通過橫向與縱向合作,居住民能發揮個人的潛力來追求充實且幸福生活的代際交流式社區;同時該社區下的居住民能夠充分調動社區資源,實現以互助為導向的社區共同體[8]。
當時間來到21世紀20年代,日本老齡化以及少子化等問題的日益嚴峻,階級固化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也籠罩著日本社區。社區內出現了類似人員短缺,社區治理成本劇增等諸多問題,社區的維持與發展也出現了巨大的危機。日本學者廣井良典提出了“社區經濟”理論,即通過政府引導,加強對報酬比例的養老金征稅,將稅收用于支援年輕人在地方的就業和生活,強化社區區域內人力、物力以及財力的正循環,加強社區內部的經濟聯系,繼而使人們轉向各地社區的特點以及風土文化多樣性的探索,從而激活社區內部的活力[7]142-149。該理論有效應對了在“后增長時代”下日本社區內部活力喪失的問題,保證了日本城鄉社區健康穩定的發展。
三、關于日本的“社區文化”
關于社區文化的研究可以說是社區研究的重中之重,從社區理論的研究轉向社區文化的研究,有助于豐富社區研究的內涵,從實際的社區治理以及社區規范等具體實例,探討日本社區文化營造的相關經驗,從而為中國的社區文化營造提供借鑒。中日兩國在社區發展上有著許多相同之處,關于社區以及社區文化的定義也是有著許多相似之處。中國學者認為社區是社會的基本單元,社區文化便是社會整體文化的基本單元;社區是社群、制度習俗在一定地域內的集合與社會生活的共同體,社區包括城鄉社區和商業街區等功能性社區,而相對應的社區文化便是不同社區依托各自特點構成的文化系統[9]。同時國內學者還將社區文化分為廣義的社區文化與狹義的社區文化兩種,廣義的社區文化指的是一定地域下的社區居住民經過長期的實踐所創造出的物質與精神文化的總和;而狹義的社區文化是指特定區域下的社區居民經過長期實踐形成和發展出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行為模式與群體意識等一系列的文化現象的集合[10]。那么日本的社區文化同樣依循上述原則,同樣是由地域下的居住民經過長期的歷史實踐所凝結的住民文化。日本的社區文化也即住民文化,住民文化主要是由基層住民組織主導的社區治理、町內住民長期實踐所形成的價值規范、町內住民的文化生活等三項基本內容構成。
(一)住民組織主導下的社區治理
說到日本的社區治理,就必須提及日本的住民組織,簡單來說就是日本民間的自治組織,這是日本社區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住民組織經歷了四個不同的歷史階段:第一階段即在古代日本到明治前期是以“上行下效”的行政末端機構而存在,以“五保”“五人組”“組”“講”等村落共同體的形式發揮著行政事務輔助職能,承擔著村落內的治安、納稅、維持村內秩序等職能;而到了第二階段即明治后期到昭和前期,以町內會為代表的日本住民組織又作為民主化媒介的角色發揮著獨立自主的主體治理功能。例如,在明治5年(即1872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近代的學校教育制度,并在日本全國建造小學,推行小學教育。在當時諸如建造校舍、教師人事、財政以及為低保家庭提供入學援助等事務,在當時則皆由町內會以及它的聯合會承擔[11]。用現在的視角來看,這些行政化事務本應納入到自治體的行政管理之下,但在當時卻由住民組織承擔,這可以說是現代日本社區自治的原型;到了第三個階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住民組織在法西斯政權的操縱下,成為了維持戰爭機器運轉的統治工具,町內會隨之成為大政翼贊會的行政末端組織,同時日本為了穩定國內的軍事獨裁統治,甚至成立了以“鄰組”為代表的基層組織。這一時期,因戰爭導致的經濟動蕩加劇了日本民眾的生活負擔,日本國內的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在法西斯暴政統治下的民眾根本無暇顧及町內的社區事務,以民主自治為特點的住民組織徹底喪失了獨立自主的治理主體地位,社區文化以住民組織的徹底轉向而喪失了發展的活力。但隨著二戰的結束,朝鮮戰爭的爆發,日本依靠美國的扶持以及政治經濟的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日本逐漸走出了由戰爭所帶來的經濟停滯,日本民眾的生活水平也大幅提升,日本民眾對于參與社區事務的熱情也逐漸高漲,積極參與社區事務成為日本民眾的普遍共識,日本的住民組織也發展到了第四階段。1999年,日本政府實施地方分權法,將地方政府的權力下放到基層住民組織,從而實現日本民眾所期望的基層自治,這一時期的社區治理已經從過去的主導型治理轉變為混合型治理[12]。日本住民組織也再次成為了民主自治的治理主體。
(二)以“互助”“忠誠”為原則的鄰里規范
正如前文所述,日本地域社區的概念出現在推行都市化的近代。在現代社區之前,日本地方是以鄉村集落的形態存續,延綿至今,雖受到城鄉經濟失衡、人口流動等因素的沖擊,但在現代日本還是存在著相當數量的農村集落,這些村落仍然發揮著以“互助”為核心的鄰里規范。在古代日本,由于勞動力短缺、生產技術落后所帶來的生產力低下,村內居住民為了維持日常生活的正常運轉以及村內治理成本的節約,鄰里之間便逐漸形成互幫互助的鄰里規范。在這樣的規范之下,青壯勞動力作為生產生活中的主要力量,在農耕以及房屋修繕等方面發揮主要作用,婦女兒童以及老年人則從事以手工業為主的輕體力勞動,鄰里互助便很好地解決了上述問題。不管是過去的“五保”“五人組”“組”“講”等村落共同體,還是現在的町內會、自治會等現代住民組織,它們始終秉持著“互助”的傳統,在鄰里關系調節、節約社區治理成本、凝聚團結友愛的鄰里氛圍發揮著巨大作用。
美國學者傅高義曾經在其著作《新中產階級》一書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忠誠就是人們將集體利益置于自己的個人利益之上。群體忠誠不僅僅意味著對群體目標的認同,還意味著樂于與其他成員合作,熱切地與群體保持一致。如果群體賦予了他一項任務,就必須承擔這份責任。人們必須在任何狀況下都避免讓其它成員感到尷尬,要在意其他成員的利益,讓他們在群體中如魚得水,感受到集體帶來的榮譽感。”[13]125
這段表述很好地闡釋了日本人從古至今的忠誠觀。對于忠誠,日本人不僅僅體現在過去的忠君愛國思想中,更在其日常生活的社區規范中。“忠誠”這一鄰里規范源自于日本人的傳統價值觀,從忠于天皇、忠于國家、再到忠于自己生活的社區,忠誠始終是日本人不變的價值規范,但忠誠的范圍卻在不斷變化。美國學者傅高義曾經以日本社區M町作為研究對象,他認為雖然戰后自由民主的理念早已深入日本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但由于科層制度的影響,大部分日本人還是認為沒有什么原則比為自己所屬的親密群體成員著想更為重要。因此,日本民眾普遍忠誠于自己所屬的社區,通過社區內的人情往來,加強內部聯系,達成相互信任的基礎,“忠誠”也自然成為日本社區內部鄰里規范的核心[13]126-130。
(三)町內住民的文化生活
日本社區通過如町內會以及自治會等住民組織引導居住民舉辦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如夏季舉辦的納涼會,社區中的男女老少伴著弦樂、太鼓聲,唱唱跳跳歡聚一堂。還有各地社區舉行的神社祭祀活動,各社區負責人召集住民組織的負責人商討儀式活動內容以及舉行要項,婦女兒童利用空閑時間準備活動物質,包括聚會人員的飯菜、活動布置等事務;男人則在活動當天抬著“神輿”繞著社區游行,祈求社區平安無事。這些文化活動對于豐富町內居民的日常生活,增強居住民間的日常交流,建立一個友愛團結的美好社區發揮了巨大作用。同時,日本政府還在各社區修建了諸多公民館以及社區中心(兩者區別見下表),通過開設各種學級的學習講座,為社區內的兒童提供各式教育服務;協助社區內的各類自治組織、團體提供活動場所,滿足社區內居住民的日常學習以及文娛活動;接受上級自治體的領導,宣傳政府政策,起到一定行政宣傳的功效;在突發災難等緊急情況時,充當臨時避難場所,提供災難應急的功能。通過自治體管轄下的公民館以及社區中心,日本社區為社區內的居住民提供了充實的文娛服務,各社區的住民組織也廣泛參與町內事務,讓社區居住民能夠在忙碌的工作后享受到幸福和諧的社區生活。

公民館社區中心設置主體教育委員會首長部局運營主體教育委員會自治組織等團體(也可以由其他地區的法人以及NPO等團體進行運營)職員來源教育委員會以及相關管理團體的成員一般沒有配置轉任職員,特殊情況下由首長部局職員擔任職員等人員的研修培訓教育委員會負責教育委員會以及首長部局共同負責主要工作內容針對各年紀學生講座的開設社會教育團體的培育支援自治公民館以及相關合作發行廣報對各種類型的自治團體的培訓開設提升職員素養的相關研修避難所的相關運營為居住民以及各類團體提供場館等與“地域再生”有關活動的舉辦針對各年紀學生講座的開設發行廣報對各種類型的自治團體的培訓開設提升職員素養的相關研修避難所的相關運營為居住民以及各類團體提供場館提供市的窗口業務等預算來源市町村教育委員會由市提供管理委托費(相關派遣職員的工資則由首長部局相關預算提供)禁止事項政治政黨、宗教活動以及營利活動(公民館認為必要的相關政治的學習活動除外)根據市條例以及社區條例明令禁止的行為
結語
“社區”概念初起于滕尼斯,興盛于以帕克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經過漫長的研究歷程,逐漸凝練出現代意義上的“社區”研究。二戰后,日本社會學界繼承了現代意義的社區研究,從鄉村地主制轉向地域社區研究,研究出了多種適應時代發展變化的社區理論,從“福利社區”到“創造性社區”,再到“社區經濟”,日本學界關于社區理論的研究重點始終致力于激活社區活力、創造社區內和諧穩定的人際關系,在發展迅猛的“陌生人社會”,賦予個體在社區內的歸屬感以及幸福感。同時日本積極構建獨屬于日本的社區文化,通過以基層自治組織為引導,社區規范中的“互助”“忠誠”為原則,居民文化活動為紐帶,團結町內居民,社區在日本社會中發揮出獨特的魅力。最后,中日兩國在社區營造方面有著許多共通之處,通過研究日本地域社區,闡明日本社區在社區治理、社區規范以及社區文化活動所發揮的作用,有助于為中國在社區營造上提供參考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