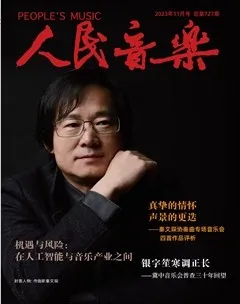創造我們這一代的新國樂
在音樂創作風格愈加多樣與個性化、人們的審美趣味也日益多元化的今天, 什么樣的民樂作品會更加引人傾聽?“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推出的上海音樂學院“民樂新作專場音樂會”或許會為我們帶來不一樣的答案。
自2012 年始,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便以“春天的律動”為題,在“上海之春”中亮相。短短十余年,“春天的律動” 已經成為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一年一度的品牌活動。2023 年4 月3 日,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指揮家吳強攜民樂系師生又為我們獻上了一臺精彩紛呈的民樂新作音樂會。本次音樂會共包含有五部室內樂作品、四部民族管弦樂作品和一部古箏獨奏作品, 上演作品均為近年來的民樂新作,充分體現了民樂系雄厚的師資力量及其在民族室內樂和民族管弦樂上的教學成果。
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作為中國民族器樂教育的重鎮,自建系以來便確立了“演、創、研”三位一體的學科綜合發展路線, 創作與演奏形成協調發展、相互成就的格局。因此,在近七十年的發展歷程中,民樂系不僅培養了大量優秀的民樂演奏家,還創作了一批經典的民樂作品,其中由胡登跳首創的“絲弦五重奏”更是正式拉開了現代民族室內樂發展的帷幕,為現代民樂創作的發展鋪下了一方厚重的基石。
本場音樂會中的民樂新作,一方面契合了大眾對民族音樂的審美趣味,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人們對民樂新發展、新動態、新樣式的接受能力,因此引起各界的熱烈反響。
一
音樂會的上半場共演出了五部民族室內樂新作和一首古箏獨奏新作品。20 世紀60 年代,胡登跳先生在民間器樂合奏的基礎上,吸收西方室內樂創作的特色和思維,創建了“絲弦五重奏”這一體裁,正式開啟了現代民族室內樂探索的歷史進程。與民族管弦樂隊相比,民族室內樂有著排演靈活、貼合民樂演奏性能等優點,因此一直是民樂作曲家們首要關注的創作體裁之一。本次音樂會上演的五部民族室內樂作品從不同的角度,展現了當代中國作曲家對于民族音樂語言以及現代民樂可能性的多元探索。
首先登場的是由強巍昊作曲的笛子重奏《》(Sè)。這部作品首演于2019 年上海音樂學院創新團隊民族室內樂作品音樂會。作曲家以意會竹笛音色的四疊字以及由四支竹笛構建的四條旋律,勾勒了“竹”這一具有豐富文人意象、具有符號意義、充滿生命力的藝術對象。在古人看來,破土而出的翠竹既是春回大地的象征,更是君子剛正人格的反映。細聽樂曲,旋律中對竹笛“實音”和“氣音”的交錯運用較為全面地發掘了樂器的表現力,其中柱式音響和民間競奏效果的并存更是增添了作品的張力與戲劇性。四名笛子演奏家王俊侃、屠化冰、朱晛、吳非以他們精湛的技巧,將樂曲中充滿律動、頗具抽象氣息但又不乏中國音樂韻味的旋律,以細膩獨到的氣息控制技術和圓潤精致的音色呈現在人們的耳畔,余音繞梁,久久難忘。音樂美學家漢斯立克曾說,作曲家創造音樂是為了永恒,而演奏家只是為了滿溢的頃刻。四位演奏家的精彩演繹似乎完美詮釋了這句富有詩意的美學見解。此外,《》中還有不少具有音響效果的高難技法,可以視為是對樂器表現力的大膽嘗試, 同時也展示了演奏家的高超技術。他們對樂曲的出色演繹,仿佛為我們繪制出一幅春意盎然的翠竹圖。
20 世紀90 年代, 追新獵奇曾是民樂創作的風尚。而王建民教授卻始終強調音樂創作應該追求可聽性和創新性的統一,并在這一觀念的主導下創作出了諸如《蓮花謠》等既彰顯新穎創作技巧,又具有極高可聽性的民樂作品。本場音樂會上演的三部原創民族室內樂作品———《龍耀》《茶馬》以及《錦繡》便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這樣的特點。
以民樂創作享譽樂壇的王建民先生并非民樂創作的“新人”,但他的“新作”《龍耀》卻頗具“新意”。《龍耀》受新加坡華樂室內樂團體鼎藝團委約而作,整部作品采用中國民間音樂多段連綴的曲體結構,其結尾的再現段落,又使作品帶有三部性曲式結構的意味。《龍耀》在編制上包含柳琴、揚琴、琵琶、古箏和打擊樂六個聲部,以琵琶開篇,盡管是弱力度的演奏與寧靜的表情,但縱使坐在觀眾席的最后一排,琵琶的泛音也清晰可辨。一個直觀的聽覺印象是,旋律的發展由簡入繁,層次分明,章法有序。以上行三度和級進下行構建的波浪式主題猶如在獅城日出時詠唱小調的一位少女,五聲調式的突出則仿佛是建構了這位“少女”作為華人的文化身份,其中琵琶音色的運用更使這個主題在初現之時充滿了“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含羞之色。在音樂進行過程中,這個極具少女色彩的主題多次變形,構建了主題的多重敘事和雙重抒情———該主題似乎就是成長并發展于獅城的“鼎藝團”的寫照。在《龍耀》的音樂空間里,主題與它的各個“變形”共同講述了“鼎藝團” 從誕生到如今蓬勃發展的艱難進程———它將華人世界的民族室內樂帶到了新加坡,并借由新加坡這一頗具世界主義色彩的飛地空間,將華人的抒情聲音散播到世界各地。透過《龍耀》,筆者似乎看見華人群體在20 世紀只身“下南洋” 以謀生計,而后在南洋地區開疆辟土、落地生根的史詩歷程。這樣的音樂想象當然是來自主題的多重敘事,這一手法構建了作品“以小見大”的文化價值和藝術特質。在“敘事”的同時,主題的疊進變形有如作曲家不斷高漲的情緒,抒發了作曲家和演奏者對于“華樂”的崇高敬意。
如前所述,《龍耀》的曲體結構更符合混合曲式的特征,將中西曲式進行融合,也正是民族器樂創作的趨勢。通常,當段落過多時,多段連綴與自由拼接的手法可能會使得作品結構松散,但《龍耀》采用主題動機貫穿式的手法又使得樂曲獲得內在的凝聚力,讓作品形成了內在與外在、宏觀與微觀層面的辯證統一。
值得指出的是,《龍耀》不僅旋律優美,配器上亦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首先,就宏觀布局而言,不同的樂器組合除了制造出意想不到的音色,同時也與曲式的結構緊密相連。例如,作品的首部,琵琶在低音區呈示主題; 中部是柳琴與古箏呈示主題,增加了旋律的厚度;最后的再現部,又以柳琴、揚琴和鋁板琴疊奏的方式對主題進行升華。其次,局部段落不同的樂器組合制造出特殊的音響音色。譬如,引子部分揚琴采用拍弦的技法, 鋁板琴用弓子拉奏,它們營造出神秘空靈的音響效果。再次,微觀層面上,作曲家還兼顧了每件樂器的個性:古箏總是不失時機地用大幅刮奏為高潮推波助瀾,中部的快板彈撥樂器交相輝映、各顯其能。由此形成了作品整體與局部的辯證統一,又充分彰顯了樂曲的重奏性,而非僅是旋律配伴奏的簡單形式。
《茶馬》是青年作曲家李博禪于2016 年創作的作品,作曲家以室內樂的形式,描繪了古代茶馬古道的音樂景觀。盡管作品包含二胡、竹笛、笙、大阮等九件樂器,但在作曲家的有機編排之下,九個聲部之間仍然形成了錯落有致的呼應關系,其中打擊樂器的使用更是出其不意地增強了室內樂的聲響效果,挖掘了民族室內樂“交響化”的潛能。品味《茶馬》, 似乎可以體會到作曲家以茶馬古道禮贊民族融合的人文情懷。
與《茶馬》相比,蘇瀟以“絲弦五重奏”為體裁創作的《錦繡》則在音響開發上顯得相對謹慎。作為王建民的學生, 蘇瀟在這部作品中一方面延續當年胡登跳先生在創制這一形式時確立的創作特點, 一方面也承繼了王建民先生對于民族色彩的重視。在《錦繡》一曲中,民歌《繡荷包》的音調時常若隱若現地出現在作品的不同層次, 彰顯了作曲家對于民間音樂的發掘和應用。在聲部關系上,《錦繡》在強調各個聲部之獨立性的同時,更加追求突出各聲部互相追逐、加花的特色。與其將《錦繡》視為是一部民族室內樂,倒不如將其定位為一部有意效仿甚至還原民間合奏樂特色的現代民樂重奏作品。《錦繡》以及與之性質相近的一些民樂作品, 為我們展現了當代作曲家對于民族室內樂這一體裁的“傳統化”詮釋。
在上半場的五部民族室內樂作品中,由付玄編配的古琴與胡琴室內樂《廣陵散》是唯一一部直接改編自傳統樂曲的室內樂作品。整部作品由一張古琴和一個以多把胡琴構成的“伴奏組”共同演奏。琴曲《廣陵散》以其長大的篇幅、多變的節奏和速度,生動地勾勒出歷史上“聶政刺韓王”的悲壯情景。陸笑姿的演繹細膩纖巧,在她的琴縵之間,我們聽到的似乎不僅是隱含“殺伐”的金石之聲,更是聶政在刺殺韓王時復雜的心理活動。
除此之外,上半場的音樂會中還上演了鄧翊群近年的古箏新作《晚晴》。作為身兼作曲家和演奏家雙重身份的古箏新秀,鄧翊群在近年來推出了多部具有極高質量的新作。2012 年,他以一曲《定風波》嶄露頭角,其別具一格的作曲天賦開始為箏界所發掘。《定風波》大氣的旋律、豐富的技巧展現,在眾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隨后數年里成為古箏專業學生考學、參賽的必彈之作。此次推出的《晚晴》,在音樂上似乎和《定風波》有著諸多相似之處,但又在很多方面上有所突破。
《晚晴》描繪了盛夏的海島在快雨時晴的氣候特點下,白沙、椰林、碧浪、晚霞之間形成變化萬千、交相輝映的無限美景。同樣的取裁自古典文學作品的意象,與蘇軾《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詩所不同的是,《晚晴》表現的是李商隱在擺脫往日厄運時倍感幸遇的寬慰。詩中有言:“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晚晴固然短暫,但足以讓人流連忘返。
二
百年前,鄭覲文以“大同樂會”的國樂實踐開啟了中國民族管弦樂的探索歷程, 百年后的今天,中國的作曲家繼續以“一手伸向民間,雙眼望向世界”的姿態,薪火相傳地為民族管弦樂的發展譜寫新的篇章。音樂會下半場的四部民族管弦樂作品:徐孟東的《廣板》、賈達群的《隨想曲·梨園竹調》、王丹紅的《狂想曲》和張千一的《大河之北》,不僅彰顯了當代作曲家對于傳統的繼承,同時也突出了他們對于現代樂潮的呼應。
首先登臺亮相的是徐孟東于2015 年應中央民族樂團委約而作的《廣板》。作品以京劇音調的核心動機發展而成,從曲體結構到音高組織、樂隊編配、音樂發展均體現出鮮明而濃郁的民族風格。值得一提的是,擔任京胡領奏的霍永剛先生在當日的演奏中很好地把握了京劇的音樂風格,極具穿透力的京胡樂聲,猶如整部作品的“龍睛”,為音樂增添了頗為亮眼的戲劇性光彩。
其后登場的《隨想曲·梨園竹調》,在樂隊的聲響效果上彰顯了賈達群對于音色之“融”的特質的追求,流露出他早年通過學習繪畫所習得的“色彩感知能力”。在這部編制十分龐大、聲響效果極其豐滿的大型民族管弦樂中,作曲家呈現給觀眾的是一幅多元化的民間畫作,其中既有戲曲聲腔的百轉柔情,亦有西北鑼鼓樂的鏗鏘有力,以色彩斑斕的交響之聲表現了對古代梨園樂人的豐富想象,整部作品讓我們看到了賈達群建構在“音樂詩學”之上、對于“人文境界”的孜孜追尋。
如何在音樂創作中有效地運用民間音樂,使音樂在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同時, 彰顯中國的當代風格,并在此基礎上將其轉換為一種具有現代性意味的世界性話語,是當今民樂作曲家尤其需要關注和思考的問題。在本次音樂會上,張千一以他創作的《大河之北》創造性地回答了這一問題。《大河之北》是張千一涉足大部頭民族管弦交響曲的濫觴。整部作品由《士———燕趙悲歌》《趙州橋隨想》《回娘家》《大平原》《梆腔梆韻》《避暑山莊———普陀宗乘》《關里關外塞外》七個樂章組成,本次音樂會僅對其中的第二樂章《趙州橋隨想》和第六樂章《避暑山莊———普陀宗乘》進行展演,筆者尤為欣賞第二樂章《趙州橋隨想》。在這一樂章中,作曲家將與趙州橋內容相關的兩首河北民歌《小放牛》和《四六句》作為兩個主題并進行創新運用,通過ABCBA 的拱形曲式結構形象地表現“橋”,以抒情委婉和幽默詼諧相對比的音樂情緒,展現了一幅生動樸實的生活畫面。第六樂章《避暑山莊———普陀宗乘》中藏族音樂“囊瑪”元素的運用,使整部作品突出了多元音樂并融的特色。當晚的演出中,二胡演奏家汝藝的精彩表演, 淋漓盡致地刻畫了作品中河北人的爽朗氣質,最后的炫技樂段更是充分展現了二胡這件樂器對于復雜段落的極強表現力。
除了上述幾部綜合運用各類民間音樂素材的民族管弦作品外,當晚的音樂會還為我們呈現了一部極具“流行風格”的管弦樂作品———《狂想曲》。作品系王丹紅在2011 年完成的交響樂隊伴奏形式版本基礎上,于2014 年改編為民族管弦樂隊伴奏。盡管十年過去,這部作品似乎稱不上是一部“新作”,但它給聽眾帶來的感受卻依然是新鮮而令人激動的。作品借用西方“狂想曲”的體裁結構,以融合爵士音調的方式,開拓了揚琴演奏的新語言,為揚琴音樂創作注入了新的血液。在吳強教授的指揮下,樂隊的力度變化強弱得當,頗帶炫技性的揚琴與樂隊相得益彰,營造一個絢麗多彩的音樂空間。
三
此次“民樂新作專場音樂會”已在觀眾的掌聲中落下帷幕,但那些極具質感和魅力的聲音注定不會從此消失于音樂的夜空。行文至此,筆者思緒再次回到本文開篇的自問:今天,什么樣的民樂作品更為引人傾聽? 甚至,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什么樣的民樂作品才有可能“經典詠流傳”?
中國的民族音樂創作早已走過了百年前的稚嫩,歷經不斷求索的成長期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可謂迎來成熟期的輝煌。但在倡導文化自信、講好中國故事的今天,置身音樂藝術全球化、放眼國際舞臺,民族音樂創作之路應該如何繼往開來?
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民族音樂家劉天華就開啟了改進國樂、創造新國樂的民族音樂發展道路,他在近百年前的熱切呼吁至今令人共鳴:“從創造方面去求進步,表現我們這一代的藝術。”
“從創造方面去求進步”,這不僅是五四時期新國樂創作寥若晨星之際的無奈與渴盼,同樣也是百年后民族音樂創作獲得極大發展后依然不可忘記的真知灼見。沒有新的創造,就沒有民族音樂的發展與進步,“表現我們這一代的藝術”就無從談起。及至20 世紀40 年代,對創造新國樂的呼聲愈加高漲,一些民族音樂家指出,新國樂最能代表民族性格與時代精神, 新國樂的創造應當迎頭趕上,成為世界音樂之林的重要一員:“新國樂之建設是富有民族的色彩、時代性的而不斷前進的一種音樂。”
楊蔭瀏等音樂學家更是對新國樂的創造充滿期待。他曾說:“世界的音樂,已隨著西洋的文化,漸漸地流注入我們的文化里面, 我們有接受的必要。國樂最后有與世界音樂互相融合的必然趨勢。……國樂有了出路之時,西樂在我國,才能度過它這‘囫圇吞棗的異常階段而真正達到它自然消化的理想時期。”
遙想中國民族音樂創作轉型時期先哲前輩們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對于當下乃至未來中國民族音樂創作當不無裨益。文化自信與民族音樂傳統的弘揚,不僅依然需要固守“民族的色彩”,更要凸顯“時代性”,同時敞開胸懷、擁抱世界,融會五彩繽紛的世界音樂,讓中國文化精神化為動人的聲音飛向世界。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和上海音樂學院民樂新作專場音樂會的不斷推出,正是民族音樂創作在“律動的春天”里展示民族音樂魅力的生動寫照。
劉天華《國樂改進社緣起》,劉育和編《劉天華全集》,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8 年版,第186 頁。
王紹先《新國樂的建設》,《歌與詩》1944 年創刊號,第3頁。
楊蔭瀏《國樂前途及其研究》,《中國音樂學》1989 年第4期,第6 頁。
馮嘉卉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2020 級本科生
(責任編輯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