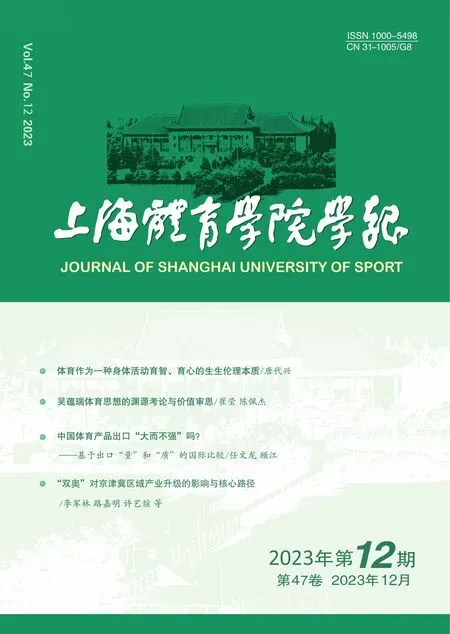近代“武俠”形象的再造與“新民”動員
周 延,戴國斌,段麗梅
(1. 上海體育大學 武術學院,上海 200438;2. 運城學院 體育系,山西 運城 044000)
作為中國文化獨特產物的“俠”[1]237,在其發展過程中,由歷史史實演變為文學社會想象[2]、由“游俠”轉變為“武俠”[3],最終積淀為一種“文化精神”[4]。由于春秋晚期“士”之文武分途,“好用力”“重意氣”[5]的“游俠”成為社會中的重要勢力。隨著漢代大一統政權對“游俠”的打擊,任俠者呈現出“由武向文”的轉向[6],但其精神氣質與行為方式逐漸成為漢末魏晉時期一些注重知識交流與傳承的士大夫的氣質與標簽[7],并作為文人詠俠詩中抒發建功立業理想的原型。唐代以來,士人在追求精神氣質的基礎上,以“游俠”為原型創作的“劍俠”再現了“俠”之“武”色彩[8],在報恩仇、抱不平的基礎上開始注重道德教化[9]。宋元明時代,“俠”逐漸世俗化,更有一些民間秘密結社將其固化為道德信仰。作為一種社會心態,“俠”還與心學、儒家、釋家交相輝映,成為士人精神活動的重要體現[10],并在災害敘事中成為警世正俗的教化內容[11]。在明代注重其“義”而非“技”的基礎上[12],受清代儒家倫理忠義觀的影響,演變出“官俠”“忠俠”形象。隨著清末國事衰微、民族危亡,知識精英將處于傳統文化價值系統邊陲地位的“俠”提升至新高度,并提煉出新的理想人格[13]。“俠”原有的私人之間的恩義心理、同門互助的同道心理[14]被“雪大恥,復大讎,起毀家,興亡國”[15]683的救國救亡心態所取代,并作為救亡圖存的主體,承擔起變革社會風氣之使命[16]。由譚嗣同開始,“俠氣”突破了傳統的“名節”,與現代的革命精神合流[1]391,“俠”被作為樹立革命偶像、組織革命活動的具體實踐[17]。同時,“身懷武術且仗義敢死的俠”也被視作重生四萬萬病夫的最佳傳統文化資源[13]。知識精英希冀通過“俠”所傳達出的尚武精神實現“召國魂”“強國強種”[18]的救亡訴求。
當前關于近代“武俠”的研究中,學者們通過考察文學文本[19]、電影文本[20]塑造出的“英雄”[21]形象,意識到“武俠”所展現的尚武精神對民族國家建構[22]以及促進民族尊嚴覺醒與責任擔當具有重要意義[23]。但同時忽視了其如何“由邊緣進入中心”[24]并參與近代民族-國家建設與國民改造的歷程。為此,本文通過查閱相關書籍與報刊,從近代“新民”思潮下梁啟超等以“武俠”改造身體、振奮精神的言論與實踐出發,剖析傳統“俠”形象的轉變及其動員國民的新實踐。通過探討“武俠”形象的再造與“新民”動員,深入“國民改造”議題,這既是對精英與民眾互動的關注,也是對歷史研究微觀化趨勢的一次回應,“武俠”再造的啟示也為當今如何塑造社會價值觀提供了一定的借鑒。
1 知識精英對傳統“俠”的新訴求
不同于晚清以前對“俠”之“忠義”“重然諾”“急人之難”等道德層面的推崇,受到內外交困的時局影響,近代知識精英將“俠”作為救國救民的重要手段,賦予其救亡圖存、強勇抗爭、匹夫成俠的新期許。由此,傳統“俠”也呈現出新面貌。
1.1 行動目標的重構:由“赴士之厄困”轉向“赴國之厄困”
從歷史上看,“俠”自出現以來一直伴隨著肯定與否定兩種聲音。司馬遷對“俠”的認可在于其“赴士之厄困”的道德品質,為了完成這一目標,可以“不軌于正義”,即不遵從法度秩序。但從維護國家權威、政權穩定的角度出發,其“不軌于正義”且“為知己者死”的行動目標必然與國家治理理念相沖突。韓非子“俠以武犯禁”的出發點就源于其行為動搖君臣關系、干擾國家治理與民風建設。因此,統治者對游俠生存空間進行打壓,史書中也以“權行州域,力折公侯”“德之賊”凸顯其“犯禁”的面向。換言之,從國家治理視角出發,個人恩仇屬于“無意識之義俠,徒助篡逆”[25]70,其行動無助于維護國家政權的穩定。
從近代民族國家建設出發,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知識精英則對其進行了新的解釋。其一,重新定義了游俠的“犯禁”行為。梁啟超[25]169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天下觀”為尺度為其辯護:“俠之犯禁,勢所必然也”,“其必所禁者,有不慊于天下之人心;而犯之者,乃大慊于天下之人心也”。“俠”是懷揣天下而抗爭,而非為私人而亂禁。其二,將為國家而“公武”作為新目標。個體借交報仇的“私斗”成為批判對象,為國家、社會而“公武”被視作“英雄”。蔣智由明確指出“為大俠毋為小俠,為公武毋為私武”[25]18。楊度則將“輕死尚俠之武士道”視作國家社會的福利[25]7。由此,“急國家之難”“赴公義”成為近代知識精英對“俠”的新期待。湯增璧將“種族”“祖國”作為任俠者的行動目標:“上古多忠于一家······中則風義相高······今茲則種族之思,祖國之念,為民請命,而宏大漢之聲。”[26]馬敘倫[27]認識到“國有俠則強,無俠則弱”。麥孟華[28]也有“亡其家以存其國······振弱鋤強,取其不平者而平之”的期望。可見,時人將“俠”定位于為民族國家“抱不平”,個體的“私家”讓位于“國家”。同時,“俠”也被視作可“立國之靈魂”[27],承載了為國家拯濟扶困的新期待。
總之,在民族國家語境下,梁啟超等人對“俠以武犯禁”的重新解讀使“俠”由個人恩義轉向國家大義,“國家”成為新目標,“公武”成為新導向,“武俠”成為“俠”文化的新表征。
1.2 精神內核的蛻變:由“任事自雄”轉向“剛強奮發”
徐灝在注解“俠”的詞義時強調“任俠者,挾負氣力以任事自雄也”[29],將其描述為挾帶氣力做自認為自豪的事情,體現出“俠”的追求在于“顯氣節”。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將這種“氣節”描述為“言必信、行必果、諾必成”的品性,以及“不愛其軀,借交報仇”“救人于厄、振人不贍”的行事風格。“俠”的氣節也呈現出兩面性,既有言信行果與振人不贍的正面性,也有以軀報仇與救援藏匿的負面性。這種“任俠”心理成為傳統社會精英群體的標志與個體性表達。近代知識精英則從救國救亡與啟蒙民眾的角度出發,思考如何解決祛怯弱、伸民氣的問題,并對“俠”進行了新闡釋,主要表現在以下3 個方面。
首先,倡導國家與民眾具備“斗爭”精神。面對世界競爭之大勢,“人恥文弱,多想慕于武俠”[30]成為普世心理。“俠”的生存哲學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一方面,革命志士以“俠”之“沖決網羅”的意志服務于革命實踐;另一方面,“俠”也成為提振民氣、感召國魂的載體。康有為以“士無俠氣,則民心弱”[31]指出俠氣與民心的關系;梁啟超[32]549-555則以“進取冒險”作為“新民”的急物之一。正如漢學家浦嘉珉[33]所認為的:“俠是大多數中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理想······將俠的意志力轉化為行動以影響自己的命運。”可見,知識精英更看重“俠”在國家危亡之際展現出的“剛強奮發”[34]的特質,并將其付諸實踐。
其次,發揚不畏強權(國)的勇敢之氣。面對強權侵略,如何“不畏強”?時人意識到需要發揮鐵血精神,由此,中國傳統的血氣觀也發生了轉變。他們將“血氣”與“進步”意識相連,批判“無血氣則寡廉鮮恥,等于行尸走肉矣”[35],并將“血氣”升華至“血性”,形成“志士不可無血性”[36]的新認識。
最后,倡導“不畏死”的犧牲精神。梁啟超、章太炎等將墨學與傳統游俠精神相結合,贊美墨子“救世之患,急人之難”的“大實行家”品格,稱贊其弟子“皆可赴湯蹈火······重然諾,重義務,輕死生”的操行[25]75。易白沙[37]進一步闡釋墨學“其學勇于救國,赴湯蹈火,死不旋踵”。蔣智由將墨家“欲以任俠敢死,變厲國風”的宗旨視作“救天下之一道也”[25]17。向愷然欣賞古俠“赴人之急,死生存亡以之”的德行,贊揚其“己饑己溺之志”的志向可與圣賢比肩[38]。可見,時人對“俠”的推崇正是看重其犧牲精神。這種犧牲精神體現在既能“輕生死”也能“忍痛苦”[39]。“輕生死”中以“流血”為最,以“流血為榮,流淚為恥”[40]引導大眾“毋寧舍其身以為眾生之犧牲,以行吾心之所安”[15]689;“忍痛苦”則是“枯槁不舍”的堅韌品德,黃侃將其釋義為“窮厄不變其救天下之心”[41]。
總之,在傳統“俠”之“顯氣節”的基礎上,近代知識精英重新發掘了斗爭、不畏強、犧牲的品質,“俠”之精神內核由“任事自雄”轉向“剛強奮發”,并成為救國救民的新共識。這種將傳統個體性的“俠”與“武”相結合的公共化改造可謂修齊治平的現代化解釋,也是對個體修身學公共化服務邏輯的延續。
1.3 尚俠對象的擴展:由“一二俠者”轉向“匹夫有責”
在近代民族國家視野下,“國民”成為國家發展的主體。梁啟超[32]528認為,若國民“愚陋、怯弱、渙散、渾濁”則“國家”無法建立。若要抗衡西方、自立于萬國之林,“必其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彼相埒,則外自不能為患”[32]532。由此,尚俠對象由原先個體性、依附性的“游俠”開始向群體性的“國民”轉化。
梁啟超指出,“一二俠者”(如“主俠”“相俠”“士大夫俠”[42])的個人英雄主義實則是刺客之行的體現,這樣的俠行多少還是帶有“精英人物”[43]的事功性,不足以成為救國救亡的主要力量,而應發動“任俠之匹夫”(四萬萬人)[42]來實現其目標。“俠”的身份涵蓋了匹夫、布衣、儒者、官吏、大臣、軍人、法官、議員、學者、醫家、僧侶等各職業者,時人將其歸納為“政治家之俠、法律家之俠、宗教家之俠、教育家之俠、農學家之俠、工學家之俠、商學家之俠、兵學家之俠、刺客家之俠”,進一步指出“吾國之賴以強大者俠乎,吾民之藉以捍衛者俠乎”[27]。同時,“俠”更有著利群的向度,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個體的差異都可以依靠“俠”進行彌合,“藉俠以同之,合億萬人而為一大群”[27]。從“一二俠者”向“四萬萬人”轉變體現出近代知識精英為救民族國家于危難而發出的吶喊,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其愿景需要通過對“俠”的改造來實現。由此,“俠”誕生了新的向度,由個體精英主義轉向全體國民。換言之,每個國民都擁有“俠”的精神意志,人人以合群為己任,民族國家的救亡與復興就有希望。“俠”在傳統社會屈從于個體的依附性身份也完成了現代化改造,承擔起“匹夫有責”的社會期待。
總體而言,傳統“俠”的現代轉型是以普通民眾為對象、以剛強奮發為內核、以救亡圖存為目標的新實踐。這也回應了梁啟超的“新民”訴求:以民族主義為邏輯起點,采合中西之道德,改變國民“怯弱柔順”“老大病夫”的形象。
2 “武俠”的新書寫:建構“救國”“尚武”“雄健”的新取向
王汎森認為,晚清至五四運動二十年來知識精英對于“自我”的認識呈現出“向上主義”的特征,即“有意識的”“人為的”“向上的”,體現出人的自我完善[44]。“向上主義”是知識精英改造理想“新民”的核心訴求。由此,從救亡目標、精神內核、尚俠對象等方面對傳統“俠”進行重構,并將三種指向融入“武俠”再造,以“救國”觀念挽救民族國家,以“尚武”精神打破“不武”心理,以“雄健”體態描繪“健夫”形貌,展現正面“武俠”形象。
2.1 “救國”觀念的重塑:塑造“為國為民”的形象
在民族國家飽受西方列強欺辱的背景下,“俠”的“犯禁”形象已不再是人們口誅筆伐的對象,而逐漸被塑造成“為國為民”的建設者形象,這一理想形象成為“武俠”再造的關鍵內容。為此,知識精英進行了以下兩方面實踐:
首先,知識精英選取古代俠士的救國事跡作為再造“武俠”的原型。梁啟超以《中國之武士道》作為宣揚尚武精神的載體,將“赴國之厄困”作為是否為“俠”的標準。一方面,報復私怨、殺仇而快心的專諸被視作“私人野心之奴隸,無與全國大計”,季布功成名就后于國家、民族毫無建樹而“以暮氣損民族對外之雄心”,他們都因私心或暮氣等不利于喚醒國魂而未列于“俠”;另一方面,贊揚以國家名譽為重的古俠,“不事二主”的王歜、“一怒以安國家定社稷”的曹沫、“急國家之難”的墨子、“力爭國權,不肯讓步”的孔子都被視作“天下之大勇”。此外,劉師培、柳亞子等知識精英極力宣傳岳飛、李廣、衛青、張騫、黃宗羲、鄭成功等民族英雄抗爭侵略的事跡。可見,“率先陷敵陣,一死揚國威”才是“大勇”,為國家御侮與奔走的人被稱為“大俠”。
其次,知識精英著重描繪近代武術人救國救民的俠義氣概與實踐。1910 年代,姜俠魂作為倡導“武俠”精神的先鋒人物,通過輯刊《三十六女俠客》[45]2,以“女子、婦人俠客”為對象,開篇就描寫女俠鋤賣國賊之事以警醒世人勿當“亡國奴”,試圖通過對女俠客群體“記其事,狀其貌,描摹其精神”從而激發時人“爭榮吐氣”的氣概。1920 年代,王五、霍元甲等武術人逐漸成為“為國為民”形象的代表。時人十分認可大刀王五“嘗有天下國家之志,招游俠之士操縱之”的游俠風范,他不僅積極謀劃解救譚嗣同,更號召“我輩武人,所重者俠義勇耳,君危不扶,國困不救,何以為人哉”[46]。霍元甲更是體現了新舊、中西交融之際社會對于“俠”的期待。向愷然所作《近代俠義英雄傳》[38]描述了霍元甲團結同胞不內斗、三打外國大力士、提倡尚武強國、創辦精武會等事跡,展現了中國人的尚武精神,也使得霍元甲的形象由拳師轉變為民族英雄。再如,查瑞龍面對無人與外國力士應戰的局面請示舉重較技,兩次較技都勝過對方,但對手均以其“姿勢不符”不予認可。查瑞龍直言:“余之來意非為獎金,僅思一洗東亞病夫之恥而已,果得獎金亦作慈善捐款,請勿為區區墨懷。”[47]近代不斷涌現的“較技爭光”的武術人事跡呼應了揚國威、抗侵略的時代旋律,通過宣傳得到民眾共識,武術人成為“為國為民”的典范人物并成為民眾的集體記憶。楊瑞松[13]在評價“俠”的時代意義時強調:“俠化身成為民族的守護神······以‘傳留數千年的拳術’······洗刷了覆蓋在全民身體上的恥辱。”可見,以“愛國主義”書寫的集體記憶扭轉了傳統“樂為臣仆”、服務于一鄉一族的私義性,并以普通人甚至是游走于江湖的底層武術人為范本,通過描繪其抵抗侵略、洗刷“病夫”形象等行動,折射出知識精英“匹夫成俠”的愿景。
近代知識精英借助“武俠”將“為國為民”的形象不斷延伸,重新解析古代武士的愛國俠義行為,宣揚“長國人志氣”的愛國大俠。通過描繪古今抵御外族侵略、維護民族氣節之事跡,構建起“為國為民”的民族主義敘事,“國家大義”逐漸深入人心并形成群體觀念,影響后世創作者的書寫,如此后金庸所言“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將“武俠”提升至新高度并延續至今。
2.2 “尚武”精神的弘揚:塑造“剛強奮發”的形象
對于民眾而言,擺脫“病夫”“文弱”的負面形象需要內在精神的脫胎換骨,進而具備進取、勇敢、剛健的尚武精神。在“武俠”的塑造中這一要素尤為重要。
其一,通過展現習武歷程之艱辛凸顯進取意志。1916 年的《青年雜志》刊載了蕭汝霖所著《大力士霍元甲傳》,描寫霍元甲少時因為體弱而被精通武藝的父親拒絕授武,結果偷學父親武藝、潛心練習,從而獲得高強武藝。實際上,許多武術人也是因“體弱”才開始走上練武強身的道路,旨在“轉強”,而刻苦的習武經歷成為展現剛強奮發精神的重要環節。《武俠叢談》記載了習武人王子仁的練武事跡:“廳事為武舉人教子弟習武之所,系繩梁間,懸布囊,中實以斗許砂粒,重數十斤,名曰砂囊,拳擊之以練臂力。而囊懸當路,頗障行。子仁出入,必以手推之,始頗覺重不任。久之,慣無所難矣。”[48]武術的習練過程本身就是對意志品質的磨煉,通過“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艱辛歷程收獲個人能力的蛻變,展現其剛強奮發的精神。正如汪涌豪所言,“俠”的人格特質之一就是以其“意志行動”來達到自己設定的目標,為了這個目標可以克服一切障礙[49]。武術人由“體弱”到“剛健”的轉變過程實則迎合了中華民族由弱變強之崛起的議題,這與梁啟超“新民”思想的初衷、國富民強的目標不謀而合。
其二,通過實踐塑造勇者無畏、剛健有為的氣質。在習武個體修習過程中,除了需要以堅韌、進取的品質換取功夫的由弱到強,還需要具備勇敢果決的斗爭智慧。但是私門爭斗只是為“小家”生存,屬于私德范疇,因其群體局限性未能升華為“大家”(國家)的公德意識。隨著近代時局動蕩,武術人開始思考如何從小我走向大我。姜俠魂在其主辦的《國術統一月刊》中專門開辟“武俠傳略”“先哲尚武”“故事烈跡”等版塊,作為宣揚俠勇的陣地,以“借武功表現俠的精神”[50]。其所撰《中國武士道故事集》開篇記載孔子如何從容不迫、力爭正義進而讓齊景公歸還魯國故地,以及誅殺邪說禍人的少正卯,闡揚其“智仁勇”的尚武精神,認為其“足樹武德之模范”[50]。
其三,在文學、影視創作中突出“尚力”面向。1930 年代,電影從業者希冀通過武俠電影來提振民風,不斷制作武俠電影以展現國民尚武硬性的風氣。如導演吳文超挑選演員演繹霍元甲的主要標準就是演員必須具備“硬性”特質,在拍攝內容上突出“生動俠義精神的鏡頭”,目的在于“發揚尚武精神”[51]。為了突出霍元甲的英雄性,刻意壓縮了男女主角的感情戲份,即使如此電影劇情中穿插的戀愛場面還是引起了公憤:“《霍元甲》中的不知所云的戀愛穿插,把全篇英雄豪魄的骨干,化為烏有了。”[52]可見,時人期待展示“武俠”矯捷勇武的英雄形象而非個體情感,反映了對剛健、進取、尚武精神的渴望。
總之,通過展現習武歷程的艱辛,塑造勇者無畏、剛健有為的氣質,并借助藝術創作樹立“剛強奮發”的“武俠”形象,進而描繪出不卑不亢、艱苦奮斗、勇者無畏、臨危不懼的尚武氣概,這成為民眾心向往之的追求,也是時代所需要的中國精神。
2.3 “雄健”體態的展示:塑造“體健技強”的形象
為激發四萬萬人的尚武精神,除了以“救國”“尚武”進行精神面向的塑造,還要通過“身體”進行尚武精神的直觀表達。為此,知識精英通過展現武術人體態雄健、武藝高強的身體特征,為大眾樹立起“健夫”的榜樣形象,武術人的“身體”走向“臺前”,成為喚醒民眾的最佳典范。
其一,通過陽剛健碩的身體形象,潛移默化地影響大眾。在身體形象的塑造中講求直接有效,給大眾以視覺沖擊感。這一點在對“大力士”的形象刻畫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武俠明星查瑞龍的“大力士”形象在1928—1929 年的《明鏡》《新聞報》《晶報》等報刊中數度出現,1930 年《萬有周刊》舉辦的“肌肉美”比賽中更是將其稱為“肌肉美模范”[53]。武術人王子平因“嘗擊敗康泰爾大力士于北京者”[54]而被大眾熟知,被冠以“大力士”稱號,并通過畫報極力展示其魁梧身姿。實際上,“雄健”體征被視作“康健”體魄的標志是在近代逐漸形成的。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的身體審美觀受到西方理念的強烈沖擊,開始由“文質彬彬”轉向“氣力之美”[55],強壯勇武的肌肉感成為主旋律。在精武體育會的報刊中常見姚蟾伯、盧祎昌等身著豹紋樣式展現健碩形態,凸顯其野性力量感。此外,《國技大觀》[56]1在開篇以大量照片展示出青年武術人王子平的“肌肉美”及吳鑒泉、何玉山等老輩武術人的矯健身姿。編者希望通過武術人的肌肉體征、定格招式展現出中國人的體質健碩且內功深厚,借此引導讀者。此外,還可從影評中追溯時人對力量感的追求。對電影《霍元甲》(1944 年),時人表達了對舒適飾演的霍元甲“瘦弱”形象的不滿,“演的很好,演技洗練,可惜外形稍嫌軟弱”[57];甚至有更為激烈的評價:“如果是一張真的提倡體育的影片······看到銀幕上這位瘦瘦的霍元甲,則僅是使人神往而已。”[58]可見,“武俠”硬朗有力的雄健形象已經開始深入人心。
其二,除了凸顯充滿力量感的身體特征,身體的靈活性與技術性是否達標也是評判標準。由傳統武術中“輕”之意向出發,近代小說中對俠客身體能力的想象性開發生產出內功、輕功以及“飛檐走壁”等武功系統[59]65。近代出現的電影技術又將“武俠”文本中“輕”之意象視覺化,在內容上也偏重展示演員的靈活度與技術熟練度,呈現出“身輕如燕”“飛騰之術”的靈巧特質。如時人評價《大俠甘鳳池》中飾演甘鳳池的演員王正卿,其技術“打得落花流水,極其純熟而自然”,但是在技術上卻不如范朋克“足捷若猴身輕似燕”[60]。可見,西方明星范朋克所呈現的“精劍術、身手敏捷、矯健活躍”[61]的表演更符合大眾期待。從武術話語來看,時人對王正卿、范朋克二人的表演評價實則是對傳統武術十二型中“起如猿”“落如鵲”的演練水平的關注。“輕”是“武俠”身體技術的重要表征,折射出武術動作是“對人全身本能性動作優化的全面訓練、對身體協同一體的聯動制度設計”[62]。總之,將力量感與輕靈感結合而構筑出“體健技強”的身體觀,使得“武俠”的形象更加立體,從而為大眾切實展現了“雄健”身體的范本,也將技擊的烏托邦躍然于人前。
綜上,在“救國”觀念、“尚武”精神、“雄健”體征的新取向下,知識精英發掘與刻畫出“卓然杰出、德義肝膽足為一世之表率”[45]5的精神氣質,建構起“為國為民”“剛強奮發”“體健技強”的新形象。“武俠”鑄就的新的身心觀也愈合了春秋以來士人的文武“人格分裂癥”[59]68,更是對“病夫”形象的強有力回應。
3 再造“武俠”的價值導向:動員國民的身體與靈魂
近代知識精英對國家的改造經歷了由政府向民眾的轉變,將“國民”視為國家興衰存亡和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63]。他們希望將國民的“孱弱不武、怯善畏首”改造為“挺身急公為舉世之所不為,戚屬之譏有所不計,鄉黨之謗有所不顧”[45]5。換言之,知識精英對國民的期待主要表現為身心皆具尚武氣概。為此,知識精英從謀改社會風俗與動員國民身心為出發點,將勇武剛健的“武俠”形象作為引導民眾愛國意識、強化尚武精神、塑造健夫身體的“藥方”。
3.1 以“為國為民”的形象引導國民的愛國意識
在知識精英的不懈努力下,“武俠”與“國家”形成聯結。他們不斷借助報刊宣揚武術人的愛國俠義之事,使得武術人“為國為民”的具有民族氣節的形象日漸深入人心。國人評價大刀王五,盛贊其拳拳愛國之心:“拳術家中之慷慨結客,享有盛名,而又有愛國之心者,以吾所知,蓋無有逾于大刀王五。”[64]其人風采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人遺忘,1940 年代仍常有報刊刊載其事跡“以供茶余酒后談助”,“不過這位劍俠與之前的游俠,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其中最為難能可貴的,是他有很強烈的國家觀念,有一個時期,他很想幫助勇敢有為的政治家,來革除積弊,復興祖國,雖則他的志愿沒有能夠實現,可是他這一番的熱忱很值得我們欽佩的”[65]。此外,霍元甲其人其事成為代表民族精神的符號,并隨著影視傳播走進無數國人內心。電影《霍元甲》(1944 年)將其定位為“強國強種的健全先驅”,稱贊其“洗刷國家衰弱的風氣,滌盡民族頹唐的風氣,為國揚眉,為民吐氣”,因而在劇情中貫穿其“高尚技藝”與“愛國愛民思想”[66]。霍元甲的民族英雄形象經久不衰,1970 年代李小龍對“陳真”的再創作也延續了霍元甲雪恥“病夫”的敘事主題。同時,“為國為民”的民族主義敘事也成為后世引導國民愛國意識的重要內容。
與此同時,武術人自覺擔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將武術作為手中的“劍”拯濟國家、型塑“新民”。涌現出一大批以武術救國為己任的人物,他們所展現出的“為國為民”的價值追求值得敬佩,如劉殿琛的“習武術、強中國”、萬籟聲的“養成其俠偉義勇肝膽,質樸淳厚道德,自衛衛國本領”。近代武術人將口號、觀念具體化為看得見、可操作的行為規范,并加入“救國”宗旨。例如,當時的“少林戒約”要求習技者懷抱“恢復河山之志”,勤修時“必須以恢復中國為意志”,演習時作“蹈中宮”以展示“不忘祖國之意”[67]。近代武術人以“為國為民”為價值導向,通過倡導習武強身、習武救國,將武術上升為“國術”,提升了武術的政治地位,拓展了武術的社會化發展;同時,依靠中央國術館、精武體育會等組織陣地培養武術人才,改善民眾的身體與心理,且積極參與社會治理,可以說他們自身就是“為國為民”俠義精神的最顯著體現。為此,有學者[68]意識到,“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武德境界和思想情操使中華武術的內在價值和功能與民族勃興、人類偉業緊密相連。知識精英將“以武救國”作為鼓舞人心的起點,將愛國與習武相關聯,并以武術人的民族氣節感染國民奮起抗爭,吹響武術救國的號角。
3.2 以“剛強奮發”的形象強化國民的尚武精神
近代知識精英敏銳地認識到,“武俠”是醫治國家與民眾的一味良藥,對于如何將其廣而告之并發揮出功效,他們開始既內求諸己,也假于外物。一方面,由于“世俗習于萎靡不振,唯尚俠以挽救之”[69],大量描繪“武俠”的作品問世,旨在“闡幽發微,表忠揚烈”[70],通過筆記、小說等文學形式“記英勇俠義之事”,展現“剛強奮發”的尚武氣概,希望“讀之增人志氣”[69],起到“警惰之良藥”[71]的效用。另一方面,他們將目光轉向傳統“說部”,并進行新的解讀,希望提振尚武之風。定一在對《水滸傳》的再評價中將其作為“遺武俠之模范”。林紓翻譯《水滸傳》的動機在于“吾國《水滸》之流傳,至今不能漫滅,亦以尚武精神足以振作凡陋······仍有益于今日社會”[72]217;為“特重其武概,冀以救吾種人之衰憊,而自厲于勇敢而已”[72]205,他還重新采補、輯錄武術人的事跡以激發尚武精神,并通過《技擊余聞》描繪了40 多位身懷武藝之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武俠”精神潛移默化地對民眾產生了積極影響,尤其有助于培養見義勇為、扶危救困的正義感。教育家舒新城曾提到《水滸傳》《包公案》《七俠五義》《儒林外史》等小說培養了他“扶弱不依強、傲上不傲下的習慣”[73]。報刊還刊載了一名叫吳玉梅的女子多次行俠仗義的事跡:她自述從初小畢業后就喜愛看武俠,正因為佩服義俠之人并且“想替國家做一點除暴安良的工作”,所以看到發生搶劫財務之事便要拔刀相助(自述“十三歲起已有九次拔刀相助的事跡,其中四次有槍也不害怕”)。她的事跡也吸引了姜俠魂,并有意為其介紹學習武藝本領[74]。晚清志士的俠行也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對于謝晉元帶領八百壯士進行四行倉庫保衛戰,時人即稱贊其繼承譚嗣同遺風,“譚瀏陽的強項遺風,在數十年之后,還有大批的繼承者在”[75]。這是跨越時間的呼應,對烈士義舉的宣傳正是對“不畏死”犧牲精神的贊頌。不論出身,無分男女,“武俠”精神影響了一代代國人。
總之,“剛強奮發”的“武俠”形象不僅通過文學作品給人以警醒,更在社會層面動員了民眾,以其尚力精神成為挽救頹風、改造國民羸弱心理的強心劑。
3.3 以“體健技強”的形象型塑國民的健夫體征
“武俠”形象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還因其呈現“體健技強”的價值導向,激發了民眾對“健夫”的渴望。
其一,近代知識精英積極引導民眾通過習練武術而強身。首先,將練拳視作“成俠”的必由之路。他們看到了國術能為國家、民眾帶來希望,呼吁民眾打好基礎將俠魂與武技融合。萬籟聲[76]倡導:“‘有國術之技能,始能有大俠魂之實力!有國術之精神,始能有大俠魂之發揚。’······‘大無畏精神’者,即寓于‘偉大國術技能’之中······提揚其‘大俠魂’之精神,莫如精研國術。”還有人將“成俠”與“拳善”“劍精”相關聯:“拳之善者成俠,劍之精者欲仙,小而言之可以強身,大而言之可以衛國。”[77]更有人呼吁道:“非武術不能養成俠義氣概······非武術不能使我民族健全。”[78]其次,武術人成為習武強身的模范、大俠魂的代言人。姜俠魂在《國技大觀》中提到霍元甲、向愷然等創辦學會、研習技擊的目的是:“以冀其天然民眾國粹體育日普及于人群,以圖謀生存在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之場。”[56]17盧祎昌在1936 年回憶:“現在全國及海外五十八家的精武會男女數十萬健兒就是這位銅筋鐵骨、義膽俠腸的霍先生造就的。”[79]同時,在報刊正文前頁常見武術家、婦女、兒童、體育教師等各類群體的習武身影,這樣的視覺編碼意在引導民眾以武術強健體魄、養成尚武精神與俠義氣概。最后,“習武強身”話語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武術家徐震自述幼時受到“武俠”的鼓舞,進而為求強壯身體而習武:“任俠之事,壯偉之行,力人猛士之所為,予為童子時,即樂聞之,以體弱力寡,益欲習技擊自壯。”[80]
其二,因受眾面廣泛,武俠電影成為振奮尚武精神的最佳傳播工具,“體健技強”的導向也影響了武俠演員身形塑造的規范。首先,演員選用標準之一即需要具有“健夫”的身型體態。演員的選角注重體征與技能的雙重要求:“一則應有武術的本領,一則該有英武的表演。”[81]之所以選用張翼作為《中國羅賓漢》的主演,就是考慮其擁有“鋼鐵般的身體、雄赳赳的精神”[82]。其次,正因為這樣的身型要求,為演員帶來了身體型塑的新標準。在1920 年代,明星公司聘請李振聲等武術家培訓演員,所有男女演員,每日必須習練武技2 小時[83];根據武俠明星范雪朋回憶:“空閑時間,常常練功、騎馬······還請了人教我舞雙刀,拳術,弓箭。”[84]可見,對于飾演武俠片的影人而言,武術是其必備的技能。換言之,武術作為“武俠”身體技術的表現形式,若要為國民展現出身體的“神話”,就需要影視從業者在表演中呈現武術技能的熟練、勢氣上的英武,才能以“體健技強”的形象激發民眾對“健夫”體征的渴望。
綜上,在“為國為民”“剛強奮發”“體健技強”的新價值觀導向下,“武俠”形象逐漸深入人心,影響了近代民眾的日常生活,形成了民眾救國救民、勇武尚力、身強體健的新實踐。
4 結束語
為扭轉民族國家的生存逆境,近代知識精英重新發掘、啟用了傳統之“俠”,對其進行了“武俠”再造,并將其作為動員國民身心的文化符碼。在此過程中,救亡作為新目標、尚武作為新期待、民眾作為新主體,產生了“赴國之厄困”“剛強奮發”“匹夫有責”的新轉向。“武俠”再造融入了“救國”觀念、“尚武”精神、“雄健”體態,以“身、心、靈”三維形構出理想的“新民”樣態,將其作為動員國民身與心的抓手。可以說,“武俠”是近代尚武精神的具象展現,其“為國為民”“剛強奮發”“體健技強”的新形象是對好勇斗狠的匹夫之勇、為王前驅的奴性、“病夫”體征的一次“手術”。這一過程不僅是“沖擊-反應”的結果,更是中國文化自身價值體系的主動轉型與現代化調適。當然,“武俠”形象的再造與“新民”動員也是知識精英與民眾的一次互動,其中既有精英借助“武俠”對民眾進行動員與教化,也有民眾對此種動員方式的回應。
近代知識精英將救國、尚武、雄健的“新民”價值導向傾注于“武俠”,希冀以“武俠”的尚武精神重整民風、重塑國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85]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離不開每個人的愛國觀念、進取精神與康健體魄,這樣的形象氣質既是新時代奮斗者身心共建繞不開的重要話語,更是闡揚民族精神、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可或缺的重要底色。
作者貢獻聲明:
周 延:收集材料,撰寫、修改、校對論文;
戴國斌:提出論文選題,審定主體框架,提供理論指導;
段麗梅:整理資料,校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