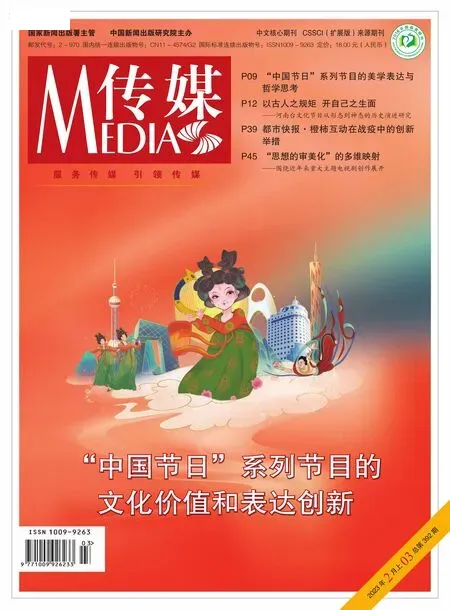舞蹈《今又鸮聲起》的詩意表達與歷史還原
文/宋德偉 岳國法
河南廣播電視臺2021年以來播出的“中國節日”系列節目爆紅各大媒體、占據網絡頭條。這些節目以敘事的方式展開,引領受眾進入故事,再輔以如詩如畫的情景,讓受眾從中感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意蘊。2022年8月3日晚播出的詩意舞蹈《今又鸮聲起》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整個舞蹈時長6分55秒,它以1976年考古專家鄭振香面對鸮鳥文物上的銘文“婦好”為引子,通過舞蹈形式向觀眾展示了商王武丁與王后婦好之間一段刻骨的愛情。恰如在舞蹈的最后,鄭振香所說的,“我們要用這些文物去還原那些隱匿的細節”,那么,舞蹈《今又鸮聲起》以哪些方式來實現這種還原呢?
物性還原:舞蹈作為藝術作品的歷史性
舞蹈作為一種藝術文本預設了一種目的性,它在認識論還原的作用下,把各種舞蹈元素深植于文本的歷史性之中。生態符號學家蒂莫·馬倫認為,“文本是一個既定文化中內在結構和外在符碼相結合的平臺……一些藝術品如民族服裝、繪畫或者音樂都可以是文本,是鑒于這些都被解釋、評價為重要的東西。”詩意舞蹈《今又鸮聲起》作為一種藝術文本,它的歷史性至少以兩種形式進行了展示。
以碎片化的歷史客體展示物性。《今又鸮聲起》的開篇是一個考古場面,鸮鳥文物的出現明示了舞蹈文本的潛文本是一種歷史文本,是過去曾經發生過的真實歷史。但是與此同時,這也告知了受眾,關于鸮鳥文物的一切,是一種非敘述性的、不可再現的歷史。它存在過,但是我們作為現代人無法去重現那段歷史,只能依靠我們像考古那樣對這種“物性客體”進行強勢還原,尋求其中的本質意義上的統一性。舞蹈從第5分47秒到6分03秒用了16秒,充分展示了這種物性還原,歷史變成了碎片化的信息,掩藏在一件件碎片化的文物中。
這里所論及的“物性”,表現為一種相對于歷史事實而言的歷史之“象”,它可以是考古專家鄭振香的感知和聯想,可以是考古發掘出來的文物自身,也可以是關于“婦好”這個歷史人物的各種甲骨文上的記錄等,它們共同構成了這個舞蹈作品的歷史性。盡管通過這些歷史碎片去獲取已經過去的歷史的真實性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安陽殷墟出土的1萬余片甲骨中,提及“婦好”這個名字的有200多次,它們所記載的“歷史”為觀眾呈現的是一種開放的文本、一種非敘述性的歷史。這些物性客體的存在是舞蹈《今又鸮聲起》的創作原材料,同時也是飽含那個時期美學的、認知的、倫理的信息,它們成了“原型”或“模式”供作者選擇,整個藝術品的創作也都是以這個“歷史性”來設定它的文本價值和意義。
以各種歷史身份之間的相互架構呈現歷史。《今又鸮聲起》的故事源自商王武丁與王后婦好之間的愛情故事。然而,舞蹈如何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來傳達一個較為豐富的歷史內容,而又不僅僅局限于一個愛情故事呢?
從還原論視角看,舞蹈明顯采用的是一種“有機主義”模式,將男女之間的倫理道德作為一個有機系統來看待,這是一種生物學意義上的倫理構建。商王與王后之間的倫理生態表現為一種多維度的對應關系:一是政治關系,如商王頭戴王冠,王后則手持斧鉞;二是婚姻關系,如商王王冠和王后的鳳冠霞帔;三是君臣關系,如商王王冠與王后祭祀禮服和冕旒等。婦好作為一種倫理對應,強調了具體時空環境中她的存在意義和價值。倫理不會憑空產生,需要借助一定的客觀環境才能生成。因此,舞蹈所要展示的倫理意義是一種歷史性的,是基于具體所指基礎上的,倫理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的關系,強調達成一種和諧共生的平衡狀態,是將倫理生態作為一個系統來考察,要求系統內各要素協調、平衡、和諧。
從故事的敘事進程看,舞蹈以商王武丁呼喚婦好開始,婦好則以各種不同的人物身份再現。在故事的表層,婦好身份的變化意味著線形敘事的反復出現,但是,時間卻被窄幅式處理了,進而相應地把倫理關系在時空上的綿延做了寬幅式處理,因而,盡管王后的身份不斷在變,但是觀眾所感受到的則主要是商王對于王后的思念。這樣的故事是典型的浪漫傳奇模式,因此,故事必定被給予了一個凄慘的悲劇結尾:舞蹈的最后,年邁的商王發須皆白,看著屋外到處飄灑的雪花,武丁的愛情歸于孤獨。在故事的深層,舞蹈則借助愛情敘事,以商王獨舞、商王和婦好共舞等形式呈現出了國家倫理與個人愛情之間的糾葛,更凸現了一種倫理與意識形態的相互作用。

《今又鸮聲起》
文明形態還原:舞蹈作為藝術形式的符號性
羅曼·雅各布森在談論符號交流的六要素(發話者、語境、信息、符號、接觸方式和受話者)時曾指出,當某種因素成為主導,就會產生對應的某種功能(如所指功能、表情功能、呼吁功能、詩學功能、寒暄功能、元語言功能)。當“符號”成為主導因素時,就會產生符號的“詩性”功能,文本同時也會相應地通過從選擇軸到組合軸的投射來產生新的符號,文本也因此具有了新的詩性話語特色。在《今又鸮聲起》中,鮮明的服飾和人物形象就變成了一種新的詩性符號,傳達出了重要的信息。
舞蹈服飾的符號性。在《今又鸮聲起》中,商王和王后穿著傳統的中國服飾,給觀眾營造了身處古代的時空錯位感。然而,在舞蹈的開始和最后,王后“婦好”又以考古專家“鄭振香”的著裝形式出現,這種常見的現代服飾瞬間拉近了與觀眾之間的距離感。古風服飾是聚合軸上的窄幅,呈現出統一的古代風格;現代服飾的出現則拓寬聚合軸的寬窄,產生了截然不同的風格效果。這樣的舞美設計,相對于當前的現代服飾來說,具有重要的符號價值。
對于“中國風”在服飾方面的還原來說,大多數人沒有明確表明這種服飾的適用性,更偏向于認為現代服飾更適合當前社會的現實狀況。或者說,盡管很多人喜歡這種“穿漢服”的愛國行為,認可中國古代服飾對于文化建設的重要性。但是總體來看,喜愛中國風的思想中所潛在的回歸意識,仍然沒有被主流的服裝設計所引入現代人的生活中。因此,在新聞報道或者紀錄片創作中,以中國風為選題進行報道,可以彌補它們在社會上缺失的話語權。舞蹈《今又鸮聲起》作為一種“軟話語”,不僅使受眾可以用感官重新感知事物,還能通過使用新技術讓受眾來發現新事物、新意義。
例如,在婦好和商王服飾的顏色方面,商王的淡藍色象征天空和大海,代表乾,而婦好的大紅色則象征女性旺盛的生命力,代表坤。二者在舞蹈時候的顏色融合,則帶給觀眾一種流動的視覺沖擊力,它不僅僅表現為夫婦二人的和諧,還在哲學認識論意義上肯定了在一定的時空環境之中,人自身、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界達成的一種和諧共生的平衡狀態的意義。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風舞蹈現象展示了中國社會文明在特定時期的一個形態。詩意舞蹈作為一個文本,它所采用的各種舞蹈技術,也是這個社會所特有的,或者至少是一個文明所特有的。因此,國內外很多人都認可“中國風”就是中華文明的象征。舞蹈作為中華文明的一種表現形式,它在生成自身的同時也塑造了中華兒女。
“婦好”和商王的符號性。從符號表意的角度看,《今又鸮聲起》作為一個符號文本,必定由雙軸操作組成,即聚合軸上的選擇與組合軸上的連接。聚合軸的寬窄變動很大,它的窄幅式處理僅作用于商王與王后的愛情,它的寬幅式處理則是為了把商王朝的文明形態展示出來。前者是詩化的,重在一種感性認知;后者則是歷史性的,凸現商朝時期的文明形態。每一種文明都有自己的形貌,它們的產物都有自己的風格,而《今又鸮聲起》圍繞“婦好”所構建起來的這樣一個符號,正是為了從不同方面表現我們那個時代的文明形態,即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存在于創建并維持著這種文明的特定社會群體的思想、實踐及產物等具體方面的總和。
《今又鸮聲起》關于愛情故事的隱喻性敘事,將觀念與人、事件與技術貫通起來,將人身體的物理特性與社會特性聯系在一起。隱喻性的舞蹈動作讓我們可以看到它作為社會身體的功能性,同時也可以看到它作為物理身體的技術性,它將身體與文化聯系在一起,以精神上的文化塑造著物理上的身體,而身體的隱喻意味著社會是一個動力系統,此刻的身體就不僅僅是一個獨立的組織,還是一種生物現象,是進化過程的產物。受眾在身體隱喻文化上的共識就成了民族文化共同意識的基礎,猶如德國文化記憶研究專家揚·阿斯曼認為的,“儀式作為一種交流方式,自身就是一種形成性的影響,它通過文本、舞蹈、意象、儀式等來影響記憶的發展。”
從哲學認識論意義上說,人是通過舞蹈的中間作用來認識和發現歷史,而舞蹈則是通過各種舞美設計來建構人們的歷史。舞蹈空間是對歷史以及歷史中曾經的日常空間的美學創造,或者說,這是一種還原論意義上的解釋關系,它的目的不是為了以一種對稱性來展示現實與虛構之間的關系,而是以一種話語觸媒的方式引導我們去關注這些符號背后的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認識論還原:舞蹈作為融媒體的介體性
舞蹈作為人類最為古老的藝術形式之一,它主要通過人的肢體動作來表達情感,實現表演者與受眾之間的意義的交流。熟悉“婦好”故事的讀者很容易發現,我國至少已有三四個版本的藝術創作,如賀嘉佳編導的舞劇《婦好》、20世紀20年代的豫劇劇目《龍鳳令》、2017年12月17日央視大型文博探索節目《國家寶藏第一季》中關于國寶“婦好鸮尊”的介紹,以及臺灣漢唐樂府新排南管樂舞劇《武丁與婦好》。
近些年,信息化、數字化等現代技術的運用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推動著傳播媒介的發展,河南廣播電視臺推出的一系列“中國風”舞蹈節目,通過革新原有的媒介元素、重構舞蹈藝術的表意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先前的觀賞方式,實現了“介體”發展的新思路。《今又鸮聲起》作為新技術形勢下的文化產品,運用了全新的影像技術,融合了不同媒介元素使科技與舞蹈融為一體,產生了新的視覺傳播模式。它將虛擬與現實空間結合,利用技術手段將舞蹈作品中的內容進行重構。從微觀層面上看只是作品中的一個元素,但從宏觀層面上看,則是一種新意義的表現。
關于“婦好”的故事,民間流傳很多,《今又鸮聲起》作為根據民間傳說生成的舞蹈文本,需要在認識論上進行諸多方面的還原,也唯有重回傳統的文化價值觀,才能重新認識“舞蹈”作為一種介體的意義和作用。
《今又鸮聲起》以簡潔的色彩和舞美,讓舞蹈回歸文明,是因為舞蹈畢竟首先是為了表達一種意義,突出舞蹈行為在整個故事中的表現,實際上就是為了能消除文化制品的“偽自然性”。文化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原本就是兩種形態,“自然的文化化”是先前的文化實踐,而現在則是要回歸“自然”,讓人回到自然之中,回到一個有機的系統之中。生物符號學家托馬斯·西比奧克曾從動物符號學的角度指出,人在利用言語進行交流之外,還會和其他動物一樣,充分利用非言語的方式進行交流,而“舞蹈是通過身體在多種形態和文化中的工具性,來表達人類思想和情感的復雜藝術形式”。盡管西比奧克注重從生物學的角度肯定“非言語”交流的意義,但也恰好說明,舞蹈也是人和動物用來進行感知和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
媒介并不能真正改變人們的認知,但在某種程度上,人們卻可以從媒介獲取一些符合他們認知的信息,這也就是說,媒介可以被視為一種調解,影響文本的建構和解釋,甚至可以自身形成一種“媒介域”(MediaSphere),替代了之前傳統的認知方式。加拿大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媒介作為人類認知方式的延伸,以工具—物的形式延伸人的感知空間,它的變化必然導致社會結構和知識體系的改變,“所有的媒介作為我們自己的延伸,是用以提供新的轉換視野和意識”。
對于《今又鸮聲起》來說,商王和王后之間的愛情是第一層次的認知,而其中所暗含的關于民族文化的話語是第二層的認知,陰陽和諧的象征則是第三層次的認知,受眾需要對這個舞蹈中的信息進行重構并加以解釋,才能真正欣賞這個富有民族特色和歷史性的舞蹈所表達一個普遍意義上的主題。河南廣播電視臺注重中國節日,倡導“中國風”,正是基于一種認識論意義上的回歸,及時關注當前人們的需要,以及對于中華文化、文明的反思。換言之,舞蹈這種藝術形式本身作為一種文化實踐,是在意義建構中形成的一種構成性實踐,我們欣賞藝術作品,就是要理解它的表意模式,思考文化的特殊性就是思考它的內部形式和關系,以及它的內在結構化過程。從這個角度看,舞蹈《今又鸮聲起》中關于文化的各種表意模式所要激發讀者的仍然是一種社會學美學,它將美學納入其中,卻仍然堅守以倫理構建為軸心。
結語
河南廣播電視臺推出的一系列“中國風”舞蹈的表意模式是詩性的,但它的軸心卻是倫理的。舞蹈《今又鸮聲起》借助融媒體形式消弭了故事與受眾之間的歷史距離,弱化了事實和虛構之間的區別,讓藝術走進生活,把藝術還原為生活的一部分。從其現實價值看,這種藝術形式的“物性”作為特定歷史的再現不像其他歷史客體那樣孤立存在,而是存在于與人的互動之中,每一次欣賞都讓受眾在互動中對它有更加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