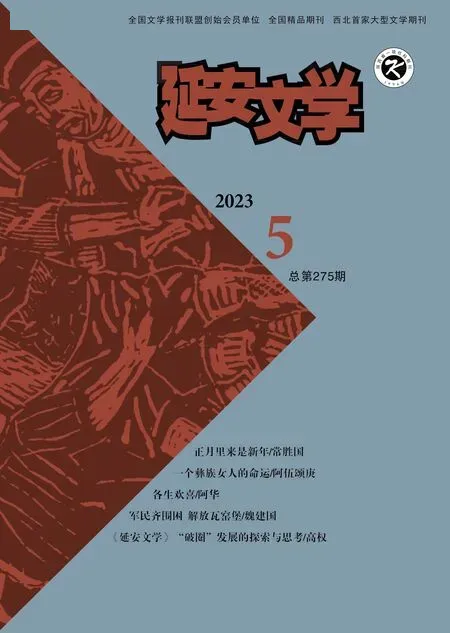出 家
施佩清
一
很怪,橋建在那里。
怎么看都很奇怪。
僅僅是為了連接南北兩個鄉,一條三十米不到的河道,要用到這樣高大駭人的鋼材結構,怎么看,都很奇怪。
李里即使站在距離那里很遠的地方也能一眼就看到橋架上的弧形拱背,那樣遠遠的,亮著救生衣一樣的橙色,漂浮在遠處的天空中。
“怎么建了那樣一座橋”以及“什么時候建了那么一座橋”……類似這樣的問題,他在心里開口好幾次,不知向誰詢問。問題拋到母親這里,她只說:“不知道,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他猜這座橋是為了城市擴大而建,在南邊那個即將開始發展的城市里,來了打印店、寫真店、電影院,還要建樓盤、建中學、建小學……李里上過的小學,即將要搬到那里去了,不用像小時候一樣,穿過老街,路過柳樹、棗樹,經過澡堂,沿著高高的河岸往前走上好遠好遠……
這個問題,原本問父親更合適,他年輕時候是賣貨郎。從前他的口頭禪是“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多”。在李里家的飯桌上,飯菜冒起的白煙中,外面世界在父親的描述之中如同海市蜃樓,被李里大筷夾起,狼吞虎咽到肚子里去。父親低頭劃亮火柴,在煙霧升騰的后面,李里看見父親瞇著的眼睛,他說起那條河的由來,父親說,它叫“胥河”。知道是哪個“胥”嗎?父親的食指點在桌上,想了想,落不下第一筆,最后說就是“伍子胥”的“胥”。
然而現在李里再問起來,他是什么也不知道了,父親就是在這樣的遺忘中,越來越顯出老態來。
頭頂上的葡萄架子是父親四十來歲時架的,是父親帶回來的外來物,據說是外面的品種,比本地的葡萄更大更甜。葡萄種在院子的南角,置了足有一張床大的地方,不是就地挖的土,而是從外邊鏟了回來自己架高的。那時候父親正當年,和李里如今差不多的年紀。春天里,父親穿著白色背心,用扁擔挑了兩個舊簸籮,一前一后,從田邊運土,一筐一筐倒下,在院里的角落堆成尖尖的小山,用鏟子打平后,又夯土砌磚。李里拿著鏟子,提著一桶水跟在父親后頭,看到他一扭一扭甩著黝黑粗壯的大臂,屁股均勻晃動,那滑稽的樣子——李里在后面哈哈大笑起來,父親不知他在笑什么,在前面罵了幾句,也笑起來。
幾年后李里多大了?應該還在上小學。小學的末尾,他坐在夏天的院子里,頭頂上是綠油油的葡萄葉子,青葡萄膽顫心驚地在陽光下悄悄剔透,陽光穿過葉與葉的罅隙照到庭院的地下。走過時如同置身水底,斑駁的光影如游魚流動,樹影如藻荇交橫,溫柔起伏。他們仰頭,看見明亮的葉子上不時有麻雀飛過的身影,它們走動,小小的爪在竹架上輕輕地試探,發出微弱的“沙沙”聲響。何時鳥頭突然在葉間攢動一下,眨眼間鳥喙已回,那盞葡萄的一只燈泡就熄滅了——一顆剛剛亮起的害羞的葡萄。
于是父親用廢棄的茅草扎了稻草人,讓它戴上那只破綻開來的舊草帽,穿上一件破布衫,藍色的粗布料子,也是父親淘汰的裝束。這只稻草人成日背對陽光,雙手與身體呈一個十字,沉默地抵擋鳥兒的侵襲。
葡萄越來越大,父親每日歸來,放下扁擔與簸籮后,就脫了汗衫,來院里放井水洗臉,喝一海碗涼開水,止了汗,等到尿意上來,解了褲子“唰唰唰”地去墻邊灌溉葡萄樹。
盛夏里他們全家看葡萄成串,上過波多爾液后不久,它們生長得越來越著急,不久就紫里泛青,一串串葡萄擁擠著,越來越沉地吊在了頭頂上。葡萄樹體的枝干不過一拳粗細,竟也支得起滿園的果實。李里緊張又欣喜地仰望,瞇著眼睛挑選。父親赤膊了上身,架著簡易的木梯,叼著煙站在上面,像是一個富有的國王清點臣子的進貢。父親不時歪頭與李里確認,選擇比較,然后才將那把又黑又沉的大剪子伸過去,李里隨著上面人的動作挪移,伸高菜籃……“咔叭”一下,父親利落地剪下一串沉沉的葡萄,彎腰把它們小心地放進籃里。等到菜籃提不起來,李里就以雙手支撐舉高,湊滿一籃子,放到井水里去浸……
如今父親就坐在這滿院的竹架下,在葡萄撤場后的空落落的庭院里,曬著太陽。
它們不知道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枯萎的,李里找不到與此有關的記憶,也許是幾年前,也許是十幾年前,自從父親身體不好就沒人侍弄它了。李里也過了期待葡萄成熟的年齡。母親不是養花養草的人,原先葡萄生長的土壤換上了一簇綠油油的小蔥,頭頂的葡萄藤早已曬干掉光,一陣風過,“咔咔咔……”排排竹架就顫巍巍地在風中冷地哆嗦一下。
父親坐在午后的陽光里,憂心忡忡,又一次說起他的夢來。
那是一個陳年的夢了。
在父親的描述里是個大雪天氣,他用小時候給李里講民間神跡一樣的語氣,帶來冰天雪地中的回聲。父親光著腳往前走著,穿著他那件早已丟失的黑色棉襖,是他冬天賣貨時候用來克風的那件。四野里一個人都沒有。在早晨四五點鐘的光亮里,父親往前方走著,夢里的聲音指引他向東,向東,他就向著太陽升起的方向走著,每一夜,每一場夢,父親在雪地中遠行……尋找那座小廟。
冬日陽光溫暖,然而終究是冬日的陽光,溫吞吞的暖意浮蕩在李里的眼皮上……李里感到困倦,有一搭沒一搭的,他問父親,母親是什么想法?
“隨他去。”她的嗓音仿佛在風雪中遠遠吹來,在他們耳邊擦過。
父親已經決定了,他說,這次叫李里回來也是因為這件事。父親是固執的,他的固執里帶著長途跋涉之后的艱辛疲憊,卷挾著冬日的云霧低低地從遠處的田野掠過。
父親說,我肯定要去那里的。
再考慮考慮吧,李里說,或者再打聽打聽,是不是有什么說法?
父親拒絕說更多了,如果兒子不能陪同,那么他就一個人上路。
李里想了想,半天才說,無論如何,得有個目的地吧。
到了就認得了。父親說完,久久地沉默了。
……
李里側頭看父親時,他已經睡著了,可能夜晚少眠,不足的部分就要由下午來補齊。他的頭發如同貓的胡須,根根驚醒,雪白稀疏,頭皮也開始泛白發粉,像嬰兒皮膚一樣的顏色。父親已經完全是個老人了,老得沒了力氣,沒了精神,只剩下固執,與日俱增的固執。
二
李里是第一次走得這么近看這座橋。下面欄桿是藍色,上面的高架是橙色。它這樣的新鮮時髦,帶著十七八歲的年輕顏色站在這里,對比兩邊河岸破落的舊房子,像個完全的外來者。是哪個粗心的城市孩子遺漏在此的一塊積木也說不定,舊河道提心吊膽地戴著這個巨大的不屬于自己的帽子,別別扭扭地站在了這里。
李里點了支煙。
晚上十點多鐘,鄉里家家戶戶早已閉門不出了。路燈只亮了幾盞,又被行道樹的影子擋下不少,照不亮半條街,遠遠看去,一陣亮,一陣暗,紗帳一樣的昏黃后面是無限的黑暗……只有橋上是全亮的,可能是新建的緣故,橋墩向上打著燈,穿過了漫漫的黑夜,筆直地向上擴散,與高架邊緣向下探照的燈光穿插,一來一回的黃色光芒中,擦出些繾綣的意味,連浮蕩的灰塵都清晰可見。然而河面是黑的,更遠處,黑水像鐵一樣凝住了。只能看見橋墩上鋼的骨架被光凜冽擦過,縱橫交錯,疏疏朗朗,看得人發冷。
原先那座石橋又短又粗笨,但也知道在底下一邊各辟出一個橋洞來,方便叫花子在洞里安家。夏天洞口拉上了舊粉花的簾子,一到晚上,里面就透出燭火的亮光,等到冬天,藍色的被褥取代原先的薄布,抵擋風口,堵得嚴嚴實實,只看到影子。每當李里上學下學,總要看看橋洞的裝飾,簾子換過幾次,卻從沒看見過里面的樣子……
楊梨就是在那座石橋上走過來的。她是一個漂亮如狐貍般的女孩,有狐貍一樣的眼睛,狐貍一樣的嬌媚,狐貍一樣的神秘……然而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是小學時候了,李里想如果再見到,他可能都認不出她了。
當晚楊梨如狐貍一般鉆入他的夢境,醒來后除了舊時學校的窗戶輪廓與黑板陰影模糊的浮現,李里什么也不記得了。他只感覺到暖暖的,夢境里,他們似乎是相愛的。
家里的老座鐘“鐺—鐺—鐺—鐺—”地劃亮黑暗,四點的鐘聲奄奄沉沒下去后,母親中斷的呼嚕聲又躍躍欲試地拉響了。母親說自己是個從不做夢的人,李里從小到大,確實也從未聽她說過做了什么夢。對母親而言夢境這種東西不存在,睡眠就是上下眼皮閉合,夜夜鼾聲,頁頁空白,醒了就醒了,干脆明亮。而父親的夢是忙碌的,父親的夢境中有無窮無盡的囈語,李里留心聽了會兒,竊竊如耳旁風,像是某種失傳已久的方言,父親就是用這種方言和夢中人長長地交談著,打聽詢問著他要去的目的地。
李里在半睡半醒之中,輾轉反側,他已經很久不和父母同睡一室了。與圓子分床后,李里總是一個人睡,他慣常失眠,一到深夜,就像赤身裸體睡在時間的防空洞中,嬰兒一樣蜷縮著身體,時間的風吹徹在頭頂,他總覺得冷。如今回到少年時自己的這張小床上,罕有的,在覆蓋著時間的香灰之下,他找到一點余溫。李里一動不動地儲藏著這難得的溫暖,他想這或許是關于楊梨的夢境帶來的。
許久不見了,將近四十,她應該早已結婚生子。李里依據不多的一點記憶拼湊出一個成年的楊梨,他在父母起床之前的一個小時里竭力虛構出一個與她有關的假想。她為他出軌了,他在某間窗簾緊閉的房間之中覆在她的身體上,他試圖與她對視,可是這么多年,他早已忘了她的長相了,他從來也沒敢認真看過她的眼睛。她會伸出一只手蒙住他的視線吧。李里把手蓋在眉毛與鼻尖,眼皮在溫暖的黑暗中顫動著,他放輕了呼吸,將這想象進行了許多次,許多次……但無論如何,他的身體像是一座死火山,一點反應沒有。
當鐘聲在疲倦之中敲響五下時,清晨降臨了,沒一會兒,他聽見母親在黑暗中打了一個好大的哈欠,拖著睡眠的尾巴,她摩挲著從暖烘烘的被窩里坐起來,窸窸窣窣地穿衣服,一件一件。父親不久也醒了,他一醒就要夠床底下的痰盂,李里等待了好一會兒,才聽見父親的喉間輕微地顫動一陣,像是小小的一聲埋怨,“呸——”他吐了一口痰。
父親的聲音浸透了早晨藍色的靜默,霧靄沉沉,今天是個雨天。
“因為是雨天,所以晚上走路走得很吃苦,挑著擔子跑了半天,發現在原地打轉。”父親與李里坐在堂前,兩人看著紗窗外的雨,風來一陣,雨就細細密密地被吹落一陣。
雨天沒法出行,一出去就是泥濘,飛蟲一樣的小雨落在人臉上,濕濕的睫毛,模糊的視線……如果要走,也等一個晴天再走,大概是哪里知道嗎?
往南京?蕪湖?郎溪?宜興?還是往哪里?總要有個地方吧?
都不是,在東邊,看到了就知道怎么走了。
父親抱著暖水袋,看著屋外陰雨的天空,他的目光好像已經丈量了雪地,赤腳走在干凈冰涼的白色大地上,四野空無一人。
母親去打麻將了,李里一時沉默,家里靜悄悄的,有貓在屋頂爬過,瓦聲輕動。臥房里老舊的鐘聲敲響在父親的腳下,“鐺——”是半點的鐘聲,意猶未盡的暫歇,在這震蕩里他看見父親一步一步,在雪地中越走越遠。
母親直到四點才回來。她打了一把巨大的花格子傘,喜笑顏開,這是在南邊贏了錢的表示。她胖胖的身體在積水的院子里跑過,腳尖一顛一顛快跑了幾步后,母親氣喘吁吁地走到廊下,甩一甩傘面,讓它花朵一樣開在地上,拍拍身上的雨珠,走進來,母親說:“我聽人講了一座寺。”
她聽人講了一座寺。
建在橋的南邊……
她是在棋牌室聽說的。她把父親的夢與頹然歸于迷信,她們打麻將的人那里有太多這樣的例子,母親舉了幾個他們知道的人名。之后比起遠行,李里覺得這是更方便可行的,他們問父親的意見。他這一輩子跑遍各鄉,聽說了太多稀奇古怪的故事,這些故事早已流進他的血液成為骨肉,他永遠是寧可信其有的。
三
清晨五點鐘,李里開車打橋上過。
在這座巨大的橋架下,鋼管平行斜出,根根豎立,紛紛亂亂,向擋風玻璃傾軋下來。
父親坐在后排,循著以前的習慣,他的肩上挑著兩簸籮滿滿的記憶,它們太重了,沉沉地壓得他開不了口。母親同樣在后面,她要歡快得多,嘰嘰喳喳地說個沒完,她向李里提前透露她要許的愿望,一二三四,條分縷析,最重要的是希望李里的妻子——圓子,早點生孩子,上天保佑,一個大胖小子,那她就什么也不用煩啦。
李里沒有打斷她的這些幻想。
他覺得自己是不被那些愿望所容納的,神、佛、菩薩,容納不了他,在他的世界里沒有,他不信,也不能相信。關于這一類的印象,于李里,是陰影一樣的存在,是十五歲那個冬天的早晨,是腳下這條路,是在一年一次“出菩薩”的早晨,同樣是他因為夢見楊梨而遺精的早晨,是他站在請神的隊伍中揮動旗桿的清晨,楊梨站在他的身邊。
隊伍里有中年男女,也有像他們一樣的青年男女,不論年紀,臉上都搽了紅紅的胭脂和口紅,個個舉著高高的彩旗,懷著對以后人生順利的愿望加入進來。從他們鄉出發,途徑周圍各鄉,熱熱鬧鬧地迎神送神。
“嗚哩啦嗚哩啦”,嗩吶吹成的調子起頭,“慶慶嗆,慶慶嗆”的鈸聲躍躍欲試地終于打起來了,樂器的震顫聲音隨著紛亂的步伐,在擁擠的人群中流水一樣地滾動起來,兩邊圍的都是人。喜氣洋洋的笑臉簇擁著這支又長又窄的鮮艷隊伍,那歡鬧的人聲與音樂一樣,也與隊伍里男女腰間的腰帶一樣,綠得耀眼,紅得綺麗。
人們的腦袋一排排傳遞向后轉看,遠遠地,看見遠處鏤空的小轎子過來了,由兒童扮成的“菩薩”化了唱戲一樣的濃妝,目不斜視,看著前方。轎子下面,四位穿著黃衫黃褲,頭上戴著滾紅邊黃緞帽的漢子,“呦呵,呦呵”地喊著口號,顛著轎子往前走,后面盛裝的隊伍慢慢地跟了上去。
李里的眼前掠過兩邊各色的面孔,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拍巴掌的,大聲喊話的,舉著小孩的,劃火柴點煙的……
他被音樂與熱鬧還有青春期的躁動所鼓動,有那樣多的話呼之欲出,蓬勃旺盛,而楊梨是那樣難以取悅,為了逗得她的一點笑,他就大放厥詞,調侃隊伍中的人,路邊的人,滑稽的裝束,最后他嘲笑神……他說了那么多的字與標點,咽了那么多的唾沫,口干舌燥,楊梨才勉強轉頭對他笑一笑。后來他把自己和她都說累了,等到周圍村落全部繞遍,回到鄉里,他筋疲力盡地看楊梨回到她母親身邊的時候,后面的中年男人意味深長地告誡他說:你講了那么多不敬的話,是要被責罰的。
你會被責罰的。
李里就是在那一刻感到自己落入了人生的詛咒,他在長久的絮叨之后感到對自我的厭煩,這種厭煩讓他感到這天是楊梨在他生命里設下的一個埋伏,比起被神詛咒,他更覺得是被楊梨詛咒了。多年后,他已想不起楊梨的長相,卻還是能夠清楚記得那年那人的那張臉,又黑又瘦,一張干巴的男人的小臉,意味深長地洞穿了他的從前與未來。這張臉后來與為他診斷的男科醫生高度重合,他也是這樣意味深長地向他宣告他的“性功能障礙”,他在那一刻久違地想起多年以前。原來暗示早已埋伏于此。
什么寺要建在島上?
如煙如霧,人們看見蒙蒙細雨中的小島,都放低了聲音,等遠遠劃來的小船。
父親在冷風中任由雨絲飄落,他抱著這一天都要寡言的固執等待著,生怕有誰驚擾了這層結界。母親早早與旁邊的婦女聊起天來,她們用交換秘密一樣的聲音交換愿望。
李里與母親一同將父親扶上了船,加上船家,湊齊了九個人才慢悠悠地向島上劃去。天上的小雨細如灰塵,李里撐傘遮住自己與父親,而母親自己遮一把。船上的人都如同考試臨近的學生一般靜默。只有兩個青年男女小聲地說:“這船不要錢倒是挺好。”被船家聽見了,喜氣洋洋地說:“渡有緣人吶……”
于是在這雨絲飄打的河面,一船人像是成了諾亞方舟上的幸存者,都默默裹緊了身體里的溫暖與心愿。不過五分鐘,他們一個扶一個小心翼翼地下船。
“諾亞”開口:看著給船費,不論多少,全看心意。
有人給五塊,有人給十塊,李里給了二十。
“去吧!”母親勸李里,“來都來了,進去拜拜。”
李里攙著父親跨進了門檻。
寺是新建的,毫無疑問,還有重重的新漆味道。畫棟飛甍,一切仿古,刷成朱紅色,扁扁的一大間,中間開著大口,一進去就是神像。他們遵照僧人的指示,先磕頭,再去旁邊一間封閉的小屋里請愿。人是要一個個進的,堂廳里如考場一樣安靜。磕完了頭的人就靜靜地站在小屋門口排隊。到父親時,他以一種虔誠的神態阻止了母親的攙扶,也不要李里的陪伴,自己進去了。之后是母親。
輪到李里時,他掀開簾子一看,里面端坐著一個中年男人,穿著藍色羽絨服,戴著老花鏡,見有人進來就一臉嚴肅地放下手機,口中默念了一句什么,然后遞給李里一個本子,讓他照著前面人寫的抄。李里拿起筆,看到父親端端正正的名字下面,是母親歪歪扭扭的名字,他跟著寫了名字,后頭又畫上了100 的字樣。
“一百元。”男人說完,從底下掏出一個透明的錢箱,里面已有不少紅色的鈔票,“或者微信支付寶也可以。”錢箱上貼著一綠一藍兩個二維碼。
“必須要給嗎?”
“不能騙佛的啊。”男人頭也不抬,拿起手機。
李里出去了。
除了他,父母都交了一百,這讓他有點惱火,想到一些忌諱,終究又閉了嘴。
母親倒是樂觀,她安慰李里,也安慰自己,求個心安,哪里還不花這兩個錢?
父親盡管覺得上了當,卻再沒說什么。回去之后他就小病了一場,他這兩年本來就纏綿病榻,母親不以為奇,她是強壯有力的,她有那樣令人羨慕的精力,上午洗衣服做飯,下午打麻將,晚上看電視,夜里鼾聲震天。
雨下了三天,父親就病了三天,因為頭昏與夢境的雙重折磨,他在夜里發出低低的嘆息。
李里走不掉,他在電話里對圓子說,再等等吧,或者鑰匙我先快遞給你?
圓子知道他心情不佳,于是也沒打電話再來催。
父親躺在床上,李里在房間里陪著,他尊重父親的節儉,燈總是關著。房間里的木門,米缸,電視,床,木桌,板凳,座鐘,拖鞋,窗架,插銷……在灰暗中拖著長而潮濕的影子,它們來自多年以前,有的是父親賣不掉的陳貨,有的是父親在進貨那里帶回來的處理品。一樣一樣,一點一點,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拼湊出了家的輪廓。
父親那兩只裝小百貨的大簸籮至今吊在臥室屋頂的吊鉤上,從前里面放了木梳、紐扣、歪歪油、頂針、魚鉤、紅手絹……為了不落灰塵,晚上父親回來后,總是用兩塊粗布小心地蓋在上面。旁邊放著褐色的磨得發亮的扁擔,它的中間有個大大的黑色斑點,輕微地拱起,像是一個臉上有著胎記的丑陋老人,默不吱聲地靠在墻角。天還未亮,李里起床刷牙時,它已經隨著父親出去了。而今兩只簸籮還在等待主人隨時將它們解放下來,一前一后地把它們掛在扁擔兩邊,穿透晨霧,從清晨出發。
里面早已空空如也,李里看看它們,又看看房間的各個角落,他沒有看到那個老扁擔。
父親在專心聽外面的雨聲,秒針“咔嚓,咔嚓”地擦動著小小的步伐,一個鐘好長,分成六十個分,拆成三千六百個秒,三千六百個“咔嚓”。
母親在外面廚房叮叮當當地拿缸子,擇菜,煮飯,切肉,往燒熱的油鍋里倒油——“嘩啦”一聲,世界喧騰,濕漉漉的炊煙在雨中裊裊散開。
父親渾然不覺。
飯桌上母親問李里:這兩天生意忙嗎?圓子一個人顧得過來嗎?
那間賣二手手機的店鋪歸了圓子,離婚協議書已簽,接下來他和圓子要分房子,分車子,分財產,清點許多東西,幸好沒有孩子,倒也省事。李里面對這些無窮無盡的煩惱說:“城里的生意不打算做了。”
父親的目光落在李里的肩膀上,半天沒有說話,只是用鼻子輕輕地呼了口氣出來。
四
李里是在橋上遇見楊梨的。
開始的時候他還沒認出來,因為長相大不同了。
她胖了好幾圈,穿了一件鵝黃色的收身羽絨服,腰間的肉一圈兩圈地鼓囊出來,她雙手插在衣服口袋里,兩邊臉頰被太陽曬得通紅,雖然臉胖了很多,年輕時尖纖的下巴也圓潤了,但那種漂亮女人才有的,眼角上揚時漫不經心的風流神態還是讓他認出了她。
李里當時正從橋的南邊過來,為了把房子鑰匙快遞給圓子。回來走到橋中間的時候,他就看見了胖女人楊梨。她正在用家鄉話和人寒暄,旁邊站著個不耐煩的男孩子,高高瘦瘦的,后來他猜是她的兒子,因為面孔,尤其是眼睛,雙眼皮一模一樣。
李里原本應該像自己少年時那樣故意在旁邊磨蹭一會,但是他沒有來得及。因為直到十米開外了他才反應過來那人是楊梨。
畢竟是將近新年了,雖然不是逢著會場,但一日一日,街上漸漸熱鬧起來,去了外鄉的人回來后先上街,本地人為置辦飯菜也要上街。街上的小攤販抓住這一年一度的商機,賣春聯、賣炸串、賣綠植、賣棉花糖……什么都賣。人們哪怕什么都不買也樂得逛一逛,上一次街,要遇見多少個熟人,誰碰著誰都像是碰見一個驚喜。李里轉了轉,最終買了幾張“福”字和對聯回去。對比以往的價格,他覺得肯定是買貴了。
春聯父親以前是賣過的,就在他們鄉里,父親在街上擺了一個小攤,賣對子和“福”字。李里正值少年,從鎮上中學放假回來,就要在街頭看店,不是怕有人偷,是因為聯子輕,要用磚頭磕,用夾子夾,一不小心就會被吹上街去,他要跑著撿回來。不停有同學認出李里,小學的,中學的,遠遠地對他笑一笑,或者走近了打個招呼。人家的目光在一地的紅色春聯中檢閱過去,父親看他們打招呼,知道是他的同學,就沖對方笑笑。李里覺得很難為情。
不忙的時候,父親給李里錢買東西吃,或者勸他去街上逛一逛;忙的時候就顧不上了,他會嫌李里找錢太慢,拿錯了東西,踩到了紅紙。罵得多了,李里就沉著臉坐在凳上,人家問他對子多少錢,他故意一聲不吭。母親在飯館里幫廚忙碌,等到下午兩三鐘客人少了,才匆匆給他們送來飯菜,他和父親把三只溫熱的鐵缸子湊在小矮凳上,一人捧一個碗,把菜夾到碗里就著米飯往嘴里塞,他們和冷風比速度,慢一點飯菜就要涼。肚子茫然,前一刻還餓得咕咕叫,下一刻就被脹得滾圓。要是有人此時來問價可太不識數,父親放下碗給人拿春聯收錢的工夫,飯菜就涼透了,冰冷的飯菜吃下去口舌一顫,喉管冰涼,不管不顧吞到肚子里,成了個冷疙瘩。
父親后來說,他的胃就是這樣吃壞的。
李里等母親從棋牌室出來,兩人一起往家走。母親不斷地遇見熟人,和人招呼,讓他叫人,回答他們自己在城里的活計與經營,是男人的話還要發煙。關于父親在街頭賣貨的記憶一次次浮現,一次次地被打斷,最終被拋在身后。
李里回頭看看,人群中早已沒有楊梨的身影。
父親并沒有因為新年的臨近而振奮,他竭力讓自己靠著枕頭從床上坐起來。隔壁人家的親戚不時造訪,來到院里七嘴八舌聊天,吃瓜子。這些閑談和冬日爐火一樣,暖烘烘地洋溢在即將到來的節日氣氛中。父親也流露出對這種熱鬧的向往,隔了一堵墻,這七個八個他認識與不認識的人,為他帶來遠方大雪的消息。偶爾外面也傳來母親的聲音,幾個女人聚在一起聊天,哈哈大笑。
隔壁院里沒有人的時候,李里的家也就空曠起來,尤其周邊人家喊吃飯,喧鬧的聲音從堂前溢出,紅燒雞的香味飄散到他家的時候,寂寞就更加具體而全面地降臨。母親是毫無所知的,不外出的時候,她就在院里坐著,不同于父親對大雪的等待,她享受著冬日的溫暖。
“暖冬真好啊!”她的身體在陽光下漸漸熱乎起來。罩褂子脫了,棉襖也脫了,不敢再脫毛線衣,然而她說腿熱得直癢,又把棉毛褲推到小腿以上,大冷天的,胖乎乎的腿上起了白白的屑。
李里看得一冷。
父親搖搖頭。
“嘶哈——”母親撓著自己的腿,陽光下白色的皮屑在空氣里慢慢揚起來,如同小小的雪,和灰塵一起,漂浮在空氣中,久久不下沉。
父親不說話,雙手放在腿上,脊背微微駝著,看得出了神。李里想,楊梨是不是也會這樣?當她老的時候,她也會像他的母親一樣,邋遢地當著自己兒子的面把腿抓出一道道白色的痕跡,像打了一層痱子粉似的。
他在久久的怔忡之中問自己,如果他成為楊梨的丈夫,他會情愿和她在此共度一生嗎?在腳下的土地上,和一個胖胖的,早已沒有過去風韻的楊梨,這樣的一個楊梨……他不知道為何,想與她在此共度余生。
五
李里夢見了橋。
一座奇怪的橋,他跑到外面一看,這座橋好像列車的軌道,在空中劃了一個大大的弧形。每隔五百多米,也許一千多米,就有一個UFO 一樣的銀白色圓盤漂浮在空中,這道弧線過山車一樣地向遠處蔓延去,圓盤在每個圓弧的頂端出現。他又跑到橋下,感覺奇怪而茫然。
醒來他嗅出晴天才有的清冷味道,幽藍而新鮮,他睜開眼睛,在母親熟悉的呼嚕聲中,在聲音低伏的片刻里,他辨出父親吃力的喘息聲。他不可避免地預感到父親又一次聽受著遠方的召喚,在空無一人的凌晨,在大雪鋪就的路上,氣喘吁吁地向遠處跋涉,尋找他說的那座廟。
醒來,父親果然又說起夢里的雪。
“也許是心理作用”,他說。
也許是迷信,母親說她去找了算命的。
懸而未決。
恢復了一些體力,父親又一次坐在了陽光里。
“等你的身體再好一些吧”,李里說,“等你身體再好一些我帶你出去。”
父親急不可耐但無可奈何,冬日即將過去,天氣預報里說,今年南方部分地區可能無降雪天氣,而春天快要降臨。在后面的日子里,母親計劃了去南邊,去遠親家吃喜酒,去城里看燈會……那些熱鬧的事情擁擠著排列在后面,一眼望不到邊。
次日他與父親四點多就出發了。凌晨四點多的田野,李里許多年不見了,而今就在道路兩旁,被風拉扯模糊,向后倒退。路上幾乎沒有車,因為怕錯過路口,李里開得不快,冬天的田野光禿禿的,悄悄準備著即將到來的春天。
感覺并未開很久,至于某一處時父親讓他停車。接下來的路不便開車,一路的泥沙,崎嶇不平,兩邊樹干兇狠地伸出枯死的枝杈。李里把車停在路邊,扶著父親下了車。父親因為久不出門,又長期吃素,走不了百米就要停下來在路邊坐一坐。李里站在旁邊點了支煙抽,天空還是暗的,但已有漸漸明朗之勢。父親一起身,李里就去扶他。但走了不過百米,父親又低頭找一找,找個地方坐下來,他說:“等一等啊,歇一歇。”
早晨的風,從田野深處路過田壟,拂過水面,掠過樹杈與荒草,吹拂過來,帶來茅草與大地的味道,新冷的空氣順著胸腔把五臟六腑都搜刮了一遍,帶走身體好不容易儲藏的一點薄溫。在風聲與草聲中,李里看見父親的脊背低低地聳起,又輕輕地落下。父親像是跑了許久許久了,才這樣劇烈地喘氣,然而放眼望去,田野是如此的枯燥,殘酷地重復著,一片片,連接著一模一樣的草野,向遙遠的盡頭延伸推進。李里瞇著眼睛,只能看見毛絨絨的藍色地平線,遙遠的,無論如何也走不到的地平線,而太陽即將升起。
等他們走到天空徹底亮了,李里回頭望去,只覺得觸目,他一眼就能看見來時的那條路,甚至他那輛黑色大眾也能清楚看見。它平靜而無聲地等待著他們。
“回去吧!”他對父親說,“一大早,也沒吃飯。”
父親不作聲。
他又問:“路對嗎?”
父親不如先前那樣篤定了,他抬起渾濁的眼睛望著這片草野,茫然如孩童,很久之后他說:“不對嘛,怎么走到楊家圩來了……”他的視線在空曠的田野上晃來晃去,目光之所及好像他已經全部用腳步丈量與踩踏過。
他說,和夢里不一樣,沒有下雪,認不清路。
最后他們用了雙倍的時間又走回車上。李里提出背著他走,父親開始不肯,后來就不由他肯不肯了。背上的人干瘦,分量全壓上來也不感覺到沉,好像只有可憐的一點點。李里沒有背過小孩子,但他感覺自己現在就背了一個小孩子,輕飄飄的,到車邊他把父親放下的時候,他感覺父親又瘦小了一些。
“等雪天吧!等下雪了再說。”李里對父親說。
父親沉默。這場雪遙遠得看不到跡象。
已經午后,回去的路上父親默默向外看,行駛間李里仿佛回到了小時候,他唯一與父親出門賣貨的那一次。午后,他跟在他后面,在一個陌生村子的巷子里七拐八拐,巷頭巷尾響徹著父親吆喝賣東西的聲音:“梳子啊,剪刀啊,收頭發啊……”陽光熱辣,生意寥落,偶爾有人路過。父親在這里坐了一陣,等了一陣,又繞了一陣,一毛錢沒有賺到手……那一次,回去路上,父親也是這樣的沉默。
李里加快速度,腳踩油門,一路飛馳往家里開。
到家時候已經過了中午,家中照例沒有人,空落落的院子,空落落的堂前,他們坐在家里吃備好的午飯。
父親面前兩碟菜,一碟素油青菜,一碟腌菜豆腐,他早已習慣,懷著一顆失落的心,吃得很仔細。
李里以前看電視,古裝劇里演到最后,總有人要出家的。有女人剪了頭發說要做姑子,也有男人剃頭說要做和尚,三千煩惱絲,仿佛一入佛門,人不生不死,又亦生亦死,成為了第三種狀態。他那時覺得索然,以為人一出家總會給故事留下些空曠的余味,好像這個人既沒有死,但與生的關系也不大了。
那個時候,他不知道父親有一天也要走上這樣一條路。
下午兩點鐘,鐘聲回蕩于堂前,父親就這樣默默地坐在李里身邊,茫然看著門外,在分分秒秒地老去。他們因思想不同生生分出兩個空間,各自被迎面而來的風暴吹襲。但父親并不知曉,或者知曉了也不作聲,他就在轟轟隆隆的波輪洗衣機的聲音里,轟轟隆隆地被時間敲打。李里不知看向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