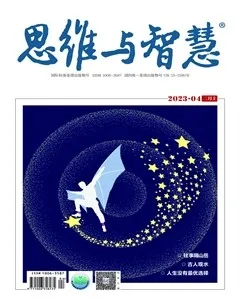近物遠逝
章銅勝

已經是雨涼風冷了。傍晚坐在車上,看見西邊遠遠的天空中,云層變得薄了一些,散了一些。此時,有陽光照在稀薄的云層之上,現出一些明黃、玫瑰金、深紅和暗紅的顏色,它們雖然不及夏日里滿天晚霞的絢爛,但在那一刻,我還是明顯感覺到了一些溫暖的東西。我知道它們不能給我真正的溫暖,但它們還是能讓我感受到一點點暖意。那一點暖意,在一場長雨中彌足珍貴。傍晚雨后驚現的那一點霞彩,只在倏忽之間,我看見它們在天空中出現,也看見它們旋即消失不見了。
剛剛還近在眼前的晚霞,在遼闊無邊的鉛云中忽然就隱身不見了。就像一股細細的溪流匯入海洋般,消失不見了,也像夏日里我在長江邊看過很多次的晚霞一樣,此刻在我的記憶里,已經難以再現了。讀白居易《簡簡吟》的末尾一句“大多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時,雖然憐惜蘇家小女簡簡的命運,但感覺還不是太強烈。及至讀到楊絳寫的《我們仨》,讀到“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時,忽然就有了無語凝噎的傷感。夏日絢爛的晚霞,眼前秋雨后的一抹霞彩,都是世間好物,都是容易消逝不見的。
在秋天,如果氣溫稍高一些,我們總能見到一些錯季而開的花,常見的如櫻花、桃花、玉蘭、海棠、牡丹等等。秋天錯開的花,花不多,數朵數枝而已,花期也很短,大概只有幾天的時間。那些花,在一場冷風冷雨中便飄零不見了。每次看見錯季而開的花,我都會站在那兒看看它們,總覺得它們是有些猶疑的,沒有春日里花開得大膽熱烈,大概自己也是知道開錯了季節。錯開的花,近在眼前,卻很快便消逝不見了,仿佛不曾來過,或者只是錯誤地推開了一扇時間之門旋即又將它關上了一樣,再也難以見到了。
錯開的花如此,那些應季而開的花呢?每年春天,很多人都是留意花開的,一有時間,便會特意去看各種花開。春天的花真是多,二十四番花信風,是無法表述春天紛繁花開的熱鬧的,幾乎沒有人會對春天的花開有免疫力。可是,每年春天,我們看過多少花,誰又能記得清楚呢?而我們依然會在春天里,趕著去看各種各樣的花開,喜歡各種花開放時的顏色、吐露的芳香,喜歡萬物復蘇的那種欣欣向榮。對于每一季花開經眼的驚艷,最終都只留給我們或深或淺的一些記憶。大多數時候,記憶都是不太可靠的東西,是根據我們的需要和喜好,被選擇、被拼接、被定義的印象混合體,即使如此,在更多的時候,我們也是善于淡忘的。我們在春天里看過的花,曾經觸手可及,我們聞著花香,漫步花間,陶醉著幸福著,而花是會謝的。花謝之后,我們在感覺清閑的時間里,還會想起它們嗎?事實上,那些我們看過的花,在某一刻,已經從我們的生活中消逝了,雖然它們可能還會等待下一次與我們的相遇,而此刻的消逝,依然會有一種落寞與傷感,是花,也會是我們。
這段時間,我在等待一樹銀杏的葉黃時刻,這是我在一年中少有的虔誠,虔誠地仰望一棵樹的輝煌。那棵葉子黃了的銀杏,是我眼前的近物,雖然我知道黃葉易落,也易于在一場風雨里零落成泥,消逝不見,但我依然會去看它們。雖然它們會在時光中遠逝,可它們仍是我曾經那樣喜愛的眼前之物,就那樣驚艷了時光,驚艷了我們仰望它的目光,也許這就足夠了。
博爾赫斯在《失明》一文中,引用了歌德描寫晚霞的一句詩:“一切近的東西都將遠去。”他說:“歌德也許不僅僅指晚霞,也指人生。一切都在漸漸遠離我們。”“傍晚,離我們很近的東西已經離開我們的眼睛,就像視覺世界離開了我的眼睛一樣,也許是永遠。”“盲人能感覺到周圍人的熱心。人們對盲人也總是抱有善意。”此時,已經接近失明的博爾赫斯,仍用樂觀積極的態度回應了我們,近物遠逝,并不意味著失去了所有的美好,而是給我們開啟了另一種可能,另一種感受美好的工具。
(編輯 兔咪/圖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