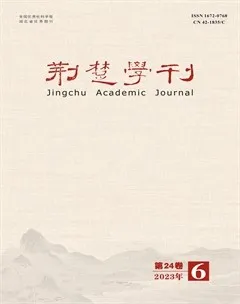電影氣氛的發(fā)生學(xué)與存在論
王 超
(鄭州大學(xué) 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河南 鄭州 450001)
無(wú)論在電影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 抑或是在對(duì)電影作品的評(píng)價(jià)中,電影氣氛都被廣泛運(yùn)用。 作為觀眾,我們?cè)谟^看電影的過(guò)程中可以感受到電影氣氛的縈繞。 這種縈繞著的氣氛往往呈現(xiàn)為無(wú)特定方位的、 全感官的感染。 特別是在自己情緒與電影所傳遞的情緒不同時(shí), 這種感覺(jué)會(huì)尤其明顯。 例如一名觀眾情緒悲傷時(shí),走進(jìn)影院觀看一部喜劇電影, 開(kāi)始會(huì)感覺(jué)到自身的情緒與影院的氣氛格格不入,但逐漸被周?chē)鷱浡臍g樂(lè)氣氛包圍和感染,這種似乎無(wú)形無(wú)質(zhì)的氣氛如霧一樣彌散開(kāi)來(lái),像浪潮一般一陣一陣地侵襲觀眾的身體, 改變著觀眾的情緒。 不同導(dǎo)演的作品帶給觀眾的氣氛體驗(yàn)通常不盡相同。 而同一位導(dǎo)演的不同電影作品,呈現(xiàn)的氣氛特征往往具有某種一致性,例如小津安二郎電影的沉靜哀愁氣氛, 希區(qū)柯克電影的懸疑氣氛, 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電影的詩(shī)意氣氛,阿彼察邦·韋拉斯哈古電影的神秘氣氛。 導(dǎo)演的作品獨(dú)特的氣氛, 和他們獨(dú)特的鏡頭語(yǔ)言或內(nèi)容層面的個(gè)性標(biāo)簽一樣,成為該導(dǎo)演的標(biāo)志性特征,甚至是其作者性的代表。 通常在類型電影的劃分中,諸如恐怖片、驚悚片、懸疑片、文藝片、溫情片、合家歡電影等類型, 也是著重從此類電影的氣氛進(jìn)行描述和界定的。
導(dǎo)演鄭正秋在1926 年的《導(dǎo)演〈小情人〉之經(jīng)驗(yàn)(續(xù))》中就談到了空氣,而他的創(chuàng)作觀念正是“使人人‘同化’在我一個(gè)空氣里”[1],此后費(fèi)穆的《略談“空氣”》一文更是知名。 早期電影人的實(shí)踐和闡釋讓“空氣”“氛圍氣”“氛圍”“氣氛”成為具有民族特色和實(shí)踐指導(dǎo)意義的理論概念,堪稱“建立在中國(guó)影人固有的宇宙觀和生命意識(shí)之上, 在主體覺(jué)醒和整體觀照的層面生發(fā)出來(lái)的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國(guó)電影理論”[2],是當(dāng)今建構(gòu)中國(guó)電影學(xué)派寶貴的理論資源。近幾年,隨著西方美學(xué)“氣氛”概念的譯介和流行,“電影氣氛”重新進(jìn)入學(xué)界視野,然而在討論中尚缺少?gòu)拇嬖谡撘饬x探討電影氣氛的發(fā)生和概念的研究,所以,本文試圖從這一角度討論電影氣氛的發(fā)生和觀眾感知。
一、從氣氛到電影氣氛
觀眾的直覺(jué)很容易感受到電影氣氛的存在,但難以準(zhǔn)確定位氣氛的來(lái)源, 甚至有時(shí)只能感知到朦朧的電影氣氛, 無(wú)法清晰地識(shí)別和分析電影氣氛的本體。 電影氣氛和電影的畫(huà)面有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但它并不是畫(huà)面本身。電影聲音也對(duì)氣氛的建構(gòu)起到直接影響,可也不能將二者等同。這導(dǎo)致我們雖然常常談?wù)摎夥眨?但我們并不清楚這個(gè)氣氛究竟是什么,在哪里。大多時(shí)候,面對(duì)同樣的電影,觀眾知覺(jué)到的氣氛是相同或相近的, 但確實(shí)存在一些情況,觀眾面對(duì)同樣的作品,知覺(jué)到的氣氛卻大不相同。例如小津安二郎的電影作品《秋刀魚(yú)之味》(1962),電影開(kāi)場(chǎng)的前三個(gè)鏡頭,自然光線充足,音樂(lè)明朗舒緩,以固定機(jī)位拍攝了工廠一排高大、紅白相間的煙囪和升騰的白色煙霧。從導(dǎo)演的用意和當(dāng)時(shí)日本觀眾的感知來(lái)看, 電影表現(xiàn)的是日常化的工作背景,電影氣氛清新明媚。而在今天的觀眾看來(lái),這組鏡頭的氣氛則略顯怪異,因?yàn)楣饩€和音樂(lè)雖然暗示了導(dǎo)演積極正面的態(tài)度, 但畫(huà)面內(nèi)容里的煙囪和煙霧很難觸發(fā)我們美的感受,直觀上給我們的感覺(jué)是污染和霧霾。 如此矛盾發(fā)生的原因在于社會(huì)的發(fā)展變遷已經(jīng)使得觀眾的審美心態(tài)發(fā)生了改變。該片誕生于六十年代初,彼時(shí)環(huán)境問(wèn)題尚未凸顯, 而日本正在經(jīng)歷著二戰(zhàn)后的經(jīng)濟(jì)騰飛,綜合國(guó)力迅速發(fā)展。 小津電影里工廠、煙囪、 火車(chē)、 車(chē)站這些常用的意象是工業(yè)化的代表, 對(duì)于戰(zhàn)敗后迫切希望看到工業(yè)化進(jìn)程的日本民眾來(lái)說(shuō), 蘊(yùn)含著美和希望。 今天社會(huì)背景已然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人類社會(huì)正由信息化向智能化轉(zhuǎn)變, 煙囪象征的工業(yè)化水平非但不再是先進(jìn)生產(chǎn)力的代表,反而給人以落后、污染的印象,讓人直覺(jué)里產(chǎn)生抗拒。
需要說(shuō)明的是, 無(wú)論是六十年代的日本觀眾還是今天的觀眾, 他們截然不同的氣氛體驗(yàn)都是伴隨著各自觀影自然而然地發(fā)生的, 也許并沒(méi)有理性的反思介入,而只是他們真實(shí)的、下意識(shí)的反映。這說(shuō)明在客體化的電影之外,社會(huì)背景與觀眾的審美心理也對(duì)電影氣氛產(chǎn)生重要影響。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伊文思的電影《橋》(1928)中表現(xiàn)了橋上行駛的火車(chē)和橋下交織的輪船散發(fā)的滾滾濃煙,以及巨大鋼筋構(gòu)成的橋,讓·維果的《尼斯印象》(1930) 最后一組鏡頭中反復(fù)出現(xiàn)高聳的煙囪和繚繞的煙霧, 這些早期電影在今天看來(lái)依然精彩動(dòng)人, 但社會(huì)文化語(yǔ)境的變遷會(huì)影響這部分鏡頭給觀眾帶來(lái)的氣氛。
由這些案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電影氣氛既受電影內(nèi)容的影響,也受觀眾主觀因素的制約,兼具著主觀和客觀的性質(zhì)。 在格諾特·波默對(duì)氣氛的詮釋中,氣氛這種“介于主客之間的、獨(dú)特的居間位置”[3]16的特性得到了特別的強(qiáng)調(diào)。 波默在生態(tài)美學(xué)的研究中, 在新現(xiàn)象學(xué)家赫爾曼·施密茨、精神病學(xué)專家胡伯特·特倫巴赫和哲學(xué)家伊麗莎白·施特勒克等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引入了氣氛這一概念。 在西方語(yǔ)境中,“氣氛”(Atmosph?re)概念起初來(lái)源于氣象學(xué)術(shù)語(yǔ),意為大氣層。在18 世紀(jì)后,氣氛開(kāi)始被用作比喻,指“在空氣中的情緒”[4]。1950年以來(lái), 氣氛才開(kāi)始逐漸轉(zhuǎn)變?yōu)槊枋鰧徝垃F(xiàn)象的隱喻[5-6]。 在中國(guó),早在西漢時(shí)期就有了“氣氛”一詞,劉向的《說(shuō)苑·辨物》中有“登靈臺(tái)以望氣氛”,此處的“氣氛”指的是表示福禍的云氣。相比之下,中國(guó)傳統(tǒng)語(yǔ)境中的氣氛含義, 包含著人的主觀情感判斷,反而更接近波默對(duì)氣氛的定義。 胡伯特·特倫巴赫從精神病學(xué)的角度將氣氛納入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的視野[7]。 施密茨用現(xiàn)象學(xué)和身體哲學(xué)的方法理解氣氛,認(rèn)為氣氛沒(méi)有邊界,居無(wú)定所,以情感波動(dòng)的形式侵襲身體,產(chǎn)生情緒震顫[8]。 氣氛是一種“侵襲著的感染力, 是情調(diào)的空間性載體”[3]17。相較于前人的研究,波默從本體論角度確立了氣氛概念。在施密茨的論述中,氣氛相對(duì)于物過(guò)度的獨(dú)立性和自由性, 波默則認(rèn)為審美對(duì)象的諸屬性是氣氛效果的條件,氣氛不是無(wú)根的、自由漂移的,而是由物或人所創(chuàng)造的,從物或人那里出發(fā)的。 波默始終強(qiáng)調(diào)的是氣氛介于主客體之間的性質(zhì),“氣氛是某種介于主客之間的東西, 盡管氣氛一方面是由客觀的環(huán)境條件, 即由所謂的營(yíng)造者所導(dǎo)致的,但就氣氛的何所是而言,也就是說(shuō),就氣氛的特征——比如壓抑的或歡快的而言,氣氛卻是被主觀地加以經(jīng)驗(yàn)的。”[3]4這就是說(shuō),氣氛本身具有某些客觀性要素, 但其特征由主觀加以經(jīng)驗(yàn)而決定。 舉例來(lái)說(shuō),在魯迅筆下的咸亨酒店,孔乙己被人嘲諷,爭(zhēng)辯中,“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lái):店內(nèi)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店內(nèi)的氣氛不是沒(méi)有來(lái)由的,是酒店和眾人共同營(yíng)造的;然而此時(shí)眾人體驗(yàn)到了歡樂(lè)的氣氛,但同樣的氣氛,在孔乙己的體驗(yàn)中卻必然是尷尬的、痛苦的。
就氣氛的特性而言, 波默認(rèn)為氣氛的根本屬性是空間性,因?yàn)椤皻夥诊@然是通過(guò)人或物身體上的在場(chǎng),也即通過(guò)空間來(lái)經(jīng)驗(yàn)的”[3]19。氣氛的空間性暗含著主客雙方的共同在場(chǎng)的內(nèi)在要求,“氣氛自身是某物在場(chǎng)的領(lǐng)域,是物在空間中的現(xiàn)實(shí)性……是知覺(jué)者和被知覺(jué)者共有的現(xiàn)實(shí)性”[3]22。氣氛的空間性,不是指物理上的空間,而是一種情感空間,“不是那種按米計(jì)算的空間……是一種懸浮的情緒”[9]。氣氛的核心并非是對(duì)某物理空間的占據(jù),而是空間的情感色彩和其可侵襲性。單純的某物,或某處物理空間是沒(méi)有所謂氣氛的,只有在與人的相遇中,有了人的知覺(jué)和情感參與,主客體共同在場(chǎng)和參與形成了氣氛的情感空間。沒(méi)有與人的相遇,物或空間的存在無(wú)法被感知,也就無(wú)所謂氣氛。
厘清氣氛概念的若干要點(diǎn)有助于我們理解氣氛理論的創(chuàng)新之處, 這對(duì)界定電影氣氛概念起到了一定的廓清作用。但電影氣氛概念的定義,絕非是僅僅給“氣氛”概念加上一個(gè)“電影”做限定詞,讓電影成為氣氛的來(lái)源或類別這么簡(jiǎn)單。巴拉茲·貝拉認(rèn)為:“一切藝術(shù)存在的權(quán)利就在于: 它在自己的領(lǐng)域中創(chuàng)造了獨(dú)一無(wú)二的表現(xiàn)形式。 ”[10]在對(duì)氣氛理論的闡釋中,波默著重于論述建筑、城市規(guī)劃、室內(nèi)裝潢等作為環(huán)境的審美對(duì)象的氣氛,兼及了光、圖像、氣味的氣氛,對(duì)于電影的氣氛并未專門(mén)涉及, 更沒(méi)有深入研究。 他所論及的藝術(shù)形式均與電影存在著較大差異, 因此也使得其關(guān)于氣氛的表述不可避免地同電影之間存在著隔閡感。此外,波默理論本身的非系統(tǒng)性也使得學(xué)者對(duì)其展開(kāi)批評(píng)和反思,認(rèn)為其“有利于我們展開(kāi)橫向的演繹,并獲得許多新的認(rèn)識(shí),但很難在理論縱深上挖掘”[11]53-54。因此,波默對(duì)氣氛的開(kāi)創(chuàng)性工作為藝術(shù)研究開(kāi)辟了新的視角和領(lǐng)域, 他關(guān)于氣氛基本特性的闡發(fā)也為后續(xù)研究提供了基礎(chǔ), 但若要讓“電影氣氛”真正獲得理論生命力,必須著力于電影的特性,同時(shí)與電影文本緊密結(jié)合,使其契合電影獨(dú)特的藝術(shù)規(guī)律。電影氣氛的特殊性,必須立足于電影自身獨(dú)特的媒介特征和知覺(jué)機(jī)制。 筆者認(rèn)為,無(wú)論是電影的藝術(shù)特性,抑或是電影氣氛的本質(zhì)屬性,都必須回到電影的相遇上來(lái)。
二、現(xiàn)場(chǎng)的相遇與現(xiàn)場(chǎng)氣氛
為了更好地厘清電影氣氛與電影的關(guān)系,本文引入“相遇”概念作為理論基礎(chǔ),相遇是電影氣氛產(chǎn)生的前提條件。“相遇概念是戲劇乃至電影最為重要的元概念。 所謂相遇,就是人與人、人與物的彼此面對(duì)面, 是他們帶著各自的性質(zhì)和特點(diǎn)來(lái)打交道, 由此結(jié)成一種在他們見(jiàn)面之前沒(méi)有過(guò)的聯(lián)系或關(guān)系。 ”[12]電影氣氛,乃至于電影本身,都誕生于相遇中。
考察電影的相遇, 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電影存在兩次重要的相遇——“現(xiàn)場(chǎng)的相遇” 與 “觀影的相遇”。 是兩次相遇成就了電影,電影能被稱之為電影,離不開(kāi)這兩次相遇。 相應(yīng)的,兩次相遇也分別對(duì)應(yīng)了兩種氣氛,即現(xiàn)場(chǎng)的氣氛與觀影的氣氛。從某種程度上講, 甚至可以認(rèn)為電影與戲劇最大的區(qū)別, 正在于戲劇的相遇是同一時(shí)空關(guān)系下的一次相遇,而電影的相遇是分開(kāi)的,至少存在著兩次相遇。 戲劇的生產(chǎn)和接受是同時(shí)的、一體的,電影的生產(chǎn)和接受是分離的。 電影的這兩次相遇在時(shí)間上必然是分開(kāi)的, 否則即使有攝影機(jī)和播放設(shè)備作為中介,我們不會(huì)把它稱為電影,而是稱作為直播或什么別的事物, 體育賽事會(huì)有多個(gè)機(jī)位的切換,各類晚會(huì)有導(dǎo)演和演員,一些小品和戲劇直播有虛擬的、完整的劇情,觀演關(guān)系跟電影頗為相似,但是這些都不是電影。
第一次相遇是電影拍攝現(xiàn)場(chǎng)的相遇, 發(fā)生在場(chǎng)景之中,我們可以稱之為人與世界的相遇。這次的相遇過(guò)程通常較為復(fù)雜,在導(dǎo)演的統(tǒng)籌下,演員各自帶著不同的身份和任務(wù), 來(lái)到被預(yù)先設(shè)定和布置好的場(chǎng)景里,彼此向?qū)Ψ秸归_(kāi)刺激與反應(yīng),攝影機(jī)則按照一定的形式予以記錄。因此,現(xiàn)場(chǎng)的相遇至少包括了演員與演員的相遇、 演員與導(dǎo)演的相遇、演員與場(chǎng)景的相遇、演員與攝影機(jī)的相遇等幾種類型。 每個(gè)要素的變化、每對(duì)關(guān)系間的反應(yīng),都會(huì)構(gòu)成對(duì)其他要素的新的刺激, 導(dǎo)致新的變化發(fā)生,以此共同構(gòu)成了一個(gè)彼此聯(lián)系的有機(jī)整體,這些元素和關(guān)系共同構(gòu)成了這一次的相遇。 每個(gè)人都帶著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來(lái), 在這一場(chǎng)相遇中人的意志展開(kāi)為知覺(jué), 在彼此的刺激反應(yīng)中不斷發(fā)展,最終知覺(jué)凝結(jié)在攝影機(jī)里。
一個(gè)鏡頭或一場(chǎng)戲拍攝完成之后, 一次知覺(jué)活動(dòng)宣告結(jié)束。拍攝到的素材并不是知覺(jué)本身,而是用電影的媒介形式對(duì)知覺(jué)及知覺(jué)形成變化過(guò)程的映射,可以稱之為一種知覺(jué)凝結(jié)物。知覺(jué)活動(dòng)只存在于當(dāng)下和現(xiàn)場(chǎng)的相遇中,是流動(dòng)的、生成的、不能被定型的; 而知覺(jué)凝結(jié)物則是知覺(jué)活動(dòng)的結(jié)果,是可被對(duì)象化的客體,同時(shí)也是一個(gè)可被觀眾知覺(jué)的“召喚結(jié)構(gòu)”。 波蘭現(xiàn)象學(xué)美學(xué)家英伽登認(rèn)為:“作品剛誕生的那一刻起, 作者的體驗(yàn)便不復(fù)存在。 ”[13]14從知覺(jué)的角度理解英伽登這一觀點(diǎn),作者的知覺(jué)體驗(yàn)在創(chuàng)作中是活躍的, 在作品完成之后則不復(fù)存在。 這些知覺(jué)凝結(jié)物,包括編劇、導(dǎo)演、演員、美術(shù)和攝影等諸多部門(mén)參與者的知覺(jué),但它不從屬于任何單獨(dú)的個(gè)體, 也不是每個(gè)人知覺(jué)的簡(jiǎn)單疊加。 “疊加”更接近于一種物理上的累計(jì),而正確的描述則是在相遇里彼此影響、改變和成就,其結(jié)果更接近一種“化學(xué)反應(yīng)”。在后期制作中,畫(huà)面和聲音的剪輯,以及加入音樂(lè)和特效的過(guò)程,從內(nèi)容層面看,是新元素的加入和舊有內(nèi)容的改變;從知覺(jué)的角度看,既是對(duì)既有知覺(jué)凝結(jié)物的調(diào)整和重組,也是新的知覺(jué)的參與和反應(yīng)。
在一百多年的電影發(fā)展史中, 電影的內(nèi)容紛繁復(fù)雜,形式花樣繁多,而凡此種種,其實(shí)都統(tǒng)攝于人與世界相遇過(guò)程的復(fù)雜性,從本質(zhì)上講,反映的都是相遇所凝結(jié)的知覺(jué)的復(fù)雜性。
在人與世界的相遇過(guò)程中, 當(dāng)然也有氣氛的存在,我們可以稱之為現(xiàn)場(chǎng)的氣氛。在電影的拍攝現(xiàn)場(chǎng),所有人都可以感知到氣氛。選定和布置好的場(chǎng)景有特定的氛圍, 編劇和導(dǎo)演設(shè)定的戲劇情境也有氛圍。而更能影響現(xiàn)場(chǎng)氣氛的,是每一個(gè)在場(chǎng)的人,尤其是承擔(dān)著表演任務(wù)的演員,所有人都或有意或無(wú)意地釋放出自己的氣場(chǎng), 參與著現(xiàn)場(chǎng)氣氛的營(yíng)造。一個(gè)敏感的人來(lái)到電影拍攝現(xiàn)場(chǎng),未必需要看到架設(shè)的燈光或攝影機(jī), 也不一定要聽(tīng)到演員富有表演性的臺(tái)詞, 仍然能立刻感受到一種迥異于日常生活的氣氛, 讓他驚覺(jué)自己來(lái)到了電影拍攝現(xiàn)場(chǎng)。
于是有一個(gè)疑問(wèn)擺在我們面前, 此時(shí)現(xiàn)場(chǎng)的氣氛,是電影氣氛么?現(xiàn)場(chǎng)的所有人確實(shí)感知到了氣氛,這氣氛也的確是由電影拍攝活動(dòng)所引發(fā)的,然而筆者仍然要指出,這不是電影氣氛。此時(shí)人們感知到的氣氛,是一種現(xiàn)場(chǎng)的、共在場(chǎng)的氣氛,是彼此面對(duì)面直接打交道中感知到的氣氛, 在此過(guò)程中,屬于電影的媒介特性沒(méi)得到體現(xiàn),屬于電影的觀演關(guān)系未能得以建立, 一個(gè)或許以后可以被稱之為電影的東西正處在醞釀之中, 卻還尚未誕生。 因此,盡管感知到的氣氛與電影息息相關(guān),但并不能稱之為電影氣氛,從某種程度上說(shuō),它反而更接近于戲劇的氣氛。
三、觀影的相遇與電影氣氛
電影氣氛的真正誕生, 產(chǎn)生于觀眾與電影的相遇,也即觀影的相遇中,我們可以稱這次相遇為人與電影的相遇。觀影的相遇,本質(zhì)上是觀眾對(duì)電影的意向性活動(dòng)。 意向性指意識(shí)必然指向意識(shí)以外的某個(gè)對(duì)象,“認(rèn)識(shí)體驗(yàn)具有一種意向(Intentio),這屬于認(rèn)識(shí)體驗(yàn)的本質(zhì),它意指某物,它們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與對(duì)象發(fā)生關(guān)系。 ”[14]胡塞爾將意識(shí)的意向結(jié)構(gòu)描述為“自我——思維者——思維物(Ego-Cogitation-Cogitatum)”,“即,自我,其意識(shí)活動(dòng)與客觀相關(guān)物”的結(jié)構(gòu)[15]。
意向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主客觀的統(tǒng)一, 意識(shí)不可能是脫離對(duì)象的,主觀必然與客觀相關(guān)聯(lián)。主體通過(guò)意向切中(Treffen)事物,意向行為指向意向?qū)ο螅栌梢庀蛐袨椋庀驅(qū)ο笤谝庾R(shí)活動(dòng)中構(gòu)造出完整的自身。具體到觀眾的觀影活動(dòng),是觀看行為讓觀眾成之為觀眾,也讓電影成之為電影。作為客體的電影,是一堆膠片,或一份數(shù)字拷貝,即使播放,也只是每秒24 幀畫(huà)面和聲音,沒(méi)有感情,也無(wú)法傳達(dá)單幅圖像以外的任何涵義。 在與觀眾的相遇中,觀眾的觀看賦予了電影以生命。單從客體層面看,電影影像只是一系列單幀畫(huà)面,之所以能在觀眾的感知中成為一段連續(xù)、完整、動(dòng)態(tài)的近乎于日常視覺(jué)感知的視頻,從視覺(jué)層面講,是由于觀眾的視覺(jué)暫留和視覺(jué)后像機(jī)制, 從心理機(jī)制上講,是觀眾心理上的似動(dòng)現(xiàn)象。
從物理意義上來(lái)說(shuō), 電影原本只是平面上的投影,是非立體的、無(wú)深度的,但觀眾觀看電影時(shí)卻可以獲得立體感和深度感。電影心理學(xué)家于果·明斯特伯格論證了電影的深度感和運(yùn)動(dòng)感來(lái)自于觀眾的心理,觀眾在平面銀幕上完全意識(shí)到深度,但又不把它完全接受為真實(shí)的深度,“我們?cè)谟捌锌吹搅藢?shí)際的深度……這是由我們自己的活動(dòng)創(chuàng)造的深度”,“我們獲得現(xiàn)實(shí)及其全部真實(shí)的三維; 然而它又保持了那一閃而過(guò)的既沒(méi)有深度又不豐滿的平面暗示”[16]。 并且,由于雙眼視差的存在,畫(huà)面中有遠(yuǎn)景的襯托,近景的立體感才會(huì)更強(qiáng)。知覺(jué)心理學(xué)家甚至認(rèn)為人類視網(wǎng)膜只存在高度和廣度二維,視知覺(jué)本身并不存在深度,是大腦“以背景暗示和對(duì)世界的畢生認(rèn)識(shí)經(jīng)驗(yàn)將二維視覺(jué)圖像理解成了三維”,“一個(gè)三維的世界被一個(gè)二維的眼睛所記錄,而后再經(jīng)大腦還原為三維”[17]。
因此, 只有觀眾的參與才能讓電影的單幀畫(huà)面成為連貫的鏡頭, 讓單獨(dú)的鏡頭具備了超越圖片的電影化表意能力。進(jìn)一步講,蒙太奇意味著依靠對(duì)畫(huà)面的組接和重構(gòu), 制造出每個(gè)鏡頭獨(dú)自出現(xiàn)時(shí)所沒(méi)有的內(nèi)涵,讓鏡頭成為電影的表意單位。英伽登在研究文學(xué)作品時(shí), 將作品中時(shí)空段之間的空隙稱為“不定點(diǎn)”或“未定域”(Places of Indeterminacy),用來(lái)表示“再現(xiàn)的對(duì)象中沒(méi)有被文本特別確定表達(dá)的方面或部分”[13]50,他進(jìn)而認(rèn)為讀者在閱讀文本的過(guò)程中, 要主動(dòng)借助想象補(bǔ)充這些未定域,這種活動(dòng)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活動(dòng)。電影鏡頭之間的空隙,也類似于英伽登所謂的“不定點(diǎn)”,需要觀眾的主動(dòng)填補(bǔ), 蒙太奇的機(jī)制歸根結(jié)底是觀眾的心理機(jī)制, 區(qū)別在于電影的不定點(diǎn)未留給觀眾專門(mén)的時(shí)間思考, 觀眾往往是出于下意識(shí)的即時(shí)反應(yīng)予以填補(bǔ); 文學(xué)作品由于閱讀節(jié)奏由讀者自由把控, 其不定點(diǎn)的填充既有迅速帶過(guò)的即時(shí)反應(yīng),也可能會(huì)有時(shí)間停頓做理性思考。 因此,電影依靠蒙太奇來(lái)表達(dá)單個(gè)鏡頭之外的意義, 這也仰賴于觀眾的心理。 導(dǎo)演可以通過(guò)蒙太奇手段引導(dǎo)觀眾的注意和聯(lián)想,在創(chuàng)作階段就預(yù)設(shè)了蒙太奇的最終效果, 這并不意味著不需要觀眾心理的參與;相反,導(dǎo)演正是基于對(duì)觀眾心理的了解和預(yù)判,才能進(jìn)行蒙太奇的創(chuàng)作,乃至整部電影的創(chuàng)作。
由此我們可以認(rèn)為,電影之所以能成為電影,必須有觀眾的參與, 純粹客體化的電影是無(wú)法產(chǎn)生意義的。正如電影理論家讓·米特里所言:“一部小說(shuō)唯有被閱讀才算存在。 如果僅僅是印刷字的組合,它就毫無(wú)價(jià)值。畢竟不比再現(xiàn)于一卷膠卷上的一系列影像更有價(jià)值。 小說(shuō)僅僅‘存在’于讀者的意識(shí)中;畫(huà)作應(yīng)當(dāng)被看,音樂(lè)應(yīng)當(dāng)被聽(tīng)。……一切‘客體’都把可感內(nèi)容和感知它的主體之間的關(guān)系視作必然。……如果說(shuō)一部藝術(shù)作品的產(chǎn)生需要藝術(shù)家,那么,為了藝術(shù)作品的存在,還需要觀眾。 ”[18]電影客體作為一種召喚結(jié)構(gòu),凝結(jié)著第一次相遇中的知覺(jué),等待被觀眾的知覺(jué)喚醒。電影成為了連接觀眾意識(shí)活動(dòng)和電影創(chuàng)作者意識(shí)的特殊中介,是主體間際的意向客體(Intersubjective Intentional Object), 它以膠片或數(shù)字拷貝為物理載體,以創(chuàng)作者意識(shí)的創(chuàng)造活動(dòng)為根源,以觀眾與電影的相遇為正式誕生的標(biāo)志, 電影只有在與觀眾的相遇中才真正成為電影。在人與電影的相遇中,演員和演員、演員和場(chǎng)景、演員和導(dǎo)演、演員和攝影機(jī)的相遇都已經(jīng)完成, 第一次相遇的知覺(jué)已不再是知覺(jué)本身,而成為了知覺(jué)的凝結(jié)物,它通過(guò)電影的媒介形式成為了觀眾知覺(jué)的對(duì)象。
觀眾的感知是一次復(fù)活的過(guò)程, 在觀眾的感知中,第一次相遇的知覺(jué)得以部分地復(fù)活,將單幀的畫(huà)面復(fù)活為動(dòng)態(tài)的影像, 將獨(dú)立的鏡頭復(fù)活為連貫的表達(dá),觀眾感知電影的畫(huà)面和聲音,感知電影的場(chǎng)景、光影、表演。在某些時(shí)候,觀眾可以循著這些元素, 想象性地感知到電影創(chuàng)作者的意識(shí)狀態(tài)。之所以強(qiáng)調(diào)是“某些時(shí)候”,因?yàn)檫@種情況并不總能發(fā)生, 只有在部分創(chuàng)作者能在影片中展現(xiàn)這種意識(shí)狀態(tài),而不僅是完全沉溺于表達(dá)某種情緒、講述某段故事或塑造某個(gè)人物, 也不是所有觀眾都能感知到這種意識(shí)狀態(tài)。之所以說(shuō)觀眾是“想象性”地感知,是因?yàn)閯?chuàng)作者創(chuàng)作時(shí)意識(shí)狀態(tài)存在于電影拍攝現(xiàn)場(chǎng),此時(shí)已不復(fù)存在,觀眾是憑借創(chuàng)作者凝結(jié)為客體的知覺(jué)殘留物, 通過(guò)自己的理性和感性知覺(jué),調(diào)用了審美經(jīng)驗(yàn)和知識(shí)儲(chǔ)備,包括觀影經(jīng)驗(yàn)和對(duì)電影的前置理解, 運(yùn)用想象來(lái)還原和感知?jiǎng)?chuàng)作者的意識(shí)狀態(tài)。 對(duì)電影的前置理解指觀眾長(zhǎng)久以來(lái)形成的對(duì)電影的審美趣味, 以及觀眾對(duì)具體觀看這部影片的了解和期待, 包括對(duì)類型的預(yù)判,對(duì)劇情、演員、導(dǎo)演的認(rèn)知等等。因此這種對(duì)創(chuàng)作者意識(shí)狀態(tài)的感知,并非直接地感知,而是觀眾基于影片客觀要素的主觀想象。 這往往需要一定的觀眾的想象,絕非憑空而來(lái),而是基于自己對(duì)電影畫(huà)面和聲音的知覺(jué)。 就像現(xiàn)代人看到拉斯科洞穴史前人類的壁畫(huà),借此可以“想象性”地感知石器時(shí)代人類的生活圖景, 這種想象受到壁畫(huà)內(nèi)容的直接影響,但終究并非是真實(shí)和直接地感知。
因此,在第二次相遇中,電影得以真正誕生。電影氣氛,正是指觀眾與電影的相遇中的氣氛,即觀影的氣氛。 電影氣氛是伴隨著觀眾觀影的意向性活動(dòng)產(chǎn)生的,也是觀眾知覺(jué)活動(dòng)的產(chǎn)物。胡塞爾認(rèn)為, 我們無(wú)法拋棄人與事物的意向性關(guān)系而探討事物的存在。電影之所以能打動(dòng)人心,引發(fā)觀眾的情感共鳴, 并且不同的觀眾可能對(duì)同一部電影有著不同的感受, 其奧秘都在這次觀眾與電影的相遇中,從本質(zhì)上講,反映的都是觀眾與電影的意向性關(guān)系。 觀眾觀影的意向性活動(dòng)不僅僅只是指向電影,更是在構(gòu)造電影。氣氛也正是伴隨著構(gòu)造電影的過(guò)程產(chǎn)生的, 并沒(méi)有客觀的電影氣氛獨(dú)立于觀眾存在然后才被觀眾知覺(jué)到, 而是在觀眾經(jīng)驗(yàn)電影的過(guò)程中產(chǎn)生了氣氛和相應(yīng)的氣氛體驗(yàn)。
四、兩次相遇的差異與電影氣氛的實(shí)質(zhì)
對(duì)比現(xiàn)場(chǎng)氣氛和觀影氣氛, 可以發(fā)現(xiàn)兩者關(guān)系緊密但有著顯著的差異。電影拍攝現(xiàn)場(chǎng)的氣氛,處在表演和拍攝的戲劇情境之中。 觀影的氣氛是在觀影情境中, 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面對(duì)電影時(shí)的氣氛,此時(shí)觀眾處在銀幕之外,借由拍攝和放映設(shè)備旁觀拍攝現(xiàn)場(chǎng)。在電影觀影過(guò)程中,拍攝現(xiàn)場(chǎng)的戲劇情境仍然存在, 但只構(gòu)成了觀影情境中被觀看的文本,也即觀影過(guò)程中“客體側(cè)”的一部分。相應(yīng)地,現(xiàn)場(chǎng)氣氛不能等同于觀影氣氛,而是以特定的形式出現(xiàn)在了觀影氣氛中的“客體側(cè)”中。 現(xiàn)場(chǎng)的氣氛以電影特有的形式,映射入電影客體。攝影機(jī)攝錄的畫(huà)面和聲音是拍攝現(xiàn)場(chǎng)氣氛的殘留,是一種機(jī)械復(fù)制, 現(xiàn)場(chǎng)的氣氛經(jīng)由攝影機(jī)和錄音設(shè)備以特定的光學(xué)、 聲學(xué)規(guī)律和特定的藝術(shù)手段加以記錄和轉(zhuǎn)譯,成為電影素材。現(xiàn)場(chǎng)氣氛的這種殘留,并不是電影氣氛本身,而是作為電影客體諸要素之一,構(gòu)成了電影氣氛召喚結(jié)構(gòu)的客體部分。在第一次相遇中電影客體攝錄了現(xiàn)場(chǎng)的氣氛, 在第二次相遇中電影客體成為了觀影氣氛的召喚物。因此,電影客體連接起了兩次相遇和兩種氣氛。
從內(nèi)容上看, 觀影氣氛和現(xiàn)場(chǎng)氣氛這兩者有時(shí)會(huì)很接近,但它們絕不會(huì)完全等同,有時(shí)可能會(huì)差異很大甚至截然不同。 兩者出現(xiàn)很大差異的情況主要有以下四種:
第一,由于觀眾和角色之間存在信息差,觀眾通過(guò)前文劇情或攝影機(jī)的特殊視角, 掌握了超過(guò)片中角色的信息。 例如電影《瘋狂的石頭》(2006)中謝小盟被道哥一伙綁票, 道哥以為謝小盟的翡翠是假的,所以意圖用此翡翠調(diào)換展廳的翡翠,但觀眾卻知道謝小盟已經(jīng)借拍照之機(jī)用假翡翠調(diào)包了真翡翠, 此刻道哥所拿的正是他心心念念的真翡翠。 因此道哥一伙的盜竊計(jì)劃實(shí)質(zhì)上成了以真換假, 表演時(shí)他們?cè)绞菄?yán)肅地計(jì)劃和執(zhí)行偷竊活動(dòng),觀影的氣氛就越是滑稽可笑。希區(qū)柯克在與特呂弗的對(duì)話中談到了如何區(qū)分懸念和驚悚, 希區(qū)柯克分別舉例子予以說(shuō)明,其中,驚悚是:“我們?cè)诨疖?chē)上聊天,桌子下面可能有枚炸彈,我們的談話很平常,沒(méi)發(fā)生什么特別的事。 突然,‘嘣! ’爆炸了。 觀眾們見(jiàn)之大為震驚,但在爆炸之前,觀眾所看到的不過(guò)是一個(gè)及其平常的、 毫無(wú)興趣的場(chǎng)面。 ”[19]而懸念則不同,是觀眾此前已經(jīng)知道有炸彈快爆炸,并且時(shí)間已經(jīng)不多,如此一來(lái),“原先是無(wú)關(guān)緊要的談話突然一下子饒有趣味, 因?yàn)橛^眾參與了這場(chǎng)戲。 ”[19]在這里,希區(qū)柯克所對(duì)比的兩種情況, 凸顯的正是觀眾和角色的信息差產(chǎn)生的效果。在觀眾知曉炸彈,而劇中角色不知道的情況下,原本表演的氣氛可能是輕松的、日常的,但觀影時(shí)的氣氛卻是緊張刺激、充滿懸念感的。
第二,觀眾存在明顯的情感趨向,感情立場(chǎng)更貼近某些角色, 因此對(duì)部分場(chǎng)景的現(xiàn)場(chǎng)氣氛無(wú)法感同身受。 此類情況常見(jiàn)于角色中出現(xiàn)了明顯的正反陣營(yíng)的電影。如影片《投名狀》(2007)中,龐青云上任兩江總督, 幾位朝中大員在圍坐笑談中決斷了龐青云的生死, 利益集團(tuán)的博弈借由龐青云的死重歸平衡,現(xiàn)場(chǎng)氛圍輕松融洽,但觀眾所喜愛(ài)和自我投射的并非這幾位軍機(jī)大臣, 而是龐青云三兄弟,因此觀眾感受到的氣氛是憤怒和悲愴。此類情況中,為了增強(qiáng)觀眾與主角的情感共振,電影往往在色調(diào)和音樂(lè)方面予以修正, 讓色彩基調(diào)和背景音樂(lè)與主角的情緒一致, 強(qiáng)化現(xiàn)場(chǎng)氣氛與觀影氣氛不同產(chǎn)生的戲劇張力。
第三,電影采用了戲說(shuō)、惡搞、戲仿、拼貼、隱喻等手法, 造成了電影文本與其他文本或外部世界的某些具體社會(huì)事件、 歷史事件具有高度的相關(guān)性, 使得影片出現(xiàn)了文本層面和內(nèi)涵層面的背反,觀眾需要超越文本的假定性,結(jié)合外部語(yǔ)境加以理解。 例如電影《阿甘正傳》(1994)大膽地將劇情與歷史事件結(jié)合,讓阿甘見(jiàn)證、參與甚至直接影響了眾多重要的歷史事件, 這些場(chǎng)景從文本層面本身看是嚴(yán)肅的、 自洽的, 但觀眾看來(lái)卻有著驚奇、搞笑的氣氛。 部分作品甚至本身不是自足的,具有一種“外鏈?zhǔn)健苯Y(jié)構(gòu),需要結(jié)合其他文本才能理解其內(nèi)涵。 影片《大電影之?dāng)?shù)百億》(2006)出現(xiàn)多個(gè)惡搞的橋段,戲仿了《阿甘正傳》《黑客帝國(guó)》(1999)、《花樣年華》(2000)、《無(wú)間道》(2002)、《十面埋伏》(2004)、《功夫》(2004)、《雛菊》(2006) 等三十余部電影的經(jīng)典場(chǎng)景, 觀眾在觀影時(shí)不是孤立地關(guān)注這部作品,而是不自覺(jué)地產(chǎn)生聯(lián)想,把它與眾多場(chǎng)景的原作聯(lián)系起來(lái), 因此其觀影氣氛不是由作品本身決定的, 而是受到了仿作與原作關(guān)系的影響。 夸張戲謔的模范固然會(huì)產(chǎn)生滑稽可笑的氣氛, 表面嚴(yán)肅的模仿同樣也會(huì)營(yíng)造幽默好笑的氛圍。
第四,依靠電影素材的后期加工,配以音樂(lè)、音效或?qū)Ξ?huà)面做特效處理, 改變了原本的氣氛效果。 如電影《大話西游之大圣娶親》(1995) 的結(jié)尾,重新踏上娶親路的孫悟空看到了城墻上的武士和戀人的分別,城墻下一片圍觀和起哄的群眾,該場(chǎng)景原本是戲謔的風(fēng)格, 主角尤其是周星馳飾演的武士,臺(tái)詞和表演風(fēng)格都帶著故意的夸張。然而當(dāng)加入了孫悟空的視角后,電影主題曲《一生所愛(ài)》響起,電影氣氛驟然變得傷感,通過(guò)音樂(lè)的加入,這對(duì)戀人的命運(yùn)和至尊寶、 紫霞的命運(yùn)真正產(chǎn)生了對(duì)照和呼應(yīng)。雖然在孫悟空的干預(yù)下,這對(duì)戀人攜手相伴, 但卻更喚起觀眾對(duì)紫霞命運(yùn)的同情和不甘,影片的氛圍仍是惆悵的。 此外,很多恐怖片也依靠懸疑、恐怖的音樂(lè)和驟起的音效,在原本尋常的場(chǎng)景中制造恐怖氛圍, 拍攝現(xiàn)場(chǎng)沒(méi)有聲音的參與則完全沒(méi)有恐怖感。需要承認(rèn),如果電影完全依靠背景音樂(lè)和音效來(lái)營(yíng)造氣氛, 的確可以制造與現(xiàn)場(chǎng)氣氛差異較大的電影氣氛, 但也往往會(huì)顯得較為生硬。
通過(guò)與現(xiàn)場(chǎng)氣氛的對(duì)比,觀影氣氛,也即真正的電影氣氛的性質(zhì)得以更清晰地呈現(xiàn)。至此,我們借由對(duì)電影氣氛的發(fā)生的考察, 得以在存在論層面發(fā)現(xiàn)電影氣氛的實(shí)質(zhì)。 電影氣氛正是電影在與觀眾的相遇中,以畫(huà)面、音響等媒介手段作用于觀眾的知覺(jué),引發(fā)觀眾的想象和情感反應(yīng),在電影場(chǎng)中形成的情感空間。 電影氣氛是觀眾意向性活動(dòng)的產(chǎn)物,它由電影所引發(fā),充分調(diào)動(dòng)了觀眾的感性知覺(jué)和理性思維,喚起了觀眾的注意、記憶、欲望、想象和情感。 電影氣氛并非作為電影的一種元素存在,而是一種電影的感知方式和感知狀態(tài)。當(dāng)電影給予的視聽(tīng)信息中出現(xiàn)了明確的元素, 引起觀眾的相應(yīng)知覺(jué)反應(yīng), 這是電影氣氛效果的直接體現(xiàn); 電影的聲音和畫(huà)面中沒(méi)有出現(xiàn)直接刺激的來(lái)源,而是通過(guò)誘導(dǎo)觀眾的聯(lián)想和想象等方式,間接地讓觀眾產(chǎn)生某種情緒和反應(yīng), 這同樣是電影氣氛的體現(xiàn)。其中,電影場(chǎng)指觀眾與電影相遇的物理空間,同時(shí)也包括了電影放映設(shè)備、觀眾和觀看場(chǎng)地在內(nèi),電影場(chǎng)以觀眾知覺(jué)的邊界為界限。
不同于電影場(chǎng)的“物理空間”屬性,也并非當(dāng)今較為盛行的社會(huì)和文化視角的空間, 電影氣氛的空間屬性是一種情感空間。 空間研究者認(rèn)為空間既是一種外在的實(shí)存, 也是一種內(nèi)在的感知,“受歐幾里得理論的限制,人們認(rèn)為空間只存在于每個(gè)人的骨骼中,是固有的;空間可以通過(guò)感官被即刻感知,如手的抓握和人體的運(yùn)動(dòng),以及視覺(jué)的穿透力,等等。 ”[20]2電影的氣氛空間存在于對(duì)電影的感知中,以身體為起點(diǎn)和連接點(diǎn)。意大利神經(jīng)學(xué)家皮耶羅·弗朗西斯·法拉利和斯特凡諾·羅茲認(rèn)為“我們的大腦會(huì)對(duì)空間的概念做出多維度的判斷,將外部空間同我們的身體聯(lián)系起來(lái)。因此我們身體的維度其實(shí)是感知的起點(diǎn), 也是身體空間結(jié)構(gòu)的起點(diǎn)。”[20]11電影氣氛出現(xiàn)的前提是觀眾的身體性在場(chǎng),通過(guò)氣氛與身體的互動(dòng),與觀眾發(fā)生反應(yīng),波默將此過(guò)程稱之為身體“收、縮的經(jīng)濟(jì)學(xué)”[3]18,也即人的對(duì)氣氛的身體性覺(jué)察。
五、結(jié)語(yǔ)
波默在論述氣氛的誕生時(shí), 將產(chǎn)生氣氛的條件表述為人的“身體性在場(chǎng)”或物走出自身的“迷狂”或“出竅”,未強(qiáng)調(diào)人與物的相遇,這或許是為了突出氣氛既不屬于主體又不屬于客體的“居間性”, 但在一定程度上不免強(qiáng)化了人與物的分離。本文將電影氣氛的前提確定為觀眾與電影的相遇,也即人與物的相遇,明確這一前提使我們對(duì)電影氣氛的發(fā)生學(xué)基礎(chǔ)表述得更為清晰和完整。 存在論意義上,電影氣氛是觀眾意向性活動(dòng)的產(chǎn)物,是電影在與觀眾的相遇中, 在電影場(chǎng)這一物理空間中所形成的情感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