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類會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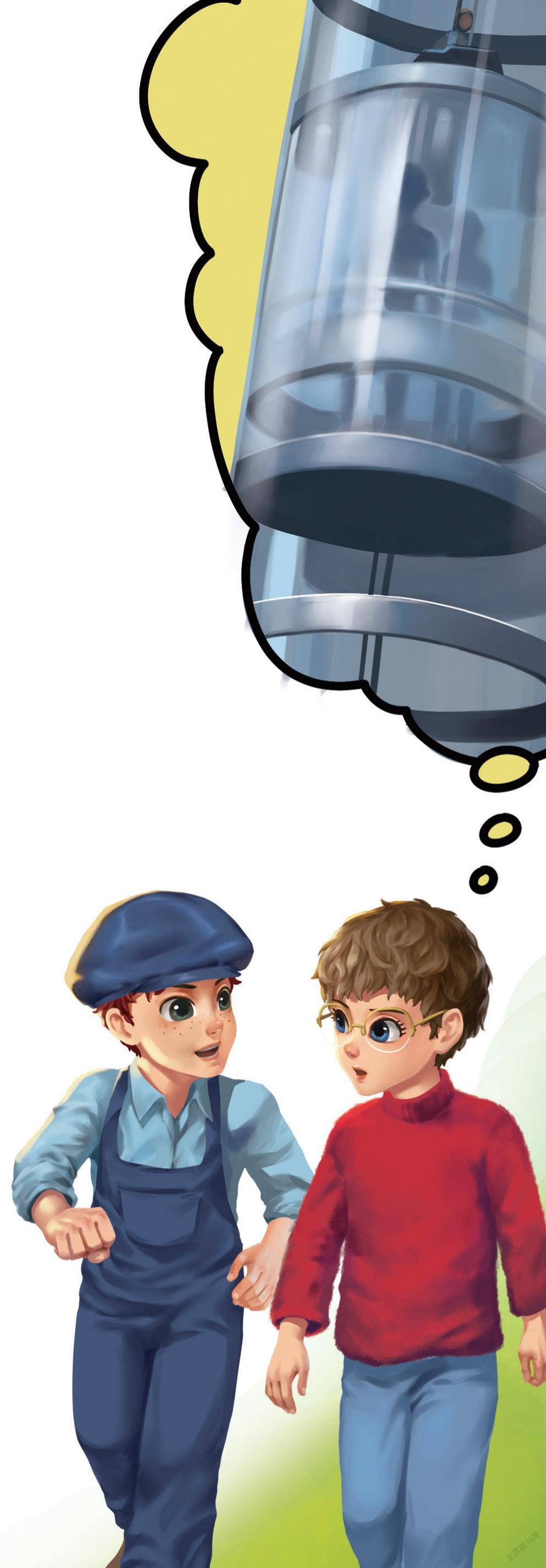






文/埃馬努埃爾·凱西爾·萊佩蒂? ? ?譯/夏笑笑? 繪/王子勝
善意的謊言
“那么,你是誰?”
“我叫南希。看,這里寫著呢。”
南希把毛衣的領子拉下來,露出了她的脖子,脖子上戴著一條漂亮的用她名字的字母做的金色項鏈。奧利弗立刻轉身去看,幾乎呆住了:“你的項鏈是很……非常漂亮。是金子做的嗎?”
“不,傻瓜,這是toc(贗品、假貨)!”
“什么是toc?”
南希咬著嘴唇。她有必要換個方式講話。她現在在19世紀,對她來說相當于石器時代,就是恐龍滅絕之后。
“就是假的!”
“哦……pacoille(劣品、次品)!”
“對,toc——pa-cot-ille。你看,把音節顛倒過來了。”南希用對頭腦遲鈍的人說話的口氣一字一頓地說道。
奧利弗吞了吞口水,緊接著問了第二個問題:“你是哪里人?”
南希猶豫了一下。不能說真話——她可不想被認為是個瘋子。而且她不想破壞她的任務,她很想和這個單純的人交個朋友,但并不愿意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告訴他。
“我來自……肯特!”她即興舉出了英國唯一一個她知道名字的地方。
“啊?!”奧利弗驚呼,越發驚訝,“你看起來不像啊!連口音都沒有!你從肯特郡哪個地方來的?”
哦,天哪!事情變得復雜了!南希想起了杰西卡的一句座右銘:要想說好謊話,得靠講真話。
“不,我的意思是,我的故鄉是肯特,我是在紐約長大的。我的父母死于一場意外。所以我回來看我的姑姑,但她可能搬家了,所以……總之,我來了!”她擠出一絲緊張的笑容。
“哇!紐約!很多人都去那里了,但他們通常不會再回來了。”
“好吧,你看,我是一個例外!”南希苦笑道。
“這解釋了你的口音。”奧利弗說,“紐約是什么樣子?”
“啊,你不知道,那兒真是太棒了!”
“怎么講?”
“Super(超級好)。”
“高級?”
南希克制住煩躁感嘆,在記憶中搜索著對于19世紀的無知者來說更容易理解的詞。
“宏偉,這個詞你懂吧?壯觀、驚人、輝煌、美妙。那邊有幾百米高的建筑,所以高到被稱為‘摩天大樓’。”
“真的?”奧利弗很驚訝,“那人們如何上樓呢?”
“嗯,當然是,他們坐電……”南希適時地停了下來。真是笨!電梯在1843年還沒有被發明出來!她完全不知道在那個遙遠的年代倫敦有什么或沒有什么。其實,仔細想想,紐約那時也沒有電梯……
“呃,紐約人的肌肉很發達,就是這樣!他們很喜歡運動。”南希隨意編造著,祈禱奧利弗至少能明白這個詞的意思。但這次輪到她驚訝了。
“我也喜歡運動!我家里有羽毛球拍,我哥哥還劃船。當然,橄欖球并不太適合女生,但也很好玩……”
南希大笑起來。奧利弗很高興與這個不尋常的女孩兒找到了共同點,給了她一個燦爛的笑容。南希垂下眼簾,她覺得有點兒自責:這個男孩兒其實超級好,有點兒傻乎乎的,但真的很好相處。可惜她不得不說假話。
奇妙的情愫
“好吧,我已經遵守了我的約定。”她生硬地說道。“現在該輪到你告訴我了,關于這些文件你知道多少?”
奧利弗很快就告訴了她,他是在什么情況下發現的這些文稿。然后,他從衣服里拿出一沓紙,用手撫平了并把它們交給了他的新朋友。
終于呀!南希就像海盜見到他的寶藏時一樣撲在文稿上。奧利弗看出她也識字,這真是很難得——在女生身上更是如此。而且還是一個穿著男生衣服的女孩兒,衣服的樣子也不是很好看。
趁著南希忙著閱讀的時候,奧利弗開始端詳她:她雖然戴著眼鏡,卻非常漂亮。波波頭很特別,但很適合她。她的頭發是淺棕色的,襯托出她的綠眼睛。然后,她左邊嘴角上有一顆痣……
奧利弗有些不好意思,轉移了視線。他是怎么了?這樣盯著一個女孩兒看是不對的!同時,南希卻沒有注意到他。奧利弗小心翼翼地瞄著南希的褲子。那藍色的布料是什么?它看起來很結實,可能是美國制造的,就像她鼻子上架的眼鏡。他得告訴他媽媽,無論如何,這是他第一次看到穿褲子的女孩兒……嗯……令人不安。
跨世紀的對話
南希讀完了文件,抬起了頭:“你怎么了?”
奧利弗猛地抬起頭朝天花板看去:“這里很大吧……”他結結巴巴地說,臉紅得像個西紅柿。
“是啊。我們現在可以談談文件了嗎?”
“當然,你看懂什么了嗎?”
南希嘆了口氣:“句子真的很長!”
“而且用詞相當復雜,”奧利弗笑道,“寫這篇文章的人一定很聰明,有文化,有教養。一定是個貴族。”
“你是說,一個貴族?為什么?”
“因為他們是唯一能接受教育和上大學的人。”
“是這樣啊?”
“或者他是個大資產階級,”奧利弗思考著,“他們有些人的兒子也會去牛津或劍橋。”
“他們的兒子?為什么不是他們的女兒呢?”南希不滿道。
奧利弗盯著她,愣了一下,在做出解釋前問:“紐約的女孩子可以上大學?在我們這兒,貴族們的女兒會學習讀書寫字。但更重要的是學習刺繡、音樂、舞蹈、管理家務……”
“那么那些不是貴族或者不是大資產階級家門的女兒呢?”
“她們?就和男生一樣,她們得工作。但沒人能識字。我能認字是因為我父母給我請了一個家教。”
“孩子們工作?!他們不去學校上學嗎?”
“什么是學校?”
南希雙手抱頭——這真是不可思議。從1843年到2030年的發展實在是驚人。
線索歸零
短暫的沉默之后,她繼續說道:“所以,綜上所述,本文件的作者是一個男人。一個貴族或大資產階級。顯然,是個數學家。”
“是的,計算非常困難。”奧利弗同意。
“這些不是計算,而是算法。”南希糾正他。
“算法是什么?”
“數學公式。一系列循環重復的方程,但存在變量。第一個計算的結果用于第二個計算,以此類推。”
“那又有什么作用呢?”
“要解決一個邏輯問題或者給電腦編程……”南希咬了咬嘴唇,“什么用都沒有!不管怎樣,我可以向你保證,這些都是算法。我父母整天都在用它們。”
“但你告訴我他們已經死了?”
“呃……是的,”南希糾正自己,“他們以前用……”用過去式談起父母,她突然覺得很不舒服。她的臉色一變——她很想念父母。
“對不起,你肯定很難過。”奧利弗同情地喃喃自語。
南希抬頭看著他,有種作為可怕騙子的不自在的感覺。“是的,這很難,但我不想說。重要的是要找到寫這些筆記的人和這個程序。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A. A. L.’?”
“當然,這一定是他名字的縮寫。前兩個字母,‘A. A.’應該與名字相對應——在我們這兒,貴族往往有兩個名字——最后一個‘L’,一定是他的姓。”
“L. 是……”南希突然想起:洛夫萊斯。但這可能太簡單了。而且,她父親說過,她是個女人,而根據奧利弗所說,作者不可能是個女人。她試圖回憶19世紀創造歷史的英國學者的名字,可惜,她什么也沒有想到。她當然想到了燈泡的發明者愛迪生,但他是美國人,而且生活在19世紀末。還有誰呢?牛頓,那個拿著蘋果的家伙,他發現了萬有引力?他是英國人,如果沒記錯的話,他生活在很早以前的17世紀。南希意識到,她不認識任何19世紀的英國科學家。也許根本就沒有!
聰明的紅頭發
“我們的線索為零!”她終于嘆了口氣,沮喪地說道。
“你忘了提花織機!”奧利弗脫口而出,“我聽大胡子說過,分析機機器用打孔卡工作,就像提花織機。紡織廠有一個。文稿的作者可能是來看看織布機的工作情況或者他就在那里工作!”
南希看著奧利弗,一臉驚喜:“他終究也不是那么傻,這個紅頭發的家伙!他甚至相當聰明呢!”
“你說得對!這意味著我們可以找到他了!我們得去紡織廠!”她滿懷熱情地喊道。
“我會要求見工頭。這不是很容易,但我的父母都是他們的老客戶了。”奧利弗解釋說。
“哦,太好了!我太崇拜你了!”
最后這句話讓可憐的奧利弗臉漲得通紅。南希覺得自己想擁抱他,不過她忍住了——她必須適應:英國人是出了名的拘謹,況且,這是19世紀。她克制住喜悅,站了起來。
“我們現在可以走了嗎?現在這個時間,之前的那些人一定是回酒吧了。”
奧利弗臉色一變:“現在是什么時間?”
南希條件反射地伸手到口袋里拿手表,然后,突然停住了:“嗯……我不知道……反正已經晚了。”
“我得走了,否則我媽媽會打我。我們明天去工廠。”
男孩兒走了幾步,又停下來。他回頭看向南希:“那你要睡在哪里?”
“在希爾頓酒店!”南希笑道。
“什么地方?”
“沒什么……我睡在這里,你以為呢?”
奧利弗神色黯然道:“跟我走吧!我給我媽編個故事,你可別在這海港上睡了,這兒不安全。”
“我們幾乎都不認識,你卻邀請我去你家?”南希驚訝地說。
“是啊,否則明早我怎么看鏡子里的自己呢?”
南希盯著奧利弗。她不知道在紐約有誰會這么做——邀請從外地來的,穿著骯臟衣服的,剛在一個聲名狼藉的街區認識的人到自己家。這讓她目瞪口呆。
被收留的“假小子”
奧利弗去倉庫拿他的小推車。然后,他帶著南希穿過白教堂區迷宮般的小巷。
“我們就說你是紡織廠工頭蒂爾伯里先生的侄女。你剛從美國來,要在倫敦停留幾天,但蒂爾伯里先生家里正在裝修,不能安頓你……類似這樣的話。”
南希點了點頭,沒有回答。她在這個地區的街道上看見的,讓她的心都提了起來,以至于她都無話可說。多么悲慘哪!所有這些可憐的人擠在一起,那些孩子們得靠自己養活自己。還有那難聞的氣味,從哪里來的?當他們遠離那個污水池進入到斯畢塔菲爾德絲綢區時,她松了一口氣。這里比較干凈,至少人看起來正常多了。當然,也不是那么高檔的街區,只是一個工薪階層的小手藝人社區。
當他們到家時,奧利弗直接把她帶到儲藏室。
“你進店之前要先換衣服。我媽媽絕不會相信我的故事,如果你還穿著……”
“你是說穿著臟兮兮的牛仔褲?我昨天摔在一個泥潭里。”
“牛崽?”
“牛仔褲,就是我穿的這個。你不認識嗎?”
“不,”奧利弗臉紅了,和一個女生談起衣服細節有點兒發窘——特別是關于褲子的細節,這是一個禁忌的話題,如果這算禁忌的話。他拿起前一天一位富有的女客戶送來修補的連衣裙。那位女士說這是她小女兒的裙子,尺碼應該合適。奧利弗把它交給了南希,然后迅速地溜走了。
美好的夜晚
南希獨自留在棚子里很開心地換衣服。她學校里的男同學們可不會這么快跑走的,他們喜歡在健身房前女生更衣室周圍徘徊。
裙子真的很美,但有一個問題:南希上一次穿公主裝是在她6歲生日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很可笑!況且,袖長不足以藏住她的手表。她只能把表藏在她的內衣里。然后,她把牛仔褲和毛衣卷成一團,塞進了棚子里一個隱秘的角落。
走出去時,她注意到奧利弗眼中的驚嘆之色。他臉紅地轉身就走,爬上那幾級臺階到門廊,為南希打開店鋪的門。然后,他走到一邊讓南希過去。
“哦,謝謝你!”南希越來越驚訝。這一點,她學校的男生也不會這么做。為一個女孩兒開門,真是個奇怪的想法!他們是那種會從女孩兒們身邊走過,并擠她們的人,為的就是在食堂里先吃到飯。說真的,回到19世紀總歸是有些好處的。
三個小時后,年輕的女孩兒欣喜地鉆進了帶著肥皂清香的被單里。她剛剛吃了她來后的第一頓真正的飯。她終于可以洗澡了,雖然不是在淋浴間,但她還是很滿意的。現在,她終于能夠度過一個美好的夜晚了!她享受著簡單的快樂,以前這些快樂對她來說是那么的理所當然。以前其實就是前天哪——仿佛已經成了永恒。
南希懷著感激的心情想起了奧利弗,他在隔壁房間睡覺。多虧了奧利弗,她才能睡在這里。走運的是,奧利弗的父母被紡織廠工頭的故事給唬住了。他們甚至非常熱情地接待了南希。南希在被單間扭動著,很不舒服。她并不是很自在,因為要對這些對她有恩的人撒謊,特別是奧利弗。但她有選擇嗎?她必須完成她的任務:摧毀第一臺電腦。它會不會是1843年在倫敦發明的,而不是在一個世紀后的費城發明的?南希還是覺得難以相信。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時光機會把她送到這里來。她和奧利弗迫不及待地想找到編寫程序的人,這樣一切就都清楚了,南希就可以采取行動了。
同時,在晚飯前,她趁著獨自一人的間隙,用手表拍下文稿的每一頁——手表可能沒有聯網,但它配備了所有的現代應用軟件!所以,她把一切都保存了下來。南希把手放在枕頭下:她的手表在那里,藏得很好。那盒蛀蟲就躺在旁邊。
可怕的街區
第二天起床后,南希假裝和工頭叔叔有急事兒,奧利弗得負責護送她去,兩個孩子剛吃完早飯,就得以從店里脫身——他們都迫不及待了。
當南希重新進入白教堂區時,她發現人們都在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盯著她。有的人甚至在她過去的時候讓開了,好像她得了什么罕見的病一樣。
“為什么每個人都這樣看著我?”
“因為你的裙子,”奧利弗低聲說,她真的很顯眼。“快走吧,不要拖拉……你身上沒帶貴重的東西吧?”
“呃……沒有……”南希撒了謊,下意識地伸手去摸自己的束胸。她跟著奧利弗,幾乎都要跑起來了。他們經過一群正在馬路中間撿地上食物殘渣的小孩子。南希看到孩子們把撿到的東西塞進嘴里狼吞虎咽地吃起來,心中泛起一陣惡心。
“這個街區太可怕了。那些可憐的人,真讓人心疼。”
奧利弗聳了聳肩說:“你知道,倫敦還有很多地方也是一樣的。呃……我是說,在東區……”
“我原先想象的倫敦不是這樣的。”南希承認。
“啊!那是什么樣的呢?”
南希猶豫著要不要回答。兩年前她和母親來倫敦度假,她對這個城市的印象與她現在看到的完全不一致。且不提紅色雙層巴士、電話亭和黑色出租車在1843年還不存在,英國首都的名勝古跡都在哪里呢?哪兒是大本鐘、皮卡迪利廣場、特拉法加廣場、白金漢宮?穿紅衣、戴黑毛帽的女王侍衛們在哪里呢?
“沒什么……”她低聲喃喃自語。
沒有必要向奧利弗解釋這一切,他不會明白的。他們根本不在同一個世界,僅此而已。到了碼頭,南希覺得被太陽烘烤過的河水,氣味仿佛比前一天更難聞了。
寶藏女孩兒
奧利弗指了指其中的一個煙囪,它正在噴出一團污染嚴重的黑煙:“就在那邊。”
南希捏著鼻子,跟在他身后。奧利弗經過了他常來取父母訂單的倉庫,工廠就在旁邊,它的厚墻是用磚砌成的,沒有窗戶。一扇巨大的木門擋住了入口。
“這兒真是個碉堡,這玩意兒!你覺得我們從哪兒能進去?”南希問。
奧利弗笑了:她真是個寶藏女孩兒。不僅使用他從未聽過的詞說話,而且還對最普通的東西一無所知。如果大門關閉,那是因為工人已經開始工作兩個小時了。它只會在晚上重新打開,讓工人們出來。男孩兒指給南希一處凹進去的、更隱蔽的、有扇鑄鐵門的地方。
“從這兒進。這是老板們走的門。好了……你還記得你要做什么嗎?”
南希點了點頭。奧利弗設計了一個進入工廠的小計謀,并獲得了和工頭面談的機會。當他敲門環的時候,南希迅速躲在奧利弗身后。一扇百葉窗打開,欄桿后出現了守門人那張令人厭惡的臉,他打量著奧利弗。
“如果你是來工作的,那太遲了。白班兒已經確定了。今晚6點回來上夜班兒吧。”他正準備關上門時,南希從奧利弗身后走出來,用她最禮貌的聲音重復著男孩兒教給她的話:“我們不是來工作的,好心的先生。我和我的朋友必須要見見蒂爾伯里先生,我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守門人瞬間變了臉色。他盯著南希穿的那件帶著緞帶的漂亮的歐根紗裙,結結巴巴地說:“當然,我給您開門,小姐。我不知道像您這樣的年輕女士……我……我很慚愧,真的。”百葉窗關上了,門就像變魔術一樣打開了。
“哼,這就是禮貌對他產生的作用!”南希在奧利弗的耳邊笑著說。
“禮貌不是唯一影響他的事情:他以為你是一個其實你并不是的人。”
“請問,他以為我是誰?”
奧利弗盯著南希,目瞪口呆:她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嗎?鑒于她的衣著打扮和高傲的說話方式,很明顯,她來自貴族階層。這個上層社會讓世界上其他人都圍著他們轉!沒有人不知道這一點。
神秘的工廠
守門人帶著極大的敬意,帶著他們走到一個通向樓梯頗為陰森的大廳。里面的熱度讓人窒息,就像在烤箱里一樣,而且噪音也讓人難以忍受。但聲音是從哪里來的呢?在走廊的盡頭,樓梯前有一扇半開的門。南希忍不住推開了它,門后等待著她的是地獄般的景象:在一個陷入黑暗的棚子里,男人們光著膀子,渾身黑乎乎的煙灰,在巨大的爐子前接力干活兒,這些爐子里升起嚇人的火焰。他們輪流用鏟子投擲黑石子——是煤!南希認出來了。女孩兒這才明白附近街區籠罩的黑煙的來歷:沿著泰晤士河一字排開的工廠里一定都有類似的熔爐!三步并作兩步跑下樓的守門人插話道:“哦,小姐,不要看!我很抱歉,我應該把門關上。”
他馬上就這么做了,然后鞠了一躬,對她指了樓梯的方向。南希順著守門人指的方向走,有些惱火。
“這個家伙怎么了?他覺得我是個脆弱的小東西嗎?”她在奧利弗的耳邊喊道。
奧利弗用手捂著嘴,噗嗤一笑,沒有回答她。
他們終于來到了工頭的辦公室門口。守門人敲了敲門,然后鞠躬示意南希進去。當蒂爾伯里先生看到她的時候,也立正站好。
“小姐……”然后他認出了裁縫的兒子,用不那么友好的語氣說:“奧利弗·福爾摩斯!你在這里做什么?”
“您好,蒂爾伯里先生,”男孩兒結結巴巴地說,“就是…… 我們發現…… 嗯……”
一個程序?做什么用?
如果說奧利弗想到了進入工廠的方法,那么他完全沒有想到接下來該怎么做,而且蒂爾伯里先生深色的夾克衫、高大的身材,還有他那彎彎的小胡子,總讓他有些害怕。南希見狀決定由她開始交談:“奧利弗和我前天在港口發現了一份奇怪的文件,我們想它可能是您的。”
工頭更仔細地看著剛才如此直接地對他說話的女孩兒。
“小姐,我現在是有幸向誰講話呢?”
“南希·華生。”她邊說邊伸出手。她以為蒂爾伯里會和她握手——但蒂爾伯里卻俯身給了她一個似有似無的親吻禮,蒂爾伯里的嘴唇甚至都沒有碰到她的皮膚。南希翻了翻白眼,向奧利弗招了招手,示意他拿出文件,以減少寒暄的次數。他們也不打算在這里待上一天!
“您看,”南希拿起文稿塞到蒂爾伯里手中,“您有什么印象嗎?”
工頭瀏覽了一下文件的前幾行內容并皺起了眉頭:“這不屬于我。”
“我們也是這么想的!”南希說,“這個簽名‘A. A. L’,您認識這個人嗎?”
“完全不知道。”工頭結結巴巴地說著,越來越對南希的語氣和態度感到不滿。
南希瞥了奧利弗一眼:是時候說正事了。奧利弗鼓起勇氣,告訴了工頭真相:他是在什么情況下獲得該文件的,他想找到文件的主人,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文稿上說的那個神秘機器顯然是由打孔卡來操作的,就像提花織機一樣。
“這上面寫著呢,”南希指著蒂爾伯里先生散落在桌上的其中一張紙說,“所以應該和你工廠里放的機器有關系。”
“確實如此……”蒂爾伯里先生喘著氣,雙眼圓睜。
“也許是工業間諜!”南希補充道。
工頭的眼睛睜得更大了:“您認為……”
“我們能不能看看這臺著名的提花機,以便確定一下?”南希打斷了他的話,“我們得把事情弄清楚,您覺得呢?”
蒂爾伯里先生驚呆了,他照做了。他帶領奧利弗以及那個奇怪的女孩兒去了制造間。當他們進入時,南希站在原地不動:在她面前,并排幾百米,有幾十臺巨大的機器在運轉。它們鏗鏘有力的手臂在長桌之上有節奏地起伏著,線被拉長了。南希意識到,這些是織布機。她還看到了忙碌的女工和不超過七八歲的孩子們。
奧利弗轉向她:“是蒸汽讓這一切變得更有意義!”他提高了聲音來掩蓋噪音。樓下的爐子里正在燒鍋爐里的水,蒸汽從那里冒出來。(他伸出手指向其中一條管道,這些管道從地下通上來,連接到每臺機器上)然后蒸汽進入這個氣缸,激活這個活塞,使這個曲柄轉動,然后動力傳遞到織機的手臂上!這太神奇了,不是嗎?
南希點了點頭,以免得罪他——她的朋友似乎對這項落后的技術非常自豪。就她而言,她不禁想,只要有一個簡單的電機,一切都會簡單得多,并且污染小,噪音低。想想這些孩子們剛夠可以玩樂高的年齡,卻每天要在這里辛苦工作10個小時!
電腦的老祖宗
蒂爾伯里先生把他的兩位來訪者領到第二個較小的房間。房間里,一臺機器像戰利品一樣居中擺放。
“這就是提花織機!”他宣布。
兩位少年仔細觀察了一下:它與臨近工作間里擺放的織布機截然不同。它的體積要小得多,且形狀也不大一樣。提花織機頂部有一個大滾筒,有節奏地轉動。下面有鉤刺,由針帶動交替抬起在臺板上水平伸展的線。其他顏色的線垂直懸掛在上面。在每一次推進卷軸的時候,它們中的一個會變成一個梭子,進行編織。在前面,布料在一毫米一毫米地往外冒。但這與隔壁房間的純色床單和棉布織品毫無關系。這里生產的是上好的絲綢,緯線勾勒出花團錦簇的形象,蝴蝶和熱帶島嶼的鳥類在采花覓食,畫面具有驚人的寫實色彩。
“它看起來像一幅畫!”南希很震驚。
她用手指摸了摸其中一只鳥,大概是一只蜂鳥:翅膀上的羽毛是彩虹色的,藍、綠、紫、黃、橙等顏色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這臺機器是怎么做到的?”她結結巴巴地說,已經失去了所有的風度。蒂爾伯里先生得意地坐了下來,他示意南希靠近滾筒,而滾輪繼續猛地向上轉動。然后,女孩兒看到一串有孔的卡片,每條線上的排列方式都不一樣。
工頭解釋道:“是這些卡片控制著機器,并告訴它何時何地要用哪根經線,要提起哪根緯線,如何讓它們織在一起來編出圖案。根據有無孔洞、每條線上孔洞的位置和數量,機器移動這個或那個操縱桿。”
“好吧!”南希低聲道,“事實上,是由卡片來給機器設計程序的。”
“沒錯。”工頭確認道,“這是一個革命性的系統。小姐,您就站在有史以來最精密的機器前!只有它能做到這一點!”
南希點了點頭:她剛剛才意識到,她是站在歷史上第一臺可編程的機器前。簡而言之,提花織機是電腦的老祖宗!
“誰創造了這個機器?”奧利弗問道。“沒準兒這臺機器的發明者和我找到的文稿的作者是同一個人!”他自言自語道。
但工頭的回答讓他措手不及:“它是由一個法國人發明的。”
“一個什么?”這份文件是用很優雅的英文寫的。奧利弗覺得很難相信一個普通的吃田雞的法國人會是作者。
“是的,年輕人。”工頭確認道。他的名字叫約瑟夫·瑪麗·雅卡爾,這臺機器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生產出的面料也是用他的姓:雅卡爾提花面料。
約瑟夫·瑪麗·雅卡爾的首字母是J.M.J.,所以不是文稿的作者,奧利弗想。但他也許是我們要找的科學家的朋友呢。
“這個雅卡爾住在哪里?”他問道。
“他是里昂人……但他已經死于1834年,也就是8年前,我的孩子!”
奧利弗皺了皺眉頭:所以,他的假設是錯誤的。但一定是有什么關聯的——雅卡爾的打孔卡一定激發了該文稿作者設計新機器的靈感。
“我們給您看的筆記也許是廠里的工程師寫的?”
“我看未必。”工頭嘆了口氣。“這個文稿太復雜。我不知道這是什么機器,但它不是織布機。它的確是用卡片,但用卡片做什么呢?毫無頭緒!”
巴貝奇先生
南希對卡片或者說對程序能讓機器做什么是比較清楚的,她問:“除了我們之外,最近還有人對這個機器感興趣嗎?”
蒂爾伯里先生撓了撓頭,仔細想了想:“很多人都在問我這個問題,你們懂的……”
“但前天,有沒有人來見您?”奧利弗堅持說。
“前天?讓我想想啊,是的,對!查爾斯·巴貝奇先生來了,但我不認為……”
“巴貝奇先生是誰?”奧利弗叫道,預感到會有新發現。
“哦,他是一位數學教授。這不是他第一次來找我了。你們覺得是他嗎?”
奧利弗把他的帽子從一只手換到另一只手上,認真地聽著,并提出了最后一個問題:“他是坐著馬車來的嗎?”
“是的,那是他自己的車。但他卻匆匆離開了:他告訴我,他想起家里的鍋爐還燒著呢,并說他很著急。”
“是他!”奧利弗說,“我就覺得他是我們要找的人:我們找到他了!”
幾分鐘后,南希和奧利弗從工廠里走出來,興奮不已。他們成功了!
“我們兩個是很好的團隊,你不覺得嗎?”奧利弗自夸起來。
“我們做得真不錯。”南希笑著說,她又皺起眉:“只是有一件事困擾著我:這個查爾斯·巴貝奇的首字母和文稿上的A. A. L.對不上。”
“你說得沒錯。”奧利弗臉色一沉,他掀開帽子撓了撓頭。
“又是一個謎團,但你知道最好的解決方法嗎?”
“呃……”
“我們一定要去見見這個巴貝奇!蒂爾伯里先生給了我他的地址:他住在多塞特街1號。”
“在哪里?”南希問道。
奧利弗手指著工廠的相反方向的西邊那片兒的教堂尖頂和橋拱處:“在西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