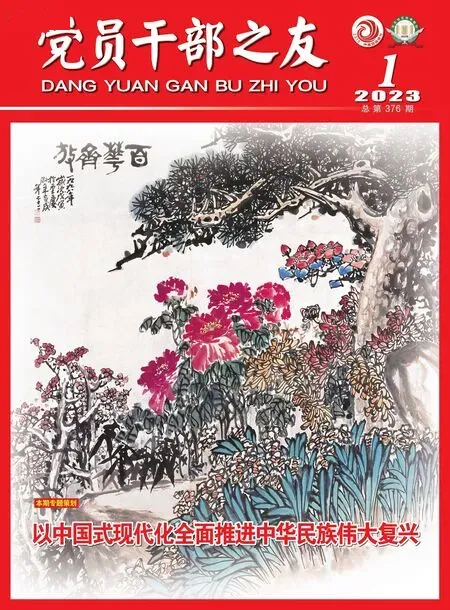面對他們,我們能做些什么事情?
□ 矯 發

黎 青/圖
壬寅年十月十三日(2022 年11 月6 日),當代著名收藏家、哲學家辛冠潔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1 歲。著名詩人孔孚先生之女、儒雅的孔德錚大姐寫了篇紀念文章,字里行間洋溢著辛孔之間的深情厚誼。
70 多年前,辛孔共事于《大眾日報》,彼時辛冠潔是副總編輯(后任總編輯),而孔孚只是文藝部的普通小卒。孔孚個性耿介,特立獨行,辛冠潔評價他“銳敏”“銳氣”;辛冠潔寬宏大度,愛才惜才,孔孚評價他“作風民主”。兩人從初識到相知,從惺惺相惜到莫逆之交,可謂同志加兄弟。嗣后孔孚去外地履職,辛冠潔有時一個月給孔孚寫17 封信、3 萬多字,恨不得把心里話都掏給知己故交。
最感人的是,辛冠潔自掏腰包為孔孚出版詩集。1995 年,辛冠潔得知孔孚病重,就去找出版社的朋友,千叮嚀萬囑咐,讓他們“用最快的速度、按最高規格”出版《孔孚集》,慷慨坦言“我不惜一切代價”,并預付了出版社5 萬塊錢的費用。后因印數只有1000 冊,出版社要求再追加兩萬塊錢的費用。為籌集款項,辛冠潔傾囊相助,還忍痛割愛賣掉了自己收藏的部分名貴字畫。近30 年前,對于一個普通家庭來說,7 萬塊錢乃是天文數字,即使時至今日,也是一筆不菲的開支!辛冠潔甘愿付出所有,其價值哪是金錢所能衡量的?
1996 年,606 頁、封面燙金、竹影婆娑的《孔孚集》面世。孔孚倍感欣慰,在“后記”中感慨莫名:“所有一切出書事宜,均有辛公操持。他是自討苦吃。在這個世界上,心里老念著為別人做點什么,自討苦吃的人,怕是不多了。”
1997 年,孔孚含笑九泉。因辛冠潔的“自討苦吃”,孔孚聲名鵲起,他的詩歌、詩論躋身文學史,經久流傳。
孔孚有首《風和海》的短詩,竊以為是宣揚“友誼”的預言。德錚大姐贈我的《孔孚詩文》(山東友誼出版社)寫道:“風和海,是一對弟兄。一個暴躁,一個任性。我倒是愛這缺陷之美,因為我自己也不安寧。”而我從孔夫子舊書網淘得的著名詩人穆仁簽名的《孔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用“減”用到極致。“一個暴躁/一個任性/你呢?先生/我是老兄”活脫脫的孔辛對話,音容笑貌躍然紙上:一個快刀斬亂、行事如風;一個大肚能容、海納百川。兩人性格迥然,而思想互感,步調默契——拾遺補闕,兩相平衡,乃增進友誼之方也。
穿越時空,歷史竟驚人的相似。辛孔之誼,讓我想起了唐代的劉禹錫和柳宗元。
劉柳有著相似的命運:政治上,參與王叔文的“永貞革新”,有著共同的政治理想與宏偉抱負;創作上,兩人詩文俱佳,往來唱和,情趣相投;在人生前半場,兩人如出一轍。公元793 年,他們一起進京應試,同登進士第。劉禹錫在貞元十九年(803 年)擢升監察御史,而柳宗元也在這年閏十月從藍田縣尉簡拔為監察御史。他們同朝為官,共舉改革大旗。不幸,“永貞革新”失敗,二人慘遭貶謫,劉貶朗州,柳貶永州。
十年后,兩人應詔返京。劉禹錫因作《游玄都觀絕句》受到小人詆毀,柳宗元亦受牽連。唐憲宗下令,劉禹錫貶播州,柳宗元貶柳州。柳宗元傷心欲絕,他不是為自己傷心,而是為劉禹錫傷心。播州窮鄉僻壤,生活條件極為艱苦,想到劉禹錫還有耄耋慈母,柳宗元挺身而出,請求“以柳易播”。朝廷里不少大臣感念柳宗元的義氣,求情唐憲宗從寬處理。最后唐憲宗重新頒旨,將劉禹錫貶至條件稍好的連州。
韓愈的《柳子厚墓志銘》有段警世之論,字字見血,句句刺骨。“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征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發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成語“落井下石”即源出于此。
共同的志向、情趣、遭遇,讓他們心心相通,心有靈犀。他們在順境時相互支持,在逆境中相互鼓勵。被貶柳州的柳宗元,身心受到極大損害。元和十四年(819 年),皇帝召柳宗元回京的圣旨還沒抵達,他在柳州赍志而歿,時年47 歲。柳宗元臨終前遺書劉禹錫:“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將子嗣與全部遺稿托付于他。劉禹錫躬身護送柳宗元的靈柩回歸故里,并三寫《祭柳員外郎》寄托無限哀思。他還花了二十多年時間為柳宗元整理詩文遺稿,將其編撰成集,親撰序文介紹其生平和成就。我們看到的《柳河東集》都是在劉禹錫整理的基礎上刊刻而成的。《柳河東集》堪為浩繁艱巨的工程,序言只追述了柳宗元的生平過往和臨終時的托付,而對自己拖著病體艱辛整理遺作,劉禹錫只字未提。更令人感佩的是,劉禹錫不忘遺言,對柳之長子柳周六視如己出,細心教導,終成大器。唐咸通四年(863 年),柳周六進士登第。遺愿既遂,九泉之下的柳宗元可以安眠矣!
世間事任勞易,任怨難。而劉禹錫“甘為他人作嫁衣裳”,雖九死猶未悔。何也?吾曰:人格魅力和友誼的力量。
歷史劇《天下長河》,讓我們又一次見識了生死之誼——他們是堪比劉柳的靳輔和陳潢。
黃河岸邊山東的德州和東營、江蘇的徐州和揚州,至今屹立著靳輔與陳潢的各式雕塑,足見他們在百姓心中的分量。有記者采訪張挺(編劇和導演):“該劇最初吸引你的點是什么?”張挺回答:“友情,靳輔和陳潢的友情。”
靳輔從發現陳潢開始,他們的坎坷命運就與九曲黃河綁在了一起,事業之舟顛簸起伏。他們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他們尊重自然,敬畏水性,踏勘河道,束水治沙;不管上天多么不公,他們直面朝廷的派系之爭,戴枷督河,巡堤督壩,終其一生,畢力黃河安瀾。一個封疆大吏,一個布衣士子,九死一生的治河事業讓他們結下山海情誼:靳輔慧眼識珠,陳潢脫穎而出;陳潢鼎力相助,靳輔如虎添翼。歷史確有記載,陳潢去世前書信靳輔,引用了蘇東坡寫給弟弟的詩:“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靳輔臨終前寫了一個奏折,言及陳潢,淚水盈眶,他引用了李白的詩句:“平生不下淚,于此泣無窮。”在生命垂危之際,靳輔忘死為陳潢鳴冤叫屈,終使其平反昭雪。
“遏浪伏波,每有中流砥柱;穿山斷石,長存大將雄風。”靳陳之誼,是風雨同舟的戰友情,是患難與共的兄弟誼,是舍我其誰的生死之交。天地昭昭,黃河可鑒!
友誼因時因事而變,他每時每刻都在上演。有的恩斷義絕,徹底決裂;有的破鏡重圓,涅槃新生;有的若即若離,分分合合。友誼是有生命力的,有的曇花一現,有的半途而廢,有的遙不可及,然劉柳、靳陳、辛孔之誼逝而不息,萬古長青!
孫犁說:“紀念死者,主要是為了教育生者。如果不是這樣,過去這些文章(指《柳子厚墓志銘》——引者注),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斯人已去,歷史如風,那些逝而不渝的友誼永遠值得回味,他們脫俗的言行舉止,永遠值得追慕踐行。
“我靜靜地走在一片樹林里,想著那些賢人君子能做些什么事情。”這是賀拉斯的話,我記得作家張煒也經常題寫給文友詩。劉柳、靳陳、辛孔,都是跨越時空、超越國度的天地君子。他們還活著,他們的心靈不染纖塵,如明鏡一般純潔得透明。
長路漫漫。面對他們,我們能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