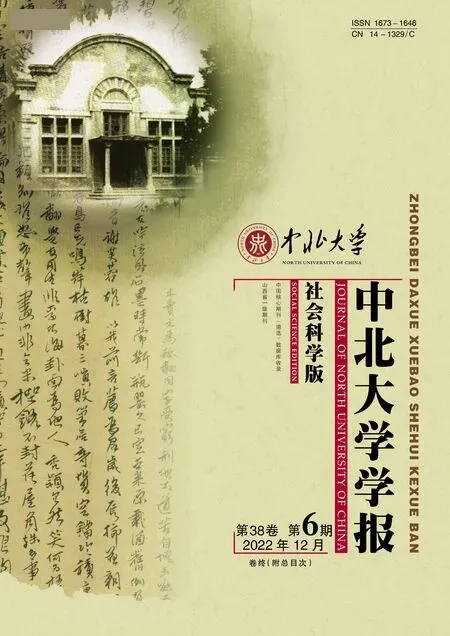南明弘光政權速亡軍事因素探討*
蘇 辰
(鞍山師范學院 人文與傳播學院,遼寧 鞍山 114007)
南明政權從1644年5月到1662年4月,經歷了弘光朝、隆武朝、魯王監(jiān)國朝、紹武朝、永歷朝的更替,弘光政權是直接對明朝北京中央政權的繼承。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持續(xù)276年的明中央朝廷覆亡。清兵乘機入關擊退李自成,控制了北方。但是,明朝統治并未全面結束,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在明朝各級官吏統治之下,迅速啟動了留都南京的政權統治。南京是明朝開國首都,永樂年間遷都北京,南京作為留都一直保留了與北京相對應的一整套中央機構。面對北京陷落,崇禎十七年五月三日,文武大臣擁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監(jiān)國,五月十五日即帝位,以次年(1645年)為弘光元年,南明歷史掀開篇章。對于南明史的研究,諸位專家學者多有論述,主要有謝國楨論述南明弘光、魯王、隆武、紹武、永歷諸政權的興亡變遷;美國學者司徒琳對南明的弘光、魯王、隆武、永歷四個政權做了系統研究;南炳文對南明作了整體研究;顧誠闡述大順軍攻克北京、清兵進入山海關攻占北京及各地反清運動的歷史,突出了農民軍的歷史作用;劉中平論述弘光政權一朝的歷史,對弘光政權建立的歷史條件、主要政策和其失敗的原因進行了比較分析。(1)謝國楨:《南明史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美]司徒琳著,李榮慶等譯:《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南炳文:《南明史》,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年;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7年;劉中平:《弘光政權研究》,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上著作都對南明弘光政權進行了各有側重的研究,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南明極度腐朽的政治軍事狀況及政權短命而亡的原因。本文在各位專家學者研究弘光政權已有成果基礎上,緊緊圍繞南明弘光政權速亡的軍事因素,陳述了弘光政權初建之機擴軍練兵、加強京師防御及強化江淮防衛(wèi)所發(fā)揮的對新生政權的拱衛(wèi)作用,解析聯清滅順失策的原因及后果;論述軍隊腐敗、武臣內訌、割據互斗是導致南明弘光政權速亡的直接因素。由此可見,歷史不會說謊,強國必先強軍。
1 調整南京防御力量,強化京師防衛(wèi)
弘光政權建立初始,內外形勢十分嚴峻。內部形勢黨爭頻仍:掌握兵權的是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南京守備太監(jiān)和提督南京軍務勛臣。閹黨鳳陽總督馬士英勾結操江勛臣劉孔昭,以及南京守備太監(jiān)韓贊周和江北三鎮(zhèn)武臣高杰、黃得功、劉良佐,組成軍事聯盟擁立福王。由此馬士英居功掌握了弘光王朝的權力,軍鎮(zhèn)武臣也因“定策”而更加專橫跋扈。史可法起初不支持擁立福王朱由崧,“定策”決策失誤,沒能得到福王朱由崧的信任,導致東林黨軍事上的孤立,致使南明弘光政權軍事力量發(fā)生變化,四鎮(zhèn)總兵形成,鳳陽總督權力因馬士英的任職發(fā)生擴張。南京的軍事力量尤其是南京守備可以直接支配的軍力,在當時居于弱勢地位。外部形勢惡劣復雜:北部有清兵,西北部有大順軍,西南部又有張獻忠部農民軍的活動,它實際控制的領土不過是長江腹地,只占東南一隅。
面對內外及軍事防御的嚴峻形勢,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獻策,兵權集中于中央,強化長江下游防御,并按照北京的格局整頓守軍及加強南京防御體系。
1.1 加強京師防御體系
南明弘光政權按照明朝北京防御規(guī)格,在兵防、衙門職能及職官運用上加強調整,將留都南京升格為首都,南京守備體制升格為京營體制,“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回部佐理戎政”,“命江南募兵”[1]132;“設勇衛(wèi),以總兵徐大受、鄭彩,分領水陸,閹人李國輔監(jiān)之。”[2]7京營體制改革了守備力量,從原南京守備體制中脫離出來。“命太監(jiān)韓贊周管司禮監(jiān)事,盧九德為司禮監(jiān)秉筆,提督京營。”[1]134由原南京守備太監(jiān)任職京營提督,使京營體制運作便利。“以杜弘域、楊御蕃、牟文綬、丁啟光等補三大營各總兵官。弘域等統一營至五營,啟光等統六營至十營。”[1]192京營以原守備體制為基礎進行整頓。“定京營之制視北京,以杜弘棫、楊御蕃、牟文綬補三營總兵。”[3]451“收朱大典募兵入京營。宗周命其募旅勤王,用贖前罪。大典得兵三千,引之至。被冢宰推以豫督。”[2]54
留都南京升格為首都。“頒各衙門新印。先是,二月二十四日,管紹寧私寓失去禮部印,投誠于馬士英。二十九日,士英即具疏請更鑄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其舊印悉行繳進。至是,鑄成頒給。”[3]535
1.2 擴編京營增兵力
弘光政權將作戰(zhàn)組織和訓練組織常設化,建立職業(yè)常備軍。“兵部請罷南京守備參贊各銜,依北都設京營等官。又請罷錦衣衛(wèi)、南北兩鎮(zhèn)撫官,俱從之。”[1]131-132崇禎十七年(1644年)六月,以南京守備體制原班人馬和兵力為基礎,“依北京更定營制為五軍、神機,三大營各一營至十營”[4]100。崇禎十七年五月,“兵部請設防江水師,定額五萬,添設兩鎮(zhèn),畫地分防。仍復操江總督,文臣協理。俱允行。舊制,操江總督憲臣與勛臣并設。崇禎時欲專任誠意伯劉孔昭,故罷憲臣。至是,兵部從郎中萬元吉議,請復舊,從之”[1]129。操江都御史名義上受南京守備管制,實是平行、雙頭管理。南京兵部奏請并設文武之臣,能夠使操江都御史與操江勛臣在權力上互相牽制。“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請增防三輔,命覆行。國維疏言:‘為國之道,必居重方能馭輕……請除舊設水陸額兵外,另于南京城外設戰(zhàn)兵三萬,少亦一萬五千,統以能將,殫力訓練,為蘇、淞、嘗、鎮(zhèn)之外藩,淮南之屏蔽,以為朝廷東輔。其溯流而上也,請于蕪湖設戰(zhàn)兵三萬,少亦一萬五千,統以能將,殫力訓練,為徽、寧、太之外藩,淮西之屏蔽,以為朝廷西輔。中輔,譬腹心也,腹心固,然后可以運四肢……異日則三路進剿,即以為中原恢復之圖。’”[1]171-172文臣要求以南京守備體制為基礎,擴充南京兵力,以此強化南京城內外兵防。“定兵額。京營□萬,神武營五千,四鎮(zhèn)每鎮(zhèn)三萬,安慶陸兵一萬,水兵五千,應撫三千,總兵五□,淮撫一萬五千,鳳督一萬,京□一萬八千,蕪采水營一萬,徐鎮(zhèn)四千,每名給餉二十兩。”[2]71與守備體制下的南京軍事部署有所不同,京營兵力皆在南京守備體制基礎上進行了擴充,在原有轄區(qū)范圍內進行了轉變。
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七日,史可法奏請從九江往東到鎮(zhèn)江以西增置五萬兵力的江防水師。具體兵力分配是“開鎮(zhèn)九江、鎮(zhèn)江,各萬五千人,聽節(jié)制于操江總督。余二萬人,操江自將之,往來策應”[5]6090。為消除南京軍隊彼此不相統率的弊端,五月八日,史可法又上《請定京營制疏》,奏請廢除南京留都體制,裁撤南京守備、參贊等虛銜,遵北京舊制,改設團營,設立京營戎政制度,“其本營兵額不敷,聽于別營選湊。如再不足,則另募補充。此皆戰(zhàn)兵也”;設置六千名兵力的巡捕營,“所以防內奸也”;將神威、振武兩營合并,兵力五千名,“所以護陵寢也”;設立兵部標營,“所以示居重也”;將侍衛(wèi)、錦衣衛(wèi)編伍操練,中央調遣各地方駐地官軍,集中兵權。明朝中葉以來,宦官專權,設立了東廠、西廠、錦衣衛(wèi)南北鎮(zhèn)撫司等為統治者御用的特務機構。為安人心,“其東西兩司街道房、南北兩鎮(zhèn)撫司官不備設,所以杜告密,收人心,省繁費也”[6]2-3。弘光政權廢除了南京留都體制,改設京營戎政制度,最后一任南京外守備忻城伯趙之龍任總督京營戎政。京營戎政制度是京營的常設化,是對南京守備制度的調整擴編,目的是把兵權集中到中央政府。
2 聯清滅順失略,強化江北四鎮(zhèn)防衛(wèi)能力
弘光朝建立伊始,清朝采用欺騙手段,承認南明弘光政權的合法性。弘光朝失察,由于階級偏見,始終把“報仇” “討賊”,消滅農民軍作為國策。弘光登極時道其稱帝原委:“朕嗣守藩服,播遷江、淮,群臣百姓,共推繼序,跋涉來迎,請正位號。予暫允監(jiān)國,攝理萬幾。乃累箋勸進,拒辭弗獲,謹于五月十五日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于南都。”因“潢池盜弄”崇禎殉國,致命“三靈共憤,萬姓同仇。朕涼德弗勝,遺弓抱痛,敢辭薪膽之瘁,誓圖俘馘之功。尚賴親賢戮力劻勷,助予敵愾。”[7]10
清軍于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二日據北京后,剃發(fā)易服激化了關內的民族矛盾,并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面對這種局勢,弘光政權本應聯合農民起義軍合力對付清軍,卻陷于仇恨之中無法自拔,得知吳三桂引清軍入關,弘光帝竟然賜封他為世襲“薊國公”,贈送五萬兩銀、十萬石糟米,犒賞吳三桂借兵滅順的功勞,并夸獎“[吳]三桂倡義討賊,雪恥除兇,功在社稷”[8]197。吳三桂降清被封為“平西王”,弘光帝認敵為友,還幻想以吳三桂聯合清軍消滅農民起義軍。
從閹黨到東林人士,都一致幻想著“聯清滅順”。兵部尚書馬士英率先提出“若可羈糜專力辦賊,亦是一策”,稱與清議和為“今之上策”。[8]189史可法上《款清滅寇疏》,闡明“目前最急者,無逾于辦寇矣”,強調“清既能殺賊,即是為我復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宥其前辜,借兵力之強,而盡殲其丑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8]235。
不論派別及黨系,整個弘光朝的文武大臣及福王,都堅持“聯清滅順”策略。遣使清朝,天真地向清割地納款,以山海關外地、歲幣十萬換得清軍助剿李自成農民軍,換得明朝對全國的部分統治。[9]219-220甲申(崇禎十七年)七月初,弘光朝派使團前往北京與清議和,十月使團到達北京,清對弘光朝使者刁難凌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懋第被拘禁于京,太仆寺少卿兼兵部職方司郞中馬紹愉降清,總兵官加太子太保陳洪范作為清方內應被單獨放回。左懋第不屈服于清的威脅利誘,慷慨就義,弘光政權的聯清滅順策略以失敗告終。
由于弘光朝志在討賊,實行“聯清滅順”,沒有清醒地認識到清兵威脅。北使議和失敗,致使弘光朝以史可法為代表的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清軍準備征討江南、剿滅南明,紛紛要求弘光朝正視清軍威脅,防御清軍南侵。
面對清軍占領北京、即將南下的嚴峻形勢,南京的安全取決于長江以北。史可法極力主張在長江以北設立四鎮(zhèn),以保南京。歷代戰(zhàn)守長江以南,必先在江北設置防守力量。史可法在留都擔任南京兵部尚書,是南京衛(wèi)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擁有實權。弘光政權建立后組成馬士英、史可法的混合內閣。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八日,史可法奏請《敬陳第一緊急樞務啟》:
從來守江南者,必守江北。即六朝之弱,猶爭雄于徐、泗、潁、壽之間,其不宜劃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分則力單,顧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后鼓銳而前,再圖進取。臣以為當酌地利,急設四藩。四藩者: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之基。凡各屬之兵馬錢糧,皆聽其自行征取。如恢一城、奪一邑,即屬其分界之內。……而四藩即用靖南伯黃得功、總鎮(zhèn)高杰、劉澤清、劉良佐,優(yōu)以禮數,為我藩屏,聽督臣(馬士英)察酌,應駐地方,相機固守。江北之兵聲既振,則江南之人情自安。黃得功已封伯,似應進侯;杰、澤清、良佐似應封伯。左良玉恢復楚疆,應照黃得功進侯。馬士英合諸鎮(zhèn)之功,爵賞似難異同。盧九德事同一體,聽司禮監(jiān)察敘。[8]131
弘光政權對江北的防御主要依靠江北四鎮(zhèn)。江北四鎮(zhèn)是指四總兵即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和高杰駐守長江以北所部及左良玉鎮(zhèn)守長江中游武昌所部。“其四鎮(zhèn)則各自劃地:[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安,……經理山東一路;高杰轄徐、泗,駐泗州,……經理開[封]、歸[德]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每鎮(zhèn)額兵三萬人,歲貢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兩,聽各鎮(zhèn)自行征取”[10]381。弘光四鎮(zhèn),每鎮(zhèn)額兵三萬由弘光朝廷供給糧餉防衛(wèi)江北。兵力皆出自南京各個衛(wèi)所。四鎮(zhèn)的兵力對弘光政權的防御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既可作為防守之地立穩(wěn)根基,又可以北進收復失地。
史可法對南京城防御設置兩道人工防線和四個作戰(zhàn)區(qū)域。由于長江的天然護城河作用,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和清軍需突破這三道防線,才能攻下南京。南炳文認為:“這一措置,給了黃、高、二劉很大的權力,將南京之北應屬朝廷直接管轄的堂奧之區(qū),變成了軍閥割據的藩籬之地,對驕將悍卒不能不說是很大的妥協退讓。但在朝廷無力限制他們的當時,這也是出于不得已的攏絡措施,目的在于寓進取于退讓之中,其間頗體現著史可法的一番苦心。”[11]4
江北四個作戰(zhàn)區(qū)域,由高杰、黃得功、劉澤清和劉良佐四鎮(zhèn)總兵各負專責,賦予很大的權力。這一戰(zhàn)略部署,反映史可法守淮安保南京,而忽視防御北方的威脅。但弘光政權無力供給軍餉,不得不讓步,賦予各鎮(zhèn)獨立的財政和軍事特權,各鎮(zhèn)自行征稅,籌措財政不必上繳,即“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jié)制,營衛(wèi)原存舊兵聽歸并整理,荒蕪田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采,仍許于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每鎮(zhèn)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聽各鎮(zhèn)自行征取”[9]167。這一系列調整,強化了弘光朝江北防御力量,也使四鎮(zhèn)將領的軍力進一步加強,逐漸發(fā)展成為藩鎮(zhèn)割據勢力。
3 武將擁兵互攻,南明軍事潰敗
南京防御體系和四鎮(zhèn)兵力的強化,壯大了藩鎮(zhèn)割據勢力,弱化架空了弘光帝的軍事指揮權。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甲辰,江督袁繼咸入見時面奏曰:“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朱由崧肯定袁繼咸之言,嘆氣說:“事已成,奈何?”[12]93斯特魯弗提供的弘光軍隊數據:“其中包括左良玉部的5萬人,江防軍4萬人、京師駐軍6萬人和史可法部3萬人。” 劉約瑟也有過一個統計,崇禎十七年冬,名義上弘光政權的軍隊超過100萬,具體兵力分布:“高杰4萬,黃得功3萬,劉澤清3萬,左良玉80萬,安慶駐軍(歸鳳陽指揮)1萬,鳳陽駐軍1萬,淮安駐軍1.5萬,黃斌卿1.8萬,李成棟(史可法指揮)4 000,吳材駐軍(水陸部隊)1萬,安慶駐軍5 000,總計100.2 萬(應為97.2萬-譯者)。”[13]289
3.1 結黨任親霸朝政
3.1.1 結黨霸朝政
馬士英與閹黨頗有淵源。崇禎三年(1630年),馬士英遷任山西陽和道副使,不久又升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后因事發(fā)被遣戍,不久又流寓于南京與逆案阮大鋮相結甚歡。崇禎十五年(1642年)六月,大學士周延儒升任馬士英為鳳督,不久后馬士英鎮(zhèn)壓農民軍立下戰(zhàn)功,其擁立新君又立新功,漸成弘光帝寵臣。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馬士英進入內閣,為將閹黨阮大鋮拉入內閣,堅持廢除經九卿評議選任大臣的制度,極力主張強化皇帝和權臣對官吏的任免權。阮大鋮曾伙同魏忠賢謀害東林黨,被崇禎帝定為閹黨逆案,永不敘用。圍繞能否起用阮大鋮,東林黨人和當權的馬士英及勛貴沖突激烈。崇禎十七年六月六日,馬士英提名阮大鋮任兵部右侍郎,大學士姜曰廣和戶部尚書高弘圖憤而辭職。九月初一,馬士英繞開九卿會議,以內傳直接任命阮大鋮為兵部添注右侍郎。第二年,馬士英又升阮大鋮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阮大鋮得勢后,迫害東林黨人,使閹黨在弘光朝霸占朝政。
馬士英起任鳳督后,為擴充實力,竭力結納當地軍事力量,與宦官盧九德及武臣黃得功、劉良佐結黨,對弘光政權的建立產生了直接影響。[14]106-122崇禎時,由宦官統率禁軍勇衛(wèi)營與農民起義軍作戰(zhàn)。“勇衛(wèi)營即騰驤、武驤四衛(wèi)也,其先隸御馬監(jiān),專牧馬。莊烈帝銳意修武備,簡應元及黃得功、周遇吉等訓練,遂成勁旅。”[15]6921勇衛(wèi)營始終由太監(jiān)劉元斌、盧九德分領監(jiān)軍,對農民軍征剿。“崇禎間,外有龍驤左、龍驤右、武驤左、武驤右四衛(wèi),為天子禁旅,名勇衛(wèi)營,后又選京衛(wèi)幼官應襲舍人六千充護衛(wèi),名選練營。而可用者,獨有勇衛(wèi)營而已。”[16]11盧九德為揚州人,幼曾侍福王朱常洵。盧九德在追剿農民軍時,逐漸與黃得功、劉良佐形成了一個軍事集團。弘光政權的外朝政治與宦官勢力形成不解之緣,盧九德出自福邸起了決定作用。崇禎十七年 (1644年)三月,“時南中咸知主兵者定議,已擬儀郎戒乘輿法物往粵矣。及士英歸鳳,則聞諸將高杰、黃得功、劉良佐畢集,大駭,呵之,知守備大檔盧九得(德)合盟,亦有所擁立,而所立者,福也。士英度勢之成也,敢無支吾,遂隱其前說,且乞附盟。于是士英稱定策矣”[17]192。“甲申(崇禎十七年)三月,先帝升遐。公與南兵部尚書史公議立君,未定,諸帥受太監(jiān)盧九德指,奉福藩至江上。”[7]393馬士英與閹黨軍事集團合力干擾弘光朝軍政,架空了弘光帝的指揮權。
3.1.2 任親信排異己
崇禎、弘光時期,尚有一人位居馬士英之上,這就是南京守備太監(jiān)韓贊周。韓贊周為陜西縣人,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任職守備南京。[5]5987崇禎初,阮大鋮因逆案罷官,避居金陵,與韓贊周相得甚歡,韓氏擁戴福王,可能受其影響。“京師陷,中貴人悉南奔,大鋮因贊周遍結之,為群奄言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俾備言于王,以潛傾[史]可法等。”[15]7940阮大鋮雖因韓得勢,不過,韓與閹黨馬士英之流政見有異,受“清流”中人青睞。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十五日,令“司禮太監(jiān)韓贊周、盧九德提督京營”[5]6099。弘光政權內廷以原南京守備太監(jiān)和鳳陽守備太監(jiān)共同輔政掌兵。這一局面,貌似韓地位比盧九德高,“立勇衛(wèi)營,聽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韓贊周節(jié)制”[5]6105,“定勇衛(wèi)營萬五千人”[5]6167,實是為閹黨派系掌管弘光朝廷的京營開辟了道路。韓贊周對朝政不滿,于次年正月“引疾去”[5]6179。
韓贊周辭職,其養(yǎng)子李國輔提督勇衛(wèi)營,馬士英又策劃逐太監(jiān)李國輔出南京。弘光元年(1645年)二月,馬士英誑李國輔請往開采浙江云霧山,將提督勇衛(wèi)營權授于己子馬錫。[7]167-168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十三日,“趙之龍召勇衛(wèi)營兵入城”[7]216。“大清兵下南京,圣安帝(即弘光帝朱由崧)遁,盧九德降。”[18]328馬士英之子馬錫則“為禁軍提督,大兵渡江,梟其首于市”[16]48。
3.2 裹挾賢臣,壯大閹黨勢力
四鎮(zhèn)皆受制于馬士英,馬士英對于史可法等人在朝中執(zhí)政不滿。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三日福王即監(jiān)國當天,馬士英就利用四鎮(zhèn),企圖逼迫史可法離開南京政治中心,劉澤清與高杰約史可法“過江共議”,“欲卸柄于馬士英也”[5]6083。馬士英還上書弘光帝,揭發(fā)史可法曾以“七不可立”反對擁立福王。四鎮(zhèn)設立后,五月十一日,馬士英排擠史可法,謂“有四鎮(zhèn)不可無督師”,督師“應駐揚州”,以“適中調遣”。五月十二日,史可法向弘光帝上疏,交出朝政并自請督師揚州。“如此則諸鎮(zhèn)各衛(wèi)其地,無不致力,而受成于督師,機不遙度,事不中制,士氣奮而民心定,江南庶幾可保矣。”[9]167馬士英逼史可法出南京,使史可法自請揚州督師。自此以后,馬士英任首輔,操縱朝政。史可法出鎮(zhèn)揚州,是為了居中調遣,協調四鎮(zhèn)之間的戰(zhàn)略布防,四鎮(zhèn)之外,另有鎮(zhèn)將左良玉駐守武昌,控扼長江上游。
四鎮(zhèn)為謀私利爭斗不斷,“藩鎮(zhèn)各自成軍,不相統率,司馬不得過而問焉”[19]252。組織力量擊退敵人需要協調軍事活動,史可法被馬士英所迫離開南京、出鎮(zhèn)揚州,親自指揮防御,著手調整各將領之間的關系,規(guī)劃新朝廷的北進作戰(zhàn)戰(zhàn)略。四鎮(zhèn)之將不受史可法節(jié)制,只聽馬士英指令調動。馬士英作為江北四鎮(zhèn)在弘光朝的代理人,使四鎮(zhèn)獲政治和財政利益。在弘光政權內部能夠清醒認識到清朝威脅、積極北上進取并付諸實際者,僅有史可法為首的少數人,多數人并不響應支持,還遭到朝中掌權的馬士英阻撓破壞。馬士英干擾史可法在四鎮(zhèn)的調解及北上進取的軍事活動,拒絕支援軍隊補給,扣押軍隊糧餉。“時高杰刻期進取開、歸,可法亟請餉于朝,而馬士英以鎮(zhèn)將與可法協為不利己,陰裁抑之。”[9]268史可法的部隊“直到順治二年(1645年)三月清兵大舉南下前,基本上沒有打過黃河,活動范圍始終被局限在江淮一帶”[11]54-58。
在馬士英的裹挾下,史可法自請出朝、督師江北,致馬士英控制弘光朝政,獨攬大權,摧毀軍政。“然而天方降割,權臣掣肘于內,悍將跋扈于外,遂致兵頓餉竭,疆圉日蹙,孤城不保,志決身殲,亦可悲矣!”[15]7034史可法提出建立江北四鎮(zhèn),導致四鎮(zhèn)控制朝廷,百姓生活困苦;史可法軍事能力不足,未能在河南、山東等黃河沿岸建立有效的軍事防御以抵御清軍。“以史閣部之設四鎮(zhèn),不設于山東河南,乃設于南畿數百里之內,此則閣部之第一失著。”[19]232史可法居官廉潔勤慎,但其決策失誤對弘光朝的損失不可低估。
3.3 軍隊腐敗,擁兵互攻掠百姓
弘光政權的腐敗,弱化了對武裝力量的控制和指揮。弘光朝加強京師防御,使擁有實力的四鎮(zhèn)將領擁兵自重,形成軍事割據。四鎮(zhèn)將領高杰、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無意抗清,卻要挾朝廷,擺開陣勢互相火拼。四鎮(zhèn)劃定好轄區(qū)之后,高杰、劉澤清隨即為爭奪揚州而互相攻擊。高杰又與黃得功勢如水火,互有攻伐,幸有史可法在兩人之間奔走調停,避免了進一步的沖突。
弘光政權的軍事制度無法適應實戰(zhàn)需要。四鎮(zhèn)將士掠奪攫取領土,聚斂財富,敲詐勒索駐地百姓,“各鎮(zhèn)挨戶打糧,民不堪命”[19]252,嚴重削弱了南明軍隊,加速了政權的崩潰。鎮(zhèn)守淮安的劉澤清“造第于淮安,規(guī)模壯麗,上擬王府,兵丁恣肆,百姓苦之[19]228,軍隊成為武將爭奪權力和利益的工具,軍隊搶劫和騷擾平民很普遍。弘光政權初期,高杰部在揚州殺人劫財,“時高杰送家口寄揚州,百姓閉門拒之,日尋干戈,可法親至杰營,曉諭百方,勸杰屯兵泗州。弘光即以可法坐鎮(zhèn)揚州彈壓四鎮(zhèn),民賴以安”[19]166。武將征召士兵, 擴充軍隊,缺乏軍餉就放縱搶劫。
弘光政權縱容武臣,武臣對軍隊疏于嚴管,造成軍隊內訌頻繁發(fā)生,紀律敗壞。順治元年(1644年)九月,駐泗州武將高杰在儀真之土橋襲擊駐廬州武將黃得功,史可法親臨和解。[9]257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高杰率部北上至睢州時,河南總兵許定國設計將高杰誘殺,許定國叛降清軍。[19]230-231軍隊的內訌削弱了戰(zhàn)斗力。軍事將領占領地方,謀取私利,朝廷卻無法指揮他們。甲申 (崇禎十七年)六月,臨淮士民因反對劉良佐在臨淮開鎮(zhèn),遭到攻擊。“劉良佐奏開鎮(zhèn)臨淮。士民張羽明等不服,臨淮士民戈尚友等亦奏叛鎮(zhèn)環(huán)攻,命撫按調和之。”[7]32弘光帝為滿足奢侈生活的需要,興建宮殿,搜刮民財,“修興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賞賜皆不以節(jié),國用匱乏”[7]104。皇室開支遠遠超過軍事開支,弘光軍隊處于潛在的脆弱狀態(tài)。
3.4 “清君側”引發(fā)自殘,清軍乘機南下
弘光政權軍事實力最強的左良玉駐扎武昌,以幾十萬重兵抵御張獻忠東下,拱衛(wèi)上游南京。在晚明將領中,左良玉是張獻忠的勁敵。崇禎皇帝封左良玉為寧南伯,弘光帝為爭取左良玉,晉封其為寧南侯,并任命左良玉信任的文官袁繼咸出任湖廣總督。[15]6988但是,左良玉與四鎮(zhèn)及馬士英素有積怨,馬士英和江北四鎮(zhèn)控制決策權,左良玉被排除在決策權之外。左良玉企圖以“假太子”案控制朝政。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底,左良玉擁護“北來太子”,以“清君側”為由,發(fā)兵南京。“清君側”的目標是馬世英。時逢清軍南下,兵臨江北,使弘光政權陷入內憂外患的境地。馬士英為保自身權位,不顧江北防線,抽調江北汛地之兵西阻左良玉,調阮大鋮、黃得功等率兵堵截并鎮(zhèn)壓左良玉的軍隊,命令劉良佐將江北的防御力量撤回到長江以南,造成清軍南下如入無入之境,這等于是自動將領土留給清軍。馬士英又命令史可法調轉兵力,渡江保衛(wèi)南京。由于威脅實來自清軍,而非左良玉,史可法不主張撤兵,向弘光帝上疏留鎮(zhèn)防江:“從古守江者必先守淮,守淮者必先守河,此一定之形勢也。今北兵自西來,直抵歸德,我之河險已失矣。……萬一長淮不守,直抵江上,沿江一帶,無一堅城,其誰為御之。不知士英何以蒙蔽至此。”[6]21-22馬士英認為阻止左良玉比阻止清軍更重要:“爾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若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12]140史可法不得不奉詔應援南京,造成清軍南下勢如破竹。弘光元年四月,多鐸率領清軍渡過淮河,臨近揚州城,馬士英命令史可法返回揚州抵抗清軍。弘光政權匆忙集結的軍隊難以防御,清軍輕而易舉地突破江北防線,迅速占領揚州,進入南京。左良玉被黃得功打敗,病死在九江,其子左孟庚率軍向清軍投降,極大地增強了清軍的實力。
弘光政權建立四鎮(zhèn)是為穩(wěn)定江北、抵御清軍南下。左良玉駐守湖北地區(qū),守住南京上游,可以西守張獻忠,北守李自成,這對于穩(wěn)定明朝后方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左良玉率軍東下進攻南京,瓦解了江北防線,清軍借機南下兵臨江淮。“清君側”未能消滅馬阮集團,反而加速了弘光政權的滅亡。
弘光政權軍事腐敗,四鎮(zhèn)將領只關心爭奪權力和領土而不顧戰(zhàn)局,惟恐自身利益受損。面對清軍占領北京、攻克太原,追擊山西、陜北大順農民軍的嚴重軍事形勢,軍隊陷入內戰(zhàn)內訌,將領無忠心報國,忙于自相殘殺,害怕與清軍作戰(zhàn),拒不出兵。弘光政權在內憂外患之時,幻想與清軍議和。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清軍大舉進兵揚州,叛軍不戰(zhàn)而降,投降后還參加了對揚州的占領。清軍殺害史可法,屠揚州城,弘光朝構筑的江北防線徹底崩潰。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清軍兵分三路、勢如破竹,直抵長江一線,僅用三個月時間就占領了江南和江北。由于清軍兵力有限,南明軍隊的投降在推動清軍南下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國家大禍,無不以四鎮(zhèn)釀成。而厥后四鎮(zhèn)身死,數十萬驕悍之兵, 俱變?yōu)閾樘弧!盵19]231-232弘光帝得知清軍渡江,五月初十日拂曉騎馬奔出南京城,逃至蕪湖投奔黃得功。五月十五日,南京守備勛臣趙之龍率領南京數百文武官員降清。隨后,清兵追上奉弘光帝南奔的黃得功,黃得功中矢身亡,屬下左協總兵田雄和右協總兵馬得功降清,并將弘光帝獻給清豫王多鐸。弘光帝被押至北京處死,留都南京終究未能贏得明朝偏安一隅。
4 結 論
弘光政權建立后,強化軍事領導權,并按照北京的格局整頓守軍及南京防御體系;廢除了南京留都體制,改設京營戎政制度;強化四鎮(zhèn)兵力;賦予各鎮(zhèn)獨立的財政和軍事特權。四鎮(zhèn)借機發(fā)展壯大,成為藩鎮(zhèn)割據勢力。四鎮(zhèn)將領無忠君愛國之志,高杰、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各自為政,無意抗清,卻要挾朝廷,擺開陣勢互相火拼。左良玉以“清君側”為由,東下發(fā)兵南京。馬士英為保自身權位,抽調江北之兵堵截左良玉,致使清軍在南明軍隊爭斗中輕而易舉地突破江北防線,加速了弘光政權的滅亡。由于弘光朝志在討賊,實行“聯清滅順”的錯誤戰(zhàn)略,沒有清醒地認識到清兵的致命威脅,武將文臣抵抗意志不強,擁兵割據互攻,速亡是其必然的結果。
弘光政權迅速滅亡的軍事原因,其教訓足以警示后世。一是弘光皇帝兵權旁落,決策失誤,任將失察,導致統兵將領擁兵自重,控制朝廷,內訌互攻,近百萬軍隊毫無戰(zhàn)力。四鎮(zhèn)之外,鎮(zhèn)守武昌的左良玉以“清君側”起兵討逆,自相殘殺,加速了弘光政權的滅亡。二是兵防體制不適應防御和實戰(zhàn)需要。面對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夾擊,弘光政權仍沿用北京防衛(wèi)格局,將南京守備體制改為京營戎政制度,繼承了北京防衛(wèi)的缺陷,削弱了新的敵情下自我防衛(wèi)功能。三是弘光政權敵我不分,認敵為友,采取“聯清滅順”戰(zhàn)略,引敵入侵,加速了南直隸的軍事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