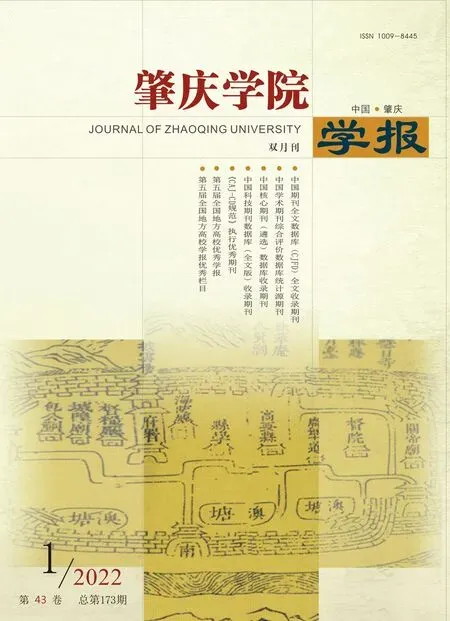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黨解決財政困難的做法與啟示
陳 曦,黃鐵苗
(1.肇慶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 肇慶 526061;2.中共廣東省委黨校 經(jīng)濟學教研部,廣東 廣州 440100)
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我們要用歷史映照現(xiàn)實、遠觀未來,從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百年奮斗中看清楚過去我們?yōu)槭裁茨軌虺晒Α⑴靼孜磥砦覀冊鯓硬拍芾^續(xù)成功……”。以史為鑒,才能開創(chuàng)未來。在建黨百年華誕之際,回首篳路藍縷創(chuàng)業(yè)路,不僅是對光榮傳統(tǒng)與精神譜系的弘揚與繼承,更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光明前景的展望。
五四運動的開展引領(lǐng)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fā)展,此后我國的馬克思主義與俄國經(jīng)驗在中國迅速傳播。中國工人運動的興起與馬克思主義相結(jié)合,推動了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新的革命領(lǐng)導核心由此產(chǎn)生。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共產(chǎn)黨從53名黨員與嘉興南湖的一條小船,迅速成長為控制600萬平方公里土地(建國時西藏、云南、貴州、四川等地尚未解放),黨員448萬人的大黨。在驚異于中國共產(chǎn)黨快速取得的偉大成就時,不禁要問為什么中國共產(chǎn)黨能夠帶領(lǐng)全國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于這一問題,已有研究的觀點主要包括三點:一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二是武裝斗爭;三是黨的建設(shè),即“三大法寶”[1]。對于這一觀點,學界的認識較為統(tǒng)一,已有研究大多以這三點作為答案。除此之外,革命的物質(zhì)保障問題也不應(yīng)忽略,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沒有物質(zhì)保障是難以實現(xiàn)革命勝利的。黨的建設(shè)、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與發(fā)展,特別是武裝斗爭都要以經(jīng)濟為基礎(chǔ)。誠如毛主席所說:“我們不能餓著肚子去‘正誼明道’,我們必須弄飯吃……離開經(jīng)濟工作而談‘革命’,不過是革財政廳的命,革自己的命,敵人是絲毫也不會被你傷著的[2]465。”由于內(nèi)外反動勢力的壓迫,資金來源有限,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武裝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大多數(shù)時間的財政狀況都是困難的。從建黨初期各地黨組織建立與刊物(如《新青年》)運營的經(jīng)費缺乏到1927年后由于封鎖造成的物質(zhì)短缺都可說明我黨當時困難的財政狀況。那么,在物質(zhì)條件困難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黨是如何克服財政困難,從而帶領(lǐng)全國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
通過對文獻的梳理發(fā)現(xiàn),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各個時期,由于革命環(huán)境的變化,我黨解決財政困難的方法存在較大差異。本文將分兩個時期對其進行梳理,并得出啟示。
二、依賴外援時期(1920—1927)
從1920 年各地醞釀并建立共產(chǎn)主義小組,到1921 年9 月前,我黨的財政來源非常不穩(wěn)定且捉襟見肘。如1920年12月,李漢俊接替去廣州的陳獨秀任中共上海支部書記。但由于經(jīng)費無著,李漢俊讓包惠僧去廣州請回陳獨秀,或?qū)Ⅻh的機構(gòu)遷至廣州,以解決黨在上海的經(jīng)濟困難。連包惠僧南下廣州的15元路費都是臨時找人借的[3]。如《新青年》作為中共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機關(guān)報,其內(nèi)容應(yīng)是較為審慎嚴肅的。但是,由于經(jīng)費的短缺,編輯部不得不在刊物中刊登一些俗氣的商業(yè)廣告,從而造成了讀者不滿[4][5]。即使這樣,由于經(jīng)費無著,《新青年》也不得不于1922 年7 月休刊。又如中共一大時,陳公博匯報說:“我們感到最遺憾的是缺少錢。《勞動界》停刊了,兩個工人工會也得停辦。因為:第一,經(jīng)費困難;……我們的機關(guān)報是《社會主義者》日報,該報每月需要七百元,很難繼續(xù)下去[6]。”造成這一境況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黨費的收入十分有限。黨員多半或收入較低,或根本沒有穩(wěn)定收入。再加上中共早期黨員人數(shù)很少,“一大”時只有53 人,能交黨費者不多,即使大半都能按規(guī)定交納,總的數(shù)量也極其有限,根本不足以維持黨開展各方面工作的現(xiàn)實需要[7]。另一方面,由于陳獨秀對于中國革命獨立性的擔憂,1921 年9 月前,黨內(nèi)對于共產(chǎn)國際的援助也抱有抵觸情緒[8]。所以這一時期,中國共產(chǎn)黨雖然接受了一些共產(chǎn)國際的援助(如對《新青年》的短期資助,對一大召開費用的支持),但數(shù)量較少且不穩(wěn)定。
1921年9月后陳獨秀對于共產(chǎn)國際援助的看法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變。當時陳獨秀被逮捕,中共設(shè)法救援,卻拿不出保釋金。后來靠共產(chǎn)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馬林支付5000元保釋金,才將陳獨秀救出。并且這一事件后馬林也表示中國共產(chǎn)黨與共產(chǎn)國際的關(guān)系并非上下級,在日常工作中的關(guān)系是“商談”,而非命令[9]。自此,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較為穩(wěn)定的接收來自共產(chǎn)國際的援助。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給共產(chǎn)國際提交的報告中寫道: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guān)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xié)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10]。由此可見,當時我黨解決財政困難的主要方式是接受共產(chǎn)國際的援助。尤其1925年“五卅運動”后,中國共產(chǎn)黨影響力大幅增強,黨員數(shù)量從“四大”時不足千人,到1926年猛增到萬人規(guī)模,共產(chǎn)國際給予我黨的援助也隨之增加到6000元每月。隨著北伐戰(zhàn)爭的爆發(fā),我黨的活動強度進一步提高,經(jīng)費需求也隨之增長,到1927年初,共產(chǎn)國際安排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預算經(jīng)費已達12萬元[7]。
綜上可見,我黨在1920年到1927年這一時期的經(jīng)費來源主要依賴于共產(chǎn)國際的資助。但這一資金獲取形式也對當時我黨的發(fā)展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這一負面影響主要指的是經(jīng)濟上不獨立而受制于人。雖然為勸說陳獨秀接受共產(chǎn)國際資助,馬林曾表示由中共完全負責中國工作,共產(chǎn)國際只是與中共就相關(guān)政策進行商議。但在后來的實踐中,卻并非如此。在馬林看來,作為共產(chǎn)國際的代理人,駐華代表對中共中央進行“監(jiān)護”是符合國際共運邏輯的,維護共產(chǎn)國際內(nèi)部黨的紀律也是無可厚非的,于是其在指導方式上往往采取“居高臨下”“藐視中央”的態(tài)度,甚至在遇到黨內(nèi)不同意見時就以所謂“小組織問題”進行壓制[11]。到了鮑羅廷駐華時期,這種專斷的指導方式更是進一步演變?yōu)榘k一切的家長制作風[12]。由于共產(chǎn)國際駐華代表對中國國情認識的不深刻,很難保證這種“一言堂”式的“指導”方式不對中國革命形式出現(xiàn)誤判并做出錯誤決策。共產(chǎn)國際與駐華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與妥協(xié)政策對大革命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三、從依賴外援到手段多元化(1927—1949)
1927年后由于革命根據(jù)地的建立,我黨解決財政困難的手段逐漸多元化。概括來說就是開源與節(jié)流兩方面。開源包括通過多渠道獲取外援,適當?shù)耐恋卣撸粤Ω慕?jīng)濟建設(shè)三種方式增加財政收入。而節(jié)流則是通過勤儉節(jié)約與反貪腐兩種方式堵住財政損失的漏洞。
(一)多渠道獲取外援
1927年到1934年長征之前,外援依然主要以共產(chǎn)國際的援助為主。據(jù)統(tǒng)計,1927年共產(chǎn)國際共向我黨提供133.2674萬盧布、30.4萬美元援助;1928年為 25.5 萬盧布、27.1352 萬美元;1929 年為 22.664 萬美元;1930 年為 23.33 萬墨西哥元、8.9 萬美元;1932年為2400金盧布、10.5016萬美元;1933年為14.7216萬美元;1934年為10萬盧布、9.7216萬美元、5萬墨西哥元[13]。這一時期雖然共產(chǎn)國際依然在給予我黨援助,但援助額度并沒有隨著革命形式的推進而擴大,相反還在逐年收縮,并且也十分不穩(wěn)定。如193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寫信給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主席團,說停撥1930年5月、6月經(jīng)費,給中共中央工作帶來困難,要求繼續(xù)給中共撥出經(jīng)費[14]142。6 月25 日,向忠發(fā)寫信給在莫斯科的周恩來,告知“最近三個月我們沒能從任何地方搞到錢, 而遠東局正式通知我們說, 它無法提供幫助”[14]208。1933 年 8 月 11 日,中共上海中央局負責人李竹聲給皮亞特尼茨基和王明發(fā)電報說:我們的財政狀況很危急,7 月我們只收到61900 法郎和2000 元,我們不得不停止聯(lián)系和把機關(guān)人員壓縮到最危險的極限[15]。除此之外,接受共產(chǎn)國際援助也使李德與王明在黨內(nèi)成為領(lǐng)導者,為后來我黨陷入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以及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埋下了伏筆。長征期間,由于四處轉(zhuǎn)戰(zhàn),共產(chǎn)國際的援助完全斷絕。直到1935 年11 月才重新建立聯(lián)系。1935年后,我黨又斷斷續(xù)續(xù)從共產(chǎn)國際處累計收到一百余萬美元[16]。
但此時,共產(chǎn)國際的援助已不再是我黨獲得外援的唯一方式。由于統(tǒng)一抗日,1936年到1940年期間,國民政府的撥款也成為根據(jù)地外援收入的一部分。國共一致抗日初期,陜北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僅有4.5萬人,國民政府撥給軍費63萬元法幣,尚可支撐。但八路軍擴張速度極其迅速,到了1940年,部隊已擴張到40萬人。但國民政府所撥給之軍費卻只增加到75萬元[17]。并且1937年后,法幣貶值迅速。1937年抗戰(zhàn)初期,100元法幣可以購買兩頭黃牛,而到了1940年則只可以買到一頭牛犢。毛主席在《邊區(qū)的貨幣政策》一文中曾寫道:“在抗戰(zhàn)最后勝利之前,法幣一定繼續(xù)跌價,法幣有逐漸在華北滅跡之可能。”[18]
邊區(qū)政府經(jīng)費需求的渠道中,國民政府的經(jīng)費支持作為一種外援方式顯然不能滿足其巨大的需求。因此,必須開拓更廣泛的渠道獲取外援。除國民政府撥款外,邊區(qū)政府的外援還包括了愛國華僑與國內(nèi)愛國人士對共產(chǎn)黨武裝的大力捐助。抗戰(zhàn)開始后宋慶齡組織的“保衛(wèi)中國同盟”與“中國工業(yè)合作國際委員會”共募集捐款約500萬美元,大部分支援了中共抗戰(zhàn)。據(jù)陜甘寧邊區(qū)的統(tǒng)計,僅從1938年10 月至 1939 年 2 月的 5 個月時間里,海外及后方捐款共達法幣130 多萬元。另據(jù)八路軍供給部的統(tǒng)計,從1937 年至1941 年,各部隊上繳的捐款有賬可查的共為892.4 萬元[19]。雖然上述外援方式能夠極大的改善邊區(qū)政府的財政狀況,但這一途徑缺乏穩(wěn)定性。1940年后,國民黨反動派懾于共產(chǎn)黨武裝的發(fā)展速度,不僅不再對八路軍撥給軍費,還對邊區(qū)政府施行嚴格的封鎖政策。雖然我黨通過地下交通仍然能獲得部分外援,但外援獲取難度大大提高,外援資金急劇減少。
(二)適當?shù)耐恋卣?/h3>
從井岡山時期開始,我黨通過一系列土地政策獲得了穩(wěn)定的收入來源。從土地政策獲得的財政收入可分三個方面:第一,通過沒收地主、軍閥、豪紳、反動派的財產(chǎn)直接獲得收入。在湘鄂贛革命根據(jù)地,“經(jīng)濟來源是到江西去捉土豪,捉到一個至少幾百元,多或幾千元或萬元”[20]。這一點在1931年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土地法》中亦有明確說明。第二,在1928年《土地法》中規(guī)定竹山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不予分配給農(nóng)民,所得收入歸政府支配[21]。到1931年《中華蘇維埃土地法》中則進一步規(guī)定森林、牧場、江河等公共資源歸政府管理。這些森林、江河、牧場資源也直接為根據(jù)地提供了資金來源。第三,則是通過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nóng)民,促進其生產(chǎn),進而獲得稅收。1928年《土地法》中對稅率進行了明確規(guī)定,土地稅率分為15%、10%、5%三種[21],一般按照百分之十五征收,遇到特別情況或天災可減免土地稅。農(nóng)民群眾的土地稅率負擔由以往地主豪紳的60%以上下降為紅色政權(quán)的20%以下,農(nóng)民生產(chǎn)積極性急劇增加,淳樸的農(nóng)民群眾在交納稅額糧食之外自愿捐贈大量糧食作為紅軍軍費[22]。由于采用輕徭薄賦的稅收政策,稅源隨之增多,充實了蘇區(qū)的收入來源。
1935年10月到達延安,短暫施行了井岡山時期的土地政策后,我黨的土地政策就根據(jù)革命形勢的需要發(fā)生了一系列變化。1935年12月開始,對富農(nóng)的土地,不再沒收[23]。1937 年 2 月,發(fā)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后則對地主的土地也不再施行一概沒收政策,只對大地主并當漢奸者的土地與財產(chǎn)進行沒收[24]。這些土地政策顯然對陜甘寧邊區(qū)的財政收入十分不利,但卻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條件。
直到解放戰(zhàn)爭時期,我黨才重新施行與井岡山時期相似的土地政策。1947年10月頒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明確“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森林、礦山、河流等公共資源歸政府管理。除與井岡山時期土地政策意義大致相似外,這樣大規(guī)模的分地運動,亦使一些出身貧苦的國民黨基層官兵家庭受益,極大的瓦解了其斗志。
(三)自力更生的經(jīng)濟建設(shè)
我黨在井岡山與延安時期的經(jīng)濟建設(shè)大致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自力更生發(fā)展生產(chǎn);二是活躍貿(mào)易;三是建立配套的財政與金融機構(gòu)。
1. 自力更生發(fā)展生產(chǎn)。井岡山時期與1940 年后,國民黨反動派長期對根據(jù)地施行封鎖政策,大量的根據(jù)地所需物資需要靠當?shù)刈约荷a(chǎn)。井岡山時期,通過土地法沒收地主土地,極大地提高了根據(jù)地軍民的生產(chǎn)積極性。土地稅收基本可以解決紅軍的吃飯問題。后來提起這一時期,毛主席說:“那時,因為江西農(nóng)民比較富庶的條件,還不需要我們自己動手解決糧食。”[2]495但到了陜北后,情況又有不同,雖然通過保障土地私有制,解決貧苦農(nóng)民耕牛、農(nóng)具、肥料、種子的困難,以及獎勵移民的方式鼓勵根據(jù)地群眾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僅1941年便開荒六十萬畝,增加糧食產(chǎn)量四十萬擔[25]。但由于八路軍發(fā)展迅速,光靠根據(jù)地群眾生產(chǎn)依然不足以彌補根據(jù)地龐大的開支。由于稅負沉重,當時甚至發(fā)生了諸如“雷公事件”這類事情。這使黨中央開始思考給農(nóng)民減負的問題。具體方法就是開展自力更生的大生產(chǎn)運動。
為了積極響應(yīng)毛主席1939年在干部動員大會上提出的“自己動手”的口號,根據(jù)地的大生產(chǎn)運動就這樣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了。據(jù)《經(jīng)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所述:從井岡山時期開始,中共中央就在江西蘇區(qū)建立了一部分公營工商業(yè)(如公營商店、藥店、被服廠),并鼓勵各機關(guān)學校種菜養(yǎng)豬,補助伙食。1938年,陜北的留守部隊就開始小規(guī)模的進行種菜、養(yǎng)豬等農(nóng)副產(chǎn)業(yè)的生產(chǎn)了,其目的是改善戰(zhàn)士生活。但1941年后各單位的生產(chǎn)行為就不僅是為改善吃穿問題了,而是要解決迫切的財政困難[2]460-462。
最主要的辦法就是軍民開墾荒地。1942 年邊區(qū)軍民開荒21萬多畝,1943年增加到77萬畝,1944年又猛增到120 多萬畝。到1945 年,邊區(qū)軍民大部分做到了“耕三余一”,即種三年地,打的糧食夠四年吃,部分還做到了“耕一余一”[26]。除此之外,邊區(qū)的政府、部隊、黨政機關(guān)還分階段發(fā)展了工業(yè)、商業(yè)。到1943年,公營經(jīng)濟所汲取的財富已經(jīng)超過了人民群眾繳納的糧食與稅收,其重要性可見一斑[2]459。
2. 活躍商業(yè)。根據(jù)地的財政困難不僅限于吃飯穿衣的問題,還包括工業(yè)品的匱乏。根據(jù)地一方面需要通過貿(mào)易打破封鎖,直接獲得工業(yè)品。另一方面需要通過貿(mào)易所獲得的利潤與稅收(公營商業(yè)直接獲得利潤,私營經(jīng)濟可提供稅收)充實財政,進而購買根據(jù)地外的工業(yè)品。
井岡山時期的做法是掃除國民黨反動派的層層關(guān)卡,興辦圩場與公營商店,鼓勵貿(mào)易。掃除關(guān)卡障礙為根據(jù)地的貿(mào)易提供了基礎(chǔ)條件。在此基礎(chǔ)上,根據(jù)地建立并活躍了圩場經(jīng)濟。如在黃洋界興辦紅色圩場,施行低稅收政策,吸引了大量白區(qū)的商人帶著急需的藥材、鹽等進入紅區(qū)[27]。又如改造的草林圩場也非常活躍,“草林圩上逢圩日(日中為市,三日一次),到圩二萬人,為從來所未有。”[28]
到了延安時期,貿(mào)易則更加成為根據(jù)地解決財政困難的重要手段。毛主席在1941年指出:出入平衡是解決邊區(qū)財政困難的關(guān)鍵,如能使畜牧業(yè)與商業(yè)繁榮,收取一定數(shù)量的羊稅與商稅,則財政問題基本可以得到解決[29]。為實現(xiàn)貿(mào)易目標,延安時期的做法是通過輕稅率吸引商人。陳嘉庚訪問延安時,南漢宸對他說:“我們支持本地商人和外面商人在邊區(qū)做生意,對他們辦的商店抽稅很輕很少。”[30]以邊區(qū)重要的財源——鹽為例,邊區(qū)鹽稅最低時僅占鹽價3.1%(1943年6月),多數(shù)時間鹽稅占鹽價5%-6%[31]。可見邊區(qū)稅率是十分低的。
除此之外,中國共產(chǎn)黨還非常注重民族資本家在根據(jù)地經(jīng)濟建設(shè)中的作用,如1940年10月毛主席寫給胡服、陳毅的信,就著重提到要邀請民族資本家參與根據(jù)地經(jīng)濟建設(shè)[32]。在《陜甘寧邊區(qū)施政綱領(lǐng)》中則更加明確的提出:“發(fā)展工業(yè)生產(chǎn)與商業(yè)流通,獎勵私人企業(yè),保護私有財產(chǎn),歡迎外地投資,實行自由貿(mào)易……歡迎海外華僑來邊區(qū)興辦實業(yè)。”[25]等一些列鼓勵民族資本參與根據(jù)地建設(shè)的措施。這些措施為根據(jù)地的經(jīng)濟發(fā)展提供了重要動力。
3. 配套財政與金融機構(gòu)。從井岡山時期到延安時期,從1928 年《土地法》的完全公有化,到鼓勵小商業(yè),再到后來鼓勵民族資本參與根據(jù)地建設(shè)。經(jīng)濟形式是在不斷增多的,必然帶來經(jīng)濟管理的復雜化。這就要求我黨建立與之匹配的機構(gòu),以制定相適應(yīng)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并對根據(jù)地的經(jīng)濟進行管理。由此,我黨成立了一系列高配置且相互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的經(jīng)濟管理機構(gòu)。井岡山時期的財政與金融機構(gòu)還較為簡單,財政機構(gòu)主要包括各級政府的財政部門,作用就是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與收稅。金融機構(gòu)則以1932年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銀行為代表,由毛澤民擔任首任行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銀行成立后,推行銀本位貨幣制度,規(guī)定一元紙幣等于一個銀元[33],并且盡可能避免紙幣的濫發(fā)。毛主席強調(diào):“國家銀行發(fā)行紙票的原則,應(yīng)該根據(jù)國民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要,財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絕對必需的。”[34]這一系列做法穩(wěn)定了蘇幣的地位,促進了蘇區(qū)經(jīng)濟的發(fā)展。
延安時期,貿(mào)易、生產(chǎn)、貨幣等關(guān)系更加復雜。中國共產(chǎn)黨則更加注重財政與金融機構(gòu)的建設(shè)。各種財政與金融機構(gòu)由林伯渠、賀龍、陳云主導的財經(jīng)委員會統(tǒng)一領(lǐng)導,制定陜甘寧邊區(qū)與晉綏根據(jù)地財經(jīng)政策并調(diào)整稅收、貨幣、貿(mào)易關(guān)系,使邊區(qū)財政手段與貨幣手段的運用能夠緊密配合。如南漢宸主導的邊區(qū)財政廳在皖南事變后,陜甘寧邊區(qū)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通過“三板斧”①第一,糾正“片面施行仁政”的作法,組織征糧工作;第二,集中收購陜甘寧地區(qū)生產(chǎn)的食鹽,實行專賣,嚴禁走私,集中對國統(tǒng)區(qū)交易;第三,經(jīng)營“土特產(chǎn)”,以陜北土特產(chǎn)從國民黨地區(qū)交換過來了大量革命所必不可少的軍用和民用物資。,迅速穩(wěn)定了邊區(qū)的財政狀況。又如陜甘寧邊區(qū)銀行則比井岡山時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銀行發(fā)揮了更大的作用,這一作用不僅體現(xiàn)在發(fā)行貨幣,抵消法幣貶值的影響。還為陜甘寧邊區(qū)的工商業(yè)發(fā)展提供了貸款,為這些行業(yè)度過艱難時期提供了重要保障[35]。除此之外,陜甘寧邊區(qū)銀行還為后來新中國金融事業(yè)(如中國人民銀行的建立與人民幣的發(fā)行)提供了寶貴的經(jīng)驗與人才支持。
(四)勤儉節(jié)約,艱苦奮斗
我黨勤儉節(jié)約,艱苦奮斗的精神也是新民主主義時期錢少而夠用的重要保障。從井岡山時期開始,包括毛澤東、朱德等領(lǐng)導人多次指出,艱苦奮斗、厲行節(jié)約、反對鋪張浪費是我黨的優(yōu)良作風。在這個精神的鼓舞下,我黨在井岡山開展了“節(jié)省每一個銅板為著革命和戰(zhàn)爭事業(yè)”的節(jié)省運動。據(jù)統(tǒng)計僅1934年4至7月,中央各部在擴大紅軍和保衛(wèi)隊員6萬多人需增加開支的情況下,反而節(jié)約了150 余萬元[36]。節(jié)約精神在之后的革命戰(zhàn)爭年代一直被發(fā)揚與傳承。如1941年6月毛主席給林伯渠信中說:“凡必不可免之錢,予以慨允……其原則就是‘必不可免’四字”。[37]再如毛主席多次提到精兵簡政問題就是對節(jié)約思想的發(fā)展。精兵簡政就是要通過精簡機構(gòu)與人員,達到減少開銷,充實基層生產(chǎn)的目的[38]。到七屆二中全會時,毛主席更是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兩個務(wù)必”,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務(wù)必使同志們繼續(xù)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領(lǐng)導人以身作則是我黨勤儉節(jié)約、艱苦風斗精神能夠長期保持的重要保障。正如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所寫:做了十年紅軍領(lǐng)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chǎn),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服。
(五)打擊貪腐,保持廉潔
打擊貪污腐敗是我黨的傳統(tǒng)手段。自井岡山時期“三大紀律”的提出,就奠定了我黨我軍始終對貪腐保持零容忍的傳統(tǒng)。如井岡山時期的謝步升案、左祥云案、唐達仁案就是明證。延安時期依然如此,《陜甘寧邊區(qū)施政綱領(lǐng)》明確對共產(chǎn)黨員貪污治以重罪,并提出俸以養(yǎng)廉原則[25]。又如1940 年陳嘉庚訪問延安后說:“縣長既是民選,官吏如貪污五十元者革職,五百元的槍斃,余者定罪科罰,嚴令實行,犯者無情面可袒護優(yōu)容。”[39]
這說明,我黨對于貪污問題的態(tài)度是堅決的,必須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縱觀革命戰(zhàn)爭年代,因為對貪污的高壓態(tài)勢,我黨的貪污腐敗的現(xiàn)象極少出現(xiàn)。這不僅封死了由貪污腐敗造成財政損失的口子,也塑造了我黨廉潔奉公的形象,與貪腐盛行的國民政府形成鮮明對比。這是我黨能夠獲得社會各界同情與支持,取得革命最終勝利的重要原因。
四、啟示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上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黨解決財政困難的措施和精神對于我們今天仍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一)堅持自力更生與財政來源多元化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經(jīng)驗說明,財政來源過于單一,容易被人“卡脖子”。只有靠我們自己發(fā)展壯大,才能夠從根本上把握自己的前途,而不受外來干涉。如今,隨著我國國力的快速增長,西方國家越發(fā)害怕中國向全球產(chǎn)業(yè)鏈頂端攀升,對我國圍堵也越發(fā)明顯。芯片封鎖、中美貿(mào)易戰(zhàn)、疆棉事件等不勝枚舉。這與1940 年后國民黨反動派對我根據(jù)地封鎖何其相似。可以預見,西方對我國經(jīng)濟的打壓還會進一步升級至全產(chǎn)業(yè),并且這一壓力將長期存在。在此境況下,以前依賴西方市場的老路將會越來越難走,必須使經(jīng)濟發(fā)展動能多元化,并做好過苦日子的準備,發(fā)揮自力更生精神,才不會被人“卡脖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關(guān)鍵核心技術(shù)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40]自主創(chuàng)新是攀登世界高峰的必由之路。只有自己掌握自己的經(jīng)濟命脈,才能“從實力地位的角度出發(fā)”,維護我們的利益。
(二)繼續(xù)發(fā)揚勤儉節(jié)約與艱苦奮斗作風
勤儉節(jié)約、艱苦奮斗作風是我黨在革命戰(zhàn)爭時期能夠戰(zhàn)勝財政困難的重要原因。這不僅為革命事業(yè)節(jié)省下了大量資源,也使勤儉節(jié)約,艱苦奮斗的作風根植于我黨的精神譜系之中。對比革命戰(zhàn)爭時期,我國財政狀況已大大改善,但國大則事多,仍然有許多領(lǐng)域(如三農(nóng)、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科技、國防投入等)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然而,當前一些干部群眾勤儉節(jié)約思想逐漸淡化,出現(xiàn)奢侈攀比現(xiàn)象。這不僅極大的浪費了資源,同時也在消磨干部群眾艱苦奮斗的意志。需知“解決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xiāng)區(qū)域發(fā)展差距、實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遠。”[41]為實現(xiàn)接續(xù)而來的偉大目標,我們必須始終保持勤儉節(jié)約、艱苦奮斗的作風,乘勢而上、再接再厲。
(三)堅決筑牢反貪污腐敗的制度籠子
對貪污腐敗現(xiàn)象的堅決打擊不僅是防止資源流失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保持黨的先進性,提高執(zhí)政能力,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的根本保障,更是共產(chǎn)主義政黨的應(yīng)有之義。在革命戰(zhàn)爭時期,如果放任貪污腐敗現(xiàn)象,那么我黨的先進性便無法體現(xiàn),就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便無從談起。
在目前復雜的全球化形勢下,腐朽文化也在不斷影響著我黨的先進性、純潔性。一些黨員干部在這些因素的沖擊下消極腐敗、脫離群眾,這對黨的執(zhí)政能力與形象產(chǎn)生了負面影響。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我們黨作為執(zhí)政黨,面臨的最大威脅就是腐敗。”[42]歷史也多次證明腐敗是能夠亡黨亡國的。因此,經(jīng)濟越是發(fā)展我們越要對腐敗保持高壓。革命戰(zhàn)爭年代對貪腐嚴格立法、嚴格執(zhí)法,筑牢制度籠子的做法對今天仍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四)切實加強黨的領(lǐng)導
上述革命戰(zhàn)爭時期解決財政困難的一系列做法的領(lǐng)導核心是中國共產(chǎn)黨。如果沒有黨的堅強領(lǐng)導,面對當時艱苦卓絕的環(huán)境,自力更生、發(fā)展經(jīng)濟、保持黨的勤儉節(jié)約、艱苦奮斗精神與清廉作風等都無從談起。歷史也反復證明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與國家的發(fā)展不能離開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如今我國雖然已躍然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但是所面臨的是更加錯綜復雜的經(jīng)濟形勢,遠遠超過了革命戰(zhàn)爭時期。面對復雜的國內(nèi)國際經(jīng)濟環(huán)境,更加需要加強黨的領(lǐng)導。黨的領(lǐng)導是我們實現(xiàn)更加富裕、全面的社會主義強國目標的根本保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經(jīng)濟工作是中心工作,黨的領(lǐng)導當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體現(xiàn)。”[43]這是我們在新形勢下做好經(jīng)濟工作的根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