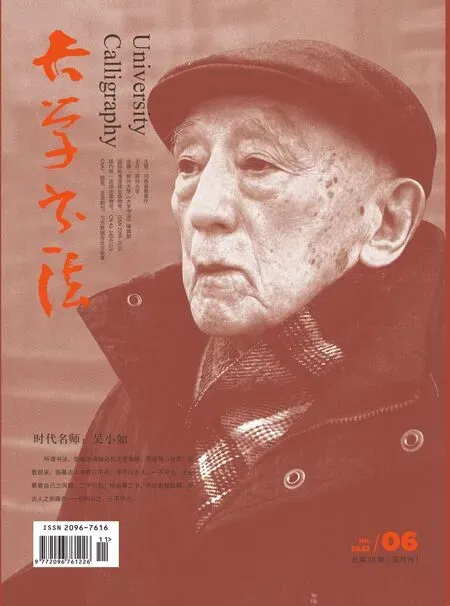現代學術語境下的書法學學科構建探索
⊙ 李穎
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關于設置“交叉學科”門類、“集成電路科學與工程”和“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的通知》(2020年12月30日),為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對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據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需要,“交叉學科”門類得以批準設立。截至2020年6月,完成交叉學科備案的160所高校中共計549個交叉學科,根據教育部發布的《學位授予單位(不含軍隊單位)自主設置二級學科和交叉學科名單》,濟南大學、西南大學等設立“書法”相關的“交叉學科”,分別涉及哲學、心理學、中國語言文學、社會學、工商管理、中國史等一級學科;中國人民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四川大學、首都師范大學等則以“國學”“中華文化國際傳播”“中國文化經典教育”等交叉學科之名,兼及了語言學、中國史、新聞傳播學等學科內涵。
2021年12月,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發布的《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專業目錄(征求意見稿)》中,“書法”之名以“美術與書法”一級學科之身份,列于“藝術學”范疇之下,至此,學界認為“書法學”一級學科在一定意義上得以初構。
可以說,相關交叉學科的設立與書法學科的名稱轉換,彰顯出新時代下我國傳承、發展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科建設需求,基于此背景的“書法學”學科發展構建路徑去向何方?此間仍存相當的探討空間。
一、多重缺失:書法學學科構建的既在困境
“書法學”一級學科構建議題一經提出便獲得學界的關注,在陳振濂先生等試圖尋找當下時代藝術之可行方案的“問題意識”[1]號召下,加之2018年由中國書協與鄭州大學主辦的“第二屆全國高等書法教育(鄭州)論壇”對書法學科建設的集中探索,一度以來,學界關于書法學學科構建的探討進行得轟轟烈烈,也形成諸多不乏價值的意見;然系統性觀之,該議題無論應有關注與相關研究仍存在不同層面的漏洞,日漸熱烈的探討背后實則暴露出書法學學科構建議題上的多重“缺失”。
這些缺失一方面表現為議題的關注度仍顯較低,另一方面則體現為有限的關注中所存在的學科建設探討共性問題與書法學科研究個性問題。以下即對此困境的“失察”“失焦”“失語”三方面進行觀察。
(一)失察:書法學科建設的整體關注度尚低
在集中討論該議題的“第二屆全國高等書法教育(鄭州)論壇”舉辦之前,以中國知網網絡數據庫搜索情況為依據,學界明確探究“書法學一級學科構建”之文僅1篇,談及“書法學科建設”的文章僅20余篇,與藝術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等一級學科建設的相關探討差以數倍甚至數10倍;在公布于2018年7月、召開于2018年11月的“第二屆全國高等書法教育(鄭州)論壇”所遴選的41篇文章中,約半數聚焦于書法學科建設話題展開針對性探究;此后,更有學者進行持續探討。
由此,盡管學界就書法一級學科建設之議已打開新的局面,也吸引到來自各類高校、研究部門乃至文博機構的有識之士,但對比于其他學科在建設階段的探討仍然不足。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反觀多個學科圍繞一級學科建設的探討,其從反思、構想、建設乃至建成的各個階段都不乏持續不斷的關注與探討,故,就該議題的所獲關注而言,在相關研討仍待展開的同時,借力討論掀起的熱潮,學科構建理應在更高的關注度中持續推進。
(二)失焦:學科建設探討的共性問題
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所制一級學科申報表為據觀察,“學科簡介與學科方向”“師資隊伍”“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培養環境與條件”是主管部門考察的五大主要板塊。
而在各個學科關于一級學科建設的已有探討中,即出現了密切關注甚至深陷學科建設申請表的板塊設置的偏向,高度聚焦于其中的“課程與教學”“招生與學位授予”“支撐學科”等細部問題以及教學團隊建設、科研項目取得等考量標準的問題——如中醫學一級學科的探討曾以“學科發展規劃”“學術梯隊建設”“科學研究”“教學與人才培養”等方面進行延展——各學科研究成果斐然,然細究則發現其已脫離學科建設議題之本身。
應當講,一級學科申報表所設置的五大板塊及其細部考察方面,從整體到局部地建立了考量一級學科建設情況的若干觀察點,對一個學科的提升之必要性與可能性提供了衡量依據;然而,問題解決所賴必要性與可能性與問題本身仍屬兩個相異的范疇,籠統視之、混為一談勢必出現研究“失焦”——而當下就學科建設所進行的研究,即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此種混淆,僅考量相關延展性問題而非學科建設的整體觀察點,使書法學科建設真正的討論焦點失于明確。
(三)失語:二級學科背景下書法學科建設探討的個性問題
書法作為藝術門類中不可忽略的一大領域,其學科定位始終模糊。從1997年至2011年,雖藝術學的所屬層級發生巨變,然書法學卻在其中憾然失語;盡管一段時間以來,其作為“特設學科”隸屬于一級學科美術學,以130405T的代碼出現,但是在整體學科架構中的地位仍不乏尷尬。反觀業界學者們基于書法學展開的探討,其所暴露的若干問題確實值得我們關注。
其一,強調重要性者多,針對學科本身展開的分析較少。
在強調書法藝術為中國傳統文化之重要部分的同時,學者們普遍看到了需將書法提至一個獨立學科的高度進行探討的重要意義(吳啟亞,1991;宋學勤,2017;黃修珠,2020),談及了書法學科升級的廣闊空間(宋廷位,2018),并站在傳統文化的視角對書法學科的特質進行了分析,強調其“顯學”之地位(呂文明,2015)。然而,對于學科本身(如書法學科的核心問題、研究方法,如何提升書法學科層級等)所展開的探討卻少之又少,僅個別幾例跳出窠臼,然應聲寥寥。
此外,學界更存在部分自視甚高抑或偏激之觀,正如學者祝帥所指:“書法領域內專業工作者對于書法的定位和位置的判斷,常常和國家的管理層、教育層,以及其他非書法專業人士的判斷之間有鮮明的落差。”[2]故業內定位極高,無論“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之斷,抑或流行一時的“符號說”“現象說”及“主體說”等,皆譽之甚隆;然在學科規范制定者眼中,多將書法學科歸于一個分支型學科,而非自成體系的獨立學科。
其二,談及具體實施策略者多,關乎頂層設計的探討較少。
通觀當前學界就“書法學”展開的相關探討,關注書法學設置后具體工作的實施者甚重,諸如畢業生去向、學科基礎理論(辛塵,1992;宋學勤,2017)、學科理論與實踐板塊設置(徐智本,2016)等問題被一一拋出。誠然,既往的艱辛探索確實為我們思考書法學學科建設問題奠定了基礎、打開了思路,但反觀上述問題的考慮層級,其偏重于“物化”性地看待書法藝術本身與書法學科,重結果、重影響式的分析與界定也確然自設障礙,將我們對書法學學科建設的思考與頂層設計層級的考量漸推漸遠。
其三,孤立視之者眾、以聯系眼光看待學科建設者少。
此外,書法學界的研究多從書法藝術本身出發進行考慮,雖時有探及學科交叉之例,然就整體而言,仍處于被動融合的狀態。但是,也正如少數學者的前瞻,“藝術與各學科之間的緊密關系決定了藝術學不能孤立存在”[3],作為要進行學科“升格”的書法學,更應摒棄以往孤立、被動式的學科發展模式,從整體出發、以聯系的眼光考量,深入掘進書法學一級學科建設的認知層次。
綜上所觀,已有的處于二級學科背景之下書法學科建設的探討暴露出研究主體針對性、頂層設計及整體構建意識等方面的欠缺,幾大問題的存在致使書法學一級學科建設探討在當前學科建設的熱潮中頻現“失語”癥狀。
二、經驗借鑒:多學科構建經驗與反思
(一)多學科建設過程經驗耙梳
除了對基于討論焦點、共性問題的關注,對學界業已形成的其他學科建設經驗與反思的耙梳,是我們進入書法學一級學科建設思考時的一把有利鑰匙。我們不妨以國內較為典型的文科領域一級學科之構建為主要參照,對書法學一級學科建設之路進行側面觀察。
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成立較早,發展至今學科范圍、內涵等皆較完備的一級學科,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以下簡稱“馬理論一級學科”)當屬典例。其由設立于1997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二級學科變化而來,于2005年根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所發布的學位〔2005〕64號通知,被增為馬理論一級學科,歸屬于法學門類,并在之后的完善中,形成目前所下設的6個二級學科。學者顧海良在該學科設立之初即以“科學理解、系統把握、整體建設”的思路對馬理論一級學科發展道路上的學科內涵、主要研究問題以及學科整體性等進行思考、提出警示。(顧海良,2006)此外,綜合對多個一級學科建設的研究案例的參考,我們發現:
首先,在對學科內涵的看待上,學者胡德坤曾以“大、特、深、廣、寬”五字在世界史已成一級學科的情況下為其建設研究方向指明道路,邢莉就藝術的文化研究進行探討,皆關注于學術研究的深度、廣度與寬度等問題(胡德坤,2011;邢莉,2012);在教育學一級學科建設的探討中,關于學科內涵的理解引發系列探討,相關學者曾就如何有效、深入地理解教育學學科內涵展開爭議(田友誼、盛茜等,2012)。應當說,一級學科建設中偏向于學術研究內涵注入的幾個考量點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在學科建設初期,內涵注入較少的問題實際上客觀地出現于多個學科。
其次,在對建設工期的觀察上,在有如中國史、旅游管理、中醫學、藝術學等一級學科的建設探討領域,相關學者也看到了學科研究務必與時俱進,“不斷推陳出新”,“在廣度與深度上也不斷拓展”[4],道出學科建設是一項長期工程。(王昊,2011;張昊旻、萬志強等,2014;劉道廣,2010)
再次,在對建設原則的認識上,學者顧海良于馬理論一級學科初建時即以警醒之態明確提出“學科建設必須遵循整體性原則”[5],其所提“科學、系統、整體”三大要點,為一級學科建設原則提出了高屋建瓴的方向指引。
總體而言,參考其他歷經多方探討且業已建成的文科領域一級學科之構建過程,內涵注入較少、建設時間較長、建設整體性不足三大問題較客觀地存在于其中;反觀同處其中、且需在理論探索階段進一步明確的書法學學科建設議題,其構成過程中的既在客觀困難是我們務必明晰之要。
(二)藝術學“升格”之經驗觀察
截至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發布《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專業目錄(征求意見稿)》之前,書法學屬于藝術學門類、美術學類一級學科下設的二級學科,既要討論“美術與書法”一級學科的“升格”問題,我們須將視角向過往回溯,觀察藝術學“升格”前后的學科建設衡量之核心要義,借此給予書法學在當前學科背景下的發展現狀及探討問題以冷靜審視。
“藝術學”獨立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美學體系,其于20世紀20年代被引入,至1990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頒布《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時,始被確立為文學學科門類下與中國語言文學等并列的一級學科;1997年學科目錄修訂時,首次在其下增設同名二級學科;后經長期論證,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于2011年3月8日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中,被正式升格為學科門類,下設藝術學理論、美術學等5個一級學科。在藝術學的“升格”前后,學界相關探討始終不絕。
第一,在其“升格”之前的探討中——學者南鴻雁、于圣維于2006年即以“藝術學的學科定位和研究方法兩個問題更有意義”[6],冷靜分析尚處學科構建初階時部分僅關注于“學科建設、基本理論和學科發展”等問題上的論斷之紕繆,明確指出“研究對象”與“研究范圍”歸為“學科定位”一環,“研究方法”與“學理基礎”則納入方法論研究。學者劉慧旻、姜麗萍于2008年就作為二級學科的藝術學之研究對象作出針對性分析,明確指出伴隨著社會的發展,事物的“內涵”與“外延”必然相應變化,以此前學科劃分只體現當時境況,而藝術學“應當根據本身的研究范圍和方向來確定研究對象,并且不斷進行調整以適應學科交叉等因素的影響”[7];同時,其亦列舉了諸如藝術原理、藝術思想、藝術分類、文獻解讀及交叉融合所產生的新分支等“研究對象”之要點,對其論點加以說明。
第二,在“升格”之后的研究中——一方面,學界對于藝術學“核心議題”的研討仍投以極大的關注:學者翁再紅、李健即直指“核心概念的有效建構”之重要意義[8];學者王謙亦在研究中表明,藝術學之“主攻方向”應在于借助該學科所能習得的實際問題及其“將會給我們什么樣的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特價值”[9]。另一方面,對其研究的深度、高度、廣度亦納入學界目光,學者曹順慶即曾以“遠沒有文學理論體系完善”之語表示,“目前藝術學學科領域最大的問題,就是藝術學理論的框架問題”[10]。
盡管探究對象隨時間變化出現了轉變,藝術學學科“升格”亦有賴于多方面力量的促成,然推動這一變化的學界探討始終保持了較為清醒而深入的認知——應當說,縱貫藝術學一級學科構建的探討中,其“核心議題”與“研究方法”始終是兩大研究重點;整體觀之,對于該一級學科的頂層設計(“框架問題”)始終占據著學科構建始末的制高點。
上述觀察之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已有少數學者敏銳地洞悉了目前書法學科升格中的關鍵問題,譬如祝帥“書法學科的文化困境就在于此:它有自己的對象和領域,卻并沒有自己的核心知識和研究方法”[11]的判斷與向凈卿“一門學科應該有特殊的研究對象、有特定的科學方法,而且這些方法是這門學科獨有的”[12]的觀點,皆指出成就一個學科之所以為“學科”,一些必須要素的具備無可爭議。然憾于呼應者寡,相關研究仍有待細部探討。
總體觀之,對比于藝術學、馬理論等學科“升格”時的研究,當下書法學界的學科升格探討,無論構想層級與實施層級均有一段路要走,尚需假以時日,在今后“美術與書法”一級學科的范疇中得以逐步提升、完善。
三、現代語境:實證主義的影響
追溯現代學術語境之肇端,我們的目光需追至20世紀之初,恰如學者白憲娟所言:“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與20世紀早期思想潮流有著密切的關系。”其于《思想潮流與現代學術的建立》一文中對影響現代學術建立的重要思潮進行了條分縷析的解讀,從進化論思潮、疑古思潮、科學民主思潮及個人主義思潮等入手,明確指出這些借助實證性研究手段、對研究問題進行逐層解構的學界思想潮流“對推翻傳統經學研究范式,確立理性、懷疑、獨立、創新的學術觀念,擴大研究范圍,突破研究禁域,養成重實證、重邏輯、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學術方法以及自由民主的學術氛圍起到重要作用”[13]。
正如學者楊晶、卓立等所看到的,“真正影響了中國實證史學的,乃是19、20世紀之交盛行于西方的‘實證史學’思想”[14],其“本質上是英美經驗主義傳統的思想,具有強烈的科學主義傾向,要求將人文研究社會科學化”[15];而恰恰由于近代中國學術研究以“科學主義思潮”為導向,推崇“客觀主義”,故對實證史學、實證主義乃至實證性研究方法的尊崇在此時推向高潮。觀察民國時期在“西學東漸”影響下的國人治學方式,即可看到這一背景的清晰烙印。
著名考古學家李濟曾于清華大學“蹭聽”心理學課程,其于1918年赴美國克拉克大學留學并“跳級”式地取得學士文憑;然正如其子李光謨先生所回憶的,他的“成績雖然不錯,但他感到這門學問所用的方法還不夠他想象的那種科學標準”[16],而李濟所看待的“科學標準”,在他后來經過對社會學的歸納與研究,并最終將個人興趣轉移到人類學中有著明顯的體現。這其中,李濟對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看待極有見地,在一篇名為《僵化》的手稿中,他對社會制度從產生到僵化的過程及背后原因進行分析,評述“許多空談改良的人只有言談而害怕乃至抵觸實踐”[17]。此外,其后工作于史語所的董作賓,其對殷商甲骨的考證手段亦吸收此間實證之法,首次以區別于既往鉆研故舊的文獻考據的“田野調查”方法,親自參與甲骨發掘,以實踐中得來的真實數據對數以萬計的骨片進行斷代研究。
可以說,民國初年,一大批懷抱“師夷長技”熱情的先進愛國人士,其所吸收西學之重要一環即在實證性研究方法,而對實證手段的興趣與學習恰恰成就了李濟、董作賓等日后的研究。
同時,中國近代美學體系及其中形形色色的概念皆屬“舶來品”,學者鄂霞即曾從“現代學術意義的視角”,將中國美學范疇體系的確立、其話語模式的轉型與學科新范式乃至美學學科的現代轉型等現象的探究追溯至近代“西學東漸”的時代大潮之下,明確指出“中國近代學者通過翻譯的途徑引進西方美學理論,從術語、范疇的譯介到學科體系的構建,逐步完善了美學學科的理論系統”[18]。
實證主義思潮興起于19世紀30年代,以法國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實證哲學教程》的出版為標志,其反對“形而上學”,看重“事實經驗”,崇尚“基于經過經驗檢驗的實證理性或科學理性”[19]。發展至20世紀,正如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及普遍性社會思潮所出現的“學術范式轉換”,盡管其于不同學科呈現出各色差異,然大體相近的“價值取向”卻為我們的觀察提供了依據,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正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占據著主體地位;盡管學界有關后現代思潮的探究將“由社會科學向人文學科轉向的趨勢”提至一定高度,在田野調查法之外加以“闡釋、內省、沉思”等文化反思,然而實證精神始終在人文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20]
學者劉道廣在看待藝術學領域的研究方法時,曾引入“現代學術研究”這一全新語境進行闡發:“‘傳統學術研究’和‘現代學術研究’的根本區別之一,就是‘現代學術研究’的基礎是實證,是在對研究對象的調查中開始的。”[21]由此反觀書法學一級學科的構建,一方面,如前所述,書法學科自設立、發展以來,始終欠缺真正獨屬本學科的核心問題與研究方法,縱然學界慣以假借“歸納法”“演繹法”“歷史文獻法”等語詞為“學術研究方法”,但或屬科學研究之共性法則,或屬借鑒相近學科之方法,獨具書法學科個性化的研究方法卻幾近于零;另一方面,進入現代學術研究的語境之中,作為基礎性方法的實證理應吸納入建成一級學科后“美術與書法”領域的關鍵話題,并隨著具體內容研究的不斷充實與提升,與時俱進地拓展獨屬于該學科的個性化面目。
四、學科建設:一個理念的“升格”
基于前述,書法學學科建設議題既是學科本身所屬層次的“升格”之探,亦是一次學界所應秉持理念的“升格”之觀。
首先,從學界探討所存問題出發觀之:一方面,各個學科在學科建設探討進程中的共性問題(即因過度關注一級學科申報表之框架,反將真正的討論焦點與必要性、可能性等衡量因素混為一談,使相關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學科建設議題本身)亦出現在書法學科建設研究之中;另一面,基于書法學自身的諸多認知,在學科建設這一話題上主要呈現于對其意義的強調、對具體實施策略的探討與對學科認知的相對孤立性。應當講,無論學科建設探討中的共有問題,還是書法學探討的個性化問題,在建設一級學科的征程上,均應伴隨著與日俱增的關注得以重視和解決。
其次,正如法國史學家兼文學評論家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所力倡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質面貌都取決于種族、環境、時代因素”,故研究自然界氣候之外,同樣“應該研究精神上的氣候,以便了解某種藝術的出現”[22];而在其所處各自環境的作用下,精神文明的產物呈現出迥然相異的特征。
進入現代學術語境,包括了對學術本身的認知與解讀、研究形式、研究方法等學術話題均產生了變化;相應地,我們在現代學術語境之下對一級學科建設的審視理應尊重學術環境施加于之的作用。與此同時,區別于傳統學術研究,現代學術研究的最根本特征正在于其實證基礎,反觀書法學科,獨屬于本學科的研究方法乃至核心議題卻始終缺位;而伴隨著現代學術語境的日漸深化,作為學術基礎的實證方法理應吸納入當下“美術與書法”一級學科建設的話題,并隨具體研究的不斷充實與提升進行與時俱進的拓展。
故而,學術研究大環境的變化促使學科建設理念發生轉變,我們的觀察與研究既應從認知層級不斷修正以往出現偏差的認知,亦應緊跟時代步伐,全面考慮現代學術研究環境的作用力,在具體方法論層面深入掘進。
再次,“學科建設”之“升格”從何著手?我們認為,摒棄“不問前路”式的“悶頭大干”,轉而關注具備針對性的書法一級學科建設探索應是重中之重。從前述問題分析、經驗借鑒及語境變化三個板塊來看,“美術與書法”一級學科建設這一議題應關注兩個層級的內涵——構想層級與實施層級。
就構想層級而言:參考馬理論、藝術學等一級學科的構建過程,其對于學科構建的整體性與系統性的建設與認知令人深省,而整體意識淡薄、頂層設計欠缺在一級學科建設的探討中確然成為造成學科“失語”現象的最大要因,故高瞻遠矚、高屋建瓴地為書法學科構建整體發展設計應是此層級下不可忽視的任務。
就實施層級而言:第一,就綜合學科建設討論點“失焦”的已存問題與藝術學一級學科建設的指導性經驗來看,學科建設話題下兩大研究重點應在于一個學科所具獨立、獨有的核心議題與研究方法,非此不能言書法學科的真正“個性化”;第二,當學術研究走入現代學術語境,其傳承自20世紀初期的研究范式、特征仍占據學界相當的地位,并隨著時間推移呈現出的新的樣貌,這一大環境的影響對書法學科獨有研究方法的找尋、探討及界定十分清晰,遵循其發展變遷規律是當下書法一級學科建設中的重要一環;第三,學界前人的經驗亦提醒我們,學科建設必然是一項長期性工程,其從構想到實施的過程需要長期培育并在建設廣度、深度上不斷拓展,不可一蹴而就。
綜上,當前對書法學科建設的探討,不應僅僅停留在“提升一級,皆大歡喜”,而應伴隨學科“升格”的恒久努力,逐漸探究出書法學科的核心議題與研究方法,使整體學界研究達到認知層次的“升格”。如此,我們今天的努力方不致錯付!
注釋:
[1]陳振濂.書法藝術及其學科建設[N].人民日報,2018—9—23.
[2][11]祝帥.書法遺跡與當代文化生態[J].美術觀察,2012(6):30.
[3][7]劉慧旻,姜麗萍.從學科角度看二級學科藝術學[J].藝術百家,2008(7):44.
[4]劉道廣.關于當前藝術學學科設置的三個思考[J].藝術百家,2010(3):61.
[5]顧海良.科學理解 系統把握 整體建設——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建設的思考[J].思想理論教育,2006(6):4.
[6]南鴻雁,于圣維.藝術學的學科定位及研究方法[J].杭州師范學院學報:醫學版,2006(6):386.
[8]翁再紅,李健.論建構藝術學理論核心概念的影響因素[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129.
[9]王謙.藝術學理論一級學科的主攻方向——以藝術學理論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兩個問題為切入點[J].巢湖學院學報,2012(5):137.
[10]曹順慶.藝術學學科理論建構與藝術本質新論[J].貴州社會科學,2014(7):33.
[12]向凈卿.結合“國學”的書學學科的“新展開”:從文字書寫、文本文獻到美學思想[G]//中國書法家協會.全國第二屆高等書法教育論壇論文集.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18:155.
[13]白憲娟.思想潮流與現代學術的建立[J].哈爾濱學院學報,2015(3):27.
[14][15]楊晶,卓立.近代西方史學三種客觀主義觀念辨異[J].歷史教學問題,2018(6):87,89.
[16][17]李光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25,27.
[18]鄂霞.中國近代美學范疇體系的生成與現代學術精神的確立[J].文藝爭鳴,2018(4):107.
[19][20]何明.學術范式的轉換與藝術人類學的學科建構[J].學術月刊,2006(12):21,23.
[21]劉道廣.藝術學:莫后退——論藝術學研究的學科構架[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1):74.
[22]丹納.傅雷,譯.藝術哲學(上)[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