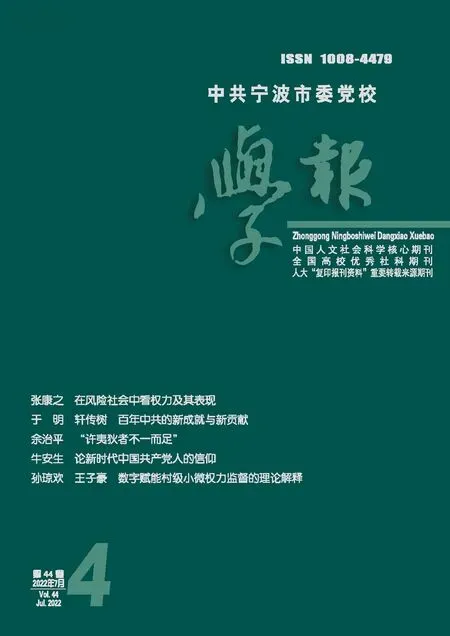“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春秋》“夷夏之變”中“進夷狄”的限度
2023-01-08 03:07:16余治平
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
2022年4期
關鍵詞:文明
余治平
“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春秋》“夷夏之變”中“進夷狄”的限度
余治平
(上海交通大學 哲學系,上海 200240)
公羊家的“夷夏之辨”并不以地緣和人種差異為標準,而以文明教化為本位。《春秋》“進夷狄”,稱呼夷狄有州、國、氏、人、名、字、子七等。夷狄能行中國之禮,可朝聘、稱王、設大夫、紀元、遣使,但還只是起步。夷狄之君楚穆王即便再賢,最高也只能稱子。夷狄雖有屈完、子玉得臣之類賢大夫,《春秋》卻不稱氏。對夷狄賢臣季札,稱名而貶。中國夷狄化沒有底線,當貶則貶,當絕則絕。夷狄中國化則有限度,夷狄之進步雖可滿足禮樂文明的一個條件但并不等于滿足所有條件,這并非出于地域、種族的歧視,也非夷夏之人先天稟賦就存在差異性,而是強調夷狄慕王向化需要一個歷史過程,必須有所積淀。“進夷狄”的限度恰恰是“熔鑄各種族為一體的一股精神力量”,它對齊桓、晉文聯合諸夏中國抗擊外侮,對武帝北攘匈奴、南征南越、建構中華身份認同都產生了影響。
春秋公羊學;夷夏之辨;進夷狄;不一而足
《春秋》強調“夷夏之辨”,設“夷夏大防”,而不容混淆邊際。歷史上的春秋公羊家實際上并不狹隘和孤陋,其所伸張的夷夏之辨始終不以地理疆域、人種膚色的差異為標準,而是以文明教化為本位。地不分東西,人不分南北,有沒有禮樂,行不行王道,存不存仁義,才是公羊家夷夏之辨問題的要害,也是糾正長期以來人們對夷夏之辨多有誤解和曲解的核心。董仲舒曰:“《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品牌研究(2022年32期)2022-11-16 01:57:18
品牌研究(2022年31期)2022-11-08 07:22:42
品牌研究(2022年26期)2022-09-19 05:54:44
小學生學習指導(低年級)(2021年11期)2021-11-30 05:49:36
銀潮(2021年8期)2021-09-10 09:05:58
金橋(2020年11期)2020-12-14 07:52:40
人大建設(2020年5期)2020-09-25 08:56:12
青年歌聲(2020年7期)2020-07-29 07:44:08
農村百事通(2020年11期)2020-06-27 14:05:13
小學生作文(低年級適用)(2019年3期)2019-11-27 20:0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