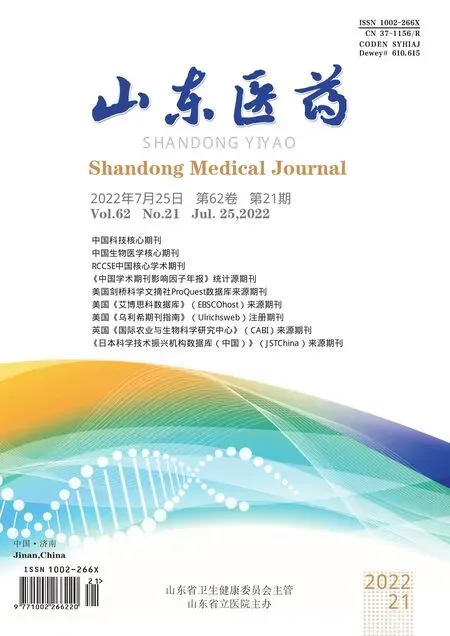膿毒癥的免疫病理機制及診斷和預后預測生物標志物研究進展
翟昭,王楠,張宇晨,鐘佳寧,劉先發,易會興
1 贛南醫學院第一臨床醫學院,江西贛州 341000;2 贛南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3 保定市人民醫院
膿毒癥被定義為由宿主對感染的反應失調而引起的潛在致命有機功能障礙,機體感染后可表現為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并迅速發展到多器官功能障礙和膿毒癥性休克,危及生命,是重癥監護病房常見死因,也是世界范圍內尚未得到充分認識的重大衛生保健問題。膿毒癥是嚴重創傷、感染、燒傷或大型手術后的常見并發癥,病情進展迅速,病死率高,據國外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每年約有超1 900萬人患膿毒癥,而只有1 400 萬人可存活出院,存活的膿毒癥患者中僅半數能康復,六分之一的人伴有持續性機體損傷,三分之一的人在出院后第二年死亡[1]。膿毒癥發病涉及組織損傷、全身炎癥網絡、免疫功能障礙、凝血功能異常、基因多態性等多方面,最初作為機體對內毒素的免疫反應而被發現。當病原體侵入機體時,宿主先天免疫系統發現并清除病原體,而當病原體作用強于免疫反應時,機體內炎癥反應與免疫反應發生失衡,表現為細胞因子風暴和免疫抑制。目前,判斷病情進展并給予相應治療是臨床膿毒癥診療面臨的一大困難,而生物標志物的應用大大提高了膿毒癥的診斷及預測準確性,為膿毒癥研究提供了新方向。現在將膿毒癥的免疫病理機制及其診斷和預后預測生物標志物研究進展綜述如下。
1 膿毒癥的免疫病理機制
膿毒癥發病機制與免疫反應關系密切。膿毒癥會導致先天性免疫及獲得性免疫反應的改變,前者表現為腫瘤壞死因子(TNF-α)、白介素-1β(IL-1β)、IL-6、IL-8 和干擾素-γ(IFN-γ)等參與的細胞因子反應,后者表現為免疫細胞如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s,DCs)、淋巴細胞、自然殺傷細胞、中性粒細胞以及抗原提呈細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APC)等的凋亡。細胞因子風暴和免疫抑制是膿毒癥中兩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兩者雖為不同階段,但在發展上并無嚴格轉變,機體內促炎與抗炎的平衡關系決定兩階段的發展。
1.1 細胞因子風暴 疾病早期,淋巴細胞等免疫細胞通過模式識別受體(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PRRs)識別病原體相關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s)或損傷相關分子 模 式(Damage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激活細胞內信號傳導和基因表達程序,導致一系列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等介質產生,引發機體炎癥反應[2]。細胞因子激活免疫細胞,被激活的免疫細胞進一步產生細胞因子,形成一個正反饋調節,即細胞因子風暴[3]。膿毒癥高炎反應還可導致補體系統及凝血系統激活,前者促進補體C3a、C5a等小激活片段釋放而發揮強大的促炎作用和促血栓活性[4],后者加重膿毒癥患者微血栓形成概率[5]。同時,高炎反應刺激抗炎因子IL-4、IL-10 等大量分泌,但其急劇分泌增加會使機體抗炎功能因反應過度而代償性下調,以致出現代償性抗炎反應綜合征(Compensatory Anti-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CARS)[6],內源性抗炎介質失控性釋放是機體免疫功能抑制的主要原因。
1.2 免疫抑制 免疫抑制被認為在膿毒癥后期占主導地位。免疫細胞凋亡是膿毒癥免疫抑制的主要發展因素,可發生于多種病原體感染、多個年齡段患者及多部位免疫組織中,主要特征在于淋巴細胞耗竭及APC 的重新編程。淋巴細胞耗竭主要與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1)及程序性死亡配體(Programmed Death Ligand,PDL)的相互作用有關。T 細胞表面PD1 表達增加,巨噬細胞上PDL 表達增加,導致耗竭的T 細胞失去其效應功能,而干擾PD1/PDL 通路后T 細胞活性可恢復[7],研究也證實抑制PD1/PDL 相互作用后膿毒癥誘導的小鼠存活率有所提高[8]。淋巴細胞耗竭的另一原因與調節性T 細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比例增加有關,效應T 細胞喪失致Tregs 百分比增加,Tregs 抑制效應T 細胞功能、延長T 細胞恢復時間并促進其凋亡以維持自身耐受性,誘導DCs 表面共刺激分子表達下調,加劇了膿毒癥免疫抑制,所以降低Tregs 表達對膿毒癥具有保護作用[9]。
APC的重新編程表現為單核細胞表面人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Ⅱ類分子(Human Leukocyte Antigen DR,HLA-DR)表達減少,引起抗原提呈能力下降,單核細胞和巨噬細胞釋放促炎細胞因子減少,IL-10 等免疫抑制因子增加,加重機體免疫抑制[10]。這與基因的表觀遺傳調控有關,我們已經了解基因啟動子和增強子的高甲基化通常與基因抑制有關,低甲基化與基因激活有關,目前臨床研究[11]表明,膿毒癥患者IL-10 表達與啟動子中甲基化水平呈負相關,這與免疫抑制病理生理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表觀遺傳修飾可在膿毒癥消退后持續存在,其可能與膿毒癥后持續免疫抑制導致多器官衰竭有關[12],且這種修飾可編寫入正常細胞內并遺傳,對機體免疫應答產生長久的不利影響[13],感染性疾病發生的遺傳關聯的存在表明膿毒癥患者存在基因組異質性,這也提示我們表觀遺傳在膿毒癥機制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大量免疫細胞凋亡也會導致尚存活的免疫細胞功能紊亂。吞噬細胞吞噬清除凋亡的免疫細胞而減少了對病原體的吞噬,表現為機體免疫系統被抑制,導致膿毒癥耐受。中性粒細胞數量增加但功能受損,膿毒癥期間可分化出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亞群,該亞群可分泌大量IL-10 從而干擾機體正常免疫功能。膿毒癥患者即使度過嚴重期存活下來,也會表現為長期慢性免疫抑制,稱為持續性炎癥-免疫抑制-分解代謝綜合征(Persistent Inflammation- Immunosuppression Catabolism Syndrome,PICS)[14]。
2 膿毒癥診斷和預后預測的生物標志物
臨床中對于膿毒癥進程的判斷會依靠不同生物標志物的短期或長期監控來實現,如何準確把控各種生物標志物對膿毒癥診斷或預后的預判作用是我們研究的重點。
2.1 促炎細胞因子 促炎細胞因子是目前膿毒癥中研究的較為透徹的一類生物標志物,即便如此,能運用到臨床中的少之又少。IL-6、IL-8、IL-18 和TNF-α 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預測膿毒癥嚴重程度及死亡率,但同時,促炎細胞因子的初始量產是導致膿毒癥高炎癥的原因之一,所以其變化程度在臨床中不易掌控。研究[15]表明,膿毒癥組患者IL-6水平顯著高于非膿毒癥和正常組,且在病后28 d左右明顯升高,這表明IL-6 高敏感性的特點可以有效預測膿毒癥患者預后情況,有可能確定膿毒癥患者發展為重癥膿毒癥的風險大小,因此可作為理想標志物之一,其他促炎因子效果則不甚理想。
2.2 抗炎細胞因子 IL-10是膿毒癥中具有高特異性的初始標志物,其可增加T 細胞IFN-γ 產生,減少TNF-α和HLA-DR表達,其中對適應性IFN-γ的產生增加僅見于膿毒癥患者,對先天性及獲得性免疫發揮負性作用。研究[16]表明,抑制小鼠IL-10水平可改善膿毒癥免疫反應及預后。臨床數據[17]顯示,與存活的膿毒癥患者相比,IL-10水平在膿毒癥危重病死者中更高,表明IL-10 升高與疾病進展存在相關性。也有與之相反的結果,早期動物實驗中,使用IL-10治療的小鼠存活率更高,阻斷IL-10 則會增加膿毒癥模型小鼠的死亡,提示高水平IL-10 與膿毒癥危重患者的預后和死亡相關[18]。這種看似矛盾的結果或許可以解釋為IL-10 變體對不同免疫細胞進行作用而導致的不同免疫效應,不同動物的耐受力及膿毒癥模型使用的病原體不同,從而表現出抗炎和促炎效果[19]。
2.3 HLA-DR 正常生理情況下,HLA-DR 被T 細胞表面受體(T Cell Receptor,TCR)識別提供第一信號,表達于T 細胞表面的CD28 與表達于APC 表面的CD80、CD86 相互作用提供共刺激信號,T 細胞被激活,參與免疫應答。而在膿毒癥病理生理中,代償性抗炎反應致使機體免疫反應減弱,表現為巨噬細胞、單核細胞等表面HLA-DR 表達減少,T 細胞激活必需的第一信號無法提供。另外,T 細胞調節陰 性 共 刺 激 分 子CD152 表 達 增 加[20],CD28 與CD152 的作用并非提供T 細胞激活所需的共同刺激,而是導致T 細胞無反應,免疫應答無法完成。研究[21]證實,膿毒癥患者體內淋巴細胞衰竭,HLADR 被顯著抑制,而存活患者體內10 d 左右會恢復,我們可以認為淋巴細胞絕對計數和單核細胞HLADR 表達減少是膿毒癥免疫抑制的生物標志物,住院一周的恢復水平可對膿毒癥預后進行一定程度的判斷。
2.4 血乳酸 目前臨床上最廣泛使用的器官功能障礙生物標志物是血乳酸濃度。膿毒癥期機體代謝功能障礙,乳酸水平變化緩慢,不能用于急性期的指導治療,但連續測定可明確患者變化,評估整體病情。臨床研究表明,應每隔1~2 h 測量血乳酸水平以進行病情評估,若在膿毒癥性休克復蘇的前6~8 h降低乳酸水平,可能改善患者預后[22]。臨床中主要偏向認為血乳酸水平升高是氧輸送不足,膿毒癥期間缺氧器官進行無氧糖酵解,丙酮酸生成乳酸[23]。但這種解釋沒有考慮到即使組織灌注沒有受到影響,其他因素也會導致乳酸堆積,高乳酸血癥除組織缺氧型外還有無組織缺氧型,后者與先天性代謝障礙、基礎疾病、藥物或毒素等相關,另外乳酸清除率降低也是原因之一,多出現在膿毒癥致肝功能損傷患者體內,回歸分析結果表明24 h 內血乳酸清除率延遲與膿毒癥肝功能障礙患者的醫院死亡率有獨立關系[24],因此血乳酸清除率可作為膿毒癥伴肝功能障礙或膿毒癥性休克初始復蘇期間患者死亡率的潛在預后標志。
2.5 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和C 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PCT 和CRP 都是機體應對感染和損傷時產生的蛋白質。PCT正常生理情況下由甲狀腺C 細胞合成,而在膿毒癥中由甲狀腺外組織負責合成,機體內輕微或局部感染、慢性膿毒癥等不會引起PCT 水平的升高,急重癥膿毒癥導致PCT水平大幅升高,可反映炎癥的嚴重及緩急程度。另外,細菌感染引起PCT 水平升高,病毒感染、過敏則不會。有研究[25]表明,PCT 可準確區分膿毒癥和非感染性SIRS,所以其又可作為鑒別細菌性與非細菌性感染的有效標志,但對膿毒癥患者28 d 死亡率沒有明顯指導作用[26]。
炎癥期間CRP 在機體內具體的作用機制尚不清楚,目前已知其在肝臟中受IL-6 刺激而合成上調,可以與微生物的磷脂成分或損傷細胞結合,利于巨噬細胞清除,是公認的感染與炎癥期生物標志物。CRP 具有高敏感性,對感染及炎癥刺激快速反應,通常用于膿毒癥早發檢查,也可預測膿毒癥患者28 d 死亡率[27],但具有低特異性。急性炎癥、嚴重感染性疾病、動脈粥樣硬化等心血管疾病中CRP水平均可升高,所以近年來其他高特異性標志物的發現降低了CRP 單獨作為膿毒癥生物標志物的重要性。
CRP與PCT單獨應用對診斷膿毒癥是否更具優勢仍存在爭議。早期UZZAN 等[28]發表了一項比較CRP 和PCT 診斷膿毒癥的Meta 分析,OR 值與集成ROC(SROC)曲線結果表明,在危重膿毒癥患者中,PCT 變化程度始終高于CRP,這表明PCT 比CRP 有更優的準確性,可以作為一種成人膿毒癥的早期快速診斷或篩查實驗;此外,研究還認為,PCT 水平升高不能確診機體感染,但可以起到很好的輔助效果,因此可以在診斷危重膿毒癥患者時發揮一定作用。
2.6 表觀遺傳修飾相關生物標志物 表觀遺傳修飾是指控制基因表達但與DNA 序列變化無關的調控機制,其建立在內毒素耐受上,主要包括DNA 甲基化、組蛋白修飾和非編碼RNA(non-coding RNAs,ncRNAs)作用,在膿毒癥代謝相關病理生理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
目前,DNA 甲基化是表觀遺傳修飾中研究最為廣泛的一類,屬于胞嘧啶殘基的修飾,主要在胞嘧啶-鳥嘌呤(CpG)基序的背景下進行[29]。DNA 上甲基的添加或去除可改變局部染色質結構,導致蛋白質結合改變,基因表達隨之改變。功能研究[30]表明,DNA 甲基化相關位點在感染性和非感染性炎癥之間存在可測量的表觀遺傳學差異,對診斷及預后有所助益。差異甲基化區域(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Region,DMR)指同一基因位點不同程度的甲基化區域,可控制基因表達。膿毒癥與非膿毒癥危重患者體內均存在DMR,膿毒癥中發揮作用的DMR 相關基因,如C3、MPO、ANGPT2 等,與涉及抗原提呈和組蛋白甲基轉移酶基因重疊[31],說明膿毒癥與非膿毒癥患者先天免疫反應和獲得性免疫系統的表觀遺傳調節存在根本差異。但目前DNA 甲基化作為臨床生物標志物仍不現實,相對于臨床中疾病的快速變化而言,基因位點檢測不夠簡單快速,不能夠作為首選。
組蛋白修飾可以直接參與基因轉錄和染色質調節,在機體正常生理和疾病病理生理中均能發揮作用。組蛋白由H2A、H2B、H3、H4 構成核小體,再由DNA 雙螺旋纏繞在周圍組成。由于受共價修飾的影響,核小體內彼此間的作用及與DNA 的關系發生改變,進而與DNA 甲基化發生互補,共同決定局部基因的表達模式。膿毒癥涉及的組蛋白修飾主要表現為H2A、H2B、H4 的高度乙酰化及H3 中的特定甲基化,在多種免疫細胞中均起作用。研究發現,機體遭受內毒素攻擊后,巨噬細胞和單核細胞的促炎細胞因子啟動子區域H3賴氨酸9二甲基化(H3K9me2)和DNA 甲基化水平增加,釋放炎性因子能力降低而產生抗炎因子能力增加,導致免疫耐受發生[32]。淋巴細胞的發育與調節過程中,組蛋白修飾通過使B細胞基因組發生低甲基化和高乙酰化,T 細胞中H3K27me3 水平升高等變化,淋巴細胞表現為不活躍,甚至基因沉默的表觀遺傳狀態[33]。目前關于膿毒癥中組蛋白修飾的研究已經非常廣泛,但其在患者體內的作用仍未清晰,距離應用于臨床還有很長的距離。
ncRNAs 中研究最廣泛的是microRNAs(miRNAs),這是一類內生的、長度約20~24個核苷酸的小RNA,在重癥膿毒癥患者血漿、尿液中均可檢測到,雖然這類小分子的來源尚不清楚,但在膿毒癥病理生理過程中,其作用網絡的動態變化可參與促炎或抗炎過程,控制機體免疫系統表達,調控內毒素耐受轉入免疫抑制。目前miRNAs 已被認為是膿毒癥的生物標志物,如miR-150與miR-155表達與膿毒癥病理程度呈負相關,miR-146a、miR-223 聯合使用的診斷效果優于PCT、CRP 等常規標志物,miR-13a 水平可反應疾病嚴重程度及患者長期死亡率,miR-15a、miR143 可以較好的區分膿毒癥和SIRS[34]。雖然這些研究已經得出針對膿毒癥的有效結果,但在臨床操作中如何應用尚存在爭議,盡管如此,該領域仍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
綜上,膿毒癥病理生理過程主要反應為免疫機制的變化,細胞因子風暴和免疫抑制的強弱關系影響膿毒癥疾病進程及嚴重程度,控制促炎反應與抗炎反應平衡是維持內環境穩定的關鍵。膿毒癥是一種高異質性疾病,不同的病原體、感染方式、個體差異等因素導致疾病效應千差萬別,以至膿毒癥治療一直不甚理想。近年來,關于膿毒癥生物標志物的研究數量穩步增加,除了對膿毒癥整體診斷及預后進行預測外,各系統損傷預測的標志物也有所發現,如Syndecan-1、血小板預測膿毒癥患者彌散性血管內凝血及死亡率[35]。目前膿毒癥的診斷主要依據器官功能衰竭評分,但反應膿毒癥患者狀態變化的生化指標仍存在不及時的問題。多標志物聯合的預測手段已經進入人們的視野,最終治療效果仍取決于患者的個體化狀態。這里所討論的是目前研究較廣泛,能夠在病床前獲得的標志物,關于其他方面如腸道微生物、補體系統等領域以及針對各器官系統的標志物仍有較大研究空間。對于膿毒癥這種進展迅速、致命性強的特點,或許高靈敏性標志物比高特異性標志物來的更實際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