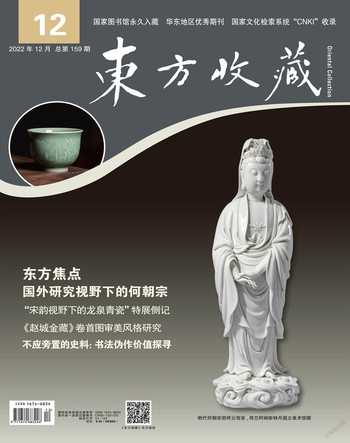從齊文化博物院文物看齊國的對外交流



摘要:齊國故城臨淄地處我國東部,姜太公封齊建國。當時列國紛爭不斷,文化通過戰爭、貿易、婚嫁等方式在各諸侯國之間進行著交流。
關鍵詞:齊文化博物院;齊國文物;文化交流;
自姜太公封齊建國到秦統一六國,臨淄作為齊國故都長達800余年。作為東夷之地,臨淄歷來憑借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物產豐饒,靠著經貿與外地取得聯系。到戰國時期,臨淄更是宇內少有的富庶之處,《史記·蘇秦列傳》中記載的“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描繪的便是當時的盛景。悠久的歷史為后人留下了眾多的文化遺存,在這些遺存中,不乏明顯不具有齊國特色的文物,由此可窺見齊國的對外交流情況。
戰國銘文雁足燈(圖1),高36、燈盤徑24、底座長16、寬11—13.7厘米。此燈于1992年出土于商王墓地M1,從墓葬形制、隨葬器物等方面分析,該墓為戰國晚期墓葬。
該雁足燈由燈盤、燈柄和燈座構成。燈盤為圓形,設計成凹槽,即橫切面為“U”形,內圈中空,直口,淺槽,平底,凹槽內有等距分布的三個錐形柱,燈盤外側三分之一處有一圈弦紋。燈柄為一粗壯的雁足,與燈盤一側相連接。雁足三趾向前,一趾在后,立于等腰梯形底座之上,三趾間有兩蹼,后一趾彎曲與燈座相接構成環形。三前趾骨節分明,趾及趾甲較為粗壯,趾間陰刻“陵夫人”四字銘文。底座的底部中央有一圓孔。圓形燈盤、雁腿形燈柱和雁足形燈座構成類似“[”形,穩定而優雅。此雁足燈整體造型優美,雁腿上部粗壯,膝蓋及足部骨節突出,造型逼真,體現了較高的鑄造水平和審美意趣。
圓形燈盤的凹槽用來盛放燃料,三個錐形柱體可同時點燃,增加照明亮度。凹槽設計也是為了把燃料集中起來,避免浪費。此燈集設計、藝術、工藝和實用于一身,在滿足生活需要的同時,也體現出當時燈具設計的科學性和美觀性。
1999年,戰國鑄銅工匠墓的發掘,使得雁足燈座模現世。根據墓葬形式、隨葬物品判斷,此墓主人為戰國晚期秦國人,且是“具有一定身份的鑄銅工匠”。秦國因地理位置便利,“與北部和西部的邊疆民族通過貿易和戰爭保持著密切聯系”,因此能將地中海藝術中比較流行的“模仿動物身體某一部分的造型設計理念”和裝飾風格引入中國,并通過饋贈、貿易等方式傳至齊國,使戰國時期東西兩端最強盛的國家有了文化上的交流。
漢代蒜頭壺(圖2),出土于臨淄區窩托村漢齊王劉襄墓陪葬坑。通高42、口徑4.1、最大腹徑21.8、足徑13.3、蓋徑4.8厘米。
該蒜頭壺為直口、方唇、細長頸、溜肩、球形腹、平底、圈足,最大徑在腹中部。蓋為母口,弧面,上飾凹弦紋,中央有一環鈕。口沿下部凸起呈蒜頭形,蒜頭形紋飾上下穿插,共計18枚分瓣蒜頭。頸部上、下各飾一周凸弦紋,肩部飾一對鋪首銜環,腹中部飾一周凸弦紋,在外底部中央有一個半環形鈕。
蒜頭壺因壺口處一周似蒜瓣的紋飾而得名,其起源于戰國時期的秦地,為典型的秦國器物,流行于秦漢時期。考古研究表明,這種分瓣的大蒜原產地是中亞,后分別傳入西方和東方。在東方國家中,印度最先引進大蒜,后又傳入東南亞,但進入我國中原地區是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后,《博物志》載:“張騫使西域,得大蒜、胡荽。”
小口細長頸壺的造型也“不是中國傳統的酒器樣式”,反而遠在地中海沿岸的塞浦路斯流行這樣的器型。蒜瓣形紋飾也不是中原地區傳統的器物紋飾,被稱為“裂瓣紋”“凸瓣紋”,不論名稱如何,都公認為“西方藝術的典型紋飾”。秦國雖地處中國西部邊陲,卻與歐亞大陸有貿易往來,將異域風情引入中國,通過與各國貿易、婚嫁、戰爭等方式傳入全國各地,聰慧的中國人民又根據市場需求和特定審美,使之與本土文化融合為獨具特色的文化產品。
該蒜頭壺造型優美,紋飾簡單獨特,不論是器物造型還是主要紋飾都不具有中國本土特色,但是環形鈕和鋪首銜環卻符合中國器物的審美觀,因此這件蒜頭壺不僅是中國東西部之間文化交流的產物,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見證。
漢代裂瓣紋銀豆(圖3),高10.9、口徑11.3厘米。出土于臨淄區窩托村漢齊王(劉襄)墓陪葬坑。
蓋呈弧形,頂置三個銅獸形鈕,淺腹,平底下接銅制圈足。銀銅合制,器身主體為銀質,蓋上三獸及圈足為銅質。蓋頂三獸臥姿等距鉚接在蓋頂上,三獸頭部皆轉向身體右側微上揚,耳朵呈圓形,眉骨較高,眼球外鼓,鼻梁較高,鼻翼較厚,鼻孔略小,口部緊閉,細長的尾巴自尾部穿過兩后肢中間貼伏于后背近尾處,一副舒適閑逸的神情和姿態;三獸四肢粗壯,后肢壯于前肢,每足三趾,皆粗壯有力;蓋內壁從右往左陰刻“木南”二字銘文。器身及蓋各錘揲兩周水滴形裂瓣紋(也稱凸瓣紋)凸泡,尖端相對交錯排列,蓋上兩周各有17枚裂瓣紋凸泡,上層一周較小,下層一周較大;器身兩周各有20枚,凸泡大小與蓋相反。每周的凸泡看似大小一致,細看卻是各個不一。銅質圈足較矮,鉚接于器身底部。銀豆整體造型優美,既有豆形器的優美,又有盒形器的實用,是一件集美觀與實用于一身的藝術珍品。
這件器物表面的裂瓣紋裝飾極富特色,它是用錘揲法制作而成的。一般認為金銀器錘揲工藝源于古代波斯地區,“通過戰爭、貿易等形式進行的文化交流,傳播至希臘、埃及、中亞等舊大陸的廣大地區”,其花瓣紋飾很可能也源于西亞的波斯等地。
它是如何傳入中國的呢?與銀豆一起出土的器物中有一件銀盤,上有銘文“三十三年”,據考證應為“秦始皇三十三年”。有人推斷,銀豆出自秦地,甚至是秦宮室,也就是說銀豆雖然出自漢墓中,但是鑄造年代可能“早至秦代或戰國”,因此有人認為銀豆或是因為戰爭,或是作為國禮,傳至齊國。因為臨淄靠近大海,齊國向來重視海上貿易,加之同樣近海的廣州也出土有類似的器物,因此也有人認為銀豆是從海上絲綢之路歷盡艱險遠洋航行而來。
無論是從陸路傳播而來,還是漂洋過海而來,銀豆本身都能體現出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和齊國的對外文化交流。
戰國郾王劍(圖4),出土于齊國故城,由當地村民在淄河灘涂之地挖沙時所得。劍長約59、寬約4.7、莖長9.5厘米,重800多克。
劍身修長呈柳葉形,兩從較寬,中脊呈直線狀微隆,內凹,下端平。脊延長為莖,莖為扁圓形,莖兩側各有一凸起的棱伸入劍身,劍刃有砍砸的缺口,無格無首。在近莖處的劍脊上有八字銘文“郾王職作武蹕旅劍”。
銘文中的“郾”是通假字,通“燕”字。燕王職(名姬職,或名平,字職)即燕噲王之子——燕昭王,是歷史上一位頗有作為的君主,在位33年(前311至前279)。“作武”是指進行軍事行動,“蹕旅”指規模不大的衛隊,銘文大意為燕昭王麾下警衛部隊的作戰用劍。這把劍為什么會出現在齊國呢?據史料記載,燕齊兩國關系比較密切,燕國地處東北邊陲,與中原各國軍事交流較少,但是與齊國地理位置較近,曾經互相攻伐,也為了共同利益聯合作戰。燕國的國力相對于齊國來說,總體較弱,矛盾爆發于燕噲王時期。燕噲王預行禪讓,燕國發生內亂,齊國趁機參與其中,借支持當時的燕太子上位之機,占領燕國都城,并在燕國境內燒殺擄掠,激起了燕國民眾對齊國的巨大仇恨。燕國國君在臣子的輔佐下,從政治到經濟,從內政到外交,從軍事到人才,準備了整整27年。在燕昭王二十八年(前284),趁齊國外交政策失利、眾叛親離之際,燕、秦、趙、魏、韓五國聯合進攻齊國,燕昭王派樂毅為將,統帥五國聯軍向齊國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齊將觸子率軍與五國聯軍對峙于濟水之西。
而郾王劍在淄水河畔出土,結合銘文內容進一步佐證了燕齊之戰的發生。通過戰爭使得文化融合,也是千百年來各地文化交流的一種常見方式。
戰國鳥篆文劍(圖5),出土于臨淄區金鼎綠城三期工地,長56.2、寬4.6厘米,重820克。
劍體狹長,線條規整。劍為單脊,劍身橫截面作菱形。圓管狀莖部上細下粗,中空透底,劍格為菱形較薄,圓首。劍格的一面兩側各有兩個錯金重字,字跡清晰。劍首環列12字,皆為錯金鳥蟲書銘文,個別字被銅銹覆蓋或是鎏金脫落,無法確認內容。中空圓管狀劍莖內有裝飾物,表面呈圓形,且有六枚圓形凸泡狀飾物,一枚位居中央,另外五枚環列四周。
此劍銘文較特別,為典型的鳥蟲書文字。從劍的形制看,此劍與《鳥蟲書通考》中著錄的“越王嗣旨不光劍”一至五、“越王旨翳劍二”“越王者旨不光劍”以及十六把“越王不光劍”都基本相同。銘文形態與“越王不光劍十一”尤為相似。
上述劍皆為越國第九任國君越王翳的佩劍。越王翳又稱越王不光、越王授,是勾踐的玄孫,在位36年,是越國在位時間最長的君王,見證了越國的興衰轉折。他繼承國君之位時越國國力強盛,其曾趁齊國執政者田和地位尚不穩固之際,興兵伐齊,也曾因繒國倚仗齊國勢力輕視越國而發動滅繒之戰,在軍事上與中原強國抗衡。在他的晚年,面臨內外交困的局面:內部,其弟豫為了繼承王位,先后謀害三位皇子;外部,吳國貴族虎視眈眈圖謀復仇,臨近的諸侯齊國和楚國日益強盛。此外,國都瑯琊遠離江南導致軍隊和物資運輸困難。為此,越王不光將國都從瑯琊回遷至吳地(今江蘇蘇州)。后在宮廷內亂中,越王不光被太子諸咎所弒,隨后又接連發生弒君事件,越國元氣大傷,顯現出衰落跡象。
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變革,也影響了漢字形體的變化,文字逐漸演變為具有裝飾作用的藝術品,而不僅僅是純粹記錄語言的符號。鳥蟲書體的出現恰恰是這一現象的實證,鳥蟲書出現于春秋戰國時期,隨著青銅時代的終結而逐漸沒落,“主要流行于長江中下游地區,影響波及中原一帶。”以先秦國別而言,楚國最早出現鳥蟲書文字,而以越國器物中出現的鳥蟲書文字為最多。從鳥蟲書的構形特點來看,“飾筆的普遍線條化,把越國鳥蟲書帶到另一番境地,而成為越國晚期鳥蟲書構形的主流。”此劍銘文內容尚在研究中,僅能從銘文結構和劍的形制來進行判斷,該劍應為鳥蟲書越國青銅劍,筆者猜測為“不光劍”。“目前已知的不光劍約有30把之多”,是否能為“不光劍”再添新物,有待于各位專業人士的考證和研究。
此劍出現在臨淄戰國墓中,充分說明了齊、越兩國在歷史上是有交集的,也為史料記載的齊越之間的關系往來提供了實物證明。
齊文化博物院館藏文物中尚有獸鈕銅鼎、高足銅鼎、提梁銅盉等具有典型楚國青銅特色的藏品,也有高鼻深目、頭戴尖帽形象的胡人石俑。臨淄的考古發現中多次出現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蜻蜓眼玻璃珠,具有齊國特色的絲織品、銅鏡等也在西方國家考古工作中有所發現。在文化交流的雙向影響下,中西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的融合。
參考文獻:
[1]陸鵬亮,王倩.雁足燈的兩千年之旅[J].美成在久,2017(06):56-67.
[2][北魏]賈思勰.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齊民要術(全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5.
[3]任雪莉,史雯.從蒜頭壺看中西文化的交流[J].湖南省博物館館刊,2019(00):323-328.
[4]李零.論西辛戰國墓裂瓣紋銀豆——兼談我國出土的類似器物[J].文物,2014(09):58-70+1.
[5]趙德云.凸瓣紋銀、銅盒三題[J].文物,2007(07):81-88.
[6]曹錦炎.鳥蟲書通考[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
[7]曹錦炎,吳毅強.鳥蟲書字匯[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
[8]魏成敏,孟凡強,侯霞.臨淄考古發現與中外文化交流[C].//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岱絲語——“一帶一路”與山東研討會論文集,山東:齊魯書社,2020.
作者簡介:
蔡亞非(1984—),女,漢族,山東淄博人。齊文化博物院文博館員,研究方向:文物管理與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