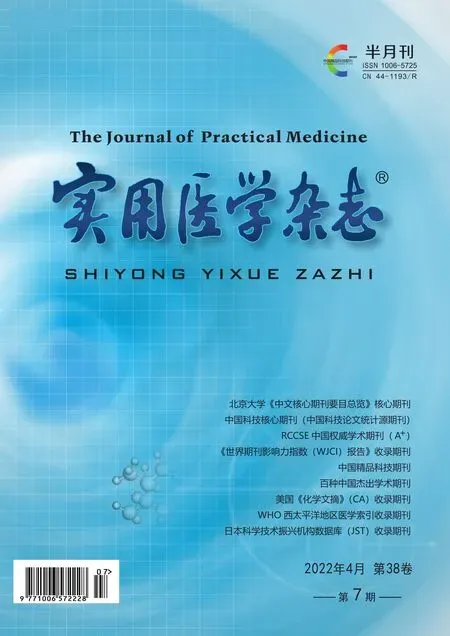膿毒癥表型研究新進展
周蘇 蔣永潑 戴罕之 林榮海
1紹興文理學院醫學院(浙江紹興 312000);2浙江省臺州醫院重癥醫學科(浙江臺州 317000);3臺州市立醫院(浙江臺州 318000)
膿毒癥(sepsis)是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伴有器官功能障礙,是全球性疾病及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及時的診斷和風險預估是減少膿毒癥并發癥和降低病死率的關鍵[1]。表現型(簡稱表型),指特定基因型生物個體在一定環境條件下所表現出來的性狀特征。膿毒癥是一種高異質性綜合征,具有大量的臨床和生物學特征,可能形成不同的潛在表型。筆者經過檢索近期膿毒癥相關表型的研究,總結以下幾類分型,幫助急重癥醫學科醫師更好的認識各類表型特征,并為膿毒癥的分類、精準醫學治療及預后評估提供更好的依據。
1 膿毒癥組學分型
膿毒癥的宿主反應高異質性一直是影響高病死率患者的識別及治療選擇的因素。隨著精準醫學研究的出現,使基因組等組學技術在分子學水平取得極大進步,這也為膿毒癥的精準治療策略提供了可能。
1.1 根據全基因組血液基因表達譜分類 SCICLUNA等[2]通過進行分子診斷和風險分層項目(MARS)研究,報告了一項關于膿毒癥轉錄組學的成果。研究收集了三個膿毒癥隊列患者的血樣并生成全血基因表達譜,通過無監督共識聚類技術和機器學習評估了140 個基因分類器,將膿毒癥患者分為四類即Mars 1 ~4,臨床資料顯示不同表型間患者的膿毒性休克患病率、SOFA評分和病死率存在差異,而伴隨疾病、APACHEIV 評分或急性肺損傷等無明顯差異。差異基因表達分析表明各型的基因表達不同:Mars1 型參與先天性和適應性免疫信號相關基因的下調,其隊列患者具有相對免疫抑制性、死亡率高;Mars2 型涉及模式識別、細胞因子、細胞生長等適應性免疫功能的基因表達上調;Mars3 型與適應性免疫途徑的基因表達上調有關,該型患者預后相對更好;而Mars4 型與識別模式和細胞因子通路的基因表達上調有關,最終還找出各型中特異表達較高的候選分子生物標志物分別為二磷酸甘油酸變位酶(BPGM)、生長停滯和DNA 損傷誘導α(GADD45A)、AHNAK 核蛋白(AHNAK)和干擾素誘導蛋白與四肽重復序列5(IFIT5)。膿毒癥Mars表型目前尚未應用于臨床,但部分學者借鑒其基因數據源、或機器學習模型以及膿毒癥免疫反應機制的啟發等衍生出新的研究。此類MARS 表型的識別也可能用于臨床試驗的個性化藥物管理和選擇,并為預測基因富集提供了機會,加強免疫療法或許能更好地治療Mars1 型患者,但以上理論還需進一步的臨床研究以驗證。
1.2 根據單核細胞軌跡分類 免疫系統是膿毒癥發病機制的關鍵,而單核細胞人類白細胞抗原DR 表面蛋白(the monocyte human leukocyte antigen DR surface protein,mHLA-DR)通過給T 細胞呈遞抗原在免疫反應中至關重要。BODINIER 等[3]運用KmL 聚類法分析膿毒癥患者入住ICU 后第1 周的mHLA-DR軌跡得出四種分型:(1)非改進型:mHLADR表達持續較低或幾乎不增加,平均低于4 000AB∕C(AB∕C,每個單核細胞結合的抗體數,表示mHLADR 表達程度,健康者測量值作為參考值);(2)衰退型:從mHLA-DR 表達參考值開始逐漸下降至7 500AB∕C 以下;(3)改進型:mHLA-DR 表達逐漸增加至第1周末幾乎達到參考值;(4)高表達型:mHLADR 表達快速增加直至參考區間,四種分型軌跡基本均低于健康者。研究表明膿毒癥患者早期(入住ICU 第1 周內)存在單核細胞的持續失活會增加ICU 獲得性感染發病率、病死率以及住院時間等風險。隨后一項研究[4]評估mHLA-DR 表達與重癥兒童繼發感染間的關聯,結果證實重癥兒童的mHLA-DR 表達低于健康對照組,這也與前文[3]得到的結論一致。還有研究將mHLA-DR 與血清降鈣素原結合發現在預測膿毒癥患者的致命結局方面更具準確性。根據第1 周mHLA-DR 軌跡可用于膿毒癥的早期風險分層,但根據mHLA-DR 軌跡的分型仍需要在臨床中得到更多的驗證。
1.3 膿毒癥反應特征(sepsis response signature,SRS)分型
1.3.1 社區獲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和糞源性腹膜炎(fecal peritonitis,FP)源性的SRS 分型 CAP 和FP 是膿毒癥最常見的感染因素,還有膽道感染、泌尿系感染、膿腫、軟組織感染等,但這些感染源是否與轉錄反應異質性有關尚不清楚。
DAVENPORT 等[5]運用無監督聚類分析CAP相關膿毒癥外周血白細胞全基因表達,發現兩種不同膿毒癥反應特征亞型:SRS1 型和SRS2 型,SRS1 型有免疫抑制、內毒素耐受、T 細胞耗竭和代謝紊亂及預后較差的特點,比SRS2 型的早期病死率更高、臨床指標水平更差,并定義了七個可預測SRS 亞型的基因(DYRK2、CCNB1IP1、TDRD9、ZAP70、ARL14EP、MDC1 和ADGRE3)。他們將基因轉錄變異相關的基因組決定因素繪制成表達數量性狀基因座(expression quantitative trait loci,eQTL),使用eQTL 映射法比較不同轉錄組間宿主對感染反應的異質性,發現膿毒癥相關基因關鍵介質(HIF1α、mTOR 等)具有遺傳變異作用,可能與缺氧反應和膿毒癥中的糖酵解反應過程相關。BURNHAM 等[6]進 一 步 比 較FP 源 性 膿 毒 癥 組、CAP 源性膿毒癥組和非膿毒癥者發現三者之間的轉錄基因組表達均存在差異,同樣找到兩種SRS 亞型,均與早期病死率密切相關,并定義了一些可預測感染源(FP 或CAP)的基因組(包括EPHB1、NQO2、ARG1、HMGB2、FGL2 和GPR162),表明膿毒癥基因表達變化的主要預測因子是SRS亞型,而不是感染源,這些發現給膿毒癥患者的分類提供了可能。兩項研究利用SRS 分型證明了FP源性和CAP 源性膿毒癥的轉錄組學表達存在差異,這豐富了膿毒癥的分類,完善了對膿毒癥異質性的理解,但在其他感染源中是否能發現類似的SRS 分型尚未給出更多的研究驗證。
1.3.2 結合兒科表型及SRS 分型 WONG 等[7-8]在早期研究中通過基因表達譜已經確定三個兒科膿毒性休克亞類(即表型A、B 和C),而后發現前期的轉錄組學研究[5]中所隱含的生物學和臨床的關聯與小兒膿毒癥表型的相關文獻報告[7]存在相似之處,則結合了兒科膿毒性休克表型和SRS 分型方法發現新的成人膿毒癥亞表型[9],評估SRS 與小兒表型之間的重疊分組,確定了分型組合模式、年齡與年死亡率之間的相互作用,最終表示兩種組合表型表現出免疫抑制性的患者死亡風險最大,其中表型A∕SRS1 分型可能會識別出免疫抑制性更高的膿毒癥人群,但該組樣本量過小,目前的預估并不精確,而且不同年齡所對應的免疫效應還需要進一步的重復驗證。
2 體溫軌跡分型
體溫調節反應是膿毒癥異質性的一種表現。發熱是感染的先兆,被感染者常常表現為體溫升高,也表現體溫正常或低體溫。一項研究表明機體受到感染時體溫過低會增加患者病死率,體溫過高則可能降低病死率[10-11]。BHAVANI 等[12]根據體溫變化軌跡定義了四種體溫軌跡表型:(1)高熱慢退型:患者年齡最小,合并癥最少,白細胞數減少或增多的發生率、ESR 和CRP 水平最高,肌酐值水平最低,每日尿量最多,心率最快;(2)高熱快退型:患者乳酸水平最低,病死率最低;(3)低體溫型:患者年齡最大,合并癥最多,白細胞計數減少或增多的發生率及ESR 和CRP 水平最低,肌酐和乳酸水平最高,尿量最少,心率最慢,院內病死率最高;(4)體溫正常者。研究表明四種表型的炎癥標志物和結局具有顯著差異,BHAVANI 等[13]在之后的研究中發現溫度軌跡表型與不同感染隊列中一致的細胞因子譜相關,這些表型可能在發現膿毒癥患者細胞因子譜的床邊鑒定中發揮一定作用。鑒于小兒膿毒癥的獨特性,YEHYA 等[14]則研究了小兒膿毒癥患者體溫軌跡分型的意義,與前者[12-13]結論基本一致。住院患者的體溫監測常規且反復進行,使體溫軌跡分型有望成為輔助型診斷手段,為膿毒癥患者的識別和預測提供了新的思路。但該亞型的差異性還缺乏免疫學基礎依據,需要進一步證明這種溫度軌跡分型與潛在的免疫反應是否存在關聯。
3 重癥膿毒癥(嚴重膿毒癥或膿毒性休克)相關分型
3.1 膿毒癥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表型 KNOX等[15]使用自組織映射神經網絡(Self Organizing Maps,SOM)技術根據重癥膿毒癥患者的年齡和SOFA 評分等生成SOM 網格并細分出四種膿毒癥相關MODS 集群:(1)伴有腎功能障礙且肌酐升高的休克;(2)輕度MODS;(3)伴有低氧血癥和精神狀態改變的休克;(4)肝功能障礙者(包括慢性肝病及各種原因引起的膿毒癥急性肝損傷等)。膿毒性休克患者以第1、3 類為主,嚴重膿毒癥則以第2、4 類為主。研究表明各集群間的臨床預測因子與病死率的相關性存在顯著差異。
3.2 潛在類別變量建模——潛在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LCA) G?RDLUND 等[16]運用LCA整合了納入患者的46 個基線人口學、臨床和實驗室變量,確定出6 種不同的膿毒性休克亞型:(1)無并發癥者;(2)肺炎合并成人呼吸窘迫綜合征(adult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3)術后腹型;(4)嚴重膿毒性休克;(5)肺炎合并ARDS和MODS;(6)膿毒性休克晚期。研究發現腹部感染可出現在不同類別,肺部感染者亦然,同一部位感染者也有不同的臨床表現和病程,但即使單個部位感染的患者,其后續的風險程度也存在著異質性,所以僅根據感染部位將膿毒癥分為不同類別還有待討論。
KNOX 等[15]排除的醫院內和術后感染者與G?RDLUND 等[16]所提出的“術后腹型”和“膿毒性休克晚期”患者交疊,而后者排除的患者(伴有心臟病晚期和肝病、腫瘤未得到控制以及服用抗血小板藥物或有其他出血危險因素者)中部分伴有肝病者卻與前者所提出的“肝病”型部分重合。兩項研究[15-16]具有相似之處,也相互區分,均不能完全解釋所有膿毒性休克患者的特征,還需在未納入隊列的膿毒性休克患者中進行驗證。
4 膿毒癥相關器官功能障礙分型
4.1 呼吸功能障礙——ARDS 分型 CALFEE 及DELUCCHI 等[17-20]在四項ARDS 相關隊列研究中得出兩種ARDS 表型——“低炎型”和“高炎型”,研究表明兩種表型具有不同基本特征,并對呼氣末正壓治療、隨機分配的液體策略都有不同反應。SINHA 等[21]發現他汀類藥物治療膿毒癥急性肺損傷(statins for acutely injured lungs in sepsis,SAILS)是與膿毒癥密切相關的ARDS 隊列[22]。為了驗證前述四項試驗[17-20]得出的兩種ARDS 表型是否適用于膿毒癥患者,SINHA 等[21]使用LCA 法也定義了兩種SAILS 相關表型,發現不同表型對不同干預措施的反應存在差異,二次分析發現在確定SAILS 表型的LCA 模型基礎上加入新的臨床變量并不會得出新表型。研究發現SAILS 隊列中高炎型患者的IL-6、IL-8、sTNF-R1、ICAM-1 和PAI-1 平均水平高于低炎型,這與ARDS 表型研究結論[17-20]基本一致。但SINHA 等[21]提出的結論僅是二次分析后的推理,SAILS 表型的說法還缺乏臨床依據,而且LCA 模型極其復雜,難以作為臨床常用工具,而使用常見變量快速識別模型亞型仍是提高臨床可行性所必需的。
4.2 凝血功能障礙分型 KUDO 等[23]運用機器學習分析膿毒癥患者得出四種基于凝血標志物的膿毒癥表型:(1)Cluster dA:有嚴重凝血功能障礙,具有高FDP 和D-二聚體水平、嚴重器官功能障礙和高病死率;(2)Cluster dB:患有中度凝血障礙的重度疾病;(3)Cluster dC:患有凝血障礙的中度疾病;(4)Cluster dD:有輕度疾病但不伴凝血障礙。研究發現不同表型進行重組人血栓調節蛋白抗凝治療的效果存在差異。此項研究僅針對日本患者,其結果存在局限,有待在其他國家或地區驗證,或可增加肝素等其他抗凝藥物的治療比對KUDO 等[23]的研究,加強對膿毒癥相關凝血功能障礙患者的診治。
5 外科膿毒癥感染部位分型
STORTZ 等[24]進行了一項外科膿毒癥(外科膿毒癥定義為在手術和創傷ICU 中治療的膿毒癥)研究,有研究表明感染部位是早期病死率的獨立預測因素[25],STORTZ 等[24]則根據感染部位分為腹部(44%)、肺部(19%)、皮膚∕軟組織(17%)、泌尿系統(12%)和血管(7%)5 類,發現皮膚∕軟組織和泌尿系統類型年輕患者多見,合并癥較少,免疫反應較輕,且器官功能障礙恢復較快,遠期結局較好;而血管型多見于老年男性患者,并發癥較多,遠期結局最差。研究表明不同感染部位的外科膿毒癥患者在基線傾向、免疫反應、器官功能障礙轉歸和遠期結局均存在顯著差異。并且COX 等[26]更證明腹部膿毒癥患者的慢性危重癥發病率高,長期預后不佳。根據感染部位的分型為預測外科膿毒癥患者的結局提供了新的思路,其他部位的外科膿毒癥結局也可在臨床進一步驗證。
6 多因素整合分型
現階段關于膿毒癥表型的研究大多利用單因素(如感染部位、器官功能障礙模式或疾病嚴重程度)進行分類,但膿毒癥的高度異質性仍不能得到充分解釋。KNAUS 等[27]認為更準確地定義表型才是確定精準治療的關鍵。
SEYMOUR 等[28]進行了一項膿毒癥表型的多維研究,選擇29 個常規臨床數據作為候選變量進行3 個隨機對照試驗(推導隊列進行建模,驗證隊列用于檢測),運用共識k 均值聚類法發現四種膿毒癥衍生表型即α、β、γ 和δ。研究表明這四種新表型具有不同的人口學特征、生物學指標水平和器官功能障礙類型,并與宿主免疫反應的模式、病死率和其他臨床結果密切相關。驗證隊列與推導隊列中的表型分布基本一致,不同表型的生物標志物模式也存在著顯著差異。模擬結果證明這些表型可能有助于臨床試驗的設計和解釋,也有助于對治療效果異質性的理解,但還需要驗證這些表型在臨床診治及護理中的有效性。
7 總結與展望
及時的診斷和早期治療是減少膿毒癥并發癥、降低病死率的關鍵,而膿毒癥高度異質性加大了疾病精準化診治及管理的難度,靶向治療便成了膿毒癥走向精準醫學的必經之路。無監督學習與臨床或生物標志物結合,已成功應用于腫瘤學以分析癌癥患者的腫瘤異質性。近年來基因型研究和機器學習也逐漸成為膿毒癥研究的主要技術,回顧關于膿毒癥分型、診治手段和預后等方向的研究發現,大多數以單項數據分析為主,雖然一些多維向研究已經能作出很好地細分,但仍需大量前瞻性研究進行驗證。膿毒癥基于基因組學的突破也將會是臨床醫學實施精確化診治的機會,雖然已經有相關研究發現新的分型和生物標志物,但操作極其繁瑣,目前仍無法應用于臨床。相信隨著對膿毒癥研究的不斷深入理解,新的分類方法將會得到突破,膿毒癥患者的個體化診治和管理也會帶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