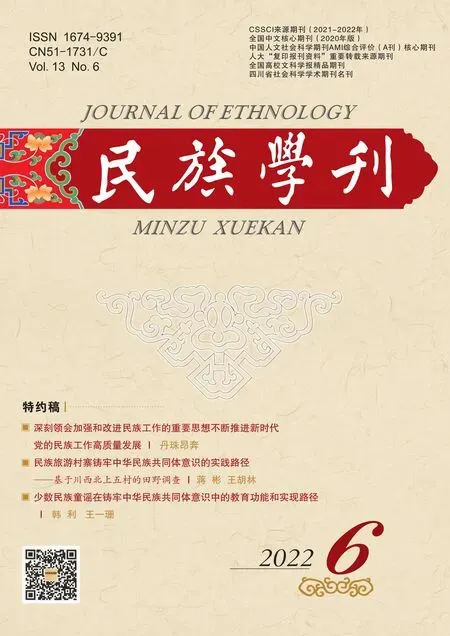史詩演述的儀式效力與知識共享:對彝族諾蘇支系“勒俄”口頭表演的民族志研究
劉嘉穎 摩瑟磁火

一、史詩演述的社會效力:列維-斯特勞斯和雅柯布森的理論視角移用
對于神話敘事和儀式話語的關聯性探索可以追溯到結構主義大師列維—斯特勞斯在《生食與熟食》及其《神話學》另外三卷中對口頭藝術和儀式音樂化言語類型的互文理解。他在《生食與熟食》的緒言中指出了神話、語言和音樂的密切關系,認為神話連接了“兩種截然相反的符號系統——一面是音樂語言(musical language),另一面是清晰言語(articulate speech)”[12]。對于列維—斯特勞斯來說,神話在儀式中的結構再現是一種重要的溝通過程,它以集體可理解的精神意象確立了某種文化的象征力量或者意義來源。
基于巴西南比寬拉人(Nambikwara)的“靈異事件”、北美祖尼普韋布洛(Zuni Pueblo)男孩“被控巫術事件”和美國西北太平洋海岸薩滿的“游巫”經歷三個案例,列維—斯特勞斯建立了“巫師—病患—公眾”三位一體的分析模型來闡釋這種集體表征的效用。他談到:
我們看到在巫術的效應中也顯示出對巫術的相信。這種相信包含著三個方面,它們相輔相成:首先是巫師對于自己法術效果的篤信,其次是病人或受害者對于巫師法力的信任,最后還有公眾對巫術的相信與需要——這種相信和需要隨時形成一種引力場,而巫師與中邪者(患者)之間的關系便在其間并從中得以確立[13]。
列維—斯特勞斯認為,巫術的可信度和實踐效力在于薩滿對患者疾病的親密體驗與群體共識之間的雙向互動[14]。如在對巴拿馬庫納(Cuna)巫師為難產婦女舉行分娩儀式的研究中,列維—斯特勞斯將儀式專家唱誦的“巫歌”理解為神話敘事的再現和意義確立過程,并借用了精神分析學的“發泄”(abreaction)概念來解釋庫納巫師擅于誘使和化解病人疼痛體驗的“病理性思維”(pathological thought),從而表明薩滿巫師的表演不僅僅是一種“儀式行為”,而是對患者疾病的精神、社會和其他原因的重新體驗。列維-斯特勞斯的論述有力說明了療愈儀式是將個人的疾病、疼痛和痛苦經歷置于更廣泛的社會和精神聯系中,通過調適不同主體間的適當關系而得以確立儀式效用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公眾對于巫術的信任是巫術效力達成的社會基礎,也是象征體系構建的根本所在。
列維—斯特勞斯圍繞神話敘事來理解薩滿療愈儀式的方法為我們理解廣泛存在于我國民間的祖靈信仰、祭祖類巫祭儀式中的復雜語用關系,以及具體儀式實踐所呈現的社會互動過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參考。具體來講,薩滿巫師的出神表演與彝族祭祖送靈儀式中的史詩演述有著相似特征,但史詩演述人并不會進入“薩滿意識狀態”(shamanic states of consciousness)來表現與超自然力量溝通和協商的行為。然而,在進入神話創造和毀滅的象征領域時,史詩演述人如薩滿一樣會強化自己的敘事和聽眾聆聽敘事的體驗。換言之,所有聆聽史詩演述的公眾都必須相信演述的內容和演述人的力量,從而參與至一種社會宇宙時空的建構過程。
如果我們采用列維-斯特勞斯的分析模型并作一定調整,那么可以看到史詩演述在遵循祭祖送靈儀式的儀軌和口頭表演程式的基礎上,其溝通力量的達成需要由三個部分組成:
1.史詩演述人對于自己演述效果的篤信;
2.儀式主人家及家族亡靈對演述效果的相信與需要;
3.社會公眾對史詩演述的期待與需要
這種三位一體的篤信、期待與需要也表現出史詩演述人所主導的文化翻譯過程。在史詩演述中,關于勒俄本源、人類起源等敘事可以理解為對祭祖送靈儀式符號交流體系的“元語言”評論[15]或者語言內解釋過程。賽維里(Severi,2014)[16]和希爾(Hill,2019)[17]分別在他們的研究中重新審視了雅柯布森[18]的翻譯理論方法,指出文化翻譯的三種過程:一是語際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或翻譯本身,即通過其他語言對語言符號的解釋;二是語言內解釋(intralinguistic interpretation),即通過同一語言的其他符號對語言符號的解釋;三是嬗變(transmutation),即通過非語言符號系統對語言符號的中間翻譯。他們對南美洲印第安社會的研究探討了敘事話語、音樂聲音和視覺代碼間的跨符號轉換機制,說明了嬗變這一文化翻譯過程在宗教儀式中的重要性。而本文將重點圍繞語言內解釋這一文化翻譯現象,考察史詩演述人如何表現出對生者與逝者、個體與公眾、人類與他者關系進行協商的能動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勒俄的神話和起源敘事能夠以其“聽聞性”“可理解性”和“賽說娛樂性”在儀式中得到觀眾的即刻回應,其在畢摩專業的宗教言語類型和日常社會生活語用之間充當著文化內部的語言翻譯,也因此建構了一個知識共享的文化渠道。
最后,由戴爾·海姆斯(Dell Hymes)開創的“講述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研究方法也為我們洞察勒俄表演的社會文化形態帶來了啟發。講述的民族志強調對“講述事件”的分析,關注口頭藝術形式在社會互動中的交流性質[19]。當前,民俗學學者們紛紛關注到表演者調度口頭傳統的知識庫(repertoires)并根據儀式語境即興創造聽覺等感官交流體驗的靈活性特點。而本項研究也旨在探討史詩演述人在演述的實踐場域和經驗積累的過程中是如何以社會建設性的方式確立其演述效力的。因此,我們不僅需要理解勒俄演述的情境,還需要把一個社區的交際習慣作為整體語境來考察其中的語言互動及闡釋規則。基于以上理論視野的啟發,我們將在下文中解讀到史詩演述如何伴隨多向度的溝通達意過程來創造、指導和解釋具體的儀式實踐。
二、彝族史詩“勒俄”演述傳統及其儀式表演語境




勒俄演述在祭祖送靈儀式中與畢摩的言語藝術相得益彰,不僅體現了這種口頭文類的傳播價值,也充分展示出其文化翻譯的重要性。可以說,勒俄演述是畢摩們的宗教知識與民眾的世俗知識之間一個重要的聯結點。
三、彝族祭祖送靈儀式的文化背景

彝人認為若不為逝者舉行超度活動,其靈魂就會無家可歸,游蕩無著,受苦受難,當然也就免不了有時會變作鬼怪來禍祟子孫。舉行送靈大典可以為逝者之靈解除各種勞累病苦和從世間帶去的各種業緣,使其輕松、愉快、健康地加入祖先的行列,得到安寧的生活,且能福佑子孫。所以,舉行超度送靈活動主要有兩大目的:一方面可藉此表達子孫們的孝心,寄托對逝者的思念,緬懷祖先;另一方面可以在舉行儀式的過程中向祖妣祈愿,祈求子孫人丁繁衍、五谷豐登、六畜興旺。


在本次進行田野調查時,我們特別關注史詩演述如何以巧妙的指意過程揭開了一個靈魂得以升華而持續影響世間的宇宙世界。史詩演述的比賽互動在畢摩儀式中嵌入了關于物種間的轉換過程(神話祖先和人類后裔、人類與動植物、男性與女性、血親與姻親、我族與他族),以及人類生命周期轉換的敘事,從而在儀式中生動展現了人與萬物的交流協商、空間想象和文化記憶的思維過程,并折射出彝族譜系觀的道德意涵。這也提醒我們密切關注神話與巫祭行為在共同促成祭奠與安撫逝者靈魂這一項儀式工作時的關鍵作用。
四、祭祖送靈儀式中勒俄演述的個案分析
我們的田野點⑧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一個高寒村寨,屬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美姑縣J鄉S村。該寨共居住有寨民13戶,分屬4個家支。舉行祭祖送靈大典的儀式男主人名叫阿伙某某,時年45歲,是家中獨子,有4個姐姐嫁去了鄰縣雷波境內,將在儀式第二日代表姻親方來參加儀式。阿伙家舉行祭祖送靈儀式的目的是為阿伙某某已故父母、前妻和夭折女兒的靈魂進行超度。由于主人家經濟條件困難,無力在祭祖儀式中自主舉行勒俄演述比賽,在征得主人同意后課題組決定予以資助,于是邀請了居住在美姑縣佐戈依達鄉溫子覺村的曲比拉合(男,時年38歲)和美姑縣拖木鄉拖木村的吉則洛哈(男,時年45歲)兩位勒俄演述藝人前來進行勒俄演述和賽說表演,并通知阿伙某某以其主人的名義向兩位演述人進行了電話邀請。
(一)勒俄演述事件與儀式性互動
在為期三天兩夜的祭祖送靈儀式中共進行了兩場演述比賽,涉及口頭論辯克智和廣義的勒俄內容。第一場安排在儀式第一天的晚上主人家屋內舉行“咒鬼”儀式環節中,待畢摩們誦完《驅鬼經》之后(當晚21點左右),按照慣例和主祭畢摩的時間安排,兩位勒俄演述人便在趕來參加儀式的親友及鄰里的簇擁下開始進行勒俄演述比賽。曲比拉合代表主人家(坐在主人家火塘里側的主人位),吉則洛哈代表姻親家族(坐在火塘外側的客人位),演述持續約2小時。
按照通行的程式,兩位演述人開場時從本次演述發生的緣由說起,先介紹本次祭祖送靈儀式的主人及儀式的主祭畢摩,然后用克智互相酬問應答,其間多有自我標榜、互相諷喻之詞,多個回合之后才進入正式的勒俄演述比賽,以雙方輪流演述的方式進行。在從克智的知識論辯過渡到勒俄的時候,通曉這一程式的聽眾積極回應并影響、參與了演述文本創造的過程,如例1⑨所示:
例1:

(聽眾:干,上升到勒俄,進入勒俄。干得好,哎呀干快點,到路上方,克智多了點。勢均力敵,許多都從來沒有聽到過呢。)

(曲比拉合:好的。你再來一段,路上方還是我先來,因為我是主人家。)

(聽眾:原來你兩是互相謙讓著來的。)
在例1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場聽眾能夠領會表演的文本內容和話輪轉換語境并予以回應,且在演述人的克智論辯文類趨于尾聲并準備過渡至勒俄時,能夠理解并進行一定程度的“干擾”,以期望并助推演述人加快節奏進入“路上方”(即勒俄)環節。另外,由于聽眾插入的話語是輪至代表主人方的曲比拉合演述的小節尾聲,曲比拉合隨即采取了應對策略,根據語境進行了“協商”,轉而告知客方代表吉則洛哈繼續演述一節克智,從而表明按照儀軌應由他本人在下一輪來“主導”進入勒俄演述。緊接著,聽眾對講述結構的調整也作出了“原來……”的評論回應。
在接下來兩人進入勒俄演述前的尾聲階段,我們可以看到兩位演述人也在話輪轉換的過程中進行了文本內容的協商。主導方曲比拉合并沒有急于進入勒俄,而是對勒俄進行了鋪墊和補充說明:
例2:

(吉則洛哈:那就往前走嘛現在就?)

(曲比拉合:等會兒,我先來。)

承咦!
…………

結婚時是重譜系的嘛

送靈時是重勒俄的嘛
…………

超度送靈是由阿署阿俄興

承咦!

為何由阿署阿俄興起呢

遠古時候尼扎山下孜阿迪勒一代生子不見父而亡

(聽眾:今夜干對了)

迪勒蘇涅兩代生子不見父而亡
(曲比拉合:哎—就是這樣的呢)
…………

你家現在.祖靈竹簍呢送到木屋石屋中去

之后就會子孫繁衍子孫千百數云云

(聽眾:哦—哦—哦啊!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哎呀。雖然是個年輕人怎么,聰明得很的呢。好好好啊。)

(聽眾:哦,曲比家的小伙子呀主人家的你也說了,客人的你也說了,我會聽。)

(曲比拉合:現在呢你就進入勒俄吧,你還是來一段史爾俄特。)

在進入勒俄環節后,曲比拉合共演述了“勒俄十九枝”中的八枝,內容包含“勒俄本源”“開天辟地”“天地演化”“修整天地”“創造生靈”“上界落種子”“武哲十二子”“人類起源”等,接著演述了“洪水泛濫”“天地婚姻”“族群繁衍”“糯恒賽變”“君長遷徙”等內容。而吉則洛哈也相應地演述了 “勒俄十九枝”中的八枝,內容包含“勒俄本源”“開天辟地”“天地演化”“上界落種子”“狐貍勒俄”“修整天地”“生靈演化”“作祭促進繁衍”等,還演述了被他們看作為“波帕”的“阿留舉日”“支格阿龍”等內容。演述過程中,聽眾們與演述者密切互動,每表演完一段,聽眾們都不由贊嘆,且有聽眾不時給兩位演述者一些獎勵。


例3:

褆比乍穆因此來發話

下界之中呢

長出什么草牛羊就吃什么草

上側有牛羊

牛羊做犧牲

下側有豬雞

豬雞做拴牲

楊樹削白做神枝

如此作祭后

靈牌掛到屋上側

杵臼安在屋下側

如此做之后

上方喊父得父了

下方喚母得母了

如此之后呢

如今此時呢

順便由此說到譜系去
例3源自吉則洛哈演述“尋父買父”尾聲階段的轉錄文本,穿插著傳說中天界畢摩師祖昊畢史楚和下界畢摩始祖禔畢乍木的人物形象。演述以詩行為結構,長度從四到九個彝語音節不等。這段演述內容強調了為祖妣作祭的起源——包括具體的貢牲、植物用品和空間實踐。鑒于彝族宇宙觀建構了一個受昊天神靈啟發的時空流轉過程,這些對祖靈信仰實踐的神話敘事也暗示了元始神話時代中,人類從“動物性”中分化開來而逐漸獲得“文化”“語言”和“譜系”的思維過程。“喊父得父”“喚母得母”即是在這種調解人與非人之間的轉換和分化狀態中付諸實踐的。從這個意義來講,這些冗長的神話和起源敘事也是對“有聲言語”的元語言闡釋。
在雙方進行多個回合的演述比賽之后,最后都謙虛地表示自己為輸的一方,互相敬酒之后收場。盡管室外的天氣非常寒冷,但一點也不影響勒俄演述者和聽眾們的熱情,大家都凝神靜聽,有的聽眾還不時激動地發出贊嘆之聲,有的大呼精彩。如上述語境介紹,講述“尋父買父”的神話起源是在祭祖儀式中演述勒俄時必不可少的一項內容,與青棚下畢摩和主人“朵體”敘話內容互文,二者之間有著一種相互呼應、相互補充、交相輝映的關系。所以,這也是畢摩們的宗教知識與世俗的勒俄知識之間一個重要的聯結點,通過在同一場所進行的“朵體”和勒俄演述,畢摩、勒俄演述藝人與民眾之間實現了真正的知識交流和分享。
勒俄演述完畢后,畢摩們繼續在青棚下舉行儀式,主要是誦讀《獻水分魂經》,將祖靈與其在世的子孫靈魂區分開。最后獻酒給祖靈讓其睡覺,當晚的儀式才算完成。儀式第三日將持續完成送靈儀式的后續環節,并最終將亡魂超度至前文所述的祖先世界。
(二)基于聽覺的交流體驗和知識共享
史詩演述的儀式化表演是傳遞和傳播彝族人的傳統知識、世界觀、語言意識形態和文化記憶的重要手段,祭祖儀式中的勒俄演述表明了彝族的譜系制度和文化記憶源于這些知識共享群體正在經歷的當下、最近的過去和神話般的過去。在許多語境中,諸如“支格阿爾”“史爾俄特”這樣的神話英雄人物在故事中的重要性不在于這些名字本身,而在于名字和故事被不斷銘記,以及史詩演述比賽的聲音被發出、聽見和篤信的過程。
在這種由口頭表演形成的賽說傳統中,所有已“出師”的克智和勒俄演述藝人都需要經過多年的口傳心授訓練和現場賽說演練。在每一次現場的口頭表演中,他們需嚴格遵照一定的程式,先互相問候平安吉祥并就紅白喜事的儀式語境來進行起源敘事、猜謎,從而在你追我趕、你來我往的賽說中比賽口才,進而才能進入勒俄演述,以及順理成章地說到屬于“布茨”的譜系范疇。經過比賽經驗的積累和榮譽獲得,某些演述藝人的名字會傳到百里開外,從而也會收到更多的邀請,并逐漸建立自己和其家族的口碑。

前面的都沒有說,后面的怎么能成立呢,最初沒有地,也沒有天,沒有太陽,沒有月亮,之后由一些神人圣人來創造出來,沒有樹木沒有水,原野沒有云雀叫,森林沒有獐鹿跳,什么也沒有之后,全部都由神人圣人阿普阿薩,天神地祇一起創造出來安在天上,上界和下界一起管理才把這些創造出來,那么,現在你卻私自要把它攪亂從中間隔開,只說譜系知識的話,不應該這樣的嘛。
可見,吉則洛哈嚴守勒俄演述的程式,并暗示出演述儀軌的道德內涵。勒俄鮮活地描摹了一個宇宙從最初的混沌時代向天地分離時代的元始轉換,敘述了世間生靈在昊天神明啟示下的創造與改造過程,以及人性的不斷建構、毀滅和重塑過程,另外還囊括了遠古部落遷徙歷史和強調親屬及性別關系的敘事。因此,諸如在喪禮和祭祖送靈儀式中的勒俄演述也說明了它為人類的起源、分化和社會建構(譜系)的穩定轉化過程提供了一個基于演說和詩唱的文化解釋。
那么,史詩演述是如何呈現出儀式主人家及其家族亡靈對演述效果的相信與需要的呢?主祭畢摩阿爾可地這樣說道:
老人去世時間太久以后就無人關注了是吧,一般做畢(家中舉行各類儀式)時他們也不知道,終有一天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已經被超度了……在家進行熱鬧的賽說他們就可以聽見。有人會說“啊呀你們家里不知怎么回事,賽說的人也在座。很熱鬧的樣子,你去家里看看后代吧,不知在做什么。”……(賽說中)談論勇士的故事,談論高低貴賤的時候,他們(祖妣)就高興了,畢摩也為他們指路,子孫們也為他們送行。
如阿爾畢摩所言,賽說暗示出一種聲音的效力,它以熱鬧和論辯的社區氛圍烘托出對家中逝者和地位躍升的祖妣的祭奠與記憶。在這些文化記憶中,我們會發現史詩演述人追憶他者生活的痕跡,對于吉則洛哈來說,每一次演述發出的聲音也是自己已故父親為其口傳心授的聲音。這些聲音在儀式場域被記住并被喚起,也能夠讓參與儀式的公眾觸及到與先賢的情感和道德聯系。基于這種聽覺交流的文化效力,有關創世神話、祖先和譜系的故事都能夠被廣泛聆聽、理解、傳播,并且得到整個社區的共鳴:






五、結語
彝族諾蘇支系史詩演述傳統與其社會歷史不可分割。史詩演述的儀式化表演是傳遞和傳播諾蘇人的傳統知識、世界觀、語言意識形態和文化記憶的重要手段之一。史詩演述人的口頭表演在畢摩主持的儀式中嵌入了關于物種間的轉換過程(神話祖先和人類后裔、人類與動植物、男性與女性、血親與姻親、我族與他族),以及人類生命周期轉換的敘事,從而在儀式中生動展示了人與萬物的交流協商、空間想象的思維和文化記憶的過程。基于對祭祖送靈儀式中舉行的勒俄演述內容和互動形態的分析,我們可以看見史詩演述為人類的起源、分化和社會建構(譜系)的穩定轉化過程提供了一個基于演說和詩唱的文化解釋,并嵌入了彝族譜系觀的道德意涵。勒俄史詩包含了彝族的當下、歷史和神話經驗所集成的知識、智慧、記憶和情感,這種具有神秘力量的演述話語被視為具有調節我者與他者關系的互為主體性力量,也因此需要在一定的口頭程式和儀式互動中來呈現與重塑。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南美儀式的研究首先轉向了以話語為中心的研究方法[29],開始出現一種更為平衡的方法來研究儀式專家的口頭表演[30][31]。本文研究表明,基于對“史詩演述人—儀式主人家(及家族亡靈)—儀式參與公眾”的溝通過程分析,能夠洞察出儀式詩唱和演述專家如何以社會建設性的方式來引導、闡釋和確立社會宇宙時空的動態轉變與更新過程。如果我們采用列維-斯特勞斯的分析模型并作一定調整,可以發現史詩演述為祖靈信仰和巫祭行為提供了可理解和交流的感官維度,其在專業的宗教言語類型和日常生活語用之間搭建了一條重要的文化翻譯渠道。這種三元一體的分析模式以及以感官和話語為中心的研究方法能夠幫助我們拓展對儀式溝通、口頭表演和日常語言的關聯性認識,有助于我們理解神話和起源敘事的社會價值。
注釋:
①畢摩是彝族民間的宗教執業者,掌握彝文典籍,熟諳彝族宗教儀禮。“畢”為“誦讀”之意,“摩”指長老、耆老,合之指誦讀經典的長老。畢摩在創造、規范和整理彝族文字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歷史上的土司轄區,世俗層面的彝文教育也曾得到發展,特別是從民眾經籍的抄后記中記載的傳抄譜系來看,大部分都會將其源頭追溯到某一家著名土司。參見摩瑟磁火《彝族諾蘇支系宗教經籍寫本特征概述》(2016)。
②儀式話語是具有語言-音樂連續體特征的話語,指儀式專家在儀式場域中強有力的誦唱、吟誦、言說等復合性溝通話語。如杜夢甦(2012)從音樂性探究了這一話語特征,將涼山畢摩儀式表演中的經文唱誦風格分為“詠唱式”“吟唱式”“誦唱式”和“綜合式”四類。

⑤彝族諾蘇支系使用彝語北部方言,具體又分為兩種次方言和五種土語。從語言、地域和服飾綜合來講,通常分為圣乍、以諾、所地三個區域。如果將勒俄傳承情況作一個比較,所地地區的瀕危狀況更為明顯,圣乍地區次之,以諾地區因為處于彝族諾蘇支系分布的腹心地帶,彝族傳統文化保留較為完整,彝族文化氛圍濃郁,所以其傳承情況相對良好。
⑥有的則認為在祭祖送靈儀式上演述的為“花勒俄”,如下文提及的演述人吉則洛哈。
⑦“克斯”為彝語音譯,“克”為“口”之義,“斯”為“談話”、“聊天”之義,合之指相互酬問應答,引申指在婚禮等場合進行的賽說。
⑧本次田野調查受到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中國史詩百部工程》子課題“彝族史詩《勒俄》(四川省美姑縣)”資助(主持人:摩瑟磁火);第一作者劉嘉穎時為美國南伊利諾伊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在四川涼山州進行了為期16個月的博士論文田野調查,并協助課題組完成了勒俄演述的攝錄工作。文章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資助(2020SQN25),在后期田野回訪和材料分析的基礎上不斷完善形成。
⑨有“括號”和斜體字標記的部分為轉錄文本中的交際話語,其余為勒俄演述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