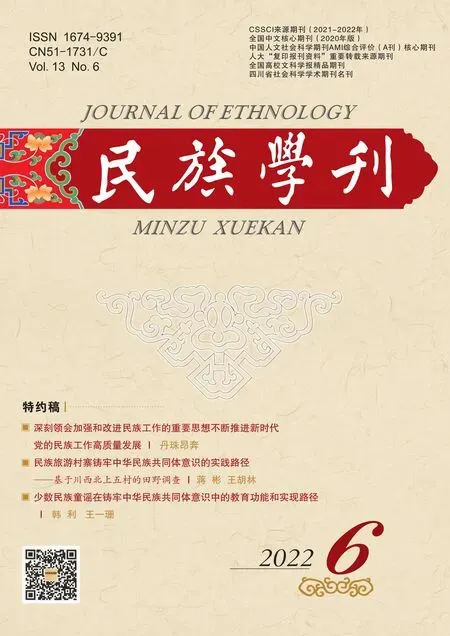身為言意 舞樂合節
——少數民族審美視域下舞與樂的三重性
熊 嫻 李延浩
近年來,隨著新文科理念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深入貫徹,關于民族舞蹈如何與民族音樂進行融通及學科交叉的研究也逐漸成為民族文化研究者所要面對的嚴峻課題。目前,學界關于民族舞蹈與音樂的研究,可以分為兩類:一為民族舞蹈與民族音樂互動研究。例如田甜的《民族民間音樂與民族舞蹈之間的互動研究》對我國民族舞蹈和音樂的關系進行了歷時性的梳理,進一步確立了兩者不可截然分割。一為民族舞蹈與民族音樂在教學實踐中的應用。例如石明燈《民族音樂教育與民族民間舞蹈教學實踐探究》以民族舞蹈和音樂為核心,闡釋了民族舞蹈和音樂在現代學科教學中的示范作用,強調了民族舞蹈和民族音樂與我國現代學科結合的可能。盡管如此,在對民族舞蹈與音樂的研究中,學者們似乎忽視了一個問題,即舞蹈和音樂在何種基礎上,以何種方式來融通?
我們知道,“有樂而無舞,似聾者知音而不見;有舞而無樂,如啞者會意而不能言。樂舞合節,謂之中和。”[1]舞蹈與音樂作為兩種藝術形態,以不同的介入方式深嵌在人類文化歷史進程中,相互關聯,交錯共生。盡管作為兩種不同的言說方式,它們分別占有相應的媒介,但是都共享同一本體——“人”。著名音樂家葉純之指出:“音樂與舞蹈之間的確存在著一種聯系,音樂提供了一種可舞性,這是一種潛在的素質,當音樂被舞蹈采用后,就使得音樂本身的可舞性變成了現實。”[2]。換言之,舞蹈與音樂是“人”這一有機體向外凸顯主體性的兩種面向。因而,舞蹈是可視化的音樂,而音樂是舞蹈的形體提純。舞與樂之間的這種關系織體便塑造了其本身的“三重性”,即互文性、納構性和表征性。或許,我們可將其視作一種知覺場,或一種環境。正是在此前提下,民族舞與樂作為一種有機體具身介入的更為“原始性”的傳達媒介,締造了一種互為嵌套的話語場。那么,它們何以在這樣的場域中協調、共生與釋放力量呢?
一、身為言意:民族舞蹈與音樂的互文性
就民族舞蹈與音樂的本體而言,一方面,民族舞蹈是有形而無聲,另一方面,民族音樂則是有聲而無形。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在民族舞蹈與音樂藝術中,民族音樂充當了舞蹈的聲音,而民族舞蹈勾勒出了音樂的形體。基于此,我們看到了民族舞蹈與音樂之間存在著一種潛在的互文性。
“互文性”也稱“文本間性”或者“互文本性”,這一概念出自法國著名的符號學家朱麗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的《符號學》(1969)一書。她在該書中認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轉化。”[3]朱麗亞·克里斯蒂娃的理論無疑為我們窺見民族舞蹈與民族音樂之間的互文關系,提供了有力的參考范式。無論是舞蹈,還是音樂,都是一種基于對“美”本身狀態的一種體驗陳述。在這種陳述中,作為審美主體的人,舞蹈借助的是人的身體,而音樂卻訴諸于人的聲音。二者都是基于一定規則上的生成。正如格羅塞所說:“跳舞的特質是在于動作的節奏調整,沒有一種舞蹈是沒有節奏的。”[4]因而,我們可將民族舞蹈和民族音樂視為一種文本書寫。那么,是什么驅動這種主體進行書寫呢?我想,是源于“美”的刺激和對“美”的認知。
脫胎于滿族“薩滿”祭祀活動的《腰鈴舞》(圖1)在表演時,在表演者的腰部系一圈筒型的腰鈴,兩手各拿兩片竹制響板。由胳膊上下左右擺動,配合腰部的扭動,帶動戴著腰間的腰鈴發生聲響。我們可以看到,作為《腰鈴舞》配樂的腰鈴是與舞者的身體處在同一的運動節律中。腰鈴可以被看作是獨立舞蹈本身表演環節中的一個獨特的單元,也可將腰鈴視為舞蹈的一部分。因為在表演者扭動腰部作為舞蹈表演的一個環節的同時,腰鈴也隨著腰部扭動所勾畫出的圓形力線而旋轉起來。力線與身體在腰鈴、響板組成的節律中相互作用,塑造了一種舞臺中不斷變化又組構的審美空間。藏族舞蹈《拉姆》中將藏族人民的歌舞與說唱相結合,作為真善美這樣美好品質的宣揚,也是基于民族舞蹈與音樂的互文性。此外,我們在彝族的《銅鼓物》中也能看到這種互文性的存在。在《銅鼓物》的表演中,男女隨著鼓的節拍,且歌且舞,以歌舞的融通來輔助整個舞蹈的傳情達意。由此,民族舞蹈與音樂中的這種互文性并非個例,而是一種普遍的審美意識。

圖1 滿族《腰鈴舞》,2019年。圖片來源: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
因而,舞蹈藝術是基于身體在特定空間中展開,而構建自身敘事的結體、姿態。動作和結構成了舞蹈進行空間文本書寫的基礎語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將舞蹈看成“用手勢說話的藝術”。這里所謂的“手勢”就是指“身體”,即:用身體說話的藝術。身體,作為舞蹈三種語匯得以構型與出場的基底,為舞蹈藝術文本的敘事書寫,提供了得以交流與傳達的場域。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認為,人類“身心的結構,就是按照它存在其中的,這個世界的結構發展出來的,所以身心就會很自然地發現它的某些結構和自然是吻合的……”“心理與生理有著同質的關系……精神根植于身體之內……指導身體朝著某個特點目標前進”。因而,我們對于“美”的感知不是通過對自然加以思考的心靈介入,而是通過一種在現實的實踐中所進行的“操作”。由此而觀之,舞蹈中行進的身體,成為了杜威意義上的“操作”,正是這種“操作”使得的舞蹈得以介入“美本身”的體驗中,并通過身體文本的書寫,將其翻譯為身體的言說。
音樂作為一種審美客體,其不同于舞蹈,它的存在方式是由其基本屬性決定的,即“僅以人感覺所及的程度為限”,音樂本體在性質所屬方面不屬于任何自然、自律的存在,而是一種產生于主客體對象性關系之中,特殊且無法觸及的流動態“感性對象”。這就是說,從感官審美切入,音樂的表現力是具有限制性的,它只能通過人體的聽覺神經,輸送快、慢、強、弱、升、降等音律的物理運動,從而實現對審美主體大腦認知的傳達。而舞蹈與繪畫等具有特定視覺化的標志性表達,是建立起創作者與接受者之間直接、面對面的意識溝通。音樂也是基于人的身體的言說,只不過其是借助于聲音引發的聯想而產生,聲音快、慢、強、弱、升、降等構型了音樂文本的敘事模式,是對“美本身”的詩意存在的描繪。
盡管舞與樂兩者對身體誘發審美的意志的介入方式各異,但二者在這一過程中都取向于使具化的形象浮現于聯想的知覺場中。另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對舞或是樂的體驗,都需要在行進的過程中與主體發生關聯。就此而言,實際是展開的知覺場提供了兩者互文的、彼此嵌合的界域。我們更應該看到,民族舞與樂所共同塑造的這種釋放自然的原真狀態,以及身體的審美強度。
二、形動樂合:民族舞蹈與音樂的納構性
相比之下,舞蹈作為一種直觀的、以視覺為傳達媒介的動態行為載體,可以通過真實、可視,甚至可觸的具象形態來刺激人體的視覺器官。在感官傳遞中同樣具備如音樂的快、慢、強、弱、升、降等物理運動屬性,繼而向大腦神經傳遞信息,以舞蹈運動的自律性,即以人體為舞蹈藝術表達媒介的主體材料,和人對自身肢體運動技能掌握的技術條件,實現對舞蹈具體實踐行為的感官審美。
誠然,舞蹈具備可視性的言說功能,可將審美對象通過物質運動方式以人體線條的運動軌跡勾勒出畫面感,并跟隨特定物理運動節律的浮動具備初始色彩感;音樂也同樣通過調性、和弦、旋律、節奏等原始材料的組合變換渲染出音律的起承轉合。而如果單純的只將審美意識駐足于感官神經,舞蹈的存在則僅是作為普通的媒介載體,在言說過程中通過肢體動作說明運動主體行為無意識的基本運動方式與宣泄軌跡,塑造出初始形態,但卻不能透過該形態清楚準確地解釋與表述行為背后所隱含的具體情感及事件來源的存在。音樂亦是如此,此階段審美只可停留在樂音組合力量與運動和比例方面的變化,即增長、消逝、急行、遲疑,或錯綜復雜或單純進行,可應答字、詞,卻不能連字成句。
朝鮮的《長鼓舞》若只作為表演性的舞蹈,其舞蹈的動勢與動作的表達就稍顯單調,但是長鼓的加入,不僅串聯起了這些東西,而且也將自身置于舞蹈本身的表演中。也就是說,長鼓在《長鼓舞》中既是動作行進的中心,也是對其動作運行節律的把控。置于胸前的長鼓看似限制了表演者動作的展開,而實際上卻在支撐整個舞蹈表演動作的展開。此外,整個舞蹈的動勢也將長鼓作為其核心。所以,當舞者在表演過程中,敲擊長鼓,并非一種音樂的合奏,而是在把控舞蹈動作的行進,并進行協調與串接。所以,我們看到朝鮮的《長鼓舞》是以慢帶動快,是圍繞長鼓作為舞蹈呈現的主線。這種納構性在苗族的《花鼓舞》中也有體現。《花鼓舞》表演時,將牛皮大鼓置于鼓架上,由一人站在直立的鼓旁,以鼓槌擊打鼓腰,繼而配合舞步步法,配以身體的閃、展、騰、挪的跳躍旋轉,且擊且舞,忽快忽慢。顯然,苗族的《花鼓舞》將以鼓為主體,以鼓牽引起了身體與節奏的共鳴。在我國的民族舞蹈中,還有藏族的《熱巴》《弦子舞》、壯族的《扁擔舞》等都是這種納構性的體現。

圖2 朝鮮《長鼓舞》表演,圖片來源: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
基于各民族文化延伸的舞與樂具有強烈的同質性。為舞與樂、聲與形提供相互吸收和重新架構的底層邏輯,在天然的共生性中去發現相互交融的支點,構建穩定的結構,傳遞視覺、聽覺的整體感知。民族舞蹈和音樂的任務并不是嘗試去創造一種新的、理想的文本,而是在實驗一種納構性。對于任何一種藝術形態的研究,我們都不能將其從文化的序列中剝離出來,獨立進行定量分析,而是要將其置于文化套疊的關系域中進行審視。從這一點出發,特定時空下舞蹈和音樂的展開就不僅僅是一種互文性的操作,它們本身具有一種納構性,在地域的流變與交流中,他們在吸收異質與自我構型中不斷豐盈自身的語料庫,鍛造自身特定的符號體系。應該說民族舞蹈作為一種民族音樂的視覺化符號,基于納構性,它象征的便是一種藝術形態所顯現的民族文化廣博與延展。
三、遺形存意:民族舞蹈與音樂的表征性
如何使單純的運動形態具有生命力,也就是說如何實現審美主體對民族舞蹈與音樂的審美層次從“感官”至“情感”的飛躍,這取決于傳達者與接受者內心對于某一特定情感的注入與凝結。通過對照,由感官送達“不確定的語言”建立起想象與情感的橋梁,最終達成“語言”表達敘事抒情的審美共鳴,也是民族舞蹈與音樂之所以能夠稱之為藝術的前提。同時,由于審美主體情感的滲入,使審美客體舞蹈運動的具體形態與軌跡更具有行為性與意識性,而音樂節律則更富有動機性。當民族舞蹈實踐主體自覺或不自覺地開始支配自身肢體進行運動,且足以因該運動對觀者造成視覺刺激、產生審美感受的瞬間,其動作與已形成的視覺形態流必然帶有有意識的民族行為性。它是基于舞者主觀思想民族情感認知積累頃刻爆發的民族意識行為,是內在民族情感剎那間刻意外化的具體形式。于審美者即觀者而言,舞者通過一系列帶有行為性與意識性的形態流在對其造成具體、強烈且刻意的視覺刺激后,足以限定觀者的情感想象空間,繼而引導觀者審美走向,與該氛圍中特定民族情感產生共鳴。民族音樂節律因作曲者某種情感認知而觸發創作內容所富有的動機性原理,皆是民族情感所引發的審美感受,使民族舞蹈與音樂完美地詮釋其民族情感。
民族舞蹈與音樂屬于作用于接受者感覺器官的信號發出者。因為情感本身即是人類所具有的特殊、具體的感覺知覺,投射于舞蹈與音樂,則或是一個體勢、一個樂音所引發的情感知覺,就足以作為對某一感性素質界定的評判標準。2019年的春節聯歡晚會,由中央芭蕾舞團推出的《敦煌·飛天》(圖3)舞蹈,借助現代舞臺的媒體技術,給予了敦煌舞以奇觀性的視覺表達。與早期的《絲路花雨》相比,現代舞臺的虛擬技術將一種虛擬的知覺場域視覺化的方式直觀的表達。也就是說,我們對于敦煌舞的理解中那些通過視覺動作喚起的想象力的欣賞,如今讓位給了視覺的直接刺激。它是直接的,卻又帶著表征的痕跡,僅僅可見,不可觸摸。我們只有在“感性”的催發下,作為知覺的諸器官才能與這種視覺化的表征發生關聯。
另一個例子是彝族的“火把節”的舞蹈表演。彝族的“火把節”是彝族民間生活的一種重要內容,多為模仿動物,或農耕的動作而來。在“火把節”中,表演者以鼓帶動群體的表演者進入鼓點組織起來的序列中,進而構建起一個群體性的舞蹈場景。這種身穿統一服飾,并且隨鼓點展現出的統一動作,以整體性的視覺張力,對觀者造成視看的壓迫或震撼感。

圖3 2019年春晚《敦煌·飛天》舞蹈表演截屏。圖片來源:https://v.qq.com/x/cover/mzc00200147okt1/t00294ow3w0.html
斯圖亞特·霍爾在《表征:文化表征與意指實踐》(2013)一書中提及表征的作用在于將文化中不可見的規范、組織或序列以可見的形式再現出來,亦即提供了一種再現的意向。他指出“表征是在我們的頭腦中通過語言對各種概念意義的生產。它就是諸概念與語言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使我們既能指稱“真實”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確實能夠想象虛構的物、人、事的世界”[5]。也就是說,舞與樂作為客觀存在的一種知覺場,它憑借身體技能將身體的底層結構與“高級”的機能建立緊密聯結,并且建立進入這一知覺場的通道。這種“移動”不是一種身體物理維度的空間變動,而是一種美學意義上的精神返鄉。我們知道,在柏拉圖的洞穴中,具象的影子是一個不能確定的能指,只有其輪廓大致可以作為對某些可能的所指的指向,但這僅僅只是眾多可能中的一個選擇。這里,“表征”與影子所寓意的效用具有相似性。正因為只有“表征”作為中介,也即影子的輪廓,我們才能使用相應的概念在特定的知識界域中認知客體對象,這一對象也才能具備被審美的可能。在此,必須警惕的是,并不是確定的、絕對的,排除一切模棱兩可的認知才是審美需要的,而介于模棱兩可之間的知覺場才是藝術存在的根本。
基于此,藝術家的創作貼合事物的感覺和知覺上的經驗在心中的重現或回憶,強調了感覺的生動性,而且看重它是一個心理事件和感覺奇特的結合。在柏拉圖看來,這種重現或者回憶是需要“迷狂”地介入,只要“迷狂”進入,舞蹈和音樂就能將一種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審美體驗流溢出來。實際上,這里所指的這一心理活動的構建,確切地說,即是審美者對舞蹈與音樂具體作品進行表征意象的探測。
結語
由此可見,少數民族文化中的舞與樂雖然是異質的載體,但其都趨向于一種超越日常生活感官的知覺過程,并促使其再回返到日常生活中,撬動被日常生活遮蔽的主體性。無論是藏族服務于宗教儀式的《拉姆》、滿族用于祭祀的《腰鈴舞》,還是苗族的《花鼓舞》、藏族《弦子舞》、壯族的《扁擔舞》都是舞與樂合一的產物。可是,現代的學科思想對獨立學科的強調,使得我國民族舞蹈中的舞樂合一的整體意識被強行切割成為獨立的學科。在這個意義上,舞與樂實際上就被人為地割裂開來。而我們對于舞與樂三重關系的論述,不僅在于揭示二者之間得以關聯、互動的渠道,而且指出兩者之間借助單純的感官編織的一種人的生存方式,或者更為準確地說,是一種文化的知覺場。互文因為相似的性質,超越了外觀上的異質,為納構提供了可以生發的基礎;納構耦合了異質媒介介入知覺場的不同的特質,成為了同質性的、集中的審美氛圍;表征在前兩者所納構的這個場域中,擔負起了輸出的功能。正因此,我國民族地區實質上是一個為民族舞蹈與音樂提供生成的知覺場。少數民族的舞蹈與音樂存在的三重審美方式正是在逐步遞進中顯現出相輔相成的連接關系,共同構成了少數民族舞蹈與音樂作為藝術形式而存在的客觀依據。在當前構建中國特色學科體系的大背景下,將我國民族舞與樂的三重關系所特有的這種整體意識重新拉回我們的學科體系中,對于我們跳出學科的壁壘限制,實現舞與樂學科的交叉與整合提供了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