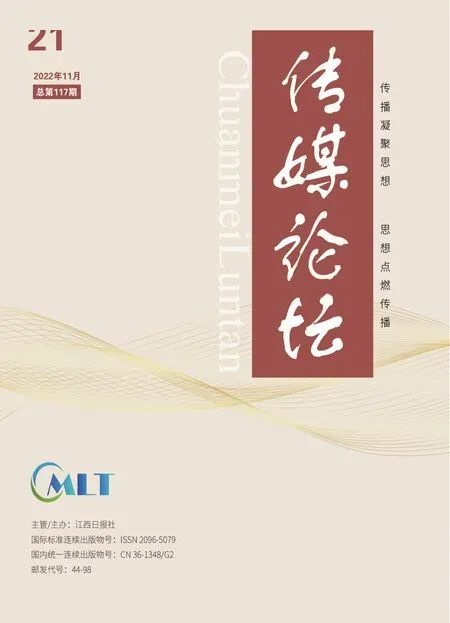符號學視角下的“新疆棉花”
——新聞報道中的國家形象建構
王一凡 王亦高
一、引言
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學者們關注的問題,西方國家對于中國邊疆問題,尤其是對新疆地區的關注和爭論也未曾停歇。近來,涉疆議題又再次成為國際傳播中的焦點。2021年3月份發生了“新疆棉花”事件(中國內地爆發的一場對于海外品牌的抵制運動),這場事件源于2021年3月24日,中國互聯網上熱傳了一則這樣的消息:“瑞典時裝公司H&M曾于2020年9月發表聲明稱‘不與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裝制造工廠合作,也不從該地區采購產品或原材料’,而不少服裝企業也因相似原因發表過聲明,不使用來自新疆的原料或產品。”
“不少品牌拒絕使用新疆棉花”的消息在中方輿論場內引發了軒然大波,明星代言人紛紛與涉事品牌進行解約,中國官方媒體和民間紛紛自發動員力挺“新疆棉花”,并抵制棄用新疆棉花的企業。與此同時,來自西方媒體的質疑聲音也源源不斷。針對這次事件,中國官方主流媒體發布了許多報道,維護中國的國家形象。對比閱讀其面向國內外的報道,會發現“新疆棉花”已經不僅是作為種植業的棉花產品本身,它是此事件中的主體,也在新聞報道中成為一種符號,生產出相應的意義。趙毅衡(2011)指出符號化的過程是賦予感知以意義的過程,意義的生產,就是用符號來表達一個不在場的對象或意義的過程,而新聞文本的呈現本身就是符號意義表達的形式。
而關于新疆地區的報道研究往往涉及意識形態的問題,國際層面關于新疆地區的研究多偏向于政治性研究,受到了西方價值判斷的影響。奧伯爾曼指出中國政府回應國際中有關涉疆問題時常使用一種隱秘的、去政治化的“發展敘事”(Alperman,2020)。而國內學者關于新疆敘事的研究往往選擇分析其民間文化和生活,例如討論地域空間、民風民俗、地方語言等歷史文化資源,并在其中挖掘更多彰顯地域、民族文化特色的符號——特定的建筑、服飾、食物等,有利于西北地區的多民族形成集體記憶。
對于涉疆問題的報道,有學者對其進行了符號學視角的解讀嘗試,莊金玉(2017)將維吾爾語作為新疆地區的一種關鍵符號,分析了維吾爾語地方媒體和其地方生活構建的關系,指出它作為族群文化的黏合劑,促進了當地少數民族的文化認同。同時,官方也會對其關鍵符號進行政治化的使用,將族群成員普通的交往有針對性地賦予政治涵義,體現了文化傳播的工具理性;國內學者鄭亮和夏晴(2021)通過閱讀《中國經濟周刊》和《新疆日報》的報道,認為中國講述的新疆故事整體上是一種基于“現代化”和“神秘化”符號的敘事,新疆在其中成為一種靜態的符號。本文所關注的問題就是從符號學的角度分析“新疆棉花”如何成為一個國際傳播中的符號,它的意指含義是什么?中國主流媒體在面對不同的受眾時?又如何用這種文化符號和敘事方式來建構自己的國家形象?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對中國主流媒體關于新疆棉花的報道進行符號學視角的分析。根據互動和傳播數據,在面向國內受眾端選取的媒體是人民網,在面向國外受眾端選取的媒體是China Daily;而后在人民網的新疆頻道和China Daily的網站內以“新疆棉花”為關鍵詞進行查詢,時間維度限制在“新疆棉花”事件發生一周內,即2021年3月24日至3月31日,在人民網檢索得到12篇關鍵詞為新疆棉花的新聞報道,China Daily英文網則收錄了39篇相關報道。通過對報道的細讀,對比分析其報道中“新疆棉花”的符號含義和建構方式。
二、政治化與去政治化:展示態度的“新疆棉花”
汪暉指出,“去政治化”中的“政治”指的不是國家生活,而是基于特定政治價值和利益關系的政治主體之間的相互運動。本文所說的“去政治化”就是忽略這種政治關系,將政治博弈關系放置在一種非政治考量的關系之中。例如鄭亮和夏晴(2021)指出,新疆區域的敘事往往是在“發展敘事”的框架內進行的,以展現基礎設施等現代化的建設成就為主,而對于新疆區域內的政治主體缺乏關注,即更多地展現抽象的經濟增長、產業收入,而少見“新疆棉農因此享受到的個體權利的保障”,也少見政府主體對于保障邊疆個體勞動者的勞動權、發展權等做出的努力。在面向國內的新疆棉花相關報道中,也出現了這種情況——新聞報道的主題、風格和編排都呈現出“去政治化”的傾向;在面向國外的報道中,則將新疆棉花事件歸類為外交政治事件,更傾向于從政治和外交的官方層面進行回應。下文將從新聞中的符號構造、主題、風格和內容組合、時間偏向和背景選擇進行討論。
(一)新聞中的強編碼:“新疆棉花”的符號建構
新聞文本的呈現就是符號意義表達的形式,借助多種符號以及對符號的操作過程,新聞文本才得以生產出來。趙毅衡(2011)指出,符號化的過程是賦予感知以意義的過程,意義的生產就是用符號來表達一個不在場的對象或意義的過程。在各類新聞報道的分析層面,傳播符號主要是語詞符號和圖片符號。在新疆棉花事件的相關報道中,其核心符號正是“新疆棉花”。
在新聞報道提及新疆棉花時,一并出現的搭配詞往往塑造了人們對于新疆棉花的意指理解,在主流媒體面向國內的報道中,與新疆棉花出現在同一語句中的詞語多為“技術”“智能化”“機械采摘”。有學者通過分析各地網站對于同一新聞事件的報道,認為某種意識形態或持有某一立場的新聞媒體的文本“往往通過使用或拒絕使用某些關鍵詞、常用語、以及事實和判斷的聚合來強化主題”(黃敏,張克旭,2000)。而國內報道中固有修辭和明確的搭配構造了“新疆棉花”和“機械化智能生產”的強編碼。“新疆棉花”在生產層面的所指不僅僅是一種物質上的棉花產品,也代表了機械化、智能化的生產過程。
除了固定的搭配外,報道中還使用了數字修辭加強其編碼效果,例如“新疆農業部門發布的2020年數據顯示,新疆棉花機械采摘率已達69.83%。兵團統計局數據顯示,兵團擁有采棉機2760臺,機采棉面積1180萬畝,棉花機采率達90.9%”。具體明晰的數字細節比一般的陳述更加有力,從而增加了其事實的權威性。這種敘事策略往往也伴隨著另一種文本行為,即大量的名詞化,在面向國內外的報道中都僅凸顯新疆工業的“結果”,而并不出現行動者,例如棉農和商人。報道內文的配圖也是如此——大型棉花生產基地的廣角俯拍,以此凸顯棉花產品的現代化水平。
(二)新聞的主題
在新疆棉花相關報道主題的選擇上,三分之二的國內新聞報道都是以新疆棉花的智能化生產為主題;面向國外受眾的多以表述中國的政治立場為主題。而新聞的主題結構是關于新聞話語的綱要、主旨、要點或者最重要的信息,整個面向國內受眾的宏觀報道結構是“新疆產業與人民發展都十分繁榮”,一個個主題就緊緊圍繞著“新疆棉花是智能化機械化生產”,中心主題的信息則散布于整個文本之中。
在媒體報道研究中,“標出項”是媒體著重選取與凸顯的意義,而“非標出項”則是為媒體次之選取甚至被隱藏的意義。標出項與非標出項常常通過對于中項的爭奪來獲得“正項”的地位。所謂中項,就是意指并非十分明確,對于其他兩項都具有模糊相關性和偏向可能性的表意。中項必須借助標出項才能夠完成自身的表達。從新疆棉花事件發生的過程看,“新疆棉花”除了是一種純粹物質意義上的農產品外,也是一種經濟產品,更是一種政治符號,它是新聞報道中的中項,同時橫跨經濟場域和政治場域。
在主流媒體面向國內的報道中,都突出了新疆棉花的機械化和智能化生產情形,報道中利用刪略、概括和組構等規則的實施,把新疆棉花的符號代指轉向了現代化的工業生產。正如對于“新疆棉花”的符號建構,在主題表達中就把“新疆棉花事件”具體為新疆生產出的棉花,將重點放到棉花的智能化生產環節,聯結“無人機”“機械化”和“新疆棉花”等內容,展示出棉花產業在中國新疆地區繁榮發展的景象。例如《北斗“護航”新疆百萬畝棉花開播》《新疆棉花憑什么是世界頂級?六大理由告訴你!》將主題劃定在了經濟場域內,在主題方面實現了一種政治事件符號的去政治化,從而將涉及政治問題的話題轉構為經濟話題和技術話題。
在面向國外的報道則突出新疆棉花的政治性,主體往往是中國政府,參與抵制新疆棉花的國家和企業則處在“被譴責”的被動體位置上。例如以《外交部:歐盟玩弄“雙重標準”》《中國必須保衛新疆棉花》《中國最高立法委員會闡明對新疆的立場》《中國拒絕接受傳喚大使》等作為標題。除了中國官方作為主體外,報道還會采用其他的主體,如《棉花行業組織(BCI)在新疆沒有發現“強迫勞動”的案例》,利用其他主體的表述和支持行為來證明新疆棉花的合法性。由此將“新疆棉花”事件定性為一場政治外交事件,是西方編造“強迫勞動”的謊言來遏制中國的行為。因此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承擔起了表明中國官方立場的作用,從而將話題轉向宏觀層面的國際政治問題。
(三)新聞的內容組合與風格
任何符號表意行為都是在組合軸與聚合軸中展開的,在新疆棉花的對內報道中,棉花和棉農/商人等行動者是一種縱向的聚合,由縱向的聚合進行報道會產生多種視角,例如棉農的勞動生產生活、棉花經濟的興衰歷史等;而棉花和機械生產則是一種橫向的組合,當文本背后擁有較窄的聚合段時,文本內容則更為單一,風格選取更為狹窄,從而使文本偏向組合軸主導的呈現。在國內新聞報道中關于“棉花”“機械化”“智能化”的組合,傾向于形成單一的敘事視角,從而固定了行為發生和符號構建的空間。
正如雅各布森把聚合軸稱為“選擇軸”(axis of selection),聚合軸的呈現是在報道生產中就有所選擇和考量的,將組合劃定在“新疆棉花”的產品本身上,其實是文本編輯者有意識的呈現。如果放寬聚合軸,將新疆棉農勞動者等主體囊括進新聞報道,就需要提及勞動者和勞動關系,還涉及其他面向的討論,對于受眾的新聞素養和知識背景有所要求;而單一的聚合軸則更簡潔,更能夠喚起受眾簡單直接的情緒,便于引導合眾的情感與行動。聚合是組合的背景,這種聚合從而形成了一種去政治化的呈現組合,將棉農和勞動關系的討論隱匿在棉花產業的背景中,但同時這種單一聚合軸的行為也可能會加深內地居民對于新疆地區的刻板印象。
梵迪克在《作為話語的新聞》中提到,“風格是文本的語境特征”。風格是一篇報道必備的特征,面向國外受眾的報道往往采用外交發言的風格,用簡練的語言表達中國對這次事件的立場,報道內容集中在中國官方的發言上,平鋪直敘地反擊國外的批評,較少引用中國居民的個人發言和態度,例如“中方堅決反對任何旨在抹黑或傳播有關中國及其人民的錯誤信息的行動”“我們拒絕西方的指責,認為這是毫無根據的”“這些都是捏造的”等等。但并沒有通過具體的敘事進行證明,即其報道的背景并沒有放置在新疆區域的環境中進行考量。
面向國內受眾的報道往往會帶有更強烈的號召式新聞風格,利用符號的組合訴諸情感表達。例如標題中常出現的“?”與“!”。在新聞報道的引用中,也多次引用新疆居民本身的表述。人民網中的一篇報道提及“教培中心的結業學員迪麗娜爾·卡哈爾憤怒地說:‘我想對那些造謠者說,你們整天胡說八道,靠詆毀教培女學員的名譽,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你們不感到羞恥嗎?你們的良心不痛嗎?’”。話語分析中認為如果新聞報道中出現了說話人,既能體現出其主體性,又能借助其表述展露新聞報道自身的立場和態度。
(四)新聞的時間偏向與背景選擇
而具體到每一篇報道里的敘述,面向國內和面向國外的報道在命題中也有所不同。趙毅衡指出:“不同的敘述可以體現敘述主體不同的關注方向,這就涉及了符號的時間偏向——過去向度著重記錄,是陳述;現在向度著重的是演示意義懸置,是疑問;未來向度著重規勸,是祈使。”從時間偏向來看,面向國內受眾的報道更強調未來,而對國外則強調過去。命題一般被認為是在陳述事實,但是事實不一定指的是現實的事實或者過去的歷史,也可能是其他替代性的事實,比如未來才會發生的承諾或者對于過去的指控。
不同于國內報道中利用命題去展示中國現在智能化的棉花生產場景,在面向國外受眾的報道中,往往使用過去的時間向度,從較為嚴肅的政治背景進行切入,采用歷史對比的敘事方式加以分析事件的整體背景。例如China Daily的報道中提到:“華春瑩在發布會上說,美國及其盟友的所作所為讓人們想起1900年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在另一篇名為《Sanctions on Xinjiang cotton use opposed(對新疆棉花的制裁表示反對)》的報道文章中,如圖1所示,配圖均為西方國家過去的行為以及中國新疆目前情況的對比,例通過對比美國黑人殖民時期的手工棉花種植(上圖)和現代中國的機械化棉花種植工業(下圖),將話題聚焦在當下中國的棉花生產,表述出中方在棉花生產中并不存在“強制勞動”這一說法。由此形成的新聞話語既堅持了客觀報道的原則,又巧妙地隱含了自己的意識形態。

圖1 對外報道中的配圖①
三、新聞神話的構造:棉花符號的行動性
正如貝克特在《棉花帝國》中分析歐洲棉花產業的興衰和資本主義、全球化變遷的關系一樣,世界上的棉花生產存在著悠久的、殖民的強制勞動歷史,棉花的“政治性”仿佛是與生俱來的。在國際傳播中,西方媒體對于中國新疆棉花的相關報道也是傾向于政治層面,比如指摘中國的邊疆政策、對少數民族的“勞動壓迫”等等,強調的是新疆區域中政治主體的互動關系。中國的對內報道則通過種種方式將新疆棉花塑造為“去政治化”的產品,淡化了新疆棉花事件中本應占據主角地位的政治主體——個體、政府以及新疆區域本身,回歸到純粹的自然種植和產品收獲關系,從而否定了西方的指摘,用這種“去政治化”的敘事解構了西方媒體對于新疆棉花背后的政治性敘事框架。
但正如恩格斯所說,“主張放棄一切政治的報紙也是在從事政治”,在新聞報道中,完全去政治化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即便在國內報道中,將新疆棉花打造為去政治化符號的背后,依舊隱匿著一種政治化背景和意圖,隱匿著國家意識形態以及相關的價值判斷。因此對于國內受眾來講,“新疆棉花”雖然是去政治化的,但它無形中成為一種象征,如同一種愛國的獎章。這種建構方式和神話的建構方式如出一轍——羅蘭·巴爾特從符號學的視角來研究神話,這里的神話指的是一種“敘述的內容”,人們把它看作是對客觀事實的一種合理的、真實的解釋,新聞就成了這種神話的構建者,如圖2所示,一切意指系統都包含一個表達平面(E)和一個內容平面(C),意指作用則相當于兩個平面之間的關系(R)。

圖2 中國主流媒體關于新疆棉花對內報道的神話建構
不同國家的新聞報道也在爭奪著神話的構造權和空間,正如曾慶香所說,“新聞話語的神話性體現在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詮釋權的追求之上”,大多數話語的出現本身就是為了爭奪對于事件的詮釋權。在剔除社會語境、回歸最原始的“新疆棉花”時,詞語代表的能指和所指都是棉花這個產品本身,而國外的報道和質疑則把其所指推向政治,棉花所指的不僅是生產產品。而中國的報道則試圖推翻西方報道中的“政治污蔑”,建構自己的神話。
在國內的新聞報道中,“棉花”在第一層解釋系統中是一種農產品,即一般常識中的“可以用來當作紡織原料的植物的種籽纖維”;第二層則是機械化的、發展良好的新疆棉花產業,意指中國發展前景廣闊而良好的邊疆政策;在第三層神話系統中,“去政治化”的棉花符號融進了隱匿的意識形態中,建構了一種與以往民族情感一脈相承的神話話語,是一種儀式,同時也是一種信念。
對于個人來講,“新疆棉花”的符號背后其實也蘊含著一種個人選擇,它蘊含著一種愛國之情愫和護國之動力。正如奧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中指出“說和敘述、行為以及結果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所有的話語都是可以分為“表述、行動和后果”,事件敘述成為神話后,可以強調主導意識形態,甚至成為一個群體的勛章。如“支持新疆棉花”成為一種愛國者的獎章和證明,這種符號同時也蘊含著行動的期許,在這個表述過程中,通過“角色設定”和“點名召喚”的策略,鼓舞人們行動,比如抵制拒絕使用新疆棉花的品牌轉而支持國產品牌等等,而這種后果本身又在新聞報道中成為一種表述,不斷地提出新的行動號召。
四、結語
凱瑞(James W.Carey)認為“各種有意義的符號就是文化的語言形式”。文化是經由符號建構起來的,它賦予生活中的事物以意義,并成為不同人們共同體的重要標識。符號不僅呈現著世界,也作為介入性的力量建構和形塑著世界,符號同時具有替代性和生產性。
誠如其言,“新疆棉花”作為一種符號,可以在新聞話語中向受眾進行表達,幫助人們形成對新聞事件的認知,并訴諸感情、號召行動、構建或打破神話,從而構建中國的國家形象。而在國際傳播和對話紛繁復雜的時代,回應西方國家對于中國涉疆問題的關切是非常必要的。
研究發現,“新疆棉花”已然成了一個強編碼的符號,新聞報道通過主題的強調、突出機械化生產的細節等敘事方式意指“智能化的新疆棉花生產方式”;而中國媒體對國內外不同的報道中,其敘事傾向和符號表達也有所不同,對內報道中將新疆棉花呈現為一個去政治化的符號,但這種去政治化的符號背后依舊存在著政治背景,構造出一種有關于民族認同的神話話語;而對外的報道則借助歷史對比和官方回應,凸顯“新疆棉花”的政治含義,例如重申中國的外交立場、邊疆立場。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棉花消費國和第二生產國,這讓西方國家往往會對于中國的棉花生產有著“過度的擔憂”。面對著西方媒體報道中的政治指摘,中國在國際傳播中,也可以解構其原有的神話策略,建構新的、有利于自己發聲的神話話語,立足自己的政治根基,通過政治化敘事的方式,在同一層面回應其他國家的關切。毋寧說,要在國際傳播中講好新疆故事,還需要探索更多的路徑:既要在同一層面回應西方國家提出的問題,實現有效的對話和構造負責任的國際形象;也要嘗試講好個體的故事和日常的故事,個體政治化敘事同樣值得大力實踐。
注釋:
①“Sanctions on Xinjiang cotton use opposed”,中國日報海外版,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103/25/WS605c40cda31024ad0 bab198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