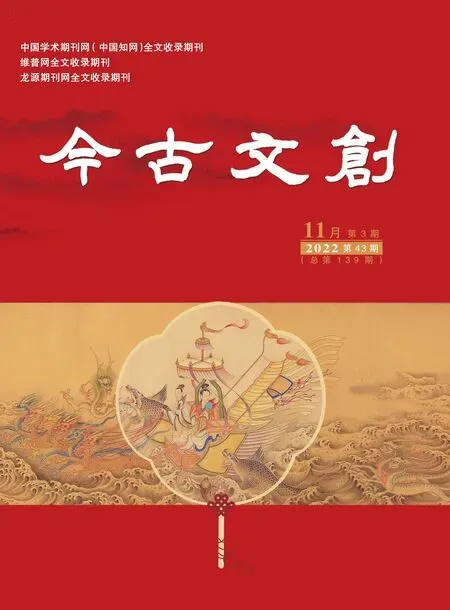傳承與重構(gòu):當(dāng)代動(dòng)漫電影對(duì)神話經(jīng)典的再詮釋
——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為例
◎李孟洋
(四川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學(xué)院 四川 成都 610207)
《哪吒之魔童降世》是于2019年暑期上映的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該片顛覆了傳統(tǒng)的哪吒神話傳說(shuō),講述了陰差陽(yáng)錯(cuò)脫胎轉(zhuǎn)生的魔丸哪吒與背負(fù)龍族希望的敖丙,扭轉(zhuǎn)兩人的命運(yùn),一起對(duì)抗天雷劫,從混世魔王到救世英雄的轉(zhuǎn)變。該片成為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長(zhǎng)久沉寂之后的突破之作,創(chuàng)下了50.13億的票房紀(jì)錄,一躍成為中國(guó)內(nèi)地票房榜的第二。本文將以這部影片為一個(gè)窗口,去尋找能真正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方法,用動(dòng)畫電影這一獨(dú)特藝術(shù)形式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神話在當(dāng)代的傳承與重構(gòu)。
一、蓮花:動(dòng)漫母題的復(fù)歸與嬗變
蓮花擁有高雅秀麗的外表與旺盛的生命力,在人類早期便成為神話傳說(shuō)中重要的象征。在中國(guó)的文化語(yǔ)境中,最早出現(xiàn)在文學(xué)作品中的蓮花只是一個(gè)美好意象的指稱,例如成語(yǔ)步步生蓮出自《南史》,用來(lái)描繪潘妃的步態(tài)輕盈美妙,其淵源可追溯至佛經(jīng)故事中鹿女夫人腳步下蓮花朵朵的傳說(shuō)。①而后隨著佛教文化的傳入和中國(guó)本土道教文明的發(fā)展,蓮花的內(nèi)涵被人們賦予了更加豐富的寓意。蓮花作為一種承載著佛教內(nèi)在抽象意義的宗教象征物,將佛教精神的神圣靈異外在化,具象化,成了佛陀在現(xiàn)世的示現(xiàn),極樂(lè)凈土的信使和佛法大義的重要標(biāo)志。
(一)中國(guó)動(dòng)畫中的蓮花母題
由于中國(guó)動(dòng)畫素來(lái)喜歡取材于古典文化,深受中國(guó)人民喜愛(ài)的蓮花母題自然也成為動(dòng)畫電影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在此選擇兩部象征意義最深重的代表來(lái)進(jìn)行分析,以夸張為特點(diǎn)的動(dòng)畫電影是如何體現(xiàn)蓮花這一神話母題的。
1993年上海美術(shù)電影制片廠出品的《鹿女》取材自敦煌壁畫上的佛經(jīng)故事。故事講述了一個(gè)婆羅門誠(chéng)心禮佛想要升天,卻因教義規(guī)定非有子嗣不能實(shí)現(xiàn),于是日日在佛前祝禱。上蒼憐憫他,便讓山中一母鹿舔舐婆羅門放下的石板,懷孕后生下了鹿女。鹿女天生香氣,步步生蓮。后為烏提王所得,封為了蓮花夫人。夫人得寵后十月懷胎生下了五百玉卵,卻因其他夫人嫉妒將玉卵投入了河中,并將一塊面餅呈給烏提王誣陷此為蓮花夫人所生。烏提王震怒,鹿女既失子,又失君心,悲憤之下回到了深山。玉卵順流而下來(lái)到鄰國(guó),被鄰國(guó)國(guó)君所得,分賞給了五百夫人。第二天所有夫人都生下了一個(gè)男孩。國(guó)王將這五百男孩養(yǎng)大,十六年后率領(lǐng)五百力士攻打?yàn)跆嵬醯膰?guó)家。烏提王節(jié)節(jié)敗退,后來(lái)在婆羅門的指引下找到了鹿女。鹿女以母乳馴服五百力士,使得兩國(guó)化干戈為玉帛。
電影簡(jiǎn)化了故事的劇情,適應(yīng)了中國(guó)本土情況同時(shí)增強(qiáng)了蓮花母題的存在。情節(jié)改為鹿女與炎王相戀后生下了一朵蓮花,蓮花被視作妖孽丟棄,被鄰國(guó)夏王撿到撫養(yǎng),蓮花化為擁有神力的十太子隨后一起攻打炎邦。鹿女在城墻上用母乳喚起母子親情,胸部幻象成一朵蓮花,母子相認(rèn)后鹿女讓十太子報(bào)答夏王的養(yǎng)育之恩,夏王被其大義感動(dòng),夏邦與炎邦從此永世和好。此處的蓮花完整地繼承了佛教典籍中母性生殖的意象,甚至在對(duì)鹿女的刻畫上也有著佛教徒的影子,她的眉間有一點(diǎn)紅痣,在勸說(shuō)夏王時(shí)做雙手合十狀。這部《鹿女》是蓮花產(chǎn)子母題神話的典型改編動(dòng)畫。[1]
同樣作為民間傳說(shuō)改編題材的動(dòng)畫電影《寶蓮燈》1999年由上海美術(shù)電影制片廠出品。影片中沉香母子出場(chǎng)時(shí)就在蓮花池中,最后沉香劈山救母成功后母子團(tuán)聚在滿池蓮花綻放之地,此處的蓮花更像是象征著沉香曾說(shuō)過(guò)的母子二人永遠(yuǎn)在一起的團(tuán)圓幸福。而貫穿全片的寶物寶蓮燈先是幫助了三圣母下凡,而后一閃而過(guò)的法力使得二郎神發(fā)現(xiàn)了沉香母子,最后還與沉香燈神合一打敗了二郎神成功救出了三圣母,這里的蓮花不僅是強(qiáng)大的外化力量的象征,更是沉香一路成長(zhǎng)后強(qiáng)大精神的證明。唯獨(dú)孫悟空成佛后所坐的蓮花座還保留了宗教的象征意義。
(二)哪吒與蓮花母題
哪吒本就是由佛教護(hù)法軍神“那吒”演化而來(lái),但經(jīng)過(guò)中國(guó)本土的消化,成了赫赫有名的道家神仙。哪吒的故事在《封神演義》和《三教搜神大全》中都有記載,其中通過(guò)蓮花轉(zhuǎn)生的情節(jié)相差無(wú)幾。蓮花作為貫穿哪吒這一神話人物成長(zhǎng)經(jīng)歷的重要意象,甚至成了哪吒的一種象征。[2]
1979年版《哪吒鬧海》中,哪吒便是包裹在蓮花中誕生的,自刎后他在太乙真人的幫助下通過(guò)蓮藕重塑身軀,在蓮花中復(fù)活,連穿著都變成了蓮花荷葉裙。蓮花這一母題貫穿了哪吒的生死,初時(shí)象征他純潔無(wú)瑕的心靈,重生后是他法力強(qiáng)大,超凡脫俗的轉(zhuǎn)折點(diǎn)。
而這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得到了更深入全面的描寫。首先是電影主題曲中便將哪吒比作了一朵降落人間的蓮花,這里的蓮花是自由逍遙的精神所在,就如歌詞“快樂(lè)不需要等到明天,下一秒都覺(jué)得遙遠(yuǎn);如果自由可以不被剪斷,好吧永遠(yuǎn)的做個(gè)神仙。”其次是哪吒的人物形象設(shè)計(jì),他所穿的小褂背后是荷葉圖案,身前是蓮花圖案,暗示著哪吒雖然作為魔丸誕生卻心地善良。接著進(jìn)入劇情,元始天尊先用七色寶蓮煉化了混元珠,靈珠魔丸得以誕生,這也是哪吒意識(shí)的初生;哪吒以魔丸之身出生后化為人類的火焰也是蓮花形狀,這是哪吒作為人類生命的開(kāi)始;太乙真人在山河社稷圖中教化哪吒,兩人掉入水中又被蓮花托起,乘著蓮花游覽仙境,這意味著哪吒邁出了接受自我和世界的第一步;而后哪吒用火蓮融化敖丙的冰層,庇護(hù)了陳塘關(guān)的所有百姓也完成了自己對(duì)既定命運(yùn)的反叛,從一個(gè)人人害怕的魔丸成了拯救大家的英雄;最后太乙真人用七色寶蓮保下直面天雷咒的哪吒敖丙二人,靈魂得以在蓮花中修養(yǎng)等待重生。
蓮花這一母題在影片中出現(xiàn)足有六次之多,且每一次都是哪吒得到洗禮,面對(duì)人生的巨大轉(zhuǎn)折點(diǎn)時(shí),它不再只是簡(jiǎn)單的重生的法寶,也不再只是高潔善良品德的暗示,它成了哪吒的象征,它可以是自由逍遙,是接納世界,是反抗命運(yùn),是生命每一次努力的證明。
二、視覺(jué)沖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碰撞
在三維技術(shù)和特效成果飛速進(jìn)步的浪潮下,《哪吒之魔童降世》在1600多動(dòng)畫制作人歷經(jīng)5年的打磨下為觀眾呈現(xiàn)出了1400多個(gè)精致的特效鏡頭,不管是人物,場(chǎng)景,打斗還是靜物刻畫都堪稱一場(chǎng)視覺(jué)上的饕餮盛宴。
許多中國(guó)經(jīng)典動(dòng)畫都借鑒了傳統(tǒng)繪畫技法。中國(guó)傳統(tǒng)繪畫寫意畫和工筆畫。工筆畫強(qiáng)調(diào)線條細(xì)膩,色彩生動(dòng),細(xì)節(jié)細(xì)膩,注重裝飾效果。寫意畫通常應(yīng)用于水墨動(dòng)畫,強(qiáng)調(diào)簡(jiǎn)單的形象、隨意的筆觸和畫家的主觀情感。例如,動(dòng)畫電影《大鬧天宮》的景觀是一幅典型的工筆畫,其中流暢的水墨線條勾勒出樹(shù)木、山、水的輪廓和紋理,細(xì)節(jié)通過(guò)非常柔和、漸變的色彩得到增強(qiáng),帶來(lái)了強(qiáng)烈的裝飾效果。每一幀,無(wú)論是波濤洶涌的大海中的宮殿,還是云彩環(huán)繞的天空中的建筑,都是一幅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裝飾畫。傳統(tǒng)的中國(guó)畫采用的是散點(diǎn)透視,通過(guò)設(shè)置多個(gè)觀察點(diǎn),把眼睛從固定的位置上解放出來(lái),就像觀察者在移動(dòng)一樣。這一視角給中國(guó)動(dòng)畫帶來(lái)了獨(dú)特的景觀表現(xiàn)效果;同時(shí),它也產(chǎn)生了一種枯燥的鏡頭語(yǔ)言:緩慢的水平和垂直的鏡頭運(yùn)動(dòng)是中國(guó)經(jīng)典動(dòng)畫中最常見(jiàn)的方法,觀眾仿佛在閱讀一幅靜止的長(zhǎng)卷軸畫。[3]
《哪吒之魔童降世》熟練運(yùn)用現(xiàn)代制圖軟件,不再局限于中國(guó)畫風(fēng)格。在中國(guó)畫中,形式是用線條來(lái)定義的,涉及光和影的細(xì)節(jié)很容易被忽略。挪用在電影中就體現(xiàn)在描述面部表情或表達(dá)細(xì)節(jié)方面不突出,特寫鏡頭的使用也不多。但這部電影中完美地還原了光線和陰影所創(chuàng)造的空間關(guān)系,全景運(yùn)鏡和特寫鏡頭切換自如,每一個(gè)特寫的人物畫面都被打磨得十分精妙。例如申公豹?jiǎng)裾f(shuō)敖丙水淹陳塘關(guān)時(shí),敖丙從眉眼到唇角都充滿了掙扎。
除此之外,《哪吒之魔童降世》還巧妙地利用了現(xiàn)代元素和傳統(tǒng)背景的刻意碰撞,營(yíng)造詼諧荒誕的氛圍,精準(zhǔn)集中觀眾的笑點(diǎn)。
太乙真人奉元始天尊之命安排靈珠轉(zhuǎn)世,在打開(kāi)七色寶蓮的時(shí)候浮現(xiàn)出了小篆字體的八卦二十四山,并且需要密碼解密,醉酒的太乙真人忘記了密碼,最后還是靠指紋解鎖打開(kāi)了寶蓮。這里的場(chǎng)景明顯是在聯(lián)系實(shí)際生活中手機(jī)解鎖的方法,增添喜劇效果的同時(shí)讓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殷夫人因除妖不能陪哪吒踢毽子時(shí),對(duì)著哪吒用手臂比了一個(gè)愛(ài)心,這也是現(xiàn)代人愛(ài)意的表達(dá)方式。哪吒逃出府中在陳塘關(guān)與百姓捉迷藏時(shí),有借用打地鼠的游戲元素;后來(lái)與敖丙等人被冰封在一起于山河社稷圖中,其移動(dòng)方式化用了這一代年輕人都熟悉的三維彈球游戲。太乙真人在山河社稷圖中幫助哪吒修煉的時(shí)候,通過(guò)轉(zhuǎn)動(dòng)坐騎的鼻子來(lái)回放過(guò)去的場(chǎng)景,也類似于現(xiàn)代生活中的磁帶的使用方法。
三、主題突破:雙線結(jié)構(gòu)下的成長(zhǎng)主題
中國(guó)經(jīng)典動(dòng)畫的觀眾通常被賦予一個(gè)無(wú)所不知的空間視角,這意味著觀眾在某一時(shí)刻比電影人物擁有更多的空間優(yōu)勢(shì),收集到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中國(guó)經(jīng)典動(dòng)畫的敘事在時(shí)間上并不是無(wú)所不知的,它在講述一個(gè)故事時(shí)嚴(yán)格遵循線性和時(shí)間順序。中國(guó)經(jīng)典動(dòng)畫的敘事具有高度的客觀性和被動(dòng)性,側(cè)重于對(duì)外在世界的描寫和嚴(yán)格的時(shí)間順序觀察行為,而不會(huì)隨意地傳達(dá)人物的心理狀態(tài)。《哪吒鬧海》便是線性故事結(jié)構(gòu),從哪吒降生到哪吒殺三太子再到哪吒自刎轉(zhuǎn)生后鬧龍宮,謹(jǐn)慎地按照時(shí)間順序講完了整個(gè)故事。《哪吒之魔童降世》則剛好相反,觀眾跟隨哪吒的主視角展開(kāi)故事,到最后才發(fā)現(xiàn)李靖早在哪吒降生之時(shí)便準(zhǔn)備好換命符替他抵擋天雷劫。而影片中沒(méi)有通過(guò)刻意的心理獨(dú)白來(lái)突出性格,而是選擇利用豐富的表情眼神和肢體動(dòng)作來(lái)代替補(bǔ)足。
哪吒的故事內(nèi)核是悲劇性的。哪吒是一個(gè)少見(jiàn)的在中國(guó)神話經(jīng)典中被正面塑造的違背父權(quán)的“逆子”,是一個(gè)抽身于封建綱常之下的心靈遺骨。他剔骨還父,割肉還母后經(jīng)由太乙真人的蓮花轉(zhuǎn)生,被天庭招安,卻又被宗教的枷鎖所束縛。哪吒那兜兜轉(zhuǎn)轉(zhuǎn)又被反復(fù)切割的命運(yùn)才是古典悲劇里所刻畫的沉重宿命內(nèi)核。《哪吒鬧海》等傳統(tǒng)影片的重點(diǎn)渲染都是其被閹割魂靈的悲劇性所在,重點(diǎn)刻畫敘述的情節(jié)是哪吒自刎時(shí)候的悲憤。《哪吒之魔童降世》重新詮釋了傳統(tǒng)的哪吒神話故事,將其悲劇性的內(nèi)核轉(zhuǎn)化為對(duì)自身命運(yùn)的突破與成長(zhǎng)。
影片的另外一大亮點(diǎn)在于其精彩的雙線敘事策略。本片故事的主角事實(shí)上有兩位—— “靈珠”敖丙和“魔丸”哪吒。在傳統(tǒng)的故事敘述中,敖丙是被哪吒抽筋殺死的,兩人是死敵;而電影表面上是更加激化了這一矛盾,從命格上看,兩人從生下來(lái)就注定了是善與惡的兩級(jí)對(duì)立,甚至人妖殊途;從人物性格上看,孩童模樣的哪吒性格似火桀驁難馴,少年樣貌的敖丙性格似水沉穩(wěn)乖巧;從關(guān)系上看,敖丙還是“盜”走哪吒原本靈珠命格的申公豹之徒,哪吒不死敖丙身上肩負(fù)的龍族期望都將毀于一旦。故事從哪吒和敖丙的視角切入,給我們呈現(xiàn)出完全分化對(duì)立的矛盾兩級(jí),但就是這樣你死我活,連配色都是水火不容的兩位主角在相遇之后竟然成了彼此唯一的朋友。由此我們才看到,這兩人不僅僅是完全不同,他們的關(guān)系就像是靈珠與魔丸,千靈同源,混元一體。作為魔丸的哪吒也是個(gè)心底里想要為民除妖的小英雄,作為靈珠的敖丙也會(huì)為了龍族私心想要活埋陳塘關(guān);哪吒看似是個(gè)孩童,卻一夜之間成長(zhǎng)為敢于扼住命運(yùn)咽喉的勇者,敖丙看似是個(gè)少年,內(nèi)心里卻和哪吒一樣渴望友情和關(guān)愛(ài)。兩人的故事線和命運(yùn)線都死死糾纏在一起,看似天壤之別,實(shí)則殊途同歸。
這樣的雙線敘事揭露出了兩人的千種面貌,塑造出了兩個(gè)豐滿的有血有肉的魂靈,同時(shí)還隱喻著一種哲理性的思考。哪吒與敖丙從一開(kāi)始就不是傳統(tǒng)的正派與反派,他們的性格是真實(shí)立體的,黑白不是絕對(duì)的界限,人性也沒(méi)有絕對(duì)的好壞。就如同太極一樣的混元珠,陰陽(yáng)兩極才是組成世界的根基。
四、結(jié)語(yǔ)
中國(guó)的神話經(jīng)典流傳至今仍然深受大眾喜愛(ài)的就是因?yàn)槠鋬?nèi)涵的豐富性和包容性足以適應(yīng)任何一個(gè)時(shí)代的價(jià)值趨向和審美觀念。而動(dòng)畫作為一種集美術(shù)、音樂(lè)、媒體、攝影等多種門類為一體的復(fù)雜藝術(shù)形式對(duì)神話故事的再詮釋是業(yè)界人士和學(xué)屆人士一直所關(guān)心探討的問(wèn)題。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成功經(jīng)驗(yàn)提醒了所有相關(guān)的從業(yè)人員,中國(guó)動(dòng)畫不是講不好故事,傳統(tǒng)神話的改編不是一定就落于窠臼。本文從神話母題的繼承、動(dòng)畫形象的改編、敘事策略的突破和動(dòng)畫品牌的宣傳上試圖全面系統(tǒng)地對(duì)動(dòng)畫電影的再詮釋進(jìn)行探討,將小說(shuō)和電影的文本進(jìn)行比較細(xì)讀,重點(diǎn)闡述了神話經(jīng)典在動(dòng)畫電影的重構(gòu)下是如何完成身份自洽的。其研究意義不僅在于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為跳板,重新振興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更是文化自信的體現(xiàn),是在為今后的文化傳承探索與嘗試新的道路。
傳統(tǒng)神話的IP先天擁有較好的受眾基礎(chǔ),是易于上手的電影素材,可是在當(dāng)代文化和審美中面臨著其獨(dú)特的生存窘境。當(dāng)代的受眾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神話的改編擁有十分敏感纖細(xì)的神經(jīng),歷年來(lái)相同的題材也拍出了不同的花樣,受眾一邊期待著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能夠向日本學(xué)習(xí)其天馬行空的想象力,以西游記為例,日本大熱的動(dòng)漫《龍珠》和《最游記》都是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在創(chuàng)作;但同時(shí)受眾又擔(dān)心故事的改編過(guò)于商業(yè)化,失去了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在重構(gòu)的過(guò)程中出現(xiàn)類似《哪吒大戰(zhàn)變形金剛》的作品。改變不是亂編,戲說(shuō)不是胡說(shuō),當(dāng)代話語(yǔ)和審美與傳統(tǒng)神話的融合還需要很長(zhǎng)的時(shí)間來(lái)適應(yīng),就算是如此成功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也難免被人苛責(zé)過(guò)于炫技,忍受不了哪吒形象的丑化。想要為故事內(nèi)容的創(chuàng)新叫好,又想要為消費(fèi)市場(chǎng)叫座,其中的尺度平衡還需要更多的作品去探索研究。
追根究底是由于當(dāng)代人的獨(dú)特的審美價(jià)值觀念,對(duì)宏大敘事的渴望與恐懼同時(shí)充斥在腦海中,我們同時(shí)患有“宏大敘事尷尬癥”和“宏大敘事稀缺癥”。這體現(xiàn)在類似的英雄故事總是格外容易感動(dòng)我們,但同時(shí)如果是一個(gè)單純的偉光正的英雄人物,其過(guò)高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會(huì)使人們感到不適。想要用當(dāng)代話語(yǔ)講好中國(guó)傳統(tǒng)神話,就要進(jìn)一步深挖人性的復(fù)雜多面,只有真實(shí)的文本才能觸動(dòng)人心。想要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型發(fā)展,就不要拘泥于傳統(tǒng)動(dòng)畫人的技法,古典美不是我們的唯一選擇。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成功讓人們真正重拾了對(duì)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的信心,希望有朝一日我們不再?gòu)?qiáng)調(diào)國(guó)漫崛起的口號(hào),而是真正看到工業(yè)體系的差距在縮小,優(yōu)秀作品源源不斷地產(chǎn)出,中國(guó)動(dòng)畫人再次去沖擊更高的高峰。
注釋:
①參見(jiàn)高列過(guò):《“步步生蓮花”源流考辨》,《古漢語(yǔ)研究》2006年第4期,第82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