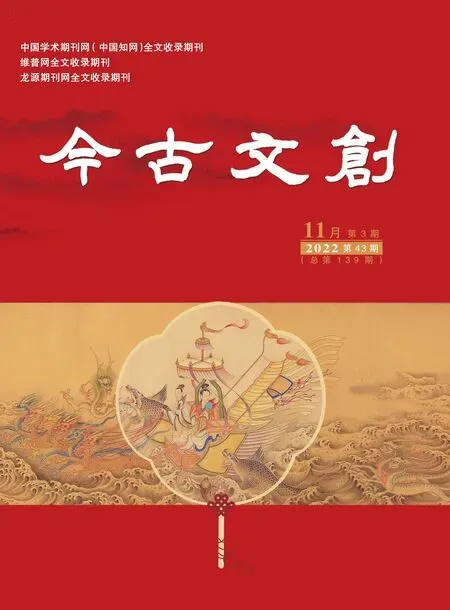列斐伏爾空間理論下《毀滅》中索菲和薩莉瑪的性別身份重建研究
◎蘇敬敬
(西安外國語大學英文學院 陜西 西安 710128)
《毀滅》是非裔劇作家林恩·諾塔奇最著名的戲劇之一,講述了在剛果內戰期間遭受殘酷對待的婦女在納迪媽媽的酒吧/妓院試圖重建生活的故事。列斐伏爾在其巨著《空間的生產》中提出了一個將物理、心理和社會聯系在一起的統一的空間理論。為了進一步論證他的空間學說,他引入了第二個“三元辯證法”,即空間同時是一種空間實踐(一種外化的物質環境)、一種空間表征(一種用于指導實踐的概念模型)和一種表征空間(用戶與環境的生活社會關系)。《毀滅》中的兩位女主角索菲和薩莉瑪在不同的空間類型中經歷了性別身份的流變。從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角度探討《毀滅》中非裔女性的性別身份建構,不僅能拓展既有的研究視角,還能更多地喚起大家對當代非洲女性生存困境和身份問題的關注。
一、物理空間中的女性性別身份喪失
列斐伏爾將空間劃分為三種類型:物理空間、心理空間和社會空間。正如他所說,“我們關注的領域,首先是物理性質,即宇宙;其次,心理的,包括邏輯的和形式的抽象;第三,社會的”(Lefebvre 11)。物理空間是可感知的自然的空間。此外,身份問題普遍存在于少數族裔群體中,而性別身份問題與一個人的身體息息相關。性別一詞在《性別考古學》中被定義為“個人的自我認同和他人基于文化感知的性別差異對特定性別類別的認同”(Díaz-Andreu 14),而性別身份則指基于性別的自我認同。卡門·門德斯·加西亞認為,身體是“保持”我們身份的東西(Garcia 134),不受歡迎的身體侵入是對身份的侵犯。同理,身體的損傷會導致身份問題。戲劇中的索菲和薩莉瑪都是武裝沖突的直接受害者。在受到非人虐待后,他們在物理空間中喪失了性別身份認同。
(一)家庭和社區的驅逐
在殘酷的內戰中,女性的身體被用作戰爭中的武器。正如加西亞指出的那樣,對女性的侵犯“不僅是身體上的侵犯,而且是對……身份的侵犯”(Nottage 134)。《毀滅》中的女性受到雙重傷害,她們受到侵犯被迫懷孕或無法生育,還必須忍受來自家庭和社區男性成員的羞辱。索菲和薩莉瑪作為戰爭的受害者,無法掌控自己的身體,她們的身份也隨之受到威脅。她們被家庭和社區驅逐,在物理空間中喪失了性別身份認同。
正如前文所說,物理空間可以指代一個外化的物質環境。在文學文本中,它可以被視為故事發生的地方或地點。在《毀滅》中,村莊和酒吧/妓院則是物理空間的代表。家庭在個人身份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曾經是一名大學生的索菲因為被民兵毀了生殖器而被家人驅逐。在開場,她的叔叔克里斯蒂安在懇求納迪媽媽接受索菲時曾說道:“村子里不容許一個被毀了的女孩繼續待下去,這對家庭來說是恥辱和羞愧。”(Nottage 26)此外,農婦薩莉瑪的處境也和索菲相似。她親眼看見叛軍殺害自己的孩子,自己也受到毆打和虐待。在被囚禁的五個月里,她過著奴隸般的生活。在她終于從叛軍的魔爪中成功出逃并回到自己的村子時,她受到了村民甚至丈夫的強烈排斥。被士兵傷害后的索菲和薩莉瑪都被家庭和社區拋棄,因而不得不到酒吧/妓院尋求庇護。在此過程中,她們無處可去,沒有歸屬感,徘徊在短暫而不安全的空間中。在這種情況下,她們經歷了身份危機,在物理空間中失去了性別身份認同。
(二)酒吧/妓院的壓迫
在列斐伏爾看來,所有的“主體”都處于一個空間中,在此空間中,他們要么認識自己,要么迷失自己(Lefebvre 35)。納迪媽媽的酒吧/妓院是一個二元空間,它既保護同時又剝削被欺侮的婦女。它充當著像索菲那樣的失去生育能力和像薩莉瑪那樣的因被糟蹋而遭遺棄的女人的避難所,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女孩們在這里被當成商品出售,淪為男人的玩物。為了在武裝沖突中生存,索菲和薩莉瑪輾轉到納迪媽媽的酒吧謀生,但她們在這里仍然找不到歸屬感,相反,她不得不忍受酒吧中男性和其他女性的雙重壓迫。
其中一重明顯的壓迫來自男性。由于職業原因,索菲和薩莉瑪不得不取悅男人,所以會不可避免地遭受他們的壓迫。索菲成為以政府士兵領袖奧斯姆本加為代表的軍事人員的欺負對象。薩莉瑪被迫為其部落的敵人提供服務甚至還意外懷上了“怪物的孩子”(Nottage 77)。此外,酒吧里另外兩名女性即納迪媽媽和約瑟芬也在剝削和欺壓著索菲和薩莉瑪。納迪媽媽是一位迷人的四十歲女性,也是一個精明的剝削者。她經營著酒吧/妓院,斡旋于政府軍和叛軍之間,從戰爭中獲利。縱觀全劇,她在道德上模棱兩可,具有復雜的性格特征:既富有同情心又殘忍。一方面,她為索菲和薩莉瑪提供庇護;另一方面,她又不遺余力地榨取她們的價值。她充分利用索菲的舞蹈、唱歌和計算天分,并且強迫薩莉瑪接待客人,以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第二位女性壓迫者是曾經是酋長女兒的約瑟芬。她看不起索菲,因為她并不“完整”。同時,她對薩莉瑪的懷舊情緒感到極不耐煩,經常與其發生口角沖突。在這種情況下,索菲和薩利瑪遭受了性別身份認同的喪失。
二、社會空間中的女性性別身份尋求
根據列斐伏爾的說法,“社會空間包含各種各樣的對象……因此,這些‘對象’不僅是事物,而且是關系”(Lefebvre 77)。當人們在社會中與他人互動和交流時,社會空間就建立起來了。《毀滅》中具有代表性的社交空間是酒吧內部和酒吧后面的生活區。盡管索菲和薩利瑪起初為她們的身份危機而煩惱,但她們仍然渴望一個能夠賦予她們家的屬性的空間:安全、滿足、隱私和歸屬感。而酒吧的生活區則作為她們尋求自己性別認同的臨時避難所。在她們尋找性別身份認同的過程中,自我治愈和姐妹情誼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追求自我治愈
“毀滅”一詞指的是對一個女人的生殖器和子宮的摧毀。索菲被“毀滅”后走路只能坡行,她受到的創傷既有身體上的,也有心理上的。不過她仍沒放棄對性別身份的追求,而這主要體現在她對身心的自我療愈上。一方面,她意圖修復殘缺的身體,努力攢錢做手術,期望成為一個“完整”的女人。另一方面,唱歌可以撫慰索菲的情緒,減輕她的痛苦。諾塔奇用了大量筆墨描寫了索菲唱歌時的情景,有些歌詞反復出現:“你來這里為了忘記,你說趕走所有的遺憾,像結束一樣跳舞,戰爭的結束。” (Nottage 31,35,40,99)在戰亂期間,這些歌詞準確地傳達出人們想要結束戰爭的強烈愿望。薩莉瑪曾評價她的歌聲:“我看著你唱歌,你看起來幾乎像一只太陽鳥一樣開心,如果你伸手觸摸它就會飛走。” (Nottage 42)作為她的密友,薩莉瑪能感受到索菲從歌聲中獲得的喜悅。雖然索菲否認了這一說法,但她承認,當她唱歌的時候,她在祈禱疼痛會消失。戰爭和男人所造成的創傷永遠不會消失,但索菲通過自己的方式來治愈身體和心理的創傷。
與索菲不同,薩莉瑪尋求性別身份認同之旅始于她的懷舊,而這種懷舊則以回憶和敘述為主要表現形式。懷舊可以通過“重新編織生命歷史中斷裂的線索”來幫助維持或恢復自我認同感(Hertz 215)。它是發展和維持個人身份的一種方式。在《毀滅》中,薩莉瑪經常回想起她被士兵帶走折磨的經歷。她清楚地記得,當她采摘自家地里的西紅柿時,四個邪惡的士兵襲擊了她,殺死了她的孩子,并將她帶到了灌木叢中。五個月的非人待遇像噩夢一樣一直纏繞著她。更糟糕的是,當她逃出森林回家后,她的丈夫和親人都對她嗤之以鼻,將她趕出家門。除了回憶外,她與人分享自己的創傷記憶已經超越了表達的目的,帶有自我療愈的效果。這些都有助于薩莉瑪更加清晰理性地認識到自己的性別身份。她逐漸開始意識到她是誰以及接下來應該做什么。
(二)發展姐妹情誼
除了自我治愈,索菲和薩莉瑪在尋求性別身份的過程中,試圖在彼此身上找到慰藉,發展姐妹情誼。社會空間不僅限于景觀,還涉及人際關系。在社會空間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影響著自我認同的形成。索菲和薩莉瑪之間的友誼有助于她們對性別身份的認知。
第一幕第一場伊始,她們就彼此扶持。當他們被克里斯蒂安帶到酒吧時,她們“手牽手”,而薩麗瑪“粘著索菲”。在接下來的事件中,她們的姐妹情誼得到進一步發展。索菲會給薩莉瑪涂指甲油,耐心地傾聽她的回憶,給予她建議,并在她與納迪媽媽和約瑟芬的沖突中充當調解人。同樣,基于相似的悲慘經歷和創傷記憶,薩莉瑪與索菲產生了共鳴,為她保守后者為攢錢做手術而偷藏錢的秘密。正是由于她們的相互支持和關懷,她們才得以在納迪媽媽的酒吧里找到歸屬感。
三、心理空間中的女性性別身份重構
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列斐伏爾將空間分為三種類型:物理空間、心理空間和社會空間。在他看來,“兩種空間中的每一種都涉及、支撐和預設另一種”(Lefebvre 17)。具體來說,心理空間也涉及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心理空間是人物意識在空間實踐中的表現。心理空間的敘事能夠真實反映人物的生活狀態和精神世界。在《毀滅》中,索菲和薩莉瑪都在心理空間中審視自己,通過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對父權社會的反抗,重新找回真實的性別身份。
(一)女性意識覺醒
在劇中,索菲通過打破納迪媽媽的規則來實現自我意識的覺醒。心理空間是由紀律和規則構成的概念化空間。借用張子凱的話說,它可以“被剝離、設想、構建并作為壓制和剝削的工具”(Zhang 12)。在這個空間里,強者可以對弱者施加影響。納迪媽媽“能夠以她自己的方式定義她的空間”(Garcia 132)。她用自己的規則構建了一個心理空間,比如“如果情況不錯,那么每個人都分一點,如果情況不好,那么納迪媽媽先吃”(Nottage 28)。在這個空間里,她處于絕對的領導地位,女孩們必須無條件服從她。殊不知,在此心理空間中,索菲已經開始通過發展自我意識來重建自己的性別身份。她從她那控制欲極強的老板那里挪用了一些錢以期支付修復手術。在這里,這種私藏的行為與她的道德無關,而是表明了她反抗納迪媽媽的規則和重建自己生活的決心。
反觀薩莉瑪,她的女性意識的覺醒表現在她對前來尋她的丈夫的拒絕上。薩莉瑪因被士兵摧殘而遭丈夫拋棄,飽受過去的夢魘之苦,但其內心深處卻一直渴望家庭的溫暖。可當她的丈夫福瓊來尋她時,薩莉瑪意識到他不會從心底里接受她,更不用說此時她已經懷上了另一個男人的孩子。更重要的是,她決定永遠不會原諒他。福瓊的英文名是“Fortune”,寓意“好運”,但諷刺的是,薩莉瑪的丈夫“把她扔在一邊等死”,給她帶來了厄運和痛苦。她對福瓊的拒絕意味著她實現了女性意識的覺醒,并試圖重構自己的性別身份。
(二)反抗父權社會
女性意識覺醒后,她們在同樣可以由父權思想構成的心理空間中,以自己的方式重構了自己的性別身份。在指揮官奧斯姆本加的糾纏下,索菲奮力掙扎,還敢往他的腳上吐口水。后者是一名有權勢的軍官,隨時可以用他的槍和手下摧毀整個酒吧以及里面的人,但索菲卻不再害怕父權制的權威,用此舉來宣布她的新身份。她曾喊出“我死了”,這句話不僅顯示了她因男人的折磨而瀕于崩潰,同時也表明了她要擺脫悲慘過去的意志。她找到了新的自我,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具有反叛精神的女人。
相比之下,薩莉瑪的抵抗更為激進。她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以擺脫男性的壓迫。在戲劇的高潮部分,由于福瓊的舉報,奧斯姆本加帶領政府士兵在酒吧里搜查叛軍領袖。酒吧里的女人都驚慌失措,生命受到了威脅。這時,薩莉瑪挺身而出,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解除了危機。臨終前,她在福瓊和所有的士兵面前宣稱“你們不會再在我的身體上戰斗了”,并且“得意地微笑”。她以自殺這一極端的方式反抗傳統和父權統治。總的來說,索菲和薩莉瑪在心理空間中重新構建了新的自我,展現了她們不愿被男性操控的叛逆精神。
四、結語
林恩·諾塔奇在戲劇《毀滅》中對黑人女性的苦難和身份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激發了人們對黑人女性的同情,同時也引起了人們對當代非洲人生活的思考。本文借助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學說,探討了劇中兩位主要女性人物索菲和薩莉瑪的性別身份。她們都在物理空間中喪失了性別身份,在社會空間中尋求構建性別身份,以及在心理空間中完成了性別身份的重建。在全球化的今天,關注非裔女性的生存困境和身份問題對處理族裔以及性別問題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