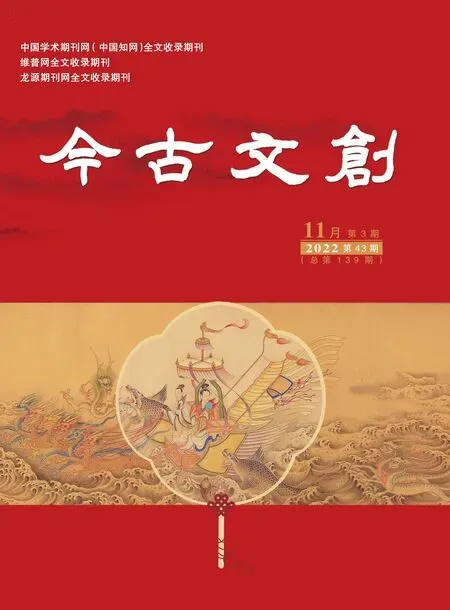中國近現代史料在論文中的運用
——以張之洞相關史料為例
◎趙曉彤
(渤海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遼寧 錦州 121000)
一、近現代史料的定義與分類
史料是指人們編纂歷史和研究歷史所采用的資料,是研究歷史問題的前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朱英在對行會史研究進行展望時曾說:“歷史研究最基本的前提即是史料的搜集,可以說,不同歷史時期取得的行會史研究成果,都與當時相關史料的發掘編纂有著密切的關系。”[1]可見,史料挖掘和整理持續影響近代史相關問題研究工作的開展。近年來,隨著我國文化事業的繁榮,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邁入了新時期,近代史史料學也隨之發展。學界對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更加重視。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先生在《國家清史文獻叢刊》總序中明確指出:“編史要務,首在采集史料,廣收確證,以為依據。”
近代以來,隨著傳播事業在中國興起,史料的內容通過全新的載體呈現在大眾視野里,如近代報刊、錄音、影像等,總量也遠超古代。面對浩如煙海的史料,常令人難理頭緒。如何對史料進行整理和分類成為歷史研究的重要任務。學界一般根據資料的表現形式將史料分為實物史料、文獻史料和口述史料三大類。許多學者也根據不同的標準進行過史料分類。榮孟源在《史料分類》一文中以史料性質為標準將史料分為“原始史料”“文藝史料”“撰述史料”和“傳抄史料”。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將史料分為“直接史料”和“間接史料”。除此之外,還可以按照史料的內容、性質、版本等標準進行分類,史料的類別隨標準的變化而變化,體現出史學工作者不同的治史思想。由于近現代史料的豐富性,這也使一些傳統的分類方式有時難以完全發揮效用。嚴昌洪先生認為,“有些史料兼有幾種情況,放到哪一類都勉強可以,如電稿報、書信,有些是從某人的檔案中取出來的,歸入私人檔案亦可。有許多奏稿、電稿、公牘、書信、日記,又收入了文集。”通過對這一問題的思考,總結前人的分類方法,嚴昌洪先生提出了自己近代史史料分類的新方法,將近代史史料分為十類:即檔案、奏議政書、書札和日記、傳記、結集、志書和典制、報刊、史實記載和筆記野史、口碑和文物、叢書和史料選集。[2]這種分類方法既可以兼顧了近現代出現的全新的史料類型,如電函、報刊類,又可以將史料進行更準確的歸類,避免分類重復所帶來的問題。
二、近現代史料的運用——以張之洞為例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中國近代思想家、軍事家、教育家、實業家。早年為清流派首領,后成為洋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被稱為“晚清中興四大名臣”。張之洞一生閱歷豐富,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東南互保等一系列歷史事件穿插其一生,他見證了近代社會萬象的變遷,在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對張之洞相關史料進行整理,對于晚清民初時期歷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本文嘗試運用嚴昌洪先生的史料分類法,對張之洞的史料進行整理歸納,以此為例,來探究其在論文寫作實踐中的運用。
(一)檔案類史料
檔案就是具有查考使用價值,經過分類立卷歸檔集中保存的文件材料。“檔案”一詞起源于清代,但實際的檔案類文獻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檔案類史料屬于第一手史料,可信度較高,為研究歷史提供重要的參考價值。以編撰者的性質來分類,分為官方檔案、私人檔案、團體檔案。近代史的檔案最主要的是編年體長編《圣訓》《實錄》和私家編撰的《東華錄》。張之洞作為晚清重臣,歷任道光至宣統五朝。有關他的官方檔案匯編可以參閱宣宗、文宗、穆宗三朝的《清圣訓》,道光、咸豐、同治和光緒朝四朝編修的《清實錄》《宣統政紀》及《光緒朝光華錄》。張之洞在外交上頗有建樹,清代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的外交史料《籌辦夷務始末》內容翔實豐富,對研究張之洞的外交思想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道光朝至宣統朝的《上諭檔》共九十一冊,以自上而下的視角反映清代社會原貌,收錄內容廣泛,都有對這位晚清名臣的相關記載。除此之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的《庚子事變清宮檔案匯編》,《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匯編》《清代咸豐朝巴縣衙門檔案》,也均涉及大量關于張之洞的內容,成為后人研究張之洞的生平的重要參考。
(二)奏議政書類史料
奏議類史料包括奏稿、政書、公牘等。有關張之洞的公奏、公電、公牘、公函大都收錄在許同莘所編纂的《張文襄公四稿》中。張之洞一生經歷五朝,奏議政書類史料還可以參見五朝的《朱批奏折》《宮中檔奏折》等。從這些奏議政書中,張之洞的整個政治生涯也可一窺究竟。張之洞早年在任兩廣總督時,提出的開設織布局、利用外資修筑鐵路等奏請,都可以體現出其在教育改革、實業救國方面的思想與主張。除此之外,張之洞一生結交廣泛,與朝中諸多大臣關系密切,還可以查閱《盛宣懷實業函電稿》、《劉坤一奏疏》等,為研究張之洞生平提供他人獨特的視角。
(三)傳記類史料
傳記類史料包括傳記、年譜、回憶錄等。根據撰寫對象的不同,分為自撰和他撰。自撰一般為回憶錄,這種史料類型以撰寫者自身的視角生動的還原人物的生平,展現心路歷程,但也存在主觀性較強的局限。他撰一般由年譜、傳記的形式呈現,記錄更為客觀公正。這里所總結有關張之洞的傳記類史料主要屬于他撰的形式。《清史稿·列傳》的第二百二十四卷為張之洞傳,文末稱其“短身巨髯,風儀峻整”“及卒時候,家不增一畝云”,對張之洞的為人品質給予充分肯定。張之洞一生致力于探索新式教育,創辦了自強學堂、三江師范學堂、廣雅書院等多所新式學堂,在近代教育方面卓有建樹。蔡冠洛的《清代七百名人傳》將張之洞傳置于教育類,意在突出其在推動近代教育發展所做的重要貢獻。1928年中華書局印行的《清史列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國史館纂修大臣列傳稿本》、清史編委會的《清代人物傳稿》中也都包含張之洞傳。1991年南京大學出版社的《張之洞評傳》、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張之洞傳》,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張之洞傳》,是近三十年來張之洞研究的重要成果,雖非第一手史料,但其中援引材料眾多,與原始史料相比更具可讀性。關于年譜,最重要的參考為許同莘的《張文襄公年譜》,它將張之洞的一生按編年的順序展現在世人面前,有助于我們理清這位處于古今交匯時期歷史人物早年思想的形成與后期變化發展的脈絡。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張文襄公年譜》,還可以關注與張之洞關系相近其他晚清官員的年譜,《李文忠公年譜》《左文襄公年譜》中均有張之洞相關的史料記載,對于研究張之洞與其他官僚的關系及其在晚清權力結構的地位皆具重要意義。
(四)結集類史料
結集類史料主要包括個人的全集、文集和多人的合集等,既有作者的自編集,也有多人著述的匯集,具有品類全、范圍廣、體裁多樣的特點,是人們從事史學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張之洞在世時命手下刊刻的《廣雅碎金》,這是張之洞最早的詩集。1930年出版的《廣雅堂詩》,是張之洞詩集最早的刊行注本,嚴修在扉頁稱其詩“嘗有經法,志懷慷慨,本末洞達,真未易才”。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所匯編的《張之洞詩文集》,以《張文襄公全集》為底本,精校《廣雅堂詩集》《廣雅碎金》等詩集及注本,附錄又增添類許多新的內容,包括的《勸學篇》《輶軒語》《書目答問》等名篇。其中《勸學篇》是其宣傳洋務思想的著作,書中提綱挈領地提出了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書目答問》是張之洞在同治四年所撰寫的一本舉要性目承書,按經、史、子、集、叢書編排,現已成為國人學習國學最重要的典籍之一。這些名篇皆為研究張之洞的治學思想提供重要參考。《張文襄公全書》是許同莘承張之洞之遺愿所整理編撰而成,包含奏議、公牘、電牘、書札、駢體文、散體文、雜著、金石文八部分。《張文襄公全書》編纂完成后,因公奏稿、公電稿、公牘稿、公函稿四稿體量巨大,故又將其單獨整理成 《張文襄公四稿》。后人在此基礎上又撰成《張之洞全集》,內容收錄更加全面,只是版本也較多。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漢版的《張之洞全集》,編撰者留心搜索《張文襄公全書》所遺漏的張之洞文獻,足跡踏遍全國,從奏折、朱批、公牘中輯錄了大量的張之洞佚文,最終成書比河北版的《張之洞全集》多了三千余件,是目前為止收錄張之洞文獻最多的結集類資料,為研究張之洞提供了更加充足、全面的史料素材。
(五)報刊類史料
19世紀以來,中國近代新聞事業開啟,報刊事業迅速發展,為歷史記載提供了新的載體。與其他史料相比,報刊以動態的形式記錄了當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風俗等內容,展示了一定時間內的歷史變遷,極大地豐富了學術研究的現實感和立體感。
張之洞所處的晚清至時期,恰恰經歷了近代新聞報刊事業從起步到蓬勃發展時期。因此,有關記載張之洞的報刊也非常多,主要有《申報》 《京報》《述報》《萬國公報》《富強報》《農學報》《新民叢報》等。其中《富強報》《利濟學堂報》都曾對張之洞奏設武備學堂一事等進行過報道。《北洋官報》也對張之洞一手創辦的漢陽鐵廠的經營狀況進行過刊載。在西學東漸的風潮之下,張之洞本身也積極投身新聞事業,參與辦報活動。《湖北商務報》是其于1899年正式創設的商業類報刊,以“開商智、振商智”為主旨,出版了五年,由于是張之洞親自操辦,為研究張之洞的商業思想提供了重要參考。在督鄂期間,張之洞除了親自辦報外,也帶動了湖北地區的報業的迅速發展,產生了“辦報高潮”,當時湖北地區發行的 《湖北學報》《楚報》《不纏足會畫報》《湖北女學日報》等報刊也都能夠體現出其治理思想下武漢地區的社會發展狀況。
三、史料運用需注意的問題
史料作為研究歷史的介質,是人們了解歷史的基本條件,史料實證是人們正確認識歷史的根本保證。近幾年,史料實證作為歷史學科中學教育中五大核心要素的其中一項,被認為是應當從中學時期培養的歷史學的重要素養,其重要程度可以想見。史料實證能力培養的關鍵一步即是進行史料甄別。在利用的史料之前對其進行分析、判斷,選擇適合的史料來進行歷史研究,在史料甄別上,應從三個方面考慮:史料的價值、史料的真偽性和史料的主客觀性。
(一)史料的價值
張之洞作為晚清名臣,有關他的文史資料記載汗牛充棟。史料的價值也有所區別,如何在史料中篩選出與自己的選題相關的資料,這要求人們對史料的價值進行判斷。“史料往往是獨立于世間,常常單舉一事。如若史者將一份史料提出來作為自己的證據,研究結果則略顯單薄,無足輕重,不具有說服力。但如果將所有相關的史料匯集起來,進行歸納總結,其研究結果將成為讜言嘉論”[3],在進行論文寫作之前,首先應搜尋各類史料,盡可能掌握充足的文史資源,在使用前進行歸納總結,為下一步的篩選打好基礎。其次,研究者應思考所收集的史料是否足以支撐論述所要證明的問題,對于問題的解決是否有所裨益,這對史學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歷史研究者搜集史料方法最關鍵的一點是要注意常人注意不到的地方,思常人所不思。走出柏拉圖所言的 ‘思想洞穴’”[4],研究者應具有創新能力與問題意識,注意從史料的不同方面來思考,發現那些不易發現的地方,最后運用嚴密的邏輯,將所選擇的史料構成證據鏈條,對相關歷史問題進行論證。
(二)史料的真偽性
史料的真實性是其最重要的特征,顧頡剛先生曾說:“治史學的人對于史料的真偽應該是最先著手審查的,要是不經過這番工作,對于史料毫不加以審查而即應用,則其所著雖下筆萬言,而一究內容,全屬憑虛御空,那就失掉了存在的資格。”[4]先人留下了浩如煙海的史料,首先需要秉承“實證”的原則,對這些史料嚴格辨析。例如,在張之洞給江湖書院山長梁鼎芬的書中“今年講習勤勞尤甚,諸生蒸蒸,規模大備,文通武達,一堂兼之,創始書院千百年未開之風氣,歆起中華十八省有用之材,公之教也。”[5]在官僚好友應酬性的文字中,出于禮儀,往往未能體現出其本人真實的感情,而這類書信來往又常常由幕僚代筆,言語之間大多是客套恭維之詞,使真實性又大打折扣。一些遺留下來的文書資料曾進行多次修改編撰,記錄者在撰寫時也常有虛構訛誤之處,出現史實的偏離。正如宋代史學家鄭樵說,“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待這類史料的真偽性更應仔細甄別,對比考訂。
(三)史料的主客觀性
史料的記錄者是人,在記錄的過程中難免會帶有主觀性的色彩,往往會不自覺地站在自己的立場上,選擇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情節來剖析,因此史料具有一定的情感偏向。特別是日記、書札、回憶錄這類史料,論述主體自身具有記憶的選擇性和視野的局限性,對于事情的認知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局限,對歷史事件往往難以形成客觀科學的認識。第二,論述者自身也具有情感偏向,會有意識地揚善隱惡,最終導致史料記載呈現出對歷史事物認識片面性的問題。例如,在張之洞的彈劾奏疏中,雖然材料來源比較直接,為第一手材料,但其呈現的歷史事件往往是站在其自身的立場進行闡述的,在實際運用時,也應考慮到其所處境遇、人際關系、利益相關等諸多問題。
史料是認識歷史事件的中介,史料的運用貫穿歷史研究的全程。能否挖掘掌握扎實豐富的史料內容并對史料進行細致入微的理解運用,影響歷史研究的質量與水平,也為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運用史料來進行歷史研究時,更應嚴加甄別,去偽存真,堅守客觀公正的立場。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將史料運用在論文寫作實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