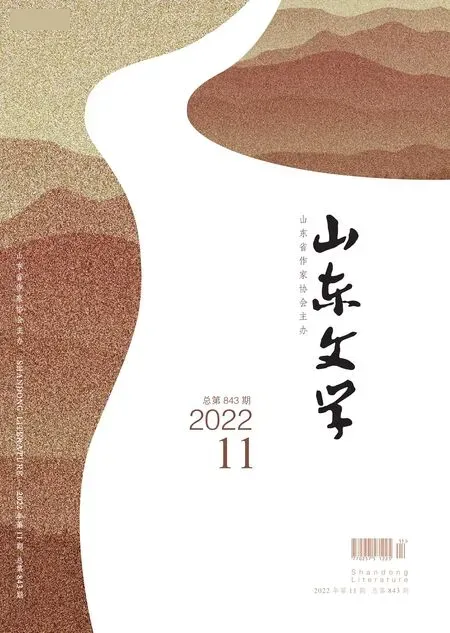壽光往事
孫鵬飛
堤里村
第一次撒謊是六歲半。
村里幼兒園的小朋友都去了鄉里,唯獨他,當天就讓老師趕回來了。
他跟爸爸說:“打架,因為打架。”
爸爸是個頭腦單純的屠夫,在太陽底下的堤里村,親手結果了無數頭黑豬的生命。爸爸扯著圍裙擦額角亮晶晶的汗,擦完看看腦袋冒著青茬的兒子,照例問他:“那你打輸了打贏了?”捆著的四蹄倒掛的黑豬,突然桀驁不馴地嗷嗷叫。
他說:“當然是打贏了。”
豬兩只眼睛充血,奮力掙扎。爸爸咬緊牙口,一刀捅向豬的肚子。
他蹲著看了會兒,裝出饒有興致的樣子,偶爾問一兩句討爸爸喜歡的話。“爸爸呀,豬到了你手里,為什么都這么聽話?”
爸爸絡腮胡子,矮個子,渾身黝黑、通亮,裹挾著一身的戾氣。周邊孩童看見了他爸爸,嚇得直哭。
爸爸也試探著問他:“跟我學殺豬?”
他若是當真點頭說好,爸爸便掄圓了膀子,一巴掌扇到他肉乎乎的嘴臉上。爸爸得說他沒出息。所以,他得拼命搖頭,他還得急得跺腳,他說:“我才不要呢,又累又臟。我以后坐辦公室,風吹不著雨淋不著。”
爸爸朗聲大笑,跟鄰里搭話,“你看看這崽子,倒是有出息呀!嫌他老子的工作臟,不知道老子一天一沓子鈔票掙得容易。”
鄰里也會討喜,觀摩著這孩子,說給他爸爸聽,“眉眼間都是一副官相,局長的料。”
到了下午,他面對幼兒園的李玉萍老師,沒了機靈勁兒。
李玉萍安排幾個圓頭圓臉的娃娃,去鄉里學廣播操,趕上六一兒童節,鄉里派得上用場。他因為不守紀律,讓帶頭的老師用教鞭打了腦門,咣咣咣,打得他那叫一個清脆爽亮。打完,老師說,“你下午不用來了。”
所以,李玉萍老師揪著他問:“為啥打你,不打別人,為啥把你趕回來了,不把別人趕回來?”他均答不上來。見問住了他,李玉萍囔著嗓子說了句,“三腳踢不出個屁。”
李玉萍全然不知,他眉眼官相,是干局長的料。背著無知的李玉萍,他放了個響屁。此后的很多年,他都在一些場合,繪聲繪色地描述童年時代打架的場面。當然,第一架,是六歲半的小腦袋里想出來的。是拿來騙他爸爸的。爸爸由頭到尾聽完,竟然聽不出任何破綻。
他姥姥家在鄉里。他在鄉里有個玩伴,叫國子平。模樣同他一模一樣。趕上趕集,國子平媽媽還抱錯過他幾次。后來,又聽姥姥說起,原來國子平的媽媽,要嫁給他爸爸來著。只是介意他爸爸是個殺豬佬。終于在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下午,同殺豬佬講清楚利弊關系,自此情盡緣清。
殺豬佬從不提這段往事,但是殺豬佬有意無意引導著孩子,一定得比那個國子平強。殺豬佬說,“你得比他強一百倍,強一萬倍。對了,你能不能打過他?”
孩子望著身高、模樣同樣周正的國子平,猛點頭。
“那好,國子平,你敢不敢跟我兒子打一架?”殺豬佬吆喝道。
國子平蹲下系鞋帶,頭使勁往上探著說,“我當然敢,你得等我系好鞋帶吧。”國子平系好了鞋帶,像老鷹抓小雞似的鋪展開兩臂,雙目放出酷似獵食的光芒。
待國子平逼近,孩子蹦蹦跳跳,學著電視里打拳擊的步伐,一路倒退著跳。國子平看不明白了,只看著好玩,也學著他的模樣,蹩腳地跳恰恰舞。倆孩子你來我往在地球上玩了一下午跳跳床,只有殺豬佬看得分明,孩子是有心讓著國子平,孩子幾次三番闖到了國子平眼皮子底下,只要揮揮拳頭,什么都解決了。一再為孩子本性善良扼腕嘆息。
對于沒有技術性的打倒對方,殺豬佬當然耿耿于懷。“打贏了,我看看國子平媽媽怎么說,承認不承認我兒子強,呔,就是血性。”孩子便活絡著一張小嘴,在這張嘴里,六歲半的他打架了,而且是狠狠揍了國子平一頓。
“你打得多狠呢?”爸爸乜眼瞅他。
“打破了頭。對,我把他圍在了墻角,一拳打得他東倒西歪,接著又一拳。”孩子拳擊手的姿態,大跳著比畫。
“那你們老師沒有管?不得了,你這是到鄉里打人。”
“老師也不敢管。那時誰敢管?我把他堵在墻角,一拳,又這樣一拳。他求饒,我說晚了,直到把他揍趴下,揍得起不來。”
“媽媽的,你真狠。”爸爸聽到興處下死手拍腿,濃郁的腿毛在陽光中戰栗。待腿毛波浪平靜,爸爸追問一句,“那國子平起不來了?”
“你說他敢起來嗎?”
“不敢,他起來,你還不是接著揍他?當他傻呀。沒那么傻。對了兒子,你說,他破了頭,你還沒說呢,到底怎么破的頭?”
兒子撓撓鬢角,摸摸耳朵,轉轉眼珠子,也不蹦也不跳,忽然大吸一口氣,瞪圓了眼睛。他說:“爸爸呀,他是一下子躺地上的,磕破了頭唄。”
胡營鄉
孩子身上不胖,從胯骨往上能一根根數清肋骨。胸骨、鎖骨一律凹陷,稱得上瘦骨嶙峋,唯獨一張大頭肉臉迷惑別人。有一年夏天,孩子穿著背心到鄉里買饅頭,讓姥姥家一個村民揪住,說你這也不胖啊。村民一把掀了他背心,一看,啥都明白了。自此,鄉里傳開了,一張大臉,干柴禾身子。有感性的逢年過節,堵上姥姥家的門,把閨女、女婿、孩子一并堵住,大嗓門喊,你這一年到頭殺豬也不行,你們家沒錢,你看看孩子瘦的。
到底是滅了殺豬佬的威風。殺豬佬走街串巷,再不散布自己掙大發了的謠言。知情的國子平媽媽才算心里踏實。
但是還有一個事,孩子壓國子平一頭,就是功課。
孩子九歲在屯里上學,同班同學皆八歲,小的七歲,個別的六歲。獨他,九歲,智商超群。
第一年摸底考試,語文、數學雙百。他懷抱著獎狀一路小跑,到了堤里村的界限,彎腰使勁喘氣。就是借著喘息的工夫,冬風一吹,獎狀脫離了孩子皸了的雙手,流向村口的蔬菜市場。有大老粗一腳踩住,看著字樣,艱難地辨認一陣,逐字逐句說,了不得,全鄉第一。
這股風也傳到了鄉里。在窗戶前做針線活的國子平媽媽也知道了,殺豬佬的兒子全鄉第一。
到了三年級,孩子不管是學習上、體育上,均不再占優勢。他自己分析原因是同班同學身高、智力已經長開了。五年級的春節,班里下發了十八張獎狀,孩子一張都沒有得到。那個西北風呼嘯的下午,孩子假裝失手打碎了班里一塊玻璃。老師揪住他耳朵訓了一陣,訓夠了,勒令孩子回家,把玻璃錢帶來。
殺豬佬的一張大臉是皸裂的,像菩提根、象牙果盤玩開了片,像窯燒的冰裂紋杯盞、茶洗,軍大衣的領子高高豎著,在西北風中養成的職業習慣是緊縮著脖子,本來身子不高,再縮脖子,便時時刻刻矮人一等。殺豬佬灌了口凍透了的茶水,問他兒子:“奎文啊,你跟爸說實在話,你考得咋樣?”
“第一名。”孩子給自己豎大拇指。
“那你這,連個獎狀都沒有?”
“我去老師辦公室談的,我說今年別給我發獎狀了,我要學習用品。我見他桌子上擺著蓋了大紅章的學習本,就說要這個。”
“那你的學習用品呢?”
“年后發。”
“我問你老師去。”
“問去吧。”
殺豬佬早已信不過孩子的解釋,打聽了孩子幾個同學,得知今年下發了十八張獎狀。又問,“那你班里發了多少獎狀?”
“十八張。”
殺豬佬瞅著風平浪靜的集市,咬咬后槽牙,握緊起了厚繭的手指,隨后攤開短粗的巴掌,隨后再一次握緊,這一次手里多了一把剔骨刀。冷颼颼,銀燦燦,滴答著殷紅的豬血。“嘿哈——”他一腳踢翻了肉案子,把尖刀逼向了兒子。“我要你一句實話,你為啥沒發到獎狀。”
“我把班里的玻璃打碎了,因為這個,老師對我意見很大,把獎狀撤了。”孩子雙手抄兜,眉目倒是清澈。
漫長的暑假計劃泡湯,孩子轉眼間就要只身闖蕩胡營鄉的大聯中。最后的胡營大集上,孩子垂著頭,踩著印象中滿大街蕭瑟的落葉。而孩子的媽媽頗費力氣地拉扯著時常癡呆的孩子,買了書包,買了被罩,要買牙刷時,孩子打斷媽媽,說是自己多嚼嚼口香糖就行,刷牙耽誤了時間,影響學習進步。媽媽點頭同意,還是給孩子選了把劣質的硬毛牙刷。其間,孩子見一個身材魁梧的身影,在一堆凡夫俗子中晃蕩個不停。同他僅有的目光交匯,孩子知道不好,國子平長成了大個子。
另一件不好的事,驗證在了國子平身上。是孩子在聯中第一次如廁,孩子跟不相識的面孔蹲成一排,旁邊的同學在那聊一次坐席吃肉的經歷,廁所的味道熏著同學齜出的一口黃牙,同學還恬不知恥地嘻嘻笑。孩子吸一口涼氣,思考了一會兒人生,這時眼瞅著國子平站到尿池前,褪了褲子,像跟誰賭氣似的撒尿斗遠。廁所墻上描了半幅世界地圖。
這時,正抽著煙的染了頭發的少年,把煙頭彈到地上,嘶嘶冒著尿渣子氣。少年已經九年級了,他走近國子平,拍拍國子平肩膀,問道:“你會打仗嗎?想跟著我們嗎?想的話留下姓名班級,我們找你。不想,我們扒了你褲子,扔尿池。”國子平說:“你等我弄好。”國子平收緊了腰帶,像是回到了小時候,跟還是孩子的奎文跳恰恰舞,國子平蹦蹦跳跳地同他們三人戰斗。
為首的少年一拳打破了國子平鼻子,剩下的倆少年抬著國子平,往孩子蹲坑的地方一扔。“噗通”一聲巨響,孩子和國子平先后泡進了茅坑。“我這是招誰惹誰了!”孩子仰天長嘯。
“奎文,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報仇。”國子平帶著孩子來到他家屋后的樹林,梧桐樹林里有摞高的磚頭擺成的梅花樁,樹杈子上掛著填了沙的化肥袋子,沿著屋墻擺了一溜長短不一的燒火棍。“你沒事就來這里練功,練成神功我們報仇雪恨。”國子平也拍拍孩子的小肩膀。
國子平還帶孩子到他家的大棚里。光鮮亮麗的紫皮茄子,往咯吱窩里蹭蹭,遞給孩子一個。孩子一口咬去大半,咂嘴咂舌評價,香甜、多汁。國子平皺眉說,“不行不行,昨天我爸用茄子砸我媽,還把兩根茄子同時賽我媽嘴里,說我媽沒有腦子,只知道吃,不知道怎么種茄子。”
大棚是國子平媽媽一個人種,國子平爸爸在外地當建筑工人。問及奎文爸爸媽媽的職業,奎文說,“爸爸在縣城開門頭,媽媽在國營企業上班。”奎文特別強調,爸爸媽媽結交了縣城的很多關系,因此也從來不過問他學習上的事,因此他完全不必為了學習和未來擔憂。
事實上,他媽媽在村里賣農藥,爸爸在集上有一個豬肉的攤位。
時有練功沒了頭緒,國子平買了武打的盜版光碟,邀奎文去看。洪拳的招牌架勢,蔡李佛,八卦掌手黑,迷蹤拳,三板斧的詠春,這些靠影視傳播、千篇一律的南北拳種,國子平和奎文如數家珍。跟著電影打一趟太極拳,國子平扎穩了馬步問奎文,“我這個樣子,還有什么破綻沒有?”僅有的一次陰差陽錯放錯了片子,該說盜版商走心還是不走心,把成龍的警察形象印在了碟片上,填充的內容卻是三級片。奎文取出碟片,一手持著碟片然后一掌擊穿。
奎文的各科成績相較練功之前,都是節節敗退。學校新出的督促孩子學習的政策是,考試后每一科的成績,都需要簽上家長的大名。孩子練了武功什么都不怕,孩子自己代表家長簽上姓名。班主任問時,孩子說,我們家長沒文化,就這個水平。惹得老師氣歪了鼻子。
孩子問國子平,“誰簽的字?”國子平直言是自己的爸爸。孩子又問,“那你考成這樣你不挨揍嗎?”國子平說,“挨揍就挨揍啊,這次考差了,下次長進就行啦。”孩子便哀求國子平,把自己的成績單委托給國子平爸爸,一并簽好了。孩子最后一個上交簽過字的成績單,上交時他在一堆成績單中發現了國子平爸爸,一個資深建筑工地的農民工字體,和他手中的簽名一模一樣,任誰也忘不了這扎眼的字。他只好悄默聲地抽走了國子平的,只留下自己的。
為此,孩子很氣悶。生氣自己,違背了兄弟的情誼。尤其是當天下午,老師說,“很多同學都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們,很多同學不是太聽話,這樣——”老師喊懵然無知的國子平起立,然后一腳踹了國子平一個大跟頭。不待無辜的國子平站起來,老師便宣布道:“誰不聽話,誰這個下場。”
后面幾次考試,國子平確有進步。孩子沒進步,孩子覺得氣悶時,找上幼兒園老師李玉萍的家,把一塊紅磚斷作兩截兒,一截兒砸向李玉萍家的窗玻璃。李玉萍老公從豬欄抄了根長竹竿,追著打孩子,孩子也不慌,把另一截兒紅磚砸向了李玉萍家的另一塊窗玻璃。
夏至未至,上一茬染頭發的少年畢業了。秋分時節,跟奎文、國子平同級的同學也染了頭發,牛仔褲上耷拉著鐵鏈子,也成群結隊去低年級招收小弟。讓校長劈手奪了鏈子,指名道姓說:“這玩意兒在農村拴狗合適。”校長開大會的目的是動員一部分學生,選擇壽光縣城的技校,宣布這是咱們自己地界的大學。
國子平想上高中。班主任找國子平談話,“你跟奎文保持距離吧,在他,是無所謂的事。在你,不一樣,你還有機會,別輕易放棄。”
奎文不想上高中,就算想上,自己也考不上。
所以兩兄弟該并肩行走江湖、鋤強扶弱的,僅剩下奎文一人了。就算結伴去廁所,從廁所再到教室的路上,國子平也要說一句,“老師對我期望很高,不要讓他看見咱倆在一起。你先走,我再走。”奎文心里酸酸的,嘴上還是說,“了然了然,兄弟不擋兄弟的路,中國人不騙中國人,你一定要加油。”
分流的當天,天空陰冷的異乎尋常,奎文自己搬著桌子,桌面上倒立著椅子,椅子上掛著書包。教室前面的草坪久無人踐踏,卻同樣是破銅爛鐵的色彩。奎文踩著影子在門口駐足,國子平隔窗揮手,奎文懷抱著桌椅所以無法揮手。在學校門口浪潮般的二道販子里,奎文精挑細選了最看得順眼的一位,桌子五十,椅子三十,一并賣了。
他知道,青春的故事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
壽光縣
那晚,殺豬佬盤腿坐在失去彈力的沙發上,樂呵呵地覷著自小帶大的孩子。兩指間的煙越縮越短,總是著急忙慌搶救下最后一口煙,臉上不無得意之色。并肩而坐的孩子垂著頭,只有在表示反對意見時才會抬頭,目光堅毅地鎖著殺豬佬。殺豬佬說:“父親是遠近聞名的屠夫,所謂一刀定乾坤,既然父親從了武,你就得從文,我們霍家才能一文一武,文武雙全。”孩子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寧當雞頭,不當鳳尾,孩兒的志向從來不在學習上,將來要在考試之外,另闖出一番天地。”殺豬佬咧嘴大笑,爽朗的共振,像年底炮仗震得房梁下落陣陣灰塵,“村里幾個念了技校的,都是遠近聞名的無賴疣子。你學他們嗎?他們是你的榜樣?我們霍家只出棟梁之材,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所謂自古侯門出將相,所謂千錘百煉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
孩子一腳踢翻了跟前茶幾子,在殺豬佬的詫異中,孩子雙膝跪地,規規矩矩地磕了三個頭。“爸呀,你當我是個不孝子,你放過我吧。”
殺豬佬面皮顫動著,連同著嘴唇一并顫動。他打量了一圈奮斗了十余年,親手打造的幾間瓦屋,最后視線定格在東屋。東屋的水泥地早讓老鼠洞糟蹋得沒了樣貌,幾塊摞高的紅磚上蓋滿了小麥、玉米袋子,袋子上面拴著尼龍繩,殺豬佬抽出一根長繩,在沒通電、漆黑一片的東屋里揮舞起來。這條長繩最終反剪了不孝子的雙臂,人同長繩吊掛在梧桐樹枝杈間。
殺豬佬搬來了茶桌,倒上清茶。殺豬佬在蚊蠅縈繞中一口口品著茶,苦等著綿綿不絕的黑夜散盡,黑夜的盡頭總是日出。“我他媽是給你臉了,小畜生。”
小畜生個子不高,甚至比發育早些的女生矮半個頭。小畜生的爸爸交了一萬二的委培費,小畜生穩當當地坐在縣城第一中學一班的第一排。迂腐的班主任是按照傳統的身高模式,給壽光境內七洲四洋的兄弟姐妹分的座位。班主任白襯衣掖在牛仔褲里,胸前當啷著紅領帶。班主任下巴打理得干凈,說是從沒有過胡子都說得過去。班主任說:“不許給女孩子寫情書,別不要臉,你們還沒到那個年紀。”小畜生也就記住了這些話,時常回望身后的漂亮女孩,并把最漂亮的一個記在了心里。
孩子的第一封情書,就是寫給這個女生。他自稱同這個女生的關系是小溪和大海,是鉛筆和鉛筆刀,是許仙和白娘子。女生也交口稱贊孩子有才華有前途。“林萬紅。”他無數次躲進細雨中的小樹林,在孔子石像下呼喊這個美妙異常的名姓。林萬紅。他在網吧的鍵盤上打字,在偷錢買來的小靈通上打字,在平白如洗的作業本上寫字。林萬紅。這個名字最終讓一雙粗糙大手當場擒獲。大手的主人,也擁有著一雙肥大的腳,寬敞的鞋底子一下落到孩子的胸口。
“不害臊的東西,心思完全不在學習上。”大手的主人再一次在孩子眼前晃晃剔骨刀,孩子一個巴掌把刀打到黃土路上,劃出塵土飛揚的一道紋路。
這雙失去剔骨刀的大手,把一個月見一次的孩子鎖在房間里。殺豬佬隔著房門說:“你哪也別去,在家好好學習,就趁著這一日,大家都放松的時候,你好好學習,一下子趕超了他們,我看他們怎么說。全班面對你突飛猛進的成績,一準都抓瞎。”
孩子困在東屋改建的閉塞書屋里,孩子卻沒有抓瞎。孩子從集上買的印著光屁股女人的雜志,上面除了影樓風格的艷圖,還有一些詭異小故事,還有港臺明星八卦,還有《小說月報》,孩子只挑出黃段子,一目十行地看。看著看著睡著了,恰好午睡時刻。想來,人也是稀里糊涂地進入到書本故事中。
故事講的也是一個男孩子午睡,睡眼惺忪間,一身白衣的女子撩門簾進來。女子三十多歲,臉色浮腫,來回徘徊。逐漸逼近臥床,很自然地揭衣上床,壓在男孩子的雪白肚子上。女子的細腰、肚臍也是盡收眼底。男孩子只覺千斤重,胸口悶,苦苦發不出聲音。一著急,手如綁縛,腳如癱瘓,全身能動彈的只有小細腰,便使足了勁兒往上頂。頂了幾下,也就一股一股釋放出來了。
孩子臊眉耷眼地坐起來,茫然四顧,肚皮上娛樂雜志封面印著妖嬈的張柏芝,一行黑體加粗字:張柏芝的小兒子是劉德華的,劉德華不敢承認。烈日正旺,窗玻璃五彩繽紛的,玻璃外是五彩繽紛的十七歲的天空。
晚自習之后,孩子把林萬紅約到操場。給林萬紅護手霜,給一張林萬紅的素描像,有時候是首尾呼應的一首小情詩,還給過奶茶、豆漿、餡餅、咖啡糖。林萬紅問孩子:“為啥叫奎文,是不是《超生游擊隊》里說的,是在濰坊市奎文區生的?”奎文說,“是生他那年,爸爸的第一套房子,在奎文區買的。”林萬紅感興趣,“那第二套呢?”一中在縣城邊緣,時有斷電。黑燈瞎火的,孩子壯著膽子親了林萬紅,親完只是說:“壞了壞了,一斷電,剛提的一箱雪糕又得化了。”其實孩子家里唯一的電器是,爸媽結婚備的一臺彩電。孩子走路只顧看自己鞋子,林萬紅倒是大方,勸孩子得放開,跟個小姑娘似的,忸忸怩怩多擰巴。
孩子同樣看見,其他男孩子約林萬紅到操場。也是黃昏時分手拉著手。孩子不上課,跑回宿舍用被子蒙著頭大哭。孩子還跟著高年級的學長翻墻上網,還跟著看午夜電影。孩子留長頭發,因為不符合校規,班主任問他:“你這腦袋上長了金條嗎,說你多少次還不去理發。”氣不過,用剪子給他絞,絞出一頭炸毛,讓他看著辦。“像精細打理的草坪,來了牛,來了羊。還來了什么,還來了豬。”
豬是騎摩托車來的。把摩托車停在教學樓前面,人穿著緊實的皮衣,腳蹬著大號皮靴子。林萬紅的幾個女同學都圍著他看。他說:“你們看啥看,把我當動物看呢,當什么,當豬呀?”惹得女同學哈哈大笑,夸贊著他的風趣幽默、知冷知熱。他把林萬紅帶出了西門崗,然后拐彎上了筆直的大馬路。路是漫長的,沒有盡頭,大概在馬路上疾馳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的同樣時間,疲憊的旅人才從地球的另一端穿越回來。回到了原點。
只是豬沒有下車,在西門口丟下林萬紅,摩托車轟隆隆的油門聲,車屁股噴著稀薄的煙,煙散了,人也消失了。
穿運動衣都顯苗條、婀娜的林萬紅,哪怕是上個廁所,身后都跟著一大群指手畫腳的男男女女。“豬拱了白菜。”嘴賤的這樣說。孩子理論:“采花不敗花,敗花皆可殺。”嘴賤的說,“拉倒吧,還殺個涼鞋呀,破了處了,小癡子。”
林萬紅頂不住壓力,最終退學了。孩子握緊了拳頭,孩子在心里定了魔鬼訓練的計劃,照他的思路,練成了就是中國的洛奇,中國的蘭博,再組建一支中國的敢死隊。他要繼承殺豬佬的手藝,最好是照著嘴臉,一刀下去,把豬頭豬身劈成兩半。
有大半年時間,孩子的正經事是跑步,是單雙杠,是鉛球,是標槍,是散打,是通背拳,是摔跤,是自由搏擊。除了頻繁的淘汰球鞋,孩子倒是長高了,茁壯了,眉眼間有英武之氣,舉手投足帶著起義的斯巴達克斯的神韻。腦子里演練的是一聲令下,攻城略地的戰爭劇。
孩子是在塑膠跑道,見到的正上體育課的國子平。當時國子平的同學在講,從實戰出發,李連杰能不能打過甄子丹。高談闊論吸引到了孩子,孩子探頭探腦扎進人堆一看,國子平也在其中。國子平沒考上高中,國子平的建筑工人爸爸給學校交了八千塊錢,作為落榜生的委培費。國子平爸爸一個月,只給國子平六十塊錢。國子平黑了瘦了,說是業余時間勤工儉學,去工地上和泥巴、搬紅磚。一日三餐是自帶的榨菜,饅頭是工地上攢下來的。
孩子拉著國子平到孔子石像下,孩子一一訴說著自己的平生不得志,說到心愛的女孩輟學時,潸然淚下。孩子說:“如果孔子有靈,看著如今莘莘學子這樣艱難,真不知作何感想。”命運是覆水難收。當年落榜的消息,是和秋天的第一批落葉一起來的。一夜之間席卷了胡營鄉的大街小巷。彼時的孩子同國子平爬到屋頂,二人喝啤酒像喝白酒,小口抿著喝。喝了一個白天,酒還剩下大半。烏鴉或者干脆是報喜的喜鵲四處盤旋,聲聲鳴叫。國子平緊抿著嘴唇,抿得嘴巴是一道擔著千斤重物的扁擔。國子平說:“好兄弟,看來我們得去壽光的大學打拼了。”
孩子寬慰道“你看成龍,也沒有學歷,但是一雙拳頭打拼了多少榮耀。我們年輕,有闖勁,我們到哪里都不怕。”
孩子和國子平自詡還算年輕,有闖勁,什么都不怕。頂著一打架就開除、一點商量余地沒有的校規,孩子再一次見到摩托男。孩子招手把國子平喊到身邊,孩子心里是有了無限的底氣。孩子說:“豬,你別走了,你今天走不了。”豬看看孩子,看看國子平,豬從兜里摸出手機,豬打電話,豬說:“哥呀,我讓幾個人物劫道了,縣一中西門,快來。”豬說話時一只手摸著肚子,許是緊張,或是天氣炎熱,天干物燥,豬的鬢角一直流冷汗。
豬的哥帶著兄弟來的。孩子并不怕,即使人多勢眾,孩子也全然不怕。孩子說:“我叫霍奎文,他叫國子平,我們可不怕你們。”豬的哥哈哈大笑,哥笑的時候,豬一個箭步上來,親自扇了孩子兩個嘴巴。孩子的臉孔先是扭向左邊,接著扭向右邊。接著豬的哥把一個沒打開的彈簧刀戳在孩子胸口,他說:“就你,劫道。”
孩子吶喊一聲,像是殺豬佬跟豬血拼之前做的準備,孩子只一下足以把豬的哥頂翻在地。只是,沒有人看到,孩子是哪個時刻,是怎樣奪過了彈簧刀。
豬的哥招呼著倆兄弟,一邊一個把揮起彈簧刀的孩子架空,孩子兩腳離了地,徒勞地蹬腿,“媽媽的。”
豬沖著孩子的肚子踢了兩腳,像是只兩腳便把充氣娃娃踢得沒了氣。充氣娃娃嘶嘶嘶撒著氣,癟了,縮成一團。
豬的哥是后知后覺。他看了會兒眾人,自己坐到地上,隨后乖乖地躺倒,他使勁兒睜開又合上眼睛。
國子平木偶人一般遠遠看著,目光里是不解、疑惑,像是沒想明白,我為什么要在這里。
濰坊市
奎文從長途車上下來,嗆著風吸著煙往龍城市場方向走。見了熟人,從后面拍拍人家,等人家反應過來,奎文早就消融在無數個晃動的背影中。這次在批發站要了兩大包里脊肉,過秤時還是無休止地跟人討價還價,販肉的都認識他,看看秤,再看看奎文,還是決定給他個便宜。
“肉不好賣了,一只豬宰了,四腳朝天掛著,你割一刀,我割一刀,都他媽要里脊,要后肘,要精的,我他媽哪兒來那么多里脊,那么多后肘,那么多瘦肉,剩下的叫我怎么賣?我還有什么,就剩個豬臉。”販肉的替他扛著一包里脊,出了市場,販肉還叨叨個不休。“對了,看你年紀不大,有三十了?”
“今天剛好三十歲生日。”
“你這么小,今天不回家過中秋節?”
出了市場,他肩膀擔一包肉,嘴巴咬著煙,大步往長途車站走。不等走到車站,凍肉會化開一部分,弄得大衣黏乎乎的,到了車上,肉會化得更快,混著血水流淌。上次司機以為他運尸呢,鬧了個笑話。路過濰坊市職業學院時,他加快了腳步,幾乎沒正眼看南門口擁擠的學生,但是穿過門口,又往前走一段上坡路,快走到柵欄的頭了,還是駐足,細細觀望著里面。
有幾個身影像林萬紅,有幾個像國子平,還有像他的。也只是像而已。沒別的了。回程的路要經過最漫長的黃沙路,沙子噼里啪啦痛快地拍打著車玻璃,車身急劇地搖晃中,他歪著頭睡著了。又是夢到那年夏天,一人午睡,一身白衣的女子撩門簾進來。女子三十多歲,腰系麻裙,揭衣上床。女子親吻他的額頭、眉眼、顴骨、臉頰、鼻子、嘴巴,一點點、一寸寸往下,他只覺手如綁縛,腳如癱瘓,窘迫難挨。他突然用盡了全身力氣,惡狠狠地咬住了她的嘴。牙齒深咬進肉里,血液流淌到臉上,濕淋淋地連枕頭都打濕了。奎文平靜地睜開眼睛,深呼吸,車子四平八穩地碾壓著黃沙路,前面是重重疊疊的樹林,似乎一切永無盡頭。
一年前盛夏,殺豬佬突然兩眼一黑,栽倒在集市上。
“中風?腦血栓?你爸這個怪突然的。這二年真累了你啦,工沒得上,錢沒得掙,一天到晚伺候個殺豬的。”
再出現在鄉親面前的殺豬佬坐在輪椅上,兒子推著他走街過巷。直把殺豬佬推到豬肉檔前,兒子系上圍裙,圍裙帶子勒出了他腰上、肚子上新添的贅肉印子。鄉親在他豬肉檔前面立住時,他臉上堆著笑散煙。一包煙拆開,很快散得只剩下一支,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沖著鄉親傻笑。待人離開,他才張開五指攏上火苗,點火深嘬一大口,一絲細煙迎風升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