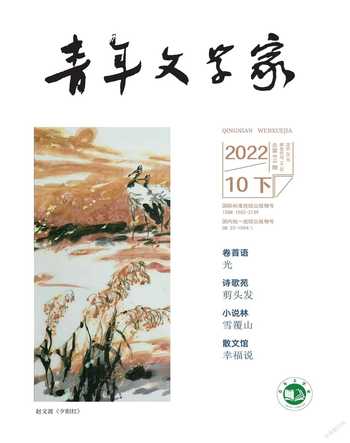論托馬斯·哈代小說的敘事藝術
劉香溪

托馬斯·哈代的小說具有顯著的過渡性質,他既賡續了維多利亞時期傳統小說的道德理想化特質,呈現出對自然和鄉土世界的無盡眷戀,同時又融入了現代主義的小說技法,在敘事間呈現出先鋒的底色。可以說,思想特質的傳統性與敘事技法的現代性在其文學創作中構成了微妙的平衡,共同鑄就了其小說獨特的藝術魅力。
一、多元復雜的敘事結構
敘事結構是小說外在形式的基礎架構,它囊括了小說情節的織構、人物關系的編排和敘事布景的設計,其中必將融入創作主體豐富的創作意圖與主觀情志。托馬斯·哈代具有濃厚的鄉土情結,他對生態自然與鄉土文明的認知同現代的小說技法結合,開創了富有隱喻意義和個人化特質的復雜敘事結構。
在哈代前期的小說敘事中常見圓形的循環結構,情節往往在開端處便偏離其應有的發展方向,然而在經歷系列的波折后能夠回歸原點,沿著其既定的方向繼續發展。例如,《遠離塵囂》中的女主人公巴斯榭芭熱情洋溢且頭腦靈活,她對新生事物有著旺盛的好奇心,時常期望能夠告別鄉村悠閑、平淡的生活氛圍。她的兩個追求者柏爾伍德和奧克都是傳統意義上的青年才俊,他們因循著傳統的生存樣態并表現出淳樸的道德思想,彬彬有禮地向巴斯榭芭求婚并承諾予以其悠閑安逸的婚姻生活。然而,巴斯榭芭卻被鄉村世界的“外來者”—特洛伊中尉吸引了視線。這個外表英俊的軍官滔滔不絕地向巴斯榭芭講述著外界的新鮮事物,最終以甜言蜜語贏得了巴斯榭芭的愛,卻最終沒有對其加以珍惜。哈代以特洛伊的形象揭示了經濟結構的變動及其帶來的社會道德體系的流變,表現了對鄉村世界寧靜原貌的追懷與留戀。最終,虛偽的特洛伊被柏爾伍德擊敗,巴斯榭芭也意識到了“激情就如同虛幻的蒸汽般不可捉摸,人們腳下粗糲豐饒的土地才是人類唯一的支撐”。拒絕了歸入傳統的巴斯榭芭最終選擇回歸原有的命運軌道,與奧克結成夫妻并重獲精神世界的平靜。不難覺察,這種圓形的循環結構具有極強的隱喻意義,“外來者”特洛伊在愛情角逐中的潰敗表征著傳統農業文明的優越性,而女主人公巴斯榭芭“去而復返”的命運更構成了內在的回環式結構,隱喻著英國鄉村社會內部秩序的穩固。
而隨著現代文明逐漸顯露了其在現代性的維度上的優勢,哈代也逐漸認識到了鄉村世界的閉塞,因而其后期小說的敘事結構也逐漸呈現出復合發展的雙拱形結構。例如,《綠蔭下》中的女主人公芳茜在青年農民迪克和牧師梅瑞德之間左右為難,她既受到傳統道德理想世界的精神召喚,又對現代文明的物質生活難舍眷戀,因而陷入兩難的境地。她與兩位表征著不同文明的男子的愛情線索交織并行,因摻雜著大量的心理描寫而變得明暗起伏,具有極大的張力。雙重情節線索構成了雙拱形的敘事結構,通過女主人公的愛情抉擇表征了傳統的威塞克斯社會與現代資本體制的文化沖突,及其帶來的當時社會普遍的精神迷茫。且現代小說先鋒技法的融入也使哈代的小說敘事結構呈現出更加多樣的樣態,如《德意志軍團中憂郁的輕騎兵》中層層嵌套的嵌套式敘述結構。小說的表層敘事展現了迤邐靜謐的鄉村風光與平靜的田園生活,在恬靜和諧氛圍中一處滄桑古舊的歷史遺跡引起了處于“此在”時空的敘述者的追憶,開始回顧起了過往他與老婦人菲麗絲的交集;而深層敘事則引入了“彼時”時空的英國女子菲麗絲與年輕英俊的輕騎兵馬修斯之間的愛情悲劇,使兩人充滿舛錯的愛情經歷因背負厚重的歷史感而具有崇高的悲劇性。無論是馬修斯與戰友出生入死,即便面對生死考驗也不愿輕易背棄諾言的質樸品質,還是菲麗絲對愛人充滿忠貞的堅守,都充滿了理想化的人性美。同時,在嵌套式的敘事結構下,表層故事與深層故事之間因時空距離而制造的延宕也使讀者與小說保持了恰當的審美距離,得以從時空秩序的變更中不斷回味小說帶有崇高性的悲劇美,在表層敘事與深層敘事的穿插切換間產生“恍如隔世”般的閱讀體驗。
敘事結構的多元復雜呈現了哈代在小說敘事方面的才能,尤其是其后期的帶有現代主義風格的小說,復雜的敘事結構不僅具有外部形式的意義,還成為小說思想主題的重要構成部分。形式各異的敘事結構折射出哈達對現代化轉型中英國鄉村社會與城鎮化之關系的反思,體現出創作主體對社會之流變的觀照。
二、喻指豐富的敘事空間
列斐伏爾的空間敘事學理論揭示了空間具有的敘事潛能,以空間負載的社會關系及其動態演變證實了空間具有的社會屬性。由此,空間不再是依附時間而存在的不可視之物,而是與時間對等的重要敘事元素。哈代的創作深受列斐伏爾空間理論的影響,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遷徙往復更使哈代形成了顯著的空間概念,積累了豐富的空間體驗,因而他小說的敘事空間往往具有豐富的喻指意義。
不難覺察,哈代的小說具有明顯的地志空間特征,地理空間的移置不但成為織構小說情節的重要線索,而且不同空間具有的特征與氛圍也往往喻示著人物的命運。例如,《德伯家的苔絲》中的地理空間便具有豐富的喻指性含義,主人公苔絲的命運及其所處的地理空間及其景物同氣連枝,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感知到人物與環境之間的和諧。苔絲出身于“生長著茂盛鮮草的廣袤原野”,布萊克谷馬洛特村怡人的自然風光賦予了苔絲充滿健康氣質的美貌和不諳世事的天真性情。她如同從未有人涉足的世外之境,保持著富有原始生命力的美麗。同時,空間的封閉性也使苔絲賡續著傳統的道德品質,使她在與外界接壤后容易遭受虛偽之徒的蒙蔽,為其悲劇的命運埋設了伏筆;而苔絲輾轉來到純瑞脊德伯府后,空間的鏡像呈現出顯著的由鄉村田園向工業資本蛻化的特質,“田野和牧場都已經毫無影蹤,成片的土地空曠著,唯有鄉紳的宅院佇立其間”。工業革命的浪潮已經無聲地進入了鄉村,解構著原生的經濟結構與生存方式。而這種文明在逐漸蛻化的進程在陵窟槐中表現得更為具體,“黝黑而粗壯的煙囪聲音嘶啞,突兀而顯眼地聳立著,不間斷地從頭頂噴吐著滾滾的濃煙”。地理空間的轉移象征著苔絲命運的轉變,在純瑞脊與陵窟槐中苔絲遇見了亞雷,隨之遭受了其蒙蔽而逐漸遠離了自己熟稔的鄉村,逐漸失掉了自己純真的本性。隨著苔絲在不同地理空間的遷移,大量的工業物象、城市景觀也出現在讀者的視野中,空間景觀及文化氛圍的轉變有力地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后期社會文化結構的內部質變。而《德伯家的苔絲》中,具有空間意義且富有喻指性的人物不僅只有苔絲,貪婪粗暴的亞雷象征著從鄉紳向資產階級轉化的空間場域,而克萊則象征著新興的現代文明空間,人物之間的復雜關系影射著轉型期的英國社會中上演的各種文化沖突,具有強烈的現實寫實意義。
而在具有社會喻指意義的敘事空間之外,哈代也十分專注于挖掘特定空間的審美喻指內涵,尤其是富有時代感的建筑空間本身的審美價值。例如,《遠離塵囂》中奧克的小木屋,“結實的板架線條粗簡,掩映在密實的灌木中,深沉的色澤令人感受到堅實的庇護”,簡明卻結實的空間傳遞著溫暖的感覺,令向往著現代城市的巴斯榭芭在無意間被奧克的質樸良善吸引,并最終與之結成眷侶。敘事空間表征著其具有的文明屬性,隱在地傳遞出作家對鄉村田園及純善人性的褒揚與眷戀;而《德伯家的苔絲》中塔布籬的玻璃花房則象征著現代社會中小資產階級的情趣,“光線透過玻璃鋪灑在柔軟的土壤上,花房內的世界似乎是與世隔絕的”。上層社會的建筑沒有實際的功用性,遠離了現實的世界而僅具有審美性的價值,這種建筑空間特征反映了人類生活方式的變化,從現代性的維度上反映了人類文明的演進的樣態漸趨多元化。敘事空間的多種樣態反映了當時社會中傳統與現代、新與舊的并置,它們在小說中不僅具有原本的物質屬性,充當著故事上演的布景,還具有相應的文化屬性。
喻指豐富的敘事空間表征了哈代對工業現代化進程的理解,不同敘事空間的變幻不僅成為小說情節據以發展的線索,還成為哈代展覽英國社會之變遷的獨特敘事策略。敘事空間內的文化景觀富有時代性,附著創作主體的情感質素。從中我們也可以瞥見哈代對城鄉文明的反思,他對工業文明向鄉村的延伸的態度經歷了由抗拒到接納,最終以理性的態度加以審視的動態過程,而這種情感態度的移異無疑是通過小說中的敘事空間加以表現的。
三、蘊意深刻的象征技法
象征物凝集著創作主體豐富的主觀情志,以具體的形象承載著豐富的抽象內涵,其象征意義的建構源自于創作主體自我的體驗,是接受者切近創作主體思維方式與情緒情感的重要方式。象征技法以直接鮮明的形象表現難以言說的豐富意蘊,物象意義的隱喻性和多義性為讀者的想象制造了廣闊而富有張力的空間。哈代的小說具有豐富的象征物,既傳遞著作家隱在的敘事意圖,又暗示著小說情節的走向與人物的命運,產生了含蓄而深邃的敘事效果。
鄉村生活的經驗使哈代小說的意象體系呈現出顯著的自然性,對自然和生態美學的熱愛使哈代對自然界的生物有著敏銳的關注,他小說的意象體系中不乏生動的動物意象,暗示著作家對人物命運的鋪設,反映著作家對整體社會及人與自然關系的思索。例如,在《德伯家的苔絲》中,老馬“王子”是苔絲家借以維持生計的重要支柱,然而它在一次趕路的途中意外與飛速行駛的郵車相撞,被“郵車尖銳的車把刺中了胸膛”而死去。老馬“王子”象征著的鄉村原始的生產方式在現代文明的象征物“郵車”面前是如此的脆弱,揭示了該時期工業文明正在以不可阻擋的勢頭取締著落后的小農經濟。同時,老馬“王子”的死去也象征著苔絲命運的悲劇轉折。在老馬死去后,被生計所迫的苔絲不得不遠離自己的家園和淳樸天然的生活方式,從而開始了充滿波折的人生,小說中的動物意象與人物命運緊密聯結,印證了哈代“性格與環境小說”的個人化寫作風格。而《卡斯特橋市長》中,哈代擇取了“鳥”的意象預示和象征主人公亨察德的命運,動物意象既成為讀解亨察德形象的妙門,又揭示著其人生境遇的內在成因。每當亨察德面臨人生的轉折時,“鳥”的意象總是會出現在文本中。當亨察德決心要改變自己的窘迫處境,不計代價地想改變時,“帳篷的罅隙中忽地鉆進了一只灰色的雀鳥,在帳篷的圓頂上不住地徘徊,一時間所有人的視線都緊緊地跟隨著它”。鉆進帳篷的雀鳥象征著想要改變當前的命運,實現自己的理想的亨察德。生動的動物意象攜帶著自然的靈性與神秘,它們在小說中的出現象征著文本未來的走向,預示著主人公即將面臨的處境,引發了讀者無盡的遐思與設想,無形中拓展了小說的想象空間。
同時,哈代也在其小說中融入了大量的自然物象作為文本中的象征物,璀璨的星輝、熱烈的暴雨和神秘的夜空等,這些自然的意象物帶有崇高的力量美與朦朧的神秘感,隱秘地傳遞出哈代對自然之美的崇敬和贊嘆。《還鄉》中,哈代以“宇宙中的星體”象征著科萊姆與尤斯塔西亞之間的關系,“他們猶如宇宙中的星體,自然地存在著無窮的引力,在周而復始地做著循環運動,在遙遠的地方向它們望去,似乎它們運動的軌跡合在了一處”。這種象征的手法一方面揭示了主人公間深受彼此吸引的強烈愛意,一方面也預示著兩者雖然看似“軌跡合在了一處”,卻如兩顆永遠無法觸及彼此的星體般無法最終相守。《遠離塵囂》中,主人公奧克常常仰望著夜空明亮的星辰,“這變幻莫測的景致與宏偉的運動,竟然能夠為渺小的人類所意識”。遙遠的“星辰”象征著浩渺宇宙的詩意,這種詩意帶給平凡的人以不凡的意識,賦予了人類超越庸常的現實生活,以有限的生命觸及無限的可貴機遇。神秘的自然意象賦予了文本以詩性的美感,展示出作家超離于現實世界的浪漫遐思,以及充滿自由主義精神的“宇宙意識”。
哈代的小說因濃厚的鄉村情結與自然生態意識而具有獨特的質地,他以喻指豐富的敘事空間寫照了維多利亞時代后期的英國社會經濟結構之變遷,具有高度的現實主義價值。同時,哈代積極地擁入現代思潮與先鋒技法,以復雜的敘事結構和蘊意豐富的象征體系拓展小說的敘事潛能,取得了外部形式與內部思想的和諧,具有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