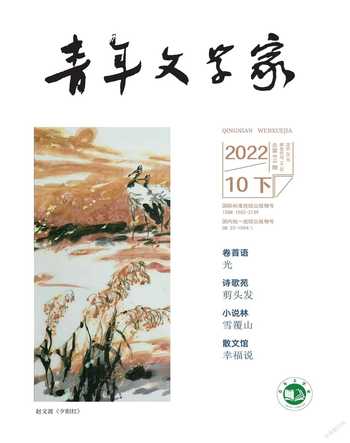用詩(shī)歌探測(cè)生命的溫度和深度
杜源

在《忽冷忽熱》的“編后小記”中,梁平提到某個(gè)年事已高卻仍然寫詩(shī)的詩(shī)人,稱贊他“這是詩(shī)人的氣質(zhì),這是一種永遠(yuǎn)的激情,永遠(yuǎn)的寫作狀態(tài)”,實(shí)際上梁平自己也是這種詩(shī)人。梁平說(shuō)過(guò)“生命就是我的一首詩(shī)”,他將詩(shī)拔高到與自己生命同等的高度,凸顯了詩(shī)歌對(duì)他的重要性,詩(shī)與生命同在,他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寫詩(shī),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寫詩(shī),對(duì)日新月異的社會(huì)寫詩(shī),寫詩(shī)貫穿他的生活,也成為他的生活,他用詩(shī)歌探測(cè)生命的深度和溫度。梁平從生活里各種風(fēng)光與事物中得到思考,反映在自己的詩(shī)歌里,在《忽冷忽熱》里,可以讀出他從任何外部事與物里牽扯出的詩(shī)意,這種詩(shī)意是自然風(fēng)光、社會(huì)事件投射出的,也是他內(nèi)心世界的現(xiàn)實(shí)倒影。
一、城市地理的溫馨記憶
作家的寫作總是打上地域文化的烙印。在梁平的詩(shī)歌中,我們經(jīng)常能找到重慶與成都這兩座城市的影子。在《回家》里,他寫道:“成渝高速/是我唯一不能感受飛翔的速度/橫臥在成都與重慶之間/混淆我的故土。”梁平作為在重慶出生成長(zhǎng)的詩(shī)人,二十一世紀(jì)初從重慶轉(zhuǎn)場(chǎng)到四川,在成都開(kāi)始寫詩(shī),主持詩(shī)刊,兩地輾轉(zhuǎn),因此他繼續(xù)寫道:“和別人不一樣/我在兩者之間無(wú)法取舍/從成都到重慶說(shuō)的是回去/從重慶到成都說(shuō)的也是回去……/我現(xiàn)在的身份比霧模糊。”“鄉(xiāng)愁”是想家的愁思,詩(shī)人將對(duì)家的情感投入在重慶與成都兩座城市里,一個(gè)是他的成長(zhǎng)記憶所在地,一個(gè)是他的事業(yè)立足地,兩地對(duì)他而言都意義重大,不管他從兩地哪方出發(fā)都可以稱為“回家”,兩地都能使他在“一個(gè)不陌生、識(shí)舊的、原有的地方從容安息”(江弱水《詩(shī)的八堂課》),因此他通過(guò)詩(shī)歌與兩座城市進(jìn)行心靈溝通與對(duì)話。家不再局限于城市的房子里,而在于城市中他留存的記憶與感覺(jué)。
卷一中幾篇有關(guān)重慶與成都兩座城市的詩(shī)歌都從城市里的一條街、一個(gè)景點(diǎn)展開(kāi)。城市的街道,只要是存在觸動(dòng)了他心靈的一景一物,他都在詩(shī)歌中有所呈現(xiàn),因此他的詩(shī)構(gòu)筑城市的特性框架,專注于城市風(fēng)光與文化的詩(shī)性書寫,從中挖掘出詩(shī)意。卷一開(kāi)篇三首詩(shī)是對(duì)成都自然風(fēng)光的書寫,龍泉山上的桃花引起詩(shī)人想象,“龍泉山第三十朵桃花/揭秘她的三生三世”。“我在樹(shù)下等待那年的承諾/等候了三十年/從娉娉裊裊到風(fēng)姿綽約/只有一首詩(shī)的距離。”(《又見(jiàn)桃花》)詩(shī)人從盛開(kāi)的桃花想到女子,女子也是桃花,桃花綻放是為了在春天守約,漫山的桃花落下花瓣雨,詩(shī)人又因?yàn)槿缬觑h落的花瓣?duì)縿?dòng)自己的內(nèi)心,對(duì)桃花、對(duì)自然、對(duì)美好萬(wàn)物的愛(ài)浸潤(rùn)著詩(shī)人。在景觀中,也有詩(shī)人心境的流露,“花好不在名貴,在于賞花人的心境”(《花島渡》)。花在自然中孕育,正如“我見(jiàn)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jiàn)我應(yīng)如是”(辛棄疾《賀新郎》),能否欣賞到花,在于人的心境,詩(shī)人“聞香識(shí)島,島上一次深睡眠/醒來(lái)就是陶淵明”(《花島渡》)。這種淡泊寧?kù)o的狀態(tài)正是詩(shī)人所追求的,在花島,他得以實(shí)現(xiàn)這種文人理想。成都的雪帶給詩(shī)人的歡樂(lè)與欣喜在于“奢侈更多時(shí)候不是過(guò)分享受/而是求之不得,而得”(《成都的雪》)。不常見(jiàn)的雪花每一粒都是珍貴難得的,下雪帶給人不常見(jiàn)的欣喜和快樂(lè),這種快樂(lè)蕩漾在城市里成為“豪華的抒情”。詩(shī)人的詩(shī)給現(xiàn)在的成都找回久遠(yuǎn)的歷史記憶,找到存在于成都以外的人文符號(hào),使讀者從詩(shī)中能真切地感受到成都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
關(guān)于重慶,詩(shī)人則更偏向于一種回憶,記憶中的農(nóng)田與荒野這些平坦之處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取而代之的重慶印象是此起彼伏的爬坡上坎,心境的袒露在于“面對(duì)任何一條路,只要心平氣和/都是坦途”(《重慶》)。城市的發(fā)展帶來(lái)了交通便利,“嘉陵江凌空的索道/高樓大廈穿堂而過(guò)的輕軌/不可思議之后,優(yōu)雅平鋪直敘”(《重慶》)。重慶在詩(shī)人不在的日子里迅速發(fā)展,詩(shī)人寫過(guò)關(guān)于重慶的《重慶書》,但對(duì)于重慶的變化詩(shī)人也不得不承認(rèn)“其實(shí)我對(duì)重慶也陌生了,上清寺/滄白路的光怪陸離,軟埋了舊年時(shí)光”(《重慶》)。這種幾十年帶來(lái)的變化使得一些回憶的發(fā)生變得措手不及,詩(shī)人論今從談古開(kāi)始,“北郊一個(gè)普通的山梁/名字很好,梁上飄飛的書香/在百年前那間茅屋里的油燈下/彌漫多年以后/從那根羊腸子的道上/走出一個(gè)秀才”(《讀書梁》)。讀書梁這個(gè)地名讓詩(shī)人賦予它一種文化內(nèi)涵,成為嶄新的文化符號(hào),然而城市化后的城市容納不了更多的人,于是房地產(chǎn)開(kāi)發(fā)到讀書梁,商業(yè)化將文化氣息沖淡。開(kāi)始談到重慶也是家,鄉(xiāng)愁是詩(shī)人對(duì)逝去的美好事物的追憶,但日新月異帶給詩(shī)人不同于以往的感受,城市化帶來(lái)的變異使人與人之間產(chǎn)生距離,人與城市也有著無(wú)法填平的時(shí)間縫隙,詩(shī)人在詩(shī)里穿過(guò)鋼筋混凝土筑造的森林去找到它被遺忘的過(guò)去,在城市化進(jìn)程中尋找喪失的傳統(tǒng)與記憶,以及詩(shī)意棲居的家園。
二、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冷靜觀照
城市化過(guò)程中必然帶來(lái)一些社會(huì)問(wèn)題,梁平作為一個(gè)有平民情懷的詩(shī)人,并不只是將自己的創(chuàng)作視野放在自然、人文景觀中。正如江弱水所說(shuō):“詩(shī)的主要功能是抒情,但它還需要敘述,也需要思想。”梁平認(rèn)為,寫詩(shī)就是要對(duì)自己負(fù)責(zé),對(duì)得起自己,因?yàn)檫@是寫作者的良知,自我的表達(dá),表達(dá)詩(shī)人對(duì)當(dāng)今社會(huì)的看法。他的詩(shī)歌用詞不算激烈,但總能直指出社會(huì)問(wèn)題的痛處,從單純描摹事件升華到事件帶來(lái)的感受與反思。
對(duì)于現(xiàn)代社會(huì)中一些真假難辨的聲音,梁平用“我確定應(yīng)該還有星期八,人神驗(yàn)證”來(lái)表達(dá)他的態(tài)度,“不然裝神的大行其道,忽悠方圓/真?zhèn)坞y辨,越來(lái)越含混”(《星期八》)。詩(shī)人嘲諷地提出一周少了一天星期八,因?yàn)榍捌咛於际怯缮系蹌?chuàng)造的,充滿一切美好、光明的事物,而星期八是混亂無(wú)序的,就像社會(huì)中各種流言蜚語(yǔ),這樣的對(duì)比用以剖開(kāi)社會(huì)虛偽的一面。同樣諷刺這種虛偽的還有《知水暖》,詩(shī)人借用蘇軾的詩(shī)句“春江水暖鴨先知”為依據(jù),用現(xiàn)代人的眼光進(jìn)行了批判,認(rèn)為鴨子下水只是本能,投映到現(xiàn)代社會(huì)里就是“假借和暗示習(xí)慣了/越來(lái)越覺(jué)得自己聰明”。詩(shī)句簡(jiǎn)單明了地描述出人自以為是和故作姿態(tài)的扭捏。
梁平關(guān)注社會(huì)生活,對(duì)新興的社會(huì)現(xiàn)象有自己獨(dú)特細(xì)致的觀察。在短詩(shī)《畫像》中,“畫像”指的是社會(huì)上人與人之間相互的評(píng)價(jià),即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樣子,這接近于創(chuàng)作中的“人設(shè)”一詞。網(wǎng)絡(luò)的發(fā)達(dá)讓每個(gè)人都擁有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機(jī)會(huì),因此“人設(shè)”已成為拋開(kāi)現(xiàn)實(shí)生活后網(wǎng)絡(luò)社交的一個(gè)重要元素,網(wǎng)上所見(jiàn)不一定為真實(shí)。在詩(shī)里,通過(guò)“畫像”這個(gè)比喻,梁平對(duì)這種現(xiàn)象加入了自己的審視:“根本沒(méi)有時(shí)間自我辨別,那些畫/無(wú)論蒙別人還是自己/反正都輕車熟路,信手拈來(lái)。”人們?yōu)榱讼嗷サ睦孢x擇說(shuō)假話,為他人“畫像”也為自己“畫像”,從別人口中了解到的都不是真實(shí)的自己,自己也永遠(yuǎn)不會(huì)反思,但是在直面真實(shí)的時(shí)候,才發(fā)現(xiàn)自己“鏡子里看見(jiàn)有白色顏料打翻/濺在鼻梁上,好有喜感”這種自欺欺人的丑陋。現(xiàn)代社交軟件的發(fā)達(dá),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聯(lián)系更加便利與緊密,但是,生活節(jié)奏的加快也增大了人內(nèi)心的空虛,“漂流瓶”等交友功能的出現(xiàn)和興起正依托于此。詩(shī)人認(rèn)為匿名的交友是“寂寞與寂寞的互動(dòng)”(《漂流瓶》),由此帶來(lái)的糾紛剛好印證了“寂寞都是誘餌,各種誘/一不小心就拽你沉入海底”(《漂流瓶》),體現(xiàn)出梁平對(duì)復(fù)雜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人際交往的警示。
梁平將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冷靜觀照轉(zhuǎn)化成詩(shī),從中尋找與建構(gòu)人類的精神家園,撫慰現(xiàn)代人飽經(jīng)滄桑的心靈。詩(shī)人對(duì)社會(huì)的審視絕不是消極的,他沒(méi)有使自己那顆真誠(chéng)的詩(shī)心消逝,而是將所觀所聞的萬(wàn)事萬(wàn)物的內(nèi)在意蘊(yùn)從詩(shī)中解放,轉(zhuǎn)化成為一種冷靜平和的力量,轉(zhuǎn)化為綻放在精神上的花朵。
三、生命本質(zhì)的詩(shī)意探尋
梁平曾說(shuō)過(guò):“我把詩(shī)歌的形式和技巧置于我的寫作目的之后,我更看重詩(shī)歌與社會(huì)的鏈接,與生命的鏈接,與心靈的鏈接。”他的詩(shī)歌中雖然存在想象,但詩(shī)歌內(nèi)容本質(zhì)上還是描摹日常生活和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寫實(shí)之作。《忽冷忽熱》中的不少詩(shī)作,就是通過(guò)對(duì)現(xiàn)實(shí)人生的詩(shī)意素描,來(lái)體現(xiàn)詩(shī)人倡導(dǎo)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當(dāng)下生活、真實(shí)生命和內(nèi)在心靈相互鏈接、相互影響并發(fā)生作用的詩(shī)學(xué)理念。
梁平寫過(guò)一些記錄和描述自己日常生活的詩(shī),通過(guò)這些詩(shī)歌剪影,我們拾起詩(shī)人的日常生活碎片,拼湊出詩(shī)人的生活狀態(tài),如《端午節(jié)的某個(gè)細(xì)節(jié)》:“詩(shī)人都在過(guò)自己的節(jié)日/我在堆滿詩(shī)歌的辦公桌上/把煙頭塞滿煙缸,把煙絲排成行/一行一行地?cái)?shù)落自己/數(shù)到第五行的時(shí)候,被迫打住/剛更換的靠椅顯得格外生硬。”作為詩(shī)人和詩(shī)歌編輯,閱讀和修改詩(shī)稿應(yīng)該是他最基本的工作了,這首詩(shī)交代的正是詩(shī)人梁平的工作常態(tài)。在《桌上江湖》與《老兄弟》里,梁平描述了生活中與朋友的交往最自然的狀態(tài):“我喜歡滿屋子蕩漾的快活/喜歡桌上沒(méi)大沒(méi)小沒(méi)規(guī)矩。”以及在兄弟面前“想說(shuō)的話口無(wú)遮攔,想做的事說(shuō)做就做”。這些都是梁平對(duì)自己日常生活的生動(dòng)描畫,但他從來(lái)不滿足于將詩(shī)歌放在只是簡(jiǎn)單敘述生活這樣一種淺層次上,而是從平凡生活的細(xì)節(jié)出發(fā),以小博大,積極思索生命的本質(zhì)與意義,于個(gè)人思考中總結(jié)出一些哲理穿插在詩(shī)歌字里行間,引起讀者共鳴。《端午節(jié)的某個(gè)細(xì)節(jié)》最后一節(jié)寫道:“窗臺(tái)看出去的街上,堵得一塌糊涂/我和城市同時(shí)胸悶、感到心慌/我們都不愿意聲張/粽子、黃酒以及府南河上的龍舟賽/與我們沒(méi)有關(guān)系。還是那個(gè)城市/我在等待另一個(gè)城市的電話。盡量保持/節(jié)前的那種安靜。端午節(jié)應(yīng)該肅穆/一個(gè)詩(shī)人的忌日,所有的人都快樂(lè)無(wú)比。”梁平將“一個(gè)詩(shī)人的忌日”與端午節(jié)“所有的人都快樂(lè)無(wú)比”加以對(duì)比,寫出了這個(gè)節(jié)日中存在的不合常理的悖論,一個(gè)人的犧牲在后世變成了一個(gè)節(jié)日,具有一定的諷刺意味。
詩(shī)集《忽冷忽熱》不僅呈現(xiàn)詩(shī)人的平凡日常生活,還可以看到詩(shī)人在詩(shī)歌里“向內(nèi)轉(zhuǎn)”的自我剖析。梁平作為詩(shī)人是真誠(chéng)勇敢的,這不只體現(xiàn)在他對(duì)社會(huì)問(wèn)題的揭露與批判上,還在于他通過(guò)詩(shī)歌展示了他自我的孤獨(dú)與寂寞這類一般人難以向大眾言說(shuō)的情感上,因此他從寫詩(shī)中挖掘更深層的自我。孤獨(dú)、寂寞是滲透在梁平詩(shī)歌中的一種感受和體驗(yàn),這種感受與體驗(yàn)給梁平帶來(lái)精神上的痛苦,可以說(shuō)正是因?yàn)檫@些痛苦,他才會(huì)寫出一些“向內(nèi)轉(zhuǎn)”的心靈詩(shī)篇。在《寂寞紅顏》里,梁平指出:“但我知道寂寞是我的紅顏/與我相依為命。”這首詩(shī)就像戴望舒的《我的記憶》一樣,把一種心境擬人化、具象化,把寂寞比擬成親密的紅顏知己—只有她與自己形影不離,也只有她能分享自己的秘密。這樣的寂寞又體現(xiàn)在親人、朋友離世上,如在《一個(gè)無(wú)法面對(duì)的日子》里,“突如其來(lái),突如其來(lái)/一句沒(méi)有任何鋪墊的應(yīng)答,比子彈/更迅疾地?fù)糁形业臓繏臁薄T?shī)人連用兩個(gè)“突如其來(lái)”克制自己的情感,面對(duì)父親的突然去世,梁平陷入痛苦的自責(zé)之中,“我無(wú)法面對(duì)這一天,手指犯賤/撥出一個(gè)不該撥打的電話”。他認(rèn)為是自己不同尋常的撥出電話導(dǎo)致父親的去世,再見(jiàn)面是面對(duì)父親的墓碑。整首詩(shī)里沒(méi)有一個(gè)詞在明說(shuō)痛苦,但讀下來(lái)全是自責(zé)、遺憾與痛苦,是詩(shī)人的一種克制帶來(lái)的情感體驗(yàn)。
然而,梁平不是一個(gè)面對(duì)痛苦就懦弱與逃避的詩(shī)人,在《人眼貓眼》里,“我”與俯臥翻轉(zhuǎn)的貓對(duì)視,“我和貓?jiān)趯?duì)視中的顛倒/貓可以順勢(shì)倒下,而我不能/決不”。在陌生的、顛倒的世界里,詩(shī)人不愿意妥協(xié),他要做一個(gè)堅(jiān)守原則,一個(gè)倔強(qiáng)的人。他甚至喜歡通過(guò)傷痛去體會(huì)生命的真實(shí)與快樂(lè),“我從來(lái)不吃沒(méi)有刺的魚/就好像,我不喜歡/沒(méi)有傷痛的快樂(lè)”(《魚刺》)。面對(duì)死亡這一沉重話題,梁平卻很曠達(dá)與平靜,“之所以為人,只有生前的事/清清爽爽,死后才干干凈凈/不求視死如歸,但愿了無(wú)牽掛”(《說(shuō)說(shuō)死吧》),與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存在異曲同工之處。可以發(fā)現(xiàn),梁平詩(shī)歌中對(duì)生命本質(zhì)的思考與尋覓總是伴隨著生命體驗(yàn)本就存在的艱難。梁平的勇敢和真誠(chéng)之處在于,他通過(guò)詩(shī)歌展示了他的脆弱、痛苦以及面對(duì)這些的勇氣和力量,而生命中無(wú)法避免的磨難變成了詩(shī)意,這種詩(shī)意讓他無(wú)論在什么情況下都能發(fā)現(xiàn)希望,享受生活。
梁平以簡(jiǎn)潔又飽含情感的話語(yǔ)探尋城市歷史與記憶,向外透過(guò)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種種現(xiàn)象剖析人性、觀照底層,向內(nèi)直面自我生命的痛苦與歡樂(lè),追求最真實(shí)的生命體驗(yàn),由此達(dá)到用詩(shī)歌探測(cè)生命的溫度和深度的高度。將個(gè)人感受與外部世界融合在詩(shī)里,這種內(nèi)外相結(jié)合所生發(fā)出的感受構(gòu)成了他的詩(shī)意,也體現(xiàn)了他的人生態(tài)度和藝術(shù)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