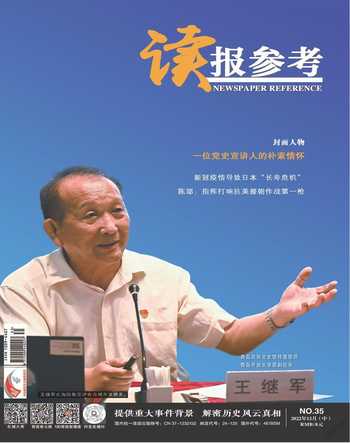網絡暴力的變與不變
馬玲清楚地記得2010年遭受網暴的感受,“好像站在一個小小的孤島上,黑色的浪頭從四面八方不停向我涌來”。 彼時,馬玲是國內知名雜志的文化主筆,受邀參與了某檔著名的綜藝節目。因為馬玲在節目中質疑主持人,網民指摘馬玲在綜藝中的“小丑”表現,馬玲的同事也在帖子里留言,編造她的工作細節和私生活。
這段經歷給馬玲的生活帶來了長久的余波,她在同一時期辭職和離婚,隨后在醫院確診了抑郁焦慮狀態。直到2013年,馬玲重新參加工作,避免把自己始終放在一個自閉的環境里,她才逐漸走了出來。
10多年里,越來越多和馬玲類似的人被網絡暴力吞噬,這個“怪獸”也顯現出越來越多新的特征。
大數據“加持”
2010年,互聯網BBS論壇是言論的主要匯集地,新浪微博才上線一年,剛剛開始流行。馬玲參與那一期節目的收視率沖上了同時段第一,而那檔綜藝擁有龐大的粉絲群,他們在天涯論壇里投入“戰斗”,反復咀嚼馬玲與主持人的互動。同事隨后的“爆料”讓網民對馬玲的攻擊擁有了更多現實生活的支撐,讓話題越炒越熱。
馬玲對記者說,起初她想用筆捍衛自己,她在博客上發表了長文章,從自己的角度復盤了錄制節目的前前后后,講述她的話語被曲解的部分,但這篇文章中的個別表達被摘取出來,繼續被曲解和指摘,成為她被攻擊的新素材。
不過,這起12年前的網暴事件沒有蔓延到更廣大的網絡空間,網民對于馬玲的攻擊許多都停留在天涯論壇內。馬玲回憶,后來她聯系過天涯論壇,那條“黑帖”就沒再出現在主頁上。
如今,網暴事件幾乎不可能只停留在一個平臺,而是會在多個平臺擴散。“女子取快遞遭誹謗”是近幾年一個典型的網暴案例。2020年7月,杭州吳女士在樓下取快遞時,被便利店店主偷拍照片和視頻,偷拍者在微信群聊里編造了“少婦出軌快遞小哥”的聊天內容,這些內容很快被轉發到了多個微信群、微信公眾號,以及微博、抖音等平臺,引發多個平臺的網民發表侮辱性評論。
過去10多年里,中國互聯網用戶的數量迅速增加。海量的平臺為超過10億互聯網用戶提供著各種細分方向的內容,從文字、圖片到短視頻、長視頻,再到直播。互聯網平臺的迅速發展,也為網暴信息的跨平臺傳播提供了基礎。
平臺用以吸引用戶的技術手段,也在某種程度上促使網絡暴力的發生。
進入社交媒體時代,在技術支持下,平臺得以計算每個人的喜好,再據此分發推薦內容,這種“投其所好”的內容可以增加用戶黏性,但也造就了“信息繭房”。
而大數據加持的精準推送真正在實踐中大規模應用,是近幾年的事情。此前的推送邏輯是“給你我想給你的”,而不是“給你你想要的”。兩者在網暴上帶來的不同是,相比以前,當下的網暴相關信息,更容易推給那些容易實施網暴的人;而以前推給的那些人,很可能對網暴無動于衷,這會造成網暴烈度的巨大差異。
紫茄在2019年遭遇了一場意想不到的網暴。那一年,曾被確診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的他因為工作與家庭的雙重壓力,“心里那根繃得特別緊的弦斷掉了”。那年2月的某個下午,紫茄吞下了300多粒安眠藥,躺在床上等待的過程中,他拿起手機,發了條微博,只有兩個字“再見”,發完微博后,他就失去了意識。紫茄的朋友看到了他的微博,報警之后,還轉發了紫茄的微博,微博被轉了幾千次,上了熱搜。紫茄很快被送到了醫院。一個星期后,紫茄辦理出院,再度登錄微博,卻發現微博充滿了謾罵的留言。甚至有人給紫茄打電話,“電話里那個人告訴我,如果要死,就不要占用公共資源,真正想死的人都是沉默地離開,我這樣子明顯就是作秀”。
紫茄說,那段時間網絡上有許多新聞反轉事件,如果在網上直播自殺的人被挽救,關于作秀的質疑也會層出不窮。紫茄認為,別人可能也對他作了這樣的判斷。
現在回憶起那段經歷,紫茄開始作一些理性的總結。他如今供職于互聯網企業,了解推薦算法背后的邏輯,“有的時候,和流量比起來,價值觀不那么重要”。
網暴的成本越來越低
自2000年初出現的人肉搜索,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網絡暴力的重要表現形式。人肉搜索意味著通過對被搜索人信息的披露,實現對被搜索人的懲罰。而相比10年前,獲取個人信息的難度已經顯著降低了。
2013年被稱為中國的“大數據元年”。隨著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個人信息不斷地被收集、挖掘、分析、傳輸,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隨之增加,而人們實際上無法左右別人收集和使用自己信息的行為。
中國政法大學網絡法學研究所所長李懷勝表示,在大數據時代,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智能穿戴設備的廣泛使用,特別是全網用戶實名制的推行,個人信息的搜集更加頻繁和密集。
在大數據時代,因個人信息泄露導致或加劇的網絡暴力事件層出不窮。2020年12月,成都公布了3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其中,趙女士的活動軌跡很快引起了網民的注意——近14天內,她前往過多個酒吧,也去過公園、美甲店、麻辣燙店。有關趙女士活動軌跡的微博評論區,充滿“轉場皇后”“一人之力,干翻整個成都”等嘲諷性回復,趙女士的身份證號、居住地、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很快也被扒了出來,網民對她的私生活展開了猛烈的攻擊。
個人信息泄露對于網絡暴力的助長,還體現在一些不易被察覺的聯系上。
李懷勝長期研究網絡犯罪,他對記者說,網絡黑灰產業的源頭實際上就是個人信息泄露,不法分子可以利用個人信息做很多事情。例如,水軍公司就會大量收購個人信息,用個人信息批量注冊賬號,這些賬號外表上看不出什么問題,但它們都是網絡水軍,一旦得到指令,就能有組織地左右話題的方向,煽動大眾情緒。
實際上,10多年前的網暴事件就已經有水軍推波助瀾的痕跡,但由于缺少大數據的加持,水軍產業鏈不完善,水軍所能造成的影響相比當下要小得多,也很容易滅火。
馬玲記得,2010年經歷網暴時,最初,她認為事情是網民自發推動的,但后來就覺得不對勁了。她說,當時有組織的水軍與“散兵游勇”不同,后者基本只是單純地謾罵,而有組織的網絡水軍是有導向的,既有歪曲抹黑的話術,也有層出不窮的攻擊點,看起來很有章法。后來,馬玲找了一位在電影圈經常組織水軍的“大牛”,請對方交涉,果然令天涯的“蓋樓”速度緩和了下來。
不過,無論網暴發起者挖掘他人隱私的方式和引導話題走向的工具發生了什么變化,唯一不變的是網絡暴民借以攻擊他人的話術。
? 從2010年的馬玲,再到2020年的成都趙女士和杭州吳女士,網暴者攻擊她們的話術幾乎一脈相承——羞辱外貌、貶低能力、人品辱沒,統一使用的手段是“造黃謠”。這些話術和手段總是能夠奏效,引發暴力的狂歡,讓她們遭遇“社會性死亡”。
2010年的網暴風波過后,馬玲曾想過起訴,但先前打官司的經歷,讓她認為令網暴者承擔法律責任十分困難,加上考慮到起訴要消耗時間和精力,她最終放棄了通過司法手段維權。
中國立法對于網絡暴力的規制力度在不斷增強。隨著立法的完善,越來越多網暴受害者開始尋求司法的救濟。2018年,在被網絡放大的辱罵聲中,四川德陽的安醫生自殺了,肇事者因侮辱罪獲刑。2020年的“女子取快遞被造謠案”,在檢察院介入下,誹謗的刑事自訴轉為公訴,造謠者承受了刑罰。
但如今,在針對個體的網絡暴力中,通過刑事自訴維權獲得立案的仍是少數,大多數是通過民事訴訟起訴對方侵害名譽權。
(文中馬玲、紫茄是化名)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張馨予、苑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