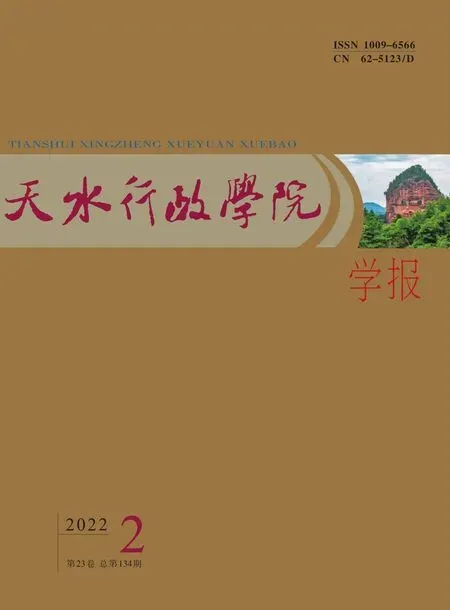行政執法案例指導制度反思與重構
蔣凌濤,查紫宴
(廣西大學法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4)
在《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1-2025 年)》之中,明確了在法治政府建設之中要將建立行政執法案例指導制度。建立行政執法案例指導制度的探索,已有十余年,從遼寧省試點到湖南省建立《湖南省行政執法案例指導辦法》其雛形已經呈現。但是,其中的問題卻一直存在,且發展止步不前。從設立主體、指導案例的法效力、指導案例公開與否到指導案例的內容、發布的頻率,各地均沒有統一[1]。行政執法具有極強的個別性、地域性,基于一般性的統一標準與基于個別性的自由裁量之間的緊張關系必然存在。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本應當成為連接法律與社會、抽象與具體、一般與特殊的“橋梁”。然而,在實踐之中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卻往往沒有全面回應案件之中涉及的定性、定量的裁量問題。在發展之中,典型案例與指導案例之間的關系缺乏明確區分,模糊了指導案例應有的內容。此外,對于指導案例的法律效力的理論探討之中,學者們多希冀將指導案例司法解釋化,成為抽象的規則[2]。但是,實踐中執法的具體情形千變萬化,指導案例如果成為明確的抽象規則,又該如何面對新出現的具體情形?矛盾之下,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需要進行系統重構回應這諸多問題,形成能夠發揮自身特性的有效制度。本文力圖揭示行政執法案例指導制度目前在實踐中和理論上遇到的矛盾,并對這一制度進行重構,以期重塑其“橋梁”功能。
一、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現下的問題
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在實踐之中,本意是針對行政自由裁量的問題。在行政執法中,行政機關存在著很大的裁量空間。例如,在《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的,對于可以進行處罰的其他尋釁滋事行為行政機關也能處于拘留、罰款等處罰措施。這些具有較大解釋空間的法律賦予了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之中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自由裁量的能力。但是,這也就導致在實踐之中,行政機關可能超出人們對法律的認識范圍行使自由裁量權。體現在一些事件中,人們就會對一些行政執法的標準產生質疑。規范行政裁量權,是我國法治政府建設的重要一環。實現法治政府,要將權力鎖在法治的籠子里,也就必須要讓裁量的基準為人所知。然而,這一制度在各省試點以來,卻漸漸成為雞肋。一方面,執法指導案例淹沒在各種不同類型的案例之中;另一方面,執法指導案例自身內容也不規范,從而導致功能喪失。
(一) 各執法案例混亂無序
指導案例制度本就意在將法律的抽象規定與實踐的具體尺度關聯起來,解釋行政自由裁量定性、定量的基準,從而使生澀的法律用語變為人民群眾容易理解的生動實例。以案說法,也是中國歷史上傳承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為人們傳頌的案例往往承載著天理、國法、人情的統一[3]。但是,在實踐之中,案例卻常常只是成為新聞介紹而非指導案例。一方面,實踐之中,不少地方仍未推行制度化的指導案例機制,而以非制度化的典型案例代之。然而,指導案例本身的規范化意義在于描述行政裁量基準。但是典型案例卻并沒有明確的制度形式,在說理程度、案例內容等方面缺乏固定的形式,無力規范自由裁量權。另一方面,在已經出臺的執法指導案例之中,對行政自由裁量的約束也缺乏穩定的結構,在定性、定量的問題上往往回應不足、缺乏說理。
典型案例相較于指導案例,是一個更為普遍使用的案例介紹方式。同樣是案例,由于缺乏明確的制度體系,導致典型案例在內容上往往是新聞式的敘述而非案例分析、裁量的說理。以廣西壯族自治區2021 年9 月公布的安全監督執法典型案例為例,其中一則案例敘述了平樂縣執法人員發現一家企業使用了不符合國家標準的管道,由此對其進行12 萬元的處罰。案例之中,對行政處罰為罰款12 萬元,行為如何定性均未作詳細的論證、分析。這種典型案例從內容上看,因為沒有討論裁量事宜,所以根本不可能成為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方式。而且,人們也難以通過了解此類案例而認識行政機關的執法標準。與之相反,指導案例則必須具有相應的分析、說理,不能僅僅只是新聞式的介紹案情。
但是,在不少地方,由于缺乏對指導案例的立法,導致典型案例就充當了指導案例的作用。甚至,即便在地方有立法的省份,由于指導案例的出臺由于需要更加復雜的手續,行政機關也就更喜歡以典型案例來替代指導案例,作為日常的案例介紹方式。由此一來,通過案例的方式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功能,就受到了非制度化的典型案例的困擾。對于一般民眾而言,本來就不清楚指導案例與典型案例有何不同,何況從詞義上看,“典型”一詞本就蘊含指導的意義。然而,在內容上不反映行政裁量的基準的典型案例,就難以對民眾、行政機關真正產生指導的作用。當然,可以辯解稱兩種制度本就存在差異。可是不指導的典型案例淹沒之下,指導案例的價值就會被稀釋,諸多的典型案例將形成對指導案例的干擾。而且,典型案例的發布由于與指導案例不屬于一個體系,兩者之間一旦產生沖突還將危及行政機關的公信力。
(二) 執法指導案例功能缺失
指導案例的功能缺失,則是指現行的指導案例制度并不能有效發揮出它規范行政裁量權的功能。在實踐中,主要體現在指導案例的數量、范圍、內容三個方面。
從數量上看,指導案例的數量與現實中執法案例的數量不成比例。事實上,行政執法之中,每一類案件都應該發布合適的指導案例。因為,幾乎每一類案件都存在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間。無論是定性還是定量,自由裁量的合理性都應當要予以說明。通過具體案件的說明,才能使相對人充分了解行為違法事實與執法裁量之間的關系以及執法裁量是否合理。然而,行政指導案例的數量,卻極其有限。以行政案例指導制度發展的較早的河南省為例,經過層層選拔在2018 年頒布了十大指導案例。相對應于一年所產生的行政執法案件而言,每次以“十”為數量級進行篩選的指導案例就顯得難以匹配。
誠然,數量并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如果足以覆蓋所有的執法種類,數量上略低一些也并不影響指導案例制度發揮作用。而且,執法指導案例制度發展快的省份早年間也發布了不少的案例。但是,行政案例指導制度在范圍上同樣存在明顯的不足。有學者統計了長沙市2012 年到2016 年發布的指導案例,其中涉及公安執法的,僅在尋釁滋事、交通肇事、特種行業許可三個事項上[4]。從湖南省益陽市的文件更是可以看出,地方的典型案例如果能夠成為指導案例,會作為政績進行宣傳。在篩選制之下,非基于執法需要而是以選拔的方式所設立指導案例顯然難以覆蓋執法的方方面面。有學者收集了湖南省400 個指導案例進行分析,然而卻發現其中不少案例所描述的裁量問題竟然是重復的[5]。從《湖南省行政執法案例指導辦法》來看,指導案例的篩選是一層一層的從縣到省逐步進行。但是,如果每次都以“十大”或類似的數量進行限制,那么全省示范性的指導案例,恐怕永遠都不可能覆蓋執法的需要。而且,作為地方政績的指導案例,就不得不考慮成為全省指導案例的價值從而忽視自身的特殊性需求。由此一來,行政案例指導制度在實際運行之中實際上就更重于形式而輕實質。
最重要的是,在已經出臺的行政指導案例的內容上,也沒有做到對執法裁量的明確解釋。不僅是市縣一級的指導案例,甚至是國家知識產權局的指導案例,都沒有很好地實現對案例中存在的裁量基準進行有效說理的問題。在國家知識產權局2017 年發布的文物行政執法指導性案例之中,第一則案例是對一起在北京靈光寺控制范圍內的違章建筑的處罰案件。在指導案例之中,僅說明了處罰所依據的法條,而沒有說明在自由裁量的幅度(5-50 萬) 中為什么選擇了30 萬。這絕非冰山一角,而是行政執法指導案例的典型。甚至,它對于適用法律的說理程度,已然遠超那些僅僅列出法條或者甚至連法條都不列出來的典型案例。
功能缺失的執法指導案例制度,如同在軀殼之中缺少了靈魂,那個以實現行政裁量合理化為目標的理想。如果這是一項剛剛出現的制度,或許我們可以認為是實踐不足、經驗不足導致的問題。然而此項制度已然問世超過10 年,不得不問的是,什么原因讓它止步不前?
二、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的應然價值
價值上不厘清,制度實施上就會陷入迷惘。例如,有的學者在分析行政案例指導制度時將其列入內部制度的范圍,但又希望其必須公開。有的學者,希望把它變成省一級統一規范的類司法解釋,但又想要它能夠注意到地區的執法特征[6]。正因為,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的價值追求在一開始就沒有完全明確,所以在發展的過程中才會畏畏縮縮,才會流于形式。所以追本溯源,我們需要重新考量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的價值,從而為重塑其功能找到支撐點。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是通過對案例的釋法說理,以明確行政機關的裁量標準。在統一執法標準的要求下,這種以具體案例對執法標準進行闡述的指導案例就具有一種“橋梁”的價值。首先,它可以連通抽象的法與具體的案件,從而解釋行政機關的執法標準。其次,它可以協調地域的差異、領域的差異,為執法差異下的自由裁量提供明確的標準。最后,它可以將自由裁量曝光于天下為民眾所理解,從而使社會監督成為可能。
(一) 釋法價值:溝通抽象與具體
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的釋法價值是指通過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對抽象的行政立法從執法主體、執法程序、執法手段等方面進行明確具體地解釋與說明,從而解釋行政機關的執法標準,以此來統一法律的適用,做到“同案同罰”。
2020 年3 月浙江省杭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發布了《杭州市市場監督局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其中的2 個口罩類執法案例較為準確地詮釋了行政執法指導案例的釋法價值。在“某藥房涉嫌經營未取得醫療器械注冊證和商標侵權的第二類醫療器械案”中將“某集團有限公司生產”實際生產時間晚于標注的銷售生產時間的的口罩,依據《醫療器械說明書和標簽管理規定》認定為涉嫌經營未取得醫療器械證的第二類醫療器械,應當按照《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 第六十三條第一款之規定予以處罰。在“某商行涉嫌銷售無中文標識的口罩案”中將沒有任何中文標識的用普通自封袋和塑料袋包裝的口罩,依據《產品質量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第(二) 項的規定認定為普通商品,并按照《產品質量法》第五十四條予以處罰。后一個案例厘清了作為醫療器械的口罩和作為普通產品的口罩的法律界限,厘清了作為非醫療器械的普通口罩的無中文標識違法行為的法律適用,將抽象的法律適用到具體案件中不僅能夠破解基層執法疑點難點案件,而且有利于整治聯合執法過程中執法主體不清晰、執法程序混亂、執法手段不合理、越權執法等問題。
(二) 協調價值:溝通一般與特殊
同案同罰還要顧及一般與特殊,在行政執法之中,地域差異、行業差異等等的特殊性是不容忽視的。然而,法律是一般規定,不可能在規定中面面俱到。正因如此,法律才會賦予執法者一定自由裁量的幅度來應對各種差異。
然而,這種自由裁量如果不能有效地基于合理差異進行,而是隨意裁量,則依法行政將僅有形式而無實質。在一般與特殊之間,行政裁量講究的就是實質的公平、合理。可是,要體現這種合理性,至少需要一個載體。如果抽象成規則,難以真正覆蓋實踐中那諸多的個別性,被忽視的特殊性就將影響規則的實質公正。而執法指導案例,則可以反映出行政機關在執法中考量的特殊性與一般性的關系。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間,杭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對惡意哄抬口罩價格的商家從重處罰。在其發布的指導案例中,它就明確指出行政機關考量疫情的特殊性與一般情形的差異,從而為從重處罰提供了依據。在裁量幅度內為何重、緣何輕,從一般到特殊,執法指導案例就具有特殊的協調價值,能夠把兩者連接起來形成有效的說理。
(三) 監督價值:溝通法律與社會
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將行政裁量的過程完整的揭示出來,法律就從紙上的文字躍居為實踐中的案例。人民群眾閱讀指導案例,就可以了解行政機關在法律授權下的裁量過程,就可以認識行政機關的裁量依據,同樣監督也自然產生了。
一旦,人們認為行政機關沒有合理的實施行政自由裁量權,那么人們就可以對行政機關在具體案件中的裁量結果與指導案例所設立的裁量基準進行比對、批評。人們可以對行政機關出現的不當裁量的情形有依據、有針對地尋求司法救濟或是行政監督、監察監督。一旦,那曾經在社會彼岸的行政自由裁量權被指導案例這座“橋梁”所打通,社會對權力的監督就將自然實現。監督也將促使行政機關在每一次裁量之中都以審慎的態度對待裁量。由此一來,社會上那些權力尋租的空間也將被極大壓縮。違法者不能再通過權力尋租的方式獲得行政裁量上的特權。正如一起醉駕案件中,民警由于執法正在直播,嚴厲警告企圖找關系的違法者:“你說任何人的名字,都是在害他。”公開的執法之下,權力被束縛住了。執法指導案例制度,恰恰就是要用制度化、體系化的方式把執法的裁量基準真真切切地擺在陽光之下,擺在社會的監督之下。
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的這座“橋梁”,對準的就是法治道路上的那條湍流,那條不為人知的卻又有法律賦權的行政自由裁量的湍流。
三、行政執法案例指導制度的重構
重塑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目的就是要讓這一止步不前的制度煥發出它應有的價值,發揮它那些獨特的“橋梁”功能。要實現這些功能,就應對每一類行政執法案例中的裁量依據進行說理、解釋,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執法案例之中真正感受到公平正義。以案說法,將行政裁量的基準大白于天下是行政執法案例指導制度應有的使命,是這一制度的靈魂。
(一) 效力上的重構
制度的重構,首先就要旗幟鮮明地回應它應有的效力。不少地方也困擾,行政執法指導案例以及諸多典型案例,在執法實踐之中究竟該有什么樣的效力?學者發現,這種案例的效力似乎難以言說,所以就提出需要增強行政執法指導案例的拘束力[7]。因為學者不清楚究竟該增強成何種法效力,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拘束力”這個概括性的詞來替代。這種效力上的不清不楚,就導致了實踐中參照適用的左右逢源、靈活變換。實踐之中,行政機關并不愿意公布那么多詳細的指導案例、典型案例,往往含糊其辭以新聞形式代之以防出現自我矛盾。即便在一些實施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較早的省份,也難以全面檢索其歷年的指導案例。明確效力,就是這一制度的發展最直接的突破口。
要厘清行政執法指導案例的效力,首先要明確它的權力從哪里來。對此,著名學者陳興良教授認為:“從成案向定例轉化的中間形態,指導性案例則成為新的規則載體。”[8]指導案例,設立了新的規則嗎?與其說設立新的規則,不如說是把實踐中的裁量基準公布了出來。一項需要自由裁量的事項,行政機關必然要通過某些裁量基準作出最終的判斷。然而,這種裁量基準如果不為人知,那么行政裁量的合理與否就難以判斷。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以規范行政自由裁量權為最初目的,就是要用案例作為黑暗中的那一雙追逐光明的眼睛。透過這雙眼睛,我們就能看清行政機關裁量的尺度何在、基準何在。
所以,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的法律效力,就應源自于執法所依賴的法律、法規的授權。法律授權了自由裁量的范圍,行政機關在指導案例中就有權且有義務提出自己在裁量范圍內基于何種具體標準。由于行政權力的垂直管理,上級行政機關有權力對這種自由裁量的基準進行修正,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監察機關、乃至全社會就有權對此進行監督。所以,行政執法指導案例,本身并不是一種新的權力,在實質上就是行政機關被法律、法規所賦予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具體體現。然而,一些學者認為指導案例的效力在于參照適用是應當還是可以[9]。可是,事實上,參照適用這種靈活的方式,本身就會把裁量基準的價值給沖淡。作為行政機關自己作出的裁量約束,不僅是要參照,更是要遵循。遇到例外,需要打破已有的裁量基準時,需要明確的說理、并通過合理的程序進行裁量基準的修正。由此一來,行政機關的裁量就被約束了,肆意的裁量是拿不出理由對裁量基準進行修正的,更是難以逃脫對權力的監督。
(二) 內容上的重構
在內容上,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必須牢牢圍繞著裁量基準這個關鍵點。只有在內容上詳細就案件中行政機關所有裁量的事項統統說明,才能讓指導案例真正起到指導的作用。之所以行政案例指導制度發展遲緩,其中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它在內容上過于保守,不愿意將行政機關真正裁量的思考過程展示出來。尤其是那些人們最困惑的裁量,比如罰款的金額幅度、尋釁滋事的認定標準、拘留的時間長短。只有真正在案例之中對每一個裁量點進行完整的說明,案例才具有發揮效用的可能,也才能真正成為聯系法律與社會、抽象與具體、一般與特殊的“橋梁”。
它相較于一般案件承載了更大的義務,既描述清楚行政機關的裁量基準。裁量基準的明確,才能使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從任意到理性,從不可知到可知。所以,在這一點上,它所具有的法治價值不容小覷。正因為,它作為裁量基準而存在,那么行政機關如果違背自己提出的裁量基準,就必須有相應的特殊理由。裁量基準的效力既在于此,強制行政機關統一執法標準,一旦超出標準必須要有理由。一旦提出理由,便是對基準的修正,同時公開的裁量基準,就可以受到司法、監察、社會的多方監督。把權力放在陽光下運行,就是把它鎖進籠子里的方法,這也是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應有的使命。
所以,指導案例的內容不僅應該矯正那種新聞式的介紹,而且要在說理上下硬功夫。行政指導案例的說理,需要以“橋梁”價值為指引。在說理之中,首先要體現行政機關就裁量事項如何定性。明確定性之中的考慮的事實變量因素,行政機關適用不同法律的理由,這樣指導案例的受眾才能通過類比指導案例推測其他案件的裁量過程。這種看似復雜的操作,其實行政機關是能夠做到的,在實踐之中一些行政機關已經作出了嘗試。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機關僅有法律授權內的裁量能力,不能超出裁量范圍設立法律解釋。也就是說,行政機關應嚴守文義解釋的要求依法執法,不能以行政指導案例作為逾越法律授權的工具。此外,行政機關還必須對裁量內容的定量問題進行解釋。行政機關需要描述,在區間內作出定量的判斷依據,并分析不同事實情節的影響,尤其是具有特殊性、地域性的不同影響。這樣,行政執法指導案例,才真正能夠將基于個別性、地域性的自由裁量的呈現在人們眼前。確定基準,批判和進步的空間也就自然出現了。遲緩的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才能重新煥發活力。
歸納而言,在內容中必須以詳盡的裁量分析取代以往簡略的介紹。只有把裁量的過程充分地表達在指導案例之中,指導案例才真正擁有靈魂。
(三) 體系上的重構
確定了效力、內容之后,更重要的一環出現了,如何建立行政執法案例指導制度體系?換言之,這種將行政裁量過程公之于眾的方式在實踐中如何實現?湖南省的實踐經驗是值得總結的,湖南經驗中,最需要反思的就是層層篩選的案例形成機制與形式化的指導案例體系。在實踐中,既然指導案例制度針對的是各執法機關的執法裁量問題,那么事實上各機關都應該就所有裁量事件有自己的基準。既然有自己的基準,這種基準就應當為人所知。而指導案例本應承載這一功能。
所以,指導案例制度,在實踐之中應當成為每一個有執法權的行政機關的義務。對機關所作出的每一類執法情形,都應當作出反映自己裁量過程的指導案例。指導案例,絕不僅僅是一種內部參考的資料,而應當充分地公開。把裁量權放在陽光之下運行,是這一體系發揮作用的關鍵一環。但是,學者或許存在疑惑,認為基層行政機關可能難擔重任。尤其,在執法權下放鄉鎮之后,鄉鎮執法能力受到了學者的諸多質疑[10]。但是,正是由于鄉鎮一級行政機關的行政能力受到質疑,它才更應該通過指導案例,明確其裁量過程打消人們的質疑。如果害怕能力不足犯錯誤,就躲起來,那么能力上的問題就會永遠得不到解決。事實上,直面問題、解決問題更是行政機關的政治要求,實事求是本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所在。
而且,一旦裁量過程通過指導案例公開,批評與進步就將成為必然。首先,基于行政機關的垂直管理,可以要求下級行政機關將指導案例向上一級行政機關備案的方式接受內部的檢察。此外,由于指導案例的裁量基準公開,在實踐之中,司法、立法、監察機關就可以有針對的進行監督。當然,更重要的一點,則是人民群眾得以了解行政機關在每一類案件中的執法裁量基準。至此,一種具有功能實現、權力監督、自我完善的良性體系則將建成。
四、結語
在《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1-2025 年)》的要求下,沉睡已久的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終將蘇醒。盡管過去的十年中,它未能全方面地展示出應有的法治功能,未能將行政自由裁量的權力清晰地擺在人們的面前,甚至在諸多非制度化的典型案例展示之中迷惘了。但是,經歷波折的行政執法指導案例制度,在依法行政、在依法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背景下,一定能重新煥發出它應有的光芒。它應是那座“橋梁”,連接著法律與社會、抽象與具體、一般與特殊的“橋梁”,那座連接著法治政府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