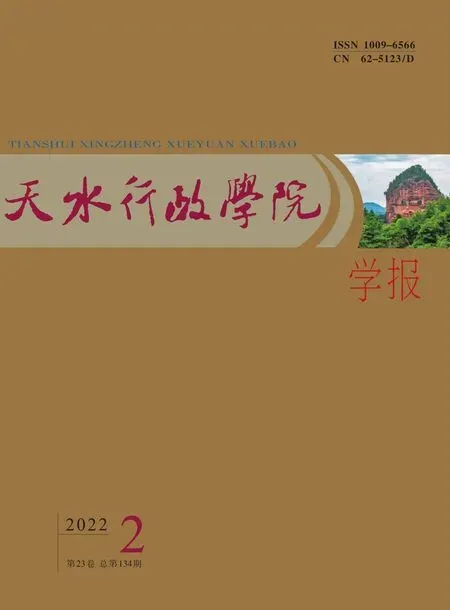如何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執法決定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功能主義行政執法的內在邏輯與風險控制
劉 翀
(中共蕪湖市委黨校,安徽 蕪湖 241000)
一、引言
習近平法治思想強調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1]。行政執法決定面廣量多,與普通群眾關系最為直接緊密,因而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執法決定中的公平正義極其重要。現代的行政執法都是在復雜的社會背景下展開的,普遍受到法律功能主義的影響甚至支配。法律功能主義的出現是為了回應現代規制國家所承擔的多樣且復雜的導控任務的需要,它要求對法律作工具化的處理,使之能在相當大程度上服務各種政策性要求。與法律功能主義范式相因應的功能主義行政執法進路有合理性,但功能主義的執法對目的、目標、政策、后果、立場等的強調,很容易將法律徹底工具化,從而導致權利被虛化,規范被懸置,法治價值被消解等問題的產生。從執法實踐來看,功能主義的執法在實踐中制造了一些頗有爭議的案例,其中部分案件執法結果的社會可接受程度較低,有些還引起了不小的網絡輿情風波。為了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執法決定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有必要對功能主義的執法進路進行恰當的反思,并對其中可能存在的風險進行有效的防范和化解。
二、功能主義行政執法進路的內在邏輯
功能主義執法進路的出現大致遵循了這樣一種內在的邏輯,即社會的復雜化發展,特別是現代風險社會的到來使得政府承擔的導控任務變得嚴峻復雜,法律需要以一種實質化、工具化的功能主義姿態來回應現實社會的變遷和滿足政府導控任務的需要,法律中的許多權利在這一過程中被相對化,從而為各類系統功能迫令的進入提供了后門。在這一進程中,法律的功能化發展及由此所導致的權利的相對化是理解功能主義執法進路的兩個關鍵方面。
法律以規范的形式表達社會生活條件,規范的背后則是更深層次的價值判斷。在傳統的形式法理論中,法律是一個封閉自足的體系,手段與目的、規范與價值都是融為一體的。一方面,法律作為一個封閉的體系,與倫理道德及政治生活等的要求是相對隔絕的,法律體系融會貫通且涓滴不漏,正確答案經由演繹推理而來,無須假于外在的因素。另一方面,形式法在功能上是自足的,其自發的運作一定能夠實現背后的價值訴求,例如預測行為、穩定預期、保障自由、限制權力等等[2]。這種形式主義的法治在歐陸以“概念法學”為代表,在美國則源于“普通法的形式主義化”發展。由于形式法視法律為科學,法律問題像科學問題一樣總有確定的答案,且答案可在形式法體系內經由邏輯推演而獲得,因此法律只具有弱的工具性,法律從總體上呈現出高度自治性的特征,在適用中強調的則是“嚴格規則主義”,其功能主義色彩不明顯。德國著名學者韋伯就曾這樣描述形式法治之下的司法過程:“就像是個法的自動販賣機,人們從上頭丟入事實加上費用,他自下頭吐出判決及其理由。”[3]韋伯的這個比喻雖然針對的是司法,但形式法體系下的執法活動也大致如此。
但形式法所預設的那幅自由競爭、公私二分的理想社會圖景在晚近以來漸趨幻滅,社會的日益復雜化發展使得形式法的“科學體系”左支右絀漏洞百出。為了應對越來越嚴峻復雜的社會導控任務,形式法遂朝著實質化方向發展。“實質化的法對法律采取工具主義態度,視法律為在具體情境之下達致特定政策與目標及落實國家價值偏好之手段。”[4]為此,現代法從形式到內容都出現了許多新變化。例如法律在相當大程度上是開放的,即法律不再被當成一個自足封閉的體系,法律外的因素通過對目的與后果等的考慮源源不斷地進入到法律之中,規則經常據此被重新解釋,曾經明確的規則可能會受到目的或后果等的擠壓而變形甚至面目全非。再如法律中的一般條款和不確定概念與日俱增。一方面,這些抽象條款和不確定概念使得法律得以應付變動不居乃至出人意料的情境;另一方面,實質性的價值判斷很容易借助于這些一般條款和抽象概念的適用而得到滿足。法律適用的過程也因此充滿了功能主義考量,而當這種功能主義被推向極端,法律的適用就有可能會出現只有立場而毫不顧及手段是否恰當或只有價值判斷而完全無視規范是否被遵守之類的現象。
法律的功能化發展反映到現代法對權利的保護上。在形式法所投射的那個社會結構中,權利主要涉及的是個人與政府間關系,在性質上帶有明顯的防御性色彩。之后,國家機器的任務由最初的形式法治下的秩序維持轉換到實質法治下對社會補償的公正分配再到集體性危險情況的應對,在這一變遷過程中,權利的性質也逐漸發生了變化,權利不再是不可克減的,其行使日益受到競爭性價值判斷的限制。功能主義的論據也因此被釋放出來并在與權利的競爭中不斷地開疆拓土,迫其簽訂城下之盟。這些功能主義的論據包括國家安全、秩序保障、公共利益、集體福利、經濟效率、政府權威、行政的權宜與便利乃至大眾情感的撫慰和輿情的平息等等。它們或者作為目的性因素,或者作為結果性考慮進入個案的法律適用,情境化地影響著對權利及相關法律規定的詮釋。許多行政執法案件的背后正是這樣一種功能主義的執法進路在發揮著支配性的作用。
而與司法相較而言,行政執法領域的功能主義進路又表現得更為突出,這與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密切相關。第一,在我國,絕大多數的法律、法規和規章都是由行政機關來負責實施的;第二,行政權力更可能會逾法而行甚至脫法而行,即便不是如此,現代社會政府導控任務的爆炸式增長使預防性規范無力調節,行政權力會進行“自我編程”,從而有“獨立于邊緣化的立法部門而自成一體之勢”[5],進而在立法之外另行設定功能性目標;第四,司法機關相較行政機關來說受到了更多的制度性約束,系統的功能迫令更容易直接傳導給行政部門;第五,行政執法通常不像司法那樣進行詳細的說理,因而更可能受系統功能迫令的驅動。
三、功能主義行政執法進路的風險控制
在當下,行政執法的功能主義進路有內在的邏輯,是現代國家和法律在面臨日益嚴峻的社會導控任務時的一種必然反應。但這種功能主義的進路會導致一些問題,如法律中的權利被虛化,規范被懸置、傳統法治價值被消解以及行政的任意與不可預見性增加等等。因此,對行政執法的功能主義進路應當反思,其可能的消極后果必須得到有效的控制。
(一) 以權利思維防止行政執法理念上的偏差
在行政執法實踐中,行政執法者具有雙重角色,既是一個政治人,又是一個法律人。來自政治系統的“功能迫令”通過壓力傳導機制對執法者產生直接深刻的影響,包括執法的起因、動力、過程,特別是作出法律決定時對法律的理解與詮釋均可到政治系統的功能迫令中去溯源。執法者對言論予以規制的執法活動往往并不是在簡單地實施法律而是要“吸納政治”,當普遍清楚的法規手段不足以貫徹系統的功能迫令時,功能主義的執法者有可能會放棄將其轉譯為法律規則的努力。當執法者不是基于法律內而是基于法律外的各類功能性目標開展行動時,就很容易在思維方式上出現偏差:即將法律中的權利與功能性目標簡單等同,或者“更上層樓”,干脆放棄兌現法律上對權利的承諾。
但權利在法理上具有“門檻性質”,既不能輕易放棄,也不能簡單地將其與那些功能性要求相提并論。被法律標記為權利的,是社會中最為典型和核心的利益,它們在政治意見形成過程中被充分地商談,得到共同體全部成員的普遍承認。我們并不希望犧牲它們來換取共同體作為整體的那些一般性利益,否則就根本沒有必要將某些利益上升為法律上的權利。權利在法理上因此具有了某種“門檻性質”,即使當權利必須與那些功能性要求分出高下時,權利也具有某種優益性,規則的形式性所確立起來的正是權利的這道“門檻”。這就像德沃金所說,雖然權利并非在所有場合均能戰勝集體目標,但它不能基于通常的成本收益的計算來予以推翻,權利能夠抵抗某些政府權力的干預,而如果沒有該權利存在,這個干預的理由會被視為是充分的[6]。特別在現代民主國家確立法律權利的立法過程中,功能性主張都會出現,都會被慎重地考慮,它們在立法的論證性商談中已經得到了解決。在權利經由民主的立法程序確立之后,權利就不能再同那些功能性的要求簡單地等同起來了,這正如哈貝馬斯所言,“目的論內容固然也進入了法律之中,但經過權利體系界定的法律通過規范性視角的嚴格優先性而在某種意義上馴化了立法者的政策和價值取向。”由于權利既關乎人之存在與尊嚴,又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有巨大裨益,因而在執法中理應且必須受到足夠的重視。應當按照“原則-例外”的邏輯去理解權利和對權利的干預與限制。若顛倒該次序,那權利被過度侵害甚至內核被掏空的危險就無法避免。
因此,雖然行政執法者首先處于政治系統中,敏感于系統的各種功能迫令,但行政執法者依然要確立權利思維。這種權利思維強調的是權利的門檻屬性。唯有如此,執法者才能在兩種身份中保持平衡,不至于完全受系統功能迫令的驅使而淡忘了自身作為法律系統內的行政執法者角色和因此需要對法律負責的立場。雖然權利思維并不意味著權利絕對,但卻提示著行政執法者,個人權利相較于功能性目標的“初顯優先性”,施加了一種有利于個人權利卻增加集體利益負荷的論證負擔[7],這使執法者在對權利予以限制時足夠慎重,避免只講立場不顧其它的隨意與傲慢。在行政執法的過程中,如果執法者的這種權利思維闕如,就極有可能在系統功能迫令的過度驅動下作出爭議較大甚至錯誤的執法決定。
(二) 以權衡方法來對個案中競爭性利益進行審慎衡量
在功能主義主導之下,權利不再是絕對的,其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在某種意義上取決于與之競爭的功能性論據的強度。但這兩者間的比較需要一種妥當的方法,否則行政執法的任意就難以控制。實踐中因為不對這兩者進行比較或者未在一個恰當的論證框架內來進行合比例性判斷的情況十分常見,這也是功能主義主導下的行政執法經常會出現的問題。例如在安徽亳州“奶奶的腿”案中,一名男子因違法停車被交警貼罰單,事后將罰單拍照發在朋友圈,并配文吐槽“奶奶的腿,接個小孩停十分鐘一百”而被行政拘留[8]。案件在網絡上被披露以后引起了輿論的關注,輿情普遍認為該案的行政處罰過于任意。此案因其發生在強調執法者執法權威的政策性背景之下而頗具代表性。為了樹立執法權威,實踐中加強了對涉警言論的控制,但矯枉不能過正,在具體案件中,執法者應在沖突性的價值之間進行審慎的衡量。
當功能性目標與公民權利發生價值層面的競爭或沖突之時,解決的主要方法是權衡。權衡在法律各領域特別是憲法領域被廣泛運用,行政執法中對合比例性的要求與權衡的要旨大同小異,只不過權衡更多側重的是方法論層面。權衡的方法有多種,德國學者阿列克西的理論框架值得關注。阿列克西在解決作為價值沖突的“原則碰撞”時,提出了所謂的“權衡法則”。權衡法則的關鍵在于狹義的合比例性原則:“一個原則的不滿足程度或受損害程度越高,另一個原則被滿足的重要性就必須越大。”[9]權衡法則能通過“重力公式”進行具體的賦值運算,按照阿列克西的分析,其具體步驟包括這樣三個方面:第一,先確立某個原則在具體個案中被滿足的程度。為了直觀和便于比較,可以將每一原則被滿足的程度分為三種情形,以“輕、中、重”三個位階來表示,然后在個案中根據具體情境判斷出其被滿足的重要性程度具體位于哪個位階上。第二,以相同的方法來確定相沖突的原則在個案中具體受損害程度所處的位階。第三,綜合上述兩個步驟,得出可能組合,組合包括重重、中中、輕輕、重中、重輕、中輕、中重、輕重、輕中等九種情形。根據前述權衡法則的核心要義可以得知,前三種組合意味著兩條原則所承載的價值在個案中的競爭形成了勢均力敵的平局情形;中間三種組合意味著通過了合比例性檢測,某原則被滿足的重要性程度能夠證立相對立原則受損害的程度;后三種組合意味著無法通過合比例性的檢測,某原則被滿足的重要性程度不足以證立相對立之原則受損害的程度。阿列克西的權衡理論,實際上提供了一個相對清楚的框架來對競爭性的利益和價值予以比較。
在行政執法的具體案件中,當引入功能性論據與權利相競爭時,可以基于權衡法則和重力公式來考量其中的競爭性因素,從而使結論獲得某種理性的證立。例如前文提到的亳州“奶奶的腿”案件,結合個案的具體情境可以認為,處罰涉案的言論對執法者權威維護的滿足程度處于“輕”的度量值上,而同樣的處罰對權利的損害卻至少處于“中”的度量值以上。此處對“輕”和“中”的刻度認定并不非任意,而是基于反思平衡的方法所得出來的。以對言論自由的規制為例,最低的侵害可能是完全放任,而最重的侵害可能是以刑事手段來予以處理,在這二者之間的則是處于中間刻度的各種行政規制。而在行政規制的范圍內,最低的侵害可能是批評教育或警告,中度的侵害可能是罰款之類,而治安拘留可以算是最為嚴重的侵害了。基于這樣的思路,認定該案中的處罰造成了對權利的“中”度以上的侵害是比較客觀的。而在該案中,根據上述理論最終將得出“輕中”的衡量結果,這種結果是不能通過合比例性檢測的,即對執法者權威的滿足程度不足以證成對權利的損害程度,故處罰不能成立。
(三) 以充分的論證來證立可預見的歸責后果
在行政執法活動中,功能性論據介入并直接影響個案處理的技術性途徑之一是對后果特別是社會后果的強調。是否“造成不良社會影響”或“影響社會情緒穩定”等是在追求社會效果時經常會考慮到的因素,但這種功能主義主導下對社會后果的評估不能過于主觀。這樣說并不是要否定社會后果作為功能性論據的引入,而是認為,在承認功能主義進路合理性的前提之下,作為歸責原因的社會后果需要得到充分的論證,任何人都不宜為那些不可預見的后果承擔法律上的責任。
對社會后果的論證應注意這樣幾點。首先,社會后果需要有社會科學所提供的知識或經驗性論據來支撐。事實上,因為司法說理的要求,在司法過程中引入社會科學的論據來論證可欲或不可欲后果的做法早已屢見不鮮,行政執法也應當予以借鑒。例如在美國開社科論據進入司法裁判之先河的穆勒訴俄勒岡案中,布蘭代斯為了捍衛女工權利,憑借深厚的社會科學素養,通過充分援引相關數據和文獻,對不規制最低工資和最長工時會給女性勞動者造成傷害和給整個社會帶來不利影響這一后果作了有力論證。再如在司法實踐中,利用統計學數據來證立某種社會后果的存在也很直觀并且具有相當程度的客觀性。雖然行政執法具有明顯與司法相區別的制度特征,但在吸納社科論據來論證后果方面并不應存在明顯的差異。事實上,我國行政執法實踐中也有這方面的努力,例如上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對上海市食派士公司的反壟斷行政處罰決定書就有這方面的嘗試并獲得了許多的好評[10],但從宏觀上看,這類做法尚不普及。其次,行為與后果之間的因果鏈條不宜隨意拉長。例如針對疫情期間編造“吃9個雞蛋可防止疫情”被行政拘留的案件,有法律實務界的觀點認為,“這樣的謠言看似無害甚至令人啼笑皆非,但由此構建信息傳播的通道,可能成為焦慮情緒的傳導媒介,使人們漠視科學防控方法,甚至妨礙現行防控措施,讓暫時取得的階段性成果功虧一簣。”[11]為將功能主義論據引入到案件的處理過程中,該觀點從“焦慮傳導”引申到“漠視科學”再到“妨礙防控”最后到“成果功虧一簣”的論證將因果關系的鏈條拉得過長,值得商榷。最后,對后果的論證應符合普通人的認知。后果不能是猜測的,也不能違反常識性的判斷,應按 “一般人”的判斷標準來予以評判,以免對后果的論證變成了隨意的“臆測”或“編造”。在龔某某編造發布“縣政府給單身漢發老婆”的微信信息被行政拘留10 日的案件中,執法者認為該信息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后果,因為有一位精神病人“看到這則消息后,到政府要填表領老婆”[12]。但這種對后果的論證是荒謬的,不符合常識,特別是其把精神病人的反應,而不是正常人對該信息的反應作為評價的標準,難以讓人信服。
四、結語
社會的復雜化發展,政府承擔的導控任務變得嚴峻復雜,功能主義的執法適應現代規制國家所面臨的日益嚴峻的導控任務的需要,將功能性論據通過目的或后果等通道引入到個案之中,試圖在法律的框架之內努力貫徹特定的政策、目標或落實國家的價值偏好。功能主義的執法邏輯在復雜社會的背景下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極易被推到極端,使權利的門檻被踏平,法律規范的防火墻功能喪失,因而其負面影響必須得到控制。從行政的制度特征來看,值得努力的方面主要包括以權利思維去抵御系統功能迫令的驅使,以權衡方法對個案中的競爭性利益或價值進行審慎的衡量,以充分的論證來證立可預見可歸責的后果。只有如此,行政執法才能在復雜社會的背景之下,在爭議個案之中達至權利與各類功能性要求的恰當平衡,實現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統一,從而讓人民群眾能在每一個執法決定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