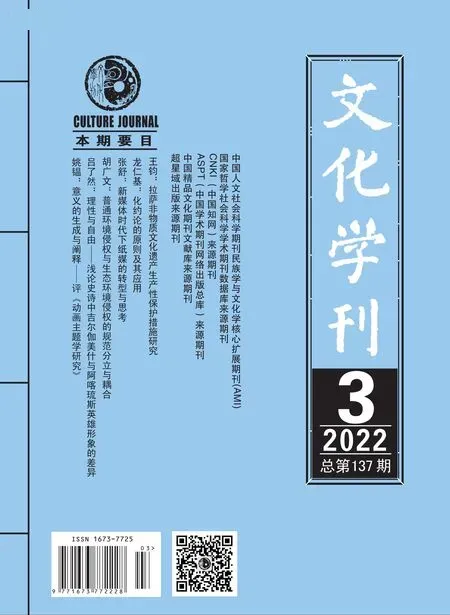理性與自由
——淺論史詩中吉爾伽美什與阿喀琉斯英雄形象的差異
呂了然
一、引言
《吉爾伽美什史詩》是人類最古老的英雄史詩,由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8世紀乃至更早時期的兩河居民在繼承蘇美爾人口耳相傳的故事基礎上總結編訂而成。吉爾伽美什是該史詩所著力刻畫的英雄人物,其主要事跡包括斬殺魔獸芬巴巴與天之公牛,目睹好友逝世后歷經艱險尋找長生仙草,在仙草丟失后摒棄了永生的執念,作為一個英雄兼理想統治者被人傳頌,其間貫串了他從暴君向賢王的轉變歷程。
長篇史詩《伊利亞特》出現于公元前9世紀至公元前8世紀,相傳為盲詩人荷馬所著。阿喀琉斯是該部史詩所塑造的最為成功的英雄,是攻克特洛伊城的關鍵人物。他在戰爭中屢建奇功,其行為直接影響著戰局的走向,殘忍與仁慈在他身上并存,背后體現的是其“為自己而戰[1]”的個人主義觀念,被稱為“個人英雄主義的巔峰[2]”。
學術界對于上述作品的研究比較深入具體,文學與史學研究成果皆很豐碩。學術界對于兩部史詩的繼承關系也有較為深入地論述,多集中于對史詩外在形式和思想主題的討論。這其中大多是針對史詩中的某一主題、母題或歷史背景等方面進行闡發,國內學者也多是局限于阿喀琉斯和關羽等本土英雄形象的對比與研究,以及從比較文學角度分析兩部史詩之間的聯系,而對于兩部史詩之中具體人物性格的比較則相對缺乏。
本文將從吉爾伽美什與阿喀琉斯這兩個典型的英雄形象入手,從比較文學的角度,采用平行研究的方式,分析二者在形象塑造方面的不同之處,并探討二者性格差異背后所體現的不同文化內涵。
二、 兩個人物形象的差異
《伊利亞特》很大程度上是對于《吉爾伽美什史詩》的繼承與顛覆,兩位英雄也呈現出眾多相似之處,然而二者的區別也同樣值得深究,二者展現了不同文化語境之下不同的審美范式。
(一) 吉爾伽美什:凸顯集體意識,代國家立言
吉爾伽美什身上的集體意識與國家觀念是他與阿喀琉斯的主要區別。他的身份構成區別于阿喀琉斯這樣偏向于孤膽英雄的勇武戰士,是統治者以及國家集體的代表,且他的故事多是圍繞著與人民的關系來展開。
1. 統治者的權威:特權意識與形象轉變。
對于吉爾伽美什的刻畫,權利意識是他前期的主要特征,由此也引發了與群眾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構成了與阿喀琉斯個人英雄主義的本質區別。眾神賜予了他英俊的外表,“大力神塑成了他的形態,舍馬什授予了他英俊的外貌,阿達特賜予他堂堂風采[3]37”,不僅如此,吉爾伽美什擁有三分之二的神性,具備遠超常人的強悍、聰穎、俊逸。然而作為強者的天命使得他以一個暴君的形象示人,正如史詩所記載:“他不給父親們保留兒子,也不給母親們保留女兒[4]”,并且“他的殘暴從不斂息”,也從不顧及“武士的女兒,貴族的愛妻”。
此時的王是自視甚高的暴君形象,其所追求的愉悅是以其非凡的身世與能力來追求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快感,“特權”成為表現其作為王的形象的重要依據,折射出了集體意識當中的消極一面(統治者作為國家核心的權威與地位,使得剝削與被剝削有很大程度上的合理性),而人民的低微也是對王權最好的參照,這使得王的個人主義不同于阿喀琉斯,也因為這些特權使得王與臣民建立起了不可分割的聯系。
恩奇都的臨降加深了吉爾伽美什的集體主義品格。與阿喀琉斯“殺死自己的對應者形成獨尊[5]”不同,吉爾伽美什在搏斗中感受到了對手的強大,二人結拜為友,共同治理國家。國王由先前的獨裁變為與恩奇都共治國家并聽從其向善的勸誡,是吉爾伽美什由暴君轉向賢王的重要節點,在王與恩奇都友情的羈絆之下,他作為個體與集體大我的相互滲透進一步深化,開始向集體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積極一面轉變。
2.統治者的責任:為民除害與后期仁政。
責任意識作為集體意識善的一面,也同樣是王與個體英雄的重要區別。這在斬殺魔獸芬巴巴與天之公牛的情節中得到體現。芬巴巴居住于杉樹林中,它“聲音聽起來像洪水,一張嘴就是烈火,吐一口氣就置人于死地[6]20”,它象征著自然之力對上古人類的欺凌與掌控。吉爾伽美什在恩奇都與舍馬什的幫助下將其殺死。而對芬巴巴的討伐展現了人類戰勝自然的力量;作為為民除害的英雄,其正面形象也由此得以具體地呈現,為民造福的集體與理性意識得到了伸展。
其后斬殺天之公牛的敘述,代表了國王對于宇宙間神力與命運的反叛。女神伊什塔爾向其父安努借來天之公牛為禍人間,吞噬了三百人的性命并造成了七年的災荒。吉爾伽美什與恩奇都再度救民于水火,恩奇都“抓住它的犄角和尾巴”,而國王則將寶刀插入牛的頭顱之中。斬殺公牛的故事是人民在生產與生活兩個最為重要的領域渴望走出“神代”的最為集中而深刻的體現,吉爾伽美什的英雄行為也從中更加深化,進而成為“英雄中的英雄”。
綜上所述,王的目的是讓自己的人民擺脫神靈的控制,走向繁榮,突出了其作為賢王的勇氣、理性與責任意識,因而王具有了崇高的特點,增添了生命的厚重感,體現出了集體主義的審美特征。
(二)阿喀琉斯:張揚個體欲望,代個人立言
阿喀琉斯相較于吉爾伽美什的國家觀念,其突出的性格是海洋文明之下的自我本位觀念與自由意志,更加側重于“自我”,體現出生命原欲之中與他者分離的自由主義傾向,體現著全希臘民族的精神。
1. 個人能力與情感:自恃勇武,個人為中心觀念的極化。
在史詩中,阿喀琉斯的勇武成為個體本位觀念的重要憑借,這也進一步內化為他對于敵人的侵略性和對于他者安排的反抗性。他在聯軍迷路之時,擊敗了忒勒福斯,并迫使其作為向導找到特洛伊;縊死刀槍不入的海神之子庫克諾斯;斬殺大將赫克托耳……勇武過人可見一斑。而這樣的勇武與功績加劇了其內在的自我意識,“不允許他人主宰自己的生命[7]”。主帥之后強搶布里塞伊斯的舉動使得這一觀念轉化為更加激烈的行動,他憤而退出了戰場,并留下了慷慨的誓言:“以這支權杖的名義——木杖再也不會生出枝葉,因為他已永離了山上的樹干……將來的某一天,全軍的將士都將翹首盼望阿喀琉斯;而你,卻只能眼看著成堆的士兵倒在殺人狂赫克托耳的手下[8]13”;阿喀琉斯的“自私”內核是其故事發展的原動力,其善舉、暴行抑或是功績均是由此發端。
阿喀琉斯對于可與之媲美的英雄人物的態度與吉爾伽美什迥然不同,自己的價值需要赫克托耳的死亡來加以襯托。而二者的關系也處于侵略性的、激烈的對抗之中,結束必以一者的消亡為代價,尤其是二人最終決斗之時,阿喀琉斯所使用的羊和獅子的比喻,突顯了阿喀琉斯的個人英雄主義。這與吉爾伽美什與恩奇都幾近融合的集體形式差別迥異,也體現了阿喀琉斯身上希臘式的勇武和對于個人本位的追求。
阿喀琉斯參戰的動因并非出于對國家民族內在價值的體認,而是對個體意識和價值的執著追求。他的故事圍繞著自由意志而展開,他的“美”與悲劇均是以“個人”而發端。而《伊利亞特》在他身上也展現了不同于傳統英雄形象的個人主義美學范式的極化。
2.個人權利與尊嚴:不懼強權,追求個人權利的合理性。
相比于吉爾伽美什為集體創造價值與意義,阿喀琉斯則更傾向于為自身創造價值,而基礎便是自己的合理要求得到別人的尊重甚至讓步,并呈現出對于權威的反叛性。
阿伽門農象征著集權與專制,代表了對抗英雄的異己力量。針對女俘被強搶一事,阿喀琉斯激憤地斥責他“總是吞走大頭[8]15”,自己浴血奮戰卻“只有那一點東西[8]11”。阿伽門農對此則不無藐視地表示自己特權的合理性,自己搶奪英雄的戰利品是為了彰顯自己的權威,亦如他所言“讓你清楚地知道,我比你強多少[8]17”,也威懾別的英雄不能違逆他的威勢。由此可見,阿伽門農俯視一般的態度激怒了阿喀琉斯,使他認為這是統帥的蔑視。阿喀琉斯此舉要通過自己的反抗性消解阿伽門農凌駕于自己的特權,其個人本位的權利意識可見一斑。
阿喀琉斯對于個人權利的追求從更深層面上體現在對于命運和神靈意志的反叛。忒提斯曾預言過兒子的兩種命運:“一是默默無聞而長壽,但被人遺忘;二是參加戰斗,雖然會犧牲卻可世代傳頌[7]34”。兩種命運也通過諸神不斷加以強調,神權與神示對于個體命運的掌控具有決定性,同時忒提斯的意愿還暗含著家長權威,由此也體現出了阿喀琉斯的異質性是對于神權和母權的雙重反叛。阿喀琉斯無視神靈的安排,他走上了戰場,屢建奇功,完成了自己作為希臘勇士的意愿和歸宿,個人的概念在他的身上被發揮到了極致,體現了強烈的生命張力。
三、 人物形象差異所折射的文化內涵差異
(一) 不同的文化背景
吉爾伽美什與阿喀琉斯的形象并非是憑空創造的,他們的傳說是古代兩河流域和古希臘社會生活與人民精神世界的反映,二者的不同特質也均是由此生發。
1. 吉爾伽美什:大陸文明影響下的集體主義觀念。
兩河流域是人類早期以農業為主導的大陸文明的源頭,嚴格的地理環境制約與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式,使得對農作物的種植以及大量人員的統治成為了其必然的選擇,農作物的自給自足使居民會長期停留于此,人們樂于與眾人從事相同的勞動。由此集體主義的泛化成為了農業文明最深層次也是最為合理的宗教,從而也造就了吉爾伽美什人物形象與群眾不可分割的聯系,農業文明的集體生產方式成就了王的權威,王也為農業集體的利益而獻身,這在其前期的統治與之后的英雄事跡當中得以凸顯。
現實政治的需要也是集體主義盛行的重要原因。統治者格外注重國民性格、政治格局與思想文化領域的“同一性”。公元前2334年薩爾貢一世在流域內建立起統一的阿卡德帝國,并且進行了一系列的大一統措施。在疆域遼闊的帝國當中,人民要為君主從事生產勞作,而君主也需要殫精竭慮地經營與民眾的關系,由此產生了利他主義精神的集體觀念,這在吉爾伽美什后期斬殺魔獸、尋求仙草等情節中得到體現,王也表示要將仙草與眾人分享,體現出了重視王權與理性的集體主義的觀念,也成就了吉爾伽美什“王”的地位與“王”的典型特質。
對神靈的敬畏也是該文明的精神特質之一,并內化成為集體無意識。在生產水平極為落后的上古時代,兩河人民將自然災害歸結為是神的意志,例如眾神之主恩利爾曾降下洪水滅亡人類,主管太陽的內爾伽勒名字的寓意為太陽的“灼熱”,伊什塔爾作為農業之神則更有降下天之公牛抑或下冥府的無常之舉,史詩當中吉爾伽美什的事跡也多與神的意志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恩奇都的生死、斬殺魔獸、尋求長生等都有著諸神直接或間接的操縱;王身上的重生懼死意識也由此發端。
由此可見,《吉爾伽美什史詩》是對于兩河流域農業文明的反映,凸顯了代國家立言的集體主義觀念。王擁有為民除害的雄心壯志,但也擁有面對諸神與命運時同凡人一致的恐懼,體現了大陸文明之下的精神面貌與時代精神。
2. 阿喀琉斯:海洋文明影響下的個人主義觀念。
相較于吉爾伽美什,阿喀琉斯身上凸顯的則是海洋文明影響之下的個人主義觀念。首先,侵略性成為個人英雄主義的基石。狹小的島嶼與山地不足以支持人們生存,侵略活動這樣的利己排他行為被視為合理的存在,與他者的分離與決裂是其話語的主流。阿喀琉斯便是由此觀念打造的英雄,他勇猛過人,對待異己力量也保持了一貫決絕的態度,作為最強大的個體得到了崇敬。
同時,政治上的不統一也為個體本位提供了條件。希臘文明所處的地中海海域,其間的任何國家都無法建立起普遍的霸權,盡管擁有相似的文化體系,但諸邦不曾擁有統一的意識形態,小共同體的存在使得思想意識得以百家爭鳴。史詩中阿喀琉斯在受辱之后率領部族罷戰,而阿伽門農卻不敢發作,其中除去眾神的決定,也表現了聯軍“軍合力不齊”的現象,自由主義得到了張揚。
此外,海洋環境迫使商貿活動成為主導產業,大宗貨物的輸送與人員的往來更加迅捷,希臘人“早已同前拉丁民族打起了交道[9]”。在等價交換的原則之下,付出后所得的回報是神圣的。史詩中阿伽門農出爾反爾將伊菲革涅亞祭獻給阿爾忒彌斯,由于戰利品的丟失轉而搶奪布里塞伊斯都成為阿喀琉斯憤怒的觸發點。而公平意識也使得史詩中的人們的命運觀念發生變化,人與命運的關系由順從轉為反抗。
兩種文明的差異造就了吉爾伽美什與阿喀琉斯截然不同的英雄特質與文化品格,也正因為不同文明的差異提供了互相借鑒的價值,世界文學才可以真正做到百花齊放。
(二)不同的生命觀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對生死的態度是史詩極力追問的重要主題,也是一種文明文化內涵的重要體現。在兩部史詩中,兩個英雄對于死亡不同的態度體現了兩種文明的生死觀念和生命意識。
1. 吉爾伽美什:對生命的焦慮與無奈。
正如學者所說,“美索不達米亞人認為人是由神創造出來的,是為了實現神的意愿[3]23”。相較于希臘的自由意識,吉爾伽美什對于生命的態度更多地體現為一種無奈與焦慮,是對于命運必然性的服從。由此衍生了吉爾伽美什身上濃重的重生和懼死意識。
(1)生命依賴于神靈:借助預言和神力擊敗異己力量。
史詩中吉爾伽美什的英雄事跡,在更深的層面表現為蘇美人在一種強大的異己力量面前巨大的不自由,表現出了他們對于生命的焦慮和恐懼。在斬殺芬巴巴時,舍馬什為他們打造了武器并且在戰斗中向芬巴巴吹出十三種風;在斬殺天之公牛前,舍馬什將恩奇都收為義子;而二人在殺掉公牛后,也用公牛的內臟向舍馬什進行禱告;……凡此種種,均體現了蘇美人的生命觀念:人在自然與神靈面前力量是微小的,人的生命不過是在塵世實現諸神的目的。
在王高歌猛進的巔峰之中,這些細節表示了其悲劇的必然性:光輝的功績實際是神在背后的操縱,對于異己力量的抗爭多是依靠神明的力量來完成的,而王的權威與才干在神與命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而人們在不屈地抗爭命運的同時,則表現出更多的焦慮與無奈。
(2)長生的失敗追尋:歷險尋找仙草而遭命運戲弄。
對長生的追尋是吉爾伽美什生命意識中對懼死意識的延伸,同樣也顯露出對于集體主義與理性精神的積極一面的追求。恩利爾眾神以殺死神獸為由,奪去了恩奇都的生命,面對好友的死亡,吉爾伽美什的恐懼與焦慮得到了深刻體現。正如詩中所說:“我曾經征服了一切,但我的死也會像恩奇都一樣,死得毫無意義,死得令人惋惜[6]37”,在旅途中,面對蝎人和釀酒神西杜麗的勸阻,王依舊執意前行;在聽了烏特納比什提牟的提示以后,毅然跳入海底尋求仙草,表現出了吉爾伽美什理性意識當中對于必然性的屈從,凸顯了無奈的生命觀念。
正如后人所言“王來承認,王來允許,王來背負整個世界[10]”。永生追求并非是個人主義的體現,也彰顯著作為統治者的憐憫與對理性的追尋。對于國家與人民前途的擔憂,是他恐懼心理的更深層次。王希望把仙草帶回城邦與人民共同享用這一細節,表明此時的吉爾伽美什依舊是以王的責任意識示人的,自己作為賢王有能力與責任幫助人民擺脫神的統治,作為強者的自己的消逝將會導致人民重新被自然與神力所控制,在仙草遺失之后王依舊回到烏魯克勵精圖治,也是其理性精神與神性的體現。在小說Fate系列的第七章,吉爾伽美什以一己之力對抗著創世神提亞馬特滅亡人類的企圖,完成了王的終極夙愿,對于他人悲天憫人式的集體主義精神也使得其精神得到了巨大的升華,體現出“王來背負整個世界”的集體主義精神魅力。
2. 阿喀琉斯:對生命的抗爭與坦然。
相較于吉爾伽美什,阿喀琉斯對于生命的掌握更少有對于異己力量的無奈和恐懼,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因而他更加坦然地直面生死,體現著對于他者安排的“必然性”的反叛。
(1)不畏宿命的坦率:不懼預言離家參戰,反叛神示。
阿喀琉斯對待死亡的坦率與其宿命的預言構成了反叛,凸顯了其身上的自由意志,他對于神的服從與無奈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阿喀琉斯的兩種命運走向根據諸神的旨意一再得以強調,顯然神靈希望其遵從前者,而且對其進行保護,而阿喀琉斯則遵從了戰士的本能,愿意坦然接受自己的必死無疑的結局,并在諸神奪走生命之前奮力實現自己的英雄理想。
同時,與《吉爾伽美什史詩》的神示不同的是,神示在最初就給予了阿喀琉斯兩條選項,使他擁有更大的權力選擇自己的命運,相比于吉爾伽美什他已然更加自由,使得他的一生短暫卻更合乎自己的意志。正如他在不可一世的主帥面前選擇憤怒一樣,在神代以人的概念徹底地對抗神的權威,從而突出了阿喀琉斯個人主義的審美范式和對于自由的追求。
(2)追求生命的價值:光榮戰死而拒絕無名長生。
相較于大陸文明的重生懼死意識,海洋文明則傾向于在崇高價值的基礎上將生死問題置之度外,極大地消解了人們對于死亡的恐懼,具有濃厚的生命自由意識。
史詩中,阿喀琉斯青年時期在聽到奧德修斯的軍號后便與眾多年輕的戰士一同拿起武器出征;不顧生命將盡的預言執意殺死仇敵;而后阿喀琉斯的馬預言了他死期將至,而他卻回答說自己早已知道“將離開母親而死在這里”。盡管如此,他仍然要“把特洛伊打得稀爛”。他橫掃特洛伊平原,屢建奇功;以憤怒對抗阿伽門農的乖張與粗暴;向普里阿摩斯歸還赫克托耳的尸首。這些行為都體現了阿喀琉斯對于個人榮譽和價值的追求,兒時父母遠去,隨喀戎習武的經歷也使得他在并不優渥的處境下更加認識到個人生命的珍貴,對他而言,成就自己的英雄精神便是價值最大的體現,他身上沒有吉爾伽美什作為統治者的不安與憂慮,他敢于藐視預言,坦然面對生死,最大限度地展現了作為個體的人的價值與勇氣。
四、結語
兩個英雄形象因繼承關系出現了許多相似之處,但身為兩種不同的英雄形象,其身上也不可避免地體現出不同文明背景下的差異。二者的差異主要表現在:
(1)吉爾伽美什主要作為君主的形象而存在,其身上也更多地體現出統治者的權威和代國家立言的理性意識;阿喀琉斯則更多地作為個體英雄而存在,他與他人的關系更多地表現為異質性,體現了他對個人價值與自由的肯定。
(2)吉爾伽美什的形象反映了古代兩河流域農業文明的生產生活狀況,其形象的產生可追溯到農業穩定的發展模式以及帝國統一的需要;相比之下,阿喀琉斯則反映了希臘乃至地中海沿岸長期的海外活動與權力真空條件下的侵略性與平等意識。
(3)從生命觀念來說,吉爾伽美什表現出了兩河流域乃至農業文明的重生畏死意識;而阿喀琉斯則多次對于命運的安排做出反叛,體現了海洋文明當中人們追逐人生價值的具有反抗性的命運觀念。
《伊利亞特》與《吉爾伽美什史詩》傳達出了兩種不同的命題,即自由與理性兩大母題。二者在西方文學當中經久不衰,貫串了文學發展歷程的始終,以交替的方式成為各個時期的主流;二者也同樣催生了人類的海洋與大陸的兩種文明形態。二者存在諸多不可調和的沖突與矛盾,總會不可避免地暴露于對方的攻訐之下,但二者之中并不存在絕對的好與壞,而是在繼承與發展中吸取對方的元素,理性與自由的對立統一也正是作品的張力之所在,《伊利亞特》的成功就足以說明這一切。
吉爾伽美什與阿喀琉斯的英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前者體現出了作為集體之人屈從于理性的必然性,也滲透了經歷生死的艱辛以后仍舊背負一切沉重責任的高傲與堅韌,后者則體現出個體生命對于理性存在的懷疑與顛覆,也是人對于自身權利與價值的認同,二者作為人文精神的二重元素,閃耀著截然不同卻同等燦爛的藝術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