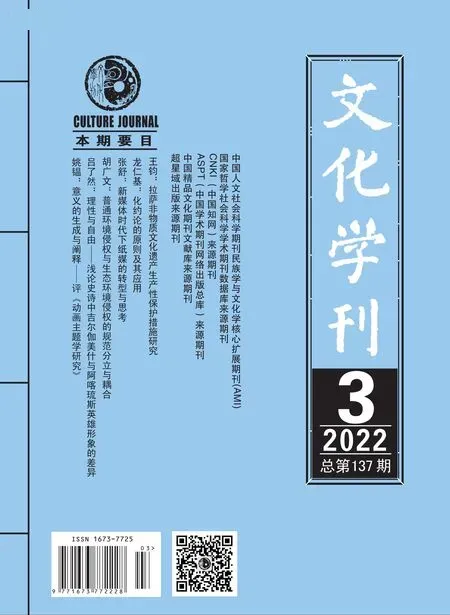東北森林號子的情感表達
顏鐵軍
勞動號子是傳統社會中與體力勞動密切相關的聲樂藝術。《中國音樂詞典》解釋勞動號子,“民歌的一個類別,北方常稱為吆號子,南方常稱喊號子,四川稱哨子。是伴隨勞動而歌唱的一種帶有呼號的歌曲”。[1]《中國民間歌曲集成·遼寧卷》則載:“號子的內容一種是與勞動作業直接配合,另一種是娛樂性的,借以調劑勞動情緒……具有娛樂性的,其一是歌唱豐收、愛情、山川、美景、鄉情等內容的……其二是唱戲曲或民間故事傳說……其三是幽默逗趣兒的”。[2]可見,相關研究亦有對號子娛樂功能的表述。但這種勞動之外的富有精神文化意蘊的研究一直被生產勞動的功能性所遮蔽,雖有涉及但也是淺嘗則止。事實上,勞動號子的娛樂性屬于情感世界乃至精神世界的范疇,是超越勞動空間的文化表征,也是號子之所以成為音樂體裁的重要原因。木幫中的勞動者就是通過森林號子來表達自己的情感的,并在藝術實踐中獲得獲得情感的宣泄與精神的愉悅,甚至通過表演與他者共娛。
一、對生命之痛的呼喊
過去,在東北森林里從事伐木、運木工作的木把(1)木把是舊社會木幫里進行伐木、運木勞動的最普通的勞動者。,基本都是因戰亂、自然災害而闖關東來的關里人。他們在東北面臨著多重的社會壓榨,往往靠出賣體力勉強生存。相關文獻記載:“迨庚子之役,俄人席戰勝之余威,藐中國之削弱,強奪橫取,肆無忌憚,自是路權遂不可問矣,且不獨路權一端已也,凡沿路之土地、礦山、森林、航運以及軍政、警政,俄皆攫而有之。”[3]在殘酷的社會現實下,東北森林里的山民們在外國侵略者、本地土匪及木幫頂層大柜(2)大柜是舊社會木幫中一個山場子、水場子的主要出資者。通過雇傭勞動者伐木、運木、流送木材,從中謀取利益。往往是名震一方的人物。等的壓迫下艱難地生活著。
(一)控訴剝削壓榨
吉林省敦化市流傳著一首朝鮮族森林號子《集材索里》(3)具龍煥演唱,李黃勛采集、記詞、記譜,李得龍譯配。,歌曲這樣唱到:
(耶嗬)集材喲,工頭的綠豆眼滴溜溜轉,讓咱可恨(嗬耶)集材呦。[4]447
歌曲非常短小,是一首山場子勞動時演唱的號子,準確地說應該是歸楞時演唱的號子。反映了朝鮮族木把們對苛刻而嚴酷的二柜(4)老板的副手,一般負責監工、督導的工作。的不滿情緒。在舊社會,勞動者與剝削者的矛盾與對抗是比較普遍的,但作為勞動第一性的森林號子卻更多地體現了指揮勞動、協調動作的功能,而表現反抗意識的內容卻很少,《集材索里》是號子中比較珍貴的一首。
吉林省靖宇縣流傳過一首《打繩子號》(5)王允獻唱,王旭、運功、九思、明高記。,歌詞為:
窮哥們喲呵嘿,甩開膀子喲嗬嘿,用力氣呦嗬嘿,打繩子呦嗬嘿,呦兒嘿,呦兒嘿,呦嗬嘿,呦兒哩,哈哩呦嗬嘿。打成團呦嗬嘿,擰成勁呦嗬嘿,捆蛟龍呦嗬嘿,拔窮根呦嗬嘿,呦兒嘿,呦兒嘿,呦嗬嘿,呦兒哩,哈哩呦嗬嘿。打土豪來呦嗬嘿,分田地兒呦嗬嘿。共產黨來了呦嗬嘿,翻了身兒呦嗬嘿,呦兒嘿,呦兒嘿,呦嗬嘿,呦兒哩,哈哩呦嗬嘿。[4]68
雖然這首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木幫勞動號子,但與木幫勞動密切相關,反映了勞動者推翻剝削階級、改變命運的愿望與決心,尤其對解放自身命運的共產黨進行了歌唱。
(二)表達生活的苦難
木幫勞動較一般勞動更為艱辛。吉林省撫松縣的山把頭崔長安總結說,砍大樹、抬大木那是體力活里最累人的勞動。《搬木頭》《抬圓木》《搬運號》《抓蹬號》等森林號子表達了木幫勞動的艱辛過程。《抬木頭號》(6)吉林省渾江市臨江林業局工人演唱,徐國慶采錄,張淑霞記。中唱到:
這個一回呀,管他那一回呀,累的個夠嗆嘿,啊那個壓得呀嘿,往推那個了嘿,推推那個嘿”![4]44-46
筆者調查發現,木把們抬木往往貪黑起早,抬的大的木頭直徑有1米以上,可見木頭的重量之大,木把門的勞動之苦。更為艱辛的是,木把們初入木幫,小杠壓在肩頭都要把肩頭壓破、壓出血水的,第二天在傷口上接著碾壓,直到肩頭慢慢形成血蘑菇(血包)失去知覺,這時木把們才算真正入了行。
吉林省和龍市流傳的一首朝鮮族抬木歌《運材索里》(7)李亨奎演唱,李黃勛采集、記詞、記譜,韓東吾譯配。這樣唱到:
哈腰掛喲站穩腳跟,(嗬咿呀喳哈嚕)這個木頭實在太沉,抬木頭汗水淋淋。(嗬咿呀喳哈嚕),好像磁鐵吸在地上,怎么也紋絲不動。(嗬咿呀喳哈嚕),哈腰掛呦再抬一根,前頭后頭一起使勁。后頭起(那么)要看前頭,前頭起,一起行進。(嗬咿呀喳哈嚕),整天抬木頭,抬個不停,一天快完了,太陽西山沉。干一天筋疲力盡,(嗬咿呀喳哈嚕),哈腰掛呦向前行進”。[4]445-446
歌曲反映了抬木勞動的艱苦,揭示了舊社會山民為了生活起早貪黑,受盡苦累,卻看不到未來的社會現實。
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森林勞動是比較艱苦而復雜的勞動,勞動號子描繪了勞動的情景,反映了勞動的艱辛。在這樣艱辛的勞動中,卻有一種歡快、熱烈的音樂風格的存在,體現了木把們的樂觀精神。
(一)對婚戀的渴望
東北森林及其輻射地帶,有一些女人靠著木幫的木把們而生存,民間稱這些女人為“靠人的”。曹保明將其系統地歸納為“計時婚姻”“拉幫套”婚姻、娼妓、娶“再婚”的等四種基本形態。
筆者根據曹保明的研究將四種形態作以簡要歸納:計時婚姻是負責流送的木幫在排窩子與當地女人兩情相悅時而形成的臨時婚姻;“拉幫套”婚姻是經人介紹形成的臨時婚姻;娼妓交往是木把與娼妓之間純粹地以經濟為手段的性交易;娶“再婚”的是指木把娶了二婚或三婚的婦女為妻的正式婚姻。
這些關系問題與木幫水場子(8)水場子是指在江河沿岸堆放木材的地方,在這里穿排,并通過江河放排,將木材運往山外。活密切相關,是木幫水場子文化的一部分,其根源是性需求的問題。過去,尤其是木幫社會,男人很多都是單身,即使有的有家庭但也需常年在外勞作,因而缺少異性的關懷。與水場子活相對的是山上的伐木群體,他們從入冬上山伐木、運木到歸楞,長時間離家在外,同樣有著對異性的渴望與被關懷的需求。但事實上,他們相對穩定性的生活幾乎并不具備與外界接觸的條件。那么,他們的需求靠什么來滿足呢?聰明的號子頭在勞動實踐中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劉仲元在1985年采錄于大陽岔的《哈腰掛》(9)劉張氏口述。這樣唱到:
哈腰掛呀么,嘿!挺腰起啦嘿!呦,嘿嘿,嘿!往前走了么,嘿!吼,嘿嘿,嘿!走要穩了么,嘿!哎,嘿嘿,嘿!嗯,嘿嘿,嘿!有個大姑娘啦么,嘿!走過來了么,嘿!真漂亮啊,嘿!你可不能看啦么,嘿!呦,嘿嘿嘿!哎,嘿嘿嘿!嗯,嘿嘿嘿!
你要扭頭看了么,嘿!非出差啦么,嘿!呦,嘿嘿嘿!哎,嘿嘿嘿!嗯,嘿嘿嘿!到了地方么,嘿!哎,嘿嘿嘿!站穩腳啦么,嘿!放下來呀么,嘿!哎——嘿嘿嘿![5]89-90
此類勞動歌謠,一般都是見景生情,見到什么就歌唱什么。有時沒詞唱時,就互相調侃。吉林省白山市撫松兩江口木把趙友志演唱的《松口氣》是一首調侃婦女的幽默歌曲。歌曲內容如下:
哈腰起呀,咳!步要齊呀,咳!慢慢走呀,咳!別著急呀,咳!一步兩步,咳!連環步呀,咳!三步四步,咳!躲點泥呀,咳!五步六步,咳!梅花瓣呀,咳!七步八步,咳!腰挺直呀,咳!九步十步,咳!正來勁呀,咳!戴花的呀,咳!大眼睛呀,咳!柳葉眉呀,咳!櫻桃小嘴,咳!笑嘻嘻呀,咳!倆酒窩呀,咳!一般大呀,咳!可惜大姐,咳!是人家的,咳!貓咬尿脬,咳!空喜歡呀,咳!前邊拐拐,咳!后邊甩甩,咳!到一站呀,咳!松口氣呀,咳!哎咳咳咳,哎咳咳咳。[5]90-92
森林號子《松口氣》大概是由學者命名的,因為民間勞動現場就是一邊勞動一邊演唱,不會有哪個號子頭會為勞動號子有意識地起個名字。這首號子從歌詞來看,非常工整,結構比較簡單,音樂結構屬接應式號子。號子歌詞中,動作指揮內容較少,對婦女的描繪語言相對較豐富,這種輕松幽默的音樂風格應該是抬小木頭時演唱的。
(二)對新生活的認同
人的身份是多重性的,在不同的語境中身份是不同的。舊社會時,木把們在木業勞動中是勞動者身份,大柜、二柜是管理者身份。從階級論角度來看,他們是剝削身份與被剝削身份的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民當家做了主人,很多木把們在新社會還在延續以往的勞動傳統,他們還是勞動者身份,但他們從階層論視角,已經從被剝削者身份實現了向主人身份的轉換。此時,他們勞動時又有著怎樣的情感呢? 《羊工號》(10)趙希夢記。這樣唱:
來一著,嘿嘿嘿呀。大家個圍上了哇,嘿嘿嘿呀。一起個撈旱灘哪,嘿嘿嘿呀。呀!流送的任務緊哪,嘿嘿嘿呀。呀哈!我們要搶時間哪。嘿嘿嘿呀。呀!我說(個)同志們哪,嘿嘿嘿呀。壓腳子前邊拽呀, 嘿嘿嘿呀。呀哈!挖杠后邊跟哪,嘿嘿嘿呀。我們的干勁蒙啊,嘿嘿嘿呀。呀哈!我們有決心哪,嘿嘿嘿呀。呀!支援大建設呀,嘿嘿嘿呀。呀哈!木頭運出山哪。嘿嘿嘿呀。呀哈!同志們哪,嘿嘿嘿呀。呀哈!刨鉤要搭緊哪,嘿嘿嘿呀。呀哈!眼睛要瞪圓哪,嘿嘿嘿呀。呀!大家個齊鼓勁呀,嘿嘿嘿呀。任務提前完哪。嘿嘿嘿呀。[6]
這首《羊工號》揭示了舊社會木把們翻身做主人后投身生產的高昂情緒和不懈的工作熱情。歌詞奇數句為領唱,偶數句“嘿嘿嘿呀”為合唱。值得一提的是,領唱前的虛詞“呀哈”為弱起音,與合唱結尾字同步,既構成了兩個聲部的重合的“合”,打一領一和的呆板的輪唱模式,又為領唱重音起音造成了音勢,形成強烈的音樂動力感。
三、對愜意生活的歌唱
木幫在江河上放排,稱為流送,是借助江河的水勢運送木材。人在排上既要面對水下激流、暗礁的危險,又要經受風雨雷電的摧殘。放排號子所唱的“伐大樹,穿木排,順著大江放下來,哪怕險灘浪千里,哪里死去哪里埋”正是排夫命運的真實寫照。每年農歷三月十六是林區放山人的節日,俗稱木把節、老把頭節或山神節。在這一民俗節日里,“木把們舉行祭祀儀式,燃香禮拜,祈求山神爺老把頭保佑木把們伐木、放排平安無恙,財源旺盛”。[4]24木把們在神圣的祈禱與勞作的險象之外,也有著愜意的山水棲居生活。
(一)唱響童年時光
對于東北山林里長大的山民而言,伐木、抬木、放排對于他們來說是再熟悉不過了。他們未必去過木幫,也不必是木把,但在他們身邊的大山里有太多的木把,有太多的木業勞作,也有太多這樣的故事。他們在這樣的環境里浸染著,對木幫的事都知道一些。張文國(11)張文國(1965— ),白山人,白山市職業技術學院,教師,采訪于2018年8月7日。從小就生活在長白山腳下,鴨綠江畔的小村。提起木幫,他饒有興致地講起他對水排的兒時記憶:
我小時候,鴨綠江里總有漂過的木排。那時候我小呀,看著木排感覺他們好長好長,太壯觀了。這一波過去了,下一波可能又來了。一些人站在排上唱歌,我非常羨慕。現在回想起來,他們唱得很好,歌聲也非常嘹亮,但曲調我早已記不清楚了。我大概十一二歲時,就和大孩子們下江游泳了。有時游到對岸朝鮮那邊玩兒,那時候朝鮮管得不嚴。等我們玩兒累了,想回去又怕游不回來。我們就等著木排來。木排來了,我們游過去,在木排上緩過勁兒來,再游回咱們這邊,大家就回家了。那時候太有意思了!
(二)唱給山民的歌
綠林覆蓋、綿延不絕的大山帶給山民豐富而獨特的山里貨,為山民增加了不少的收入。但大山里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如交通閉塞、信息交流不暢、文化娛樂生活缺乏等等。住在山林里,時間就仿佛靜止了一樣。當木排沿江漂過時,就會打破山林的寂靜。2018年8月8日,筆者采訪曼江的文化學者朱明春時,他講述了木排與小村的生動的關系:
過去,木排年年從松花江這里漂過,這是一種常態。在江邊生活的人們,缺少娛樂,他們就愛站在江邊等著木排經過。木排來時,人們主要是聽木排上唱的號子。人們駐足遠望,一邊聽一邊還和木排上的人打招呼。兩相互動,可熱鬧了。喊號子的看到山里來百姓聽得來勁,他們唱得就更有勁了。江面平緩的地方就不是為了勞動而唱了,而是為了消遣而演唱,尤其是還有聽眾的時候。唱的內容都是即興的,有的夸夸姑娘如何漂亮,大嫂多么心靈手巧,有的看到老年人,說他們是老壽星,唱些祝福的話。大家都愛聽。唱完這首唱那首,直至木排漂過這一片江灘。沒聽夠的老百姓還會等,因為還可能有木排漂來,他們就再聽別的排夫唱。此外,木排的經過還帶動了老百姓的經濟交流和發展。他們有的是排夫的親戚、朋友或是村鄰之類的,事先就和排夫聯系好,知道木排哪天路過。干什么呢?他們往往搭乘木排去吉林船廠,那是當時的大地方,或是賣點自己家里的山貨,或是到鎮里買些自己需要的物品。總之,木排對于老百姓又衍生出一種新的功能。
從朱明春的口述中可以看出,放排在特定的語境中的功能發生了轉變,即由實用性功能轉變為娛樂性功能。排夫和江邊的山民互相排遣著漫長的時光,為生活增添著靚色。在這個過程中,排夫與山民也形成了非盈利性的“表演—欣賞”的互動關系。這看似不經意的表演,實踐了一種精神生產,也反映了山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隨著時間的發展和生活方式的轉變,森林號子既作為一種與勞動緊密結合的藝術形式存在于勞動之中,又從勞動之中游離出來,成為一種模仿號子的新的藝術樣態。[7]
不管是普通山民還是木幫,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稱謂——山里人或者林中人。康德曾說:“能照亮心靈的東西,乃是閃爍著星星的蒼穹,以及我內心的道德律”。那么,能照亮東北森林里山民與木幫心靈的是一代代傳承下來的民間信仰和勞動實踐。森林號子作為東北文化的一部分,在勞動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也寄托著東北山林人的深厚情感,成為代代人難忘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