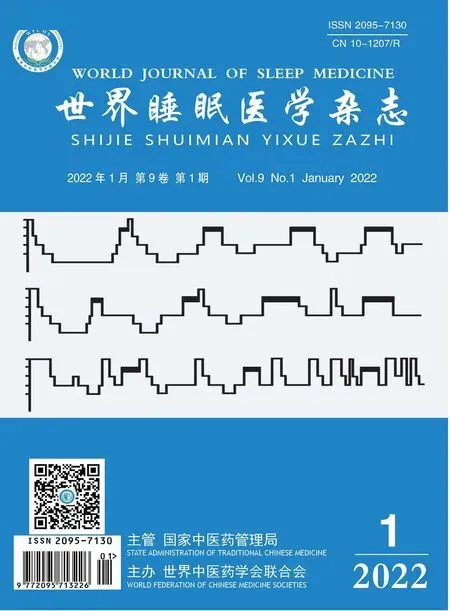腫瘤相關性睡眠障礙的研究進展
賴小英 陳麗君
(廣西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南寧,530021)
腫瘤患者常常合并有抑郁、焦慮、疲乏等癥狀,睡眠障礙也是腫瘤患者較常見的癥狀。有研究結果顯示,睡眠障礙在腫瘤患者中的發生率為30%~88%[1]。隨著腫瘤診療技術的提高,越來越多的患者可獲得長期的生存。腫瘤患者的睡眠障礙即可出現在腫瘤診斷后、治療前、治療過程中及治療后[2-3]。睡眠障礙不僅可影響腫瘤患者的日常功能,降低患者的生命質量,甚至影響預后降低腫瘤患者的生存[4]。故本文對腫瘤相關睡眠障礙的流行病學、發生機制、影響因素及治療方法進行綜述,為減輕腫瘤患者睡眠障礙的程度、降低睡眠障礙的發生率、提高腫瘤患者的生命質量提供理論基礎。
1 腫瘤患者睡眠障礙的流行病學
睡眠障礙可在腫瘤治療前、治療中及治療后出現。有研究結果顯示,腫瘤患者治療前使用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測試患者的睡眠,其睡眠障礙的發生率為26%~57%[5-6]。在治療過程中,有研究對823例不同腫瘤類型患者在第1周期化療后第7天評價患者的睡眠,有36.6%患者有失眠癥狀,43%患者達到失眠綜合征的診斷標準。在治療后,對肺癌患者化療后進行調查的結果顯示約69%的患者有睡眠障礙[7]。鼻咽癌患者放療結束后1周內高達64.7%的患者睡眠質量差[8]。而一項Meta分析結果顯示中國普通人群中僅有15%出現失眠[9]。Leger等[10]大樣本研究結果顯示意大利及法國普通人群失眠發生率約為37%,美國約為27%,日本則為6.6%。上述研究結果提示腫瘤患者睡眠障礙的發生率往往高于普通人群。
腫瘤患者的睡眠障礙可持續存在。對962例不同腫瘤類型患者研究隨訪結果顯示治療后18個月仍有36%的腫瘤患者有睡眠障礙(18月前基線水平為59%)[2]。在另一項研究中74%的腫瘤患者開始時存在失眠,而3年后仍有46%的患者存在失眠,特別是對于既往有失眠、女性及年齡較大的患者更易持續失眠[11]。
2 腫瘤患者睡眠障礙的發生機制
由于患者群體來源、腫瘤類型、治療方案及生活方式等因素的不均一性,目前腫瘤相關睡眠障礙的機制尚不明確,但與控制睡眠及覺醒的相關神經環路相關,主要有下丘腦及腦干,而特定神經群釋放的神經遞質/調質對控制覺醒狀態起主要作用。下丘腦泌素/食欲素(Hypocretin/Orexin,HO)神經元表達的hypocretin-1及hypocretin-2是哺乳動物調節睡眠和覺醒的多肽類神經調質。實驗研究結果顯示下丘腦神經元對睡眠及覺醒之間的轉換必不可少,刺激小鼠此部位神經元可持續抑制非快速眼動(Non-rapid Eye Movement,NREM)睡眠從而引起覺醒[12],而通過轉基因干預此神經元可導致嗜睡或昏睡[13]。與HO神經元相融在下丘腦的黑色素聚集激素(Melanin Concentrating Hormone,MCH)神經元在快動眼(Rapid Eye Movement,REM)睡眠時活動明顯,在NREM睡眠活動較少,而覺醒狀態時則靜止。有研究表明小鼠敲除MCH會出現REM睡眠異常,NREM睡眠減少,覺醒增多[14]。下丘腦腹外側視前區(Ventrolateral Preoptic Nucleus,VLPO)的神經細胞主要包括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γ-GABA)能神經細胞及甘丙肽能神經細胞,是促睡眠調節中樞之一[15]。VLPO主要與NREM睡眠相關,而Extended VLPO則與REM睡眠相關,這些區域的細胞受破壞可抑制NREM睡眠及REM睡眠。中腦腹側被蓋區(Ventral Tegmental Area,VTA)多巴能神經元與REM睡眠相關,其激活會促進覺醒[16]。另外中縫背核的血清素(5-HT)能神經元及藍斑(LC)去甲腎上腺素能神經元也參與睡眠及覺醒的調節。所有腫瘤存在固有免疫及適應性免疫細胞浸潤,腫瘤可通過炎癥機制作用于腦睡眠及覺醒中樞從而引起睡眠的改變。中樞或全身注射IL-1β可增加NREM睡眠δ波,而通過給予中和抗體或IL-1β受體拮抗劑抑制IL-1β使自發性NREM睡眠減少[17-18],但高劑量IL-1β卻抑制REM睡眠[19]。IL-6在覺醒時水平較低而睡眠時達到高峰[19],人體皮下注射IL-6可增加慢波睡眠并減少REM睡眠[19],IL-6對睡眠的影響呈時間及劑量依賴性。而TNF可促進NREM睡眠及慢波睡眠。
3 腫瘤患者睡眠障礙的影響因素
腫瘤患者睡眠障礙的影響因素除了不良生活習慣及睡眠衛生如營養不良、吸煙、飲酒或飲用含咖啡因飲料等以外,還包括人口統計學資料、并發癥狀及抗腫瘤治療等。
人口統計學資料包括患者性別、年齡、文化水平、卡氏評分(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 Scale,KPS)、婚姻狀況、收入水平等。在一項對820例晚期腫瘤患者睡眠調查的研究結果顯示,年齡、KPS及文化水平與患者睡眠相關,年齡較小、KPS得分較低的患者更易合并睡眠障礙,而接受過中學或者本科教育的患者則較少出現睡眠障礙[20]。Miaskowski等[21]對前列腺癌患者睡眠的研究也支持年齡較小的患者較易出現睡眠障礙。另有研究支持文化程度較低的患者越容易合并睡眠障礙[22]。一項對1903例腫瘤患者睡眠隨訪長達9年的研究結果顯示經濟困難與患者的睡眠質量差及睡眠障礙相關[23],低收入的患者睡眠質量更差[24]。然而,也有研究結果表明腫瘤患者睡眠與性別、年齡、婚姻及文化水平等無關[8,25]。腫瘤患者的睡眠質量與人口統計學資料的關系尚需進一步研究。
睡眠障礙是腫瘤患者常見的癥狀,但患者往往合并焦慮、抑郁、疲乏及疼痛等,部分患者以癥狀群的形式出現,這些癥狀與患者睡眠密切相關[24,26],合并這些癥狀的患者往往睡眠更差。在腫瘤治療方面,患者化療及放療均可對患者睡眠產生影響,接受過化療或放療的患者更易出現睡眠障礙[27]。其他與睡眠障礙相關的有糖尿病史、關節疼痛、潮熱等[28]。另有研究顯示獨居、失業、惡心、手足麻木、化療引起的發熱及晚期腫瘤也是腫瘤患者睡眠障礙的高危因素[29]。
4 腫瘤患者睡眠障礙的非藥物治療
腫瘤患者睡眠障礙的治療包括藥物治療和非藥物治療。本文重點介紹常見非藥物治療在腫瘤患者睡眠障礙中的研究進展。
4.1 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認知行為療法主要從睡眠限制、刺激控制和認知重建3個方面進行多維度干預,通過睡眠衛生和放松訓練2個潛在的輔助手段改善睡眠。Meta分析結果顯示,認知行為療法在改善腫瘤患者睡眠效率、入睡時間、覺醒時間和失眠癥狀的嚴重程度方面有重要意義[30]。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也支持認知行為療法可改善腫瘤患者的睡眠。然而,認知行為療法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通過網絡或者視頻進行認知行為療法干預,患者的睡眠效果并不及面對面的互動干預,運用互聯網對腫瘤患者進行認知行為干預仍待進一步考究。
4.2 正念療法(Mindfulness-Based Therapy) 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正念療法可改善腫瘤患者相關睡眠障礙,通過標準訓練方法如正念壓力減少、正念癌癥康復或正念認知療法(共通點為正念的聚集,即對當下開放的、不反抗、不評判的理念)及各種冥想訓練(包括站立、坐姿和行走等),提高患者的正念意識,并逐漸增加冥想時間,從而改善睡眠。有研究對失眠的乳腺癌患者進行正念減壓干預6周后,患者的客觀睡眠明顯改善,總體睡眠時間增加,干預12周后患者的睡眠效率、睡眠時間和夜間睡眠時間均有較大改善[31]。在化療期間對乳腺癌患者進行正念減壓干預,結果顯示正念減壓療法可改善患者的睡眠質量[32]。正念療法改善腫瘤患者的睡眠質量可能是通過改善非特異性的并發癥如抑郁、焦慮和痛苦等發揮作用。
4.3 瑜伽(Yoga) 瑜伽是一種集冥想、放松、想象、控制呼吸、伸展肢體及體力運動于一體的健身項目。瑜伽的修煉主要涉及人的心靈、呼吸和身體3個方面,因此修煉者要追求和掌握心靈、呼吸和身體三者的聯結、統一和控制,最終達到身心和諧,從而改善睡眠。瑜伽影響睡眠的機制可能取決于瑜伽的類型。Mustian等[33]對410例癌癥幸存者采取為期4周的瑜伽干預,結果顯示瑜伽鍛煉可以顯著提高患者的睡眠質量,并減少催眠藥物的使用,但體動記錄儀結果并未發現其可改善患者的客觀睡眠。對91例遠處轉移乳腺癌患者進行綜合瑜伽干預鍛煉后,患者的主觀睡眠效率明顯提高[34]。然而,也有研究表明西藏瑜伽并不能改善正在接受化療的乳腺癌患者的睡眠質量[35]。提示瑜伽是否改善腫瘤患者睡眠質量尚存一定的爭議,有待進一步研究。
4.4 其他 有Meta分析結果顯示,氣功/太極可改善腫瘤患者的睡眠質量[36]。針灸作為中國傳統的治療手段,可提高患者的睡眠質量[37],原因可能為針灸刺激了中央或自主神經系統釋放去甲腎上腺素、褪黑素、γ-氨基酸和β-內啡肽從而影響患者睡眠[38-39]。目前腫瘤相關睡眠障礙非藥物治療手段作用機制尚未明確,未來期望更多研究證實非藥物治療手段可改善腫瘤相關睡眠障礙。
隨著腫瘤患者生存率的提高,患者對生命質量的要求也逐漸提高,在以患者為中心的整體性照護的時代背景下,解決腫瘤患者睡眠問題顯得越加迫切,在未來應常規評估腫瘤患者的睡眠質量,并尋找相關危險因素,對高危患者進行適當的預防或干預,從而提高患者的生命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