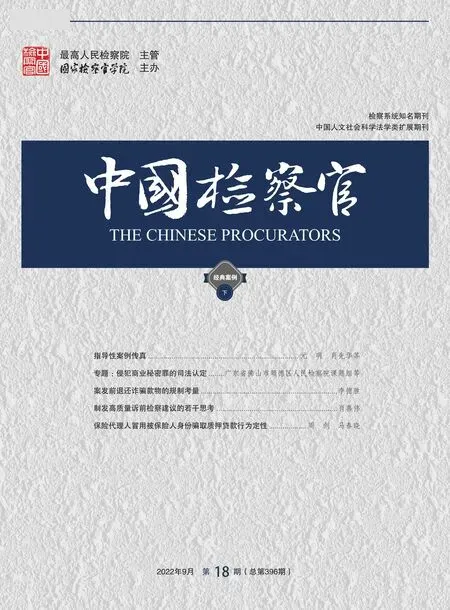“以票配貨”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是否構罪
● 鄭 巖 宋光恩 吳 劍/文
一、基本案情
A公司系寧夏T市經營廢舊物資回收的企業,是一般納稅人,主要經營廢鋼加工、銷售業務,經營模式為從散戶手中收購廢鋼后出售給下游鋼廠,包括兩種方式,一種是收購后加工再出售,A公司自稱為“自營模式”,一種是組織散戶將廢鋼直接運送到鋼廠,A公司稱之為“組織經營模式”。無論何種方式,收購時散戶均無法向A公司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但A公司出售時需要向下游鋼廠開具增值稅銷項發票。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 A公司為抵扣稅款,在時任副總經理被告人王某的決定下,經王某甲介紹,從遠在山東省的B公司等20多家無實際經營的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5000余份,價稅合計6億余元,稅額共計8784萬余元,A公司全部用于抵扣稅款并自制憑證下賬,且為逃避監管進行了資金回流。開票公司與受票公司之前互不認識,雙方從來沒有過真實業務往來,A公司支付的開票費為價稅合計金額的7%-8%。
二、分歧意見
本案自營模式中,A公司買貨加工后出售,是最常見的經營增值,增值稅本身就是針對商品或者應稅勞務在流轉中的增值設立的稅種,A公司出售時向下游鋼廠開具銷項增值稅專用發票自然是合法的,不存在爭議。爭議點為組織經營模式中A 公司向下游鋼廠開票是否合法。A公司為抵扣發票銷項,根據“自營”“組織經營”中收購的散戶廢鋼情況,從B公司開票,“以票配貨”,此種情形是否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
第一種觀點認為A公司在組織經營模式中給下游鋼廠開票不構成犯罪,根據自營模式和組織經營模式中散戶的真實交易,從B公司等20多家公司“以票配貨”,取得進項用于抵扣銷項,也不構成犯罪。理由為涉案發票是根據A公司實際收購的貨物情況開具的,有對應的真實交易,A公司之所以從B公司開票是因為散戶無法向其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這種模式在廢舊物資行業較為普遍。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廢舊物資回收經營業務有關稅收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國稅函〔2002〕893號文件”)規定,廢舊物資收購人員(非本單位人員)在社會上收購廢舊物資,直接運送到購貨方(生產廠家),廢舊物資經營單位根據上述雙方實際發生的業務,向廢舊物資收購人員開具廢舊物資收購憑證,在財務上做購進處理,同時向購貨方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或普通發票,在財務上做銷售處理,將購貨方支付的貨款以現金方式轉付給廢舊物資收購人員。鑒于此種經營方式是由目前廢舊物資行業的經營特點決定的,且廢舊物資經營單位在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時確實收取了同等金額的貨款,并確有同等數量的貨物銷售,因此廢舊物資經營單位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違背有關稅收規定,不應定性為虛開。A公司的組織經營模式與該規定非常契合,A公司向下游鋼廠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是根據真實交易的“如實代開”,不構成犯罪。同理,不論自營模式還是組織經營模式都是散戶向A公司的真實供貨,B公司等20多家公司根據這些真實供貨向A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也可以視為B公司代散戶向A公司“如實代開”,根據國稅函〔2002〕893號文件,也不應認定為犯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A公司組織經營模式中給下游鋼廠開票構成犯罪,自營模式和組織經營模式中從B公司“以票配貨”,用于抵扣也構成犯罪。理由為國稅函〔2002〕893號文件雖然認可組織經營模式,但國稅函〔2002〕893號文件本身是否符合刑法規定有待商榷,組織經營模式中貨物流是散戶到鋼廠、發票流是A公司到鋼廠,資金流是鋼廠到A公司到B公司再到散戶,“三流”不一致。鋼廠涉嫌從A公司買票匹配到散戶交易上,是為了非法獲得進項,A公司向鋼廠開票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因B公司等20多家公司并未參與A公司收購廢鋼的業務,A公司為了抵扣開具到鋼廠的銷項,從B公司等20多家公司買票抵扣的行為也構成犯罪,犯罪數額是進項和銷項的稅額之和。
第三種觀點認為A公司組織經營模式中給下游鋼廠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不構成犯罪,但從B公司開具發票“以票配貨”用于抵扣,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根據國稅函〔2002〕893號文件的規定,組織經營模式中,A公司根據散戶供貨向鋼廠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現象,在廢舊物資行業比較普遍,廢鋼是由A公司聯系并組織散戶運到鋼廠的,A公司實際參與了業務聯系,本質上與自營模式的先買后賣沒有區別。因此,A公司組織經營模式符合國稅函〔2002〕893號文件規定,向鋼廠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嚴格按照散戶供貨情況開具,并不違法,也不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同時,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檢、相關規范性文件規定,如果能夠證實開票方系沒有實際經營業務的開票公司,則不適用國稅函〔2002〕893號文件規定,開票行為構成犯罪的,適用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經查實,B公司等20多家公司系無實際經營的走逃公司,存續時間均在1年以內。因此,A公司為了抵扣開給鋼廠的銷項從B公司等20多家公司購買進項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還要回到刑法層面上予以認定。而是否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關鍵是看A公司是否有騙取稅款的目的、是否給國家稅款造成了損失,本案中因A公司“以票配貨”的目的是為了抵扣稅款,支付的開票費點數遠遠低于稅點,客觀上給國家稅款造成了損失,因此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理由如下:
(一)A公司組織經營模式合法,因其真實參與了聯系散戶向鋼廠供貨,故按照散戶真實供貨情況向鋼廠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廢鋼是大宗物品,如果無需加工的話,現實中沒有必要先運到A公司再送貨至鋼廠。散戶按照A公司指令直接送貨到鋼廠,是經營回收公司將先買后賣的兩次交易縮短為一次供貨,客觀上縮短了交易環節,節約了資源。根據國稅函〔2002〕893號文件規定,鑒于廢舊物資行業的經營特點,A公司作為廢舊物資經營單位,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違背有關稅收規定,其行為不應定性為虛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是行政犯,既然不違反稅法,自然不能評價為犯罪,這也符合公眾對期待可能性的認知。同時,根據最高法研究室《〈關于如何認定以“掛靠”有關公司名義實施經營活動并讓有關公司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的性質〉征求意見的復函》(法研〔2015〕58號),如果是散戶先與鋼廠之間有了合作意向,為了給鋼廠開票主動找A公司合作,掛靠在A公司名義之下供貨,此種行為亦不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這兩種業務模式是經濟交往形式和市場主體多元化的體現,恰恰說明了市場經濟的活躍,傳統機械根據“三流”不一致就認定為虛開的觀念在現代經濟中已經過時,應當摒棄,國稅函〔2002〕893號文件是適應市場做出的變通,有積極意義。
(二)A公司為抵扣稅款,“以票配貨”從B公司等20多家公司開票,客觀上造成了國家稅款損失,主觀上有騙取稅款的目的,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1.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應以主觀上有騙取稅款的目的、客觀上給國家稅款造成了損失作為入罪標準。1994年我國稅制改革,對增值稅實行憑票抵扣制度,隨即出現通過虛開騙取國家稅款的行為。1979年刑法未規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為打擊虛開行為,1995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了單行刑法《關于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規定了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法定最高刑為死刑;1997年3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入刑。
本罪是具體危險犯、抽象危險犯還是實害犯,是否存在未遂、以開票稅額還是以抵扣稅額作為犯罪數額,對為了向下游虛開而從上游虛開的,犯罪數額是雙向累加還是取單向較大值,理論和實踐中多有爭論,各地在執行標準上也不盡一致。近年來,最高法通過會議紀要[1]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經濟犯罪案件審判工作座談紀要》規定:主觀不以偷逃稅款為目的,客觀上未造成國家稅款損失,不應認定為犯罪。、復函[2]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如何認定以“掛靠”有關公司名義實施經營活動并讓有關公司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的性質〉征求意見的復函》(法研〔2015〕58號)。、無罪判例[3]參見《蘆才興虛開抵扣稅款發票案——虛開可以用于抵扣稅款的發票沖減營業額偷逃稅款的行為如何定性》,載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第二庭:《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7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的形式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作了入罪限縮,認可了“掛靠”的合法性,將為了虛增業績、環開、虛增實力用于談判等不具有騙取稅款的目的,同時未給國家稅款造成損失的行為認定為無罪,認為本罪主觀上須具有騙取稅款的目的,客觀上給國家稅款造成了損失。目前對主觀的入罪標準認識較為統一,但客觀上是否必須造成稅款損失仍有爭議[4]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姚龍兵認為沒有造成稅款損失一概不認為是犯罪的觀點是放縱犯罪,主要觀點參見《論“有貨”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之定性》,《人民法院報》2019年9月26日。。筆者認為,從實務角度考察,客觀上本罪法定刑偏重(根據司法解釋規定,虛開數額250萬元以上為“數額巨大”,法定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至無期徒刑),而實務中虛開數額在250萬元以上的情形比比皆是,如果入罪門檻低,勢必過于嚴苛,造成打擊面過大。因此,除數額標準外,結合司法判例及理論觀點,以主觀上具有騙取稅款的目的、客觀上給國家稅款造成了損失作為入罪標準能夠有效縮小打擊面,保持刑事司法謙抑,更有利于實現懲治與保護并重的目的,為企業發展營造相對寬松的司法環境。
2.開票費點數是認定國家稅款損失的切入點,也是判斷受票公司是否具有騙取稅款的目的的重要依據。增值稅是以商品(包括應稅勞務)在流轉過程中產生的增值額作為計稅依據而征收流轉稅,征收對象是交易環節中的新增價值。該稅種有三個特征,一是只對增值部分征稅,沒有增值不征稅,在流轉中存在重復申報,因此需要用抵扣方式避免重復征稅;二是“先繳后抵”原則,交易主體抵扣的權利來自繳納,正常情況下,上游開票后依法申報納稅,稅款雖然是上游繳納的,但實際是下游以支付含稅貨款的形式承擔的,因此下游取得發票后可以用于抵扣,抵扣權源于先行繳納;三是由消費者最終負擔,增值稅為國家委托中間環節代理收稅,因消費者不再進行商品流轉,無法使商品再次增值,因此不能再進行抵扣。
從2019年以來筆者所在轄區辦理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類案來看,開票費點數多在6%-8%之間,發票來源常見的有四種:(1)從上游虛開后向下游虛開,買票賣票;(2)從稅務局領票開票,次月不繳稅走逃[5]在現有“金稅三期”全國稅收管理信息化系統之下,開票留痕,對異常開票能及時監管,此類案例減少。;(3)向下游賣貨不開票,將多余的票賣給第三方,即“富余票”;(4)開票費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利用政策賣票賺差價。第(2)種一般是暴力虛開公司,沒有正常經營,第(1)、(3)、(4)種涉案單位可能既有正常經營也有違法虛開,本案B公司等20多家開票公司都是第二種沒有實際經營的暴力走逃公司。無論是哪一種,開票公司都必須首先保證自己有足夠的進項以抵扣開出的銷項,不用真實繳稅,否則,根據“金稅三期”征管系統一開票就必然申報,必須繳納貨物價值17%的稅(以本案案發時的稅率為例),轉算后約是價稅合計金額的14.53%。換言之,A公司只有支付14.53%的開票費,且上游合法申報納稅,才不會造成稅款損失,根據“先繳后抵”原理,A公司才有抵扣的權利。
本案中,A公司支付的開票費是7%-8%,遠遠低于14.53%,A公司及中間介紹人明知開票公司不會替A公司繳納足額稅款,會造成稅款損失,依然買票用于抵扣,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王某供述買票的目的就是為了抵扣,因此,如果不買票抵扣就需要全額納稅,A公司實質上是通過低成本的違法開票逃避高成本的納稅義務,自然不會支付14.53%以上的開票費。同時,如果不能夠通過異常進項來抵扣開到A公司的銷項,B公司等開票公司勢必“賠本賣票”,不符合常理,本案中B公司等20多家公司系以更低的開票費點數,從上游購買發票用于抵扣開到A公司的發票賺取差價。A公司經王某甲介紹方知道B公司等20多家開票公司的存在,雙方除買賣發票外沒有過任何往來,供貨散戶都是A公司自己聯系的本地個體戶。A公司明知遠在千里之外的B公司等20多家公司與自己沒有任何交情、與散戶沒有掛靠關系,自然明知開票公司不會賠本替自己承擔稅款,也不可能將稅款以掛靠費的形式轉嫁給散戶。因此,A公司能夠判斷出開票公司低價賣票行為異常,能夠預見到開票公司進項可能來路不明,也應當預見到買賣發票的行為會造成稅款損失。反之,如果A公司支付的開票費點數是14.53%(可能出于其他目的,比如為了少繳企業所得稅虛構成本),不宜認定其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因為從增值稅角度來說,其已經將足額稅款交給了B公司,如果B公司依法納稅,自然不會造成國家增值稅款損失。即便B公司不合法繳稅造成稅款損失,也不能歸責于A公司,因為根據“先繳后抵”原理,A公司有抵扣的權利。
(三)“有貨開票”如果主觀上有騙取稅款的目的、客觀上造成國家稅款損失,依然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法益是入罪的基礎,本案以開票費點數為切入點能夠推導出受票方低價買票行為造成了幾千萬元的稅款損失,開票方、中間介紹人對受票方騙取稅款的目的都是明知的,即便按照筆者認為的較高的主客觀入罪標準,也已經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實踐中,類似“以貨配票”的案例不在少數,行為人往往以“有貨”作為出罪的辯解,對于此類案件如果不嚴厲懲治,便是對法益侵害行為的視而不見,勢必導致打擊不力,并形成錯誤的價值導向。可見,是否構成本罪,與是否“有貨”沒有必然關系。山東省人民檢察院典型案例中有“以票配貨”構成虛開的案例,“有貨虛開”一定不是犯罪的觀點得到法官的批判[6]參見姚龍兵:《論“有貨”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之定性》,《人民法院報》2019年9月26日。,認為構成本罪必須有騙取稅款的目的,而有真實交易與是否有騙取國家稅款目的之間沒有必然聯系,“有貨”型虛開犯罪,行為人在買貨環節沒有繳稅,以從第三方取得的發票(大多是購買)抵扣稅款,是將交易成本轉嫁給國家,與無貨套取稅款沒有本質區別,判斷是否屬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行為,不能基于“有貨”“無貨”這個標準,有貨的虛開也可構成犯罪,“無貨”的“虛開”,如果不是為了騙取稅款的目的,也不能以本罪論處。
同時,國稅函〔2002〕893號文件是針對廢鋼行業慣常存在的經營模式做出的變通,前提是不違背稅收規定,更不能違反刑法,公檢法三機關對該函所做回復,類似于注意規定,即便不做說明,如果行為模式符合騙取稅款主觀目的,且客觀上造成稅款損失,也應當認定行為人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