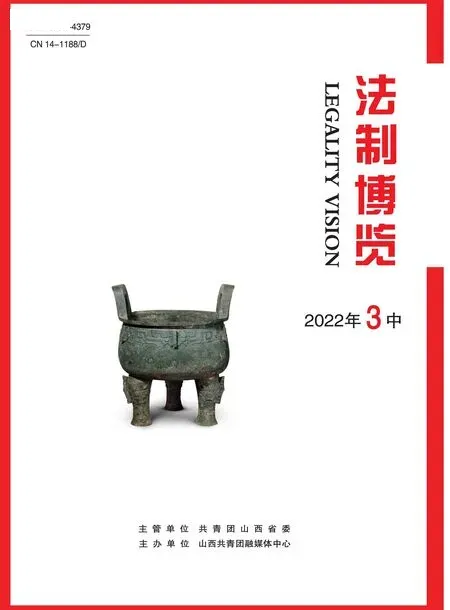基于醉酒駕駛情形談危險駕駛罪
康瑞超 凌海軍 范曉劍
陜西理工大學,陜西 漢中 723001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至今,關于酒駕入刑的規定,廣為法律學界和社會人士所爭議。現如今,“醉駕”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一度成為刑事追訴第一大犯罪。基于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和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需要,我們有必要將醉酒駕駛納入刑事處罰制度,但是從目前實施的效果上來看,也反映出了一些問題。
一、我國酒駕入刑的必要性探究
2011年酒駕規定入刑以前,我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2007修正)》第二十二條規定飲酒后駕駛機動車、醉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行政處罰。隨著我國經濟持續穩步發展,人均收入水平的顯著提升,全國公路建設四通八達,機動車數量節節攀升,具有駕駛資格人數與日俱增。這也負面地導致我國的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呈多發頻發態勢,因酒后駕駛造成的社會危害更是慘不忍睹。
2008年世界衛生組織在關于車禍致死的事故調查中得出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是酒后駕駛的結論。我國公安部于2009年8月15日至2009年12月30日,在全國部署開展嚴厲整治酒后駕駛交通違法行為專項行動,在整治期間共查處了酒后駕駛違法行為30.4萬起,其中引發交通事故的是1382起,事故中死亡600人,受傷1573人。
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將醉酒駕車情形定義為危險駕駛犯罪,在社會層面引起廣泛的討論,褒貶不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第一百三十三條新增: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修正)》適時修改第九十一條,對于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醉酒駕駛營運機動車的,適用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規定,同時加重了行政處罰的力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規定的出臺,更為科學合理地應對伴隨經濟增長呈現的新領域犯罪形態,更加有效地懲治和預防犯罪。犯罪預防是指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犯罪的原因和因素,對可能犯罪的人進行早期防御和矯正,以減少或消除犯罪行為發生的活動。所以基于社會形式的變化,為了達到預防與懲罰并重效果,有必要將醉酒駕駛納入刑事處罰體系中。
二、酒駕入刑的法律規定存在的缺陷
危險駕駛罪規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醉酒駕駛作為一種犯罪形式,法律規定其與情節惡劣的追逐競駛,嚴重超過額定乘員載客或規定時速行駛的校車業務或者旅客運輸,以及違反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規定運輸危險化學品危及公共安全的行為并重,應予刑事處罰。從一般公眾視角理解該條款,難以想象“醉酒”一詞可以和“情節惡劣”“嚴重超過”“危害公共安全”這些限定修飾詞語產生同等的危害,這也是酒駕現象屢禁不絕的一個原因。懲罰性法律條款如果符合社會大眾的理解和認知,罪責刑相適應,那么就可以起到規范社會秩序的作用。
“兩高一部”出臺的《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明確: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屬于醉酒駕駛機動車,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第一款的規定,以危險駕駛罪定罪處罰。這一關于體內酒精閾值的規定,為司法辦案人員具體如何適用醉酒駕駛情形的危險駕駛罪認定,提供了直接的標準。危險駕駛罪屬于抽象危險犯,指足以產生嚴重危害結果的行為,并不要求實際發生危害結果。懲罰危險駕駛的行為,在于其存在潛在的巨大危害,將對社會造成不利影響。飲酒人員駕駛車輛,總是過于相信駕駛技術,認為可以逃避處罰,很少去考慮自身血液酒精含量值的多少,亦存在少喝一點可以開車的錯誤認識。
根據最高檢發布的2021年1至9月全國檢察機關主要辦案數據,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和決定逮捕各類犯罪嫌疑人670755人,同比上升20.6%;從起訴罪名看,排在第一位的是危險駕駛罪263281人,同比上升30.6%。距離危險駕駛罪入刑已經過去了十年之久,我們對更多的危險駕駛違法犯罪者進行了懲處,極大地降低了社會危害。貝卡里亞認為,刑罰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殘折磨一個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業已犯下的罪行,而僅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規誡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1]。我們實現了提前阻止罪犯侵犯公民的保護作用,但是“規誡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似乎難以完成,從根源上降低危險駕駛罪的危害還有待加強。
三、完善我國危險駕駛罪中醉酒駕駛情形入罪的幾點意見
(一)新設罪名,將醉酒駕駛情形的危險駕駛行為單列為《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三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情形中新增加從事校車業務或者旅客運輸中嚴重超過額定乘員載客或者嚴重超過規定時速行駛的違法行為,以及違反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規定運輸危險化學品危及公共安全的違法行為。事實上成立醉酒駕駛情形的危險駕駛罪顯然已經成為主要犯罪行為,我們有必要再一次通過法律修改和完善的手段,將酒駕行為上升到新設罪名,這樣不僅能夠引起普通民眾思想上的重視,更能凸顯法律的強硬態度,向全社會傳達出公安和司法機關懲治醉酒駕駛違法犯罪行為的堅定決心。
在危險駕駛罪的法條具體規定中,醉酒駕駛情形屬于將行為人的犯意產生默認在飲酒或者過度飲酒后開車的瞬間,后面駕駛車輛前行則是放任這種危害繼續發生,直接認定駕車行駛時就屬于故意犯罪。實際上交通警察執法檢查酒駕,也采用的是案發時車輛在道路上行駛、現場測量駕駛員體內酒精含量超標的認定辦法。另外,追逐競駛、嚴重超載或者超速,以及違反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規定危及公共安全的行為,需要考慮具體情節,來判斷犯罪人犯罪行為所產生的社會危害性。相比較而言,醉酒駕駛情形更容易確定為犯罪。
我國于1979年《刑法》第一百六十條規定產生、1997年修訂時被取消的罪名流氓罪,當時根據不同構成犯罪的情形將其分解為強制猥褻罪(現為強制猥褻、侮辱罪)、猥褻兒童罪、聚眾淫亂罪、聚眾斗毆罪、尋釁滋事罪等罪。應當廢除流氓罪罪名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我們此刻討論的是這種修訂法律的精神值得借鑒的,適時地將一個罪名構成犯罪的情形分開單獨成罪,似乎同樣是更有利于打擊犯罪和維護社會治安。無論立法者多么充滿理性和睿智,他們都不可能全知全覺地洞察立法所要解決的一切問題,也不可能基于語言文字的確定性和形式邏輯的完備性而使法律文本的表述完美無缺、邏輯自洽[2]。在適當的時候,要去解決社會上醉酒駕駛的突出問題,這是立法時不能完全預料的,我們有必要通過新設罪名,從立法上去維護社會秩序。
(二)兼顧醫學和生理標準,在量刑上有所區分。根據《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GB19522-2010)中明確的醉酒駕車是指機動車駕駛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mg/100ml的一種駕駛行為,有學者針對這個標準提出異議,認為一概以80mg/100mL的標準難以區分不同人群對于酒精的耐受力。對于生理醉酒的人來說,一杯酒就足以使其失去正常人的理性判斷,而對于體內具有大量的乙醛脫氧酶、代謝率高的人,我們是否可以采取更高的閾值來計算。
法律不僅要保護遵紀守法的公民,對于觸犯法律的犯罪分子,同樣也應該給予保護,這與現代法治國家建設的總目標是一致的。在面對國家執法、司法機關時,犯罪分子也是弱勢,我們國家司法審判追求的公平正義,是對于每一起司法案件、每一個當事人而言的,絕不僅僅是為了還原一個真相。當然,我們反對絕對確定的法定刑,那相當于讓司法機關喪失了自由裁量權一樣,違背區別對待的政策。
筆者認為,法律的制定實施,是為了警示教育他人,不得已才對違法犯罪的人進行懲罰。《刑法》雖然明令禁止酒駕,但是我們也需要考慮個體的差異性,可以在確定犯罪后,結合實際,在量刑上有所區別對待,兼顧醫學和生理標準,這樣更能體現法律在執行時的公正。例如:對于血液中酒精含量同樣是85mg/100ml的醉酒駕駛者甲、乙、丙,甲具是正常人的身體狀況,我們可以嚴格按照酒精含量閾值執行;乙屬于酒精過敏體質,頭腦已經完全失去控制,此時乙的危害可能性更大,我們可以高于正常標準量刑;丙具有很高的酒精耐受力,雖然此時血液酒精含量已經屬于醉駕范圍,但是丙思維沒有混亂,依然可以控制車輛,社會危害性顯著低,我們可以低于正常標準進行量刑。
(三)增加主刑適用,法定刑升格至一年有期徒刑。《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規定:醉酒駕駛處拘役,并處罰金。《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規定了飲酒駕駛、醉酒駕駛均五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面對居高不下的危險駕駛罪犯罪案件數量,有的學者提出刑事處罰太輕,甚至應該將法定刑升格至有期徒刑,提高犯罪違法成本。我國在醉酒駕駛情形的危險駕駛罪司法案件的處理過程中采取對被告人適用緩刑的制度,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中規定,關于構成危險駕駛罪的“可以在一個月至二個月拘役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根據危險駕駛行為等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事實”“考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處罰;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恰恰是我國刑法罪刑相適應原則的體現。但是我們仍然有必要針對社會危害程度大、再犯的情形,在刑罰適用上法定刑升格至有期徒刑。“一至六個月的拘役,并處罰金”的刑罰評價,不能完整地涵蓋不同醉酒程度、不同危害程度的危險駕駛行為,司法實踐中法官適用刑罰也具有一定選擇困難。
與世界他國相比,目前我國關于危險駕駛罪的處罰刑期明顯偏少。日本的《新道路交通法》規定醉酒駕車者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德國刑法》中規定危害公路交通安全罪和酒后駕駛罪,適用五年以下自由刑;英國作為判例法國家,對構成放任駕駛罪判處罰金或者兩年監禁,或并處罰金和監禁;美國紐約州的車輛與交通法規中規定初次酒后或吸毒后駕車的可判處一年至七年有期徒刑。
筆者認為,對于危險駕駛罪適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更為合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二所規定的“高空拋物”條款,適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如果將一個重度醉酒的人駕駛車輛行駛在公路上的危害程度同一個在高層建筑室內向室外投擲物品的人所產生的社會危害程度進行比較,兩者均足以危害他人生命和財產安全,如果不加以控制,造成的后果難以估量。如果我們適用三年有期徒刑的規定,這是將抽象危險犯的危險進行擴大化了,畢竟危險駕駛罪的危險是推定的,并沒有產生實害結果。
邊沁的功利主義刑罰觀認為,以最大多數人的幸福作為衡量法律的好與壞[3]。法律是反映并調整一定社會關系的,我們判定醉駕入刑所產生的社會效果,不能簡單地以案件數來衡量。每一起案件的背后,都是對于國家安全、社會秩序、人民生命財產的維護。在危險駕駛罪的管控方面,同樣的危害依然大概率地發生在身邊,我們還沒有完全意義上實現刑罰的目的。
筆者認為,單純依靠刑罰難以徹底緩解酒駕帶來的社會之痛,這時我們需要更多的支持。一是增設行政處罰規定。例如:增加酒店、商超等大型停車場,對于顧客離店前酒駕行為的阻止義務,針對未履行義務產生不當后果的,可以進行一般行政處罰。二是采取技術監測手段。例如:在汽車出售階段,可以推廣適用車內酒精濃度監測報警儀器,提醒駕駛人員杜絕酒駕,甚至可以將車輛自動鎖死,迫使駕駛人員放棄選擇實施酒駕違法行為。三是增加同乘人員的民事責任。公安部于2009年在《關于修改酒后駕駛有關法律規定的意見(征求意見稿)》擬定增加“與醉駕司機同乘一車的乘客也應進行處罰”內容,時至今日,我們是否應該再次將此議案提起呢。此時亦可以選擇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自甘風險”條款,或者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條“好意同乘”條款,新增加類似“乘車人負有阻止駕駛員酒駕行為的義務,自愿乘坐酒駕人員車輛,對于因為駕駛人酒駕所產生的后果,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法律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