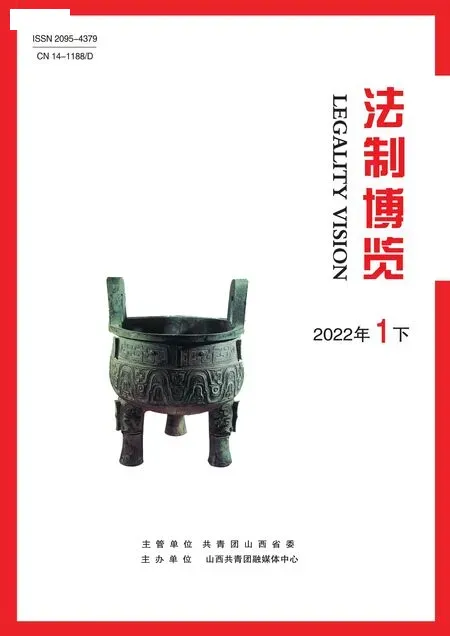居住權視角下“以房養老”的新進路
鄭 波
湖南云天律師事務所,湖南 長沙 410007
據2021年5月11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報告載明:我國目前人口總量約為14.12億人,60歲以上的人口為2.64億人,占18.7%(其中,65歲以上的人口為1.91億人,占13.5%),與2010年相比,60歲以上的人口上升5.44個百分點。人口的持續老齡化,對我國的養老事業形成了很大壓力。我國目前組建家庭的主力軍為80后和90后,據最新調查顯示,大多數的家庭結構均為:“4-2-1”“4-2-2”家庭,這也意味著在一個普通的家庭里,一對小兩口要承擔四個老人的養老和一到兩個小孩的撫養和教育,兩個人掙錢八個人花,壓力明顯很大,加上如今國家二孩政策全面放開并鼓勵有條件的家庭生三胎,我們國家面臨的養老形勢將會日益嚴峻。基于此,筆者在《民法典》物權篇增設居住權制度的宏觀背景下,嘗試初步探索“以房養老”的新模式、新進路。
一、居住權的創設及本質
居住權制度作為一項古老的法律制度,源自大陸法系的古羅馬帝國,當時的奴隸社會生產工具相對簡單,社會的整體生產力相當有限,因而古羅馬當時的整體財產非常有限且實行家長制,當時的“家長”(奴隸主)為保障“家長”之外的其他成員(有貢獻的奴隸)的居住利益,設立了居住權這種“為了照顧某一特定的人”的權利,作為用益物權之一種[1],換言之,居住權同時也是一種“為滿足特定權利人的居住需要為目的”的人役權,它具有高度的人身依附屬性,原因在于當時的古羅馬社會“無夫權婚姻和奴隸的解放日多,每遇家長亡故,那些沒有繼承權又缺乏或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的生活就成了問題,因此丈夫或家主就把一部分家產的使用權、收益權等遺贈給這一部分‘特定的人’,讓他們在生命復歸塵土之前有所依靠”[2]。在原《物權法》的立法過程中,關于設立居住權制度更是一波三折,關于居住權制度的規定最早見諸2002年全國人大法工委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的征求意見稿中,當時的全國人大為回應社會的需求和現實呼聲,首次提出為“切實保護老年人、離異婦女以及未成年人等弱勢群體居住他人住房的權利”,設專章,共八個條文。在接下來的人大法工委三次《物權法》草案審議稿均保留了這一制度的規定。2005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關于居住權制度的條文甚至增加至十二條。然而在2007年正式頒布的原《物權法》關于居住權制度的章節最終被刪除。是因為當時國內學術界的大多數聲音認為房屋租賃等權利的設定,已然能滿足人民的現實需求,增設居住權的實際效用并不大。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老百姓對住宅房屋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在國家確定“小步快進”編纂思路的《民法典》編纂過程中,立法機關認為,“為落實黨中央和國務院的要求,認可和保護民事主體(主要是針對普通老百姓)對住房保障的靈活安排,滿足一部分特定弱勢人群的居住需求,有必要創設居住權制度”①沈春耀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關于提請審議〈民法典各分編〉方案的說明》。。基于此,《民法典》在物權編增設了居住權的規定,這顯然是對《民法典》“小步快進”編纂思路一個理論上的重大突破。[3]依據《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條之規定:“居住權人有權按照合同約定,對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權,以滿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基于此規定,居住權最本質的特征在于通過將房屋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兩權分離,從而滿足民事主體也就是普通百姓對房屋的多元化需求。也正是基于此,探討“以房養老”的新進路才成為現實的可能。隨著我國老齡化逐年加劇的趨勢,且房屋自有率奇高,無論總體還是城鎮房屋自有率均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顯而易見,我們的養老事業如果光依靠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對于80、90后的肩膀而言明顯不堪重負,因此老年人如何自食其力,自籌養老資金,既讓自己的老年生活有保障,又能給子女減輕負擔,成為新時代養老事業的痛點和難點。基于我國目前房屋自有率居高不下的實際,目前最現實的途徑莫過于如何盤活老年人手中自有的房屋資產,而房屋的高價值性和低流通性決定了盤活房屋資產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現實難題。居住權的創設為破解這個現實難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進路。
二、養老事業面臨的現實困境
目前我國流行的養老模式,除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之外,新興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反向抵押模式(又稱倒按揭),此種模式(英文名:reverse mortage)起源于美國,和傳統的抵押模式不同的是,老人先以自己所有的房屋抵押給銀行等金融機構取得定期貸款,作為自己老年生活的必需開支,在約定的期限到期或者老人去世后,銀行等金融機構再處置老人抵押的房屋一次性償還老人生前的貸款。但這種模式與我國現行法律和制度存在著不可協調的矛盾,如果認定這一模式的實質是不動產讓與擔保,抵押人以不動產買賣合同為借款合同提供擔保,依照傳統讓與擔保的視角,和我國原《物權法》的原則是相違背的;如果認定這一模式中的擔保行為是虛偽意思表示,借款行為才是隱藏的真實意思表示,依據《民法典》一百四十六條之規定,虛偽意思表示下隱藏的法律行為效力是否有效尚且待定,該行為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等強制性規定則當然無效,如未違反,則該行為有效。自2006年兩會期間有代表提出“以房養老”提案被采納后,反向抵押模式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實踐結果并不理想。第二種模式為售后回租模式,此種模式由老人將自有房屋出售給銀行等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定期按每月支付老人生活費(其實質就是售房款分期給付),老人再向金融機構租回自己的房屋居住。但此種模式下,由于老人伊始將自有房屋出售給金融機構,已移轉房屋的所有權(屬于物權),之后回租房屋因租賃合同獲取的房屋使用權(屬于債權),基于債權的相對性和弱對抗性,這種模式對老年人這個弱勢群體而言,毫無疑問具有較高的風險。同時這種模式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保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三、“以房養老”模式的新進路
黨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指出,“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從根本上說,我國創設居住權制度的初衷是為了有利于盡快實現老百姓“住有所居”的目的,老子曾曰:“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可見“安其居”是老子倡導的理想,也一直是古往今來普通百姓對幸福美好生活最重要的向往,杜甫先生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愿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也是普天下所有老百姓最殷切的愿景。[5]長期以來,我國調整房屋利用關系主要依靠的是租賃權,但通過契約或者占有制度規范的租賃權明顯存在缺陷,租賃權僅僅只是一種債權,不足以有效制約所有權人和使用權人,[3]也難以對抗現實中的第三人,而居住權作為一種用益物權,居住是“由人類系統發出,以尋求和獲得更好的棲身場所為動機和目的,以建造、尋找、選擇以及使用、利用自己居住空間的方式和手段為行使。”[6]居住權通過合同或者遺囑的方式有效設立后,經登記公示后,具有絕對的對世效力。這是傳統的租賃權作為一種債權所難以企及的,也正是基于居住權的這種內在特質,可以為我們國家新時代正處于改革探索中的“以房養老”模式提供如下四種新的進路。
第一種新的進路:針對目前城市部分老人“以房養老”的現狀,有真實案例:南京有七旬老人A,老伴早逝,有自住房屋一套,為減輕獨子的負擔,決定自籌資金養老,于是與某金融機構B公司達成“設定居住權并以房養老”的協議,老人A在協議生效后將房屋所有權移轉給B公司,同時B公司在房屋上為老人A設定居住權,直至老人A離世,由B公司每月向老人A支付養老金,確保老人A生活品質不下降。同時該協議規定,在老人A的有生之年,B公司雖然可以取得協議項下房屋的所有權,但還不能實際占有該房屋,而只有等老人A身故之后,B公司才享有該房屋完整的所有權。這種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老人可以通過提前變現自己的房屋,將“死”的財產變為“活”的現金,自籌資金養老,有三大好處:一則將本為死后的錢拿到生前來花,改善了自己老年的生活品質;二則通過設定居住權保障自己“老有所養”;再則提前處置了房屋所有權,避免子女眾多的家庭因房屋出現遺產糾紛。[7]
第二種新的進路:針對目前城市部分老年人合資購房抱團養老的情形,有真實案例:成都市A女、B女、C女和D女因兒女大多已成年,幾個人厭倦了大都市車水馬龍的紛擾,于是集體逃離城市,在云南麗江鄉間尋覓到一處青山綠水、風景秀麗的所在,購買當地農民的自建房重新裝修,一起抱團養老。這個想法固然很好,但現實卻面臨一個重大的法律障礙:農民自建房的宅基地屬于當地集體所有,非當地集體戶口之間不得流通轉讓。在居住權創設以前,只能通過租賃合同以債權的形式取得房屋的使用權,毫無疑問,這對抱團養老的老年人而言具有較高的法律風險。而居住權作為一種用益物權,它的誕生,則很輕松地破解了這一法律難題:A、B、C、D四女通過與當地農民協商,盡管目標房屋的所有權無法流轉,但通過在該房屋的產權證上給A、B、C、D四女設立一個帶有期限的居住權(比如30年)并公示,這樣A、B、C、D四女就可以安心集資裝修該房屋,一起抱團養老。
第三種新的進路:針對我國再婚的老年婦女或者保姆等無房的弱勢群體,老人離世前往往想把自己居住的房屋所有權留給子女,畢竟在當今社會,房屋有可能是每個人能留在這個世界的最大一筆財產,但老人又會擔心一旦自己將房子遺贈給子女,等自己離世后,子女會趕走悉心照顧自己多年的再婚伴侶或者保姆,讓其無家可歸,甚至流離失所。居住權的設立則可以很好地為老人解決這一難題,老人可以通過遺囑將自己居住的房屋的所有權留給子女,但同時在該房屋上設立一個永久的居住權,這樣就可以既保證房屋的所有權留給子女,又能保障自己去世后,再婚的老伴或者保姆可以在該房屋上擁有居住權和使用權直至離世。
第四種新的進路:針對我國比較普遍的父母墊資購房的傳統,在城市尤為普遍,有真實案例:A男和B女系80后,2018年大學畢業后留在北京工作,想在北京買房,婚后定居北京,A男的父親C和母親D系長沙的普通工薪階層,通過一輩子辛苦的工作,攢了一套大三居和一臺車,銀行小有存款20萬,小日子本來過得不錯,但為了兒子A的事業和未來,二老決定賣了長沙的房子,資助兒子A在北京購房的首付款,同時兩人北上跟兒子一起生活,但又擔心將來兒子A在北京購房后,將房子登記在兒子A及其媳婦B的名下,二老對房屋不享有任何權利,萬一婆媳關系處理不好,有被掃地出門甚至流離失所的風險。我們都知道,中國的父母對自己的孩子從來都是最無私的,但據法院的統計數據表明,在當今的社會里關于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或父母與離異子女爭奪房屋產權的糾紛中,一開始中國的父母都是基于好意,傾囊甚至傾家蕩產資助剛成年的孩子購房以自立,但往往父母并不在房本上署名,一旦發生爭議,父母并不能就當初自己墊資購買的房屋提出任何主張,一旦家庭關系處理不好或者子女離異時導致房屋旁落甚至露宿街頭者亦不在少數。但如今通過居住權的創設,則能很好地為墊資的父母解決這一難題,父母既能因為親情為子女的購房事宜貢獻一份力,又能為自己的“老有所養”留有一條可靠的退路。
四、結語
在老齡化日趨嚴重的今天,養老問題是我們每個人終究要面對的現實問題。筆者認為,居住權作為古羅馬法的一種古老制度,其生命力已經歷經了歷史長河的檢驗,我們如何吸收其精華,結合我們國家層面制度的頂層設計和本土實踐,探索“養老”模式的新進路,實現“老有所養,住有所屋”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