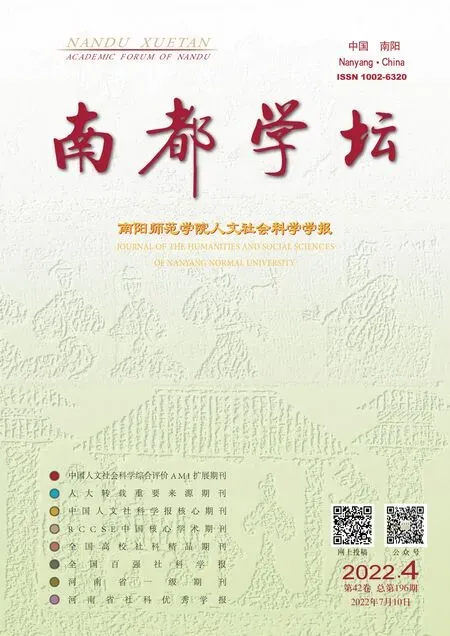七月詩派論詩歌創作的“形象力”
王 治 國
(南陽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南 南陽 473061)
就具體的詩歌形式問題而言,抗戰時期頗為流行的詩歌“形象化”理論是七月詩派要面對的一個理論話題。詩歌“形象化”理論并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如何在詩歌創作中“塑造形象”的問題,也是一個深入到詩歌本質層面的重要理論命題。七月詩派非常重視詩歌創作中的形象問題。如胡風、阿垅、艾青等都對詩歌形象問題進行過專論,特別是胡風,這在他的基本上是呈分散狀態的詩論中是很少見的。七月詩派詩人認為詩歌創作的“形象化”理論內含“技巧論”和“概念化”的不良傾向,并不能從根本上克服“狂喊詩”“口號詩”的弊端。詩歌創作需要的是“形象力”而不是“形象化”。形象不僅不是詩歌(尤其是抒情詩)所必需的,而且即便是靠形象取勝的詩歌也不是因為形象本身。
一、詩歌形象與詩歌創作
詩歌形象與詩歌創作關系緊密。古今中外的詩人和詩論家都有很多經典論述,古今中外許多優秀詩歌也以形象取勝。在抗戰時期,為了克服抗戰詩歌為現實斗爭服務過程中存在的空泛、粗陋、直白傾向,形象之于詩歌創作的重要性不斷被強調,甚至被看作是詩歌的本質性規定,認為沒有形象就不是詩歌,形象化也因此成為詩歌創作的核心問題。
抗戰時期形象化理論的提出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現實契機。一是在抗戰初期,詩人熱情的膨脹使詩歌創作中充斥著“種種粗礪的叫喊和直白的議論”[1];二是在抗戰相持階段,因為“低徊,沉郁”的時代氛圍,很多詩人“被生活所腐蝕,漸漸失去了情熱,終于只是在一寸一寸的生活現象上寄托自己”[2]85。如果說前者是一種主觀熱情的宣泄,那么后者則是對生活的“漠不關心”。兩種情況都脫離了生活,所以胡風將這類創作稱為“文學上的投機主義”[3]614。許多詩人和詩論提倡詩歌創作的“形象化”,主張“形象是詩歌的生命”,正是為了克服當時抗戰詩歌的這兩個弊端。就實際創作而言,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抗戰詩歌的“概念化”弊端起到了校正作用。艾青的一系列詩歌創作及其所塑造的“乞丐”“吹號者”“手推車”“驢子”“太陽”等形象,幾乎影響了一代人,七月詩派在創作上本就以艾青為榜樣,九葉詩派的穆旦在《他死在第二次》《〈慰勞信集〉——從〈魚目集〉說起》等文章中也對艾青大加贊賞。
其次是理論淵源。胡適針對新詩創作中“抽象的題目用抽象的寫法”的弊端提出了“詩須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的主張,“凡是好詩,都是具體的;越偏向具體,越有詩意詩味”[4]14。俞平伯認為寫詩要“注重實地的描寫”[4]27,宗白華認為詩人可以借助“繪畫的作用……使詩中的文字能表現天然圖畫的境界”[4]30,“繪畫美”更是聞一多“三美”主張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這種對“具體性”“繪畫性”的追求,不僅與中國傳統詩學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理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因為朱光潛從中西詩學角度對“情趣與意象”內在關系的探討而得到了重要的理論支撐。于是,在抗戰前后的詩壇上,出現了一個被廣泛認同的結論:形象是詩歌的生命,為了塑造形象,我們必須提倡“形象化”的詩歌創作方法。如蔣天佐在《低眉集》和《談詩雜錄》中就十分推重“形象”和“形象化”。
七月詩派不僅在詩歌創作中塑造了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特色與主體的情感化體驗性傾向”[5]的詩歌意象,如“曠野”“纖夫”“戰士”“母親”“土地”“暴雷雨”“春雷”“旗”“星”“夜”等,而且在詩論中非常重視對詩歌創作與形象的理論探討。胡風有1篇專論,阿垅有4篇專論,相關的論述在七月派其他詩人的詩論中也經常見到。
詩歌“形象化”理論的合理性在于它揭示了文學藝術的“形象思維”特質,對抗戰詩歌的“概念化”傾向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七月詩派詩人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對詩歌“形象化”表示了部分認同。胡風認為:“文學創造形象,因而作家的認識作用是形象的思維。并不是先有概念再‘化’成形象,而是在可感的形象的狀態上去把握人生,把握世界。”[3]613阿垅主張詩歌作為文學的一個部門,要遵循“形象思維”的基本規律,因此詩歌“形象化”有合理性。因為形象塑造有助于藝術向著感性特質靠攏,所以阿垅說:“要表現這樣概念似的東西,就往往要依附一些東西。好像宗教藝術中人們建筑了無數多色大理石的宮殿來表現神,通過一種實際存在的物質,使人肉體地感到神。在詩,往往采用譬喻,借讬,諸如此類,來敘述情緒狀態,來放射精神沖擊。在詩,大概這個就是所謂‘形象化’了。”[6]216胡風也說:“詩得從現實生活里面的事象里面誕生,實際上,大多數的場合也正是通過甚至擁抱著從現實生活里面攝取或提煉的事象的。”[2]88那些“概念化”的抗戰詩歌,不管是主觀的空洞叫喊,還是客觀的冷情描寫,是作家的主觀精神力量脫離了生活實踐后導致的,沒有做到“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反映到詩歌創作上便表現為缺乏鮮明生動的詩歌形象。在這個意義上,詩歌“形象化”理論觸到了詩歌“概念化”問題的“痛處”,所以,當詩歌“形象化”理論提出,特別是有了優秀詩歌作品后(如艾青的詩歌),那些“狂喊詩”“口號詩”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校正。
二、七月詩派:“形象力”而非“形象化”
詩歌“形象化”理論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狂喊詩”“口號詩”的弊端,但七月詩派詩人認為用“形象化”這服“藥”治療抗戰詩歌中“概念化”的“病”并不對癥,因為“形象化”理論內含“技巧論”和“概念化”的不良傾向。七月詩派詩人認為詩歌創作需要的是“形象力”而不是“形象化”,形象不僅不是詩歌(尤其是抒情詩)所必需的,而且即便是靠形象取勝的詩歌也不是因為形象本身。
所謂“形象力”指的是形象在詩歌作品中的表現能力。詩人在創作中追求“形象力”目的是以詩歌形象的“形象性”特質最大限度地發揮詩歌思想內容的實踐能動性。
這一理論認識與七月詩派思考詩歌本體的角度密切相關。七月詩派詩人是從詩歌的思想內容層面出發探討詩歌的本體問題的。他們認為詩歌的情志因素,即阿垅所說的“典型的情緒”是詩歌本體的真正所在。詩歌的形象、語言、排列方式等等都作為形式要素而獲得存在意義。詩歌在本質上是一種抒情現象,是詩人以詩歌為憑借的傳情活動。而傳情可以通過形象,也可以通過直接抒發達到,“在人和人的現象之中,還存在人底精神現象。對于詩來說,則有感情的現象。而詩,又是作為抒情的手段的。這種精神現象,或感情現象,有時和對象統一地表現出來,但有時卻從人底胸臆當中直接抒發了出來(不能等于沒有感受,更不是沒有對象,如果沒有,詩就沒有任何的可能性來寫了,這里不過是說,有的詩,卻不是依靠某些事物的形式而表現的,或不是把某一對象作為它底表現形式的)”。因此,“詩底特質,詩底特色,是以情緒的東西或感情作用于人們。因此,它可以有形象,也可以沒有形象”[7]82-83。“我們所要求的,在詩,是那種鋼鐵的情緒,那種暴風雨的情緒,那種虹采和青春的情緒,或者可以說典型的情緒。那么,詩底問題是:這種情緒底高度的達到,和它底完全而美麗的保證。形象不是外在的,當這典型的情緒春風野火似的燃燒起來,重炮巨彈似的爆發起來,或者,管弦樂隊似的奏鳴起來,那就一切足夠了;形象不形象,既不成問題,而形象,也得完全服從于情緒底要求。”[6]86胡風也認為:“人不但能夠在具象的東西里面燃起自己的情操,人也能夠在理論或信念里面燃起自己的情操的。沒有了形象就不能算是詩嗎?理論或信念之類不能是我們的血肉所寄附的東西嗎?人知道形象能舞蹈,能飛翔,能歌唱,人卻不知道理論或信念之類也能舞蹈,能飛翔,能歌唱,因而他不懂得沒有經過熱情孕育的形象只是一些紅綠的紙片,因而他更不懂得在一個偉大的革命者或思想戰士的論文或演說里面我們能夠讀到莊嚴的詩。”[2]89總之,就詩歌的本質而言,問題的關鍵在于它能否以“情感的濃度”達到“思想的力度”,形象只是為了實現這個理論目標的“形式要素”而已。
所以,在七月詩派看來,詩歌不需要“形象化”,它要的是“形象力”。這是從七月詩派對詩歌形式本質的理解中自然得出的結論。詩歌形式在本質上乃是基于詩歌思想內容的一種“表現能力”。于是,對于詩歌形象的本質來說,從“表現能力”的角度來看,它只能是一種“形象力”,其目的就在于以自身的“形象性”特質為最大限度地發揮詩歌思想內容的實踐能動性服務。實際上,胡風在論述“形象的思維”時,與其說他強調了形象(事象)的重要性,不如說他強調的是“現實生活”的重要性,即其重心同樣在“形象力”所指向的詩歌內容層面。
而詩歌創作要獲得“形象力”,僅僅依靠成熟的技巧刻畫“形象”是行不通的,其關鍵還要看詩人能否將主觀的思想感情與客觀的生活現實相結合。所以,阿垅認為“要是思想底大的燃燒,要是情緒底大的激蕩,形象,假使和這些結合,而且兩者的關系并不失去平衡,那么,才產生了形象力”[6]216。反觀當時的詩歌“形象化”理論,它恰恰是偏離了這個理論關鍵點的。從這樣的理論依據出發,詩歌“形象化”理論將“形象”作為詩歌的生命首先就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點,因為它忽視了形象背后的“人的東西,人和人底生活的東西”;而一旦忽視了形象的“所指”,“形象化”就淪為一種“技巧論”了,這勢必讓詩人們將注意力從現實生活中脫離出來而只是專注于“技巧”的修煉,其結果就只能是“概念化”了。所以,本是為了克服抗戰詩歌的“概念化”,詩歌“形象化”理論卻出人意料地帶有了“技巧論”和“概念化”的雙重性質:“技巧論的本質,是無思想的本質。因為它不是在生活中(即在內容中)發現美,無力從生活中發掘美,那所謂‘美’,不過是一種裝飾,一種脂粉,就像顏料、油彩似的,但排斥生活的時候,實質上也就是排斥了思想性或思想之美的。至于它那‘概念化’的本質,則是由于它不能從生活中看出那思想、思想的意義、思想的因素,而是以主觀的、無實踐意義的那種‘思想’代替了現實生活內容,因此是不真實的思想的本質,只是化裝講演一番,這樣,也就得不到思想力,說服力或感染力也就沒有了的。”[7]63-64胡風也說:“至于‘形象化’,那是先有一種離開生活形象的思想(即使在科學上是正確的思想),然后再把它‘化’成‘形象’,那就思想成了不是被現實生活所懷抱的,死的思想,形象成了思想的繪圖或圖案的,不是從血肉的現實生活里面誕生的,死的形象了。”[2]90
抗戰詩歌“概念化”弊端的實質是一個詩歌內容層面的問題,而詩歌“形象化”理論卻企圖通過形式層面的方法解決,所以它根本上是乏力的。這就是為什么胡風和阿垅異口同聲地認為詩歌形象化理論不僅克服不了“概念化”,反而掩蓋了它的根本原因。七月詩派詩人認為,詩歌“形象化”理論至少犯了兩個錯誤:一個是將“形象”看作是詩歌的本質,即所謂“形象是詩歌的生命”;另一個是從詩歌形式的層面解決詩歌內容的問題,即以“形象化”的方法克服抗戰詩歌中出現的“概念化”傾向。盡管詩歌“形象化”理論背后有許多理論資源支持,七月詩派卻依然認為它是有問題的,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七月詩派正是從“形象力”的角度來探討詩歌所需要的“形象特質”的。以艾青的《乞丐》為例,那個“用固執的眼/凝視著你/看你在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齒的樣子”的乞丐形象雖然讓人有些覺得可怕,但阿垅卻認為:“這是形象底可怕么?不,這是饑餓底可怕!‘可怕’者,是形象力!”再比如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以及宋太祖的《詠日出》(“日出欲出光辣達,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卻殘星趕明月!”)之所以是成功的,并不是因為“形象化”,而是因為“那種風格,那種境界”,因為它們都反映了某種特定的“典型情緒”:“《天凈沙》是士大夫底意識形態的——士大夫底典型的情緒的;《詠日出》是帝王思想的,英雄氣概的——‘馬上得天下’那一類的軍閥政客底典型的情緒的。”[6]88-89而“魯迅底‘如磐夜氣壓重樓’和‘慣于長夜過春時’或者普式庚底《致西伯利亞的囚徒》甚至《給奶娘》《我又從新造訪》,或者綠原底《你是誰?》《咦,美國》,鄭思的《秩序》。那里面是充滿著特定的詩人底由于戰斗要求而來的對于人生形象的擁抱的春情和強力,而和僅僅外部地或者技巧地要求那種‘形象化’完全無緣”[6]96-97。
在詩歌創作中,形象不僅不是必須的,而且即便是那些以形象而聞名的優秀詩歌,從根本上看,也不是因為形象本身,而是因為“形象力”。相比而言,宗白華、聞一多提倡的“繪畫性”(“圖畫的美”),因為講求“圖畫的美”,最好也不過是通過借用繪畫的長處為形象塑造增添若干亮色,而其末流則只能是一種“技巧論”了。所以阿垅說:“如果為了‘圖畫的美’,很不必做詩,顏料和畫布有的是。而詩,也決不是線條、色彩、陰影之類的六面畫;不是對于眼睛的愛撫,而是為了靈魂的交通。”[6]89
在梳理七月派詩歌中的形象類型時,江錫銓說:“戰士與母親,是‘七月’詩人的作品中得到了比較集中表現的兩大抒情形象系列。”而仔細體會這兩類抒情形象,我們會發現七月詩派塑造它們的著力點并不是戰士或母親的外貌特征,而主要是它們所蘊含著的文化思想的、乃至美學的力量。以母親形象為例,雷蒙、又然、曾卓、綠原、牛漢等人在塑造母親形象時就很少刻畫她們的外貌、長相等外部特征,而是將更多的關注點放在了她們的形象所包含的詩人“對親人、對民族、對人民、對祖國深摯豐厚的依戀與親情”[8]77-78上。例如,雷蒙的《母親》:“母親 遺留在我記憶中的/是帶我到古城上看大江澎湃的母親/母親遺留在我氣質中的/是扶了鋤頭在庭園里種瓜種菜的母親”,曾卓的《母親》:“幾年來,/當我從行囊中/檢點出你手縫的冬衣時/我要想起您;/當我看見旁人的/慈祥、勤勞的母親時,/我要想起您;/當我從報紙上知道/您居住的那個小城被炸時,/我要想起您;/當我聽到或看到/一些女人的悲慘的故事時,/我要想起您”,綠原的《小時候》:“小時候,/我不認識字,/媽媽就是圖書館,//我讀著媽媽”,這些例子中的“母親”形象的外貌特征都是模糊的,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們領會詩人飽含其中的思想和情感。駱寒超將這種塑造形象的方式稱作“綜合性抒情方式”,而以此構成的形象的特點是:“它的如實性不足,但從整體看,是直抒胸臆中摻入多量主體化了的客觀具象。因此他們的詩是一種明朗與含蓄、具體與抽象的統一。”[9]駱寒超的概括當然是十分準確的。但深究其根源,顯然還是得回到七月詩派提倡“形象力”、反對“形象化”的詩學觀上來找答案:七月詩派塑造的形象之所以是“明朗與含蓄、具體與抽象的統一”,其根本目的正是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形象力”。
詩歌的形象或者說意象問題是一個復雜的話題,七月詩派雖然有偏頗之處,并且沒有對這個問題進行更為面面俱到的分析,但他們在詩歌形象問題上對“形象化”和“形象力”的區分的確揭示出了一部分詩歌創作的真理。
三、對朱光潛“本身形相”觀和艾青“詩歌形象”觀的理論辨析
對于詩歌形象,朱光潛從“審美直覺說”出發認為它應該是事物的“本身形相”。所謂“本身形相”乃是一種與周圍的一切相隔絕的獨立自足、孤立絕緣的事物本身。它拒絕任何“名理的知”,即對事物間關系與意義的知識[4]477。艾青則傾向于將形象看作詩歌的本體要素,“一首沒有形象的詩!這是說不通的話。詩沒有形象就是花沒有光彩、水分與形狀,人沒有血與肉,一個失去了生命的僵死的形體”[10]94。由此,艾青特別強調詩歌形象表達的具體性。認為:“愈是具體的,愈是形象的;愈是抽象的,愈是概念的。”“所謂形象化是一切事物從抽象渡到具體的橋梁。”“意象是純感官的,意象是具體化了的感覺。”[10]24-25
朱光潛、艾青對詩歌形象的理論認識與七月詩派的形象力理論是不同的。胡風、阿垅等人對此進行了理論辨析,這突顯了七月詩派關于詩歌創作形象力理論的獨特性。
首先,針對朱光潛的“本身形相”概念,阿垅認為詩歌意象可以分為人物形象和事物形象兩大類。但無論是人物形象還是事物形象,都不可能是與周圍的一切相隔絕的獨立自足、孤立絕緣的事物本身。“人物形象”的內涵就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文學創作過程中,這種“人物形象”是作家“以自己底思想武裝或思想力(這是從生活實踐里和從理論學習中積累的,形成的,發展的),在創作過程里發掘它,認識它,批判它(是形象的批判,或形象之間的批判即斗爭)”[7]67后才產生的,是集個體性與群體性、現實性與歷史性于一身的,不可能獨立自足、孤立絕緣。藝術中的“事物形象”在本質上還是“人的東西”,“這是詩的熱情的對象化,同時對象又人格化的一個過程,一個矛盾過程,一個辯證過程。簡單地說,詩中的事物,乃是被人格化了的事物”[7]74。總之,不管是人物形象還是事物形象,都是“以人和人的現象作為中心……在根底里意味著是人的東西,人和人底生活的東西”[7]82。
其次,七月詩派雖然將艾青作為自己創作的榜樣,但在理論上從情志論出發,認為“典型環境的典型情緒”才是詩歌的本質要素,形象是一種形式要素,不能提升到本體的層面上。艾青詩歌中讓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如“乞丐”,之所以能夠成功,不是因為形象本身,而是因為形象所指向的社會、歷史內涵給讀者帶來了強烈的思想震撼。乞丐“用固執的眼/凝視著你/看你在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齒的樣子”,之所以可怕,不是因為乞丐本身可怕,更主要的是災民的饑餓給我們帶來了深深的震撼。在這一點上,七月詩派與艾青是有著根本的不同的。與之相關,七月詩派認為艾青過于強調詩歌形象的具體性容易限制詩歌藝術性。從形象力角度出發,更應該強調的是詩歌形象的可感性。根據胡風和阿垅對“形象思維”的理解,他們所強調的乃是形象的“可感性”,而不是具體性。抒情詩當然可以通過塑造具體的形象來達到可感性,但也可以通過直接訴諸人的情感的方式達到。因此,過于強調“具體性”,勢必就會構成對“可感性”內涵的“限制”。正因為“形象力”的所指是詩歌的整個思想內容,而不是“形象”本身,所以“形象或者形象力在詩,和在小說或者戲劇,又是有所不同的;后者是一條鐵路,前者是一個方向,——后者說一不二,前者聞一知十。形象是一個限制。特別在我們底詩是一個限制”[6]223。例如,艾青在《雪里鉆》中將戰馬豎起的耳朵描寫成為“像兩個新削的黑漆的竹筒”就是因為他過于追求形象的“具體性”,反而歪曲了形象,喪失了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形象,也就喪失了暗示性,也就成了詩歌表達的限制了。
總之,七月詩派認為詩歌創作的關鍵在于能否以“情感的濃度”達到“思想的力度”,詩歌形式在本質上乃是基于詩歌思想內容的一種“表現能力”。對于詩歌形象的本質來說,它只能是一種“形象力”,其目的就在于以自身的“形象性”特質為最大限度地發揮詩歌思想內容的實踐能動性服務。也就是說,七月詩派在探討詩歌形象問題時,著眼的是形象背后的社會、歷史、生活的鮮活內容,詩歌形象所具有的“戰斗力”指向的是現實生活中人的血肉豐滿的戰斗實踐,有礙于這一點的理論都是七月詩派要進行理論辨析的對象。朱光潛的“本身形相”概念顯然與七月詩派的觀點相異,即便是他們的創作偶像艾青將形象提升到詩歌本體形象上,也是他們不認可的。因為在胡風、阿垅等七月詩派詩人看來,朱光潛和艾青的理論觀點都容易導致詩歌創作上的主觀公式主義或者客觀主義。
七月詩派詩人對朱光潛觀點的理論辨析難免有門戶之見,對艾青詩歌形象觀的理論分析也過于嚴苛。但若從七月詩派緊扣主體“情志”因素的詩歌本質論、以人生實踐為旨歸的詩歌思想論、以“戰斗力”為準則的詩歌形式論的理論體系來看,七月詩派的這些理論認識都是為了糾正詩歌創作中的主觀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所進行的努力,都是為了使革命詩歌能夠兼顧詩歌的工具性和藝術性,都是為了協調革命詩歌創作所面對的來自外部的社會歷史使命和來自內部理論建設的藝術使命。從這角度出發,七月詩派詩論是中國革命詩歌創作在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一次較為全面的理論提升。包括“形象力”在內的許多理論觀點都值得我們去進行理論的梳理和辨析,以期為今天的詩歌理論研究和詩歌創作提供有益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