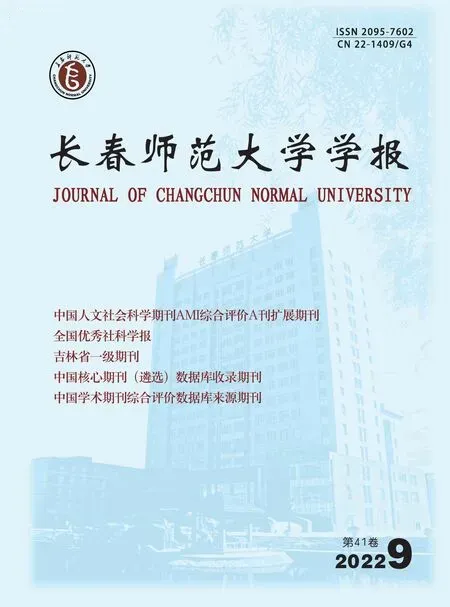宛敏灝先生詞學思想探賾
——圍繞《詞學概論》詞調觀展開
沈文凡,林婉心
(吉林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詞原是配合隋、唐以來燕樂而創作的歌辭,后來才脫離音樂關系成為一種長短句的詩體。”[1]3詞在剛剛興起時,并無所謂詞學。兩宋以來,詞樂研究、詞史研究、詞譜研究等逐漸興起,明清時期達到興盛。近百年來,詞學進一步發展,大家名家輩出。其中宛敏灝先生潛心研究詞學,不僅在詞人別集方面有頗多建樹,還將數十年研究心得匯編為《詞學概論》,推動了詞學知識的傳播與發展。
詞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體,上不類詩,下不似曲。從詞的本體論而言,詞調是詞區別于其它文體的顯著標志,是詞之為詞的本質特征。在《詞學概論》中,宛敏灝先生從整體上展現出詞調史的起源發展,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辨析詞調三分的標準,闡明調題離合的問題,體察入微,論析精警,立論公允。
一、概論詞調沿革
詞調研究是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由于詞樂文獻的缺失、研究方法的不足等原因,詞調研究相對落后。研讀《詞學概論》,可知宛敏灝先生早于幾十年前已從多側面、多角度探討詞調,不但提綱挈領地概述了詞調史,還形成了詞調以節拍而非字數進行劃分的判斷,并總結了詞調別體產生的三條途徑,具有極強的問題敏感性和學術前瞻性。
(一)提綱挈領的詞調史概述
隨著樂曲的流變與聲韻的發展,詞調的數量和種類不斷增加。現存的千百個唐宋詞調經歷了幾百年的變化,追述其源頭極為困難。宛敏灝先生溯源析流,闡釋了詞調的由來與繁衍,邏輯清晰,層層遞進,語言精省且錘煉得當,展現出深厚的學術功力。
宛敏灝先生遍查古籍,剔抉爬梳,先將音譜的來源歸為六類,即“截取隋、唐的大曲或引用琴曲”“由民歌、祀神曲曲、軍樂等改變的”“從國外或邊地傳入的”“宮廷創制”“宋大晟樂府所制”“詞人自度(制)曲”;并指出這六種來路中,“前三種屬于因襲,后三種則出自創新”[1]70,以極簡潔的方式勾勒出詞調的來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各類來源舉證,如“從國外或邊地傳入的”這一類中舉出《菩薩蠻》《蘇幕遮》《普贊子》《蕃將子》《八聲甘州》《梁州令》《氐州第一》的詞調;“宮廷創制”一類中又劃分為“出自帝王”的《水調》《河傳》《破陣樂》《雨霖鈴》《燕山亭》和“出自樂工”的《夜半樂》《還京樂》《千秋歲》;“詞人自度(制)曲”一類中特別強調:“柳永《樂章集》里用調達一百二十個,但僅有七個同于敦煌舊曲。其《晝夜樂》《佳人醉》《殢人嬌》等,可能都是為歌妓制作。”三言兩句間把自己潛心考辯的成果呈現出來,足見其扎實低調的治學態度。
在詞調發展歷程中,自度腔、自制腔是其繁榮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雖然后世常將兩者混為一談,但其實它們是有區別的。“率意吹管成腔,然后填詞,這種叫做自度腔;先率意為長短句,然后制譜,就叫做自制腔。”[1]73詞人往往在序言中說明所創制的詞調為自度腔或自制腔,如《揚州慢》:“因自度此曲。”《長亭怨慢》:“予頗喜自制曲,初率意為長短句,然后協以律,故前后闋多不同。”《淡黃柳》:“因度此曲,以紓客懷。”經考證,這類記載和真實情況頗有出入,這是因為宋人已將兩者混淆,后世之人更“不復措意”[1]75。除了這兩類出自一人之手的詞調外,還有“又一體”。“又一體”即詞調的別體,表現形式多樣,實質是“把舊調平仄互換”,是明清學者對詞調規律的總結。萬樹《詞律》、杜文瀾《詞律補遺》中記載,別體有成千上百之多。
“詞體發生史的研究,最基礎、最重要的‘歷史本身’,乃是產生于人們的實踐、凝聚著歷史‘行為過程’的詞(詞調、詞體、詞文)。而‘詞調’研究則是破譯詞體‘起源’發生密碼的關鍵之一。”[2]24-34辨明源頭、疏通脈絡,是詞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宛敏灝先生在概述詞調發展的來源后,從因襲和創制兩個角度說明了音譜的發展,并詳細說明了自度腔、自制腔和“又一體”,繁簡得宜,詳略得當。
(二)見解獨到的詞調“三分”考論
詞調“三分法”是明清詞學研究的重要成果,“標志著中國詞學由音樂譜時代進入到格律譜時代,改變了明代以后詞選與詞譜編刻的體例及其發展方向”[3]。“三分法”是指將詞調劃分為小令、中調、長調三類,這已經被學術界廣泛接納和認可,但劃分的依據有待商榷。
明清以來,一般以字數為劃分詞調的依據。毛先舒說:“五十八字以內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為中調;九十一字以外為長調,此古人定例。”但沈雄說:“唐、宋作者只有小令、曼詞,至宋中葉而有中調、長調之分,字句原無定數,大致(中調)比小令為舒徐,而長調比中調尤為婉轉也。今小令以五十九字止,中調以六十字起至八十九字止,遵舊本也。”[1]46-47兩種說法雖然都以字數為標準劃分詞調,但彼此之間存在出入。朱彝尊和萬樹也曾對此論點提出質疑,因此宛敏灝先生指出:“這類按字數來嚴格區分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1]47這是對前人觀點的反思和判誤,展現出辯證的學術思維。
詞調“三分”的依據究竟是什么呢?“令、引、近,慢的名稱,是表示就節拍的不同來區分曲類”[1]50。宛敏灝以王易和吳梅的說法佐證自己的觀點。王易在《詞曲史》中提到:“令、引、近,慢在宋時名曰小唱,惟以啞觱篥合之,不必備眾樂器,故當時便于通行。其節奏以均拍區分,短者為令,稍長者為引、近,愈長則為慢詞矣。”此外,王易將“均”作為節拍的標準,指出:“故不少六均之調,明稱為令;八均之調,明稱為引,近者;至于八均以上之慢,又不勝數矣。”吳梅認為,“詞中之引,即如大曲之散序,無拍者也;近、令者,有節拍者也;慢者,遲聲而歌,如后世之贈板者也。”[1]50這兩種說法在細節上稍有出入,但都表明詞調的差別在節拍而非字數。唐圭璋和夏承燾先生也有類似觀點。唐圭璋在校釋《云謠集》雜曲子時,發現同一詞調字數不定的現象,如“《竹枝詞》第一首五十七字,第二首則六十四字。《花間》亦有同調不同數之詞,是知唐詞往往如此,不似后世不能歌之詞,一字不容出入也”[4],夏承燾說:“這種完全以字數劃定詞調的方式十分機械,令、引、近、慢的區別是由歌拍節奏的不同決定的。”[5]42-43可見,詞調以節拍而非字數進行劃分的觀點被普遍認同。
詞調“三分法”作為詞學轉型的重要標志,對推動詞譜編訂、促進詞學批評具有積極影響,但該觀點仍有不完善之處。宛敏灝先生提出詞調劃分的依據是節拍而非字數,認為在掌握相關拍眼名詞的基礎上,進一步加深對詞調音樂性的了解,有利于掌握詞的本質特征,展現出審慎嚴密的學術判斷和深微獨到的學術見解。
(三)簡明扼要的詞調別體闡釋
詞調作為詞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原指詞的文詞和音調;隨著詞體中音樂性的消亡和文學性的突出,變為專指律詞的格調。詞在發展過程中,發生了復雜的變化,出現了衍生現象。“詞之為調,有六百六十余,其體則一千一百八十有奇。”[6]44這些別體列在詞調之后,稱“又一體”。別體產生的原因紛繁復雜,宛敏灝辨其來源、梳其根本,總結出由簡而繁、由繁而簡、譜拍間的變化三條途徑。
首先,由簡而繁的特點往往體現在“先有小令,后來又有同調名的中調或慢詞”[1]77。以常見的《憶江南》為例,皇甫松的“蘭燼落,屏上暗紅蕉。閑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瀟瀟。人語驛邊橋”共二十七字。吳文英同詞調“又一體”五十四字,而馮延巳的“又一體”為五十九字。吳文英和馮延巳的“又一體”在皇甫松的基礎上加了一疊,從單調到雙調,由簡省到繁復,這是別體出現的重要途徑之一。
其次,由繁而簡指的是“先有大曲、法曲,然后有歌頭、摘遍等”[1]78。大曲指唐宋時代的大型歌舞曲,由同一宮調的若干曲子組成;而法曲作為大曲的一部分,因融合佛門、道門曲而得名。《詞學概論》以三個詞調說明此類途徑。吳文英的《夢行云》看似與一般的詞一樣,但根據詞人自注,“即六幺花十八”,可知其摘自大曲。除了詳細說明吳文英《夢行云》的來源,宛敏灝還指出:“《泛清波摘遍》、《法曲第二》等都是從大曲或法曲摘取其聲音美聽而又能自為起結的一遍,單獨譜唱成為一般的詞。”[1]78論據充分,詳略得當,說明了別體出現的又一途徑。
最后,譜拍間的變化情況較為復雜,主要有“增減腔調因而字數亦有變動者”[1]79和“因律調的變動而成為新體者”[1]80。其中,南唐李璟《攤破浣溪沙》、宋代張先《減字木蘭花》《偷聲木蘭花》、唐代白居易《楊柳枝》以及后蜀顧敻《添聲楊柳枝》是因增減字數而發生詞調的變化;轉調的《轉調踏莎行》、犯調的《凄涼犯》則是因律調的變動而改變詞調。考察詞調別體的變化途徑,除了以詞調本身的轉韻結構為規律外,詞人的自序往往是最直接的依據,姜夔在《湘月》的自序中提到:“即《念奴嬌》之鬲指聲也,于雙調中吹之。鬲指亦謂之過腔,見晁無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過腔也。”
詞調別體產生的三條途徑是宛敏灝先生在考辨、深思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他不僅將千頭萬緒的別體途徑歸納清晰,為詞調衍生變化厘清頭緒,更通過豐富的論據闡明觀點,可見其學識之豐富、態度之嚴謹。
二、辨析調題一致
詞調是詞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是區別于聲詩、樂府、曲體的標志,調名則是指每一個唐宋詞調的名稱。蘇軾提出“自是一家”的詞學主張后,詞調和詞題、詞作內容的關系逐漸疏離,常常出現舊調作新詞的情況,如今學界也往往只將詞調名作為區分聲調格律的標志。事實上,“詞調最初創制的時候,應該都有意義,而且和內容有密切關聯,大多數調名也就是詞的題目。”[1]71宛敏灝先生主張最初詞調與詞題相一致,且與詞章內容密切關聯。
“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仙事,《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詠祠廟,大概不失本體之意。爾后漸變,去題遠矣。”[7]21《花庵詞選》表明詞調最初與詞題相合,詞作內容也與詞調契合,后來因為宮調失墜、樂譜失傳、詞律演變等原因,詞調與詞題逐漸疏遠。《詞學概論》詳細論述了調題離合問題,指出調題最初是緊密聯系的,強調了詞調本事的重要性。
宛敏灝先生將調名的來源分為沿襲與創新兩類。沿襲這一類恰好可以說明詞調與詞題的離合問題。起初,詞調與詞題是緊密聯系的。比如,以所詠之物命名的,有寫摸魚的《摸魚子》、寫賣卜的《卜算子》、寫梁祝故事的《祝英臺近》、寫牛郎織女相會的《鵲橋仙》、寫南方風的《南鄉子》、寫迎神祀廟的《河瀆神》、寫江妃水媛的《臨江仙》等。再如,以本詞的字數或詞句命名的,有《十六字令》(全首共十六字),《三字令》(通首為三字句)。之后,由于摘句成名等情況的出現,詞調和詞題、詞的內容的距離不斷疏遠,關聯也逐漸變小。
近代以來,有頗多學者與宛敏灝先生的觀點一致。吳梅在《曲學通論》中認為,調名“有取古人詩詞中語名者”[8]201。詹安泰在《論調譜》中探討調名之由來,在“以所詠之物命名”“就本詞的字數或詞句命名”兩類之外,還有“以詞中情意為調名”“以句舉詞因而為調名”“以句法為調名”“取古人詩語為調名”“以非所詠之物為調名”“以地名俄日調名”“以人名為調名”等共計十一類[9]71-76。吳熊和在《唐宋詞通論》中提到:“詩文都有題目。一般說來,根據題目就可以推知詩文的內容。詞則不然。有的賦調名本意,詞的內容與調名相合,那么其調名也就是詞題。有的與調名無涉,其調名不過是表明所用的曲調聲腔,那么就無法根據調名窺知詞意。”[10]133田玉琪在《詞調史研究》中也說:“詞調命名原理與漢魏樂府題名十分相似,多以本意命名,即敘何事、賦何物即用何名。”[11]62
宛敏灝先生值得稱道的不僅是于細密幽微之處發現問題,更能在剖析問題之后尋找出問題本質與學術內核。以調題的離合問題為例,宋代以來,便有人主張詞調與詞題存在由合向離的發展趨勢,幾百年間多有相似言論,宛敏灝先生卻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他指出:“知道創調時原詞的內容寫的什么,可以作為了解這一詞調聲情的參考,因而調名起源確可考查的不妨搞清楚,如將那些來歷不明的也都加以懸揣附會,就沒有什么意義了。”[1]73發現問題往往不是最終目的,透過問題回歸學術研究的初心,理性思考問題背后折射出來的種種現象才是目的。若還能為后來研究者撥開謎霧、掃除荊棘,才真正稱得上是大師名家。
詞調與詞題最初具有一致性,詞章內容和傳達出的聲調情也與調題緊密關聯。因此,掌握詞調本事對詞意解讀、詞作鑒賞等具有重要作用。調題一致的主張,不但促進了宛敏灝先生詞調觀的完善,而且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詞調是詞的本質屬性,詞調本事反映出詞調與詞題之間的離合關系。“在詞樂尚未完全失傳以前,有部分腔調已逐漸失去音譜,無法歌唱;作者依照舊詞填寫,也無意為應歌之用。另一方而,樂工和文人根據需要,繼續不斷地在創制新調并填詞。”[1]73由于各種原因,詞調與詞題的關系逐漸疏離,但不可否認的是,詞調創制之初,調名即為調題,與所詠內容密切相關。《清平樂》“樂”字讀音看似在討論讀音問題,其實是詞學知識在當代社會中應用實踐的體現。在了解調名起源的基礎上,才能考察詞調聲情,也就不難反證詞調的讀音。
三、闡釋選聲擇調
“詞,既已成為格律詩體之一,則運用舊形式而賦以新內容應是可行的。”[1]335《詞學概論》由宛敏灝的課堂講義補綴而成,不僅在理論建構層面論述詞學知識,詳述詞調主張,更在學術實踐層面幫助后學者厘清概念,指導學術創作。宛敏灝先生從應否依照格式和怎樣選調兩個方面闡釋選聲擇調,主張作詞應當巧妙使用選聲擇調的技巧與方法,在既有的規范體式內進行靈活創新。論述語言精簡洗練、一語中的,展現出深厚的學術功力。
(一)詳談“應否依照格式”
“作詞之法,論其間架構造,卻不甚難。至于擷芳佩實,自成一家,則有非言語可以形容者。所謂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有一成不變之律,無一定不易之文。”[6]43作詞之難,不僅體現在講究詞境、詞意、詞法,更體現在詞調、詞韻、詞律的使用。宛敏灝先生主張以舊形式寫內容,寫詞應當依照格式。
首先,在寫詞的實踐中,應當依照格式。若襲用舊調而改其格式,則喪失了詞調的價值。“詞,早已成為‘句讀不葺之詩’。它源于樂府,并各有詞牌。我們現在所謂填詞,實際是舊瓶裝新酒。倘取消這一包裝,那就完全失去再用舊稱的意義。”[1]345有學子請先生給自己所寫的《西江月》提意見,先生說:“只有個別字建議改一下,最好是《東江月》,‘南’或‘北’也行。以你‘壯歲旌旗擁萬夫’的豪氣,何苦老守什么《西江月》的清規戒律受罪呢?”面對習作,先生并未疾言厲色、大聲呵責,而是通過幽默的比喻、活潑的語言闡釋觀點,認為填新詞可不受舊詞《西江月》的束縛,盡可率性而為、施展才華;欲填舊詞而出新意,則需嚴守詞牌詞調的限制,不妨在內容上創新,以舊形式寫新內容。先生認為,隨著詞譜的遺失、詞律的演變,詞的音樂性不斷減弱,“詞至今日,已和詩中的近體同屬于格律詩。”[1]346但是格律詩包含的內容多、范圍廣,詞則各有詞調。既然詞調各異,聲情、體式自然更不相同。
其次,“自度曲”重在音譜而非歌辭。有學子問及,隨意所作的長短句自命為“自度曲”是否正確。先生認為,“關鍵在于其人是否也作了樂譜,否則只可視為一首雜言的古體詩。倘他人代配樂譜,則應如現代分別標明某人詞,某人作曲,不存在是否自度的問題了。”[1]346詞是一種音樂文學,詞的本質屬性是音樂屬性,自己譜曲、作詞方為自度曲,若無曲則是雜言古體詩;若由他人譜曲,便屬于現代音樂的范疇。在開門見山說明觀點后,先生以委實詳盡的論據進行佐證。《白石道人歌曲》中記載姜夔常在小序中指出詞調情況,如《長亭怨慢》:“予頗喜自制曲,初率意為長短句,然后協以律”,說明作詞制譜的先后順序;《玉梅令》:“石湖家自制此聲,未有語實之,命予作”,說明旁譜為范家新曲,而白石僅依譜填詞。此外,其他自度曲也有類似情況,如《揚州慢》“因自度此曲”、《淡黃柳》“因度此闋”、《惜紅衣》“自度此曲”等[1]346。可見古之“自度曲”的形式多樣,重在音譜而非歌辭。
“為配合音樂而提出的嚴格要求當然不必墨守,但如忽視必要的格律,也是不成其為詞的。”[1]346現代人寫詞可以創新,可以用舊形式寫新內容,但不能完全忽略格律形式。面對舊體詩詞在新時代運用中出現的問題時,宛敏灝用質樸平實、言簡義豐的語言解釋詞學理論,又以幽默風趣、輕松活潑的方式開導解惑,說理有邏輯,釋疑有方法,實為大家之風。
(二)細說“怎樣選調”
作詩擇詩體,作詞擇詞調。“調有定格,字有定音”[6]1。詞調選擇頗有講究,從千百詞調中選擇一個合適的并不容易。“擇調不當,或聲文乖戾,或有誤美聽,或不合曲名與傳統作法,都將妨礙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結合。”[10]119選聲擇調要從長短和聲情兩個方面考察。
一方面,小令、慢詞各有所長,要根據作者需求選擇。從初學者的角度而言,應先寫小令,不作孤調僻調。宛敏灝先生引用張炎《詞源》和蔣兆蘭《詞說》的說法,認為“初學宜從小令入手,漸進而及于慢詞。”[1]348張炎說:“大詞之料,可以斂為小詞,小詞之料,不可展為大詞。若為大詞,必是一句之意引而為兩三句,或引他意人來捏合成章,必無一唱三嘆。”說明大詞可為小詞,小詞卻不能展為大詞。他又說:“詞既成,試思前后之意不相應,或有重疊句意,又恐字面粗疏,即為修改。改畢凈寫一本,展之幾案間,或貼之壁。少頃再觀,必有未穩處,又須修改,至來日再觀,恐又有未盡善者。如此改之又改,方成無瑕之玉。”[1]347說明慢詞需字字琢磨、反復修改。蔣兆蘭說:“初學作詞,如才力不充,或先從小令入手。若天分高,筆姿秀,往往即得名雋之句。然須知詞以沉著渾厚為貴,非積學不能至。至如初作慢詞,當擇穩順習用之調,平仄家可移易者為之,庶幾不苦束縛。既成,再將詞律細心對勘,務使平仄悉諧,辭意雙美,改之又改,方可脫手出以示人。逮至功夫漸到,然后可作單傳孤調及研究上、去聲字。”[1]348強調作詞擇調應當從易到難、循序漸進。
另一方面,詞調固有長短之別,但更重要的是聲情的區別。哀怨或是愉悅,剛勁或是柔婉,急促或是輕緩,“由于字句的長短、聲韻的平仄都是互相配合的,不能皮相觀察。惟有反復吟誦,才能悠然心會,更好地領略其聲情。”[1]350由于詞律的變化、詞譜的遺失等因素,考察詞調本身的聲情難度頗大。部分詞調可以從最初的詞中感受,“如《憶秦娥》最早的一首‘簫聲咽’見于《花庵詞選》,題李白作,其詞幽咽悲涼。后來賀鑄改為平韻‘曉朦朧’,亦未改變其怨抑的情調。《望海潮》始見于柳永《樂章集》,極寫錢塘的繁華。秦觀依調作洛陽懷古,仍然是寫勝況多而憑吊意味少。”[1]348-349然而大部分詞調屬于舊調新作,早就失去最初的聲情,難以考察。如“《鷓鴣天》這一詞調看:賀鑄曾以之寫悼亡詞(中有‘梧桐半死清霜后’句,易名《半死桐》),張孝祥卻以之寫春游雅興‘日日青樓醉夢中’。在姜白石詞里,既有‘歌以壽之’,也有抒寫元夕的傷感。”[1]349因此,先生總結道:“一句話,情調是歡愉的還是悲傷的,主要只看歌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而已。所謂從文字去探索某一詞調的聲情,也只是求得其近似而已。”[1]349-350
在作詞的實踐中,循舊例而出新詞需要通曉詞學基本知識,掌握選調的基本方法,審慎考察詞的長短和聲情,由小令到慢詞,由簡易到困難,循序漸進,時常吟誦,把握聲情。宛敏灝先生從實踐指導角度深化了詞調理論,于細微處展現出完備嚴謹的詞調觀。
四、結語
作為民國時期重要的詞學家,宛敏灝不僅總結了傳統詞學,也奠基了現代詞學。《詞學概論》涉及詞的章法、句法、體制、詞韻、詞調、詞話等詞學知識,面面俱到,包羅巨細。詞調觀是宛敏灝先生詞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整體上把握了詞調的發展歷程,也說明了詞調三分的依據是節拍而非字數,并總結出由簡而繁、由繁而簡以及譜拍間的變化等三條途徑,還強調了調題一致的詞本事的重要性,其中頗多簡明扼要、切中肯綮之言,注重普及與拔高的結合,既能幫助初學者得其門徑,也能使精通者完善知識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