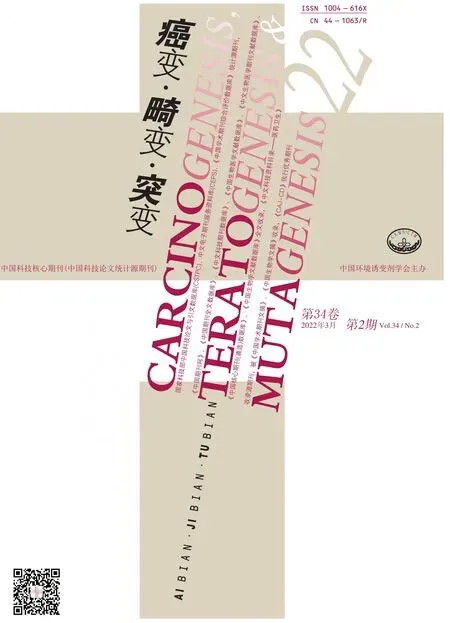PPAR-γ在巨噬細胞炎癥調控中的作用及機制的研究進展
涂永梅,彭 潔,龍 子,孔德欽,陳宇豪,覃梓瀚,劉 瑞,李文麗,*,于衛華,*
(1.空軍軍醫大學軍事預防醫學院毒理學教研室,陜西省自由基生物學重點實驗室,特殊作業環境危害評估與防治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陜西 西安 710032;2.空軍軍醫大學基礎醫學院學員大隊,陜西 西安 710032;3.陜西中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陜西 咸陽 712046)
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γ,PPAR-γ)屬于核受體轉錄因子超家族的關鍵蛋白,主要通過配體結合途徑激活,參與調控脂肪細胞分化和脂肪酸代謝,在肥胖和糖尿病等疾病進展中發揮重要作用[1]。巨噬細胞作為機體的主要炎癥效應細胞,其浸潤激活與肥胖、腫瘤、膿毒癥和動脈粥樣硬化等多種急慢性炎癥疾病的發生密切相關[2]。近年來研究表明,PPAR-γ信號在T細胞和巨噬細胞功能調控中發揮關鍵作用[3],PPAR-γ表達可影響內臟脂肪組織中調節性T細胞的數量及其免疫功能。此外,PPAR-γ信號還參與調控巨噬細胞的促炎和抗炎分化走向,其激動劑可增強機體抗炎反應,有效改善多種急慢性炎癥疾病[4]。因此,明確PPAR-γ在巨噬細胞中的抗炎機制有望為炎癥疾病防治提供新策略。
1 巨噬細胞的炎癥調控作用及其生物學意義
炎癥反應是人體中最基本的生理和病理過程,其本質是炎性細胞浸潤和炎癥因子大量釋放,形成以血管為中心的局部或全身反應。巨噬細胞是一種來源于骨髓,由單核細胞轉變而來的固有免疫細胞,廣泛存在于機體各組織器官內,其主要生物學功能包括抗原呈遞、介導炎癥反應和吞噬病原菌作用,在多種生理和病理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5]。巨噬細胞是機體內最主要的炎癥效應細胞,按照其功能及表型可劃分為促炎(M1)型和抗炎(M2)型兩大類。在感染、創傷早期,病灶周圍募集M1型巨噬細胞,產生大量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一氧化氮(NO)等促炎因子,幫助機體清除病原菌和外來異物;而在感染和創傷后期M2型巨噬細胞轉居主導地位,能夠吞噬凋亡和碎片的中性粒細胞,并分泌大量抗炎因子和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參與調控機體炎癥消退和創傷愈合。當M1型巨噬細胞持續激活或者M2型巨噬細胞活化不足時,機體內促炎因子大量分泌,容易導致炎癥持續存在和創傷難以愈合,進而形成慢性炎癥疾病[6]。臨床研究提示,在急慢性感染導致的肝炎、肺炎和膿毒癥患者中,M1/M2型巨噬細胞比例失調,具體表現為M1型巨噬細胞比例升高,而M2型巨噬細胞比例降低,因此,調控巨噬細胞極性能夠減輕感染性疾病。最新報道發現,在肥胖、脂肪肝、糖尿病、動脈粥樣硬化和心肌梗死等非感染性炎癥疾病中,也存在M1/M2型巨噬細胞比例失調,通過藥物干預降低M1型巨噬細胞、升高M2型巨噬細胞,有助于減輕機體炎癥水平、增強胰島素敏感性、修復受損血管組織,進而達到改善病情的作用[7-8]。此外,巨噬細胞在腫瘤的發生和發展中也發揮關鍵作用,M1型巨噬細胞有助于殺傷腫瘤,是正常情況下機體清除惡性轉化細胞的有力武器;而腫瘤微環境中巨噬細胞被馴化為M2型,又被稱為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參與腫瘤的生長、生存、侵襲轉移和耐藥抵抗等一系列過程[9]。許多臨床證據也表明,腫瘤組織中M2型巨噬細胞比例與腫瘤的惡性程度正相關,靶向干預巨噬細胞是近年來腫瘤研究和治療領域的國際熱點[10]。因此,調控巨噬細胞的分化方向,抑制機體過度炎癥,可能是感染和非感染性炎癥疾病治療的新思路。
2 PPAR-γ的結構、分型和生物學功能
PPARs是一類核受體轉錄因子超家族蛋白,主要有PPAR-α、PPAR-β/δ和PPAR-γ三種亞型。作為一種配體激活的核轉錄因子,PPAR-γ活化后進入細胞核與視黃酮X受體(retinoid X receptor,RXR)結合形成二聚體,與PPAR應答元件(peroxisome proliferator response element,PPRE)作用后,可以激活或抑制靶基因表達[11]。PPAR-γ蛋白由4個功能結構區域組成:①A/B區含活化功能域(activation function-1,AF-1),位于氨基末端,該位點絲氨酸磷酸化能夠抑制PPAR-γ與配體結合激活;②C區是PPAR-γ的DNA結合域,與RXR形成二聚體;③D區為鉸鏈區,含DNA結合域,賦予配體結合域靈活性;④E區為配體結合區域,位于PPAR-γ與RXR的二聚體區域。PPAR-γ基因按5′端序列不同可產生3種mRNA,分為PPAR-γ1、PPAR-γ2和PPAR-γ3。其中,PPAR-γ1與PPAR-γ3 mRNA翻譯后生成蛋白質完全相同,而PPAR-γ2蛋白N端相較PPAR-γ1蛋白多出30個氨基酸序列。PPAR-γ1是PPAR-γ的主要形式,表達范圍相對廣泛,主要在脂肪細胞,免疫細胞(包括巨噬細胞、T細胞和樹突狀細胞),平滑肌細胞和肝臟細胞大量表達;而PPAR-γ2表達范圍較窄,主要在脂肪細胞和平滑肌細胞內表達;PPAR-γ3僅表達于巨噬細胞和大腸中[12]。PPAR-γ在調控脂肪細胞分化和脂糖代謝中發揮關鍵性作用,阻斷PPAR-γ信號激活可抑制脂肪合成[13]。此外,PPAR-γ信號還與機體胰島素抵抗的形成密切相關,PPAR-γ敲減小鼠會出現脂肪萎縮、胰島素抵抗和脂肪肝等癥狀[4]。最新研究發現,PPAR-γ信號抑制與多種炎癥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生密切相關。正常人群脂肪組織PPAR-γ保持穩定活性,巨噬細胞數量較少且呈現M2型,這有利于維持胰島素敏感性;而肥胖患者脂肪組織中PPAR-γ表達和活性降低,巨噬細胞數量增多且為M1型,呈現一種慢性低度炎癥狀態,是導致糖代謝紊亂和胰島素抵抗發生的重要基礎[14]。研究提示,PPAR-γ基因突變或敲減后小鼠對化學因素誘導結腸炎敏感性增加,過敏性哮喘和胰腺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風險也提高。PPAR-γ激活還可誘導單核細胞、巨噬細胞和中性粒細胞等炎癥效應細胞凋亡,抑制機體過度炎癥,提高膿毒癥動物存活率[15]。不僅如此,PPAR-γ還能夠誘導腫瘤細胞凋亡,抑制腫瘤血管生成,參與調控肝癌、胃癌、食管癌和卵巢癌的發生及發展[16]。
3 PPAR-γ在巨噬細胞炎癥調控中的作用及機制
PPAR-γ與巨噬細胞成熟過程密切相關,單核細胞向巨噬細胞分化過程中PPAR-γ活性逐漸升高,并隨分化成熟達到峰值,PPAR-γ激動劑可刺激人單核細胞中巨噬細胞表面標志物CD163和CD36表達升高[17]。不僅如此,PPAR-γ可通過調控氧化還原平衡、抑制促炎信號通路和激活多種抗炎因子表達,最終決定機體巨噬細胞的炎癥走向。
3.1 PPAR-γ抑制M1型巨噬細胞促炎信號的啟動
M1型巨噬細胞的促炎反應是導致多種急慢性疾病的始作俑者,抑制其過度激活對于膿毒癥、肥胖和心腦血管等疾病防治具有重要意義。研究表明,多種信號通路參與調控了巨噬細胞的促炎反應,其中最主要的包括Toll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s,TLR)、核 因 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激活蛋白1(activator protein 1,AP-1)、環氧化酶-2(cyclooxygenase,COX-2)、信號傳導及轉錄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STAT)和誘導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OS,iNOS)等[18]。大量研究提示,PPAR-γ信號激活可顯著阻斷TLR4、NF-κB、AP-1和COX2等轉錄因子與靶基因啟動子中同源位點結合,抑制巨噬細胞TNF-α和IL-6的表達,進而改善小鼠膿毒癥[19]。PPAR-γ的激動劑曲格列酮、羅格列酮等可抑制骨髓原代巨噬細胞的M1型極化和促炎因子轉錄表達。此外,大黃素能夠激活RAW264.7巨噬細胞中PPAR-γ信號,抑制LPS誘導NF-κB及下游促炎信號啟動[20]。高良姜素可激活小膠質細胞中PPAR-γ信號,抑制促炎細胞因子、趨化因子和細胞黏附分子表達[21]。上述結果表明,PPAR-γ可抑制M1型巨噬細胞促炎信號的啟動。
3.2 PPAR-γ促進M2型巨噬細胞抗炎信號的過程
此外,PPAR-γ信號可能參與M2型巨噬細胞抗炎信號的啟動。研究[22-23]報道,PPAR-γ激活可促進巨噬細胞M2型極化,并上調CD206、IL-10和Arg1等抗炎因子表達。Odegaard等[24]報道顯示,骨髓細胞PPAR-γ敲除小鼠的M2型巨噬細胞減少,脂肪組織抗炎因子表達降低,高脂飲食誘導的肥胖和胰島素抵抗風險增加。在高脂喂養的動物模型中PPAR-γ表達和活性降低,促進Kuffer細胞M1型比例升高、M2型比例減少,進而導致非酒精性脂肪肝。且動脈粥樣硬化患者巨噬細胞中PPAR-γ活性與M2型標志物表達呈正相關,激活PPAR-γ可促進單核細胞向M2型巨噬細胞分化。此外,IL-4能夠誘導STAT6表達升高,與PPAR-γ結合促進其轉錄激活,進而啟動巨噬細胞和樹突狀細胞中抗炎信號表達[25]。研究表明,姜黃素、白蘆藜醇和小檗堿等多種中藥單體能夠激活PPAR-γ信號,啟動RAW264.7巨噬細胞的抗炎癥反應。Yao等[26]發現PPAR-γ激動劑可與整合素αVβ5結合,進而促進M2型巨噬細胞抗炎信號Arg-1和Fizz1的表達。
3.3 PPAR-γ通過氧化還原調控巨噬細胞分化
大量文獻顯示,氧化還原(Redox)信號與巨噬細胞極化和炎癥調控密切相關[27-28]。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不同劑量對炎癥信號的影響也存在差異,ROS增多或抗氧化減弱調控巨噬細胞向促炎分化,ROS減少或抗氧化增強有利于巨噬細胞向抗炎分化[29]。生理條件下,機體中PPAR-γ內源性配體富含不飽和雙鍵,極易被ROS攻擊,形成脂質過氧化產物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30],失去對PPAR-γ的激活作用。本課題組前期發現,在高糖培養肝細胞和胰島β細胞中ROS升高,而PPAR-γ表達和活性降低,提示ROS可能是PPAR-γ的負向調控因子[31]。PPAR-γ激活可抑制小膠質細胞ROS和促炎因子的釋放,保護神經元免受損傷。此外,在帕金森動物模型中使用PPAR-γ激動劑可抑制氧化損傷,減少促炎因子表達,增加抗炎因子釋放,發揮神經保護作用[32]。因此,PPAR-γ信號激活可能通過氧化還原平衡調控巨噬細胞炎癥反應。
4 PPAR-γ激動劑在炎癥疾病中的應用
按照來源,PPAR-γ配體可以分為內源性和外源性兩大類,內源性配體包括亞油酸、亞麻酸和二十二碳四烯酸等多不飽和脂肪酸及其代謝產物15-脫氧前列腺素J2(15d-PGJ2);外源性配體包括羅格列酮、吡格列酮等噻唑烷二酮類(thiazolidinediones,TZD)類抗糖尿病藥物以及GW1929等。研究表明,15d-PGJ2、羅格列酮和吡格列酮等可阻斷M1型巨噬細胞NF-κB及下游促炎信號激活,并促進M2型巨噬細胞抗炎因子轉錄表達[33]。15d-PGJ2和TZD類藥物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腫瘤、抗纖維化和抗血管生成的作用,在多種炎癥疾病治療中具有應用價值。
由生物和化學因素導致的腸道炎癥疾病是近年來國際研究的熱點,大量研究發現提高PPAR-γ配體水平對多種腸道炎癥疾病具有保護作用[34]。羅格列酮和吡格列酮干預可改善三硝基苯磺酸誘導的大鼠結腸炎癥反應和黏膜潰爛[35],小鼠腸道上皮細胞中過表達PPAR-γ可抑制LPS等誘導的炎癥反應。此外,共軛亞油酸也可通過激活PPAR-γ,調控野生型小鼠腸道M1/M2型巨噬細胞比例,減輕炎癥反應和腸道損傷,但對結腸特異性敲除PPAR-γ的小鼠則無明顯保護作用[36]。臨床試驗也表明,潰瘍性結腸炎患者中PPAR-γ表達顯著減少,而七葉皂苷(aesculin)可通過激活PPAR-γ途徑改善腸道炎癥[37]。
膿毒癥是一種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易導致多器官衰竭和死亡,而巨噬細胞M1型激活及其介導炎癥風暴是導致疾病發生的重要基礎。大量研究表明,羅格列酮和吡格列酮可抑制膿毒癥小鼠巨噬細胞的促炎分化,并增加抗炎因子的分泌,抑制肝臟、肺臟和腦部等組織的炎癥損傷[38]。臨床研究也提示,羅格列酮和吡格列酮可降低膿毒癥患者血清中TNF-α和IL-6等促炎因子表達,改善其肺部和肝臟等組織的炎癥反應[39]。
自身免疫性炎癥疾病是指自身抗原免疫紊亂導致機體炎癥損傷的一類疾病,包括類風濕性關節炎和系統性紅斑狼瘡等。研究發現,PPAR-γ激動劑吡格列酮和羅格列酮有助于促進單核細胞向M2型巨噬細胞分化,預防小鼠系統性紅斑狼瘡及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40]。此外,吡格列酮可減少類風濕性關節炎和椎間盤退變患者外周血單核細胞的IL-17A、IL-22和IFN-γ表達,減少脾臟巨噬細胞IL-6的分泌,延緩病情進展[41]。TZD類藥物還能夠誘導滑膜細胞凋亡,減少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滑膜細胞中TNF-α和IL-6的分泌。
代謝性炎癥是肥胖、非酒精性脂肪肝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發生的重要機制。以往研究認為,TZD類藥物可通過激活PPAR-γ調控脂肪細胞分化和脂糖代謝,能夠改善脂肪肝和胰島素抵抗。最新研究提示,羅格列酮調控肝臟和脂肪組織的巨噬細胞M1/M2型極化比例,減輕動物胰島素抵抗,羅格列酮增強胰島素敏感性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其自身的抗炎特性[42]。此外,吡格列酮能夠改善非糖尿病患者的代謝綜合征,服藥6周后患者血清和單核細胞中促炎因子表達下調,抗炎因子升高[43]。
5 小結
作為機體的固有免疫和炎癥調控的核心組分,巨噬細胞的數量和功能穩態對于維持機體健意義重大。PPAR-γ是一種配體依賴的核受體因子,是機體維持正常脂糖代謝和胰島素敏感性的基礎,在肥胖、脂肪肝、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中發揮關鍵作用。近年來研究發現,PPAR-γ還與巨噬細胞的極化和炎癥調控息息相關,不僅可抑制M1型巨噬細胞促炎信號激活,還能促進M2型巨噬細胞抗炎反應。PPAR-γ激活還可影響巨噬細胞內氧化還原平衡,進而間接發揮抗炎調控功能。TZD類PPAR-γ激動劑在膿毒癥、肥胖、腸道炎癥和自身免疫炎癥性疾病中發保護作用。但也有研究指出,長期服用羅格列酮和吡格列酮等藥物能夠導致機體體質量增加,增加膀胱癌和慢性腎炎的發生風險。此外,姜黃素、二苯乙烯苷、丹皮酚、人參皂苷等中藥單體也能促進巨噬細胞抗炎反應,減輕機體炎癥損傷。因此,PPAR-γ是調控巨噬細胞炎癥走向的核心分子,其激動劑在各種急慢性疾病中應用具有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