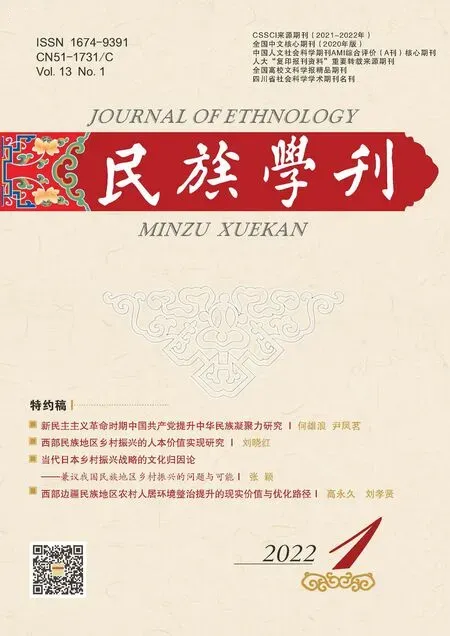納若敢嘯:足球、族群性與麗江男性氣質的建構
高詩怡
2019年12月一個周末下午一點,鄭哥匆匆趕來球場,一手開始翻弄裝備包里的球衣,另一只手拿著手機正在通話,“沒錯,你去找小王①,一切不變,只是換個人接你。”鄭哥今年31歲,麗江納西族,是一名從事旅游業的包車司機。為了參加這場業余聯賽中的焦點之戰,鄭哥特地與哥們調了班,取消了原本要開車帶游客去藍月谷②的行程。他告訴筆者,“生意是生意,足球是足球。他們都說我們麗江商業化,宰起客來狠的。但你看看我們的足球,就知道我們很純粹的。”
這種通過男性成員表現族群性的描述引起了筆者的注意。要知道在中國語境下,有關族群與性別的交叉研究通常包含了“中心-邊疆”的前提。學者們發現族群不僅是“想象的共同體”,也是與中央相對照的文化意義上的“他者”[1][2][3]。誠如劉琪所說,當邊疆成為整體性的“他者”時,它在大多數地處中心的人的眼中“形象注定是落后的、愚昧的、沉默的,只能被‘中心’言說的”[4]64。男性氣質又往往與現代性、全球化相聯系,強調了理性、職業化與自主選擇[5]15。如何同時接受相對弱勢的族群與較為強勢的男性氣質在同一場域下的合流?尤其是如何跳出男/女二元性別的傳統思考模式,去探索族群男性群體間的權力動態?
當我們意識到西南民族地區的男性氣質鮮有被討論時,究其原因,到底是其男性文化的公共表征被隱匿于整體民族“女性化”的刻板印象之下;抑或是如學界所說,其男性成員“自我客體化”、主動將自身游離于本族群之外,“以客位(‘現代’)的視角來打量隸屬的族群”的結果[6]32?
問題的答案也許可以從鄭哥賽后發的朋友圈“納若③敢嘯④”看出一二。對當地人而言,族群的性別化想象與媒體、學界等上述視角所呈現的大相徑庭。正因如此,進入田野、觀察族群內部的日常實踐變得尤為重要。筆者在文中將闡述,在足球這一高度男性化的體育運動中,處于非支配地位的男性主體何以與社會、市場等多種力量進行互動,并展演其在地的男性氣質。
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眾媒介的蓬勃發展讓足球成為一個全球觀眾都能消費的文化商品。不少學者注意到這項現代運動在建構男性氣質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制造一種“強健、勇武、剛毅、頑強、堅忍、自信、信念、認同、自制、激情、情義”的男子氣概[7]89。但人們對男性氣質的體認是否受到不同時空、文化場景等要素的影響?更明確地說,東方的足球文化是否制造出了與西方主流表述中相似的“自我規訓”(self-discipline)、“自我負責”(self-reliant)的男性主體[8]?學界依舊缺乏相關的經驗研究。
此外,中國的男性氣質研究依舊是以家庭本位為取向的。家庭包含的親屬組織、代際關系、法律慣習等功能[9],使得男性身份的表達在特定時空下逃脫不了“兒子、丈夫、父親”等性別角色的期待[10]。如何考察家庭之外,在民族、城鄉等權力維度上,少數民族的男性氣質在社會轉型中所遭遇的可能性與不確定性,我們依舊缺乏更為深入的田野考察。
基于此,本研究聚焦西南少數族群男性氣質與足球的關聯性探索。首先,突破“中心-邊疆”的局限,重新審視“族群”在以足球為核心的男性氣質生產機制中的作用;其次,剖析在地男性氣質的內在邏輯,分析市場經濟中足球與族群互動時產生了何種張力。試圖說明:當地方性的族群認同與性別化的現代文明產生聯結時,當麗江納西青年們將一種理想化的性別預設投射在現代足球之上時,男性氣質建構的過程關聯了中國社會的深刻轉型,凝結了個體欲望、族群傳統、話語建構、性別實踐等要素的復雜展演。
一、男性氣質建構的理論視角
(一)關系化的男性視角
伴隨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性別研究學者開始由婦女史(women’s history)逐漸轉向社會性別(gender studies)的考察。所謂社會性別,應當被理解為一種以生殖場域(reproductive arena)——如性行為、生育、養育子女等——為中心的社會關系。它的存在,標志著生殖差異,通過身體的具身實踐,最終進入社會化場域的過程[11]71。換言之,性別的概念由生理結構為基礎的身體出發,經由后天建構,逐步由生理“差異”轉向社會“關系”。
將男性氣質納入社會性別的范疇進行考察,亦表明了一種由性別角色理論強調的“男/女”生物學意義上的二元差異向一種“關系化”性別實踐的研究轉向。它探索了一個男性如何獲得“男人”的性別身份的“創造”和“表演”過程。即男性氣質應當被看作具體的表征與行動,在多種情境化的社會合力的作用下,完成社會意義上“男性”性別化特質的建構。
盡管男性氣質并不為生理性別為男性的群體所獨有,同理,若后者沒有表達男性氣質也并不意味他們沒有“男人味”。但我們所處的社會結構、政治經濟文化都形塑著某種特定的主流男性氣質范式,以獎勵符合規范、懲戒規范之外的性別秩序。如康奈爾所提出的“霸權式男性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等級模型便反映了這一點[12]:男性氣質的支配性地位取決于以“女性/自然-男性/文化”為核心的父權制的意義系統。除卻這一理想范式,以從屬的、共謀的、邊緣的男性氣質(們)為代表的關系化他者,客觀上拓寬、復數化了男性氣質的內涵,卻又事實上以類型化差異確立的邊界幫助鞏固了霸權式男性氣質的支配性地位。換言之,霸權式的男性氣質不僅表明了男性對女性的整體統治,也反映了男性群體內部權力的傾軋與宰制。
康奈爾在后續的研究中繼續提到,霸權式的男性氣質并非一成不變,它只是特定時空下主流價值文化,通過特定的“權力關系、生產消費、情感關系與符號文化”[13]120-132,不斷再生產的一種性別秩序。它同樣受到“競逐”(contested),這樣的權力“并不比其他種類的權力更徹底或絕對”[13]123。這使得我們需要挖掘更為靈活、動態的視角,尤其是在體察霸權式男性氣質通過何種機制完成其性別氣質的再生產之外,給予邊緣、從屬群體的能動性足夠的關注[14]849。
(二)足球與男性氣質
現代足球作為“保證父權制結構發揮其功能的主要場所”[15]79,連接了身體、社區、市場、國家等不同主體間性別化的互動。民族國家時代的競技體育,通過職業聯賽的開展、體育課程的培養,不斷強化了個人的身體、球隊的勝負與國家的榮譽之間的聯系。歷史地看,以強身派基督教(muscular masculinity)精神[16]87為指導的西方性別理想范式奠定了現代足球的男性氣質。它使得一種借由身體的表達、戰爭的隱喻,強調肌肉、尚武、忠誠與英雄主義的品德成為了足球性別氣質的底色。
以市場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與足球的商業化,一定程度撼動了自上而下社會機制所培育的男性氣質的支配性地位。當金錢成為衡量“現代性”中個體為之奮斗的最終目的時,如何獲得金錢、轉化資本成為市場邏輯下行動者的主要訴求。[17]足球世界性別氣質的發展,也反映了這一趨勢:一方面男性的消費能力成為體現男性氣質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資本為驅動的市場經濟積極引導、形塑一種城市中產精英男性的“都市麗男”形象,成功豐富了原本以硬漢形象主導的陽剛足球文化:如以貝克漢姆為代表的帥氣、英俊的“陰柔特質”受到廣大球迷的喜愛[18]73。以傳控等為代表的技戰術配合也逐漸取代長傳沖吊找高點的粗糙球風,一定程度地反映出“眼球經濟”下“美麗足球”的市場偏好;另一方面,政治、經濟、科技、媒體等力量的不平等配置,讓商業足球愈發成為一個“限男性”且“超男性”(hyper-masculine)的公共空間⑤。運動員的身體成為資本博弈的工具,年輕人唯有取得職業生涯的成功,收獲高收入,才能成為個體家庭乃至家族的有力供養者,并完成“男子漢”的成年。
然而這種被物質的巨大滿足感所構建出來的欲望主體,似乎夸大了個體性別化行為的能動性。盡管已有學者注意到非洲足球運動員從母國通過運動移民到歐陸聯賽時,男性氣質被足球產業假借“自我企業家式的管理”(selfentrepreneurship)之名,巧妙地被剝削[19][20]1770。在討論中國情境時,青年男性如何想象、定位,以及構建其主體性的過程,鮮有學者從社會階層[21][22][23][24]以外的角度深刻論述,更少有研究聚焦地方性少數民族青年面臨日益商業化的生活世界所遭遇的困惑與掙扎。當今的足球世界,很難再有一球成名的童話故事。族群、階級,乃至區域發展差異在欲望橫生的現代性條件下遭遇的矛盾、張力與不確定性,依舊需要民族志的佐證。
(三)性(別)化的邊疆
具體場景的田野作業重要性不言自明。在有關中國的民族志中,族群與性別的論述并不少見,但仍缺乏西南少數族群中男性與男性氣質的相關探討。現有的研究對族群男性化的意象:一方面多集中于歷史上的北方邊陲。如烏·額·寶力格(Uradyn E.Bulag)[25]有關蒙古男人做出“陽剛之氣”的判斷,又如希爾曼和漢弗萊(Hillman & Henfry)[26]對藏民男性得出“真漢子”的結論。然而,在研究者看來,對于地處邊疆的男性特質的提煉——往往從其身材、體力、性格等方面——目的是為了服務中原正統而作為“他者”參照而存在。以傳統中國文化中“標準”的“文(文化素養)/武(孔武之氣)”男性氣質視角來說,少數民族的男性氣質并不在此列,甚至很多時候,誠如雷金慶所說,被直接“性化為動物的蠻性”[27]10。
另一方面,南方族群與性別的內部聯系,如杜磊(Dru Gladney)[28]所說,往往暗含了“現代”的漢族男性與“原始”的少數民族女性之間統治/被統治的隱喻。如路易莎(Lousia Schein)[29]在貴州西江苗寨的考察中便發現,苗族婦女們平日里與漢族女孩衣著并無二致,唯有在文化慶典、商業活動中,才特地穿上節日盛裝、跳起民族的舞蹈。這一形象被來自外地的游客、學者、攝影師等城市男性精英們捕捉到,成為了外界對苗寨女性化想象的主要根源之一。少數族群的男性形象,在公共表征中,或被“閹割”成整體區域女性化的一部分,或如李瑞福(Ralph Litizinger)[30]在研究廣西瑤族的田野調查中所發現的那般,這種性別化的凝視也發生在族群內部。即當地少數族裔精英男性們默認了——主要以當地女性參與的民族文化活動等同于一種本民族文化的本質化表達——這一觀點,參與到了將本民族公共形象女性化的合謀之中。
自1996年麗江地震災后重建工作開始,尤其是1997年12月麗江古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麗江民族旅游的迅速發展標志著邊陲地區社會結構的轉型進程由傳統的農業種植的生計方式轉向以文化旅游為主、兼之以“清潔載能產業、高原特色農產業、生物醫藥大健康產業”的結構性變化[31]。如果我們承認上文所說西南中國少數民族女性乃民族文化符號的主要載體,我們不難發現民族男性在主動構建其性別主體性的過程中被雙重邊緣化:他們既無法以文化掮客的角色施展本族文化的男性氣質;又無法在國家族群認同的一系列實踐中完全挑戰沿海、城市精英的霸權男性地位。
有鑒于此,要回答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男性氣質的生產過程,我們既要厘清當地男性氣質與霸權式男性氣質之間的異同;又要看到族群內部,同性/異性之間,他們自我的表達。因此當足球作為一種超級男性氣質(hyper-masculine)的文化進入麗江地區時,它究竟完成了何種男性氣質的再造,抑或加劇了何種男性氣質的焦慮?這正是筆者希望探討的問題。
麗江的足球傳統由來已久。明代詩人木公在描繪族人開展足球活動的詩中便已提到,“緋紅舞翠秋千院,擊鼓鳴鉦蹴鞠場”[32]318。回述近百年來納西青年追尋足球之旅,從“傳教士、外出求學歸來的學者、和駝峰航線的美國大兵”將現代足球傳播至麗江伊始[33][34],到從學校走向鄉村(1909-1952年),開始與國內如“燎原”足球隊等進行交流(1950-1959年),加入少體校班、開始轉型(1960-1969年),國內交流頻繁、開始轉折(1970-1979年),推進大眾化、進入發展時期(1980-1995年),開始走上職業化道路(1995-2003年),開啟本土職業化足球的發展道路(2004年-至今)[35]88-90,尤如麗江卷入現代化浪潮的縮影。
本文旨在探究一個核心問題:筆者借助足球這一勾連個體欲望、地方社會和現代性的中介,分析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男性氣質的建構過程。具體來說,當民族文化的“傳統”表征落于女性主體之上時,男性群體是否憑借現代性的足球挽救其族群化的男性氣質表達?答案如果是,那么麗江足球世界中男性氣質的具體生產機制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么足球的性別文化與族群的男性群體又發生了什么聯結與碰撞?
首先,筆者將男性氣質作為一種話語的建構來看待,發現“納若”(納西男人)作為一種被主動制造出來的族群性傳統,不斷地在足球場景中被策略性地應用。其次,在市場經濟改革轉型的特殊階段,納西男人作為一種具體的生產與消費的性別化主體,踐行了一種極致的男性氣質,或者所謂的“敢嘯”(沖啊)。然而,在足球少年逐漸成人的生命歷程中,以市場機制為主導的足球世界并未全然鼓勵男孩們實現其性別身份、成為“真正的男人”;有時甚至復刻了現有的權力結構,進一步加劇了個體的男性氣質危機。
二、足球、族群與男性氣質的建構
本文遵循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主要以參與式觀察的方式,考察納西族群內部不同行動者在不同情境中的性別實踐。從2019年6月整月以及當年10月至2020年12月總共為期16個月的時間里,筆者在麗江當地及滇西北地區進行少數民族(以納西族為主)足球的田野調查。本文將少數民族足球的范圍定義為以少數民族參與為主的足球活動,包括但不僅限于(半)職業足球聯賽、友誼賽、野球和杯賽。
作為球迷,筆者感受到格爾茨所說的近距離經驗(experience-near)與遠距離經驗(experience-distant)在研究者與田野報道對象間關系化的互動:作為球迷的參與經驗使筆者在很多時候成為田野的局內人(insider),一定程度上以“本土觀點”(native’s point of view)體會當地人的處境;然而筆者的日常經驗與作為人類學研究者的觀察與分析,則令筆者不斷調整自己的個體身份,研究經驗性材料背后的演變過程與作用機制。本文以深描(thick description)來透視地方性社群所編織的社會生活意義,透過納西青年的足球生活所言說的意義,探索足球、族群與男性氣質的建構過程。
本文所提的年輕人或青年,大多指的是20-35歲上下的納西男子,之所以集中于此年齡段,首先是因為青年男性正值“男孩”到“男人”的中介狀態,對男性氣質的呈現更具“戲劇”性。此外,該階段的男子出生、成長恰逢麗江足球的深度發展期,他們自幼從長輩口中得知早年間麗江美好但艱苦的足球歲月;也見證了職業足球在麗江發展、衰落的全過程,親身經歷了少體校、(半)職業道路,對少數民族地區的足球發展有著獨特而深刻的感觸。
(一)納若:族性張揚
筆者初到田野,便遇到本地一樁足球盛事。以二哥、阿華為首的足球愛好者,集結了一支球隊代表麗江參加云南省十一人制的業余足球杯賽,并最終獲得了冠軍。復盤淘汰賽四場正賽,阿華告訴筆者,全隊基本貫徹了極富納西風格的4-4-2打法,收效頗豐:
“業余球賽看經驗也看打法。納西的球員耐力普遍都好,就是跑不死嘛。所以中后場保持防守陣型,兩個邊路拉開,大腳傳到禁區,獲得門前機會的思路,我們一直做得不錯。當然確實速度上,有時候跟不上平原地區的短平快,但我們敢拼敢沖、輕傷不下火線。”
有趣的是,參與麗江足球的球員并非都是納西族,但在對外的宣稱口徑中,往往以“族群”的頭銜相稱。如上文的杯賽,麗江隊參加的球員雖囊括了納西族、白族和傈僳族的球員,但在交流切磋時,都自稱納西、納若⑥。尤其是在與同來自麗江的寧蒗彝族自治縣的球隊進行決賽前,朋友圈紛紛造勢這是一場“納西與彝族”一爭高下的強強比拼。
球隊中的白族球員張哥,對此并無半分介懷。他甚至鼓勵筆者說,“小高,你要盡快融入當地,學民族話(納西話)。我來麗江二十多年了,開始也一句不會講。”顯然,張哥學習納西語的過程幫助他更好地融入了當地生活,而在球隊內部講民族話不僅更方便隊友之間的交流,同時也避免了其他球隊聽懂本方的技戰術配合。甚至在奪冠后,接受采訪時,張哥也未對記者默認全隊是納西隊員時提出任何駁斥。他認為大家一起奪得冠軍更為重要。
換言之,球員認同的確立,不僅指向他們常年生活的地緣社區(麗江),更為關鍵地,在足球的場域中,被“收編”入主流的族群話語(納西)中。“納若”,被球員們掛在嘴邊,寫在朋友圈里,可直譯為“納西男人”。與現代性消弭了族群間的認同、國家清晰化了民族的政治性分類不同,“納若”一詞在足球文化中的流行,其族群身份的邊界是模糊的、包容的、策略性的。
類似“納若”的話語在筆者的田野中被反復提及。絕大多數的麗江籍球員司職中后場。如一位從事當地青訓的朋友解釋道,“因為是高海拔,我們的心肺功能、體力耐力會比平原、沿海地區的(球員)好一些。”好的耐力意味著相對差的瞬間爆發力和相對粗糙的腳下技術。然而,略失技巧性的踢球風格并未令本地球員自覺落后于人,恰恰相反,他們更像是比較后、“自動放棄”了前者并繼續原先以血性、原始、充滿拼勁為特點的“納若”踢球方式。這或許從側面反映出他們對足球場上男性氣質的感知建立于后者之上。
這種隱匿其他族群身份、集中張揚納西性的做法,恰好暗合了足球諸多男性氣質中“陽剛之氣”這一特殊面向:借由“納若”啟動了一種看上去“真正”具有男性氣質的意義系統,并在足球這項綜合體現技戰術與身體素質的運動中,強調斗爭、身體與拼命。進球固然值得稱頌,經典陣型中對四后衛與門將的推崇與注重,則反映出“納若”將“男人味”建立于剛硬的、粗糲的踢法之上。這種看似“超驗性”的性別文化并非自然而然,其涵括的各種符號、隱喻,有時也是人為制造的。
較之皮膚白皙的外地游客,麗江的球友們皮膚黝黑、身材敦實。多數球員胳膊、手臂、小腿上著紋身,圖案多為納西史詩中象征勇武的猛獸圖騰。繼麗江古城被都市人重構為一個可欲的、與現代性對立的烏托邦空間后[36],本土球員身體所承載的意涵,與其成長的物理空間,同樣沿襲了作為民族文化商品的消費邏輯。如足協推出的首部草根足球微電影,渲染麗江玉湖村的足球文化時,重點描摹了雪山、草甸、牛羊等自然元素。誠然這一意象是為了突出滇西北地區人民對足球的熱忱,然而這些看上去更符合都市人對邊疆“與世隔絕”的靜態想象,主動屏蔽了當地業余足球與外界熱火朝天的互動與交流。
有意思的是,這種區別于主流印象的邊緣性別化符號不僅為都市公眾所“凝視”,也被本地人不斷識別與施展。比如,麗江足球不斷通過再現“傳統”來幫助實現上文的納若形象。
在當地業余聯賽的球員熱身訓練結束之后,筆者常能觀察到他們圍成一圈,進行儀式化的助威活動。通常由一名主唱者發出一段低沉、短促的唱詞,球員們逐句附和,聲響震天。歌詞大約可以翻譯成,“玉龍雪山高又高,金沙江水長又長,我們偉大的阿普三多神,祝福各位吉祥如意!沖啊!”主唱者之一的二哥向筆者解釋,這個納西唱段頗有古風,已鮮有納西青年知曉,也就在酒酣耳熱、踢球之余,才會被象征性地展演。
外地游客第一次目睹球員的行為,很難不令其聯想到古時納西武士挾短刀、兩軍對壘前肅穆的場景,也很容易想起2016年歐洲杯冰島隊球員、球迷在球場、看臺交相呼應的維京怒吼。這些常被描述成尚武、狂熱、強悍的、充滿男子氣概的品德,事實上包含了大量的被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稱之為“被發明的傳統”的運作——借由一再重復的儀式,使人恍惚間生出一種不辨過去當下的感觸。然而,這種與過去的聯結,就如同維京怒吼事實上是冰島球隊斯塔爾南(Stjarnan)的球迷從2014年歐聯杯對手蘇格蘭的馬瑟韋爾(Motherwell)的助威歌曲中得到靈感[37],納西的陣前助威同樣是近十年才經由納西族祝酒歌嫁接到足球場景中的。
但很顯然,參與儀式的球員們并未覺得有何不妥。對“納若”而言,這些強調“傳統”的做法區別于職業足球的普遍助威、帶有民族性格的儀式性表達,是當地人面對迅速變化的世界、一種刺激性反抗機制。正如在昆明念大學的小木所言:“我們納西族在外面組隊的時候熱身也會搞這一套,很有氣勢,是別的(地方)沒有的。不是說,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嘛。”
這種主動對立城鄉、回歸“傳統”的論述也內化于“納若”記憶中特定的足球話語空間。與城市足球少年規范系統的踢球訓練相比,“納若”往昔的足球記憶與納西民族的歷史根基融會貫通而顯得“原始”而“野蠻”。
家住拉市,28歲的小馬向筆者回憶了自己幼時踢球的情形,“別看咱們(指筆者)年紀差不多,我小時候(1990年代末)踢球就在壩子上踢。”所謂的壩子,指的是云貴高原地區一種常見的“散布于山脈河谷間的平地[38]1。拉市地區作為麗江城郊一片被水域包圍的壩子,孕育出一種獨特的足球景觀:一方面,踢球時間不固定,小馬接著道,“水會退(潮)嘛,我們就去淺灘上踢。水一漲,就沒辦法踢了。”另一方面,足球裝備也異常匱乏,“我們一個村就一兩戶人家里舍得買足球,就那種四號球,踢小場的。(平時)大人給我們搞一個豬尿泡,往里面吹氣、扎緊,我們拿這個當足球踢。”
家住古城的楊哥回憶起自己最初的“足球生涯”,也感慨萬分,“小時候我家就在(麗江古城)四方街附近。(1980年代)太窮了,好不容易有個足球。我就天天在石板路上踢。有時候就對著墻踢。也沒機會學(專業的足球知識),我就蠻練,一下午幾百下幾千下的顛球。”
艱苦的足球環境,使曾經每一次上場機會都彌足珍貴,男孩們需要拿出十足的拼勁和誠意參與到球賽中。而對往日這些“野蠻生長”片段策略性地重拾,也讓當地男子們重構了一種“純粹”的、獨特的“納若”敘事,族群的認同也變得更為強烈。麗江足球越被抽離、包裝成一個遙遠的、異鄉的故事,本地人愈發將情感、記憶投射其中,制造出一個傳統的、烏托邦式的美好世界。
(二)敢嘯:生產與消費的性別化實踐
不夸張地說,足球在麗江有著不可撼動的特殊位置。二哥如是說,“只要是個男娃,我們一定讓他從小抓(踢)(足)球。”無論是最終進入職業聯賽的球員,或是從小學、初中到高中甚至進入大學校隊的半職業運動員,還是閑來無事約野球的球友,足球成為同性之間建立兄弟情義、締結“納若”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
除了以“納若”為核心向外構建策略性的話語系統與其陽剛之氣,我們勢必要考慮到族群內部不同主體間在足球場域的性別實踐,尤其是西方足球全球化與中國足球的不同“范式”指導下,麗江的足球群體表達、生產,乃至再生產了何種男性氣質。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足球的發展首先依托于“國家隊——專業運動隊”舉國體制的組織框架,將個人命運納入集體與民族國家的榮譽話語建構中。將運動員的身體看作一種被控制、被馴服的原始力量并不是件稀奇事兒[39][40]。體育訓練場中,軀體動作的表達與完成不僅需要適應日復一日高強度的訓練節奏,也令運動員們對“為國爭光”的渴望而對傷病、獎懲逐漸習以為常。
1992年“紅山口會議”的召開,與隨后1994年甲A聯賽、2004年中超聯賽的成立,標志著中國足球職業化的展開:商業資本的進入、大眾媒介(如電視、網絡轉播)的發展,一方面帶動了以職業俱樂部為導向的國內商業聯賽模式(中超-中甲-中乙)的不斷深化;另一方面,全球性的足球狂熱在中國本土也不斷發酵:克服時差觀看歐陸球賽、購買正價球衣、球鞋等周邊產品,逐漸成為當下球迷的新興生活方式。
布迪厄在《體育與社會階級》一章中指出,當我們將體育看作一個“場域”時,具體一項體育運動的實踐取決于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閑暇時光;也取決于不同社會階級各自的道德與審美的性情傾向(dispositions)[41]369。
如若我們將麗江的足球世界看成一個相對獨立但又與外界相互聯系的“場域”時,當我們考察納若足球青年的行為時,我們應當同時注意到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閑暇時光在其中的作用,與日常生活中更為具身化的狀態(審美、做派等),或者說上文所提及的性情傾向。
與其說足球在麗江是一項特定社會階層的運動,不如說是一項以族群為核心的運動。誠然族群的邊界如上文所說,包容且具備策略性,然而與族群這一分析單位進行對話的,往往是歷史的麗江足球往事與當下的都市足球景觀。
“敢嘯”成為了麗江足球場域中重要的行為準則。所謂“敢嘯”,在納西語中可直接翻譯為“向前沖,沖上去就干”。這種蠻勁既可以被理解為對早年間麗江民間尚武風尚的佐證;又可以被解釋為如今面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困境而做出的彌補。如趙曉鷹在整理民國時期以麗江省立第三中學(現市一中前身)高17班男生為班底的“老母雞”隊的相關資料時發現,“敢嘯”作為球隊的精神氣質,支撐其與國民政府在麗江駐軍“團管區”的球隊交手時,力保球門不失并最終以2∶0拿下比賽。他援引當時“老母雞”隊主力后衛趙行修老先生對賽前準備的回憶,“為了防備‘團管區’軍人的霸道和賽后報復……隊員們鼓足了勁,做好了在球場上決一死戰的準備。隊里還有幾個隊員上身穿隊服,下身打綁腿,綁腿里藏了刀子以備不測,然后在綁腿外套上長褲來遮蓋。”⑦
對于當下的足球青年們而言,“敢嘯”不再成為反抗趾高氣揚的軍政府球隊的底層童話,而是逐步演變為他們初試職業足球圈的內心準繩。一名曾參加青訓的球員如是說,“我們已經很幸運了。比我們年長四五歲的大哥們,他們訓練的時候根本沒有專業持證的(足球)教練。這個體現在球場上,(他們)基本功就沒我們扎實。”另一名前青訓隊員也指出,“我們的條件肯定是比不了大城市的。那怎么辦?只能拼了命地踢。要吃苦!”
如一名高中參加校隊的隊員想起舊時拉練便感慨道,“最難熬的是用阻力傘。逆風跑、順風停。風吹過來的時候,(阻力大得)真的受不了。我總算知道了什么叫作絕望!”目前在一家中甲球隊踢球的小和回憶起曾經在麗江的青訓生活時也指出,訓練內容辛苦僅是一部分,日常生活的撕裂也需要時間去克服和消化。他說,“我們一個月才回一趟家,純軍事化管理:早起跑圈、晚上統一熄燈。煙也不敢(抽)。吃飯都在食堂,也沒法出門吃串串。說實話,比(學校生活)苦多了。有時候想起來就跟‘坐牢’一樣。我以前在學校里還會翻墻出去打游戲,但(青訓)這邊有紀律,我都不敢和伴兒們約酒了。漸漸地,身邊的圈子也小了。就宿舍、食堂、訓練場三點一線。”
男孩們默認了訓練體系的艱苦與殘酷,并堅信唯有這種身體化的投入才是獲得成功的不二法門。包蘇珊[42]在有關中國體育與身體的研究中指出,身體是有權力階序的,農民、邊緣群體往往更需要通過身體化的表達(如肉體的傷病、拼命)來完成其階層的躍升。雖然麗江足球的傳統由來已久,但因為地處邊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足球基礎設施的資源配置仍處于相對劣勢的地位。在田野時筆者發現,報道人時常提及麗江足球條件,并試圖以此為理由,合理化枯燥的訓練生活,恰好也驗證了這一觀點。即邊緣化的身體必須通過吃苦才能獲得更為“合法性”的認可。
如果我們承認市場經濟改革進程得以推進的重要原因在于現代性由生產向消費領域的轉型[43][44][45][46],那么我們應當注意到足球市場化過程中所帶動的商品化與消費主義是如何影響個體在消費領域的性別化實踐。“敢嘯”在足球社交中也比比皆是。踢完野球,約一頓啤酒燒烤局,似乎已成為納若球友們的慣例。然而不同于都市中產工作后閑散地喝一杯,納西青年們的消費往往是“極端的”“非理性的”。以下一則田野筆記記錄了此類社交場景的特點:
(一場友誼賽后)我如約來到KTV。推門進入包間,映入眼簾的是逐一排開的三件雪花啤酒。每件啤酒二十四瓶,地上還有四件(均為24瓶,當地人一般將此數量稱為“一件”)未拆封的啤酒。踢完球的球員陸續到來,有四個帶來了女朋友。加上我一共16人。沒有人點歌。等卡座四邊均勻地分配了四個人,球員們玩起了骰子與行酒令。(2020年11月13日)
拼酒和勸酒是足球社交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在球員們看來,吹瓶不僅是男子氣概的體現,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上文提到的納西族群性中一種特殊的精神氣質:敢嘯。這種充滿力量、“原生態”、極致的表達,一方面高調地展現了與現代性劃清界限的姿態;另一方面,也暗合了民族身份、中國文化與男性氣質的關系。這體現在性別的領域里,表現之一即男人始終被期待作為在兩性關系中積極主動的形象,如敬酒中常提到的“你們(女性)別喝了,我幫你喝。”表現之二,他們更渴望得到同性之間的認可抑或征服后者。足球青年們喜歡用“(玉龍)雪山不倒我不倒”“夾biu(厲害了),干(酒)就完了!”來揶揄、“挑釁”酒桌上的哥們兒。
值得指出的是,這種借由消費表達的主體性既是夸張的、充滿陽剛之氣的;又在主流的表達中是邊緣的、非精英式的。麗江男人抽煙、喝酒、打架的片段,常被游客解讀為一種與城市中產精英男性“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經濟地位、思維理性、獨立上進”相對立的負面形象[47]145。
有趣的是,納西足球青年的生活邏輯,既希望反抗、掙脫后者,鍛造一種屬于本族群的男性氣質;卻又在此過程中,反映出對現代性、消費主義的渴望,因此或自愿或不自愿地參與到了市場、資本等權力的合謀之中。小興的故事正體現了這樣的矛盾。
筆者在阿明組織的一次聚會中認識了他的兒時玩伴小興。小興在酒局上一眼就能讓人注意到,他的膚色比起大部分本地的納西族青年要白皙一些,穿了件潮牌的大衣,脖子上纏著圈無線耳機,左耳戴著耳釘,看上去和時髦的都市青年并無二致。他被一群年齡相仿的少年們簇擁著,很熟絡地開始順時針方向給大家分發大重九的香煙。這種一盒一百塊的香煙,比起同伴們平日里抽的十幾塊就能買到的紅塔山,顯得矜持而貴重。而小興似乎并不介意,每次舉杯恨不得就分一圈煙。
他和阿明同齡,今年22歲,和阿明留在本地的一所大專院校讀體育專業不同,小興五年前因為過硬的身體素質,被東部一家中甲俱樂部看中,以二十萬的身價轉會加盟。
“我四五歲就開始抓球了。先在麗江踢,后來就出去了。(比起麗江)我肯定學到了更多,方方面面的,談吐、打扮,(麗江)比不了。(剛簽約時)心里頭有點發憷,和他們大城市的人比起來,我當時連普通話都有點說不利索,說不慌肯定是假的……但你想想現在很多球星哇,小時候條件也不太好,你看那個法國的姆巴佩,就是靠自己現在站穩腳跟。我就想著,只要能吃苦,一定也能踢出來。(笑)當然和他(姆巴佩)比不了。”
小興談起五年前的轉會神采奕奕,“當時家里擺了殺豬客,請村子里的老鄉來吃了好幾天。”在小興的哥們看來,這是件值得全村驕傲的事。阿明說道,“我們小時候聽說,光是代表麗江縣隊踢全省的比賽,回來都跟現在巴薩、皇馬奪冠了一樣,要舉辦慶祝游行的。別說他(小興)能出現在電視鏡頭里。”另一位朋友也點頭同意,認為小興的成功讓朋友們與有榮焉,“那次他上場,我還專門截了圖發了朋友圈。”
事實上就目前的足球生態而言,22歲在中甲踢非主力陣容,小興有極大可能,最終并不能登上諸如中超一類的頂級賽事的舞臺。這意味著,足球只能成為小興一份普通的工作,他既不可能就此發財,更難真正出人頭地。更令人沮喪的是,小興最終告知了筆者他回麗江的真正原因,“現在足球都挺難的,我們球隊沒啥錢了,說得蠻好聽的,讓我們放冬假。本來收入主要也是靠一些雜七雜八的績效,一個月就兩千多塊的基礎工資。現在一放假,連工資都沒有了。雖然有宿舍住,吃飯不要錢嗎?”小興將回家休養的原因歸結于自己來自小地方,父母根本幫不上忙。按照他的說法,“很多有門道的人,都開始托關系找下家了。”自己只能“回家待一段時間。至少家里管吃管住。”
所謂“有門道”,小興指的是那些來自大城市的同隊球員,他認為他們從小熏染職業足球文化,“有想法有格局”,會為自己的職業生涯鋪路。不像自己,只是“憑著一腔熱情和賣力氣,傻傻踏入這個圈子”。小興告訴筆者,“他們和我不一樣的。說實話,我有時候挺羨慕他們(同隊隊員)。我們從小接觸的圈子都不一樣。但怎么說呢,這些話我也不知道怎么和家里人、伴兒們講,覺得有點丟臉。”
這是大部分走出麗江的足球少年的現狀。年少時因一技之長閃耀麗江,在即將“成人”之際,帶著親族或羨慕或祝福的目光來到更廣闊的職業平臺,追尋夢想、實現自我價值。對于家鄉的同輩好友們來說,能在“外面混”已經成為了“年輕人衡量個人能力與男子氣概的指標”[48]52。對于年輕球員來說,他們所能憑借的僅是隨時可能受傷的身體,因此當殘酷的資本攪動市場導致球隊的入不敷出,他們的職業生涯隨時會被打斷,甚至終止。
小興自覺回家“挺丟人”,由一個養家者退回到被照顧者的角色,對個體男性氣質的體認十分不利。但他也承認,依舊放不下面子,生怕辜負故鄉親友對自己殷切的希望。小興說,“我有空還是得再找找人,看看能不能轉會到別的俱樂部。(球隊)戰績差點無所謂,關鍵得能踢上球。”
小興的故事并不是孤例。筆者在田野中發現數位因球隊賬面出現問題而賦閑在家的年輕球員。在納西足球青年這一濃縮的身份中,我們可以看到地處邊疆的男性身體如何同時被超男性的足球文化塑造成渴望現代性的欲望主體,又被嚴苛枯燥的訓練所規訓為可變現、可交換的資源,并最終說服自身只有借助身體的生產才能完成他們在足球中的合法性。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消費成為建構身份認同、社會分層的第二場域”時[49]146-147,男性如何借以消費為主的“限男性”的公共空間,試圖構建一種當地人所稱為“敢嘯”的男性氣質。然而,他們既迷茫不知前路去往何方,又對暫回家鄉受到同輩的吹捧放不下面子,在酒局這樣一種暫時失序的狀態中,他們似乎離自己的夢想越來越遠。
四、結語
在有關西南中國族群的民族志田野作品中,一直有當地男性的身影,卻很少作為主體進行自我表達。即便有,在公共展演的形象中,其性別分工也越來越明確:婦女們被推到臺前,穿民族服裝,載歌載舞;男人們獲得了更多參與到地方公共事務、政治生活的機會,逐漸退居幕后。此舉的后果之一,便是少數民族女性成為了公共表征中被消費、征用的“資源”。當西南族群被想象時,女性化的面貌便會被記錄在公眾的討論中。
我們也許不能武斷地得出男性氣質作為族群性別化表達在西南中國被結構性隱匿的結論,但少數民族男人們從充滿現代性意義的足球中找回族群的男性氣質,則敦促我們重新審視族群、傳統、足球與男性氣質建構在市場轉型過程的微觀聯系。
本文將男性氣質的微觀構建機制分為話語建構與性別實踐兩個方面。首先,作為男性氣質的重要生產機制,足球與族群的互動不止于后者對前者霸權式的主流男性氣質的認可與順從。與現代性足球倡導的技戰術配合、身體、心理等全面均衡的職業化導向不同,納西青年們主動講述、展演出“納若”的男性形象。慣用的4-4-2陣型與對身體、力量的推崇,反映出納若對足球場上男性氣質的理解建立于傳統的陽剛之氣也就是以勇猛的體力拼殺來佐證足球賦予男人的榮譽。同時,田野中族群邊界的模糊,并策略性地運用族群性的傳統再造,使麗江足球創造性地制造出一種“純粹的”“美好的”男性世界,用以同時對抗“整體陰柔化”的中國西南印象中不夠威猛的納西男人形象與“邊疆的、野蠻的”少數民族足球敘事的經典刻板想象。
其次,足球除了作為聯結“納若”認同的最重要的紐帶之一,也反映出少數族群男性在現代性生活方式下的具體生命體驗。通過族群內部不同主體的足球歷程,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性的男性氣質在社會經濟轉型中的復雜演變與面對不同結構性力量時呈現的張力。一方面,處于非支配地位的“納若”在以金錢驗證男子氣概的市場經濟時代被不斷邊緣化,因此,以足球生涯所帶來的尊嚴、收入、價值成為其重新獲得男性氣質的重要途徑。他們心甘情愿將自己身體商品化為經濟營收的資本,并通過艱苦的日常訓練,能且僅能通過“極致”的身體化表達,在職業足球中初露頭角。另一方面,現代性所制造的欲望主體,在族群一以貫之的傳統“敢嘯”的性別話語支持下,令納若將一種“極端”的消費視作區域、城鄉發展中落后方的彌補手段。此舉看似擴大了個體的自主性,使現代性話語下消費主義的欲望得以暫時滿足,實則將區域、城鄉等結構性的不平等關系以更隱晦的方式掩蓋在當地少數民族足球青年豪邁的身體吶喊與掙扎之中。
注釋:
①鄭哥的朋友,另一位包車司機。
②位于玉龍雪山景區,麗江著名的旅游景點。
③納西語意為納西男人。
④納西語意為沖啊。
⑤筆者并不認為在足球領域沒有女性的參與。但競技運動在商業社會的運轉邏輯,無論是理想身體的展演,或是媒體報道中的性別化呈現,時刻充斥著男性凝視的目光。男性依舊是場上的主角,女性繼續充當背后的角色。
⑥本文無意對語言學中“納西、納、納日、納罕、納若”進行區分。之所以強調“納若”,是基于筆者在田野中與報道人的交流和觀察中發現,對方習慣性用“納若”一詞。
⑦趙曉鷹.秘史!“駝峰機場”與麗江足球:民國時期的“老母雞”隊.文章來源:三眼井58號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