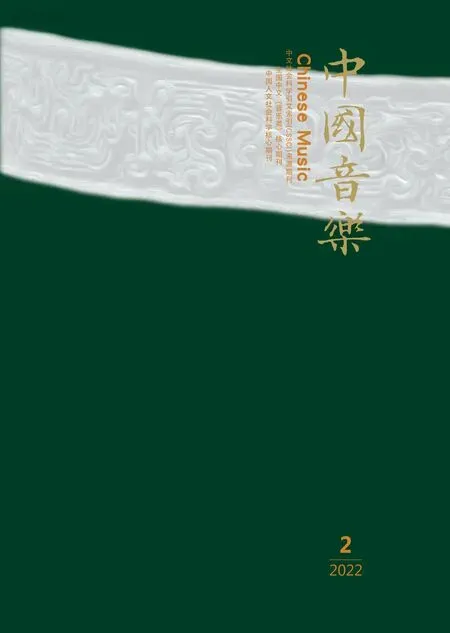中國音樂史學研究中的“點—線—面”問題的思考
○ 洛 秦
引 言
歷史學研究自始至終都是圍繞問題的提出、思考或解決而展開的。換句話說,沒有問題意識,也就沒有了歷史學研究的品質和意義。猶如著名史學家柯林武德所提出的那樣,對于問題的思考“在歷史學中乃是主導的因素”,而且歷史學研究“論證中的每一步都有賴于提出一個問題”。①〔英〕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77-378頁。
中國音樂史學是一門正在建設中的學科,不僅因為其年輕而尚未完善,而且也更由于其本身的復雜性帶給我們很多需要去思考的問題。從學科整體的宏觀角度來看,其中有三個層面的問題值得思考,即:一個關鍵的“點”—“音樂”觀念及其屬性的理解;一條重要的“線”—斷代分期及學科的“一統性”;多個層級的“面”—與相關各種學科領域的關系。如標題所示,我將其稱為“點-線-面”問題。
在此所謂的“問題”并非是那種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是期待我們一起來思考和探討的論題,如同英語的issue,而不是problem。因此,筆者在此拋磚引玉,以期大家批評討論。
一、中國音樂史學研究的“點”—“音樂”的屬性及其觀念
作為一門歷史研究的學科,中國音樂史學的核心無疑是“音樂”。也因此,對于“音樂”的屬性及其觀念的認知將極大程度上影響到音樂史學研究的相關問題,尤其是對于中國音樂史學而言,更是如此。
(一)一般意義上“音樂”的屬性及其觀念的論題
屬性是一個事物具有的共同性質和特點。音樂是人類的財富,世界所有民族皆擁有自己的音樂。因此,從本質上講,音樂的屬性就是一種文化的表達。從音樂人類學的角度來審視,音樂的文化屬性多樣而豐富,大致歸納為以下特征,即:1)人類自身的資源,2)文化的形式,3)社會的行為,4)文本形式,5)符號及象征系統,6)藝術形態。②〔美〕提莫西·賴斯:《音樂的屬性》,張伯瑜譯,《中國音樂》,2014年,第1期,第14頁。
當代西方音樂學界對“音樂”多重屬性的理解也在不斷自我反思和改變,由原來將音樂定義為藝術和審美的屬性,逐漸調整為一種集藝術、社會和文化為一體的表達。例如,國際權威的《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2001年)中對于音樂學研究的目的就明確指出:
(Musicology)should be centered not just on music but also on musicians acting within a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This shift from music as a product (which tends to imply fixity)to music as a process involving composer, performer and consumer(i.e.listeners)has involved new methods, some of them borrowed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particularly anthropology, ethnology, linguistics, sociology and more recently politics, gender studies and cultural theory.This type of inquiry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ethnomusicology.③〔英〕斯坦利·薩迪(Stanley Sadie)主編,約翰·泰瑞爾執行主編:《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麥克米蘭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出版,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引進出版,2012年,第17冊,第488頁。
這段文字大致意思為,受到社會科學,如音樂人類學(ethnomusicology)的影響,音樂學的定位應該不僅是對于音樂本身的研究,而且更應該對于與之相關的社會和文化環境的關注。對音樂的認識不只是將其作為一種靜態的作品,而是包括了對于作曲家、表演者和聽眾在內的一種過程性思考。這體現出西方社會對于理解音樂與文化關系復雜性問題的不斷全面和深入。音樂人類學家梅里亞姆在其《音樂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Music,1964)中有非常清楚的論述。他將人們(西方學界)對于音樂的認知歸為三個階段:1)the study of music in culture,即“音樂在文化中的研究”,顯而易見,此時音樂并不等于文化(音樂≠文化);進一步,2)the study of music as culture,也即開始將“音樂作為文化來研究”,換言之,可以視音樂為文化(音樂≈文化),但本質上依然不是;現在,3)music is culture,最終普遍認同“音樂即文化”,也就是說,音樂就是文化的一種表現,其自身就是文化(音樂=文化)。也因此,現在可以從西方學術研究中看到music不再是一個抽象的藝術審美詞語,而有了它的復數形式musics,以體現音樂的多樣性、復合性的文化屬性。
正是因為音樂的文化屬性,古今中外不同文化環境中的人們對于音樂的觀念是不同的。例如,與傳統的西方文化將音樂(泛指所有的音樂種類,但常附帶著價值判斷)作為單一概念不同,中東伊斯蘭文化對于音樂的觀念,分為兩類,并有專門的相應詞語。Musiqi一詞類似于西方文化的音樂概念,主要指代器樂,用于世俗社會環境,而不用于神圣音樂。Khandan意思為吟誦和歌唱,具有即興、神圣和嚴肅的風格。另一個例子來自美國音樂人類學家安東尼·西格的《蘇亞人為什么“歌唱”》。我在《音樂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音樂》中做過以下表述:蘇亞人的“歌唱”并不是我們概念中的歌唱,因為在蘇亞人語言中沒有相等于我們的音樂和歌唱這樣的詞匯。所以蘇亞人并不認為他們是在歌唱或從事音樂活動。那么,在我們聽來他們的確是在歌唱的“歌唱”是一種什么樣的東西呢?也就是說,這種“歌唱”對他們來說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呢?蘇亞的“歌唱”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內在的,另一是外部的。內在的意義體現在“歌唱”對血緣、家庭的維系,對生產、生活、生存的作用,對視覺形象的表達,對宗教膜拜的渲染。在這個意義上,“歌唱”不是音樂活動而是語言傳達,“歌唱”不是藝術形式而是心靈的表述。對音程、音階、音值、音節、音色、音響的規范在這里是沒有多少價值和意義的,真正的價值和意義在于他們必須“歌唱”,因為這是蘇亞人的生命。蘇亞人“歌唱”的外部意義是象征性的,是一種部落的符號,是我與你的對比,是自我存在的化身,是歷史傳承中牌坊式的東西,也類似于戰爭中號角式的作用,是一種社會化、政治化的意義。從現象上說,這種“內在”和“外部”的意義是功能性的,但是,本質上它們是觀念的產物。也就是為什么我們覺得蘇亞人歌唱的“歌唱”對于蘇亞自己來說卻不認為是歌唱的原因。④洛秦:《音樂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音樂》(新修訂版),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21年,第34;36頁。
音樂是一種文化普遍性現象。但由于每個社會和民族都根據其對自然、超自然、環境和社會的觀念,使用其文化自身的方式來理解和表達他們對世界的認知。因此,我們需要采用跨文化方式來理解不同文化語境的音樂屬性,特別要意識到,西方文化中的“音樂”概念及其詞語在別的社會文化中是很少能遇到與之相對應的。只有具有這樣的文化立場,我們才可能以客觀和恰當的學術方式來看待音樂的多樣性與復雜性。
(二)對中國音樂史中“音樂”的屬性及其觀念的探討
上述討論了一般意義,或者說是從宏觀角度探討了音樂的屬性及其觀念,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音樂”在中國古代的概念及其文化屬性。那么,什么是音樂呢?
對“什么是音樂”的解釋涉及的是音樂的形態問題,對“音樂是什么”的解釋關心的是音樂的本質問題。形態和本質是不能分隔開來的,這是因為本質—觀念的因素才形成了特定的形式,反過來,形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質。然而,無論從形式還是本質上來探討,“什么是音樂、音樂是什么”的解答沒有標準答案,它是因文化不同、社會屬性不同、人們的思想觀念的不同而異的。⑤洛秦:《音樂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音樂》(新修訂版),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21年,第34;36頁。
對此,中西古今存在很大的差異,中國的“樂、音、聲”與西方的“音樂”源自不同語境,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內涵。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西方教育體系中的“音樂”認知已經被普遍認同,即“音樂”是一種藝術及審美形式,而在中國古代則完全不同。先秦儒家音樂思想集大成者《禮記·樂記》中明確地論述了音樂的緣起:“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⑥劉德等編:《樂記·樂本篇》,載《中國歷代樂論·漢代卷》,王小盾審訂,洛秦主編,“漢代卷”編者鄧穩,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年,第93;98-99頁。也由此,它又有對于樂、音、聲三者不同屬性的歸類:“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于禮矣。”⑦劉德等編:《樂記·樂本篇》,載《中國歷代樂論·漢代卷》,王小盾審訂,洛秦主編,“漢代卷”編者鄧穩,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年,第93;98-99頁。
王小盾先生對此有如下解釋:
《禮記·樂記》認為:“樂”是不同于“音”和“聲”的。“樂”指配合樂器或儀式的音樂,亦即通于倫理的君子之樂;“音”指成章曲的音樂,亦即通于心識的眾庶之樂;“聲”指不成曲調的音響,亦即噪聲或僅作用于感官的禽獸之樂。這三者有倫理上的不同。這種三分的觀念,幾千年來,已經深入人心,成為音樂分類的基本綱領。比如古代目錄學家便把音樂典籍解散,分別歸入經部、集部和子部,亦即把經部當作“樂”的部類,把集部當作“音”的部類,把子部當作“聲”的部類。而在批評家那里,“樂”通常代指祭祀音樂或雅正之樂,“音”通常代指宮廷燕樂或一般意義上的音樂,“聲”通常代指民間情歌或繁雜淫穢的音樂。比如所謂“靡靡之音”“鄭衛之聲”,盡管都含貶義,但它們分別指的是兩個倫理層級的音樂:前者指已經進入宮廷的粗鄙之聲,后者則指仍處于鄉野的粗鄙之聲。⑧王小盾:《中國音樂學史上的“樂”“音”“聲”三分》,載《隋唐音樂及其周邊—王小盾音樂學術文集》,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2年,第15-31頁。
從《樂記》的記載以及上述引文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對于“音樂”的表述是一種結構性的認知。但也要理解,在不少古代樂論使用“樂、音、聲”詞語的表述時,并非完全絕對地對應上述層級,例如 “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⑨《隋書》卷一五《音樂志》中“牛弘議樂”,載《中國歷代樂論·隋唐五代卷》,王小盾審訂,洛秦主編,“隋唐五代卷”編者孫曉輝、王皓,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年,第19頁。的“音”似乎應為“樂”,再者“鄭、衛之音者,奸聲以亂”⑩《隋書》卷一五《音樂志》中何妥“定樂舞表”,載《中國歷代樂論·隋唐五代卷》,王小盾審訂,洛秦主編,“隋唐五代卷”編者孫曉輝、王皓,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年,第33頁。的“音”似乎應為“聲”更符合“三分理論”的倫理層級。然而,從總體而論,筆者贊同王小盾先生的觀點,他認為“可以說,‘樂’‘音’‘聲’三分理論是中國音樂學最重要的理論—它顯示了中國古代音樂事物的基本關系?同注⑧。”。它們充分體現了“音樂”的概念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所指向的倫理和社會功能的特質。
相比之下,無論是西方社會,或是上述中東伊朗或南美蘇亞人,中國古代“音樂”的概念更為多重和復雜。我們看到樂、音、聲三個詞所涉及的是文化意義的概念,而非音樂表現的具體形態,它們是一種階級地位的分類、存在空間的差異、文化功能的區分、社會結構的分層,以及國家意志的規范。雖然類似于伊斯蘭教音樂詞語的musiqi與khandan的類型差別,但“樂、音、聲”更體現出皇權制度下的社會倫理層級的特性。對于具體的音樂形態,中國古人則有另一套相當精細的表述,例如以“律、調、腔、曲”來為不同聲音、音與音的關系、聲音表達方式和風格的界定,出現頻率最多的相對應詞語有“律呂”“宮調”“聲腔”“曲唱”等。
盡管如此,中國古代音樂史仍是被公認的“啞巴”音樂史。所謂“啞巴音樂史”的含義就是沒有音樂,或者說那些被寫入音樂史的“音樂”并非音樂。那么,“音樂”在這里意味著什么呢?
如果“啞巴音樂”的認定是因為西方音樂觀念中的樂譜缺失,那是對于中國古代音樂的無知和寡聞。著名的紐姆譜是歐洲早期用于記錄圣詠歌唱的一種記譜方式,大約形成于9世紀,于10世紀發展出四線譜,約12世紀逐漸出現了標記音符時間長短的方法。就是幾乎在同樣的時期,中國古代已經具有敦煌琵琶譜、古琴減字譜,以及姜夔在其《白石道人歌曲》中使用的俗字譜。因此,同時期的中西記譜功能相差無幾。
如果“啞巴音樂”的認定也是因為西方音樂觀念中的歌唱性匱乏,那也是對于中國古代音樂的偏見,甚至是蒙昧。10—13世紀的宋詞不僅是中國文學的偉大成就,同樣也更是音樂的輝煌成果。詞樂可以曲唱而成為三百年宋代社會的普遍現象,“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便是宋詞歌唱的一個縮影,而相比之下,同時期的西方圣詠僅限于教堂的演唱而已。
如果“啞巴音樂”的認定也是因為西方音樂觀念中的戲劇性不足,那是對于中國古代音樂的極大蔑視,甚至更是愚昧。綜合性音樂戲劇理念在西方音樂中的實踐是瓦格納的“樂劇”,瓦格納實現了其戲劇、詩歌、音樂三位一體的“樂劇”理想是在19世紀中葉,1859年完成了《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1876年上演了《尼伯龍根的指環》這兩部舉世聞名的歌劇。
然而,中國古代相似的舞臺綜合音樂戲劇形式就是被聯合國列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昆曲。昆曲發源于14世紀,在歷史上成為中國古典藝術集大成者,其核心為“以文化樂”,即以文詞作為聲調的基礎,以語言作為旋律的根本,以韻律作為節拍結構的核心而形成的音樂文化風格。音樂是建立在文辭語言的基礎上的,是“依字行腔”的。最典型的就是昆曲的唱。昆曲的音樂是地地道道、徹頭徹尾地按照語言的聲韻、文字的意思而來的。文辭的平上去入各有其“打譜”和演唱的規定。音樂完全依附于文字語言,這就是為什么很少有單獨的昆曲中的旋律成為器樂音樂的原因。因此,魏良輔在《曲律》中總結:“五音以四聲為主,四聲不得其宜,則五音廢矣。”昆曲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代之文藝”,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就是梁辰魚(伯龍),他將“依字行腔”的方式和“以文化樂”的理念實施到了舞臺,一出開天辟地的劇目《浣紗記》,使得魏良輔的新昆山腔“冷板凳”成為集念、打、做、唱為一體的綜合性舞臺藝術。昆曲建立了完整的舞臺表演體系,腳色制一直作用在今天的傳統戲劇舞臺上;昆曲發展了自身獨特的舞臺語言規范,它的唱腔道白的語音推動了中國音韻學趨于成熟;昆曲音樂創作是語言與音樂相輔相成的典范,又是音樂和詞文完美結合的樣板,從而形成了中國曲牌體音樂的特殊風格;昆曲的唱,更是以“水磨調”的演唱修養、“頭腹尾”的吐字技巧、魏良輔十八節《曲律》規范給后世的傳統戲曲和民族歌曲的演唱產生了巨大影響;昆曲的價值不僅在音樂,而且它的劇目中的不少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經典。?洛秦:《蘭苑芳鰲—中國昆曲六百年》“序言”,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9年,第2-3頁。
我們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今約翰·凱奇的《4'33''》定性為“劃時代”的偉大作品,因為其沒有任何“音樂形態”而被視為“大音希聲”的典范。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大音希聲”概念創建的中國古代音樂卻是“啞巴”呢?問題就在于標準及其觀念。不同文化產生各異的“音樂”觀念,由此而發展了不同屬性和樣式的“音樂”形態。古代中國文化強大的文字表意性、語言音韻性、文辭結構性決定了中國古代“音樂”主體的特征和形態,以及與文學的相輔相成關系。文字語言的聲音和文辭文體的格律框定了“音樂”曲唱聲腔的屬性。因此,此“音樂”非彼“音樂”,“啞巴音樂史”的說法是一種對中國古代音樂史的嚴重曲解。
古代被稱為“啞巴音樂史”的現象發生在近現代,那是因為1840年的“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倒了清王朝,1919年的“五四運動”開啟了“啟蒙”與“救亡”,隨著一系列的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改變,“音樂”的觀念及其屬性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其直接的“導火線”是“學堂樂歌”,大量反帝反封建的文辭套上了從日本借來的歐美旋律,新文化運動的“音樂”產物誕生了—“學堂樂歌”成為一種教育手段。因此,正如劉再生先生所述:“學堂樂歌的劃時代意義就在于它在中國傳統音樂和中國近現代音樂之間劃了一道涇渭分明的‘分界線’。”?劉再生:《中國音樂史簡明教程》,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6年,第120頁。這樣的定性被學界和社會普遍認同。也由此,這一道“分界線”從根本上顛覆了中國傳統和文化意義上的“音樂”屬性及其觀念。古代的“樂、音、聲”及其相應的“律、調、腔、曲”完全失去了“中國性”。當此“分界線”成為“中國性”終結的同時,它成為“西方性”音樂屬性及其觀念開始的起跑線。
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在此暫以大多學者采用的分期概念,即1949年前為“近代”,1949年至今為“現代”。關于“音樂史分期”下文將專門討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它的歷程。起步于對封建王朝音樂的批判到向西方音樂的學習,“新音樂”成為其主題和主體。由此,有學者認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就是“中國新音樂史”?劉靖之:《中國新音樂史論》(增訂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不論其內容包含了“藝術性”“救亡性”“革命性”,還是“人民性”“現代性”或“國家性”,“新音樂”的歷史就是一部作曲家及其作品的歷史。阿德勒的“歷史音樂學”的思想及其實施架構在“新音樂”理念下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正是“學堂樂歌”的這道“分界線”使得中國音樂史及其作為一個學科,將古代部分劃歸為“音樂”缺失的“啞巴音樂史”,而近現代部分則成為正宗的“音樂風格”的歷史。然而,如果讀者還記得或回到前文所述的“音樂的一般屬性及其在不同文化中的觀念”來審視,我們會發現,近現代史中音樂的屬性是不完整的,所體現的主要是西方音樂概念中的“藝術審美”價值,而古代史中的“音樂”倒是承載了較為豐滿且完整的一般屬性,而且更具有民族文化的特性。
二、中國音樂史學研究的“線”—斷代分期及學科“一統性”的探討
“學堂樂歌”所建筑的“分界線”,使得中國音樂史學的古代與近現代形成了“事實分居”的格局,同在中國語境中的音樂史學研究的內涵與外延驟然分裂。
(一)中國音樂史學研究中的“斷線”問題
在任何古代和近現代音樂史著作以及相關學科論題研究的文論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以下的差別:
以同樣的歸類方式來梳理近現代音樂史學研究的內容:1)史料與考證,2)思想與闡釋,3)人物與著作,4)作品與分析,5)機構與制度,6)事件與活動等;研究范疇主要為專業音樂、主流音樂或部分流行音樂等;研究方法以“歷史音樂學”為主導。
盡管筆者試圖以“統一”的分類方式來對照古代與近現代兩個部分,但只要了解這兩個時段的音樂史學內容的學者,會很清楚地知道二者不只是“體量”上的巨大差異,例如古代與近現代音樂史學的著述數量的懸殊不在一個等量級上,更主要的是它們各自研究的對象即“音樂”的內涵與外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正如戴嘉枋先生所指出:“中國近現代(當代)音樂史研究既然是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它就必然具有自身的本體性質。”?戴嘉枋:《中國近現代(當代)音樂史研究》,載楊燕迪主編:《音樂學新論—音樂學的學科領域與研究規范》,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5頁。在戴文中提及的“本體性質”,也就是音樂學界常言的對于音樂本身的研究,事實上所指的就是狹義的以專業音樂研究為主體的學科屬性。如果從“歷史音樂學”的角度來說,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非常接近主流西方音樂史學的“自律論”為基礎的“風格史”的學理方式,而非“他律論”的“音樂社會或文化史”的立場。
也因此,這就產生了整體學科在縱橫經緯上“分裂”與“斷層”而無法銜接的問題。如上所述,從筆者的角度來看,近現代時段的中國音樂史學,在“學堂樂歌”的“音樂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積極迎接“西學東駐”(早已經不再是“西學東漸”),而主動“瘦身”放棄了音樂在中國語境中的多重性和文化性。例如,古代末期的戲曲曲藝等傳統主流音樂到了近現代就不再被關注,更不用說地方性和族群性的音樂種類。為什么會產生如此“削足適履”的現象?20世紀中葉之前的西方音樂學理論與思想的影響應該是其根源。
在《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2001年)的“音樂學”條目中指出:
1955年美國音樂學會(AMS)委員會將音樂學定義為“一個知識領域,其對象是音樂藝術作為一種物理、心理、審美和文化現象的研究”。盡管作為“藝術”的音樂仍然是研究的中心,但最后的文化屬性賦予了音樂學宗旨相當大的范圍。?同注③。
顯而易見,與前文所述的21世紀的觀點即“音樂學的定位應該不僅是對于音樂本身的研究,而且更應該對于與之相關的社會和文化環境的關注”相比而言,20世紀中葉的音樂學立場雖然有了文化屬性,但視音樂為“藝術”仍然是其中心。因此,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作為學科領域建構之際(學界公認其誕生于1958年)就是以“藝術音樂”作為其內涵基礎的。由此而論,為適應這樣的“音樂學”標準和框架,其“削足適履”的狀態便就容易理解了。然而,被近現代音樂史學“遺忘”或“放棄”的中國傳統音樂由此而“分身”成為一門相當獨立的學科領域,而且茁壯成長、日益興盛,如今成為中國音樂學領域規模最大、輻射面廣泛的學科。無論從研究主題、教學內容、學科隊伍、學術地位,乃至社會影響等方面,都是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完全無法與之相媲美的。
對此問題,馮文慈先生早在21世紀初就已經呼吁“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教學:兩個傳統并存與古今銜接”?馮文慈:《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教學:兩個傳統并存與古今銜接問題》,《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第9頁。。陳聆群先生對于馮先生的觀點給予了積極的支持,而且提出將其作為“‘重寫音樂史’擇定正確的突破口”?陳聆群:《為“重寫音樂史”擇定正確的突破口—讀馮文慈先生提交中國音樂史學會福州年會文章有感》,《音樂藝術》,2002年,第4期,第59頁。。學界對此也有不同看法,例如居其宏先生認為,此種學科擴張將導致“視野過分闊大、包容過分龐雜、體態過分臃腫”“不大具有現實性和可操作性”?居其宏:《史觀檢視、范疇擴展與學科擴張—陳聆群、汪毓和兩篇文章讀后談“重寫音樂史”》,《中國音樂學》,2003年,第4期,第4頁。等問題。馮長春對于解決上述矛盾問題提出了“關鍵在于如何把握兩個傳統的‘平衡’分寸”的觀點,強調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可以“采取相應的簡化處理,著重于新舊傳統嬗變、交融與更迭的規律性和原理性論述,避免出現居其宏先生所謂‘體態過分臃腫’的學科面貌”。?馮長春:《艱難的突圍—“重寫音樂史”史學思潮的回顧與思考》,《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13年,第4期,第2頁。
研究數據用SPSS20.00軟件進行處理,計量資料用均數加減標準差(±s)進行表示,t值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我們能否進行這樣的反思:如果認同一門歷史學就是對于特定歷史階段所發生的所有事象進行整體研究的學科,那么從理論上講,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也就應該涵蓋對于近現代歷史上所有音樂事象的研究。應該沒有理由可以回避甚至放棄最具有中國文化屬性的傳統音樂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目前已經相當成熟的中國傳統音樂研究,其作為學科領域的屬性并沒有“史學傾向”,其以“律調譜器”的專題性、地域性、民族性,特別是“形態性”作為主體研究范式。“音樂史學”的方法與“傳統音樂研究”的理論并不在同一維度上,各自的屬性和宗旨完全不同。前者探討的是音樂現象在歷史語境及其演變或發展過程中的價值,而后者更關注的是音樂事象其本身的樣態、屬性及功能在當下的意義。因此,“傳統音樂的歷史性”成為“被遺忘的角落”流蕩在外、無人顧及。如果今天的“重寫音樂史”依然是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的重要視角,那么上述的反思也應該成為其“不得不說的話題”?“重寫音樂史”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等同于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的論題,該“命題”出自戴鵬海:《“重寫音樂史”:一個敏感而又不得不說的話題—從第一本國人編、海外版的抗戰歌曲集及其編者說起》,《音樂藝術》,2001年,第1期,第61-70頁。。
進一步說,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對于歷史音樂學“風格史”的訴求—無論自覺與否或承認與否,已經成為現實,不僅造成學科“文化屬性”?在此的“文化屬性”主要指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性,即文字與文辭、語言與言語、文學與戲劇及其思維方式。而思想或主義及意識形態在近現代音樂史上的主導作用,不在此“文化屬性”的范疇之內。的缺失,也更影響了自身論題研究的深入。因為諸如藝術歌曲的中國性、歌劇的中國化等討論都離不開深厚的中國文字與文辭、言語與語言、文學與戲劇及其傳統文化思維的緊密關系。
(二)中國音樂史學斷代分期及學科“一統性”的探討
從史學學科的完整性來說,古代、近現代或當代一直面臨各自“音樂史分期”的問題,對此音樂學界已有不少成果。例如2009年5月30—31日,由中國音樂學院與中國音樂史學會舉辦了“文化視野中的音樂歷史分期”研討會,首次對于“音樂史分期”舉行專題討論,眾多專家學者根據各自的專業領域,分別對古代或近現代(當代)音樂史分期各抒己見、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例如,對于古代史的分期,學者提出從政治史、文化史或社會史、禮樂歌舞演進史、五大時期說、六段說等等的各種思考。是年《音樂研究》第4期設專欄對大家的討論意見進行了刊載。此外,近年來還有不少相關的論文發表,在此不做一一贅述。但其中有一些專家的意見值得我們重視,例如關于中國近現代(當代)音樂史的分期問題,居其宏指出:
歷史研究和寫作必須忠實于歷史對象的真實面貌,必須將歷史對象置于它賴以生存發展的具體歷史環境之中,按照它的本來面貌進行歷史描述,這是史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因此,任何一種歷史分期方法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風格分期法”符合西方音樂史的實際,但套用到中國近現代當代音樂史的研究和寫作中來,顯然是張冠李戴的。?居其宏:《中國當代音樂史的歷史分期及其依據》,《當代音樂》,2015年,第1期,第4頁。
程興旺的文章《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分期的若干問題》中提出了他提倡的“分期”的學術立場與學理原則:
解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前提與依據多元性問題,主要在于:一方面鼓勵倡導學術爭鳴,寬容相待,真誠對話,以營造良好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氛圍,以形成真知灼見。另一方面,該階段前提與依據的多元性,應該注重自身作為一“元”的自相關性,合規律性和整體性,特別是支撐“這一種分期”的學理的深度探求。第三,解決多元性問題,應該積極推進實踐創新。?程興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分期的若干問題》,《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第79頁。
上述探討基本都是將古代或近現代音樂史分期作為單獨的歷史時期進行分別討論的。在此,筆者更關心的是中國音樂史學作為一個整體學科應該怎樣處理“一統性”的音樂分期問題。古今無法“接通”(項陽語)在中國音樂史學中成為大家心知肚明而鮮有觸碰的“灰色地帶”,也因為既已約定俗成“古今”兩個學科,而書寫“通史”者又寥寥無幾,故而操心者甚少。
從學界目前的分期方式來看,無論是從社會、朝代,還是音樂事件或形態,或再是音樂風格或題材或體裁,都很難用統一的分期標準進行“接通”。目前看到的“通史”性質的中國音樂史的古代部分按照朝代分期,而近現代部分按照專題或政治事件或風格分期,即按照通行“分期”的方式將“古今”兩部音樂史合而為一,事實上依然是互不相干的兩部音樂史。有學者提出一種方式,即保持傳統的按照朝代進行音樂分期,例如先秦……明、清、中華民國(1912—1949)、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分期原則上講,這是一種“統一”的學理方式,作為學科整體而言,可以作為一種選擇。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因為以“朝代”為分期原則,“音樂屬性”的歷史失去了自身的意義,依然是一種“政治主義”的思路。
眾所周知,西方音樂史的書寫,自1885年阿德勒建立的“音樂學體系”以來,無論是斷代的,還是通史的,大多都是音樂的“風格史”。阿德勒這位德國音樂學家明確指出:“風格史即音樂史。”?姚亞平:《風格史·斷代史·現代性·后現代—西方音樂歷史編撰學若干問題的討論》,《人民音樂》,2018年,第3期,第77頁。讀到姚亞平的文章《風格史·斷代史·現代性·后現代—西方音樂歷史編撰學若干問題的討論》,很受啟發。他在文中論述了由“所謂歷史的終結,只是指一種特定的歷史的終結”概念出發,提出了“另一種音樂的斷代史”設想:
“西方的音樂”(而非“西方音樂”)的歷史無疑將永續,對它的歷史的書寫也無疑將永續;專名斷代或許不再延續,但21世紀、22世紀、23世紀……的音樂歷史—“世紀斷代”的西方音樂史可以無限地永遠書寫下去。真正的未來音樂,告別了現代性,也就告別了宏大的社會內涵,告別了思想史,告別了意識形態、哲理和深刻,它真正返回了自身,漫長等待的“為音樂而音樂”的歷史承諾終將得到兌現。對于現代性,或許如鮑曼所說,它經歷了“一種失常的狀態,一段偏離目標的道路,一個現在應予以糾正的歷史錯誤”,在經歷一段偉大的精神遠征之后,音樂終于回家了,西方的音樂表現出與周圍的文化鄰居融合的意愿—它們過去本來是融合的;它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一段它許久以來都沒有經歷過的、或許已經有幾分陌生的歷史!?同注?,第83頁。
類似的“世紀斷代”的思考與實踐也已經出現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的分期討論和史著的撰寫之中。凌瑞蘭曾提出以“20世紀中國音樂史”替代“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凌瑞蘭:《音樂本體的歷史分期—論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歷史分期》,《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第73頁。的建議。事實上,居其宏先生于1992年就已以《20世紀中國音樂史》為標題出版了著作,明言的《20世紀中國音樂批評導論》也是“世紀斷代”的很好例證。因此,筆者設想,是否有可能將“世紀斷代”的思路用于整個中國音樂通史呢?例如:前21—前11世紀(夏商);前11—前3世紀(周);前3—3世紀(秦漢);3—6世紀(魏晉南北朝);6—10世紀(隋唐五代);10—13世紀(宋遼金);13—17世紀(元明);17—20世紀(清);20世紀(上半葉—中華民國;下半葉—中華人民共和國);21世紀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參見《現代漢語詞典》附錄《中國歷代紀元詳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這是一條最簡單的音樂史分期的“線”,也許是可行的方式,也比較容易與其他國家的音樂史或一般世界史“接軌”參照。
當下中國音樂史學的發展伴隨著學科內部的不斷細化、裂變與整合。中國音樂史學以研究古代為開端,逐漸分層出近現代,以及再細分為當代,這種學科分層有著深層次的學科布局與發展的內因,但如前所述,它們帶來了學科“一統性”的缺失。打通學科之間的溝壑,改變分層割裂的狀態,建立融合“一統的”中國音樂史學體系,應該是我們需要去研究與實踐的命題。
三、中國音樂史學研究的“面”—與相關各種學科領域的關系
學科既是知識體系的總結與創新,也是一種學術研究范疇的邊界規范。人們不斷發展與構建知識邊界,也不斷更新、消融與重構邊界,因而學科始終是變化與向前的。自20世紀以降,隨著西樂東漸,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音樂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得以確立,在百年歷程中,學科不斷分解、細化,產生了許多分支學科,同時又不斷綜合甚至整合,與其他人文學科之間互相貫通、互為支持,具有綜合性強、范圍廣泛、界限模糊的特征,也帶來學科的邊緣化趨向。也就是說,中國音樂史學的發展并非是孤立與封閉的,其在學科內部與外部都與諸多相關學科發生著分層、交叉與融合的關系,而這種關系的發生與探討推動著整個中國音樂史學的發展。
(一)從“面”上與相關各種學科領域的分層、交叉與融合
在研究內涵與外延的表象上,古代史領域與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的問題不同。雖然古代音樂史自身的內容具有豐富和濃郁的“文化屬性”,但作為一門學科領域,其誕生于20世紀初,也同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歷史音樂學”的影響。也許出于默認“啞巴音樂史”的“自卑感”,其研究視角大量投入于“音樂性”的鉆研和開發,樂律學、古譜學、樂器學是被認為最具“音樂性”的領域而受到高度重視,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樂、音、聲”多重復雜的“音樂”的文化性探索,這是一個方面。而另一方面,也由于古代音樂史研究需要較高的“專業性”和“技術性”,用現在流行的語言來說,學科“內卷化”嚴重,對于一般學界的社會人文學科的思想、思潮、研究范式和方法論較少關注,更沒有與時俱進。如果我們期待古代音樂史學的新面貌,那么在學科“一統性”理念下,打開藩籬而關注中國音樂史學與之相關學科關系分層、交叉、融合將成為新的動力,這就是本文所倡導的學科研究的多層“面”的論題。因此,可以圍繞以下問題展開思考。
一方面,作為歷史學與音樂學交叉學科的中國音樂史學,常年來與一般歷史學卻保持著相對疏離的關系。歷史學研究的斷代史、編年史、整體史乃至“人類學”轉向等研究思路,影響至音樂史研究甚為晚遲,而音樂研究的特殊性又促使音樂史學研究更強調音樂本體,更傾向囿于一隅,以相對封閉的姿態疏離于一般歷史學之外。因此,打通中國音樂史學與一般歷史學的學術溝壑,以更為宏觀的史學觀念引導學科發展,使得音樂史學研究走入一般歷史學,期待開啟更廣闊的人文社會學科的視野。
另一方面,中國音樂史學在發展過程中常出現與內部姊妹領域相互交疊、糾纏不清的局面。例如,“江南絲竹”被視為中國傳統音樂學科的研究對象,較少出現于音樂史學研究;“戲曲音樂”是明清音樂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同時卻更為一般戲曲史研究所關注;二胡大師“劉天華”常見于近現代音樂史研究,而“阿炳”則更多見于中國傳統音樂或音樂人類學(亦稱民族音樂學)的研究領域;等等。音樂“姊妹”學科屬性與邊界之間的纏繞重疊,在很大程度上“模糊”和“淡化”了人們已經習慣了的中國音樂史學特性。梳理中國音樂史學與姊妹學科之間的關系,有意識地與中國傳統音樂研究、音樂人類學、中國少數民族音樂、音樂分析學等學科領域形成交叉與融合,在不斷拓寬中國音樂史學研究的論域與視角的同時,也將形成一種“雙贏”的發展態勢。事實上,這也是在不斷拓展中國音樂史學的學科范疇,期待最終實現真正的整體音樂事象研究的中國音樂史學。
中國音樂史學科內部也逐漸形成分支化趨勢,諸如出現音樂考古學、音樂文獻學、樂律學、音樂美學史、古譜學等,而且某些分支學科又再次細化,諸如樂律學分支為樂學與律學,音樂考古學中延伸出音樂圖像學,樂器學中發展出音樂工藝學、樂器形態學、樂器文化學等。這些分支學科的不斷出現,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中國音樂史學的不斷完善。因此,需要梳理清楚中國音樂史學學科內部的分解與整合,進一步探尋和挖掘中國音樂史學的內在動力。
(二)相關問題的嘗試性探討
圍繞學科面對的各種問題與論題以及思考,筆者組織了一批年輕學者進行嘗試性的具體研究,讀者將看到我們團隊的部分研究成果。諸如,伍維曦的文章《中國音樂史學與現代學術思維》,試圖將中國音樂史學置入20世紀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的背景中,對現代學術思維的一些與音樂史學有密切關系的特征進行總結與闡釋,從而對中國音樂史學這一學術系統及觀念結構的語境生態加以勾勒渲染,力求為這一學科的學術史研究描述出一個較為廣闊而生動的精神場域。康瑞軍的文章《當代中國語境中的“音樂新史學”理念與實踐》指出,隨著學科間交流交叉的深入,中國音樂史學視野愈益開闊,對“新音樂學”“新文科”“新史學”以及音樂人類學等多學科思潮,展示出勝過以往的積極反應。“音樂新史學”的正面提出和實踐,是其顯著特征之一,目前已形成了一批成功融通“文化視野”與“技術分析”的新成果。文章通過對20世紀中國音樂史學在理論、方法和實踐等方面進展情況的分析,探討這一理念產生的語境脈絡,在此基礎上,揭示其當下學術實踐的學科意義和未來可能。胡斌與孫焱的研究《互鑒共贏 殊途同歸—從“學術史”視角看中國音樂史學與中國傳統音樂研究、Ethnomusicology的學科關系》認為,隨著各學科研究的深入開展以及西方學科在中國“本土化”進程的加快,“古今”“中西”等多重學術語境對中國音樂史學科研究的影響也越發明顯。中國音樂史學、中國傳統音樂研究及音樂人類學雖然在現行學科劃分中各有其位,但在實際研究與專業人才培養過程中卻又相互影響。研究對象的部分重疊、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鑒、研究學者的多重身份等特征漸漸貫穿三個學科的發展,不僅在研究范式上形成了新的交叉整合,而且共同促進了中國音樂學術研究思維與視野的拓展與深化。黃藝鷗的文章《論中國音樂史學的領域劃分、疏離與整合》從縱橫兩個方面來探討了中國音樂史學的領域劃分、疏離與整合問題,梳理中國音樂史學及其分支學科/研究領域交疊纏繞的學科關系及相互影響,從而探尋中國音樂史學科發展的內在動力、困境與機遇。一方面,由歷史分期而引發的學科分層、分段與斷代,體現出中國音樂史學歷史進程的動態發展趨向;另一方面,多重互證性建構下的學科細化、交叉與整合,既是中國音樂史學科內部驅動也是多學科、跨學科對話與融合的體現。分支學科領域的逐步成熟與細化推動著中國音樂史學的不斷演進與日臻完善。然而,學科的分段分層以及學科分化所帶來的碎片化現象也在無形中筑起了學術藩籬并形成了強烈的研究隔閡,成為我們當下需要面對的音樂史學挑戰之一。
簡短的結語
其他相關的研究尚在努力中,筆者希望能夠通過中國音樂史學在現代學術思維層面上的“問題意識”“歷史意識”和“范式意識”的討論中,期待與學界共同努力,在相同、相通或相近的學理層面,以及被廣泛認同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上,對本文所提出的論題,即中國音樂史學研究中的“點—線—面”問題不斷深入討論與反思,推動中國音樂史學的成熟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