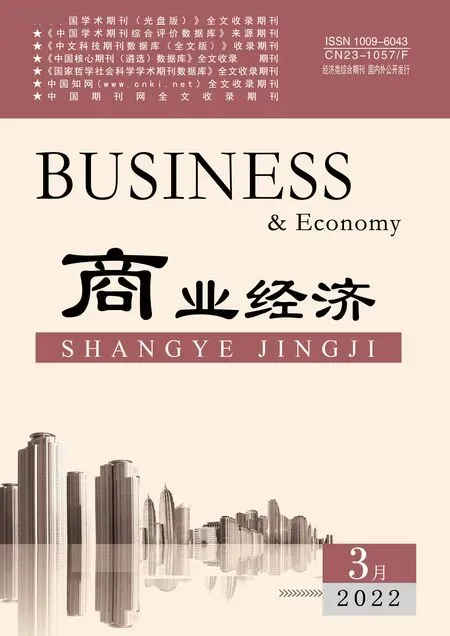人類社會的組織難題與管理的使命
楊立宇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北京 102488)
一、引言
研究表明人類社會自公元1800 年左右至今200 多年的時間創造了人類幾百萬年以來97%的財富,那是什么力量推動人類文明在近現代短短200 多年里突飛猛進?西方經濟學認為分工、市場經濟與科技主導了人類社會的這種突飛猛進,也就是自公元1776 年開始的工業文明引領人類社會進入了快速發展軌道。事實果真如此嗎?西方經濟學所論證的分工、市場經濟與科技對于效率提升的作用是自動產生的嗎?人類社會進入工業文明以后社會形態發生了什么變化?這種變化是為分工、市場經濟與科技提供了施展作用的舞臺,還是催生了新問題?
本文從理論上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回答,論證了人類社會自1776 年進入工業文明的同時,也宣告社會形態演進為組織型社會。正是組織型社會為分工、市場經濟與科技提供了發揮作用的舞臺,同時人類社會也不可避免地面臨新問題,即組織難題。經濟學為此無法提供解決方案,這個重任交給了管理學。所以,本文也試圖就此進行研究,并回答管理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二、組織型社會的誕生
斯坦福歷史學和人類學家伊恩.莫里斯在研究人類文明發展史的過程中,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從攝取能量的能力、社會組織能力、信息技術能力、以及戰爭動員能力等四個維度構建了“人類發展指數”,對人類5 萬多年的文明史進行了考察。在縱軸為“人類發展指數”,橫軸為“時間”的坐標系中,“人類發展指數”曲線在公元1800 年之前幾乎就是一條水平直線,表明在公元1800 年之前的幾萬年間,人類文明的進步極其緩慢。而公元1800 年之后,“人類發展指數”呈現垂直上升態勢,表明人類文明快速而明顯的進步發生在1800 年之后短短的200 多年間。
美國伯克利大學經濟學家德隆從人均GDP 的角度考察人類的歷史進程。他發現,人類從舊石器時代到公元2000 年的250 萬年間,用了99.4%的時間,到15000 年前,世界人均GDP 達到90 國際元。隨后,到公元1750 年,世界人均GDP 達到180 國際元。從1750 年到2000 年,即在人類歷史0.01%的時間內,人均GDP 達到6600 國際元,增長了大約37 倍。如果在坐標系中畫出德隆的研究結論,可以看到,從250 萬年前至今,公元1750 年之前的世界人均GDP 基本是一條水平線,但從1750 年開始的短短250 年間,突然有了一個幾乎是垂直上升的增長。
伊恩.莫里斯和德隆兩位學者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用一句話來講就是,人類社會僅僅在公元1800 年左右至今的200 多年時間里,貢獻并積累了97%的人類財富和發展能力。
根據伊恩.莫里斯的研究,1776 年可能是人類文明進程中里程碑式的時間節點。在那一年,發生了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兩件大事:一是亞當.斯密在英國出版了《國富論》;二是瓦特在伯明翰宣告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臺蒸汽機。
《國富論》的出版,論證了分工和市場經濟的效率與作用,由此人類社會進入了市場經濟起主導作用的時代。蒸汽機的成功發明和使用,讓人類社會看到了科技的力量,以機器驅動的大規模生產方式從此成為主流。
那是不是可以認為分工、市場經濟與科技是推動人類社會在公元1800 之后短短的200 多年里創造奇跡的主要力量呢?
誠然,如果沒有分工、市場經濟與科技,很難想象人類社會的文明程度、財富和能力會發展到怎樣的水平?但是,如果我們深入研究分工、市場經濟與科技所根植的人類社會本身所發生的形態上的變化,就會發現,人類社會形態的演變才是推動公元1800 年以來人類社會產生天翻地覆變化的最根本的力量。
從舊石器時代到公元21 世紀,人類文明經歷了大約250 萬年的進化,可以劃分為狩獵文明、農耕文明和工業文明三個社會形態迥異的階段。狩獵文明的社會形態以個人、部落為主,農耕文明的社會形態以個人、家庭、族群為主,而工業文明與之前的兩個文明完全不同,整個社會的基石不再以個人、部落、家庭和族群為主,而是以組織為主,每一個個體只有加入組織,才能獲得生存與發展,個人價值的實現、財富的擁有、名譽和社會地位的獲得也都要依賴于組織。
德魯克稱組織型社會為功能型社會。正是組織型社會的誕生,才提供了驗證分工、市場經濟、科技是否有效的沃土。換言之,沒有社會形態向組織型社會的進化,人類文明的進程將大大延緩,也看不到公元1800 年之后200 多年創造了人類社會97%的財富這一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就。
三、人類社會面臨的組織難題
按照巴納德的定義,組織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按照共同目標展開協同的行為關系。
人類進化到工業文明,邁入組織型社會后,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既取決于組織內部運行的效率,也取決于組織間的合作效率。那么在分工、市場經濟背景下,組織內部和組織間的效率能否自動產生?科技又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證了分工有助于效率的提升,但并沒有論述分工是組織效率提升的必要條件,還是充分條件。
產生分工的條件首先是人要能夠集聚在一起,當人集聚在一起,形成集合時,組織就誕生了,進而在組織內部就有了分工的基礎。問題是人們為什么愿意集聚在一起?集聚在一起后分工是自動產生的嗎?有了分工之后效率是自動提升的嗎?這些問題經濟學并不能給出正確解讀,原因就是經濟學把人的“本性”剝離了,僅僅留下抽象的理性的人。
當我們還原人的本性,人便不再是理性的經濟人,而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各種需要的社會人。這些抱著不同欲望的社會人,聚集在同一個組織內部,并按照分工的法則組織起來,如果沒有協同,分工的效率并不會產生。有著不同欲望的人,各自的目標和利益訴求也不同,如果不能夠在他們之間建立共同的目標,并讓其擁有協同的意愿,真正意義上的協同根本不會產生。沒有協同,分工又何來效率?這便是人類社會面臨的第一個組織難題:組織內部分工之后的協同難題。
組織型社會是由一個個不同的組織構成,分工不僅產生于組織內部,也產生于組織之間。按照西方經濟學的邏輯,基于市場經濟的供求法則完成組織間的分工,形成了全社會各類產業鏈、供應鏈、以及各種非上下游的供求關系。
這種基于市場經濟的供求法則所形成的組織間分工,從學理上而言是具有效率的,資源在全社會絕大部分時候能夠實現優化配置。不過,市場失靈、壟斷、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經濟周期性波動、貧富差距過大等市場經濟的附屬產品卻給人類社會帶來傷害,也極大限制了社會整體效率的提升,同時也很難為人類社會提供一個基于長期主義的發展導向。因此,人類社會面臨的第二個組織難題是:市場經濟的非效率難題。
四、破解人類社會組織難題的立論基礎
人類社會組織形態和制度的演化,都是朝著有利于人的集聚、有利于分工方向發展的。從家庭作坊、手工作坊,到工廠,再到公司,不僅組織形態發生了變化,更重要的是組織規模和人數越來越大,同時人和資本的來源也徹底社會化。隨著組織規模和人數增大,分工更容易在組織內部實行,程度也不斷加深。人和資本來源社會化以后,組織的經營與擴張能力也隨之增強。所有這些變化都提升了組織的效率。
但是,人類社會面臨著兩種組織難題,一種是組織內分工之后的協同難題,另一種是市場經濟的非效率難題。不管是組織內的協同難題,還是市場經濟的非效率難題,都不能依靠分工、市場經濟、科技的力量來解決。組織內協同難題涉及人的協同意愿和組織目標的認同,必須從完整的人性角度去解決這個難題,而分工、市場經濟以及科技不關注人性,無法解決人的心理和思想層面的問題。市場經濟的非效率難題本身就是市場經濟的附屬產品,依靠分工和市場的力量無法解決,科技只是技術手段,對此也無能為力。
市場經濟、分工與科技為效率而生,但是其本身并不能破解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兩種組織難題,因而在難題沒有被破解之前,組織的效率和社會的秩序并不會如期而至,人類需要尋找破解難題的立論基礎。
組織內的難題是分工之后如何協同。西方經濟學的邏輯是,在市場經濟背景下,所有的價值創造活動依據市場信號展開,在市場信號指引下,組織內部按照價值創造流程進行分工。組織內部的這種分工并不像組織間分工那樣,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由供求關系主導,而是由資本主導。資本雇傭勞動,將具備不同技能的人集聚在同一組織中,依照組織外部的市場信號,完成價值創造活動的選擇,并依據價值創造流程進行分工。但是,如果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協同過程,由西方經濟學所定義、資本期待的效率并不會出現。原因就在于,資本雖然雇傭勞動者,但是勞動力的支配權卻仍然掌握在勞動者手中,知識型勞動者更是掌握著自己勞動的絕對支配權。
既然西方經濟學理論解決不了組織內部的協同難題,解決難題的重任自然就交給了管理學。管理學家西蒙在1947 年發表的《管理行為:管理組織中決策過程的研究》一文中認為,決策關鍵在于價值立場或者價值前提。西蒙的觀點為我們找到了解決組織內部協同難題的根本所在。
激發組織內部人們協同意愿的關鍵是,將現有公司制形態下資本為大、股東利益為大的價值觀和價值前提,轉變為價值共創、價值共享的價值觀,從而讓組織內部的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管理者、員工,擁有相同的價值立場和價值前提,能夠共創、共享價值成果,才能真正激發人們的協同意愿和認同組織的共同目標。因此,破解組織內部協同難題的立論基礎是在組織內部建立共同的價值立場和價值前提,這也是管理學家西蒙所主張的。
人類社會面臨的第二個組織難題來自于市場經濟的非效率。本質上市場經濟是一種利己的經濟,在追求私利的過程中,形成了基于社會整體分工下的供求關系網。只要人追求私利的本性不改變,市場經濟就是到目前為止最有效率的一種經濟模式。但是有效率的市場經濟也會帶來很多對社會有害的副產品,比如壟斷、市場失靈、經濟周期性波動、貧富差距拉大、以及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等等。不管基于分工的市場經濟本身多么富有效率,帶來這么多對社會有害的副產品,是需要從根本上加以解決,否則經過非效率對沖后,社會整體是得不到改善的。
市場經濟本身沒有解決這個難題的辦法,科技也做不到。如果把國家視為一個大的組織,在國家這個框架內解決這個難題,就要在國家層面建立全社會的共同價值立場和價值前提,這也是解決市場經濟非效率難題的立論基礎。
五、管理的使命:構建命運共同體型組織
人類社會面臨兩種組織難題:一是組織內部的協同難題,二是市場經濟的非效率難題。破解這兩種難題的立論基礎是建立共同的價值立場和價值前提,只不過一個是在組織內部建立,另一個是在全社會建立。
經濟學、科技無法承擔建立共同價值立場和價值前提的任務,這個任務只能交給“管理”來做。所以,管理是人類社會轉型為組織型社會后才誕生的,幫助人類社會解決組織難題是其根本任務。
圍繞提升組織運行效率、達成組織效果目標,管理學展開了長達100 多年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對于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遺憾的是,迄今為止,管理學理論并沒有真正意義上找到解決組織內部的協同難題的辦法,人類社會賦予其的根本任務也沒有徹底完成。
組織內部的協同之所以難解決,根本的原因是現代公司制這種組織形態本質上是以資本為中心的。在資本雇傭勞動,股東大會、董事會成為公司制企業最高權力機關的背景下,股東利益最大化既是西方經濟學所倡導的,也是公司制企業的現實必然選擇。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實現途徑只能依賴公司為社會創造價值,而資本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小,資本所雇傭的人所起的作用反而越來越大,在知識經濟時代,人是能夠創造價值的最重要來源。在公司制企業中,如果價值分配不是依據價值創造和貢獻大小,而是依據資本,那么,矛盾就會產生,會抑制人們創造價值和協同的意愿。
解決這個難題的關鍵是構建命運共同體型組織。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基于資本為紐帶的組織是一種虛幻的共同體,因為資本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是存在矛盾的。當資本對價值創造的貢獻越來越小,而知識、技術對價值創造的貢獻越來越大的時候,以資本為核心的虛幻共同體就會成為組織提升效率、發展壯大的阻力,命運共同體型組織就有了產生和存在的客觀必然性。
構建命運共同體型組織的落腳點在于科學處理好資本、知識、技術、勞動之間的關系,實質是處理好這些要素的所有者之間的關系。以價值創造、價值共享為基本原則,將資本、知識、技術、勞動連接在一起,人與人之間是同呼吸共命運的關系。打破資本在管理、決策、用人、分配上的支配地位,在價值創造、評價和分配上堅持以奮斗者為本。重新設計治理結構和管理系統,以貢獻、能力、道德為衡量標準來選人、用人和育人。不是依據資本多少、裙帶和親疏關系,而是將有能力、有貢獻、有道德的人選拔安排到管理系統,賦予其充分的決策權。資本仍然對組織擁有法律上的所有權,但是治理結構要做出根本性的調整。組織要逐步發展成為全員持股型組織,外部單一個人或者法人不能成為第一大股東,員工持股委員會代持員工股份,成為事實上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至少不低于51%,內部前4 大個人股東股份之和不能超過25%,外部股東擁有分紅權、沒有投票權。真正建立命運共同體型組織需要大股東在股份占比上做出犧牲,通過不斷稀釋股份,來提高員工整體持股占比。華為公司是命運共同體型組織的典范,創始人任正非先生所持股份占比已經被稀釋到只有1.4%,真正實現了全員持股,真正做到了價值共創和共享。
解決市場經濟的非效率是人類社會面臨的第二個組織難題。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無法解決自身非效率問題,只能交給看得見的手來解決,也就是交給國家,通過政府管理來解決。國家在解決市場經濟非效率問題的時候,必須超越各種利益集團狹隘的利益,從全社會共同利益角度去做決策。如果把國家視為一個更大的組織,那么站在全社會共同利益角度去解決市場經濟非效率問題,實際上就要求建立一個命運共同體型國家。如果做不到這點,國家在解決市場經濟非效率問題的時候,一定會有所傾向和偏袒,最終市場經濟的非效率問題也得不到解決。這方面的典范就是中國,相對于西方國家而言,中國政府能夠從全社會共同利益角度去解決市場經濟的非效率問題,而不是偏向于利益集團。所以,中國比西方社會更好的解決了這個問題,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也更快、更平穩。
六、結論
1776 年亞當.斯密在英國發表了經濟學開山之作《國富論》,論證了分工和市場經濟的高效率;同一年,瓦特在英國伯明翰宣告發明成功蒸汽機,機器替代人力由此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也讓我們看到了科技的力量。
分工、市場經濟與科技成為推動人類進入工業文明的主導力。但是,我們不能忽略的一個重要事實是,進入工業文明也意味著人類轉型為一個以組織為細胞的社會,組織型社會從此誕生。不可否認組織型社會為分工、市場經濟與科技發揮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作用提供了舞臺,但是組織型社會天然存在兩個組織難題,一個是組織內部的協同難題,另一個是市場經濟的非效率難題。
組織內部如果不能協同好,不僅不能享受分工和市場經濟帶來的高效率,而且不同利益訴求的主體會產生矛盾、沖突,阻礙組織進步與發展,最終延緩人類文明演化。如何才能讓有不同利益訴求的人們在同一組織內部很好的協同起來呢?經濟學與科技無力提供解決方案,這個重任就交給了管理學。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按照西蒙所講的讓組織內部的人們有統一的價值立場和價值前提,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命運共同體型組織。但是實現它并非易事,尤其在現代公司制的治理模式下,需要大股東稀釋股份,并提高全體內部員工的持股比例,發展成為全員持股型組織。
對于市場經濟非效率問題的解決需要從國家層面尋找辦法,并且國家政府不能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而應該超越各個利益集團,從全體人民的利益、從社會的公共利益角度,運用看得見的手,也就是管理之手去調控市場經濟,解決市場經濟的非效率問題。所以,要做到這一點,唯有建立命運共同體型國家,才可以從根本上解決。
建立命運共同體型組織和命運共同體型國家是解決人類社會組織難題的根本辦法,是管理的使命。雖然,華為為我們提供了建立命運共同體型組織的樣本,中國也為全人類提供了建立命運共同體型國家的范本。但是,從整個人類社會來看,我們并沒有很好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盡管在近現代短短200 多年里,人類文明取得了令人嘆為觀止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認,這還遠遠沒有達到其應該達到的高度。未來,我們還應該繼續探索如何建立命運共同體型組織和命運共同體型國家,為人類文明的持續繁榮保駕護航,這是管理永遠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