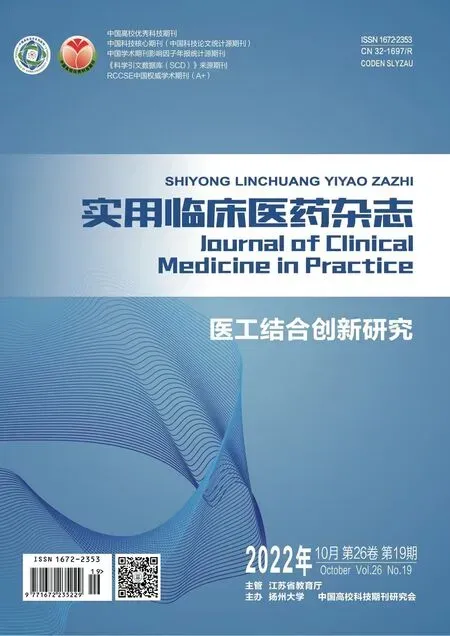血清低氧誘導因子-1α、甲胎蛋白表達對肝癌患者肝動脈化療栓塞術預后的影響
殷夢杰, 戴 鋒, 王 斌, 王曉維, 沈建東, 丁 葦, 付守忠
(江蘇省南通市第三人民醫院 介入血管科, 江蘇 南通, 226000)
肝動脈化療栓塞術(TACE)是中晚期肝癌患者的首選治療方式,可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率。但部分肝癌患者經TACE治療后仍難以獲得完全緩解或部分緩解,預后不良風險較高[1]。因此,尋找影響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不良的相關指標,對治療方案的制訂與調整尤為必要。作為氧平衡調節的重要因子,低氧誘導因子-1α(HIF-1α)影響腫瘤基因及細胞的合成、表達,對腫瘤的復發、轉移起重要作用[2]。HIF-1α可通過誘導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基因轉錄,增加VEGFmRNA穩定性,上調VEGF及其受體表達,影響癌細胞及內皮細胞,促進血管生成,導致腫瘤細胞的增殖[3]。甲胎蛋白(AFP)是一種糖蛋白,且是臨床應用較為廣泛的標志物,肝癌患者接受合理的治療后,血清AFP水平降低[4]。有研究[5]將AFP用于肝癌的診斷且獲益。由此猜測,血清HIF-1α、AFP的異常表達可能對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造成一定影響。本研究重點觀察血清HIF-1α、AFP水平對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的影響,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9年1月—2021年12月南通市第三人民醫院行TACE術治療的80例肝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 符合《原發性肝癌診療規范(2017年版)》[6]關于肝癌的診斷標準者; 肝功能Child分級[7]為A~B級者; 首次接受TACE治療者; 卡氏(KPS)評分[8]≥60分者。排除標準:合并其他部位惡性腫瘤者; 接受其他抗腫瘤治療者; 嚴重肝硬化者; 凝血功能異常者; 嚴重腎功能不全者; 大量腹水者。80例肝癌患者中男60例,女20例; 年齡45~72歲,平均(56.06±5.25)歲; Child分級為A級49例, B級31例; 單發45例,多發35例。患者及家屬均知曉本研究方案,并簽署知情同意書。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已審核本研究方案,并批準實施。
1.2 方法
預后評估方法: 全部患者均治療2個周期,并于治療結束后接受至少1個月隨訪,參照實體瘤療效評價標準[9]評估所有患者的預后情況。完全緩解:可測病灶完全消失,全部病理淋巴結短直徑必須減少至<10 mm, 且維持4周以上;部分緩解:可測病灶的直徑之和比基線水平減少≥30%, 且維持4周以上;進展:以所有可測病灶直徑之和的最小值作為參照,直徑之和相對增加≥20%, 且滿足直徑之和的絕對值增加≥5 mm, 或出現新病灶;穩定:可測病灶減小的程度未達到部分緩解,增加的程度也未達到進展。將部分緩解、完全緩解患者作為預后良好患者,納入良好組(n=46), 其他則納入不良組(n=34)。
基線資料統計方法: 設計基線資料調查表,詳細統計2組基線資料。① 一般資料: 性別、年齡、Child分級(A級、B級,將患者的一般狀況、血清白蛋白、腹水、膽紅素、凝血酶原時間分為3個層次,分別計1、2、3分,其中A級為5~6分,B級為7~9分)、腫瘤數目(單發、多發)、最大腫瘤直徑、腫瘤部位(左半肝、右半肝及左、右半肝)、肝硬化病史(有、無,通過查閱患者病歷資料判斷); ② 實驗室指標檢查: 治療前,取患者的空腹肘靜脈血3 mL, 以3 000轉/min離心10 min, 分離上層血清,采用日立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測定谷草轉氨酶(AST)、谷丙轉氨酶(ALT)、總膽紅素水平,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測定血清AFP、HIF-1α水平。
1.3 統計學分析

2 結 果
2.1 預后情況
80例肝癌患者經TACE治療2個周期且隨訪1個月時,完全緩解10例,部分緩解36例,穩定27例,進展7例。預后良好46例,占比57.50%, 預后不良34例,占比42.50%。
2.2 不良組與良好組基線資料比較
不良組血清AFP、HIF-1α水平高于良好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組間性別、年齡、Child分級、腫瘤數目、最大腫瘤直徑、肝硬化病史、腫瘤部位、AST、ALT、總膽紅素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3 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影響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將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情況作為因變量(1=不良, 0=良好),將2.2基線資料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作為自變量,逐個納入進行單項Logistics回歸分析,后將P條件放寬至<0.2, 納入符合條件的變量(AFP、HIF-1α)作為自變量(均為連續變量),建立多元回歸模型,結果顯示,治療前血清AFP、HIF-1α高表達可能是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不良的風險因子(OR>1,P<0.05)。見表2。

表1 不良組與良好組基線資料比較

表2 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影響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2.4 血清AFP、HIF-1α水平評估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不良風險
將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情況作為狀態變量(1=不良, 0=良好),將治療前血清AFP、HIF-1α水平作為檢驗變量,繪制ROC曲線,結果顯示,治療前血清AFP、HIF-1α水平預測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不良風險的AUC均>0.70, 預測價值較為理想,且以聯合預測價值最高。見圖1、表3。
3 討 論
TACE可通過減少、阻斷腫瘤血供,導致腫瘤缺血、缺氧壞死達到治療目的,可有效延長肝癌患者生存時間。但有研究[10]指出,肝癌患者在接受TACE治療后的1、2、3年生存率分別為61.3%、44.2%、40.5%。本研究結果顯示, 80例肝癌患者經TACE治療2個周期且隨訪1個月時預后不良34例,占比42.50%, 說明肝癌患者接受TACE治療后仍有較高的預后不良風險。因此,尋找影響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不良的相關指標十分必要。

AFP屬于糖蛋白,由肝臟實質細胞合成,在健康人體內含量極低,但當肝細胞發生癌變時, AFP蛋白功能會恢復,且隨著病情的加重AFP表達增加[11]。研究[12]指出, AFP可反映腫瘤內在的負荷及活性大小,可用于評估治療效果,當肝癌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療后, AFP水平迅速降低。同時,有研究[13]指出, AFP可用于原發性肝癌的診斷,且診斷效能較好。HIF-1α作為調節細胞內氧代謝的關鍵因子之一,可通過誘導VEGF, 對新生血管進行刺激,促進腫瘤的生長[14]。研究[15]發現,惡性腫瘤患者因組織氧濃度降低,可引起HIF-1α的表達增高。同時,有研究[16]指出, HIF-1α的釋放,可誘導VEGF的表達,促進癌組織生長、浸潤及轉移。由此,猜測血清AFP、HIF-1α的異常表達可能對肝癌患者TACE預后造成一定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不良組血清AFP、HIF-1α水平均高于良好組。初步說明血清AFP、HIF-1α的異常高表達可能與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不良有關。簡單分析可能的原因: AFP作為診斷肝癌的特異性標志物,其高表達提示臨床高分期,腫瘤侵襲性高,可能存在血管侵犯及腫瘤高負荷,直接對TACE治療效果造成影響,增加患者預后不良風險[17]; 此外, 高表達AFP可作用于免疫系統,協助腫瘤逃逸免疫功能,促進癌細胞增殖,因此AFP高表達可促進腫瘤的侵襲、增殖及轉移,增加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不良風險[18]。研究[19]報道稱腫瘤生長依賴于新生血管生成, VEGF有自分泌功能,可刺激癌細胞增殖,加快腫瘤新生血管速度。而HIF-1α可通過誘導VEGF表達,促進癌組織增長,若肝癌患者治療前HIF-1α高表達,可進一步促進VEGF的表達,加快腫瘤進展,影響TACE治療效果,增加預后不良風險。

表3 血清AFP、HIF-1α水平預測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不良風險
為進一步證實血清AFP、HIF-1α表達對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的影響,本研究行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治療前血清AFP、HIF-1α高表達可能是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不良的風險因子,進一步證實上述結論。本研究中, ROC曲線結果顯示,治療前血清AFP、HIF-1α水平預測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不良風險的AUC>0.70, 預測價值較為理想,且以聯合預測價值最高。上述結果證實,血清AFP、HIF-1α高表達不僅可影響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也可能是其TACE治療預后不良的風險因子。這表明臨床應在肝癌患者接受TACE治療前測定血清AFP、HIF-1α, 針對上述指標高表達患者,采取積極且合理的治療措施,以改善患者預后。
綜上所述,肝癌患者TACE治療預后不良可能與血清AFP、HIF-1α高表達有關,臨床可考慮在治療前測定其血清AFP、HIF-1α水平,預測TACE預后不良風險,以指導治療方案的調整,改善疾病治療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