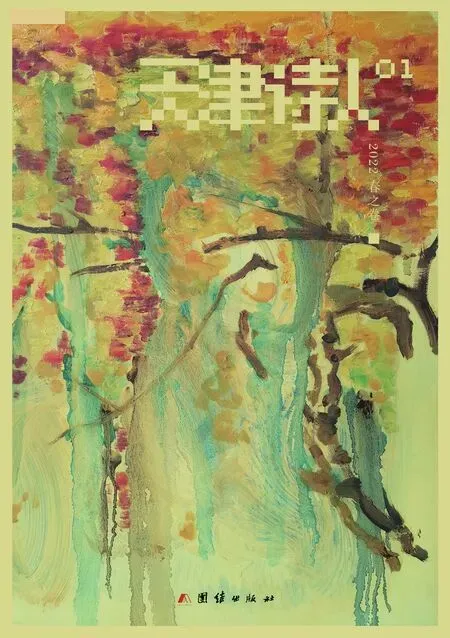漫游向一片云(組詩)
陳赫
我總是懷揣著偏執
以童年為例,玩泥巴
我要搭起一座村莊。阡陌交通
雞犬相聞,一個都不能少
這樣,沒有人可以看出,我是留守兒童
以中年為例,放風箏
我總要在正午時分。陽光毒辣
影子眾多,“我愛把臉擱在那里”
這樣,沒有人可以看出,我的脫發之頂
以暮年為例,算年頭
我習慣放在春天進行。草長鶯飛
陌生依然,“我就不會被你嚇著”
這樣,沒有人可以看出,我還有多少活頭
我總是懷揣著偏執
過著一生
滿頭白雪
腳步聲復雜如同伴著幽閉的虛無
乖戾曾揚起船帆,要與戲謔的回答決裂
我有孤憤在手,像我一樣
有且只有一個方向的河流,都默然不語
少年時代我善談,口袋中時常裝著
一切井然的秩序
中年時代我貪婪,鞋子里總是藏著
不堪示人的歸宿
暮年時代我寒冷,手掌間總是握著
近乎初垂的夜幕
我遇見的所有可能性
都帶有星星的碎片
我被捉弄不已的
還有不可測度的至誠
“如今死了,我又必須聽命于
一個傻瓜替我鐫刻的墓志銘。”
提耳之痛
那時候,他們習慣把這個叫做拔蘿卜
用風馬不相及的形骸,辨別著厚厚的積塵
爺爺習慣用那個夾頭發的推子
在我的頭上,耕耘出一片安眠
父親則帶著一個長者的皺紋
不讓樹木倒下時,顯現新鮮的顏色
我在極力抗拒這些行為
用近乎撕裂的哭聲,打破結霜的沉寂
這么多年了,我們都開始懷疑
我們所做的,是否能撐起一個時辰的搖搖欲墜
早發
不如就放錯黃昏的位置
在深度昏厥中,對一個身體置之不理
不如就解散霧靄中的光亮
在溪流涌動中,對一片清澈充滿敵意
不如就按住薄弱的呼吸
在無人問津時,抽出水底的火焰
不如就背誦出一粒葡萄說出的名字
在還記得自己時,放下自己
風,總如此沖動
積在上層的雪,總如此冰冷
“你重吧,上百人壓著你”
白夜
面對一次湖面上叫醒,類似于一次裂痕
從收藏的孤獨里,縫補的過程
流質本身是個謎,無休止的起伏
像海從不平靜
它撞擊海岸,撞擊你的胸脯
生存在你所生存的地方,不管發光者的時辰
我漫游向一片云,盡量弄青梅時
躲過繞床的聲音
已知虛空恒定才是博大
那么不如歸去
才是他在夢中吻過的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