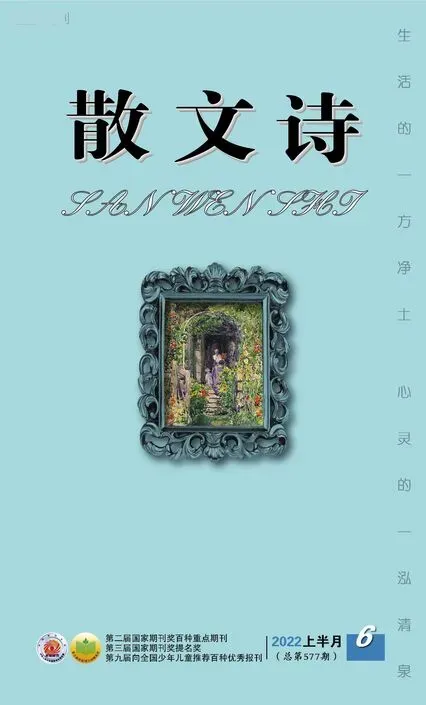萬物各有尺度
◎石桂霞
刀 子
為了避免傷口, 我盡量遠離刀鋒。
生活, 讓我不得不拿起刀子。
好鋼都用在了刀刃上, 削鐵如泥的輕快, 游刃有余的技巧,把一年切成四季, 四季切成三百六十五日, 每一日再切成柴米油鹽的樣子。
舌尖, 品咂酸甜苦辣, 含辛茹苦的手, 與刀子飽滿而深情地交談。
細水長流的日子, 有五味雜陳, 有繚繞的瑣碎, 撫摸對方,無非是把銳器和鋒芒, 隱于時間的指紋。
常常在紙上說一些斬釘截鐵的話, 拋出比刀子還鋒利的語言。
但我, 比瓷更容易碎。
總有一些詞語懸而未決
至今, 我還無法指認具體的事物。
包括愛與不愛, 包括我曾經觸摸而又放棄的, 都在流轉和通用: 糖果, 杏仁, 書桌, 飲料瓶, 和公交車上的靠背椅。
常有陌生的嬰兒, 對著我突然笑出了聲。
我乘坐的火車削尖腦袋, 穿過了漫長的隧道, 為這黑暗中的捷徑和重見天日, 發出歡呼的長鳴。
身邊的河流一路曲折坎坷, 在艱難險阻的交錯咬合, 和群山萬壑的圍追堵截中, 逃出一條命來, 繼續趕路。
我獨坐西窗, 遠望千嶺。
它們, 從龐大敦厚的山體中, 拔高和突出自己, 不過是一紙剪影。
世事多變, 忽而浩蕩, 忽而簡單, 總有一些詞語, 懸而未決。人心隔著肚皮, 但從未與世隔絕。
眼下, 一場大雨自絕于云天, 急急地投奔人間。
春天的和弦
盛產湖光和柳腰, 夭夭灼灼, 好運遇見了桃花。
老樹又泛新意, 手指閑云, 冷香引著水滴。
風在籬笆外, 偶有落紅。
日子生出枝葉, 細雨洗塵。 織錦, 大地的布匹上, 嫩綠, 暖黃, 粉白, 嫣紅。
春眠太深, 不覺曉, 聞花蕊漫漶的酒香, 聞綠云朵落下的啼鳥, 正是夢醒時分。
酒是涼的, 不如換盞, 飲茶。
一撥一撥的箏音, 鳴是百鳥的和弦。 瓷碗的青花蓋住了泥土,盡是鮮嫩的汁液。
一只離群的白鷺, 忽而走秀, 忽而靜止, 它以灘涂立命, 專注自身的孤獨與美。
一卷流水, 浣洗絲綢和落日, 煙火淺, 不足以喂養倒影, 這些十指相扣、 盤根錯節的名詞, 都是親上加親的, 木字偏旁。
標題未定, 落款尚早。
春色有適量的毒, 不需要側身和擠壓, 均能獲得自身制造的溫度和動靜, 它們擁有彼此, 互為表里, 不想孤立其中。
如果不急于趕路, 善睞, 身段, 就都是想入非非的慢動作。
酒窩醞釀的浪花, 綴著妙語連珠的好句子。
煙 花
毀滅是有預謀的。
沒有比這驚艷的暴力, 更疾速的破碎, 我仰望的目光, 來不及托舉。
接二連三, 重復升騰的燦爛轉瞬即逝, 這極致誘惑下的殺戮,優雅, 別致。 誰的胳膊能扭過命運的大腿, 甚至不能替它們說出一個 “不” 字。
夜色善誘, 天空的舞臺上, 星光, 璀璨之光, 目光, 萬眾如潮, 溢美之詞, 一下子就能擊中了軟肋, 被緊緊地攥在手里。
閃亮登場, 多么奪目的毀滅。
誰能說出真相, 誰能拽住生命的裙裾。
香消了無痕。
沒有比這曲終后一散而空的場景, 更令人心灰意冷。
奈何不了, 這敗絮, 這狼藉, 我的視線逡巡最后的慵懶和岑寂, 仿佛迷宮, 仿佛陷阱。
是的, 煙花怕冷落, 怕寂寞, 需要綻放, 需要挑戰極限, 只有夜, 欣然接受。
我們一目了然, 卻從不制止。
且一直縱容。
影 子
它, 是從我的足部突然生出來的, 很直接, 很貿然。
我確定和它不是孿生。
它演喜劇, 玩魔幻, 尤其是陽光, 月光, 燈光, 和眾目睽睽下, 它善變的表演, 時高時矮, 時粗時細, 即使接近丑陋, 扭曲, 變形, 我也從不糾正。
我停, 它不走; 我靜, 它不動。
看似同步, 我們卻從不交頭接耳, 勾肩搭背。
我對它視而不見, 甚至忽略和遺忘。
一個沒心沒肺、 沒血沒肉的影子, 我從不拿借光寄生的它當回事。
沒光的時候, 它縮小在我的身體里。
因為, 它不是另一個我, 也不是我的替身。
或者, 它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