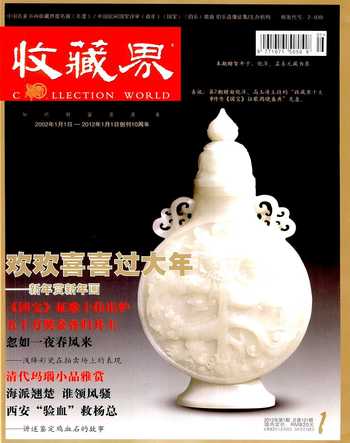拾來的文明
高功



鼓樂喧天,禮炮齊鳴,又一個民間博物館在華夏大地上誕生了。2011年12月6日,鄭州市華夏文化藝術博物館舉行了盛大的開館儀式,正式成立。
鄭州市華夏文化藝術博物館是經河南省文物局批準成立的一家綜合性股份制民辦博物館,位于鄭州市嵩山南路168號鄭州市博物院院內。博物館展廳、倉儲面積680平方米,藏品1200余件套。史前陶器、北魏墓志、漢唐名硯及銘文青銅器為其四大特色收藏。
甚愛必大費
館長李寶宗等四位華夏博物館的創辦人,出于對中華文明的熱愛,數十年來節衣縮食,備嘗艱辛,耗費大量錢財,錙積銖累,收藏和保護了許多散落在民間的珍貴文物藝術品。這些文物藝術品有的來自住戶家中或田間地頭、荒郊野外;有的來自古玩市場甚至廢品堆中;也有的來自古董藝術品拍賣會或古董販子手中。這些零珠散貝,長期散落在民間,但都是珍貴的歷史文化遺存,其上承載著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把它們撿拾器起來,就如同“撿拾”了文明,華夏博物館人親切地稱之為“拾來的文明”。 功夫不負有心人,遺散在田間地頭或居民家中的文明就這樣被他們“撿了起來”,陳列在展顯現華夏歷史文明的神圣殿堂—博物館的展品柜中。
由于對華夏文明的孜孜追求,對傳統文化藝術的摯愛和癡迷,他們歷經艱難、散盡錢財“撿拾”這些承載著華夏文明的收藏藝術品,并將其保護和珍藏起來。誠如圣人老子所說“甚愛必大費”,他們為此付出了大量的時間、辛勞和金錢,甚至家人的親情與歡樂。但為了“甚愛” 之物,他們無怨無悔,不僅繼續甘當“撿拾”文明的“尋寶者”,而且成為文物藝術品的“守護神”—博物館人!
背靠大樹好乘涼
天時、地利、人和,是事業成功三者缺一不可的條件。當前國家不僅鼓勵民間建立博物館,而且出臺了許多扶持政策,建立博物館順應“天時”;博物館建在哪里合適,是確定參觀者多少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華夏博物館的決策者選在鄭州市博物院的閑置場地設立博物館,因“地”而“利“,無疑是聰明之舉。鄭州市博物院位于市中心,歷史悠久,每天都有大批的觀眾參觀,華夏博物館就在她的院內,相當于博物院的一個分館,展品又有自己的獨特之處,自然會吸引大批參觀者;能在博物院內建博物館,毫無疑問得到了鄭州市博物院的大力支持,依托國有博物館的資源優勢,在藏品保護、展廳布置、展品講解以及學術研究等方面,“師傅”就在眼前。俗語說得好“背靠大樹好乘涼”,李寶宗館長和他的團隊占盡了“人和”的優勢。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備,華夏博物館已奠定了成功的基石。
走股份制之路
建館難,建成后管理更難,尤其是如何籌措巨額的運營資金,這是所有民間博物館共同面臨的難題。為了破解這一難題,華夏博物館采取股份制的形式管理和運作博物館。博物館籌備時由四個收藏家組成董事會,按照董事會成員每人所有藏品的價值及投入的資金劃分股份,由李寶宗出任法人。為了擴大董事會成員,籌措更多的資金,他們把館藏文物“變賣”給愿意參股的人,館藏文物的所有權就從原有股東的手中轉屬于新入股的股東,但前提條件是“變賣”的文物必須永久性放在華夏博物館內收藏和展出(博物館的文物成立時已注冊登記)。“變賣”文物的錢作為股份入股。如果一件文物“變賣”一百萬元,一千件文物就能變賣一千萬元。這就相當于新進來的股東出資“認領”館內的文物成為新的股東,原有的股東讓出一部分股份。參與博物館管理和運營的股東越來越多,每個股東占有的股份逐步減少,不僅博物館的運營資金有了保證,而且減輕了博物館所有投資人的負擔和風險。采取股份制的形式興辦和管理民間博物館,華夏博物館走出了“敢吃螃蟹”的第一步,值得所有博物館人借鑒和學習。
現在,讓我們一起走進華夏博物館,親身感受“拾來的中華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