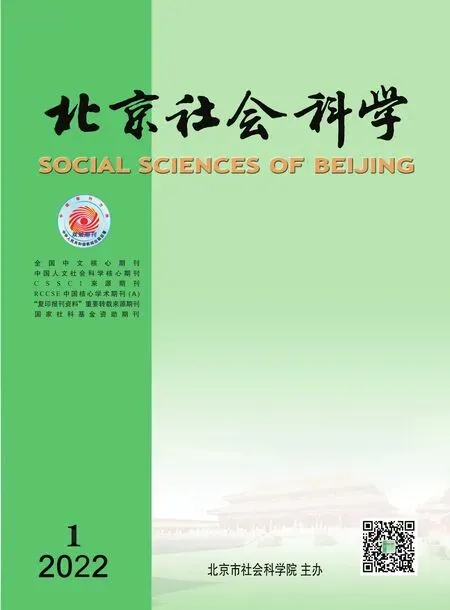論晚明家具的審美“真趣”
儀平策 周坤鵬
一、引言
晚明時(shí)期的家具一直是中國傳統(tǒng)家具研究領(lǐng)域的熱點(diǎn),雖然其形制和工藝在南宋時(shí)已基本成熟,但其突出的藝術(shù)價(jià)值和多元化的美學(xué)風(fēng)格卻與這一時(shí)期特殊的審美文化背景息息相關(guān)。在心學(xué)泰州學(xué)派“圣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等思想的影響下,晚明文士群體開始將自己的熱情投注到日常生活領(lǐng)域,他們積極地參與家具等日用器的設(shè)計(jì)和品鑒,致力于經(jīng)營一種藝術(shù)化的生活方式,其審美趣味對當(dāng)時(shí)社會各階層的家具審美起到了重要的引領(lǐng)和示范作用。這一點(diǎn),許多學(xué)者都曾指出。在對晚明家具審美特征與文人趣味之關(guān)系的闡釋上,學(xué)者們大多圍繞“素樸”“淡雅”等古典美學(xué)趣味展開,如王世襄所提出的“明式家具”藝術(shù)價(jià)值較高的“十六品”多數(shù)都偏于簡約素樸、清新自然的風(fēng)格;朱家溍先生也稱明式家具“淳樸厚重”“空靈秀麗”“典雅清新”。然而,從大量晚明時(shí)期的話語、文本、圖像以及現(xiàn)存家具實(shí)物上還可以看到,包括晚明文人在內(nèi)的社會各階層的家具審美也在很大程度上流露出崇新尚奇、溺情享樂的一面。那么,為何這一時(shí)期的家具會呈現(xiàn)兩種看似矛盾的美學(xué)風(fēng)格?到底是哪些文人趣味,又以何種邏輯對當(dāng)時(shí)士民的家具審美產(chǎn)生影響的?這些問題尚有進(jìn)一步深入的理論空間。我們認(rèn)為,這種復(fù)雜的、多元的家具審美現(xiàn)象與當(dāng)時(shí)的社會文化語境,特別是晚明士民拓展了、豐富了的尚“真”趣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而這種聯(lián)系尚未得到學(xué)界充分的論證,本文試就此作一探討。
二、晚明文人承自傳統(tǒng)的崇“真”尚“淡”趣味
“真”,是古典美學(xué)尤其是道家美學(xué)的重要范疇。道家將“自然”視為生成萬物、規(guī)范萬物的最高法則,《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在莊子看來,“真”就是“自然”之道的體現(xiàn),所以他說:“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從現(xiàn)象層面看,道家的尚“真”趣味突出地表現(xiàn)在其對自然、平淡、素樸的審美意象的強(qiáng)調(diào)上。《老子》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又云:“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莊子也稱:“若夫不刻意而高,……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又稱:“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無為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可見,在道家那里,“恬淡”“樸素”是合于天道之“真”和圣人之德的大美所在。道家的這一崇“真”尚“淡”趣味,一方面表現(xiàn)為崇尚“物性自然”的自然主義審美觀,另一方面表現(xiàn)為對平淡、素樸的審美意象的偏好。魏晉南北朝士人喜談玄說莊,道家這種崇“真”尚“淡”的觀念也隨之在文士階層中扎根。宗白華先生認(rèn)為,正是在這一時(shí)期,“初發(fā)芙蓉”的天真、自然之美在人們眼中開始成為比“錯(cuò)采鏤金”的雕飾之美更高的審美境界。
儒家對平淡、素樸的審美意象也多有推重。子思評《詩經(jīng)》“衣錦尚絅”,由穿衣引申為君子外表暗淡,而美德日益彰顯,小人外表鮮明,但美德卻日漸消退,認(rèn)為君子之道在于平淡、質(zhì)樸而有文采。《中庸》作為儒家的重要經(jīng)典,其對君子之道的闡釋使平淡、素樸也成為儒家重要的審美意象。
唐宋以后,佛教禪宗思想的流行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了文士群體崇“真”尚“淡”的審美觀念。唐代禪師馬祖道一說:“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舍,無斷常,無凡無圣……只如今行住坐臥,應(yīng)機(jī)接物盡是道。”馬祖道一的俗家弟子、深受袁宏道等晚明文人推崇的龐蘊(yùn)居士也有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神通并妙用,運(yùn)水及搬柴。”禪宗在北宋時(shí)達(dá)到鼎盛,也正是在這一時(shí)期,“平淡”趣味成為文藝領(lǐng)域中極為重要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在文學(xué)領(lǐng)域,與高僧多有交往的蘇軾認(rèn)為詩文應(yīng)“發(fā)纖秾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梅堯臣稱“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陶淵明的詩亦因其“平淡”“自然”的風(fēng)格而在宋代被推至高于其他任何時(shí)代的地位,如葛立方稱贊陶詩:“平淡有思致,非后來詩人怵心劌目雕琢所為也。”在繪畫領(lǐng)域,米芾稱贊董源“不裝巧趣”的畫作有“平淡天真”之趣。可以說,融會儒、道、釋三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本體論色彩的平淡、自然趣味在北宋時(shí)已成為古典美學(xué)的核心內(nèi)容。
然而,隨著程朱理學(xué)與倫理、政治的深度捆綁和對文藝領(lǐng)域的不斷滲透,傳統(tǒng)的“崇真尚淡”趣味逐漸被“崇道尚理”的風(fēng)氣所淹沒。朱熹在闡釋周敦頤的“無極之真”時(shí)稱:“所謂‘真’者,理也。”在朱熹那里,只有體現(xiàn)封建綱常倫理的文藝作品才可稱得上“真”。對此明代李夢陽批評道:“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而今之文……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
直到明代中后期,古典美學(xué)的崇“真”尚“淡”趣味才重回人們的視野。晚明吳從先直言“趣要澹泊”,陳繼儒在為董其昌《容臺集》所作的序中贊其詩文:“漸老漸熟,漸熟漸離,漸離漸近于平淡自然,而浮華刊落矣,姿態(tài)橫生矣。”繪畫領(lǐng)域也是如此,董其昌稱贊元代倪瓚之畫“古淡天然”,王世貞在談及萬歷年間士民對繪畫作品喜好的變化時(shí)稱:“畫當(dāng)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鎮(zhèn)以逮沈周,價(jià)驟增十倍。”在許多晚明文人眼中,倪瓚、沈周等人蕭疏淡雅、有“平淡自然”之趣的畫作的藝術(shù)價(jià)值是高于端莊、典雅的宋畫的。
以“平淡自然”范式為主體的古典美學(xué)尚“真”趣味之所以在晚明時(shí)重新成為文士群體判斷文藝作品藝術(shù)價(jià)值高低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一方面與道家美學(xué)、禪宗美學(xué)長久以來的文化“積淀”“濡化”有關(guān);另一方面也與心學(xué)諸子“援禪入儒”的理論路向所導(dǎo)致的“佞禪”世風(fēng)有關(guān)。晚明心學(xué)創(chuàng)始人王陽明本人就承認(rèn)其“心學(xué)”與禪學(xué)有一定的相似性:“夫禪之學(xué)與圣人之學(xué),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陽明的弟子王畿也曾言:“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這種不刻意、不造作、順其自然的學(xué)道方法,與唐代禪師臨濟(jì)義玄所謂“隨緣消舊業(yè),任運(yùn)著衣裳……無一念心希求佛果”的修佛路徑如出一轍。
泰州學(xué)派王艮的思想也跟禪宗多有相似,他說:“良知之體,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要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又說:“凡涉人為,皆是作偽。”嵇文甫先生稱這種不假人為、純?nèi)巫匀坏挠^點(diǎn)“全然是一種自然主義”。王艮再傳弟子趙大洲也承認(rèn)自己與禪學(xué)的關(guān)系:“仆之為禪,自弱冠以來,敢欺人哉!”晚明思潮的中心人物李贄甚至將篤信佛禪的趙大洲譽(yù)為泰州學(xué)派翹楚,當(dāng)時(shí)的佞禪之風(fēng)由此可見一斑。
陽明后學(xué),尤其王畿和泰州諸子與禪學(xué)的這種親密關(guān)系,使晚明文人與道家美學(xué)和禪宗美學(xué)淵源頗深,對以“平淡自然”范式為主體的古典美學(xué)尚“真”趣味有一種天然的親近,這一觀念背景對晚明士民的家具審美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
三、晚明士民家具審美的古典“真趣”
晚明文人承自傳統(tǒng)古典美學(xué)的尚“真”趣味對家具審美的影響首先體現(xiàn)在他們對自然天成、不假人為的家具造型、材料、紋理的喜愛上。顧起元稱友人嚴(yán)賓的棗根香幾:“天然為之,不煩鑿削,最稱奇品。”高濂《遵生八箋》記載過一種“以怪樹天生屈曲環(huán)帶之半者為之”的“隱幾”,還有其好友吳破瓢藏有的一“幾”:“樹形皺皮,花細(xì)屈曲奇怪,三足天然,摩弄瑩滑,宛若黃玉。”文震亨《長物志》也記載過類似造型的“幾”,文氏還提到一種自然天成、不事斧鑿的“禪椅”:“以天臺藤為之,或得古樹根,如虬龍?jiān)懬纺[,槎牙四出……更須瑩滑如玉,不露斧斤者為佳。”文氏所言以天然老藤、古樹根制成的坐具與陳洪綬畫作(《隱居十六觀圖(之一)》《吟梅圖》《祝壽圖》)中的坐具亦相仿佛。
在中國傳統(tǒng)家具史上,柴木家具、漆作家具一直在數(shù)量上占據(jù)優(yōu)勢,但晚明士民卻偏愛用天然紋理優(yōu)美的“文木”制作的家具。文震亨曾直言“天然幾”應(yīng)“以文木如花梨、鐵梨、香楠等木為之”。早在明初,曹昭《格古要論》便已記載過“花有鬼面者可愛”的“花梨木”、“花細(xì)可愛”的樺樹“癭木”和“有山水、人物等花”的“骰柏楠”等“文木”,但當(dāng)時(shí)這幾種“文木”主要被用來制作小件工藝品。晚明蘇州、松江一帶的文人熱衷于家具的設(shè)計(jì)和品鑒,他們的審美趣味使紋理優(yōu)美的“文木”成為家具設(shè)計(jì)的新寵。萬歷年間松江人范濂記載:“細(xì)木家伙,……民間只用銀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韓與顧、宋兩公子,用細(xì)木數(shù)件,亦從吳門購之。隆萬以來,雖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xì)器。……紈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貴,凡床櫥幾桌,皆用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與黃楊木,極其貴巧。”莫廷韓與友人用“椐木”(即櫸木)家具替代民間流行的銀杏木金漆家具,與他們對櫸木自然紋理之美的喜愛有很大關(guān)系。“紈绔豪奢”用花梨、癭木、相思木來制作家具,其動機(jī)雖在競奢夸富,但也不乏對這些木材優(yōu)美的自然紋理的欣賞。張岱曾祖張?jiān)碓凇督B興府志》中也記載了幾種當(dāng)?shù)爻霎a(chǎn)的“文木”,如“木紋理縝密,而黃色可愛,堪為器具”的柘木,“理堅(jiān),斜斫之有文,可作器”的相思木等。從張氏行文不難看出,木材的自然紋理之美已成為晚明家具審美的重要因素。在這種文人趣味的引領(lǐng)下,使用“文木”制作家具在晚明逐漸成為時(shí)之所尚,目前存世的大量以花梨木、鐵力木、紫檀制成的晚明家具正是在這樣的審美文化背景下出現(xiàn)的。
此外,還有一些材料也因優(yōu)美的天然紋理而為晚明士民所喜愛,例如斑竹。斑竹,又稱湘妃竹,因竿部生有不規(guī)則的黑色斑點(diǎn)而有清雅自然之趣。《紹興府志》載:“越中有顧家,斑竹用以作床、椅及他器,具甚清雅。”文震亨、屠隆二人都曾提到可用斑竹裝飾榻的圍屏,高濂稱可用斑竹制作“禪椅”。張岱則提到一位因擅長制作斑竹家具而聞名的姜姓匠人:“又有以斑竹為椅桌等物者,以姜姓第一,因有姜竹之稱。”仇英畫作《人物故事圖(之七)》中賓主三人所坐之玫瑰椅、坐墩也是以斑竹制成。晚明士民對用天然樹根、古藤制作的隱幾、坐具和用紋理美麗的“文木”、斑竹制作的家具的欣賞,與崇尚自然天成、不假人為的古典美學(xué)尚“真”趣味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
其次,晚明士民家具審美的古典“真”趣還體現(xiàn)在他們“尚古樸不尚雕鏤”的偏好上。晚明之前,一般百姓家中多使用價(jià)格低廉的柴木家具,而富裕的士商階層則喜歡裝飾性強(qiáng)、富貴華麗的漆作家具。據(jù)嘉靖年間巨貪嚴(yán)嵩的抄家錄《天水冰山錄》記載,嚴(yán)嵩家中最珍貴的家具主要是17張未作“變價(jià)”直接收入內(nèi)庫的床,如“雕漆大理石床”“黑漆大理石床”“螺鈿大理石床”“堆漆螺鈿描金床”等。這些床用大理石、螺鈿等珍稀材料裝飾,用雕漆、堆漆、描金、鑲嵌等復(fù)雜工藝制作,可謂窮工極巧。此外數(shù)百張折賣成白銀入庫的“變價(jià)”之床,如“螺鈿雕漆彩漆大八步床”“描金穿藤雕花涼床”等,也都極盡裝飾之能事。這種以雕鏤為美的家具審美趣味在晚明之前的官紳階層中非常普遍。
而在晚明,隨著文士群體對家具設(shè)計(jì)和品鑒的參與,他們的審美趣味使原先以雕飾為美的家具風(fēng)格在很大程度上發(fā)生了改變。如文風(fēng)鼎盛的蘇州地區(qū)孕育出了為今人所激賞的古樸、清雅、不事雕琢的“蘇作家具”。晚明王士性曾言:“姑蘇人聰慧好古……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齋頭清玩、幾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為尚。尚古樸不尚雕鏤,即物有雕鏤,亦皆商、周、秦、漢之式,海內(nèi)僻遠(yuǎn)皆效尤之,此亦嘉、隆、萬三朝為始盛。”蘇作家具素樸、淡雅的美學(xué)風(fēng)格與文士群體的“平淡自然”之趣息息相關(guān),這一點(diǎn)從當(dāng)時(shí)的文人話語中也不難看出。文震亨曾明確反對“雕繪文飾,以悅俗眼”的家具風(fēng)格,他認(rèn)為亭榭中所設(shè)之桌須“舊漆方面粗足,古樸自然”,而臥室所用家具、陳設(shè)須“精潔雅素”,倘若“一涉絢麗”,則“如閨閣中,非幽人眠云夢月所宜”。文震亨是文徵明的曾孫,家學(xué)淵源使其深諳傳統(tǒng)文人趣味,他在家具及其陳設(shè)方面所提倡的“寧古勿時(shí)、寧樸勿巧、寧儉勿俗”的審美取向,正是對古典美學(xué)以“平淡自然”范式為主體的尚“真”趣味的一種傳承。
四、晚明浪漫美學(xué)思潮中“真”范疇的拓展
“真”也是晚明浪漫美學(xué)的核心范疇。湯顯祖稱“不真不足行”,李贄說:“人而非真,全不復(fù)有初。”袁宏道則稱贊“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的民間戲曲為“真人”所作之“真聲”。在袁宏道看來,能夠“任性而發(fā)”,與審美主體真實(shí)的情感、個(gè)性、欲望息息相通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不難看出,湯顯祖、袁宏道等人口中的“真”已不再局限于古典美學(xué)帶有形而上色彩的“平淡自然”之“真”,而更多是以主體的情感之“真”、個(gè)性之“真”,甚至以欲望之“真”為核心。晚明美學(xué)“真”范疇的這種拓展一方面源于文士群體對明初文藝領(lǐng)域“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的理學(xué)風(fēng)氣,及明中期李夢陽等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xué)復(fù)古運(yùn)動所導(dǎo)致的模擬剽竊之風(fēng)的修正;另一方面更與高揚(yáng)主體精神、追求個(gè)性解放的晚明浪漫美學(xué)思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袁宏道在評價(jià)張幼于的詩文時(shí)稱:“兩者不相肖也,亦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安,殆不可強(qiáng),率性而行,是謂真人。”所謂“率性而行,是謂真人”,表面看是對儒家經(jīng)典話語“率性之謂道”的轉(zhuǎn)述,但其真正意涵已與儒家經(jīng)典有很大不同。儒家“心性論”所言之“性”,自子思、孟子而二程、朱熹,再而王陽明,都是指純?nèi)恢辽频南闰?yàn)道德理性,如王陽明稱:“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在王陽明看來,《中庸》所言“率性”之“性”即是“至善”的“道”:“‘率性之謂道’,性即是道。”而“率性”之“道心”與“人欲”有著清晰的界限:“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于人。”可見,陽明所言“率性”尚未脫出儒家經(jīng)典的框架。
真正將“率性而為”導(dǎo)向自然人性之“真”的是泰州諸子。王艮講學(xué)不似其師陽明般謹(jǐn)嚴(yán),他認(rèn)為“良知現(xiàn)成”,提倡頓悟之學(xué)。在他看來,一旦悟得良知本體,便可信心而行,甚至不須防檢。他說:“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識得此理,則現(xiàn)現(xiàn)成成,自自在在。即此不失,便是莊敬;即此常存,便是持養(yǎng),真不須防檢。”王艮弟子徐樾也說:“圣學(xué)惟無欺天性,聰明學(xué)者,率其性而行之,是不自欺也。率性者,率此明德而已。”雖然王艮、徐樾等人仍算站在道學(xué)立場而言“率性”,但他們這種不加檢防的修養(yǎng)方法為顏鈞、李贄等人走向自然人性論開了一道口子。王艮弟子顏鈞稱:“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睹聞?著何戒懼?平時(shí)只是率性所行,純?nèi)巫匀唬阒^之道。”在顏鈞看來,欲望只是人之本性的自然流露,他稱:“貪財(cái)好色,皆從性生,天機(jī)所發(fā),不可閼之,第勿留滯胸中而已。”顏鈞弟子,深受李贄等人推崇的羅汝芳也說:“萬物皆是吾身,則嗜欲豈出天機(jī)外耶?……天機(jī)以發(fā)嗜欲,嗜欲莫非天機(jī)也。”
在教學(xué)過程中,教學(xué)理念是教師開展教學(xué)工作的核心標(biāo)準(zhǔn)與計(jì)劃依據(jù),對整個(gè)教學(xué)過程起關(guān)鍵性作用。然而,傳統(tǒng)語文教學(xué)中,大部分教師將教學(xué)目光集中在促使學(xué)生積累語文專業(yè)知識與學(xué)習(xí)技巧、提高學(xué)生語文基礎(chǔ)能力上,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學(xué)生的情感素質(zhì)人文性教學(xué),這與現(xiàn)代化新課改背景下的教學(xué)要求不符,也不利于構(gòu)建學(xué)生的自主認(rèn)知,難以培養(yǎng)學(xué)生形成逐步完善獨(dú)立的學(xué)習(xí)思考意識。鑒于此,教師應(yīng)積極轉(zhuǎn)變教學(xué)理念,注重在語文教學(xué)過程中增加對學(xué)生的人文素質(zhì)性教學(xué),提高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自主獨(dú)立意識,增加學(xué)生的主人翁意識,豐富學(xué)生學(xué)習(xí)體驗(yàn)。
李贄明確將“真”的意涵歸結(jié)于人的自然本性——“童心”,他說:“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李贄所言之“真心”是跟王陽明的“良知”類似的本體論概念,在他看來,包含情感、欲望等自然人性的“童心”便是“真心”,順著自己的自然本性去做事便是合道“真人”。而且“童心”還是文藝創(chuàng)作的根本,文章只有從自己的“童心”流出,才是“真文”、好文。也就是說,文藝作品的最高境界不是達(dá)到“禮義”等外在倫理的要求,而是要符合主體情性之“真”的內(nèi)在要求,藝術(shù)家的真情實(shí)感、個(gè)性甚至欲望才是作品最重要的內(nèi)容,正如他所說:“蓋聲色之來,發(fā)于情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fù)有禮義可止也。惟矯強(qiáng)乃失之,故以自然之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復(fù)有所謂自然而然也。”
經(jīng)由泰州諸子的理論演繹,主體的情性之“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本體論色彩,成為“道”、天理的體現(xiàn)。雖然他們口中到達(dá)“真”之境界的路徑從表面看也似前人所說的“率性”而為,但他們這里的“性”之“所指”顯然已不再只是子思、孟子、朱熹、王陽明等人那里純?nèi)恢辽频南闰?yàn)道德理性,而是包含主體的情感、個(gè)性和欲望的自然人性了。在晚明浪漫文藝思潮的主要干將中,湯顯祖曾師事羅汝芳,袁宏道視李贄為知己,泰州諸子帶有自然人性論色彩的思想對其文藝創(chuàng)作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而他們杰出的文藝作品又將這種帶有個(gè)性解放色彩的新“真趣”傳播到晚明社會包括家具審美和設(shè)計(jì)制作的各個(gè)行業(yè)領(lǐng)域,對儒家傳統(tǒng)的“溫柔敦厚”趣味造成了“嚴(yán)重的沖擊”。
五、晚明士民家具審美的浪漫“真趣”
在晚明浪漫美學(xué)思潮的影響下,主體的情感之“真”、個(gè)性之“真”,甚至欲望之“真”逐漸成為“真趣”的核心內(nèi)容。這種對前人以“平淡自然”范式為主的古典美學(xué)“真趣”的拓展,其實(shí)質(zhì)是傳統(tǒng)文人的精英趣味與新興市民階層趣味的互滲和融合,正如羅筠筠先生所說:“原來彼此毫無共同之處并且相互排斥的文人士大夫的審美情趣和市民階層的審美趣味,向著各自的對立方面的杰出之處重新選擇、過渡。”這種拓展了、豐富了的新“真趣”對當(dāng)時(shí)的家具審美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使其表現(xiàn)出許多與眾不同的特征。
晚明浪漫美學(xué)的新“真趣”首先表現(xiàn)在審美主體和創(chuàng)作主體對情感之“真”的重視上。如袁宏道稱:“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真詩,可傳也。”湯顯祖則批評在創(chuàng)作中缺乏真情實(shí)感、一昧模擬古人的李夢陽等輩只是無緣“真趣”的“三館畫手”“一堂木偶”。在這種文化語境中,晚明士民的家具審美開始更多地關(guān)注自身的情感體驗(yàn),家具成為人們陶冶性情、寄托情思的重要手段。沈春澤在《長物志》的序文中稱:“夫標(biāo)榜林壑,品題酒茗,收藏位置圖史、杯鐺之屬,于世為閑事,于身為長物。而品人者,于此觀韻焉,才與情焉。”明末清初的李漁在家具和室內(nèi)陳設(shè)的設(shè)計(jì)上更是主張:“物物皆非茍?jiān)O(shè),事事具有深情。”在李漁看來,家具的欣賞和創(chuàng)造與主體的情感體驗(yàn)、情感表達(dá)密不可分,是值得付出深深情思的審美對象。清代張廷濟(jì)的藏品中有晚明書畫家周天球的一把紫檀椅子,其上刻有蘇軾之詩:“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這種在自己喜愛的家具上刻字的做法在晚明很流行,也是晚明士民在家具上寄托情思的一種表現(xiàn)。
其次,晚明浪漫美學(xué)的新“真趣”還體現(xiàn)在對主體個(gè)性之“真”的推重上。袁宏道稱贊其弟中道的詩文:“大都獨(dú)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dú)造語。”在袁中郎看來,創(chuàng)作主體獨(dú)一無二的個(gè)性和創(chuàng)造力才是文藝作品的核心要素,即使文章有瑕疵之處,但只要是主體的“本色”流露,便也是美的。晚明士民對個(gè)性之“真”的推崇是王艮、李贄等人高揚(yáng)主體性所啟蒙的個(gè)性解放思潮的結(jié)果,其在現(xiàn)象層面的突出表現(xiàn)是人們對“新”與“奇”的極力追捧。如袁中道評價(jià)周伯孔的詩文:“抒自性靈,清新有致。……多出新意,不同世匠。”在他看來,創(chuàng)作主體的性情各有不同,順應(yīng)主體個(gè)性之“真”的文藝創(chuàng)作就自然能“新”、能“奇”,即所謂:“性情之發(fā),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張大復(fù)也稱:“木之有癭,石之有鴝鵒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此見貴于世。非世人之貴病也,病則奇,奇則至,至則傳。”也就是說,正是個(gè)性之“真”、之“病”、之“奇”才賦予了主體和藝術(shù)作品獨(dú)特的價(jià)值。
高濂曾提到當(dāng)時(shí)的一種新式折疊家具:“作二面折腳活法,展則成桌,疊則成匣,以便攜帶,席地用此抬合,以供酬酢。”這種“疊桌”結(jié)構(gòu)巧妙,是很實(shí)用的創(chuàng)新之作。屠隆記載過一種時(shí)之所尚的琴臺:“用紫檀為邊,以錫為池,于臺中置水蓄魚,上以水晶板為面,魚戲水藻,儼若出聽,為世所稀。”這種琴臺可以在水晶臺面下蓄水養(yǎng)魚,給人以色彩斑斕、光怪陸離之感,可謂極盡奇巧,與古人所用琴臺肅穆、清雅的風(fēng)格迥異其趣,足見晚明士民對新奇家具的喜愛。文震亨性情簡淡好靜,品評器物唯尚古雅,因此他將屠隆所言琴臺斥為“俗制”。然而,即使像文氏這樣標(biāo)榜“古雅”的文人也難掩自己對一些新奇家具的喜愛,如他每次提及來自日本的倭漆器都大加贊賞,稱“有鍍金鑲四角者,有嵌金銀片者,有暗花者,價(jià)俱甚貴”的倭臺幾“俱極古雅精麗”,又說“黑漆嵌金銀片”的倭箱“奇巧絕倫”。事實(shí)上,常用金銀片裝飾,喜用描金、剔紅等工藝的倭漆器視覺效果富貴華麗,與傳統(tǒng)文人的古典雅趣其實(shí)并不相符。文震亨身上的這種矛盾之處,一方面或如英國學(xué)者柯律格所言是文氏對文士階層高雅品味的刻意標(biāo)榜,是一種對新富裕起來的、正日益對文士階層地位造成威脅的工商階層所設(shè)置的文化壁壘;另一方面也說明,在晚明家具審美“崇新尚奇”的風(fēng)潮影響下,倭漆器等新奇的異域之物使文震亨等趣味偏于古典、保守的文人也迷戀其中。高濂、李漁等來自市民階層的文人對待新奇家具的態(tài)度與文震亨相比則開放、圓融許多。高濂在談到“竹榻”時(shí)說:“或以花梨、花楠、柏木、大理石鑲,種種俱雅,在主人所好用之。”在高濂看來,家具設(shè)計(jì)并無一定之規(guī),完全可以根據(jù)主人的喜好來選擇材料和工藝。高濂的寬容態(tài)度實(shí)質(zhì)上是對新興市民趣味的接納和認(rèn)可。
晚明士民還將自己的個(gè)性和創(chuàng)造力投入到了新奇家具的設(shè)計(jì)上。萬歷時(shí)人戈汕設(shè)計(jì)出了以13只斜形桌面為基本單元,可自由搭配成130多種形式的新式組合家具。高濂設(shè)計(jì)了冬暖夏涼的“二宜床”和“式如小廚”可攜之山游的“提盒”等家具。“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的李漁設(shè)計(jì)了夏天在座面下放置冷水給人降溫的“涼杌”和冬天在座位下放置炭火來暖身的“暖椅”等極有新意的家具。總而言之,“崇新尚奇”的家具審美觀在晚明已成為一種極具普遍性的審美文化現(xiàn)象。但這種追新逐異的風(fēng)氣也使部分家具的設(shè)計(jì)走上刻意求新、窮工極巧的歧途,李漁曾談及他在東粵所見:“市廛所列之器,半屬花梨、紫檀,制法之佳,可謂窮工極巧;止怪其鑲銅裹錫,清濁不倫。”王世襄先生所言明式家具“八病”中的“悖謬”“失位”等幾品或也因這一風(fēng)氣所致。
此外,晚明浪漫美學(xué)的新“真趣”還有一個(gè)充滿爭議的維度,即士民對欲望之“真”的肯定和追逐。萬歷中期以后,一種縱情任性、帶有濃厚物欲色彩的審美觀和人生觀在民間蔓延,張瀚對此曾批評道:“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fēng)以侈靡相高。”這種特殊的審美文化現(xiàn)象與李贄等人帶有自然人性論色彩的思想的風(fēng)行和市民趣味的流行都有一定關(guān)系,部分文人的相與鼓倡也對此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袁宏道在給龔惟長的信中稱:“真樂有五,不可不知。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談,一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不朽矣。”張岱曾宣稱自己:“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袁中郎和張岱的說法充滿欲望和享樂色彩,與儒家傳統(tǒng)“修齊治平”之道德實(shí)踐的人生理想幾乎是背道而馳的,但這種肯定欲望,放任、肆意的人生態(tài)度在當(dāng)時(shí)確是許多人的心中所向。這種審美風(fēng)尚對晚明士民的家具審美也產(chǎn)生了不小的影響,使其呈現(xiàn)出一種物欲化的傾向。
張岱曾提到其叔父張聯(lián)芳在萬歷三十一年購買一張鐵梨木天然幾的經(jīng)歷:“有鐵犁木天然幾,長丈六,闊三尺,滑澤堅(jiān)潤,非常理。淮撫李三才百五十金不能得,仲叔以二百金得之,解維遽去。淮撫大恚怒,差兵躡之,不及而返。”為爭奪一張?zhí)烊粠祝矒峋箘佑霉俦汾s,這一事例折射出晚明文士群體的強(qiáng)烈物欲。晚明宦官群體也對精美的家具趨之若鶩,據(jù)太監(jiān)劉若愚記載:“大抵天啟年間,內(nèi)臣更奢侈爭勝。凡生前之桌、椅、床、柜、轎乘、馬鞍……皆不憚工費(fèi),務(wù)求美麗。”晚明世情小說《金瓶梅》的人物、故事雖以北宋末年為背景,但因其成書于嘉靖至萬歷年間,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書中情境與晚明士民的日常生活較為貼合。該書第二十九回提到,潘金蓮因妒忌李瓶兒的“螺鈿敞廳床”而要求西門慶花六十兩銀子為其買了一張“有欄桿”、“兩邊槅扇都是螺鈿攢造”,裝飾有“樓臺殿閣”和“花草翎毛”的螺鈿床。潘氏對精美家具的渴望和攀比心理也反映出這一時(shí)期市民階層物欲化的家具審美風(fēng)尚。
六、結(jié)語
心學(xué)泰州學(xué)派所帶來的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個(gè)性解放思潮使晚明士民突破了宋明理學(xué)的禁錮,發(fā)展出一種意涵豐富的尚“真”趣味。這種尚“真”趣味既有承自傳統(tǒng),以“平淡自然”范式為主的古典美學(xué)“真趣”,又有富于時(shí)代氣息、以追求情性自然之“真”為主的浪漫美學(xué)新“真趣”。晚明士民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這兩種“真趣”的雜糅、沖突甚至撕裂,而就萬歷以后的普遍風(fēng)氣而論,追求情感之“真”、個(gè)性之“真”,甚至欲望之“真”,帶有鮮明的市民階層趣味的浪漫美學(xué)“真趣”觀似乎更占上風(fēng)。這一風(fēng)尚使晚明士民的家具審美在崇尚自然天成、平淡素樸的古典雅趣之外,開始愈發(fā)重視家具審美中的情感體驗(yàn),追求家具審美和設(shè)計(jì)的個(gè)性化與新奇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走向物欲化。這種融攝古典與浪漫的家具審美“真趣”,是晚明家具的一大文化特征,也是“雅俗互融”的時(shí)代風(fēng)尚在家具審美領(lǐng)域的一種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