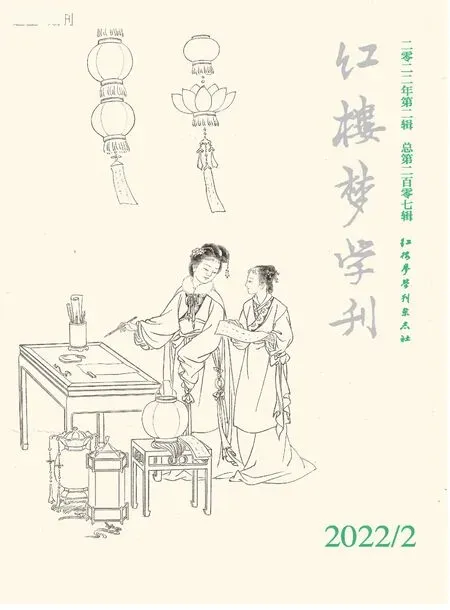脂畸二人說與一人說之重審
——沒有靖批我們能否證明脂畸二人說?
李鵬飛
內容提要:通過對脂畸問題研究史的重審,我們發現周汝昌先生所提出的脂畸一人說的四大證據都不能成為一人說的確證。其中有兩條反而是二人說的有力證據。此外,從脂批中還可找到被前輩學者所忽略的證據,證明脂畸二人說有更大的合理性,這一證明無需引用靖批。
在《紅樓夢》早期三大抄本所保留下來的大量批語中,有很多都署名脂硯齋和畸笏叟。因此,紅學界歷來很重視此二人身份的研究,對于他們是兩人還是一人,以及他們跟曹雪芹的關系如何,都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形成了激烈的爭論。
1953年,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出版,提出并論證脂畸一人說。俞平伯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引言》則提出脂畸二人說,但幾乎未作論證。此后吳世昌支持一人說,并加以論證,一人說相對而言占了上風。但到1964年,橫空出世的“靖藏本”卻讓這一局面發生了改變,二人說漸占上風。俞平伯1964年所撰《記毛國瑤所見靖應鹍藏本〈紅樓夢〉》即指出:根據靖本上的批語可知脂硯齋和畸笏叟非一人,脂硯齋在曹雪芹卒后不久也就死了。此后,吳恩裕、孫遜、鄭慶山等學者相繼撰文論證脂畸二人說,或多或少都憑借了靖藏本批語,相關討論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其中海外學者趙岡原本持一人說,后看到靖藏本批語,也改主二人說。
關于靖本及其批語的真偽問題,學界有過很多爭論,斥其為偽的聲音很高。其實,俞平伯先生當年也未嘗沒想過靖本作偽的可能性,但他還是相信了其真實性。最近又有學者極力出來論證靖藏本是毛國瑤偽造的,其偽造的一個目的是證明脂畸二人說,支持俞平伯的觀點。靖藏本如果是偽造的,則其所支持的脂畸二人說也就站不住腳了。靖藏本的真偽問題,筆者未作深入研究,不持任何立場。本文只想討論一個問題,即在完全不依靠靖藏本批語、只依靠早期抄本批語的情況下,我們還能否對脂、畸的身份做出一個比較可靠的判斷?這個問題是《紅樓夢》早期抄本和批語研究中的基本問題,如果對此不能得出一個比較明確的結論,那么后續的其他研究都將是空中樓閣,失去了前提和基礎。
一、脂畸一人說的論證及其問題
(一)周汝昌先生的一人說重審
主脂畸一人說的代表人物是周汝昌和吳世昌先生等人,其中論證最力的也是周吳二先生。吳先生全面接受了周先生的觀點,并提出九條證據進行論證,但吳先生對脂批的理解和論證的邏輯都存在重大失誤,筆者完全不能認同他的觀點,故這里不作評述,只著重介紹一下周先生的觀點。
周先生在其《紅樓夢新證》中從兩方面來對他的觀點加以論證:
1.看有沒有反面證據足證畸笏絕不可能是脂硯。
周先生認為:無論從文法、用字、題材、感慨、口氣哪一方面去分析脂畸二人的批語,都找不出微不相同的地方來。
2.看能不能尋出正面證據來證明畸笏即是脂硯。
周先生從批語中找出了四條證據來論證他的觀點,這些證據看上去頗為有力,故至今仍被有的學者視為脂畸二人說的鐵證。
周先生又通過對脂批時間的排比,發現署名脂硯的批語都出現在己卯、庚辰以前,署名畸笏的批語則始于壬午(集中于壬午和丁亥),而且自從畸笏出現后,就再不見脂硯署名了。周先生由此得出一個看法:從首至尾,屢次批閱的主要人物,原只有一個脂硯,所謂“畸笏”這個怪號,是他從壬午年才起的,自用了這個號,他便不再直署脂硯了。這就是著名的改號說。
我們先看周先生所說的反面證據:脂畸二人的批語風格是否真找不出微不相同之處來?
俞平伯先生在《記毛國瑤所見靖應鹍藏本〈紅樓夢〉》中曾指出:以文章風格論,脂齋與畸笏也有些區別。脂齋的評比較曲折細致,畸笏的口氣比較直率,老氣橫秋;脂齋看上去跟雪芹平輩,而畸笏則是長輩。他這一說法并未明言針對哪家觀點,我個人認為他應該是針對周先生所謂的反面證據而發的。我本人認同俞先生的判斷。但文章風格的辨別要靠敏銳的文學感覺,不容易說清楚,也不容易達成共識,故本文暫置不論。這里只重點討論周先生提出的四條證據,它們包括四組八條批語。
第一組:庚辰本第十八回首次提到妙玉時,有一段未署名的墨筆雙行夾批云:
妙卿出現。至此細數十二釵,以賈家四艷再加薛林二冠有六,添秦可卿有七,熙鳳有八,李紈有九,今又加妙玉,僅得十人矣。后有史湘云與熙鳳之女巧姐兒者,共十二人,雪芹題曰“金陵十二釵”,蓋本宗《紅樓夢》十二曲之義。后寶琴、岫煙、李紋、李綺皆陪客也,《紅樓夢》中所謂副十二釵是也。又有又副冊三段詞,乃晴雯、襲人、香菱三人而已,余未多及,想為金釧、玉釧、鴛鴦、茜雪、平兒等人無疑矣。觀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費筆墨。
這條批語上方有一條署“壬午季春畸笏”的朱筆眉批則云:
樹(“樹”各家多校改為“前”)處引十二釵總未的確,皆系漫擬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諱。壬午季春,畸笏。
第二組:第二十七回紅玉說跟著鳳姐可以“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見識見識”處,庚辰本有一條署“己卯冬夜”的朱筆眉批云(己卯批語均出自脂硯已成學界共識):
奸邪婢豈是怡紅應答者,故即逐之。前良兒,后篆兒,便是卻(確)證。作者又不得可(“可”多校改為“已”)也。己卯冬夜。
在這條批語的左側另有一條署“丁亥夏畸笏”的朱筆眉批云:
此系未見抄沒獄神廟諸事,故有是批。丁亥夏,畸笏。
周汝昌先生認為,以上兩組批語都是前一批是脂硯所寫,后一批是畸笏所寫,“最為分明”,而兩組批語的關系“皆似前后自注說明,而并非二人彼此辯駁攻擊”。換一句話說,即兩組批語各自的內部關系是:后批是對前批的自我注解和說明,而不是不同批者在相互辯駁詰難。
第三組:第二十二回寫賈母給寶釵過生日,眾人點戲,鳳姐點了一出《劉二當衣》。此處庚辰本有一條不署名的朱筆眉批云:
鳳姐點戲,脂硯執筆事,今知者聊聊(當作“寥寥”)矣,不怨夫?
在上面這條批語左側又有一條未署名的朱筆眉批云:
前批書(鄙意此處當脫一“知”字)者聊聊(當作“寥寥”),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寧不痛乎(或校改為“殺”)!
這組批語的第二條因為寫于丁亥夏,且批者自稱“朽物”,當屬畸笏無疑。但第一條是誰寫的呢?周汝昌先生和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是脂硯寫的,但孫遜先生在《紅樓夢脂評初探》中指出這條批語應該是畸笏寫的,因為如果是脂硯所寫,他不會說“脂硯執筆”,而應該說“批書人執筆”。
第四組:第二十三回寫黛玉葬花,庚辰本上有兩條朱筆眉批,一條是:
此圖欲畫之心久矣,誓不遇仙筆不寫,恐褻我顰卿故也。己卯冬。
這是己卯冬的批語,屬脂硯無疑。另一條是丁亥夏畸笏所批:
丁亥春間,偶識一浙省(新)發,其白描美人,真神品物,甚合余意。奈彼因宦緣所纏,無暇,且不能久留都下,未幾南行矣。余至今耿耿,悵然之至。恨與阿顰結一筆墨緣之難若此!嘆嘆!丁亥夏,畸笏叟。
以上這兩組批語,周汝昌先生認為從內容上看,應是同一人所批而前后照應。
為了后文討論的方便,筆者給上述這些有著明顯聯系的成組批語命名為“關聯性批語”。下面我們要來討論一下上面這幾組“關聯性批語”究竟是不是如周先生所斷定的那樣,是同一個人的“自注說明”或“前后照應”。
自從周汝昌先生提出脂畸一人說的四大證據以來,對這些證據進行過認真深入辨析的當屬孫遜先生。孫遜先生在他的《紅樓夢脂評初探》中認為周先生所舉出的第一組和第四組批語屬于“兩方面理解都可以的”,既可以理解成同一個人的前批和后批,也可以理解成兩個人的“相互辯駁攻擊”。孫先生也談到了上述第三組批語,但這組批語的第二條批語他引的是靖批,因為筆者已經限定本文的討論要排除靖藏本的任何影響,因此凡依靠靖藏本資料所得出的結論本文一律不予采用。孫先生對于第二組批語的討論則是這里要重點介紹的。
這組批語的前一條署時為己卯冬夜,是脂硯之批,他認為紅玉是個“奸邪婢”,不配待在怡紅院,所以作者讓她跟鳳姐兒去了,這等于是把她從怡紅院趕走了。后一條批則是畸笏叟在丁亥夏所寫,說己卯冬夜批書人之所以寫下那條指責紅玉的批語,是因為他沒看到后面的抄家和獄神廟等情節。言下之意是,如果他看到了,就不會指責紅玉了。
因相關原稿已迷失,故抄沒及獄神廟情節的具體內容已不可知,但我們從庚辰本第二十回和二十六回的兩條丁亥夏的畸笏批語可以得知其內容之一斑:賈府抄沒后,寶玉、鳳姐等人被拘押在獄神廟,紅玉、茜雪等人曾前去探望慰問。
若按周汝昌先生的脂畸一人說來理解這組批語,則前一條批語是脂硯齋己卯冬夜所批,當時他還沒看到后面的抄沒及獄神廟等情節,所以說紅玉是“奸邪婢”;到丁亥夏,已經改稱畸笏叟的脂硯齋看到了這些情節,所以寫下了第二條批語,解釋一下自己當年為何會斥責紅玉。
但孫遜先生對這種理解進行了有力的反駁,他的主要理由如下:
在脂硯齋的許多早期批語中,他多次提到了八十回后的一些情節,比如庚辰本第二十一回的一條雙行夾批提到了“懸崖撒手”一回,甲戌本第八回一條朱筆眉批、庚辰本第十九回的一條雙行夾批和第二十二回一條“己卯冬夜”的眉批都提到了最后一回的“警幻情榜”。還有,己卯本第四十回前的總目頁上就已經有“脂硯齋凡四閱評過”的題記。另外,從創作時間來看,至己卯冬曹雪芹理應已經完成了全部初稿,以脂硯和他的關系,也不可能沒看到全部的初稿。由此可見,脂硯齋在己卯以及己卯前數次批閱中,肯定已經看到了八十回之后的原稿。因此,認為脂硯在己卯冬夜還沒看到抄沒、獄神廟等情節的說法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竊以為,孫先生提出的這一理由是極有說服力的。由此來看周汝昌先生的觀點,顯然陷入了邏輯上的困境:如果畸笏就是脂硯的話,那他明明己卯年(1759)就已經看過小說全稿,而且應該還看過不止一次,當然也看過抄沒和獄神廟諸情節,為何到丁亥夏(1767)他卻說自己當時還沒看到過這些情節呢?
因此,光是這一條理由,就足以證明脂硯和畸笏絕不可能是同一個人!在這一前提下,我們就可以再來解釋這組批語:脂硯齋對小說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回等回中紅玉的種種表現(對賈蕓有私情、私下傳遞手帕、不安其職、想攀高枝兒)是有所不滿的,故視之為“奸邪婢”,即使他看到過獄神廟等故事情節,他也仍持這種看法。而畸笏叟看到這條批語,覺得脂硯齋不應有這樣的看法,故猜測他寫下此批時應該還沒看到獄神廟的故事,這完全是他個人的主觀臆測。這正跟他看到秦可卿托夢鳳姐的情節,就“姑赦之”,因命雪芹刪去她“淫喪天香樓”的情節一樣,出于類似的心態。
或許主一人說者還會提出質疑說:庚辰本上那些提到八十回后情節的批語都沒有署時間和批者名號,萬一它們都寫于己卯之后呢?這樣不就沒法證明己卯冬夜脂硯齋寫下斥罵紅玉的那條批語時他已經看完了小說全稿了嗎?
這種質疑實際上是很難成立的:就算脂硯即畸笏,就算己卯冬夜脂硯寫那條斥罵紅玉的批語時他還沒看到獄神廟等情節,但兩年半以后的壬午季春他在小說第十八回寫下了那條提到“警幻情榜”的批語,說明他此時已看過了小說全稿,而且壬午夏他又寫了不少批語,其中就有寫在第二十七回的批語,既然此時他肯定已經看過小說全稿,而且他自然也應記得自己寫過那條斥罵紅玉為“奸邪婢”的批語。那這時他為何不說明他己卯冬夜寫下這條批語時尚未看到獄神廟故事,而非要到己卯之后八年的丁亥才說呢?這種情況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脂硯齋和畸笏叟并不是一個人,畸笏在壬午夏日沒有注意到脂硯在己卯冬夜的這條批語,或者雖然看到了,卻沒有產生脂硯寫批時未看過獄神廟故事的想法,直到丁亥年他再評時,才注意到這條批語,產生了這一想法。
或許還會有人提出如下質疑:畸笏批語中不是幾次提到抄沒、獄神廟那幾回原稿被借閱者迷失了嗎?那有沒有可能脂硯(畸笏)自始至終就沒見過這幾回稿子呢?這種說法顯然也是難以成立的:
第一,脂硯齋至己卯、庚辰年已經四次評閱過《石頭記》,對小說的創作進程保持著密切關注,難道抄沒、獄神廟等原稿在脂硯尚未寓目時就被借閱者迷失了嗎?就算他還沒來得及看就被迷失,以他跟雪芹的密切關系,難道他就沒從雪芹口中了解一下迷失部分的情節嗎?
第二,畸笏批語幾次提到抄沒、獄神廟諸事,也提到紅玉、茜雪獄神廟慰問寶玉的事,其中有些批語透露出他知道這些回的具體內容,比如下面這幾條批語:
第二十七回甲戌本上的一條墨筆回后批云:
鳳姐用小紅,可知晴雯等理(埋)沒其人久矣,無怪有私心、私情。且紅玉后有寶玉大得力處,此于千里外伏線也。
同回甲戌本上兩條朱筆側批云:
紅玉今日方遂心如意,卻為寶玉后伏線。
且系本心本意,“獄神廟”回內方見。
可見,畸笏不可能沒看到過抄沒、獄神廟等情節,既然他看到過,那脂硯不管跟畸笏是不是一個人,他當然也應該看過這些情節了。
因此,經過反復推究,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那就是:周汝昌先生所舉出的第二組批語不但不能證明脂畸一人說,反而是脂畸二人說的一條有力證據了。
接下來需要討論一下的是周汝昌先生所舉的第三組評語,即前引與“鳳姐點戲,脂硯執筆”相關的兩條。其一云:
鳳姐點戲,脂硯執筆事,今知者聊聊(當為“寥寥”)矣,不怨夫?
其二云:
前批書(此處當脫一“知”字)者聊聊(當為“寥寥”),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寧不痛乎!
周汝昌先生認為前一條的批者是脂硯齋,這也是很多學者的看法。后一條的批者是畸笏,這也是學界的共識。但周先生認為二批雖署二名,實出一人,主脂畸二人說者則認為二批是出自兩個人。
前文已經提到,孫遜先生認為前一條批的作者并非脂硯,而是畸笏,其理由已如前所述。如果這兩條批語的作者確實都是畸笏的話,那么畸笏在批語中說“鳳姐點戲,脂硯執筆”云云,自然可以說明他跟脂硯不是一個人。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鳳姐點戲,脂硯執筆”這條批到底是誰寫的?這里從以下幾個方面試做討論:
1.孫遜先生指出,如果此批是脂硯所批,那么他不當自稱“脂硯”,而應該自稱“批書人”。筆者翻檢全部脂批,批語中出現“脂硯齋”的共有三處,除了此處討論的這條之外,還有甲戌本第二回一條朱筆眉批,云“且諸公之批,自是諸公眼界;脂齋之批,亦有脂齋取樂處”,這里的“脂齋”顯然是脂硯齋的自稱。此外,庚辰本第十九回還有一條墨筆雙行夾批,云:“脂硯齋所謂‘不知是何心思,始得口出此等不成話之至奇至妙之話’,諸公請如何解得,如何評論?”這顯然是他人轉述脂硯齋評論的口吻,而非脂硯齋自稱。從這些例子來看,批語中出現“脂硯齋”這一名稱,可能是脂硯自稱,也可能不是。另據筆者檢索統計,批書者自稱“批書人”的批語大約有14條,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證明他們的全部自稱都必定會用這一稱謂,而不使用其他的稱謂。因此,孫遜先生這一說法雖然有道理,但也不能憑他所提供的理由而得以成立。
2.這組批語的第二條中有“前批”一詞,周汝昌先生認為這正是畸笏跟脂硯為同一人的證據。因為說“前批”“后批”,正是同一個人說起自己不同時間所寫批語的口氣。筆者檢索全部脂批,共找到9條包含“前批”一詞的批語,確實都是同一個人在提及自己的前后兩批時使用的,且絕大部分都是脂硯寫的,只有一例是畸笏所寫(即這里討論的“前批書者聊聊”)。因此,周先生認為“前批”這個用法可以說明這組批語是出自一人之手的觀點是可以成立的,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同一個人是前脂后畸呢?還是都是畸笏呢?從一般情理而言,如果畸笏是脂硯改號之后的稱號,他應該隱藏自己曾叫脂硯這一事實,不應再以“前批”這樣的說法暴露自己的身份;而且,既然他是在“丁亥夏畸笏”的“后批”里用了“前批”這樣的提法,那逆推一下,這個“前批”自然也應該是畸笏所批,才能算是他所謂的“前批”。但這只是一個推測,無法當成硬證。
總之,目前來看,這組批語的第一條批并不必然如周先生等人所認為的,是脂硯的批語;也難以確證一定是畸笏的批語。但平心而論,畸笏的可能性更大。因此這一條證據只能暫且擱置不用了。如此一來,周先生所提出的四大證據中,有三條是無效的,另一條適足以證明脂畸非一人,而是二人。
(二)脂畸一人說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1.“一芹一脂”如何解釋
周先生首倡的脂畸一人說的一個關鍵點在于:他認為脂硯齋壬午以后改號畸笏,此后再也不署名脂硯了。但是這一關鍵說法需要對以下兩條甲戌本上的著名批語進行合理解釋: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兄,余(奈)不遇獺(癩)頭和尚何!悵悵!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本(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淚筆。
學界對這兩條批語有很多的研究,這里只提一下跟本文的討論有關的兩個問題:
首先,這兩條批語是什么時候寫的?第二批的末尾署了一個“甲午八日淚筆”,“甲午”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此時離曹雪芹辭世已有十一年或十二年。20世紀60年代,曾隨著靖藏本出現過一個所謂的“夕葵書屋殘頁”,上有一條批語,跟上批幾乎完全相同,但末尾署的時間則是“甲申八月淚筆”,“甲申”乃乾隆二十九年(1764),是曹雪芹逝世后的第二年或第三年。本文不擬利用靖藏本的資料來討論問題,因此先不考慮這一署年,而以“甲午八日”為準來進行討論。
其次,這兩條批語的作者是誰?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這兩條前后相接的朱筆眉批顯然出自同一人之手,但出自脂硯還是畸笏?蔡義江先生認為出自畸笏,他還認為批語中所云“余二人”是指畸笏和杏齋。揆諸批語行文,這一說法是講不通的。而且蔡先生立論,也借助了靖藏本批語,故本文不取其觀點。這一批語的作者,包括周汝昌先生在內的很多學者都認為是脂硯,筆者也認同這一看法。
那么,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疑問:既然周先生認為脂硯從壬午(1762)開始改稱畸笏,為何到了十二年之后的“甲午”(1774),他卻又在批語中說“一芹一脂”這樣的話,也就是仍在自稱為“脂硯齋”呢?是他十二年之后又從畸笏改回了脂硯,或者雖然改叫了畸笏,卻心頭筆頭仍不能忘記自己是脂硯呢?更進一步,我們不妨設想一下:這條批語如果要署名,應該怎么署?如果署脂硯,表達上順理成章,但豈不是直接跟周先生的壬午改名說相違背?難道脂硯齋壬午改號為畸笏后,又在甲午改回了脂硯?他為何要這么改來改去,不憚煩若此?如果這條批署畸笏,就更讓周先生的改名說陷入了邏輯上的困境:既然改叫了畸笏、署的也是畸笏,那他為何不說“一芹一畸”,非要說“一芹一脂”?如果他對脂硯這一名號如此難忘難舍,為何還要把它改掉呢?這些矛盾,以周先生為代表的主脂畸一人說者未能進行任何解釋,但如果不能有效解決這些疑問,一人說和改號說都是無從談起的了。
2.為何要署名?以及為何會出現不同的署名?
在《紅樓夢》早期三大抄本所存留下來的數千條批語中,署名者主要有四人:脂硯、梅溪、松齋、畸笏。其中梅溪和松齋各只一條批語。署名脂硯(或脂硯齋、脂研)的大約32條(未署名的脂硯批不計入),大部分都出現在庚辰本的墨筆雙行夾批中,被認為是脂硯齋早期的批語。署名畸笏的批語大概有45條(未署名的畸笏批也不計入),絕大部分為庚辰本朱筆眉批,集中出現在壬午和丁亥,乙酉也有一條。此外,還有一些靖藏本保留的畸笏批語,時間分布在壬午前和丁亥后,但因跟靖藏本有關,此處先不予考慮。
如果我們認同周汝昌先生的脂畸一人說,那么上述的署名現象就有一些不可理解之處:
既然早期抄本叫作《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這說明脂硯齋手中有一個他本人抄錄整理的自用本,有了這個自用本后,他自然應該會一直在上面寫批語,到一定階段,重新整理一遍(包括整理批語,增入雪芹新完成的章回等),形成一個新的自用批閱本。若如周先生所言,脂硯從壬午開始改稱了畸笏,他仍然應該會在他手中的自用本上加批。那么,在自用本上加批,為何還要如此頻繁地署下“畸笏”“畸笏叟”“畸笏老人”這樣的名號呢?他是要跟誰的批語進行區分呢?
中國古代小說的評點史上,也曾出現過同一個人使用不同名號來施加評點的情況,比如評點《型世言》的陸云龍,就曾使用多個化名。但《型世言》刊刻行世,要面對廣大讀者,偽裝多個評點者,多少有些自高身價、促進銷售的作用。但《石頭記》僅在小圈子內流傳,如果主要評點者原本只有一個脂硯齋的話,他為何要改號,又為何要頻頻署名呢?
這種最基本的疑問,持脂畸一人說者從未認真面對,更未加以合理解釋。
二、脂畸二人說的論證及其問題
(一)二人說回顧
主張脂畸二人說的學者主要有俞平伯、吳恩裕、孫遜、趙岡(從一人說轉為二人說)、丁淦、鄭慶山、蔡義江等人。其中丁淦、鄭慶山、蔡義江等先生著重考證了脂硯和畸笏的身份,這無異于認為他們不是一個人。但他們都沒有直接論證二人說的問題,故這里也不作詳細介紹。下文主要討論一下吳恩裕和孫遜兩位先生的觀點。
1972年,吳恩裕先生撰文從兩個方面來論證脂畸為二人:
一是從靖本和他本批語的年代及署名證明脂畸是兩人。這一證明借重了靖本那條“不數年芹溪、脂硯、杏齋諸子皆相繼別去”的批語,因此本文暫不接受這一論證。
二是從批語中對某些人和事物看法的不同來證明脂硯齋、畸笏叟是兩人。吳先生主要利用了前述關于紅玉是否“奸邪婢”的兩條批語以及其他幾條未署名的關于紅玉的批語來探討這一問題。
吳先生對“奸邪婢”二批的討論遠不如后來孫遜先生深入,且又依托未署名批語來立論,故其論證的說服力不足,這里也不再多論。
孫遜先生的《紅樓夢脂評初探》有一部分論證依托了靖本批語,我們也暫不接受其結論,也不作討論。但孫先生意識到了靖批或不可靠,故另從評語的觀點、內容、語氣等方面來尋找脂畸二人說的證據,這個方法跟周汝昌先生用來證明其脂畸一人說的方法是相同的。
他找到的第一個證據乃是周汝昌先生所舉四大證據中的第二組批語,孫先生對這組批語進行了深入考證,最后認為這組批語正足以證明脂畸二人說。筆者對他的論證做了一些補充。這在前文已經詳論,此處不再重復。
他的第二個證據是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寫寶玉酒后續《莊子》處的兩條朱筆眉批:
趁著酒興不禁而續,是作者自站地步處:謂余何人耶,敢續《莊子》?然奇極怪極之筆,從何設想,怎不令人叫絕?己卯冬夜。
這亦暗露玉兄閑窗凈幾、不寂(即)不離之工(功)業。壬午孟夏。
這兩條批語,從所署時間來看,前批可以確定屬脂硯,后批屬畸笏。孫遜先生認為,前批中,脂硯以寶玉的模特兒自居,聲明自己并不敢續《莊子》;后一條批語則完全是不相干的第三者的語氣。因此,兩人口氣之不同是很清楚的。但遺憾的是,孫先生這里對前批的理解存在著一個明顯的失誤:即把批語中的“余”理解成了脂硯的自稱,但這個“余”實際上應理解成脂硯站在作者的立場,來揣測作者的心理,即:作者為了不讓人覺得他狂妄到可以續《莊子》的程度(雖然小說寫的是寶玉續,實際上不還是作者自己續的嗎),于是安排了寶玉趁著酒興來續《莊子》的情節。也就是說,此批如果翻譯成白話,應該是這樣的:
作者寫寶玉趁著酒興,禁不住續了《莊子》。這么寫,是作者給自己留下余地,等于在說:我是什么人,(不趁著酒勁)難道敢續《莊子》?
而且作者似乎覺得這么安排還不夠,后文又安排林黛玉寫了四句詩,嘲笑寶玉續《莊子》之舉是“作踐南華《莊子因》”,庚辰本在此處又有一條脂硯的批語:
又借阿顰詩自相鄙駁,可見余前批不謬。己卯冬夜。
“前批”顯然是指上面說作者“自站地步”的那條批,而這條批在“前批”基礎上進一步認為:作者寫黛玉嘲笑寶玉,其實是作者借此“自相鄙駁”,即自我貶低,說他續《莊子》續得不好,從而不讓人覺得他太狂妄了。
因此,孫先生在誤解的基礎上利用這組批語來論證脂畸二人說,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但他找到這組“關聯性批語”仍然有意義,這一點后文還要再討論。
除此之外,孫先生還找到第十五回的一組“關聯性批語”:小說寫鳳姐接受尼姑的三千兩賄賂,卻表示她并不在意這些銀兩,此處有三條批語,均未署名,但第一條是墨筆雙行夾批(“阿鳳欺人如此”),公認屬于脂硯的早期批語;第二條批是行側批(“欺人太甚”),第三條批是朱筆眉批(“對如是之奸尼,阿鳳不得不如是語”)。孫先生認為這種眉批多為畸笏后期批語,故認為這條批語既跟脂硯批意見不一致,那么自然可以由此斷定他們不是一個人。這一論證中,第三條批的作者存在不確定性,不一定就是畸笏,但他認為這條批的作者跟脂硯不是一個人,這個結論是完全可靠的。
另外,孫先生還找到第十四回的一組“關聯性批語”:小說寫到鳳姐吩咐彩明定造簿冊和念花名冊,這里庚辰本有三條眉批:第一條未署名,誤以為彩明是貼身丫頭(實為男童),批評曹雪芹寫丫頭跟賈府男人交接,是個疏忽;第二條也未署名,嘲笑前一批的作者連彩明是男是女都沒弄清,就瞎批評作者,實在“可笑”;第三條則署“壬午春”,是畸笏的批語,云“且明寫阿鳳不識字之故”。孫先生認為,這三條批語從內容看,顯然出自不同人之手,只要前兩條有一條是脂硯所寫,那么他跟第三條的作者畸笏自然就不是一個人了。
以上兩組“關聯性批語”,孫先生的分析都有一定道理,如果他的分析成立,那么脂畸二人說也能成立;如果他的分析不能成立,且原因在于其中有的批語不能確定批者是誰,那么這兩組批語就不能證明脂畸二人說。但是,他認為這些批語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的結論還是不可動搖的。
這兩組批語既非出自同一人之手,自然出自不同人之手,那么從上述第一組批可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其中有個批者跟脂硯不是一個人;從第二組批也可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其中有個批者跟畸笏不是一個人:如果真如周汝昌先生所言,脂畸是同一個人,從頭到尾,主要的批者就是脂硯(或他的化身畸笏)。那么,這個跟脂硯不同的人,以及這個跟畸笏不同的人,他到底是誰呢?這個問題,是脂畸一人說必須重新考慮,也應該進行回答的。
(二)脂畸二人說面臨的問題
脂畸二人說也面臨著難以解決的矛盾,這一點,俞平伯先生當年就談到過。這矛盾就存在于下面這幾條批語里:
第一條就是“鳳姐點戲,脂硯執筆事,今知者聊聊,(能)不怨乎”,其歸屬或認為是脂硯,或認為是畸笏;第二條批語說“前批書者聊聊,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寧不痛乎”,這被認定是畸笏的批。如果按照脂畸二人說來理解這兩條批,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從中可以看出一個重要信息,那就是到丁亥夏(1767)脂硯已經不在世了。這就跟下面甲戌本第一回這條批語矛盾了: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淚筆。
這條批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是脂硯的。既然脂硯丁亥夏(1767)就已經不在世了,為何他到“甲午八日”(1774)還在寫批語呢?這確實是一個巨大的矛盾。此前,俞平伯、吳恩裕、孫遜等人都利用了靖應鹍所提供的“夕葵書屋殘頁”上所署的“甲申八月淚筆”這個時間來解決上述矛盾。但既然靖本和殘頁都被懷疑作偽,我們現在當然就不應該再用這些資料了。
對于這個問題,筆者試提出以下幾種可能的解釋:
第一種解釋。“甲午八日”這個時間確實是值得高度懷疑的:從庚辰以后,我們就沒再看到過脂硯的批,壬午、乙酉、丁亥的署名批一律都是畸笏的,畸笏的批最晚截止于丁亥。但為何到離丁亥七年之久的甲午突然又冒出來這么一條脂硯的批呢?退一萬步講,就算接受蔡義江先生的說法,認為這條批出自畸笏之手,或者接受周汝昌先生的看法,視脂畸為一人,那么這個疑問也依然存在:即為什么從丁亥到甲午,時隔七年后,他會寫下這么一條孤零零的批?
而如果結合跟以上這條批有緊密關聯的前批“余嘗哭芹,淚亦待盡”來看,更有一疑存焉:雪芹卒于壬午除夕,到甲午已經過去十年有余,十余年之后,批書人竟然還對雪芹之死如此悲傷,似乎也有點不合乎情理。
因此,“甲午”被誤抄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至于正確的文字是什么,就難以妄加推測了。
第二種解釋。“甲午八日”是甲戌本上固有的寫法,胡適曾在這幾個字左側用墨筆批了一句“此是八月”,意思是說“八日”應為“八月”,是抄手把它抄錯了。此后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接受了胡適這一看法。但這里是不是也還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抄手根本就沒有抄錯,原批就是“甲午八日”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甲午”就不能看成年份的干支,而是月份的干支了。“甲午”作為月份,只能是以丙、辛為首的年份的五月。不管曹雪芹逝世于壬午還是癸未,這兩個年份之后,緊接的只有丙戌年(1766)五月的干支是甲午。因此,“甲午八日”就可以理解成丙戌年(1766)的五月八日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以上的矛盾就全都渙然冰釋了。對此,也許會有人表示反對,說:全部脂批中所署的時間就不曾有過這樣的用例,這個甲午也不可能這樣來理解吧。但是,這條批作為人們所認定的脂硯的絕筆之批,特意標明一下月日,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或許,脂硯去世就在這一年,故畸笏在第二年(丁亥)寫了那條“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的批語,以呼應可能是他在壬午年寫下的那條“鳳姐點戲,脂硯執筆”的“前批”。
第三個可能的解釋,那就是,學者們從“鳳姐點戲,脂硯執筆”那兩條“關聯性批語”中得出丁亥夏脂硯已去世的結論或許根本就是錯誤的。這兩條批語如果確如前文所論,都出自畸笏之手,那么它們完全可以理解成:那知道“鳳姐點戲,脂硯執筆”的寥寥數人中,其實是不包括脂硯本人的。脂硯本人是其他人“知”的對象,畸笏所說的寥寥數人,是指脂硯之外的其他人。這些人到丁亥夏只剩下他畸笏這一枚朽物了。
不過,以上都是筆者的猜測而已,并無任何確鑿證據。因此,脂畸二人說面對的問題依然存在,這也是這一觀點唯一的障礙。
三、關聯性批語:對脂畸二人說的進一步論證
周汝昌和孫遜先生在論證脂畸一人說或二人說時,都利用了批語中的“關聯性批語”。其實,在批語中還有不少“關聯性批語”,利用這些批語,我們還可以對脂畸二人說作進一步的論證。
(一)第十八回寫到寶釵跟寶玉說:“唐錢珝詠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煙綠蠟干’,你都忘了不成?”庚辰本此處有墨筆雙行夾批云:“此等處便用硬證實處,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何心思,是從何落想,穿插到如此玲瓏錦繡地步。”這自然是脂硯較早的批。在這一頁上,還有一條朱筆眉批云:“如此穿插安得不令人拍案叫絕!壬午季春。”既署“壬午季春”,這是畸笏的批無疑。我們仔細觀察后可以看到:前一批說“穿插到如此玲瓏錦繡地步”,是夸作者穿插筆法用得精巧;后一批同樣夸作者的穿插筆法,但措辭不一樣。試問:如果脂硯、畸笏是同一個人,他對同一個筆法,夸過一次了,還用得著再夸一次嗎?如果認為脂畸是兩個人,那么這一不合理之處就不存在了:畸笏看到脂硯夸作者,他也表示贊同與附和,說了一句差不多的話,這就順理成章了。
(二)第十八回寫到林黛玉替寶玉作詩處。庚辰本上有一條墨筆雙行夾批云:“寫黛卿之情思,待寶玉卻又如此,是與前文特犯不犯之處。”同頁有一條朱筆眉批云:“偏又寫一樣,是何心意構思而得?畸笏。”前一條應是脂硯較早之批,是說黛玉也跟寶釵一樣,想到要幫寶玉作詩,這種寫法叫作“特犯不犯”,這是借自金圣嘆的一個批點術語,是指某個情節跟前面的情節同中有異。后一條批是畸笏的,顯然是看了脂硯的“特犯不犯”之后,表示同意,說偏又寫得一樣,即對“特犯”之意表示了贊同和附和。試問:如果脂硯和畸笏是一個人,這后一批還有何必要?
(三)第十九回,寫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縱坐了,也沒甚趣。”此處庚辰本有一條墨筆雙行夾批說:“調侃不淺,然在襲人能作是語,實可愛可敬可服之至,所謂“花解語”也。”同頁上有一條朱筆眉批說:“‘花解語’一段,乃襲卿滿心滿意將玉兄為終身得靠,千妥萬當,故有是。余閱至此,余為襲卿一嘆。丁亥春。畸笏叟。”前一批當為脂硯早期之批,對襲人本分明理的答話表示贊賞,認為這就是“花解語”的含義之所在;此后畸笏丁亥的批也關注“花解語”一段,這應該是受到脂批的影響,就此情節談他的看法,但他的看法顯然跟前一批不同:襲人原本滿心滿意、死心塌地追隨寶玉,最后卻不得不琵琶別抱,嫁了蔣玉菡,故畸笏要為襲人一嘆。
(四)第二十一回寫湘云發現寶玉頭發上的四顆珠子丟了一顆,就說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不防被人揀了去,到便宜他。”庚辰本此處有一條墨筆雙行夾批云:“妙談!道‘到便宜他’四字,是大家千金口吻。近日多用‘可惜了的’四字。今失一珠,不聞此四字。妙極!是極!”同一頁上有一條署名畸笏的朱筆眉批說:“‘到便宜他’四字與‘忘了’二字是一氣而來,將一侯府千金白描矣。畸笏。”我們看到,這兩條批除了關注點一致,表達的內容也差不多相同,都是指出“到便宜他”這句話寫出了湘云這么一個千金小姐的身份。畸笏的批語跟脂硯批語的前一半基本上是重復的(僅多提了一下湘云說的“如今我忘了”這句話),如果是同一人寫的,則何必如此重復呢?但如果理解成畸笏對脂硯表示贊同與附和,那就沒有任何問題了。
(五)第二十一回寫黛玉見寶玉續《莊子》,便作詩嘲諷。此處庚辰本上有四條批語:其中一條墨筆雙行夾批和一條朱筆眉批,都出自脂硯之手無疑。這條朱筆眉批云:“又借阿顰詩自相鄙駁,可見余前批不謬。己卯冬夜。”
此處還有一條朱筆側批云:“不用(‘用’或當作‘寫’)寶玉見此詩若長若短,亦是大手法。”此批未署名號和時間,但可以證明為脂硯所批:后面第二十二回寫到寶玉參禪而遭黛玉、寶釵盤詰嘲笑處,有一條己卯冬夜的朱筆眉批云:“前以《莊子》為引,故偶續之。又借顰兒詩一鄙駁,兼不寫著落,以為瞞過看官矣……”此批也作于己卯冬夜,自然是脂硯批,其中提到的“又借顰兒詩一鄙駁”顯然是指上引己卯冬夜批語中的“又借阿顰詩自相鄙駁”這句話無疑;“兼不寫著落”一句則是指“不用(‘用’或當作‘寫’)寶玉見此詩若長若短”這一句無疑。如前所言,這一句批語未署時間和名號,但我們從三處批語的時間關聯可以斷定:這句批語既在己卯冬夜被脂硯跟另一條他同在己卯冬夜寫的批語相提并論,那么它一定也是脂硯在己卯冬夜或之前所批,而己卯所批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確定“不用寶玉見此詩若長若短,亦是大手法”這條批的作者為脂硯后,我們再來看一下庚辰本上隔頁的一條朱筆眉批:“寶玉不見詩,是后文余步也,《石頭記》得力所在。丁亥夏。畸笏叟。”很顯然,這條批語是畸笏看了脂硯“不用寶玉見此詩若長若短”這條批語之后,表示贊同附和而寫的,意思跟脂硯的批也差不多,只不過略微具體了一些。如果畸笏就是脂硯,這種對自己之前批語的贊同附和就是一種重復,實在看不出有什么必要。
(六)第二十一回寫賈璉跟多姑娘兒偷情,那媳婦越浪,賈璉越丑態畢露。此處庚辰本上有一條朱筆眉批云:“一部書中,只有此一段丑極太露之文,寫于賈璉身上。己卯冬夜。”同頁又有一條朱筆眉批云:“看官熟思:寫珍、璉輩當以何等文方妥方恰也?壬午孟夏。”我們可以看到,前一批(脂硯所批)明白地說了:這一段“丑極太露之文”放在賈璉身上“恰極當極”。后一批(畸笏所批)則讓看官好好想想:寫賈珍、賈璉之流該用什么文字才妥當呢?這無異于又在贊同脂硯那句批語了,只不過換了一種表達方式而已。試問:如果畸笏就是脂硯,他有何必要如此自我贊同和重復呢?
(七)第二十二回寫鳳姐說那個小旦像一個人,眾人都不吭聲,只有史湘云笑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樣兒。”此處庚辰本上有一條墨筆雙行夾批云:“口直心快,無有不可說之事。”這是脂硯早期的批語。同頁上又有一條朱筆側批:“事無不可對人言。”這條批未署名,但是朱筆側批,為脂硯所寫的可能性比較大。這暫且不談,再來看一下同頁另一條朱筆眉批:“湘云、探春二卿,正‘事無不可對人言’芳(之)性。丁亥夏。畸笏叟。”這條畸笏的批語又一次重復甚至照抄了前一條朱筆側批,如果這條朱筆側批也是他自己寫下的,那么他為何又要來重復自己?這也反過來證明前一條批絕不會是畸笏所寫。既不是畸笏所寫,那脂硯所寫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脂硯所寫的可能性更大,則脂畸為二人的可能性也相應地更大了。
(八)第二十七回寫寶玉聽到黛玉泣吟《葬花詞》,甲戌本此處有一條無署名朱筆眉批云:“‘開生面’、‘立新場’,是書多多矣,惟此回處(“處”當作“更”)生更新。非顰兒斷無是佳吟,非石兄斷無是情聆。難為了作者了,故留數字以慰之。”庚辰本此處則有一條署名畸笏的朱筆眉批:“‘開生面’、‘立新場’,是書不止‘紅樓夢’一回,惟是回更生更新,且讀去非阿顰無是佳吟,非石兄斷無是章法行文,愧殺古今小說家也。畸笏。”
比較此二批,可以發現它們原本應該是畸笏一條批語的兩個不同版本,這兩個版本的文字同中有異,差異還不小。從這一現象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和推測:
第一,甲戌本上的“難為了作者了,故留數字以慰之”這一句話說明,畸笏寫這條批語時,作者曹雪芹還在世。而目前所見署名畸笏的批語,主要集中于壬午和丁亥,乙酉僅存一條。壬午時,雪芹還在世;乙酉和丁亥時,雪芹已去世。故這條批語的寫作時間可以推定為壬午。
那么,這條批語是批在哪個本子上呢?前輩學者吳恩裕先生認為:這條批語是“留”給作者雪芹的,“慰”也是慰作者雪芹,當然也是批在雪芹自己的稿本上。聯系庚辰本第二十一回一條朱筆眉批所云“壬午九月,因索書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頭記》也”云云,吳先生認為,壬午九月,畸笏就把稿本還給了雪芹。所以我們看到畸笏壬午的批語截止到了壬午重陽日。壬午從春到秋,雪芹稿本一直在畸笏手里。
第二,為什么后來畸笏要把“難為了作者了,故留數字以慰之”兩句改成“非石兄斷無是章法行文,愧殺古今小說家也”呢?吳先生認為,甲戌本的這條批語寫得比較早,是畸笏跟雪芹之間的個人交流。后來庚辰本上的批語要面向讀者,所以作了刪改。
吳先生的說法值得商榷。如果我們仔細研究批語,將會發現:畸笏壬午寫批的這個本子上應該有脂硯己卯寫下的批語,因為畸笏壬午批語有的跟脂硯己卯批語有著十分明顯的關聯,如上面第6條所論。另外,畸笏丁亥的有些批語跟脂硯己卯的批也形成了緊密關聯(如第二十三回庚辰本那兩條提到要畫黛玉葬花圖的朱筆眉批)。由此看來,這個本子似乎是脂硯的批閱本,畸笏壬午批閱的也是這同一個本子。而且,以常理來推斷,脂硯在自己擁有批閱本的情況下,也不應又把雪芹的稿本拿來寫批,而后這個本子又被畸笏借去批閱半年之久。如此一來,我們似乎應該考慮如下的可能性:那就是畸笏借閱的是脂硯手中的本子,壬午九月“索書甚迫”的也應該是脂硯。考慮到脂硯跟雪芹的密切關系,畸笏認為他寫在這個本子上以慰勞雪芹的批語雪芹應該會看到,或者脂硯會轉告他。
在脂硯去世之后,這部稿本可能轉入了畸笏之手,畸笏對自己壬午所寫之批做了一些修改,其中之一就是把“難為了作者了,故留數字以慰之”兩句改成了“非石兄斷無是章法行文,愧殺古今小說家也”,因為此時雪芹已經去世,他覺得原來的批語已經無法告慰死者,于是做了修改。
以上兩說,孰是孰非難以遽斷。如果吳恩裕先生的觀點可以成立,則我們可以由此推斷:畸笏和脂硯絕不可能是一個人。其理由是:
己卯冬月和庚辰秋月的定本上都題寫了“脂硯齋凡四閱評過”的字樣,且己卯、庚辰本(也包括“甲戌本”)每回回目前都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題名,“甲戌本”上也有一句話: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另外,“甲戌本”所存十六回每頁中縫都有“脂硯齋”三字——凡此皆說明:脂硯齋手頭至少有一部他親手抄閱加批的《石頭記》。這就意味著,他不必去借閱雪芹自己的稿本,更不可能一借就是半年多(從壬午春到壬午重陽日)。因此,壬午年借閱雪芹稿本并寫下慰勞之語的人,借閱書稿半年多、以致作者“索書甚迫”的人,絕不會是脂硯或脂硯的化身畸笏,而是一個跟脂硯完全不同的畸笏!
而如果筆者的觀點可以成立,則同樣也可以推斷:脂硯和畸笏絕不會是同一個人。道理很簡單:借書、還書這種事當然是發生在不同的兩個人之間才是合理的,難道畸笏會自己跟自己借書、還書嗎?
總之,這里最不可能的就是脂硯和畸笏是同一人!如果他們是同一人,那么其手頭自然有一部或一部以上的抄閱評點本,為何還要找作者(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是作者了)借閱書稿,一借就是半年多呢?
四、另兩條新證據
第一條新證據。熟悉《紅樓夢》各抄本情況的人都知道如下一個特別的事實:庚辰本第二十二回結尾是殘缺的。這一回寫賈母帶著眾人猜燈謎,她命賈政猜猜幾位姑娘所制謎語,賈政一連猜出了元春、迎春、探春的謎語,但當他看到第四個謎語時,小說只寫出了此謎的謎面,就戛然而止,沒了下文。庚辰本在此謎上方有一條朱筆眉批云:“此后破失,俟再補。”隔一頁則有墨筆所寫的兩條批,其一為“暫記寶釵制謎:朝罷誰攜兩袖煙……”云云;其二則為“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丁亥夏畸笏叟”。
在《紅樓夢》各抄本和刻本中,甲戌本、己卯本、鄭藏本均無此回,可不討論。其他各主要版本中此回結尾的情況如下:
1.列藏本大致同庚辰本,但無朱筆眉批和兩條墨批;
2.蒙府本、戚序本、舒序本此回有完整結尾,寫賈政猜出了惜春的謎底,但還沒猜出寶釵的謎語,賈母就讓他歇息去了。
需要注意的是,惜春的謎是賈政所猜的第四個謎,但庚辰本正文沒說這是惜春的謎,只有該謎最后一句下的雙行小字批語說“此惜春為尼之讖也”。
3.甲辰本此回也有結尾,但無惜春燈謎,并把庚辰本上所記寶釵燈謎放到了黛玉名下,還給出了謎底。又制“鏡”謎,歸于寶玉;制“竹夫人”謎,歸于寶釵。另有簡短結尾。
4.程甲本和楊藏本此回結尾把甲辰本和戚序本的結尾融合為一,看上去比較完滿,卻發生了很大的矛盾:因為明明寫到了寶玉做了“鏡”謎,后文卻又寫鳳姐打趣寶玉說剛才忘了攛掇老爺命你也制一個詩謎兒。
紅學界對于這些結尾的看法大致可分為三派:一派以梅節為代表,認為甲辰本此回結尾是作者原稿,其他各本則不是。他的說法遭到了蔡義江先生的有力反駁,顯然難以成立。第二派以蔡義江先生為代表,認為庚辰、列藏之外各本此回結尾均為后人所補。第三派以張愛玲為代表,認為戚序本“此回可靠,是最早的早本”,即曹雪芹的原稿了。
筆者贊同張愛玲的看法。但她的理由比較薄弱:只指出戚序本這個結尾中賈政說話用到了“嗄”這個道地蘇白,充分顯示此回可靠。筆者相信張愛玲不只是根據這個語氣詞做出了上述判斷,她真正靠的應該還是她敏銳的文學感覺。的確,戚序本這個結尾無論是文字的生動、情節的周密和敘事的高明,還是賈政、鳳姐、寶釵、寶玉、賈母等人的言行和心理特點,都無不跟曹雪芹的原稿手筆極度符合。尤其是寫賈政離開后,寶玉頑劣之態復萌,寶釵委婉規勸,鳳姐嘲笑打趣,都跟這些人物一貫的性格特征完全一致,也體現出曹雪芹文筆傳神的特色。這絕不是其他人所能做到的。
但上述結論是憑借文學感受力而得出的,難以成為令人信服的論證。因此戚序本此回結尾為曹雪芹原稿的看法在此只作為一種可能性來對待。也就是說,在這一可能性成立的基礎上,我們再來看看脂硯和畸笏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有一個基本的事實可以先確認:雪芹原稿中的第二十二回肯定有過完整的結尾,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第二個可以確認的事實是:脂硯齋肯定看過這個完整的結尾,他的抄閱本也應該有此完整的結尾。理由是:現存庚辰本在元春、迎春、探春的燈謎下都有一段脂硯的批語,指出謎語對制謎人未來命運的暗示。在探春謎語后,寫到賈政看了第四個謎語的謎面,此后就沒有下文了。我們看不到這個謎語是誰制的,也不知道謎底是什么。但這個謎面下面同樣有一句脂批云:“此惜春為尼之讖也。公府千金至緇衣乞食,寧不悲乎!”脂硯寫出這句批語,說明他看到過下文——也就是此回的完整結尾。如果他從一開始就沒看到過這個結尾,他憑什么如此肯定地說:這個謎語預示著惜春將來要出家為尼呢?脂硯齋曾至少四次評閱過《石頭記》,如果他最早(甲戌之前)看到第二十二回時,其結尾就是殘缺的,那他為何不督促雪芹修補一下殘缺,以至于如此靠前的一回在他初評、再評、三評、四評時都維持著殘缺的狀態呢?我們確實很難相信,此回殘缺后的若干年中,雪芹竟然一直沒補上這個原已寫出、只是后來丟失了的一段小尾巴!這跟第七十五回缺中秋詩的情況并不一樣:第七十五回比較靠后,且中秋詩原來就未寫出,雪芹去世前沒來得及補上,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筆者認為,脂硯評閱過第二十二回的結尾部分,這個結尾在他手頭的批閱本中原本也是存在的。我們無法想象這個結尾在雪芹原稿中就已經丟失、以至于脂硯都沒來得及抄入他的評閱本中這種情況。
庚辰本在惜春謎語上方有一條朱筆眉批:“此后破失,俟再補。”這指的應該是他手頭的批閱本中這個結尾“破失”了,要再補抄一下——只有本來就有,但后來紙張破損而文字丟失,這才叫“破失”;也只有曾經抄錄過,現在又要重抄一次,才能叫“再”補。他絕不可能是在說雪芹原稿此回結尾即已“破失”,要等雪芹來補寫!請注意:“破失”這個詞,其意思除了丟失之外,顯然還有作為文字載體的紙張破損之意。而說紙張破損,只能是指批語所在的稿本紙張破損,且看到此批語的人也能看到書稿紙張破損,這么說才有意義,否則誰知道是什么“破”了呢?若是雪芹原稿紙張破損,又何必要在脂硯的批閱本上提起?他何不說得更明白一點,說此后原稿破失?因此,“此后破失”一句,理解成脂硯的批閱本從惜春謎語后破毀丟失了,是最自然的。另,庚辰本上的這種朱筆眉批公認是比較晚出的批語,或晚于庚辰秋月之后。因此,第二十二回結尾的“破失”很可能就是發生在庚辰秋月之后。我們今天看到的庚辰本(實為庚辰本的過錄本)把殘缺的結尾和提示這一殘缺的批語都照錄了。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推出如下兩個可能性:第一,雪芹手中原稿上的第二十二回,應該是有完整結尾的。后來的戚序本、蒙府本、舒序本就保留了這個結尾。第二,脂硯齋當然知道雪芹寫出了這個結尾,也知道他的原稿上有這個完整的結尾。既然如此,在丁亥夏寫下“此回未成而芹逝矣”的畸笏叟,自然就不可能是脂硯!“未成”是尚未完成,是根本就沒寫完過,這跟寫成了而“破失”的意思截然不同;而更重要的則是,雪芹不但寫成了這個結尾,還流傳下來了。但畸笏卻對這一情況全然不知,竟然說雪芹未寫成就去世了!
那么,畸笏為什么會說這么一句話呢?筆者的猜測是:他手頭拿著的《石頭記》應該正是脂硯尚未補抄上這個“破失”結尾的本子。因為他跟雪芹的關系應不如脂硯跟雪芹的關系那么密切,故他對于二十二回結尾的情況并不是很了然,看到那條“此后破失,俟再補”的眉批,又看到依然殘缺的結尾,所以就說了一句有違事實的話。
第二條新證據。庚辰本第二十一回有一條墨筆雙行小字批語云:“……寶玉有此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后文方有‘懸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寶釵之妻、麝月之婢,豈能棄而為僧哉?此寶玉一生偏僻處。”這是脂硯的早期批語,從中可知他看過“懸崖撒手”一回,知道具體內容。但庚辰本第二十五回另有一條朱筆眉批則云:“嘆不能得見寶玉‘懸崖撒手’文字為恨。丁亥夏,畸笏叟。”從中可見畸笏沒看過“懸崖撒手”一回。那么他跟脂硯怎會是一個人?
總之,經過以上論證,筆者認為:脂硯齋和畸笏叟是兩個人的可能性要遠超過他們是一個人的可能性。二人說面臨的唯一困難就是“甲午八日淚筆”這條批語。而一人說面臨的困難則比二人說要多得多。因此,本文的結論是:一人說應不能成立,二人說雖還存在一些困難,但可能性極大。
① 俞平伯《俞平伯論〈紅樓夢〉》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27頁。
② 第二十二回鳳姐點戲處,靖藏本上有眉批云:“前批書者寥寥,芹溪、脂硯、杏齋諸子皆相繼別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寧不痛乎(殺)!”因這條批語公認是畸笏所寫,故成為脂畸二人說的鐵證。
③ 見裴世安、柏秀英、沈柏松輯“紅學論爭專題資料庫”第1輯《靖本資料》,2005年版。此文乃俞平伯先生未刊遺文。
④[19] 趙岡、陳鐘毅《紅樓夢新探》,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112、110—112頁。
⑤ 此類文章可參見前揭《靖本資料》。
⑥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增訂本)下冊第九章第一節“脂批概況”,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709—718頁。此書初版于1953年9月。對于脂畸一人說之論證,增訂本與初版本并無區別。
⑦ 吳世昌《論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構成、年代和評語》,《吳世昌全集》第八卷《紅樓夢探源外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186頁。
⑧ 庚辰本上的墨筆雙行夾批是隨正文一起抄寫的,以雙行小字形式系于相應的正文之下,非在正文之側,也不在書眉之上,這一位置說明這類批語是脂硯齋(也有別人的批語,但極少)早期所寫,這一點紅學界基本達成了共識。
⑨ 本文所引庚辰本批語皆據《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影印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后不再一一出注。
⑩[15][17]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增訂本)下冊,第713、714、21頁。
[11][12][21] 孫遜《紅樓夢脂評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4、51—52、44—46頁。
[13] 本文所引甲戌本批語皆據《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影印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后不再一一出注。
[14] 蔡義江先生也持同樣的看法,參見《脂評選釋》“第二十二回”,收入《蔡義江論紅樓夢》,寧波出版社1997年版。
[16] 參見《脂評選釋》“第一回”,《蔡義江論紅樓夢》。
[18] 周先生也注意到了“一芹一脂”的問題,但他徑直認定“一脂”即畸笏,并不認為這種表述跟他的主張有矛盾。參見周祜昌、周汝昌合著《石頭記鑒真》,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210頁。
[20] 參見《吳恩裕文集》第五卷《曹雪芹叢考》,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324—332頁。
[22] 筆者寫完此段論述后一日,偶閱吳恩裕先生文集中《“壬午九月索書甚迫”解》一篇,發現吳先生早已提出相同的看法。因確屬本人思考所得,偶合前賢高見,故仍予保留。
[23] 參見《記“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的批語》,《俞平伯論〈紅樓夢〉》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3、1114頁。此文寫于1964年,發表于1979年。
[24] 以上兩個疑問乃筆者自己思索而得,后拜讀俞平伯先生《記“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的批語》一文,看到他多年前就已經提出同樣的疑問,并做了精辟的論述。
[25] 俞平伯先生《記“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的批語》一文認為:脂硯“甲申八月”尚有批語,蓋卒于乙酉。同上,第1128頁。但“甲申八月”之說來自毛、靖二人所提供的可疑材料,故俞先生的觀點暫且為筆者所不取。
[26] 這句批中的“前批”是指庚辰本上第二十一回另一條己卯冬夜的朱筆眉批,提到作者寫寶玉趁著酒興續《莊子》是自站地步云云,前文已引,并作討論。
[27] 吳恩裕先生也認為此批寫于壬午,但未作論證。見《吳恩裕文集》第五冊《曹雪芹叢考》,第343—345頁。
[28][29] 吳恩裕《“壬午九月索書甚迫”解》,《吳恩裕文集》第五冊《曹雪芹叢考》,第341—345及373—375、45頁。
[30] 吳恩裕先生的解釋跟筆者頗不同,見《吳恩裕文集》第五冊《曹雪芹叢考》,第345頁。蔡義江先生提出過相同的看法,見于他的《畸笏叟考》,《紅樓夢學刊》2004年第1輯。
[31] 下文的介紹參考了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77頁;王旭初《惜春詩謎與二十二回結尾關系新說》,《紅樓夢學刊》2012年第2輯。
[32][33] 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76—190、177頁。
[34] 張愛玲《紅樓夢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47頁。
[35] 蔡義江先生認為“破失”的是雪芹原稿,參見《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第179頁。對這一看法筆者不敢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