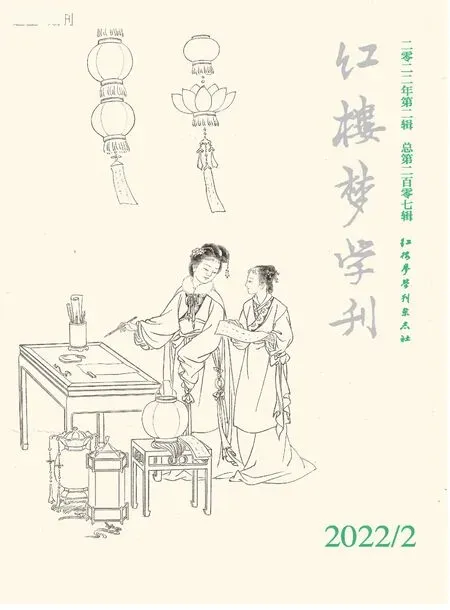從《申報》所刊戲劇廣告看民國上海京劇紅樓戲的誕生
吳雨彤
內容提要:民國時期,新劇紅樓戲在上海蓬勃發展,春柳劇場·新劇同志會及新民新劇社編演的一系列新劇紅樓戲掀起熱潮。1915年6月13日,春柳劇場·新劇同志會推出的“古裝歌劇”《黛玉葬花》標志著民國京劇紅樓戲的起點,而1916年秋冬梅蘭芳在滬演出其新編的紅樓戲可視為京劇紅樓戲取得的新發展。1915年6月至1917年2月,新民及春柳相繼解散,新劇中興之后的紅樓戲開始轉向民鳴社又最終穩定在笑舞臺,而笑舞臺的紅樓戲以歐陽予倩為絕對的中心。整體上,上海的紅樓戲演出呈現出新劇與京劇并行、且主導地位逐漸向京劇轉移的傾向。
民國時期的紅樓戲在上海隨著早期話劇——“新劇”的蓬勃發展應運而生。《申報》戲劇廣告中最早出現的新劇紅樓戲上演記錄是1913年11月28日新民新劇社的《鴛鴦劍》,以此為發端,新民社陸續推出《風月寶鑒》《大鬧寧國府》及《夏金桂》,共四部紅樓戲。1914年4月起春柳劇場·新劇同志會開始在上海謀得利演出,也編演了《鴛鴦劍》《王熙鳳大鬧寧國府》《林黛玉焚稿》《夏金桂自焚記》《風月寶鑒》《劉老老進大觀園》《晴雯》等一系列紅樓戲。民國初期上海的紅樓戲編演數目不少,上演次數也很多,且主要集中在新劇界,以新民社及春柳劇場·新劇同志會為個中翹楚。然而好景不長,1915年1月,新民社被民鳴社吞并;春柳劇場·新劇同志會在1915年春季經歷了幾度人事變動后也已大廈將傾,終于在1915年秋陸鏡若英年早逝之后走向消亡。從1913年11月新民社首演《鴛鴦劍》開始至新民被吞并、春柳在1915年6月25日與民鳴合演《鴛鴦劍連演寧國府》作為其紅樓戲絕唱為止,可以劃作民國時期上海紅樓戲發展的第一階段:新劇獨占鰲頭,且編演內容傾向于寶黛故事以外的人物及相對獨立的劇情。關于民國早期紅樓戲的出現,詳見拙論《民國紅樓戲之新劇先聲》。在此之后,紅樓戲的發展所呈現的態勢、與第一階段的異同還有待仔細梳理。
本文試從《申報》所刊戲劇廣告入手,結合當時劇人發表在報刊雜志的劇評及后期的回憶性文章,分析新劇中興以來紅樓戲的第一波熱潮之后——即春柳劇場·新劇同志會面臨解散、歐陽予倩演出第一部京劇紅樓戲《黛玉葬花》起至梅蘭芳第三次來滬演出為止——上海紅樓戲的具體上演狀況。本文將以時間軸為縱線,以演出紅樓戲的主要劇場及編演紅樓戲的主要劇人為中心,探索這一時期上海紅樓戲新舊交融的具體上演情況。
本文將1915年6月至1917年2月劃分為民國紅樓戲的第二階段,實際劃分的標準不是單純的時間線,而是演劇界的具體事件及紅樓戲演出的發展階段。春柳劇場實際解散是1915年秋,但在此之前其分崩離析之勢業已出現。歐陽予倩1915年4月暫別春柳轉簽第一臺開始演出京劇,這一事件看似與紅樓戲無關,但卻從根本上對上海紅樓戲的發展方向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1915年6月3日,重回春柳的歐陽予倩在春柳劇場首演其“歌劇”作品《黛玉葬花》,這正是上海首次演出的京劇紅樓戲,以此為起點,上海紅樓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當前學界多用“文明戲”一詞來指代早期話劇,但在這一時期無論在戲劇廣告上還是劇學論著中仍多用“新劇”稱之,故本文中除廣告原文外一律用“新劇”以便于行文。此外,《申報》廣告中出現了“古裝歌劇”這一概念,如歐陽予倩先后在春柳、民鳴、第一臺等劇場都曾演過的《黛玉葬花》。現代漢語中的“歌劇”為西方Opera,但西方Opera在中國普遍上演之前,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以前多稱Opera為“樂劇”、或音譯為“奧披剌”“歐拍拉”“阿別拉”等,即使少數稱“歌劇”,也會加上限定詞如“西方歌劇”或“德國歌劇”“法國歌劇”等以示區別;歐陽予倩所用的“歌劇”一詞大約表示其采用新式舞臺表現手段但以戲曲歌唱為該劇的主要表現方式;此外,因新劇不唱或幾乎不唱,故“歌劇”有時也指代京劇等傳統戲曲,如春柳劇場的“余興”曾有《朱砂痣》《御碑亭》等“歌劇”,有時“戲中串戲”也常唱“歌劇”。本文除引用文獻外,均以是否采用傳統戲曲演唱為主要表現方式為判斷標準,將紅樓戲二分為新劇與傳統戲曲,而本文中出現的劇目未發現京劇以外的劇種,故統稱新劇與京劇以分別之。
一、民鳴社一家獨大:“后春柳時代”的新劇紅樓戲演出(1915年6月-1917年1月)
王鳳霞《文明戲考論》中將民鳴社的演出分為五個階段。每個階段內,民鳴社的紅樓戲演出都因發展狀況、人員流動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第一階段:自1913年11月成立至1915年1月之前,此為民鳴社與新民社競演時期。其間民鳴社的紅樓戲只有1914年2月15日至17日演出的許嘯天編《紅樓夢》一部,該劇由“王熙鳳毒設相思局”“賈璉偷娶尤二姐”“縱淫心金桂自戕生”三段構成。
第二階段:自1915年1月19日與新民社合并至1916年3月8日的演劇時期。1915年6月之后,春柳劇場逐步分崩離析,吞并了新民社的民鳴社在一段時間內幾乎可執上海新劇之牛耳。吸收了大量新民及春柳的優秀劇人之后,紅樓戲更是幾乎被民鳴社獨攬。整體看來,民鳴社演出紅樓戲最多的時期也正是這一階段。
從1915年6月25日的《鴛鴦劍連演寧國府》開始,歐陽予倩、吳我尊、汪優游、查天影等曾經春柳·新劇同志會演出紅樓戲的中堅力量及鄭正秋等原新民社元老開始在民鳴演出,民鳴社也就此邁出了正式進軍新劇紅樓戲的第一步。
1915年6月26日至1916年3月8日,民鳴社演出《鴛鴦劍》《大鬧寧國府》《劉老老進大觀園》《王熙鳳毒設相思局》《金釧兒投井》五部紅樓新劇共13次。其中,《鴛鴦劍》《大鬧寧國府》應該是已經在春柳劇場上演過的作品,《劉老老進大觀園》(1915年7月17日首演)和《金釧兒投井》(1916年3月4日首演)的廣告中則明確寫出是民鳴社新作。但民鳴社在這一階段演出的《王熙鳳毒設相思局》究竟是新作還是之前新民和春柳演過的《風月寶鑒》,抑或是之前民鳴演過的許嘯天《紅樓夢》的三部曲中“王熙鳳毒設相思局”單獨上演,廣告中則并未言明。
新劇的演出基本以幕表制為主,僅以必要的劇情為大綱。依靠幕表排戲,演員自由發揮的成分很高,即使是同一劇團同一批演員上演同一劇目,很有可能每次演出的細節都不盡相同,因此,除非有很明確的大幅度的情節增刪,否則很難用以劇本和導演為中心的現代劇場觀念去縱向研究、拘泥于某一劇目演出的異同;而紅樓戲因其以小說為基礎,很多臺詞可以直接從小說中挪用,相對來說情節等比較固定,各劇團縱有同名或相近、即從劇名可以明顯看出是根據小說同樣章節改編而來的劇目,其相似度應該較高,因此,橫向探討各劇團上演的不同“版本”,尤其是在劇本不存的前提下,也意義不大。但此處仍想要對劇目做出簡單探究,從中試圖厘清新劇紅樓戲的傳播和發展脈絡。
首先,民鳴社《王熙鳳毒設相思局》廣告中并未像《劉老老》和《金釧兒》一樣標注“新作”等字樣以借機宣傳,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民鳴新編的可能性;其次,這一時期擔綱演出紅樓戲的主要是歐陽予倩等春柳劇人和鄭正秋等新民主力,且根據小說同樣章節改編的新劇《風月寶鑒》早已在兩大劇場上演過,為紅樓名作,故演出此作的可能性較許嘯天作更高,當然也不排除這一時期在民鳴社上演的過程中吸收之前排演許嘯天作的經驗進行調整的可能。
民鳴社雖為新劇團體,但歐陽予倩等春柳劇人加入之后,1915年7月15日以查天影臨別紀念的名義演出曾經只有1915年6月13日在春柳劇場演過一次的“新編歌劇”《林黛玉葬花》。扮演寶玉的自然是查天影,14日起刊登的廣告中寫扮演黛玉的是歐陽予倩,15日實際上演時改定由凌憐影演黛玉,歐陽予倩演王熙鳳。通常所演《葬花》為林黛玉葬花傷春一節,是沒有賈母與王熙鳳登場的,而15日廣告中寫著這一次演的是“自別父起至葬花止”,似比通常所見的《葬花》篇幅更長,包含林黛玉進賈府情節。或許不過是在新作調整中的嘗試,這一短暫的改動在之后的《葬花》中沒有得到保留。而9月1日以歡迎查天影回申的名義及10月16日,民鳴社又演過兩次《林黛玉葬花》,但歐陽予倩已于8月離開民鳴社,故這兩次演出沒有歐陽予倩的參與。
1915年12月,顧無為因政治原因被捕,歐陽予倩于1915年12月中旬離開民鳴社去第一臺搭班唱京劇,民鳴社在失去主心骨及紅樓戲主力之后勉強支撐,紅樓戲的演出也暫且擱置。但1916年1月29日,在鄭正秋、查天影、汪優游、張嘯天等人的努力下,民鳴社重啟紅樓戲《王熙鳳毒設相思局》,3月4日又推一部新作《金釧兒投井》。可惜以上兩劇都僅僅演出一次。3月7日民鳴社演出《鴛鴦劍·大鬧寧國府》,3月8日之后竟再無廣告刊登。王鳳霞《文明戲考論》中也注意到了這次不告而別,并根據朱雙云《初期職業話劇史料》推斷這次沒有告別的消失是因為劇場租金問題,而后3月13日笑舞臺開幕,大部分民鳴劇人的名字得見于笑舞臺的演員名單。
第三階段:1916年5月顧無為出獄,與鄭正秋二人帶領民鳴社卷土重來,至1917年1月再度陷入停頓。在這幾個月中,民鳴只演過兩次紅樓戲,一次是1916年9月28日的《鴛鴦劍》,馬絳士飾演尤三姐,蔣鏡澄飾演薛蟠,趙燕士飾賈璉,鄭正秋作配角,另一次是10月13日“正秋新編”《鴛鴦剪發》。
第四階段:1917年4月30日至6月19日“民鳴社愛華社男女合演”,此階段未見紅樓戲上演。
第五階段,即1917年6月中旬至9月中旬,轉移至杭州的民鳴社在汪優游等人的組織下也演過《劉老老進大觀園》《風月寶鑒》,但終究已是強弩之末,次數不多。民鳴社日薄西山,汪優游等也重返上海,輾轉其他演劇團體繼續戲劇活動。
二、歐陽予倩在第一臺:京劇紅樓戲的新時代(1916年1-7月)
1915年6月13日,春柳劇場·新劇同志會推出了一部“古裝歌劇”《黛玉葬花》,這就是歐陽予倩所說“在春柳劇場當余興演的,可算是在上海第一次的古裝京戲”。這一部“古裝歌劇”《黛玉葬花》的問世無論對歐陽予倩本人還是民國紅樓戲的發展來說都是一個重要事件,正是從這一部《黛玉葬花》開始,紅樓戲史上一個全新的編演京劇紅樓戲的時代徐徐開啟。
從歐陽予倩的個人經歷來看,其對京劇的喜愛早已有之,如《自我演戲以來》中提到的在東京春柳社與吳我尊搭檔唱了一次《桑園會》作為余興以及1912年底在張家花園演《宇宙鋒》的經歷,《申報》廣告中也可見1914年12月24日歐陽予倩與吳我尊、熊天聲合作《四郎探母》,隨后1915年1月1日在競舞臺還與吳我尊唱過一次《彩樓配》。但這些經驗畢竟都是零星的,甚至更多的帶有幾分游戲性質,1915年4月25日至5月29日在第一臺這一個多月的時間才算是歐陽予倩成為京劇演員的初次嘗試。這一時期唱的完全是《玉堂春》《宇宙鋒》等傳統京劇劇目。之后歐陽予倩又回到春柳,1915年6月13日演出“古裝歌劇”《黛玉葬花》。歐陽予倩的這一次嘗試很有可能出于第一臺演出京劇的刺激。歐陽予倩在《我自排自演的京戲》中提到,最初搭班演京戲時經驗尚少,會的戲不多,難免捉襟見肘,對于《妻黨同惡報》之類的新戲又不感興趣,于是想要“排一點適合于自己演的新戲”。這應該是催生歐陽予倩京劇紅樓戲的一個直接原因。
1915年12月12日至13日,丹桂第一臺連續刊登廣告,宣告歐陽予倩正式受聘開始在第一臺演出。隨后,在每日刊登的廣告上可以看到此時歐陽予倩主要演出的還是《汾河灣》《真假金蓮》《三娘教子》等京劇青衣花旦的常規劇目。
1916年1月,歐陽予倩在第一臺首次演出紅樓戲《鴛鴦劍(尤三姐自刎鴛鴦劍 王熙鳳大鬧寧國府)》,1915年12月31日及1916年1月1日連續兩日刊登的廣告如下:
是劇系歐陽予倩君生平最得意拿手杰作。前在文明戲園中開演,其情節之佳妙,早已膾炙人口,所惜配角不齊,不能盡臻完善。今本臺特煩重為編排,去蕪存菁,場場乞緊。又以馮君子和飾尤三姐,真能顯出顏如桃李、冷若冰霜之態。歐陽君飾王熙鳳,風流潑辣,無不描摹盡致。以外各配角純用京白,俱能各盡其妙,較之文明戲中之角總能略勝一籌。并添制新奇布景,務請各界光臨賞鑒,方知所言不謬矣。
實際上演日期為陰歷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即1916年1月2日,可惜該日《申報》休刊,未能看到演出當日廣告,但應照計劃上演。而后19日與25日又重演,可知與歐陽搭戲的是麒麟童(周信芳)、馮子和、陳嘉祥、李慶棠等人。預告中提到“各配角純用京白”,有可能指的是京劇中的說白采用京白而非韻白等,也有可能指的是此劇目為以臺詞為主要表現方式的新劇,但歐陽予倩提到過《鴛鴦劍》縱使由話劇改編成京劇,也還是“話多而唱少”,這樣一來,從這一句廣告詞中無法確定此次第一臺演出的《鴛鴦劍》是新劇還是京劇。再看演員表,馮子和雖有演出文明戲的經驗,但整體看來畢竟還是京劇演員的陣容,考慮到第一臺原本為京劇舞臺的性質,再加上初演廣告中強調“重排”、與之前的“文明戲園中”所演不同,結合之前提到的歐陽予倩想要排演“私房戲”的嘗試,或許可以推測此次演出的《鴛鴦劍·大鬧寧國府》有已被改編成京劇的可能,只是缺少直接證據,未能斷定。
《鴛鴦劍·大鬧寧國府》隨后又于2月20日、3月3日、4月8日上演,合作的人只少了陳嘉祥,其余基本不變。《鴛鴦劍》加《大鬧寧國府》時時連演,甚至連演時干脆將劇名略稱為《鴛鴦劍》或《全本鴛鴦劍》。從劇情上看,尤二姐、尤三姐、王熙鳳三個女性角色戲份都不少,可知角色之吃緊。在第一臺演出幾次所標注的主要角色名稱中,歐陽予倩、馮子和、宋志普都是重要的旦角,而與歐陽搭戲的馮子和于1916年5月9日離開第一臺,《申報》上可見其已從6月開始在明明舞臺演出的廣告。自馮子和出走后,第一臺再沒演過《鴛鴦劍·大鬧寧國府》,或許角色分配的確受到了很大的沖擊。事實證明,而后的紅樓戲演出也的確迅速轉向了人物較少、易于支配、且之前在春柳民鳴已經嘗試過的《黛玉葬花》。
5月12日至17日,第一臺連續推出廣告,宣告歐陽予倩要在17日演出新作《林黛玉葬花》,配賈寶玉的仍然是麒麟童,而后在5月23日、28日、6月5日、11日、7月10日重演,歐陽予倩與第一臺的合約也于七月末到期。從1915年12月中旬到1916年七月末這七個多月的時間里,除了1916年5月24日至26日為紀念顧無為出獄、民鳴社假座演出新劇《法國拿破侖》的特例之外,歐陽予倩在第一臺幾乎每天都演出京劇。這期間演出紅樓戲《鴛鴦劍·大鬧寧國府》《林黛玉葬花》兩種,《申報》廣告可見的上演次數記錄分別為6次及7次,雖說從比例上看,仍是演出其他傳統劇目占絕大多數,但這兩部新作在京劇舞臺能得到如此頻次的持續上演,已經可說是京劇紅樓戲一個成功的開始。
三、笑舞臺異軍突起:新舊交融、分庭抗禮(1916年3月-1917年2月)
新劇劇場笑舞臺誕生于1915年,在新劇中興之后方才成立,由此見證了新劇中期的繁榮及后期由盛轉衰的重要過程。而在紅樓戲劇史上,笑舞臺也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1916年以后,從新劇紅樓戲的頻繁上演到京劇紅樓戲新作不斷涌現,笑舞臺都是重要演出場所,這一點從歐陽予倩、徐半梅等劇人的回憶性文章中也有著明確體現。下文將從1916年笑舞臺開始演出紅樓戲到1917年2月末歐陽予倩暫別笑舞臺為止,對笑舞臺紅樓戲及上海劇壇紅樓戲的整體演出狀況進行整理,分析這一階段紅樓戲演出的特征及發展趨勢。
(一)笑舞臺開始紅樓戲演出
笑舞臺由民樂公司進興公司開辦,原本為女子新劇,后因經營不善,于1916年3月13日刊登“民樂進興公司取消合同聲明”宣告停演,并在此則啟事旁刊登笑舞臺已轉手成安、大成公司的廣告,宣布“笑舞臺改演男子新劇”。有了汪優游、李悲世、鄒劍魂等“新劇大家”加入,新的笑舞臺于3月17日正式開幕,19日即演出《劉姥姥進大觀園》(按:此劇名常作“劉老老進大觀園”,但此日廣告中,“劉老老”作“劉姥姥”),而后鄭正秋也加入笑舞臺,29日演出新編的紅樓戲《璉二殺鳳姐》,由標題與廣告中的簡介可知是從小說第四十四回“變生不測鳳姐潑醋”情節改編而成。5月8日鄭正秋、汪優游、李悲世、鄒劍魂等演出《鴛鴦劍聯演寧國府》。5月20日查天影加入,同鄭正秋、汪優游等演出《金釧兒投井》,6月3日演出《相思局》,即“王熙鳳毒設相思局”“風月寶鑒”故事。
(二)歐陽予倩的紅樓戲
1916年七月末,歐陽予倩結束了第一臺的合約,按照《自我演戲以來》文中歐陽予倩的回憶,其之后去蘇州演出一段時間,受查天影邀約回滬加入笑舞臺。徐半梅在《話劇創始期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笑舞臺回復了以前的組織,又加入了歐陽予倩、查天影二人,于是七人委員會,變成九人委員會了。歐陽予倩一到,就有許多新的資料可以演出了。他是愛好紅樓夢劇的,而且喜歡用歌劇方式來演出,我們本來有《王熙鳳大鬧寧國府》,《風月寶鑒》,《鴛鴦劍》,《劉老老進大觀園》等戲,予倩的歌劇也分幕,也用布景,可并不像皮簧劇那么一場一場接連下去。他第一次演的是新排的《晴雯補裘》。后來還陸續排了《黛玉葬花》、《饅頭庵》、《寶蟾送酒》、《鴛鴦剪發》、《黛玉焚稿》、《負荊請罪》等紅樓戲,真是洋洋乎大觀。
歐陽予倩在《自我演戲以來》文中也提到過:
笑舞臺雖然是演新戲的戲館,可是自從我到了那里,三天兩日總要加演紅樓戲,臨時從外面去找鑼鼓,租配角的衣服,雖然費點兒事,卻總是滿堂,也就不在乎了。
前面提到的歐陽予倩加入之前的笑舞臺曾演過的五部紅樓戲自然都是新劇,歐陽加入之后,他的編演才能及已有的京劇紅樓戲劇目又重新得以施展。可以看到,歐陽予倩1916年8月12日正式開始在笑舞臺的演出,而廣告從11日刊登開始就在為已經在第一臺等劇場取得成功、預定14日上演的《林黛玉葬花》預熱,15日又緊接著演出了《鴛鴦劍連演寧國府》,徐半梅關于歐陽第一次演的是《晴雯補裘》的記述有誤。這兩出紅樓戲在笑舞臺首演之后又連續演了幾次,想來反響不錯,而無論是笑舞臺劇場一方還是編演者都非常重視,笑舞臺花了很大力氣為歐陽予倩紅樓戲新制布景,而歐陽予倩本人也從春柳初試《葬花》時開始便對《黛玉葬花》不斷修改,增加幕數以使戲情合理流暢。
(三)新舊交融
歐陽予倩在《自我演戲以來》一文中提到,在笑舞臺與查天影隨編隨演,演出了《黛玉葬花》《黛玉焚稿》《晴雯補裘》《寶蟾送酒》《饅頭庵》《鴛鴦劍》《王熙鳳大鬧寧國府》《摔玉請罪》《鴛鴦剪發》九部京劇紅樓戲,這一記述與《我自排自演的京戲》一文中也是一致的,但實際上歐陽予倩此次在笑舞臺演出的紅樓戲不止京劇而已。
1916年8月12日至1917年2月,《申報》可見歐陽予倩在笑舞臺演出的廣告中,有《(林)黛玉葬花》(1916年8月14日首次在笑舞臺演出)、《鴛鴦劍連演寧國府》(1916年8月15日首次在笑舞臺演出)、《璉二殺鳳姐》(鄭正秋作,歐陽予倩加入之前笑舞臺已經演過,1916年9月3日歐陽予倩首次演出)、《金釧兒投井》(歐陽予倩加入前笑舞臺已經演過,1916年9月10日歐陽予倩首次演出)、《晴雯補裘連演芙蓉誄》(1916年9月20日初演)、《相思局》(歐陽予倩加入之前笑舞臺已經演過,1916年10月3日歐陽予倩首次演出)、《黛玉焚稿》(1916年10月26日初演)、《寶蟾送酒》(1915年秋創作并初演于杭州西湖舞臺,1916年11月6日首演于笑舞臺)、《饅頭庵》(1917年1月3日初演)十部。
將這兩個劇目單對照來看,除《摔玉請罪》《鴛鴦剪發》此時尚未問世之外,可知歐陽予倩此次在笑舞臺演出的《璉二殺鳳姐》《金釧兒投井》《相思局》三部不見于歐陽予倩九部京劇紅樓戲的記述。當然這三部劇是笑舞臺在歐陽予倩加入之前就有的劇目,并非歐陽予倩的創作,自然沒有被收錄進歐陽予倩“自排自演”的劇目中。但此處要注意的是:這三部劇作雖然在歐陽予倩加入笑舞臺熱演京劇紅樓戲的時期演出,卻應該不是京劇,而是新劇。
笑舞臺雖然是新劇劇場,但在歐陽予倩簽約期間是京劇與新劇并行的。這一時期笑舞臺演出的京劇除了著名的紅樓戲之外,還有《玉堂春》等傳統戲;而新劇則既有春柳時代的名作《不如歸》等,也有新作如《香鉤情眼》《秋海棠》等。雖說歐陽在笑舞臺期間演出了一系列京劇紅樓戲,但并不等于加入笑舞臺之后的歐陽參與演出的每一部戲、每一部紅樓戲都是京劇。
再看這一時期《申報》上笑舞臺的廣告,因其本質為新劇劇場,故演京劇劇目時必稱“京劇”或“舊劇”,或標注為歐陽予倩的“(紅樓)歌劇”以示區別。名作如《黛玉葬花》等觀眾早已耳熟能詳者,廣告中或可省略“歌劇”二字,但如為新作,則廣告中一定要標明“歌劇”或“新編歌劇”以引起讀者和觀眾注意。《璉二殺鳳姐》《金釧兒投井》《相思局》三部劇是已經在笑舞臺演過的新劇,如果因歐陽予倩加入而改為京劇(歌劇)形式重新上演,則廣告中不可能不特別標注。實際上1916年9月3日演出的《金釧兒投井》劇名前綴只有“古裝”,并無“歌劇”,也無“新編”,也并未提到與之前有何不同,也看不到如何改編創造或是笑舞臺演出京劇時廣告中常見的對于演員歌喉的贊揚,這兩部作品基本已經可以斷定仍是之前演出的新劇形式。
但關于10月13日上演的《相思局》尚有一些疑問。《相思局》雖仍為笑舞臺原有的紅樓戲,但因有擅唱京劇的歐陽予倩,故采用了“戲中串戲”的方式使歐陽予倩在劇中唱《狀元祭塔》。《祭塔》是歐陽當年在第一臺初次嘗試演京劇時的拿手好戲,故廣告中也十分用力贊揚其唱祭塔之精彩。當日廣告中還有“何為杰作?笑舞臺之相思局杰作也。歐陽予倩之祭塔杰作也。兩出好戲同時演唱,觀客之莫大幸福也”,以及“兩出難得之戲同時演唱,真真難得,不知諸君前世敲破多少木魚,得于一晚亨(按:應為“享”)這耳目之福”等宣傳語。“演唱”京劇《祭塔》固然無誤,《相思局》如為新劇卻也被囊括在“演唱”的范圍內,似有不妥。但無更直接的證據,只好暫時理解為笑舞臺刊登廣告時對“演戲”“唱戲”表述不甚嚴密。至12月13日演出《相思局》時,“戲中串戲”《真假金蓮》,廣告詞中宣傳“新戲之中還有老戲看,便宜之中最便宜”,“新戲”可以指新劇,“老戲”可以指舊劇即傳統戲曲京劇,但“新戲”也可以指新作,“老戲”也可以指京劇中既有的骨子老戲,單從字面無從判斷,但結合笑舞臺廣告宣傳的規律,畢竟《相思局》中沒有出現“新作”“新編”及“歌劇”等字樣,只好當作仍為新劇中加唱京劇的形式。
關于《相思局》的疑問暫且按下,笑舞臺此時的演出是新劇京劇交錯進行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笑舞臺1916年11月5日廣告中將笑舞臺原本演過的新劇與歐陽予倩加入后新演出的歌劇分別列出:
凡紅樓夢戲,出出有趣味,幕幕有精采,可惜能演紅樓夢戲之人材不可多得,所以他家往往想演紅樓夢戲而不能演,即使能演一二出,又不能多演,獨本舞臺人才完備,紅樓夢戲,演之又演。如《鴛鴦劍》《寧國府》《風月寶鑒》《劉老老》《璉二殺鳳姐》《金釧兒投井》等,那一出不是本舞臺的拿手好戲?再加新排之《黛玉葬花》《黛玉焚稿》《晴雯補裘》等歌劇,更是錦上添花。
11月25日廣告中提到的(紅樓)歌劇僅有《晴雯補裘》《黛玉葬花》《黛玉焚稿》《寶蟾送酒》四部(此時《饅頭庵》尚未問世),可為這一時期笑舞臺所演出的紅樓戲新舊并行之佐證:
笑舞臺四歌劇,論熱鬧則以《補裘》為冠,論香艷則以《葬花》為首,論凄慘則以《焚稿》為最,若以情趣論,當以《送酒》為巨擘。
由此又產生了另一個問題:以上兩則廣告中提到的《鴛鴦劍·大鬧寧國府》均未被列入“歌劇”行列,徐半梅所提到的歐陽予倩加入之前笑舞臺所演的應為新劇無疑,但以上兩則廣告中刊登的時間點是歐陽予倩已經加入且編演了一系列京劇紅樓戲之后。根據歐陽予倩的記述,《鴛鴦劍·大鬧寧國府》是加入笑舞臺后隨編隨演的京劇紅樓戲之一,但《鴛鴦劍·大鬧寧國府》的廣告中,即使是歐陽予倩加入之后,也全無“歌劇”字樣,與笑舞臺其他劇目刊登時的普遍規律不符不說,反倒時時提起之前在春柳民鳴第一臺演時如何如何,而春柳民鳴演出的也是新劇無疑。或許此處標注不備僅為例外,提到“春柳民鳴第一臺”可能側重的是劇情故事及劇目本身而非表現形式和劇種體裁,但如前所述,筆者懷疑《鴛鴦劍·大鬧寧國府》在第一臺上演時很可能已被排成京劇,而1917年8月10日及16日,歐陽予倩在第一臺時又與麒麟童、宋志普、李少棠等演過幾次《全本鴛鴦劍》。在笑舞臺,一般不唱或極少唱的新劇作品,如以戲中串戲的形式唱幾句京劇,廣告中都要大肆宣傳,則此劇縱使再“話多而唱少”,廣告中都不應該對演唱只字不提。故筆者大膽提出假設:歐陽予倩的《自我演戲以來》作于1929-1930年,《我自排自演的京戲》為1958年寫成,帶有回憶性質,不排除時隔多年的記憶有細微出入的可能,有無可能在笑舞臺之時演出的《鴛鴦劍·大鬧寧國府》仍為新劇,而在笑舞臺演出之前及之后簽約第一臺時演出的是京劇?這一假設畢竟不過是推測,這部“改成京戲話多而唱少”的《鴛鴦劍·大鬧寧國府》“不如《葬花》等戲賣座”,演出次數不算多,缺乏更多更確鑿的證據,只好將疑問錄于此處以備日后詳細考證。
(四)北梅南歐
《鞠部叢刊》下編之“粉墨月旦”中(周)劍云所記《梅蘭芳之黛玉葬花》中寫道:“近代伶工擅演紅樓劇者有二,北數蘭芳,南數予倩。”“品菊余話”中(周)劍云《劍氣凌云廬劇話》又提到:“然北之梅蘭芳,南之歐陽予倩,固皆以演紅樓夢而得名。”二人的確在紅樓戲上各有所長,都占據舉足輕重的位置,才得以如此相提并論。
1916年8月至1917年2月,歐陽予倩在笑舞臺演出的六個月時間里共演紅樓戲57次,上演頻率極高,且廣告中常常出現連續三天上演三部不同紅樓戲的情況,紅樓戲平均一周至少上演兩次。歐陽予倩在笑舞臺期間基本確立了在上海紅樓劇壇首屈一指的領導地位,而從北京南下的梅蘭芳則給上海紅樓戲演出注入了新的力量。
梅蘭芳曾在1913年冬、1914年末至1915年初兩次到上海演出,1916年冬是他第三次南下上海。《舞臺生活四十年》中提到過,前兩次上海公演無論是新劇的發展還是與北京完全不同的京劇市場生態,都使梅蘭芳受到了新的刺激,回京后也開始編排自己的新戲。而歐陽予倩也曾自述去看過梅蘭芳的戲,后來也參考了梅蘭芳的古裝扮相。二人后來私交不錯,而在藝術上也互相影響,特別在這一時期,正當紅的北京京劇名角梅蘭芳來到上海演出紅樓戲,無疑對以演紅樓戲著名的歐陽予倩來說也是個挑戰。
梅蘭芳從1916年10月4日至11月20日演于天蟾舞臺,而后赴杭游覽西湖,被杭州第一舞臺邀請挽留,演出約一周時間,12月5日至17日又回上海天蟾舞臺,而后返京。這一次梅蘭芳攜姜妙香、姚玉芙帶來了新作:《黛玉葬花》和《晴雯撕扇 千金一笑》兩部紅樓戲,于是“北梅南歐”開始了在上海這個繁華的舞臺上“同臺”競技。
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笑舞臺與天蟾舞臺競相上演紅樓戲,梅蘭芳在天蟾舞臺共演出《黛玉葬花》7次,《千金一笑》6次;原本就以紅樓戲著名的笑舞臺在這兩個余月間所演的紅樓戲的密度也遠高于梅蘭芳來滬之前與之后,共上演了《黛玉葬花》《鴛鴦劍》《晴雯補裘》《相思局》《黛玉焚稿》《寶蟾送酒》六部紅樓戲,合計上演次數足有29次之多(28次為歐陽予倩擔綱演出),其中《葬花》與梅蘭芳相同,也是7次,《焚稿》與《送酒》并列,各演了6次。歐陽予倩的京劇紅樓戲中,《黛玉焚稿》與《寶蟾送酒》兩部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搬上笑舞臺。另,11月20日(梅蘭芳去杭州前一日)以及12月16日(梅蘭芳返京前二日)晚,笑舞臺和天蟾舞臺都推出《黛玉葬花》,幾是唱對臺,可見競爭之激烈。
紅樓戲難演,角色難以討好,在這一次梅歐二人的紅樓戲競演中,二人各自都有固定的搭檔,把演出維持在穩定的高水平線上:在笑舞臺期間,歐陽予倩的紅樓戲有了查天影作固定搭檔的小生,甚至廣告中常將二人名字并稱為“倩影”,另外與之配戲的固定旦角為之前曾在民鳴社有過紅樓戲演出經驗的鄒劍魂;而梅蘭芳原本就有固定的班子,演紅樓戲常與之搭檔的是小生姜妙香與青衣姚玉芙。有了固定搭檔,配戲形成默契且易于為觀眾所接受,也是紅樓戲演出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梅蘭芳的到來使上海的紅樓戲熱潮更加高漲,梅蘭芳在1916年末回京后,上海的紅樓戲巨擘歐陽予倩也沒有停止其紅樓戲創作。1917年1月3日笑舞臺推出“新編歌劇”《饅頭庵》,甚至采用“電光布景”和“空中歌舞”作為噱頭,歐陽予倩在《我自排自演的京戲》中對《饅頭庵》里秦鐘死前夢見已經死了的智能一幕演出有比較詳細的描述,智能在空中蕩秋千飛來飛去,邊做身段邊唱戲,難度極高,觀感一定十分刺激。
1917年2月22日至3月24日,歐陽予倩與查天影受蘇州振市新劇社之邀赴蘇州演出,其間也演出了《黛玉葬花》等多部紅樓戲。在蘇州的演出結束之后,歐陽予倩返回上海,但卻并未像2月21日《申報》所刊笑舞臺聲明中所言“演畢即歸”,而是簽約第一臺演出四個月之后才回歸笑舞臺。關于1917年4月歸滬之后在第一臺和笑舞臺演出紅樓戲的情況,筆者將另行撰文,此處暫且不表。
又及,1917年3月至10月,即歐陽予倩與查天影暫別笑舞臺的八個月時間里,笑舞臺僅僅演過一次紅樓戲,即3月22日的《瑞大爺想吃天鵝肉》(即風月寶鑒、相思局)。可以想見,歐陽予倩在笑舞臺乃至上海的紅樓戲演出中的確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徐半梅在《話劇創始期回憶錄》中提到:
紅樓夢戲需要許多旦角,而笑舞臺旦角獨多……就是予倩本人,他后來離開了笑舞臺,雖然查天影老是跟在他旁邊,他總演來不舒服,就因為沒有這許多旦角來扮演大觀園里許多姑娘丫頭們,這是予倩在他寫的《自我演戲以來》中也曾提起過的。
歐陽予倩《自我演戲以來》中也的確強調了紅樓戲在笑舞臺上演的得天獨厚的優勢:
雙云為了我的戲特意做些新布景:譬如《葬花》……我以后在其他的舞臺演,都沒有像這樣的精美。《晴雯補裘》也是在笑舞臺演得好,其他的地方一則沒有那么許多旦角,二來不肯專為一出戲十分排練,所以不容易整齊。……如《補裘》這種戲,換一個地方,換一個配角,便簡直不行。不止《補裘》,別的戲也都是一樣。
由此可見,笑舞臺在這一時期的紅樓戲演出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為歐陽予倩的紅樓戲編演提供了別處所無法比擬的良好條件,歐陽予倩的大部分紅樓戲作品都是在笑舞臺演出時上演的,在個人藝術得到發揮的同時應該也為笑舞臺帶來了良好的經濟效益,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成就了這一時期新劇及京劇紅樓戲交相輝映的局面。
結語
1915年中春柳劇場·新劇同志會逐漸解體后,新劇紅樓戲演出從民鳴社轉移到笑舞臺。而自編演“古裝歌劇”《黛玉葬花》開始,歐陽予倩在上海掀起了紅樓京劇的熱潮,紅樓戲演出中,新劇逐漸讓位于京劇。歐陽予倩橫跨新劇與京劇兩界,既是劇人也是文人,在紅樓戲創作與編演上,其開始之早、作品數量之多、劇目上演之頻,在當時都無疑是無人可出其右的。梅蘭芳作為北京的外來力量,既受到上海的影響,也給上海的京劇、特別是京劇紅樓戲帶來了積極的刺激。
通過這一時期上海紅樓戲演出的實際情況可以看出,新劇紅樓戲演出的中心是隨著有能力編演紅樓戲的演員而轉移的。從新民春柳,到民鳴和笑舞臺,從前期的馮叔鸞、馬絳士,再到貫穿大半個民國紅樓戲劇史的歐陽予倩、鄭正秋、汪優游、查天影、徐半梅,編演紅樓戲的劇人們幾經分合,但歸根到底,還是脫不開這幾支主要力量。在新劇紅樓戲尚未出現之時,有力量將其創作出來的非知識水平較高且熟稔《紅樓夢》的馮叔鸞、馬絳士、歐陽予倩、鄭正秋等人不可,即使是在紅樓戲劇目大量產生之后,因其角色不易討好、程度較高,也非人人可演,從《申報》所刊戲劇廣告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隨著時間的變化,民國紅樓戲在不同的階段主要演出的劇場也不同,但其背后真正起決定力量的還是劇人的流動,非有人才薈萃于某劇場不能上演,且自始至終,承擔林黛玉、王熙鳳等主要角色的都是同一批文化和藝術水平都較高的劇人。
而歐陽予倩的紅樓戲編演在新劇與京劇之間的穿梭,則是作為他個人戲劇生涯的一部分,隨著其演劇活動重心的變化而變化的。這一時期上海的紅樓戲、特別是京劇紅樓戲,幾乎是歐陽予倩一人獨領風騷,梅歐二人短暫交鋒后的上海紅樓劇壇有了怎樣的改變、其中是否又有新的力量醞釀、日后的上海紅樓戲又將呈現怎樣的局面,則留待另行撰文論述。
① 吳雨彤《民國紅樓戲之新劇先聲——從〈申報〉所刊戲劇廣告試論民國早期上海紅樓戲的出現》,《紅樓夢學刊》2021年第3輯。
② 本文中的《申報》廣告內容皆引自《申報》影印本(上海書店,1982年11月),不另出注。
③④ 參見王鳳霞《文明戲考論》第九章“中興”期的上海新劇團體(1944-1917)第四節民鳴社考論(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331、327頁)。
⑤⑥[11][12][18]《自我演戲以來》,《歐陽予倩全集》第6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55、18及32、67—68、67、68頁。
⑦⑧[13][16]《我自排自演的京戲》,《歐陽予倩全集》第6卷,第266—267、272、272、272頁。
⑨ 參見黃愛華《上海笑舞臺的變遷及演劇活動考論》(《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
⑩[17] 徐半梅《話劇創始期回憶錄》,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版,第91、91—92頁。
[14] 周劍云《鞠部叢刊》,民國叢書第二編第69冊,上海書店1990年版(據交通圖書館1918年版影印)。
[15] 參見梅蘭芳述、許姬傳記《舞臺生活四十年》(平明出版社195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