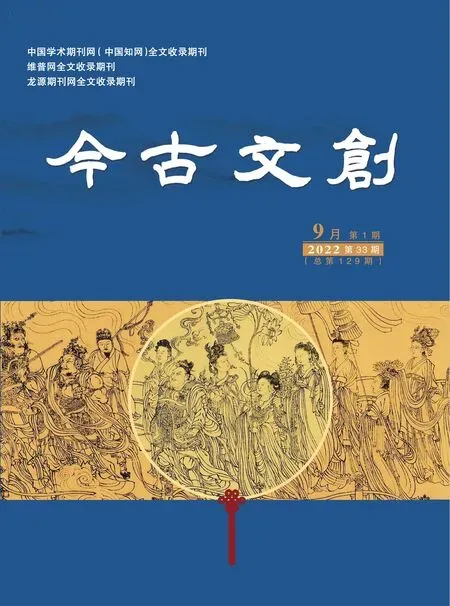余光中與米蘭 · 昆德拉鄉愁書寫的區別及成因
◎周 悅
(中國傳媒大學 北京 100024)
一、引言
中國作家余光中和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是具有代表性的鄉愁書寫者。然而,他們對“鄉愁”這一普遍性情感呈現出了不同乃至相反的認知及表達。從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可以發現,余光中以正面的態度看待鄉愁,對故鄉抱有長久而深厚的眷戀,用詩文抒發內心的情感。米蘭·昆德拉看到的卻是鄉愁負面的因素,指出其影響當下的現實生活,并希望通過放下鄉愁而獲得平靜。
“言,心聲也。”本文將對余光中和米蘭·昆德拉的文學作品進行分析,從而解決一個由文本而生發的疑問:二者對鄉愁的情感態度為什么會呈現出這樣的差異?
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明晰故鄉與鄉愁的概念。本文中的“故鄉”,主要是指兒時居住或長期生活的地方。“故”為“過去的”意思,在“故鄉”一詞中帶有業已遠離的前提含義。因此,故鄉包含了兩個主要的因素:時間上相對久遠的從前和空間上遠離當下居所的地方。
鄉愁即是基于故鄉的時間與空間不可復現而產生的一種深切的思念之情。四川大學張嘆鳳教授認為,“‘鄉愁’是家園文化與離散現實沖突的結果,并人生旅途心靈訴求所觸發的、帶有悲劇意味的情思與感想。”鄉愁最基本的訴求是抒發離散現實的愁苦。正如弗洛伊德對“生命本能”和榮格對“集體無意識”的解讀,鄉愁情結始終潛伏在人類心靈深處。因此,無論地域、文化如何,鄉愁都是普遍存在的情感。然而,不同文化語境中的人們對這種本能的情感有著截然不同的認知和評價。
本文對余光中和米蘭·昆德拉作品的比較主要基于以下前提:一方面,他們生活在同一時代,具有相似的個人經歷。他們都受到本國文化的深刻影響。同時,他們也都有離鄉的經歷,對離愁別恨有著切身的體驗。另一方面,他們對于鄉愁的書寫代表著各自文化的鮮明特性,呈現出較大的差異。
因此,依據“文化洋蔥理論”,可以將他們的文學作品作為文化現象或文化產品進行審視、分析,通過對不同文化中深層次價值觀的比較,揭示出二者對鄉愁的認知存在區別的原因。
綜上,本文將分析余光中和米蘭·昆德拉的文學作品中對故鄉的時間記憶及空間環境的不同表述,比較二者對于鄉愁的價值判斷,進而探討現象背后的文化差異及深層次原因。
二、對過去的懷念:留住還是放下
故鄉的回憶處于相對久遠的從前,而鄉愁包含著對過去的懷念。在不同的價值判斷標準下,對故鄉產生的懷舊情感存在正面和負面的評價。通過兩位作家的文學作品,可以發現他們對鄉愁中時間因素認知的不同。除了作者本身的經歷之外,對時間認知上的文化差異也影響著兩位作家對鄉愁的價值判斷。
在《思臺北,念臺北》中,余光中回憶過往的人、事、物和自身的經歷,表達出對故鄉深厚的懷念。他寫道:“廈門街,水源路那一帶的彎街斜巷,拭也拭不盡的,是我的腳印和指紋。每一條窄弄都通向記憶,深深的廈門街,是我的回聲谷。”余光中在遠離故鄉后,仍會回想起在窄巷走過的腳步。雖然投入了新的生活環境,但是他依然飽含深情地追溯在故鄉的記憶。
余光中的人生經歷是其鄉愁的源頭之一。《思臺北,念臺北》創作于1976年,余光中離開臺灣,居于香港已經兩年時間。從22歲到48歲之間,余光中在臺灣居住生活了十九年。他在臺灣的經歷包含求學、結婚、文學創作、教師生涯等關鍵的人生階段。“把一座陌生的城住成了家,把一個臨時地址擁抱成永久地址,我成了想家的臺北人。”雖然余光中并不是自幼生活在臺灣,但長期的人生經歷使臺灣承載了作者深厚的感情,成為猶如“妻子”的故鄉。時間長度和特定回憶加深了作者的生命與故鄉的聯結,因此而產生了離鄉后的愁緒。
反觀米蘭·昆德拉的鄉愁書寫,他們對故鄉的懷念是一致的。然而不同之處在于,昆德拉揭示出故鄉的不可再現,并采取一種批判性的眼光來看待鄉愁。相比于余光中的“留住”鄉愁,他的態度更傾向于將其“放下”。
在小說《無知》中,主人公伊萊娜流亡二十年后重返祖國捷克,卻發現故鄉已是今非昔比。在回鄉的聚會上,伊萊娜因重逢的幻想場景破滅而感到失望:“沒有人對自己的奧德賽之旅感興趣”。米蘭·昆德拉寫道:“對現時的眷戀驅走了他的回憶,使他免受記憶的干擾;他的記憶并未減少惡意,但是一旦被忽視,被排斥在一邊,它也就失去了對他的控制力。”作者通過小說人物的命運揭示出“過去”的欺騙性——過往的時間如同一條赫拉克利特之河,“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在故鄉中度過的時間僅存在于記憶中。
小說《無知》的主人公伊萊娜的經歷也可看成是作者自身的投射。米蘭·昆德拉于1929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爾諾。1968年,蘇聯軍隊入侵捷克后,米蘭·昆德拉在電影學院的教職被解除,著作也遭到封禁。1975年,雷恩大學向他提供了一個助教的職位時,米蘭·昆德拉就前往法國,踏上了流亡之路。作家在法國時期的多部作品反映出他在流亡狀態下自我認知的迷失。在他的小說中,記憶中的故鄉必然發生改變,離鄉的人便無法再尋得身份認同,于是“回歸”也就成為一種悖論。
由此可見,一方面,作者對于鄉愁的態度來源于其離鄉的生命體驗;另一方面,文化環境作為潛在的因素影響著他對鄉愁的認知。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鄉愁濃郁而深長,這個特點在余光中的鄉愁書寫中也有充分的體現。在《思臺北,念臺北》一文中,余光中引用賈島的思鄉詩《渡桑干》:“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由此生發出感慨:“如果十霜已足成故鄉,則我的二十霜啊多情又何遜唐朝一孤僧?”“二十霜”即是指余光中在臺灣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時間。余光中與唐代的詩人賈島遙相呼應,引發共鳴的便是這份跨越時間的離愁別恨。
那么,是什么使中國人對故鄉的情感一以貫之?從時間因素來說,中國文化重視回望過去,從中獲得經驗,以史為鑒。具體到個人的情感,則體現為懷舊和鄉愁。懷念故鄉,也是反思自己的過往。根據克拉克洪的“文化模式理論”,中國文化屬于“past orientation”,具有指向過去的特點。相較之下,西方部分國家的文化則屬于“future orientation”,價值觀朝向未來的目標,更傾向于做出改變和嘗試。
中國文化中指向過去的時間觀念在生產方式、社會結構的基礎上產生。從西周的宗法制起,人們就通過傳承制度規范來維護社會的穩定。如費孝通教授所言,長期的農耕傳統下,中國逐漸形成了鄉土性的熟人社會。長老統治維持家族中的權威和管理,禮儀規范、風俗習慣得以穩定地傳承。“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中國文化由此而形成了重視歷史的傳統。人們回顧過往,用經驗來指導未來的行動。對離鄉者來說,故鄉的記憶即是一種確鑿的經驗,其中蘊含著人長時間下形成的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除此之外,中國文化中的鄉愁作為一種情感也被賦予了道德價值。余光中寫道:“有那么一座城,錦盒一般珍藏著你半生的腳印和指紋……珍藏著你一顆顆一粒粒不朽的記憶。”其中蘊含著他對臺北的感恩和銘記。從諺語中也可以看出中國人對待過往經歷的態度。如“數典忘祖”,出自《左傳·昭公十五年》,比喻忘本,也比喻對于本國歷史的無知。忘記故鄉,也同于“忘本”“忘祖”,被認為是一種對過去、對故鄉的背叛。思鄉如同飲水思源,結草銜環,象征著懂得感恩、不忘根本等道德品質。從先秦時期遵循典籍向周天子進獻禮物,到個體無論身處何方也要銘記故鄉,重視過去的觀念加深了鄉愁中時間因素的影響,使得鄉愁在中國文化的價值體系中受到肯定。
兩相比較,余光中對鄉愁賦予了審美價值和情感道德價值,而米蘭·昆德拉對鄉愁的態度則更傾向于實證主義,即關注鄉愁對人帶來的實際效果。這與英語中“懷舊”(nostalgia)一詞的詞源所透露出的意味形成了某種呼應。追溯至鄉愁的近義詞“nostalgia”產生的源頭,它被視作一種病癥。1688年,一位法國大學生從荷馬史詩《奧德賽》中借來了nostos(漂泊返鄉)一詞,拼接在意為“疾病、苦痛”的希臘文詞根algos上,在畢業論文里用以描述當時在歐洲四處征戰的瑞士雇傭軍中十分流行的“思鄉病”。從詞根來解釋,西方的鄉愁即是“因無法回歸而感到痛苦”。斯維特蘭娜·博伊姆認為,懷舊和憂郁有一些共同之處,都會造成軀體和情緒的癥狀。鄉愁會影響遠離家鄉的士兵和水手的情緒,會致使人回顧過去而阻礙社會的進步。
這種認知方式的背后有其深層次的文化原因。17世紀的啟蒙運動是西方文化發展的奠基。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宣揚“理性”,強調科學的重要性。人們通過探究原理認識世界,發現事物運行的規律。辜正坤教授提出,西方人擅長建立條分縷析的理論體系,重視邏輯與概念的建立。
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來看待鄉愁,他們傾向于采取實證主義的方法,將鄉愁看作一個科學的研究對象,列舉出其癥狀、病理和解決方法。米蘭·昆德拉的《無知》中也有這種觀點的文學化表達。他將故鄉比作“一個不復存在的田園之夢”:“一把無形的掃帚掃過了他年輕時代的景物,抹去了他熟悉的一切。”鄉愁作為“心理疾病”的癥結就在于,回顧過去只會影響當下的現實生活。回歸故鄉亦是徒勞,記憶中的故鄉已經發生改變。
由此,可以從比較中看到兩位作家所處的文化對于鄉愁時間維度認知的不同影響。余光中所代表的中國文化中,重視過去的傳統引導著人回顧來路。同時,思鄉被賦予道德情感的價值,具有正面的意義。米蘭·昆德拉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則揭示出過往時光的不可再現,聚焦于“鄉愁”的徒勞及其對于新生活的干擾,因此對“鄉愁”形成了負面因素占主導的認識。
三、固定的故鄉:駐足還是離去
時間與空間上的特殊性共同構成了故鄉的主要內涵。除時間取向的因素之外,故鄉所處的固定空間為鄉愁提供了物質環境,承載著游子復雜的情感。
不同的文化價值判斷體系內,看待故鄉所處空間的視角存在差別。一磚一瓦,一草一木,既能勾起對故鄉的懷念,也能引發故鄉改變的痛苦。具體到文化中的個體,這種差別影響著余光中和米蘭·昆德拉對鄉愁的認知。
廈門街的市井街坊承載著余光中關于故鄉的記憶。這些記憶中有的關乎他的文學事業,“多少篇詩和散文,多少部書,都是在臨巷的那個窗口,披一身重重疊疊深深淺淺的綠蔭,吟哦而成”;有的是街坊鄰里的厚誼真情,余光中離鄉多年后與藥行的老板娘重逢,聽她一口潮州國語,“心里滿溢著溫暖的鄉情”。故鄉的空間因這些回憶而變得特別,它聯結著事業、情感、自我認同等等人生中關鍵的方面,猶如樹木的根系盤根錯節,交織成對故鄉深刻的眷戀。
家文化、安土重遷等是中國文化突出的特點,這也體現出中國人對固定空間的獨特情感。辜正坤在《中西文化比較概論》中提出“萬物自協調理論”,文化通過自我協調、自我適應找到在所處環境之中最好的存在方式。通過這一理論可以解釋文化形成的原因。中國的地形、氣候條件與農耕的生產方式相協調,農耕定居則“促進了家族體制的完整延續”。這使得中國人長期地居住在同一個地方,安居樂業而少有遷徙流離,靜態的文化模式因而發展起來。中國的百姓自古長居于穩定的環境中,安土重遷,不肯輕易遷移。因此,中國人安于固定的空間,在經年累月中加深對故鄉的感情。對余光中來說,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都曾是他懷念的故鄉。鄉愁不一定局限于唯一的地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是一種對過往生活空間的依戀,可以指向多處長期生活過的地域。
相較而言,米蘭·昆德拉對于過往生活空間的感知則不盡相同。在其小說《無知》中,有一段關于田園之夢的描述。伊萊娜和丈夫被別墅和花園的美景吸引。走近時,卻發現“他們闖進了一個被廢棄的工地,到處是機器、拖拉機、土堆和沙堆。”作者在書中發出疑問:“《奧德賽》在今天還可能想象嗎?回歸之英雄史詩還屬于我們這個時代嗎?”從這些片段中可以看出作者對鄉愁的懷疑。時間的流逝改變了故鄉的原貌,使其呈現出陌生而疏遠的狀態,因此而帶來的是無奈與悲傷。
對于這份鄉愁的痛苦,米蘭·昆德拉寫道:“這就是受虐記憶性的規律:隨著自己生命的構架坍塌在遺忘中,人就會擺脫他不喜歡的東西,從而覺得更為輕松,更為自由。”作家對鄉愁提出了質疑,并把放下鄉愁當作一種解決之道。
米蘭·昆德拉所采取的認知方式有其深層次的文化原因。根據辜正坤教授的中西文化比較理論,與中國靜態的文化不同,西方的地理環境、氣候促成了流動性文化,血緣的紐帶相對薄弱。韓少功也提出,“‘馬背上的民族’難有家園,習慣于浪跡天涯”,即便有較為固定的活動大區域,“家園”概念也要寬泛和模糊得多。不斷變動的生活空間促使他們及時融入新的環境,而非固守一方,止步不前。因此,為了解決鄉愁帶來的干擾,米蘭·昆德拉提出應當“忽視、排斥”故鄉的記憶,擺脫回憶的控制,投入現實生活。就如同牧民逐水草而居,商人為從事貿易而漂洋過海,不斷遠離熟悉的空間是一種必然,放下過去則是一種生存的需要。這種需要存在于人的意識中,從而形成對懷舊的負面判斷。鄉愁是余光中和米蘭·昆德拉重要的人生體驗和寫作主題。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可以發現二者對鄉愁認知上的差異。鄉愁是一種對過往時空的懷念,寄托著對理想生存狀態的向往。同時,鄉愁也是一條赫拉克利特之河,過度的懷舊會影響當下的現實生活。
任何事物都具有其兩面性,價值判斷取決于看問題的角度。無論是余光中深沉的懷想,還是米拉·昆德拉清醒的質疑,都承載著他們對鄉愁這一人之常情不同側面的思考。留住與放下,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選擇。
對鄉愁書寫的區別進行追根溯源,我們最終發現的是人類文明的豐富多彩。經過深入的理解,我們更能以包容的眼光看待文化的差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不同的文明相互融合,共同發展,才匯聚成世界文明的浩瀚汪洋。
①美國學者R·博亞特茲提出“文化洋蔥理論”,指文化的核心要素可以由外而內分為四層,分別是符號(包括語言)、英雄人物、禮儀及價值觀。
②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洪提出“文化模式理論”,根據不同文化中的人對時間的觀念將文化分為過去指向型,當下指向型和未來指向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