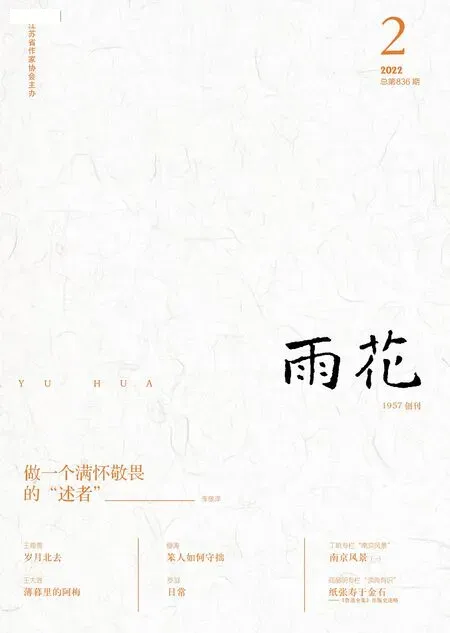凝視、隱匿與成長
——讀王寧婧《金魚》
劉志權
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認為,嬰兒六至十八個月可稱為“鏡像階段”,在此階段,嬰兒能夠認出自己在鏡子中的影像,并能通過他人目光之“鏡”,意識到自身的完整性,將鏡像內化為自我,從而區分開自我與他人。如果說,鏡像階段的嬰兒完成的是對自我身體的確認,那么,“精神自我”的確認需要更長的過程—如果跟拉康理論不那么精確地對應,大致是六至十八歲,正好貫穿了一個人從童年到青年的成長。
從鏡像理論談起,是因為《金魚》是一篇獨特的、具有代表意義的成長小說。成長的過程本質上是通過自我審視完成自我認同的過程。在通常的成長文學中,作者作為成人,無論以“同情之理解”旁觀他人,抑或以今日之我審視昨日之我,都注定了是自我成長的外部視角。可惜的是,作為內部視角的孩子自身,一方面當局者未必清,另一方面也難以對“自我”的成長進行感性把握、理性思考、準確表達。《金魚》的“獨特性”或“代表性”意義正在此:作者王寧婧年僅十六歲,本身處于成長的進程之中。她以自己早慧的成熟與才氣,同時完成了十二歲的敘事主人公對“自我”的凝視,以及十六歲的自己對十二歲的自己的凝視,展示了關于個體成長的生動圖畫。
“凝視”是成長的核心。小說中有典型的拉康式鏡像凝視:“我十二歲,對許多事情有了自己的朦朧判斷,譬如說有時候我會在鏡子前端詳自己的臉,不相信這張真切存在的臉可以代表我,代表一個活生生的靈魂。我發現自己沒有周云好看,這是一張扁平、粗糙的臉,一具略顯干瘦的身體,一條過分鮮艷的蹩腳裙子。”對自我軀體的陌生與疏離,是對嬰兒鏡像期無條件自我認同的“背叛”,向背之間,意味著成長帶來的自我不滿,蘊含著自我突破的驅動。喜歡“捉迷藏”(hide-and-seek)幾乎是每個孩子的天性,Hide(隱匿)的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Seek(發現),通過“他者”之眼確認“自我”存在。對自我的不滿之凝視從自我軀體向所處空間的拓展,無盡的蒼穹映照出的“我們蝸居穿行的窄小人間”,正如鏡中呈現的自身陌生的軀體。“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伏在地上看天,才知道織就我們生活的歪歪扭扭的建筑們究竟是有多么矮小。”(小說另一處,眺望中顯現出的是“我們的小小的學校”),這是從鏡像期軀體自我向開放的世界自我飛躍時的必然之途。
上述分析,并不意味著這篇小說是拉康理論的圖解;相反,我相信作者對“凝視”的把握,毋寧說來自于藝術直覺。這既證明了藝術可以直面哲學而無須自卑,也證明了小作者的天賦與才氣。我們甚至可以借由小說更深地領悟“凝視”與“成長”的關系:作為時間之流中的聚焦與靜止,凝視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動作,還可能體現為成長中一次次偶然的“走神”狀態:“六感漂游在一片浮躁之中,時間撥慢它的指針,然后突然靜止。”光怪陸離的花鳥市場,正如日常生活本身一樣,以其瑣碎阻礙了“六感”(也就阻礙了自我凝視),在此情形下,“走神”如同頓悟前夕的空明,反倒是從瑣碎中捕捉意義、從生活之流中凝視自身。伴隨著偶然的成長事件,凝視的對象還從空間轉化到生命本身。正如在經歷了“落水”事件、感受到“死亡的陰影”后,我和周云“趴在倉庫狹小的窗邊向外遠眺”,此時作者添加了看似漫不經心的一瞥:“窗欄里滿是死去蒼蠅的殘骸和蜷曲腹部的甲蟲”,這一“走神”意味著“凝視”的對象繼軀體自我、世界自我之后,豐富了死亡自我。三者的結合,才標志著精神自我的成長。
對上述精神自我成長內蘊的捕捉,意味著這篇小說僅在成長意蘊方面,已經超過了大多數無關痛癢的成長小說。從技術層面而論,小說也沒有走“講故事”的陽關大道,僅有買魚、造船、落水三個核心片段,裹挾在關于成長的情緒之流中,因而也是一篇散文化的情緒小說,但這并不意味著小說缺少構思。在遍布全篇的凝視目光下,突顯于前景的,是彼此呼應、“成物皆著我色彩”的意象。首先是作為題眼的“金魚”。它作為雙重主角懸浮于小說中心的同時也懸浮于敘事主人公十二歲記憶的中心,如小說所言,“我們實在也是宇宙這座大花園里的金魚”,對金魚的凝視同樣是自我凝視。金魚之所以是“血紅色”,是因為它“像對半剖開的瑪瑙”,它指向了關于魚化石被禁錮于時間之中的隱喻;同時,“血紅色”作為一種跳脫的顏色,也隱含著“我區別于他人”、從普遍中跳脫出來的愿望。因此,金魚既是自憐也蘊含著力求獲得自我權利的反抗。
圍繞著這一核心意象,小說還有兩個值得一提的次級意象。一是蘆花雞,“剪掉一半翅膀”的細節是神來之筆,再次呼應了“禁錮”;而當“我”觀察它時,注意到它“誠惶誠恐的眼神”,在此,凝視再次體現了互相凝視、彼此確認的鏡像特征。二是兩個孩子著意打造的航船。對航船的渴慕,緣于“無盡未知的大海”以及“往無盡去,往未知去,往死亡去”的成長沖動。“讓金魚在船上游”的創意,不只是兩個核心意象之間功利性的結合,而是植根于成長過程中的破禁潛意識,其現實結果,是牽引著情節走向一次可能的“死亡”,構成了小說的核心沖突,但并不牽強—在臆想中無盡的大海與現實中貌似尋常的池水之間,覺醒的意識與未完善的能力體現了彼此的分離與抵牾,體現了作者對成長復雜性的認知。
語言能力是衡量一個作家發展潛力的重要指征。小說篇幅不長,語言有超出年齡的冷靜與準確。例如寫在食堂擦桌子:“每張桌子上都鋪有花色不同的廉價桌布,同一種甜美的歐式花紋無限地重復下去,從桌上垂到桌下。菱形的石磚從腳下向前延伸,延伸到遠處刷成墨綠的墻根。”簡潔的描述呼應著生活的重復與禁錮。再如,寫幼童失足落入池水:“小葉子甚至來不及伸開雙手,就以一種即將伸展的姿態像雛鳥一樣歪進水中。”一個“歪”字盡得風流。“冰涼生澀的池水好像也倒灌進了我的鼻腔,乃至朦朧無序的意識。……而冗長的等待還在繼續,無盡的絕望還在拉長。黃昏時節天邊浮動著寒鴉,我多么希望我也變成其中之一,可以輕捷地掠過這漫長無望的等待。可是命運迫使我注視那一串浮動的氣泡,在池水中一定正有一場殊死掙扎。”綿長的敘述、張弛節奏的把握,準確傳達出人物幽微的內心世界,并舉重若輕地再次叩應小說主旨:“注視”在此意味深長地出現了,對“氣泡”的凝視其實就是對死亡的凝視。如作者最后指出,“或許我們的童年有太多這樣蟄伏而被遺忘的線索”。成長本身就是一個得魚忘筌的過程,氣泡的消逝,與金魚在池水中的隱匿,是這篇微型成長小說的最后一塊不可或缺的拼圖。
因此,無論是生活感悟、細節發現還是語感把握方面,十六歲的王寧婧,已經體現出作為優秀作家的天賦與潛質。我們需要等待的,是作者對自己才華的珍惜,以及在生活中淬煉、思考與成長。